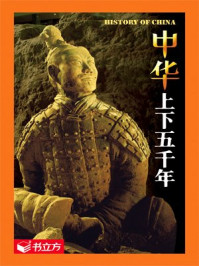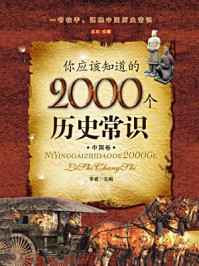福建也下了一场雪,朝廷派来的行人催叶向高北上。已过耳顺之年的叶向高说:祥瑞之雪啊,就是太冷了,开春再就道吧!
叶向高(1559—1627),字俊卿,号台山,福清(今福建福清)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
对天启朝的官场来说,叶向高的复出应该也是一种祥瑞之象。
在万历朝,叶向高一人主持内阁有七年之久,人称“独相”。这在官场,还不是最值得炫耀的资本。
叶向高最引人注目的资历资本,是曾在太子东宫任职,并始终设法维护皇长子朱常洛的利益。说叶向高是“太子党”,也不能算错。
叶向高还主持、组织过内宫的宦官“扫盲班”,让这些内宫底层的宦官初识文字。著名的大太监王体乾、魏忠贤皆出其门下,并且与叶向高友善。这一说,又把叶向高说成了“阉党”。
看惯官场的秋月春风,叶向高依旧不失士人之心。规模庞大的“东林党”,则奉叶向高为领袖。阉党的《东林点将录》,送给叶向高的头衔是“总兵都头领、天魁星及时雨”。官场若是江湖,叶向高就是江湖老大——“及时雨宋江”。
但是,无论江湖上有怎样的传说,叶向高都不承认自己与“党”有关。
这里有必要作个说明:传统社会的“党”,始终是贬义的,是“朋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以叶向高的道德情操,是看不上任何“朋党”的。
叶向高的认知,也是同僚中的“天花板”。不论处于官场上的什么位次,叶向高都有基本的底线和原则。
《大明律·吏律·奸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
历朝历代,朝廷都严禁官员结党,明朝尤甚。宋濂是明初的文胆,明太祖朱元璋的亲信。有一天,朝会结束,大家都夹着“笔记本”回去,朱元璋朝宋濂一招手:宋先生过来!宋濂回来问皇帝有什么事,朱元璋说:没事,这个周末又写了什么新作?宋濂就说:哪有时间写文章!现在的年轻人坏得很,周末跑过来一大帮,说看望我这老人,实际上就是敲诈我一顿酒!
于是,朱元璋接着问谁去了啊,吃了什么啊,第一道菜是什么,接着问第二道、第三道……宋濂一一如实作答,朱元璋听后一拍桌子:你很老实!宋濂听后,吓出一身冷汗。
那时代,禁止官员搞小圈子是一种规矩,也是一种制度,监督官员的日常举动是惯例。
叶向高怎么可能会结党呢?百官之首的叶向高,他要泰山不让土壤,江海不择细流。这是官场之福,也是朝廷之福。
事实上,叶向高主政时期又是明朝党争的一个高峰。万历皇帝近三十年不上朝,“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利益驱动,是非莫定,东林党与宣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相互之攻讦。善于统领的叶向高,一下子头都大了。
万历皇帝为什么不上朝呢?贪图享乐,崇信道教,都是可能的。但开拓“万历中兴”局面的,也就是这个皇帝。有一天,叶向高悟出了这是为什么。
万历四十年(1612),叶向高病了,内阁中又只有他这么个“独相”,各种奏章叶向高带病也得草拟,拟好后再派人送进宫里。发往内阁的诏书,也只能让人送到家,阅后再分发到六部。叶向高在家带病坚持工作了一个月。结果,言官们群起而攻之。
言官们骂得都对,叶向高确实违规了,但言官们的话没有一句是有用处的。不在家里处理公务,难道让公文在府衙堆成山?
脾气再好,也受不得委曲,叶向高愤而提出辞职。万历皇帝一再好言挽留,十分理解叶向高的苦衷。
万历皇帝也有这个苦衷,据《诏对录》中记载,他一再表示,自己腰痛脚软,足心疼痛,行立不便,但大臣中几乎没人相信。这个问题,只有当代的考古学家们相信:1958 年,万历陵墓被发掘时,专家亲眼看见了万历皇帝的右腿腿骨,比左腿腿骨短了一大截。万历皇帝的病,真不是装的。
不能为天子分忧,叶向高觉得自己太难了。当下的士大夫,好意气用事,对于皇帝与首辅的一举一动,督责太严,丝毫不相假借。朝臣对朝廷也无多少感恩之心,都认为自己的官是凭本事考来的。朝廷一有大事,很少有人酌理准情,婉言规劝,而是呼朋引类,喧呼聒噪,堂而皇之地大加鞭挞。放大君主之失,堵死回旋余地,激其老羞成怒,博取一己之名。官员们的清流之名是有了,但于国事毫无裨益。
风气,几十年的风气!
还有更加无法无天的:为了博人眼球,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在皇城里面放炮告状!
乡下妇女鸣冤敲碗打锅,锦衣百户王曰乾放上了大炮。
王曰乾是个品性很差的武人,跟孔学、赵宗舜、赵思圣等人矛盾很深。为了干倒对手,他竟进入皇城放炮上疏。这事很出格,刑官拟判其死刑。
死到临头,王曰乾没有吓傻,而是蹭“国本之争”的热点,“爆料”孔学与郑贵妃的内侍姜严山等用巫术诅咒皇太后、皇太子死,企图拥立福王。这料猛啊,一下子将当年的热点事件、热点人物全拉进来了。
王曰乾的奏疏,还真把万历皇帝吓傻了:各怀心思的廷臣,这下不吵个几年都不会熄火。尽管两条腿不方便,万历皇帝还是拖着病腿,绕着宫殿走来走去。但除了震怒,他实在想不出什么高招。
持论刻酷,遇事生风,推测过深,其所欲加之罪名,往往超出对象者应得罪名之上。官场的风气,只会因一事火上浇油,任何招数都不可能整出风清气正。这时,只有叶向高给万历皇帝出了一个主意:王曰乾所奏子虚乌有的东西,只会越查越乱。王曰乾违法的案子,交由法司依法审判。皇上关于太子、福王的安排,按照计划正常实施。不为妖风所惑,妖风也就刮不了几天。
快刀斩乱麻,牵着牛鼻子又不被人牵着鼻子,叶首辅确实太老到了。骨肉不被离间,朝政不被紊乱,万历皇帝感慨万千:“我父子兄弟的名誉能够保全了!”
客观地讲,万历皇帝是个病人,而病人是很难侍候的,叶向高萌生急流勇退的念头。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万历皇帝恩准了叶向高致仕。
居乡六年后,万历皇帝驾崩,泰昌皇帝急召叶向高回朝,叶向高婉辞了。叶向高不想再蹚官场的浑水。
天启皇帝登基,再度急召叶向高回朝。皇帝太年轻了,亟须老成的臣子辅佐,叶向高为难了。
难啊,太难了!难就难在士人之心,而不是名利。反正都是为难,那就迎难而上。
叶向高登上了北上的舟楫车马。大明官场,不能简单地一言以蔽之曰“坏”,八股熏陶出的程朱门生,不足与语通权达变,但还是要有人殉道。虽说积重难返,但有一帮人出来担当,天下还是有未来的。
天启元年(1621)十月,叶向高即将到达京城。吱吱呀呀的车轮声,叶向高想打个盹又睡不着。他想起了一个人。
他认为,这个人能整肃风纪,澄清吏制。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士人之心,行君子之道,世界是可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