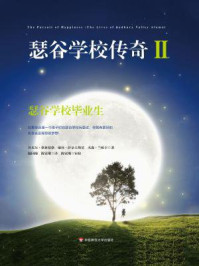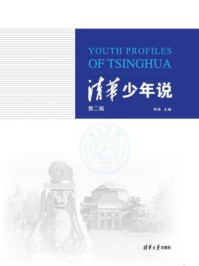江寄余来或不来,戏都是要唱的。
台上的人不能撑伞,更不能欺场。戏已开腔,八方来听,一方为人,三方为鬼,四方为神明。
即使台下无人,天上落刀,也要从头到尾唱完。有敬畏之心,才能立世存身。
头一出戏,唱《观音得道》。
小九演妙善,早已换掉舞龙灯的哪吒红裳,上了观音妆。踏着四平调,最先登场:“金殿上宣我所谓因何?奴这里一心念佛陀。”
戏衣是薄薄的绢与纱,比冰雪还白,在风里猎猎涨扬。
她很冷,手指快没了知觉。海灯澄明,火光映上粉妆面,烤得心头火热。
热闹都热闹过了,元宵夜的灯亮过,爆竹也响过。像他们的戏,有盛有衰,赶上雨就是雨,赶上雪就是雪,没办法的。
“佛在心头坐,三万八千无量佛……”
观音咿呀唱着,清亮喉嗓,穿透苍茫夜雾。心中除了佛,也夹杂些世味难言的哀矜。
谢了场,下一出是连翘和远绸的《踏伞》。
南戏四大名剧《拜月记》中的一折,讲北宋时,金兵入侵汴梁,尚书千金与家人失散,和书生在逃难途中相识,结伴而行,情定终身。
戏中是大雨滂沱,戏外风雪连天。锣鼓声催,兵荒马乱。同病相怜的乱世儿女,执一柄红伞,互诉衷肠,一时人戏难分。
风大且冷,带丝丝河水的潮气,冷进人心里去。小九抱着棉衣,匆匆跑回八角楼。
看戏箱的老师傅抱病,临时借用的后台,此刻空无一人。
铜盆里烧着木炭,她蹲在火塘前,烤一烤冻僵的手,冻得瑟瑟发抖。四周很静,楼上突然传来隐约人语。
“今晚遇到很奇怪的人……算了,没什么。”
窸窣动静过后,是一把清甜绵软的嗓,十分活泼爱娇,“无事献殷勤,彩衣娱亲呐?”
“不过班门弄斧吧,让钟年年女士见笑。”
笑声未停,徐徐响起一段清唱。
从“落花满天蔽月光”,到念白“六代繁华三日散,一杯心血字七行……”
粤曲腔调,咬字风流婉转,针落可闻的暗寂里,氤氲缭绕着,动魄已极。
是谁在唱?
小九茫茫然,拾阶而上。
木梯窄陡而长,冬色甚隆,夜更显空旷。
楼上灯影依稀摇晃,是甩袖带起的风。一长排雕花窗,拉上了暗蓝丝绒帘子,被油灯的火光镀上一层淡金。
满目灰扑扑的残败里,勾勒出一道触目剪影。
戏中人半侧着脸,身着最隆重的戏服嫁衣。乌亮大红绸,彷如铺天盖地血挂了一身,张扬着颤抖的风情。
踩着细碎脚步,转身回眸。头稍低,面庞稍偏七分,将眼睑轻抬。
戏文正渡到那句:“有缘生死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那么低幽,仿佛贴近耳边。
舌乃心之苗。
她怔忡站在那里,一动不能动。头发里融化的雪水,啪嗒落在地上。
穿火红戏衣的伶人,身段颀长袅娜,动态极利落,妆容却十分随意。没贴片子也没戴头面,只用勒头黑巾束发,翠眉斜飞,秀长凤目吊起。面颊上拍彩、揉红,都涂抹得有些潦草,但很美。
“所谓劫火余生,恍如隔世,花月总留痕……”
余音在斗室回荡,是意犹未尽的玉珠滴答弹响。
彼此在火光明灭中对望。
突然的惊艳令人失语。小九喃喃说:“阿姐,你唱得真好。”
对面轻笑,“小妹妹,你认错人了。”
分明是男人的声音。
她大窘,这才注意到他的手,探出宽大的袖口,还挽着垂露式。
匀净如竹,白皙修长……曾挑起乌篷帘,在青瓷杯沿轻叩。惊鸿一瞥,印象尤其深刻。
是他?
依然不敢确定。
雨夜狼狈的年轻人,脸上蒙着黑纱,不能视物。可眼前的男子,双眼明明完好无缺。
“你……”
他转身之际,把架在妆台前的手机关掉,视屏通话戛止。小九没发现屏幕彼端,还有双眼睛在注视这意外相逢。
“我是傅山海。”男子走近几步,投下高大阴影,把她整个笼罩住,说:“我们见过面。”
真的是他。近在眼前,她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心口异样地轻,完全一片空白。
“你还没告诉过我,你的名字?”明知故问,是不想吓到她。
这次她不再犹豫,“叶观音。”
当然他记得她扮的观音,白衣莲冠,清澈无邪,疏离于满台风月情浓。
“罗少廷的第九个徒弟?”
她点头,“他们叫我小九。”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难道来秋后算账的?
小九有点慌,语无伦次地解释,“那天闹误会的是我二师哥,他是个好人……”
“你别紧张。”傅山海温和地笑,“我喜欢听戏,听说萃乐堂有元宵夜场,票友可以同台演出,很想试试。后台找不见人,一时技痒——”他抖落搭在臂弯的水袖,“还请叶小姐原谅我的不问自取。”
凤凰岭雨夜冲突,半字未提,仿佛从未发生。
“没、没关系的。”她松口气,小心望着他:“你的眼睛……”
“已经不用敷药纱了。”
原来他不是盲人。
“上次走得太匆忙,没能好好道谢。今晚终于有机会看清楚,我的恩人长什么模样。”他微躬身作揖,把戏腔拖长:“小生这厢,谢过观音菩萨。”
亮嗓清亮而缠绵,表情十足诚恳,丝毫不显做作。
小九霎时脸红,本能地用念白回应:“公子不必多礼。”
心口突然划开一道口子,有什么陌生的东西不着痕迹,又满当当地灌进去了。一颗心没处放,反而飘在风里,全不着边际。
雪珠温柔绵密,沙沙打在木窗上。妆镜蒙尘,映出煤油灯跳跃的火苗。
寂静更让人发慌,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绕回戏上:“傅先生刚才唱的,是帝女花?”
天下戏曲同出一源,凡经典故事,在不同的剧种里都有,很容易分辨。
“对,粤剧折子戏‘香夭’。崇祯帝的末代公主殉国,和驸马在洞房夜共饮毒酒那段。”
彩凤还巢日,当以颈血溅宫曹——难怪拣了件凄艳嫁裳,他扮的是亡国帝女长平。
“我有个师兄学乾旦,班里也排过这戏,只是唱词不太一样。粤剧用方言,跟我们的戏不同,发音很难,大多是会说不会唱。”小九赞叹,“你唱得真好听。”
“小时候跟家里人学过点皮毛,也就只会这几句。”他笑着低下头来,“我教你?我们把香夭唱完。”
说着拉起水袖做绣球,两人分持一端。已是拜过天地后,双双步出月华宫外,来到含樟连理树下。
没有宫娥仪仗,如此断肠花烛夜,明珠万颗映花黄。公主对景不胜感慨,重起旧调:“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偷偷看,偷偷望……”
他脉脉望向她,是公主带泪含悲望爱郎,湿润的眼眸含着海,明澈光亮。
几真几假?颠倒了水月镜花。
小九扮那忠贞驸马周世显,甘愿为妻含笑饮砒霜:“将柳荫当做芙蓉帐……递过金杯慢咽轻尝,将砒霜带泪放落葡萄上。”
乱世鸳侣,情凤痴凰,寸心只盼能同合葬。他屈指微拢作酒杯,“合欢与君醉梦乡。”
小九也学他,将手指并拢弓起,“碰杯共到夜台上。”
爱是含笑饮毒酒。
相触的瞬间,仿佛被烫,下面的词全忘光。
“百花冠替代殓妆……”
不着情之一字,声声调调总关情。公主“举杯”饮尽,最后一幕是和驸马相拥而亡。
他没有冒失地去抱她,只在女孩冰冷的手背轻握,隔着薄薄水袖,点到即止。
她最先记认的,不是他的容貌,声音,眼睛和头发的颜色,是他的掌纹。
戏只是戏,应该不算唐突吧。
可她睁大了水雾迷蒙的眼,望向他的,眨一下,再眨一下。
咦?两瓣浓黑桃叶底下,含着异色的瞳。分明东方面孔,左目浓黑,右目却有一汪深含碧色的眸,闪亮如狐。
镜子里人影叠双,定住,姿势何等缱绻。
时间几乎停滞,彼此都觉得那一刻很漫长,似听见胸腔成千上万只鸽子同时振动翅膀。
戏唱完了,他需要好好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做。直接摊牌吗?
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只顾盯着他的眼睛好奇。
刹那怜惜,他有点恍惚,“怎么?”
小九半晌回神,嗫嚅道:“这妆不对,不是这样画的。”
“唔,那以后你帮我改。”
以后?她来不及想太多,“今晚天气不好,观众也少,没人愿意同台扮戏……师父一定很高兴。”
他脱下戏衣,端坐镜台前,脂粉油彩一把把擦掉,露出洁净脸容。
至此,她终于看清他长什么模样。森林迷雾拨散开,逆光描出深邃的轮廓,是墨云衬托皎月。
静暗雪夜,浮动着忍冬清凉黯淡的气味。
“人人都说,向观音许愿会灵验。”他抬起脸,漂亮的薄唇微仰,“小观音,带我去见罗少廷。”
夜已深,最后的观众也走光。戏还未停,按规矩要演到天亮。
台上胡琴拉得悠扬,正唱杜十娘的徵调《雪花飘》。
群山环绕间,回荡连翘缠绵的拖腔:“雪花飘北风起,飘来飘去三丈三尺高。黄昏时候,公子他不见归,我的心担忧……”
雪下得太大,冰珠刮在脸上生疼。
傅山海单手撑开一把伞,沉声说:“来。”
小九裹紧棉衣,轻手轻脚走进一隅为她空出的天地。
他抬起手臂,绕过她的肩,虚虚拢在身侧,半掩入怀。
姿势妥帖迁就,始终保持着谨慎的分寸,没碰到她分毫。小九偷偷抬眼望,发现他整条胳膊和半边肩膀,都暴露的雨雪里,已经全部淋湿。
雪水顺着指缝滑落,那手在夜色和黑伞的衬托下愈发莹白。
呵气的薄雾交融,她听见伞面上嘈杂的敲打声,心里莫名安定,不动声色地往他的方向靠了靠。
“我不冷。”他还是察觉了,唇角轻抿,伞又朝她倾斜几分。
青砖湿滑,不到两百米的一段路,走得很慢很仔细。
前方戏台被灯火照耀得亮堂,四周挂满绢花红彩,远远就能看到。
小九踮起脚,寻找罗师父的身影,怎么也望不见。
紧锣密鼓敲得急,小伍在表演摔叉。赌气似的,一口气翻腾七八个还未停。再来,再来,不肯罢休。
身板挺直摔在硬木板上,砰砰作响,比掌声还铿锵,斗志昂扬。
变故发生太快,谁也没反应过来。
横架在谷桶上的木板不够结实,或许是年久松朽,被雨雪一浸,突然断裂开。
台坍了,从中凹陷,盛满灯油的大缸翻倒,火油如毒蛇咝咝吐信,四处游走。台上台下顿成一片火海。
风助火势,雨雪浇不熄。
绸花纸灯都是助燃之物,戏台成了火海里覆没的扁舟。
一幅泛黄的古画,飞快地被火舌吞噬,爱恨情仇的幻梦,转眼都化作浓烟。
小九张着嘴僵在原地,想叫喊却发不出声音。
棚顶轰然垮塌,漫天的红绸覆盖下来,被烈火的藤蔓缠住,红到极处便成灰。
戏台底下是中空的,用谷桶架起,人掉下去就看不见。
火舌不怀好意地蜿蜒,逼近脚边,呛鼻的焦糊味惊醒了她。
小九跌跌撞撞往戏台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还能做什么。
一根木柱倒下,发出瘆人的爆裂声。
“别过去!”
傅山海扔了伞追上前,把她用力摁在怀里,往边上一滚,堪堪躲过。
谷桶受热炸开,尖锐的木屑四下飞崩。
灼热的空气扭曲,万物支离破碎。黑暗那么近,她摔得很重但不觉痛,被兜头的巨浪拍晕。
再清醒,天还没亮。
夜那么长,总也过不完似的。
元宵戏台大火,像一场惨痛怪诞的噩梦。她在医院睁开眼,急泪汹涌,四周人影乱晃,可是没有那个会唱帝女花的年轻人。
柳与徽心急如焚地穿过酒店长廊,裤脚裹满泥泞,留下一长串歪斜足印。
门口守着的保镖认识他,识趣让开。
医生刚告辞,他忙伸手挡住门,侧身钻入套房。
咔哒落锁,所有声光关在门外。
“是意外,还在抢救。”傅山海坐在窗边讲电话,袖子高挽起,手臂的擦伤已经上过药,用纱布扎好。
“先等人脱离危险,再想办法跟他谈。我还好,让妈不要担心——”抬头看了柳与徽一眼,嗓音淡淡,“先挂了。”
扔下手机,他松开领口,单手摘掉眼镜,有些疲倦地揉捏鼻梁。
窗帘拉得密不透风,室内很暗。
“医生怎么说?”
柳与徽拿起金丝眼镜,满脸担忧。右侧方形镜片,又蒙上整块黑纱,散发寒凋凋的药味。
“别一惊一乍。烟熏得有点疼,已经好多了。”傅山海坐起身,重新把眼镜戴好。
地灯照过来几缕脆弱的光,勾勒出分明棱角,像斯文海盗。
“怪我咯?皇帝不急太监急。”
“谁急?”他托一托镜框,装作无辜地托着腮,唇角促狭挑起,“多说点,这话我爱听。”
柳与徽噎住,更没好气,“身娇肉贵自己不晓得当心,真出点事,就算傅叔不怪罪,我妹也得扒我一层皮。”
提到柳绰云,傅山海表情有点不耐烦,直接换话题,“罗少廷这边,一时半会很难进展。江寄余有消息吗?”
“你上次让我查这个人的底……”
柳与徽欲言又止,脸色罕见地凝重。太多前尘旧怨,该从何说起。
“有什么问题?”
“傅叔和江伯伯那些事,我了解不多……”话音稍顿,“他是江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