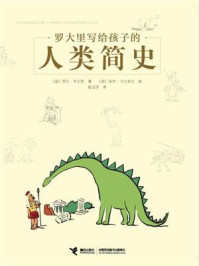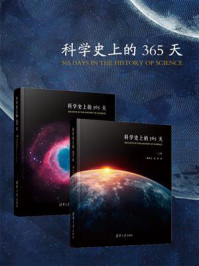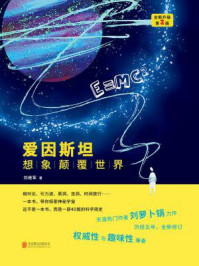20世纪初以来,建立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基础上的现代物理学的飞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与思维方式。在一代代物理学巨匠的精心哺育下,现代物理学已经成长为看似坚不可摧的巨兽,导致新的违背现有理论的自然现象没能如期带来库恩式的科学革命,反倒是进一步把旧的物理学框架推至大伪阶段。物理学的混乱进一步波及哲学与宗教,使得人类的思想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与迷茫。哲学的衰落伴随着宗教的式微和物理学的混乱,科技发展带给人们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依然生活在混乱、迷茫与纷争的新世界。在这一时代的大背景下,对哲学与物理学的交叉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我们走出思想困境的希望所在。
哲学是在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哲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索世界的本原和人生的意义。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系统工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科学是哲学的一部分。与哲学试图探寻物质世界的本原不同,科学是以不完美但最实用的方法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类社会的第一生产力。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乃至人文科学的基础。近现代物理学家在揭示自然规律方面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与现实成就。尽管现代物理学在理论与应用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在基础的物理学理论方面依然是矛盾重重,这些矛盾的困难程度在物理学的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希格斯粒子在2013年被探测到,量子力学仅剩下所预言的质量为0自旋为2的引力子幽灵般地游离在物理学大厦之外。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的不相容集中地体现在对真空零点能的计算上,二者计算结果的差异竟然高达几十到一百多个数量级,这里显然是量子物理学家犯了世界观的错误。如果说19世纪末物理学的天空飘浮着两朵乌云,那么20世纪末期发现的暗物质与暗能量已致使物理学的天空乌云密布。现代物理学发展的困境主要在于物理学家对于超经验的自然现象似乎无从下手,历史传承下来的物理学研究范式对于宇宙学研究是无能为力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传统的基于自然表象和局域经验的物理学研究范式尽管硕果累累但已经积重难返,物理学须要重回麦克斯韦开创的对物理机制的研究中来。
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成果与矛盾为自然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薛定谔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物理学研究的困境根源于近代物理学建立在古希腊人预先形成的观念和无根据的假设基础之上”,并试图从古希腊哲学的思想源头上寻找突破口。那么,古希腊人的“预先形成的观念和无根据的假设”又会是什么呢?静态无限大的三维空间只是人类坐井观天的本能错觉,无论狭义相对论还是广义相对论抑或量子场论都没能从根本上摆脱三维空间的桎梏,建立在这一错觉基础上的近现代物理学大厦如果不岌岌可危才是令人惊讶的。如今,纤维丛在场论研究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意味着宇宙空间更可能是由无数的局域三维空间(流形)构成的纤维丛空间。
面对物理学研究的重重困境,空间物质化(即物质与空间的统一)已经成为当代理论物理学发展的大势。历史上,一些物理学家对空间问题也做过初步的思考与探索,但由于哲学思想的缺陷和数学工具的缺失,这些探索也只能浅尝辄止。汤川秀树在《四维广延性的本体》一文中,论述到“尽管电子是被假设为限制在一个点上的,狄拉克却在运动的相对论处理的基础上完全不依赖于轨道运动而成功地导出电子本身所固有的自旋;他在这样做时能够说明半整数自旋。我们可以作为给粒子指定一个广延性的推理来导出这一同样的结果。我们知道了,如果一个刚体是由一种连续物质构成的,则自旋能够取整数值也能够取半整数值,而如果主张刚体是由一组点粒子构成的,那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除非对点粒子集合体的几何位形加上一定的约束;知道了这些,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因此,看来从一开始就从连续体出发而不从点粒子系出发来进行工作似乎是合理的”。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在研究统一场论的后期也认识到空间的物质属性,并认为“引力场可叫做空间”。然而,爱因斯坦与汤川秀树都没能找到描述空间物质化的几何模型,对无限大的引力场空间物质化则意味着无限大的引力场能量,直至现在,主流物理学界尚不知道如何定义引力场的局域能量。
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在揭示物质世界的规律方面,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这些工作带来的成果与矛盾为辩证思维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中国古代对立统一的哲学在解决矛盾问题时有着先天的优势,如何将这种优势转变为物理学研究中的可操作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需要根植于近现代物理学的成果与矛盾并对其进行系统地梳理与整合,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工程但必须有人尝试去做,即使这种尝试会大概率以失败的方式而告终。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熏陶下,精通西方科学的汤川秀树曾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寄予厚望。与杨振宁对易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近乎全盘的否定不同,汤川秀树在《创造力与直觉》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我们考虑到将来时,肯定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希腊思想应该仍然是科学思想发展的唯一源泉……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没有产生纯科学,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将来还会这样”。
在长期沉思于道家思想物理学化的过程中,笔者于2014年6月在公园停车休息时,看到淅淅沥沥的雨水一幕幕地坠落,顷刻间脑中浮现空间在整体坠落的画面,进而萌发了用引力场空间的超循环研究引力的思想。阴阳对立统一的太极图自然成了理想的物质复空间的几何模型。在此后的四年里,笔者一直在权衡和修正由此带来的诸多矛盾,其中,厘清引力场流速与引力场加速度的关系占据了笔者绝大部分的思考时间。之所以选择研究引力,在可行性上笔者有着两方面的考量:
1.引力作用的物理机制尚不明确,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几何化只是引力作用的某些表现形式,缺失了客观的物质载体;
2.引力作用的过程虽然复杂但其基本原理与机制应该是大道至简的(真理是朴素的),对其原理与机制的初步研究应该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
本书汇总了“物质复空间理论”和“暗物质效应的多重机制研究”以及近年来笔者的一些新思考,着重于从自然哲学的高度探索近现代物理学的哲学基础与逻辑框架。在近十七年持续的探索与反思的过程中,笔者因物理学专业知识的浅薄而走了很多弯路,也只能对大道至简的基本原理进行力所能及的探索与研究。物质复空间理论继承和拓展了源于易经的道家思想,试图为道家思想朴素的复合场论找到物理学上的可操作性。在此两篇论文中,笔者以易经的对立统一法则为基础,在道家思想的启示下系统地论证和推演了物质复空间的几何结构与物理属性,给太极图赋予了现代物理学的内涵,论证了引力作用的机制与暗物质效应的多重机制,明确了负能态的引力场空间在场论研究中的本体地位。
那么,我们如何证明高维空间的存在呢?尽管我们不能直接给出证实,但可以通过间接的物理实验和综合的逻辑判断进行间接的论证。首先,我们可通过物理实验测量不同引力场环境下的真空磁导率,如果其是可变的,则空间确实具有物质属性。此外,量子物理学家对真空不空的发现也证实了空间具有物质属性;然后,由空间的物质性和等效原理以及力学的相对论,可进一步推理出引力场等效于负能态空间的外向流动;由此可反证存在高维空间,否则,引力场空间的流动就是无源的,这显然不符合我们关于自然的一般常识。
物质复空间理论构建了“引力场空间化和空间物质化”的逻辑规则与几何模型,其与广义相对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基于反对称的太极几何(物质复空间)构建的引力理论,空间被解释为引力场超循环的叠加态,引力被归结为物质负能态的引力场空间的交换;后者是基于平坦静态的四维时空构建的引力理论,引力被归结为质量弯曲时空的几何效应。物质复空间理论系统地解决了以下问题:
1.在易经和太极思想的启示下,统一了物质与空间并构建了反对称的动态复合场论,解决了引力作用的物理机制;
2.不加假设地解决了暗物质与暗能量问题,将二者归结为引力场空间超循环的场效应;
3.提出并证明了“相对论的绝对性原理”,厘清了狭义相对论的历史遗留问题;
4.在空间不空、等效原理和力学的相对论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广义等效原理”,解决了广义相对论的历史遗留问题;
5.引力场空间的正电子态属性支持了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位移电流假说,并解决了由狄拉克的真空电子海所引发的空间须要带有正电的窘境;
6.构建了引电统一的基本公式;
7.论证了光速是广域绝对可变与局域相对不变的统一;
8.基于动态复合场论证明了哈勃定律,从而否定了宇宙大爆炸理论;
9.负能态引力场空间的发散(膨胀)是引力作用的基本方式。
人类的一切知识来源于直觉经验。我们须要根据哲学、数学和物理学获得的知识与矛盾去审视和质疑我们的直觉经验,进而形成“综合的逻辑判断”。综合的逻辑判断是物理学深入发展和走向终极统一的必由之路,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也将历经从直觉现实到抽象现实的重大转变。当代物理学被主流学界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所禁锢,教条与反教条的斗争是长期和曲折的,广大民众科学素养与辩证思维的提高有助于破除科学的教条主义,促进科学的良性发展。
薛定谔曾认为“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对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知识的强烈渴望……要想把所有已知的知识综合为一个统一体,除非我们中间有些人敢于去着手综合这些实事和理论,即使它们有的是第二手的和不完备的知识,而且还要敢于承担使我们成为愚人的风险,除此之外,我看不到再有摆脱这种困境的其他办法了”。考虑到思想的碰撞可以启迪灵感与智慧,错误的思想并不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更值得人们去审视。门捷列夫说“一个人要发现卓有成效的真理,需要千百万个人在失败的探索和悲惨的错误中毁掉自己的生命”。本书作为对近现代物理学成果与矛盾的整合与拓展,笔者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初步的探索与研究,其中的错误与不足肯定存在,也很可能会沦为“失败的探索”但不会是“悲惨的错误”。希望本书开放式的系统性批判思维能够抛砖引玉以推动对人类认识论的深入研究与发展,或许这才是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谨以此书献给开拓易经与道家思想的先贤,献给两千多年来为物理学大厦添砖加瓦的物理学家与数学家,献给无数在探索宇宙真理的道路上遭遇挫败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