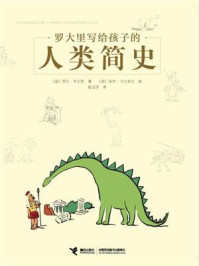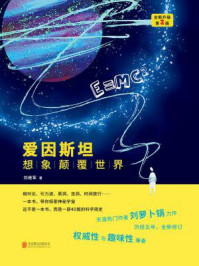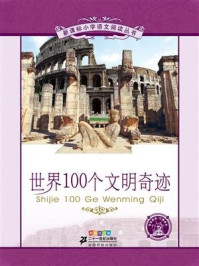哲学是在人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构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就过去几千年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而言,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人类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诉求,哲学愿景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决定了科学与哲学分离后才能轻装上阵并在自然科学的细分领域优先深入发展。
科学摆脱了哲学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诉求,通过对人类活动的局域经验的研究与应用,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并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另一方面,人类在自然科学细分领域的探索与发现,尤其是天文学和量子力学的研究成果与矛盾,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现代的主流科学家轻视哲学思辨主要是因为哲学尚不能为科学提供有效的逻辑基础与框架,所谓哲学对科学的指导即便不是一厢情愿的也是零散与粗放的。那么,科学可以彻底与哲学切割而独自良性发展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把科学比作树木,那么哲学便是森林。
哲学与科学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片面的世界观。毫无疑问,一切的科学与哲学都建立在人们片面的世界观基础之上。建立在局域经验基础上的近现代物理学尽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模拟和预测自然,但其公理化的逻辑体系并没能建立起来,除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两大基本的物理学理论之间也存在难以调和的尖锐矛盾,而前沿的理论物理研究仍旧被各种浅层次的突发奇想和深度的数学推演所充斥。为此,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地探索和拓展人类认识论的边界,通过严苛的批判与自我批判推动科学与哲学的相互促进与发展,避免长期陷入僵化的科学主义与哲学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与哲学的二元对立。就人类现实的认知而言,科学对物质世界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而哲学对科学的概括与总结仍然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历史性倒退。空间是哲学与物理学研究的共同出发点,但对空间问题的深度思考与追问很容易令人陷入思维的黑洞。于是,过去的哲学家通常只能拘泥于直觉无限大的三维空间进行浅层的思辨,过去的物理学家也没能探索空间的结构与属性,而是在由局域经验抽象出的各种数学空间中游走并莫衷一是,以至于哲学与物理学都没能摆脱坐井观天的宿命。空间、引力场和以太,作为三位一体的重叠性存在,何本何化是值得人们深度思考的重大问题。
哲学的未来取决于哲学家的基本素养和大系统思维的驾驭能力。科学家不了解哲学,通常只是减缓了科学研究的进程和基础理论的滞后;哲学家不了解科学,则会在自然哲学上裹足不前甚至沦落为科学的附庸,从而导致科学主义与科学独裁。科学是哲学的基础,而哲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自然辩证法对纷繁复杂的科学理论去伪存真。科学与哲学的分流与汇合都具有历史必然性,交叉学科研究是实现二者汇合的必要途径。自然哲学研究须要通过综合的逻辑判断对科学的局域经验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整合,不断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从而促使人们从直觉现实走向抽象现实。这将是一个漫长、曲折和反复的过程,但需要有人去做,否则不会有任何摆脱困境的希望。
“认知的举步不前,根本上是因为哲学的失败,我们没有建立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世界观”。过去的自然哲学主要是概括、总结和批判自然科学,新的自然哲学要通过改造自身的方式改造自然科学。
我相信,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文明中吸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
伯特兰·罗素
一群专家在一个狭窄的领域所取得的孤立的知识,其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当它与其余所有知识综合起来,并且在这种综合中真正有助于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时,它才具有价值。
埃尔文·薛定谔
我们身处的时点,正是一个四百年的老东西在病榻上垂死挣扎,而一个新生命奋力脱壳而出。这种文化、科学、社会组织上的变迁,其幅度之大与速度之快,均为前所未见。等在前方的“机会”,是个人、自由、社群与道德的再生,是与自然、彼此以及神圣智慧的和谐共处,一些大家不曾体会但一直梦想的境界。
狄伊·哈克
《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心灵,包容着几千年来中国伟大智者们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至今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
卡尔·荣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