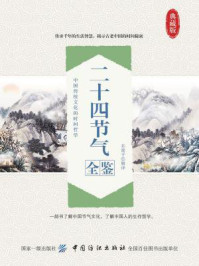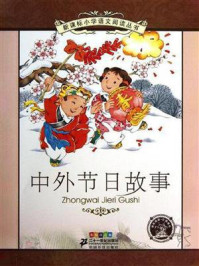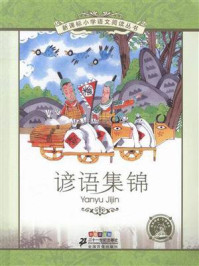陈志良在广西期间,记录下了诸多颇具本地独特性的文化现象,其中“扬州”信仰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项。这里“扬州”不是具体的地理位置,而是“阴间”的代名词。
按照广西民间信仰,人死后的归宿有几种说法。一种是“飞升入太阳”。铜鼓的中心即太阳,环绕其外的是护送魂魄的白鹭,再外围则是接引灵魂的巫师羽人。另一种是“飞升入天上花园”。这一说法源自花婆神信仰,该信仰认为花婆神掌管人世轮回,花园的花开后,她会送花到人间,白花变为男,红花变为女。人死后灵魂回归花园,等待下一次盛开和送入人间。此外,还有一种奇特的说法,即所谓“魂归扬州”。
陈志良在1940年所撰的《漫俗札记》一文中“扬州”词条中记录:“扬州是江苏省长江北的县名,禹九州的扬州地望,也在东方。在盘傜系傜人的歌谣里,常有提起扬州的名词。榴江的板傜,以为人死后,魂到扬州,有条河不能渡过,烧了纸钱,死人才花钱过河,管理鬼是阎罗王,傜语为ni lu hong(音为尼罗河,记得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里主张‘阎罗王’与‘尼罗河’有关,后为别人驳倒。然傜语与‘阎罗王’‘尼罗河’音既相近,单词孤证,不敢肯定其相互间的傜系也值得注意)。照我目前在风俗方面的感觉,傜人与长江下流的风俗,有许多是相同的,扬州这名词是东方的,傜人从东方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瑶族分支众多,陈志良这里所谓“阎罗王”在瑶语中发音为“ni lu hong”,恐怕只能是某瑶族支系恰好如此,“阎罗王”与“尼罗河”之间就算发音相同也缺少内在关联性。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他觉得有趣的这些片面的例子实在不能作为严谨的学术例证。这里比较可惜的是,陈志良已经敏锐注意到瑶人歌谣里常提起“扬州”一词,但他没有进一步详细搜集这些歌谣。或者有可能他已经收集了,但毁于日军敌机对桂林的轰炸。

笔者比对他所编的《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里面只有两首涉及“扬州”的板瑶歌谣。迁江盘瑶的《叹情歌》里唱了人生十二种忧愁,其中就有涉及“扬州”:“七愁怕有寒风病,八愁手着价钱求;九愁为人无几久,十愁不久到扬州。”修仁板瑶的《苦情歌》里有一段提到:“夜里迷床浮沙泪,五魂六影到扬州;流落世间逃秋难,淘沙含泪化街游。且游修世扬州过,阴王十殿诉因由;几多结配成林杵,亏苗世上手荒秋。”
这里显然,“扬州”就是“阴曹地府”的代名词。陈志良没有考证“魂归扬州”的民间信仰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可能是因为相关问题的确难以问出个所以然,至今学界同仁也没能确定这一奇特信仰的源头。笔者倒是推测此信仰或许源于外省传来的诗歌和信仰的杂糅。古代诗歌中关于“扬州”的意象颇多,比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人生只合扬州死”之类,地处偏远的广西少数民族对“扬州”带着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想象,再结合汉族民间信仰中关于阴曹地府的描述而以讹传讹,最后演变为这一奇特信仰。

陈志良提到这一信仰的发生范围为榴江区域,但实际上这一信仰的范围比他想象的还要大,涵盖了今天柳州到百色这一大片区域(榴江县位于广西雒容县东,洛清江入柳江处。1951年与雒容县、中渡县三县及修仁县第二区合并成鹿寨县至今)。21世纪以来,当代学者海力波在广西那坡县“黑衣壮”聚居区进行了调研,他撰写的调研报告里也涉及“扬州”这一“死后世界”的意象。据他访问的当地人口述:“这个世界上有天,天堂,中间是人间地上,地下面有‘扬州大地’,上下我们看不见的,只看得见中间地上。人死了魂不上天,还是在人间,地上。天上是天堂,看不见,道公才晓得,天上是玉清、上清、太清三个最大了,他们下面还有丞相,兵马,天上主要是他们三个了。‘扬州大地好风流,千年万载不回头。’扬州大地是个好地方,祖宗死了,就送去,和我们人间隔山隔海隔水,再也回不来了,扬州大地在哪里?就在埋祖宗的地方,坟下面就是扬州大地,死了埋在哪里,哪里地下就是扬州大地。扬州大地也可以说就在地上,和我们人间是一团团的,但是要分开,就叫扬州大地。”“人死后肉都烂了,肉不要紧的,死了就烂了,肉不重要,所以死过后三年要道公‘安龙’,把骨拣出来,用木炭熏得干干黄黄的才好,封在坛子里封得好好的,由我们道公送到‘扬州大地’。……人死了魂就飞回家里面的神台,不过要三年脱孝后才回,没有脱孝以前魂就在家外面,在寨子外面由‘社令’‘社弄’管,回到神台后就自由了,由自己的祖宗管(‘社令’‘社弄’是‘黑衣壮’人的民间信仰中,掌管寨子周围的田地和更为僻远的荒野的地位低下的小神)。”
 作为“死后世界”的“扬州大地”存在于地底某处,与人间有河流相隔。因此在“黑衣壮”的丧葬法事中,道公要杀一只黑鸭子送给死者,在黑鸭子的托载下,死者的灵魂得以渡过宽阔的河流到达“扬州大地”。海力波进而认为,“黑衣壮”干栏建筑的“呢嘎”“迭真”“登栏”三个层次恰恰与他们宇宙观中的“天”“地”“水”这“三界”形成对应关系。
作为“死后世界”的“扬州大地”存在于地底某处,与人间有河流相隔。因此在“黑衣壮”的丧葬法事中,道公要杀一只黑鸭子送给死者,在黑鸭子的托载下,死者的灵魂得以渡过宽阔的河流到达“扬州大地”。海力波进而认为,“黑衣壮”干栏建筑的“呢嘎”“迭真”“登栏”三个层次恰恰与他们宇宙观中的“天”“地”“水”这“三界”形成对应关系。
依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获得一条线索,即无论是瑶族还是壮族、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扬州”这一“死后世界”的意象都是由道公主持的仪式性活动传承下来的,与道公信仰密切相关。而且海力波在21世纪采集到的“黑衣壮”民俗信息与陈志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采集到的瑶族民俗信息显然具有同构性,逝者到达“扬州”都必须经过河流,这或许暗示此信仰的形成就如王旭推测的那样,与唐代以来的河运文化有关。
陈志良搜集到的迁江盘瑶《叹情歌》中的“十愁不久到扬州”一句,在吟唱者这里“扬州”已经被作为相当口语化的词汇来运用,这意味着将“扬州”作为“死后世界”的民间信仰在陈志良的时代已经是发展成熟期了,这一奇特信仰发源的时间无疑比陈志良的时代更早。虽然现在资料有限,难以追溯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扬州”民间信仰究竟始于何时,但这一信仰的独特性还是颇具文化价值的。
作为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者,陈志良的研究还是略显粗糙,他所开展的具体调研还有经验主义的内在缺陷,所研究的内容不是依据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而是根据他自己的视线。他观察到什么内容或者采集到什么素材,就按照自己的观察和采集线索撰文。对于他所未能详细目睹或采集到的空白,以及那些他所不了解的内容,都没有进一步补充挖掘,也没能在现代民俗学和艺术人类学框架下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学科化的归纳总结,这才会导致他记录下诸如“一条一丈余而特制的稀奇古怪的鬼神画像”这类模糊不清的描述,“鬼神画像”究竟包括哪些谱系的神灵鬼怪也语焉不详,这种记录属于口语性质的日常用语而非具有科学性、明晰性和体系性的学科语言。
同样是记录“亡魂”内容,陈志良只统称为“鬼”,没有从更详细的细节上观察和记录。而作为对比,当代学者则会细化到这些“鬼”的不同分类。比如海力波在调研那坡县“黑衣壮”时,就注意到同样是“游魂”,当代人会将“夭折而死的”称为“毗摆”,将“因意外或暴力事件而非正常死亡的”称为“毗松”,而且这两种游魂都没有接近寨子的资格,只能永远在荒野中游荡,听凭“社弄”和“社令”的摆布。
 文明向现代的进化,必然伴随着诸多传统文化的退化。马在古人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关于马的称呼就非常详细。如膝以上全白的马称为馵;膝下四胫全白的马称为驓;四蹄全白的马称为首;前足全白的马称为騱;后足全白的马称为翑;右前足白的马称为启;左前足白的马称为踦;右后足白的马称为骧等。
文明向现代的进化,必然伴随着诸多传统文化的退化。马在古人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关于马的称呼就非常详细。如膝以上全白的马称为馵;膝下四胫全白的马称为驓;四蹄全白的马称为首;前足全白的马称为騱;后足全白的马称为翑;右前足白的马称为启;左前足白的马称为踦;右后足白的马称为骧等。

但现代人对马的称呼只有简单的白马、黑马、斑马之类。“鬼”也是一样,对现代人而言,鬼就只有“鬼”一种称呼。但在生产力不发达而巫术繁盛的时代,对“鬼”的称呼是相当细化的。身处现代文明的陈志良对此存在“文化盲点”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