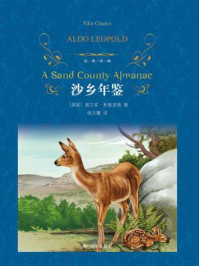根本来不及坐下。
主殿猛地一把夺过书桌上的书本,呵斥道:“哼,你这家伙,读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呀!”说着,就朝着拉门扔了过去。
“弟弟呀,抬起头来,看着我!”主殿情绪激动,在他眼中,市十郎的沉默显得格外冷漠,这越发激起了主殿内心那汹涌澎湃的情绪。
“我受忠右卫门所托过来看看,结果得知了这般令人惊愕的详情。真是岂有此理,我都没脸去见忠右卫门夫妇,也没脸去见阿缝小姐了呀。”他一边重重地踏着榻榻米,一边把膝盖往前挪了挪,说道:“咱们家从家祖忠教、忠政大人那时候起,就从来没出过像你这样无耻、没骨气、没出息的人呀。我真不甘心,怎么像你这样走歪门邪道的人,会是大冈家的血脉呢。不过,就算你再怎么荒唐,也不至于还痴迷于水茶屋那个卖水女的风情,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了吧。”
他沉声说道:“听好了,在这一点上,我就算拼上这条命也要跟你说清楚。我刚刚在忠右卫门大人的屋里,也是这么跟他们三位说的。你体谅一下我吧,弟弟。我身为兄长,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立场呀,就算咱们已逝的父亲还在世,我也得这么说呀。”
市十郎低着头,默默地流着泪,双手紧紧地放在膝盖上,就任眼泪这么流淌着。
“喂,弟弟呀,但愿这不是真的,但愿你的心思也不是这样的呀。这两三年来,你闭门思过之后那谨慎的态度和勤奋学习的样子,我这个做兄长的,心里其实也暗暗高兴呢。我也不多说了,三年前那次偶然的过错,我也不再追究了。只是,你给我写一封信,交给我保管吧。就是写给那个叫袖什么的女人的,写明和她就此断绝关系的信。”
“啊?兄长……”
“哼!”主殿打断道,“你以为我是要做残忍的事吗?你放心交给我来处理吧,哪怕是卖掉祖传的家宝,我也要拿出和她断绝关系的钱,把孩子的事也一并解决。”
“那、那这个,兄长……”
“怎么了,你还留恋不舍吗?”
“倒不是留恋不舍。只是那女人,她不会答应的呀。”
“蠢货!”主殿大喝道,“所以才让你写呀!写一封断绝关系的信,我拿着信去跟她说清楚。要是她还不知好歹,纠缠不休的话,那我还有最后的手段。”
“最后的手段?您是说……”
“那可是关乎你一生的事呀。要是再重蹈前年叔父五郎左卫门的覆辙,又传出什么不好的风声让官府听到,那可就关系到大冈十家的安危了。别心疼一个女人的命。”
“啊,您是说要杀了她?”
“大惊小怪什么,难道你还留恋不舍?”
“不,兄长,那她太可怜了呀。这罪过原本全在我市十郎身上。”
“够了,你根本不懂女人。水茶屋的女人,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可是阿袖她……和这世上普通的女人不一样呀。”
“哪里不一样了?”
“她的性情……”
市十郎刚要开口解释,主殿突然伸手,一把揪住他的领口,呵斥道:“哼,你这家伙,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吗?”说着,使出全身力气推了他一下。
亲人之间出于爱意的愤怒,比起对陌生人的仇恨所产生的怒火,还多了一份强烈的本能。
市十郎的脸变得铁青,像死人的脑袋一样,不停地颤抖着。紧闭的双眼流下泪来,面对兄长的力气,他没有丝毫抵抗。
“断绝关系的信,你写还是不写?说呀,说话呀!”
“我写。”
“什么,你说写?”
“但、但是,兄长,求求您了。万一她不肯断绝关系,您可千万别做那种动刀杀人的事呀。恳请您要向我保证,绝对不会那样做。”
“我怎么能给你这种愚蠢的保证呢?对忠右卫门大人也好,对阿缝小姐也好,都没法交代。”
“那、那我不写了。”
“什么,你不写了?”
“要是阿袖不能真正幸福,我怎能写这断绝关系的信。这罪过原本就在我市十郎的身上,她虽然在水茶屋做事,可在那之前,她就像洁白的绢布一样,是纯洁的女子呀。”
“你这个混账东西!”
松开的手,瞬间又朝着市十郎的侧脸狠狠地掴了一巴掌。
看着抱着头倒下的弟弟,主殿的手又追上去,再次揪住他的领口,用力一推,任由愤怒驱使,把市十郎的脸在榻榻米上使劲地来回蹭着。
“你倒是想想收养你的家人们呀!竟敢说出这样的话,你以为你这身子是谁的呀?生在武士之家,却对祖先、对官府都不知分寸,你这个、这个没家教的东西!”
比起被推倒在地的弟弟,攥紧拳头、不断挥拳的兄长,到最后反而满脸泪痕,脸上的皱纹因为哭泣而扭曲着,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打你的不是我呀!像你这样的蠢货,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爱,要打醒你才罢休。借我这双手打你的,是咱们已逝的父亲呀!你就把这拳头当作是父亲的,好好想想吧。”他说着猛地把市十郎推开,最后说道:“你再好好想想吧。静下心来,好好考虑考虑。”
主殿说完,便往室外去了。因为在走廊外,用人嘉平过来禀报说大冈兵九郎来了。
这个兵九郎也是大冈十家的一户,算是市十郎兄弟的叔父。市十郎的养子收养事宜,就是兵九郎从中牵的线。鉴于这个关系,之后市十郎和阿缝的婚事也打算让他来说媒。因此他一听说这事,就急忙赶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