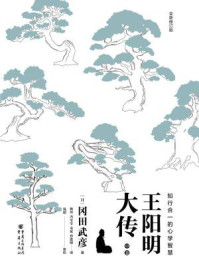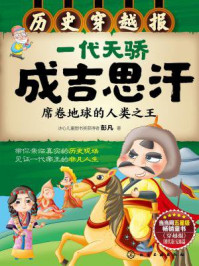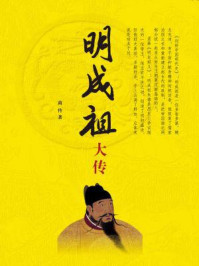人世间,有这样一种人,在别人懵懂无知的年纪,已经饱览群书,才识博洽,闻达于世上。自那以后,名声之于他们如影随形,慢慢变得不悲不喜。自幼读遍百书,专研学问,母亲教导有方,自身天赋异禀,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传奇胡适。
十一岁,胡适的名字便流传甚广。夸赞赏识、羡慕嫉妒,自然也随之而来。小小年纪的他,只是想做好自己,将学问做到极致。对于那些外界的纷纷扰扰,根本无从感受,一派风淡云轻。
十一岁,已经能用朱笔点读《资治通鉴》,字里行间别有一番滋味。之后,更是独自编创了《历代帝王年号歌诀》,这是他写的第一本读物,也是它让他正式走上了文学之路。
《历代帝王年号歌诀》在胡适的手中流转出去,最后辗转到了知府大人手中。面对十一岁孩子写的书,知府大人眼前一亮,对书中的内容赏识不已。他根本无法想象一个孩子是如何完成这种近乎完美的撰写的。
摘艳薰香,辞丰意雄,金辉玉洁,言简意赅。知府大人赏识之情溢于言表,即刻命人用宣纸印发数百份,四下散发出去。一传十,十传百,自此以后,胡适便小有名气。获得“小神童”称号,方圆百里,声名遐迩。
可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不时会激起波澜,一层一层蕴开,打击着世间小小的生命。不管你是否愿意,但无从选择,只能任命运一步步靠近,随后去面对。也许,是生活想测验一下胡适,看看他能否在逆境中前行。
这一时期,胡家遇到了经济危机,生活条件每况愈下,甚至难以维持生计。面对这样的困境,冯顺弟万般无奈,可一时间却也无法解决。思来想去,只能让胡适乘船去泾县寻找舅父,在舅父的药店里打杂来贴补家用。
胡适来到舅父家学习经商,可拿起十三档(算盘),丝毫提不起兴趣。一有时间,就寻得一处安静之处,独自阅读起来。线装古书,一页一页在手中游走,他不由的着了迷。回味之余,更是满心欢喜。
胡适一点不想弃笔从商,一心只想着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可眼下的境况,让他百转千回。突然,想起在上海的二哥胡绍,知其境遇尚可,心想只身去投奔,希望能重拾读书之路。于是,急忙拿起笔给胡绍写信,告之其自己心中所想。
冯顺弟得知此事,一时间也有些左右为难,想起胡传的遗言:“你要尽力让他读好圣贤书。”心中立即有了主意,毅然在“经商”和“读书”之间,选择了后者。既然儿子和亡夫都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她没有权利去阻止。
这样的选择,即遂了儿子的心愿,也随了亡夫的遗愿,可偏偏不是她的意愿。胡适是冯顺弟一点一点带大的,那种感情深入骨髓,眼下他要远去求学,心中伤感万千。可她愿意成全儿子,独自伤感,这样的心伤陪着她度过了今后的许多年。
求学是一条漫漫长路,那时的交通,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她怕是只能在远方盼着儿子成长,用书信来传送信息,即使是望着他,都是奢侈。聪明如冯顺弟,自是料到了这些,可她也愿意放手,放手让胡适自由翱翔。
心中的牵挂并非说放就放,为了留下一些念想,冯顺弟亲手为胡适缝制了一个枕头套子。用紫红色线绣再套子上绣下了两行字:“男儿立志出乡关,读不成名死不还。”他抱着枕头套子,自是泪流满面,可她的嘴角,越在上扬。
彼时,胡适名为14岁,其实是个刚满12岁的孩子,他自小随母亲长大。此般离开是第一次,可是却不知要去多少年,心中更是眷舍不已。可那时的他,心中有着更大的向往,遂依依不舍后,还是转身踏上了求学之路。
后来,胡适忆起当时的情景,不由写到:“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自此,胡适开始了自己的新的求学之路。从那以后,他所学所问和冯顺弟几乎脱离了关系。在外面漂泊了二十多年,天下地大,人山人海,却再也没有人约束他。任何事,都由着他自己做主。可他依旧是那个有约束力的胡适,一如往昔。
冯顺弟对胡适九年的殷殷教诲,他自是念念不忘,感恩之情更是不言而喻,后来在《四十自述》中写到:“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很久以后,胡适在《我的母亲》中写到:“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只身来到上海后,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每一个学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些学堂因为胡适而骄傲。他在那里不仅仅是一个学生,还留下了很多文学作品,颇有造就。
上海梅溪学堂是胡适在上海的第一个学堂。那时,他不会上海话,又没有闻名的文章。先生只当他是乡下来求学的孩子,想来没读过什么书,便将他编到五班。当时,五班是上海梅溪学堂最差的一班了,可他没有抱怨,安心上课。
那天,国文课上,国文先生在讲解“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古文时,无意间提及此话出自《左传》。彼此的胡适,来上海已经6个星期,已经能略略听懂上海话,听着先生的话,他想了想,知道先生讲错了。
胡适并没有立即指出先生的错误,他知道那是对先生的不尊重。等先生让大家自习之时,他悄悄走到先生身边,轻声对先生言:“先生,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
听胡适一言,国文先生震惊不已,推了推眼角的老花镜,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望着站在面前的胡适,乡下打扮,不卑不亢,眉宇间器宇不凡,心中不由暗自惊叹。随即,问其胡适念过什么书,背过什么文章,胡适一一回答。老学究目瞪口呆,他没想到小小胡适竟然已经博览群书。
之后,先生和胡适对了对子,随即又让胡适写文章。胡适拿起笔,洋洋洒洒的写起来,一气呵成,满纸沉思翰藻。国文老师读过后,惊才艳艳,心中的敬佩之情油然而起。胡适的博学,震惊了这位先生。
隔天,胡适便离开了五班,直晋二班。自此,他在上海大展拳脚。15岁,发表了自编的白话小说《真如岛》。十几岁的胡适,还曾主编了《竟业旬报》(白话报刊)。属于胡适的上海传奇,就这样毫无征兆的开始了。
那是的传奇,并不叫胡适,那时的他,有另一个名字——胡洪骍。胡洪骍之所以改名胡适,皆因《天演论》。胡适初次接触《天演论》,其中的深意丝毫不理解,对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也是茫然无知,对进化论的了解更是粗俗浅显。
胡适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印象深刻的只是八个字“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对“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一类的口号和公式更是深有感触。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国列强想方设法瓜分中国,中国随时面临灭国的危机。
《天演论》犹如晴天霹雳,冲击着这些莘莘学子的爱国之心。但他们毕竟还小,做不出过激的反应,第一个反响竟是改名字。“竞存”、“天择”等名字在学堂里流传开来,胡洪骍自是不甘落后,也改了名字。
那天早晨,胡适来找二哥,希望二哥帮忙想一个表字。胡绍一边洗脸,一面答道:“就用‘物用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胡适听后,万般喜欢,欣然接受,“适之”二字就这样成了胡适的表字。
后来发表文章,偶然间用了“胡适”作笔名。1910年,胡适之考试留美官费,正式用了“胡适”的名字。“胡适”是《天演论》留给胡洪骍的小小“纪念品”,自此以后,他开始接受进化论思想。小小年纪,遐迩闻名,屹立在乱世之中,有着万丈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