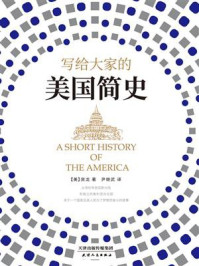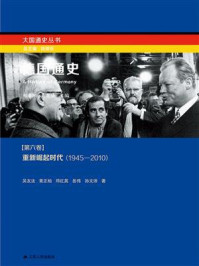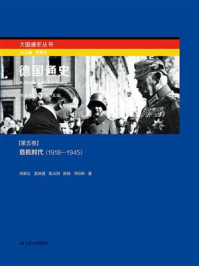在18世纪俄国,理性时代的精神和思想借助通俗文学的形式得到传播,这些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并非某一位职业哲学家或大学教师,而是作家和讽刺作家 尼古拉 · 诺维科夫 (Nikolai Novikov/Николай Новиков,1744—1818)。
诺维科夫的家庭属于贫穷的乡村贵族。他就读于莫斯科大学附属中学,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完成学业。他为自己在教育方面的种种不足而抱憾终身,尤其是不懂外语。1767年和1768年,他是法典委员会的秘书之一,负责在为“中产阶层委员”设立的特别委员会上做记录,同时也在首席委员会的会议上做记录。这项工作使他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广泛了解,尤其是那些与“中产阶层”,甚至农民相关的问题。这段经历似乎影响到他后来的所有活动。法典委员会解散后,诺维科夫以极大热情投入讽刺期刊的出版事业,不仅作为出版商,而且还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11]
俄国第一份讽刺杂志《万象》由叶卡捷琳娜本人首倡出版,她希望通过这一姿态表明,她尽管解散了法典委员会,但并不打算放弃她的开明自由主义。该杂志名义上的出版人是女皇的私人秘书科济茨基(Kozitsky/Козицкий),但文学界全都清楚,其真正的主编是叶卡捷琳娜本人。在第一期上,她鼓励俄国文人效仿她的榜样,目的是刺激社会热情,对政府的各项政策提供支持。她的鼓励大获成功,甚或超出她的胃口。很快,讽刺期刊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叶卡捷琳娜的杂志试图扮演“祖母”角色,她想控制其他杂志,确保批评不会超过某些明确划定的界限,但这项任务实属不易。
在这些忘恩负义的“孙儿”中,最有趣、最大胆的杂志就是诺维科夫的《雄蜂》,这是1769—1770年间出版的一份周刊。从第一期起,诺维科夫就反驳了叶卡捷琳娜的建议,即讽刺应是“愉快和善意的,讽刺作家要牢记爱其同胞的责任,对现实进行批评的前提是要注意到现实生活中的积极方面”。面对《万象》发出的种种威胁,诺维科夫诙谐地提醒叶卡捷琳娜不要忘记她自己制定的文学游戏规则,他的刊物上还有一些对女皇本人的恶意影射。在《雄蜂》中,对作为《万象》主编的叶卡捷琳娜的尖锐的(虽说是间接的)批评与对女皇叶卡捷琳娜的赞美相互交替。一段时间,这些策略使诺维科夫得以继续他尖锐的社会讽刺,对《万象》展开无情攻击。最终,叶卡捷琳娜失去耐心,决定采取行政措施。起初,她实施严格的书刊审查制度,后来则决定查封所有讽刺期刊。《万象》也停止出刊,不久之后,《雄蜂》告诉其读者,它必须与他们告别,尽管并非出于自愿。
诺维科夫在1772年又得到一次机会,当时叶卡捷琳娜的喜剧《哦,时代!》在圣彼得堡上演,该剧嘲笑保守的贵族反对派,诺维科夫知道如何奉承叶卡捷琳娜的虚荣心,他于是得到女皇,同时也是这部新喜剧之作者的赞助,获准出版另一本期刊,即《画家》。
诺维科夫讽刺的主要目标是既坏又蠢的地主,他们吹嘘其高贵出身,对农民却十分残忍,他们对社会毫无益处。他最引人注目的讽刺作品是发表在《画家》前几期上的《旅行记片段》,其中有关于“破败村庄”的惊人描述,“哭泣的农舍”在“残忍暴君”的枷锁下呻吟。在拉季舍夫之前,俄国从未有过对农奴制如此强烈的谴责。因此,许多学者后来将《旅行记片段》归在年轻的拉季舍夫笔下,亦不足为奇。
《旅行记片段》和《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的主要区别在于,拉季舍夫笔下的农民有抗议甚或起义的能力,而诺维科夫笔下的农民则胆小谦卑。在诺维科夫对公众良知的呼吁中并无任何东西可被理解为对贵族阶级的攻击,但《旅行记片段》仍在有势力的圈子里引起极大愤怒,1773年7月,《画家》停刊,其存在仅持续一年。
当诺维科夫在作品中对俄国现实做出尖锐批评时,他持有怎样的社会观呢?他的理想模式显然是父权君主制,这种体制能超越一切个人利益,联合所有阶层去进行追求共同利益的和谐活动。在这种体制下,贵族不会拥有或奴役农民,反而肩负着在农民和最高政权之间进行调解的责任。诺维科夫建议,在履行监督职责时,贵族应以“父亲般的”方式行事,关顾其农民,并在洪灾、火灾、歉收或其他自然灾害发生时伸出援手。尽管他深知他的父权田园诗与俄国的现实相距遥远,但他仍相信这一理想化的愿景,即一个好地主能成为其农民的父亲,一个好沙皇将成为整个民族的父亲。 [12]
这种父权制乌托邦与理性时代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很少共同之处,后者主张用基于非个人的理性立法的人际关系来取代个体的人身依赖。诺维科夫认为,国家财富应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他不喜欢资本主义倾向。尽管他尊重,甚至同情商人阶级,但他看不到工业资本的必要性,厌恶一切金融诡计。如果仔细观察他的社会理想,我们会发现这实为一幅关于彼得改革之前俄国社会关系某些方面的理想化图景。
诺维科夫几份期刊的主要读者群是小贵族、中产阶级和商人阶级。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理由称他为俄国“第三阶层”的思想家。但必须记住,俄国的这种第三阶层并非一股能够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力量。
“俄国第三阶层”意识形态的一个典型因素即其法国恐惧症,他们所针对的主要是越来越热衷盲目模仿法国一切的大贵族和富有贵族。不过,他们的谴责并不极端。诺维科夫也带有这种厌恶,他在《雄蜂》上也曾抨击对方言土语的普遍蔑视,对巴黎最新时尚的盲目追捧,以及被以法国方式教育出的“年轻贵族猪崽子们”的其他缺陷。
正如前文提及,在与百科全书派的接触以失败告终后,叶卡捷琳娜也对维护民族传统产生了兴趣。在这场战役中,广受欢迎的诺维科夫似是一位潜在盟友。于是,叶卡捷琳娜资助了诺维科夫的“俄国古代文献丛书”,此为一套系列出版物,诺维科夫出版了多种历史古籍。利用叶卡捷琳娜的支持,诺维科夫于1774年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出版一份讽刺杂志。这份期刊有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刊名,即《网袋》,此指当时时尚人士戴的假发上用来包裹脑后头发的丝绸网袋,这个刊名本身即表明该杂志将与崇拜外国时尚的风气做斗争。
诺维科夫在一篇讽刺文中表达了他的厌法情结,他讽刺的是一个名叫门松日的骑士[“门松日”(Mensonge)意即“谎言”(lie)],他在法国是一位美发大师,但在俄国却做了贵族子女的家庭教师,他不断地向他的学生们灌输对俄国的仇恨。他的对手是一个可爱的德国人,后者为俄国人辩护,将那些真正的、珠宝般的“伟大而古老的俄国美德”与法国流行的人造宝石进行对比。这位德国人是这样结束其讨论的:
唉,如果有某种人类力量能把俄国人先前的道德再归还给俄国人就好了,他们先前的道德在引入假发网袋后便遭到破坏,如果俄国人的道德失而复得,他们就会成为人类种族的典范。在我看来,早期那些智慧的俄国君主似有预见,在艺术和科学被引入俄国之后,俄罗斯人民最伟大的财富,即道德,便将永远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宁愿他们的许多事情一事无成,也依然保持美德,保持对上帝、君主和祖国的忠贞。 [13]
争论似可到此为止,但诺维科夫显然仍有一些疑虑,他在其杂志的下一期又发表一封信,声称是一位“不知名的”法国捍卫者写来的,他对那位古代俄国美德的拥戴者说道:
您为何要平白无故地糟蹋纸张呢?如今的年轻人活泼机智,轻浮大胆,他们会嘲笑您对祖国的古老的爱。您出生在很久以前,当时的俄国沙皇在婚礼那天把蜂蜜涂在自己的头发上,第二天早上和新娘去澡堂,在那里吃饭;当时,所有知识都被写在教会的日历上;当时,蜂蜜酒和葡萄酒要论壶喝;当时,年轻的夫妻直到结婚那天才首次见面;当时,浓密的大胡子是一切美德的同义词;当时,人们在火刑柱上被烧死,或者出于某种特殊的虔诚,因为在做十字架时出了差错而被活埋。 [14]
诺维科夫向他的读者承诺,他将对这种法国式辩护做出回应。在此信第二部分,他让他的“来信者”道出许多夸张之词,因此显得很可笑,比如他说,俄罗斯人不能称之为人,除非他们学会用法国人的方式跳舞和问候。然而,诺维科夫似乎无法找到新的论据来捍卫“古代的俄国美德”,《网袋》的读者们徒劳地等待,终未看到诺维科夫所承诺的回应。 [15]
用诺维科夫自己的话来说,在编辑这些讽刺期刊的年代,他“置身于宗教和伏尔泰主义的分岔路口”。也许可以补充说,他同样也置身于爱国主义情感和启蒙主义之激进的,却是国际化的观念之间,前者在当时局势下即意味着墨守传统,后者则被他用来批判俄国现实。1774年,在主编《网袋》时,他正经历一场严重危机,新近爆发的普加乔夫叛乱更加重了这场危机。1775年,诺维科夫加入共济会,他借助共济会运动缓解了他的危机。更确切地说,他与其说是主动加入共济会,不如说是应邀参与集会,因为他的引领人甚至不愿为他举行正式的入会仪式,以免令他们这位新会员感到失望。 [16]
在18世纪,共济会运动(Masonic movement/масо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秘密或半秘密(取决于环境)社团。共济会(Freemasonry/масонство)的意识形态从未得到过明确表述,当然,任何明确的声言也均不符合该运动的密谋性质及其深奥教义。不同的系统,甚至不同的会员可能持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信念,从激进的自由主义到彻头彻尾的守旧派,不一而足。所有共济会成员的共同点则在于,他们相信天下人皆兄弟,相信道德自我完善的目标,相信即将来临的黄金时代。然而,这种信念与任何系统的政治行动纲领均无关联。
总体而言,共济会是一种特殊的、世俗化的宗教生活方式,是封建社会解体和教会权威瓦解的产物,也是传统的宗教信仰完全或部分丧失导致的结果。对于像诺维科夫这样一个置身于传统宗教信仰和理性主义之间的人来说,共济会成了宗教的替代物,而共济会则凭借其等级秩序和精心设计的崇拜成了教会的替代物。
相对于传统宗教,共济会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吸引人们远离官方教会,通过宗教经验的理性化来使得人们的世界观逐渐世俗化;另一方面,它也在吸引人们返回宗教,使他们远离启蒙运动之世俗的、理性的哲学。第一个功能借助共济会中理性主义的、自然神论的派别得到最有效的落实,这一派别确立了理性面对教会的权威,坚持宽容和个性自由。共济会的各种自然神论在英国尤为盛行,它与自由主义运动有关联,它在法国也很时尚,常与百科全书派结盟。共济会的第二个功能最常借用神秘的仪式来实现,尽管这也表现为宗教信仰的现代化,因为它提出的信仰模式在根本上是反教会的,假定在灵魂与上帝直接接触的基础之上可能存在高度内在化的信仰。
神秘共济会的追随者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的德意志诸邦国,尽管在德国也产生了光照会(Illuminati/иллюминаты),此为共济会一个极端理性主义的分支,它并不畏惧政治行动。共济会的神秘主义主要自雅各布·波墨和圣马丁的著作获取灵感,他们两人的著作均被译成俄语,尤其是圣马丁,他在俄国非常受欢迎,在“马丁主义者”(Martinists/мартинисты)中间更受推崇,诺维科夫与马丁主义者也有联系(不过,“马丁主义者”并非得名自圣马丁,而得名自他的老师、葡萄牙神秘主义者马丁内斯·帕斯夸利)。
俄国的第一批共济会分会出现在18世纪中期,即伊丽莎白女皇在位时期。但从著名的共济会成员叶拉金的回忆录中似可清楚地看出,这些早期的分会更像上流社会的俱乐部,很少能提供智性或精神上的激励。这场运动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变得显眼起来,因为叶卡捷琳娜对共济会充满敌意。共济会成员中有一些最杰出的古老贵族的代表,其中包括帕宁兄弟和谢尔巴托夫公爵(他们是贵族反对派领袖),以及苏马罗科夫、赫拉斯科夫和卡拉姆津等杰出作家,甚至连拉季舍夫也是“乌拉尼亚”分会的成员。大多数共济会成员均来自贵族阶层,但知识分子中的一些非贵族成员,乃至仆人,偶尔也会成为成员。
1770年代下半叶,在普加乔夫起义之后,共济会分会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这一时期,更为开明的年轻贵族面临一个令人不安的两难选择:农民起义是一个可怕的警告,诱使他们放弃开明的自由思想;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无法返回先前的态度,即理所当然地接受上层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于是,他们只能步入个人自我完善的王国,即“灵魂的内在生活”,换言之,即步入共济会分会。这种氛围也导致了俄国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 /сентиментализм)和其他前浪漫主义潮流的兴起。
与许多西欧的共济会不同,俄国的共济会运动在世俗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从彼得大帝时代起,东正教便几乎完全失去对知识精英的控制,国君们很少对东正教会表示尊重(伊丽莎白女皇或许构成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共济会主要就是对开明社会的“伏尔泰主义”(Voltairianism/вольтерьянство)的反拨。因此,莫斯科都主教普拉东不顾叶卡捷琳娜的明显敌意,仍相当青睐共济会运动。
当时最杰出的共济会成员之一 伊万 · 洛普辛 (Ivan Lopukhin/Иван Лопухин,1756—1816),年轻时也是百科全书派的热心追随者。他对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印象深刻,译出该书具有总结性质的最后一章《自然法典》。洛普辛对于其译作十分满意,一直想把它分发给更多的人。但正如他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告诉我们的,第一册译作刚一备好,他便开始感觉不安,受到良心上的折磨。他始终无法入睡,直到他把不敬的手稿扔进火堆,在他专门写成一篇论“理性之滥用”的文章后,他方才复归平静。然而,由于他已无法返回传统的东正教信仰,他便在共济会的神秘主义中找到了安慰。 [17]
沉湎于神秘主义的一个通常结果,即逐渐放弃对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兴趣。洛普辛是一个有着热烈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人,他以从事慈善事业而广为人知,但与此同时,他坚决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他有一篇论著,题名《目睹平等和狂暴自由种种有害后果之时关于专制之益处的内心思考》(1794),他在其中提出一种理论,以证明社会不平等是一种自然法则,他宣称,自然本身即体现着分化和等级原则,如果没有不平等,世界将失去其多样性、和谐与美。
另一位杰出的共济会成员是平民知识分子 谢苗 · 加马列亚 (Semyon Gamaleia/Семен Гамалея,1743—1822),他是诺维科夫的好友和合作者。他鄙视物质利益,被视为一位圣徒式人物。他在白俄罗斯为政府服务,后获赠300个农奴作为回报,据说他一口回绝,理由是他连自己仅有的一个农奴都对付不了。还有一则趣闻,说他遭到强盗袭击,他并未抵抗便交出其怀表和金钱,回家后,他还祈祷那些被抢走的财产别遭受虐待。另有一次,他的一个仆人偷了他的东西,仆人被抓获后,加马列亚却把被偷的钱作为礼物送给那位仆人,并让那位仆人“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 [18]
这些故事表明,加马列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赞同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原则。这种对个人道德的强调,即坚信只能通过自我完善和道德重生来克服恶,是俄国共济会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这一点使得米留科夫称俄国共济会为18世纪的“托尔斯泰主义” [19] 。虽然这种比较的确引起了人们对共济会信仰一个特殊方面的关注,但它仍具误导性,因为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加马列亚所宣称的福音派伦理毕竟与托尔斯泰特有的社会激进主义相去甚远。
从纯哲学角度看,俄国共济会成员中最有趣的人物是一位俄罗斯化的德国人,他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名叫 约翰 · 格奥尔格 · 施瓦茨 (Johann Georg Schwarz/Иоганн Георг Шварц,1751—1784)。施瓦茨作为一名教师来到俄国,1779年被任命为莫斯科大学教授。不久,他遇到诺维科夫,与他一起组建学者联谊会。1780年代早期,他俩出版两份期刊,即《莫斯科读物》和《晚霞》。
除了干劲十足和理想主义这两种特殊品质外,施瓦茨还具有很高的教学天赋。他倾尽其资产,在莫斯科大学创办一个“教学讲习班”,他在那里通过对斯宾诺莎、卢梭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们的批判研习来培训未来的教师。在学生们的帮助下,他还成立一个“翻译讲习班”,将西欧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和道德哲学家的作品译成俄语。当与校方的争执迫使他递交辞呈之后,他在家中继续授课。他在俄国共济会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个组织者,因为他建立起玫瑰十字会(Order of Rosicrucians/Орден розенкрейцеров)的俄国分会,这缘起于他在1781年旅行德国时与玫瑰十字会取得的联系。莫斯科玫瑰十字会成员是俄国共济会主体中的秘密精英。
施瓦茨不仅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是雅各布·波墨的追随者,同时还是“神秘科学”的狂热信徒。他实践炼金术,相信有可能获得关于自然秘密的神奇洞察力,认知自然在人类堕落之前真正纯洁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说为谢林的自然哲学在俄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20]
施瓦茨在他发表于《晚霞》上的文章中阐述自己的观点。 [21] 他的哲学主要关注人的本性。施瓦茨区分了人的身体、精神和灵魂,在他看来,后一种存在是物质元素和精神元素这两者化学融合的产物。他相信动物也有灵魂,而人是连接动物世界和纯灵魂世界的生命链中的中间环节。身体由感官控制,灵魂由智性控制,精神由“理性”控制。智性,或者说是启蒙哲学家们称之为“理性”的那种能力,只能通过感官发挥作用,而真正的理性则能进行超验认知,能理解普通经验无法把握的神性真理。真正的知识是道德的同义词。随着绝对知识的获得,人也会获得绝对道德,人将获得重生,“堕落后的崛起”,这将宣告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现在让我们回到诺维科夫的观点和活动上来,他在施瓦茨早逝后成为莫斯科玫瑰十字会的领袖人物。对诺维科夫而言,共济会运动代表理性主义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妥协,因此,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之前信仰的彻底放弃。与施瓦茨不同,诺维科夫对神秘学不感兴趣,仅在很小程度上受到神秘主义的影响,总之,他大体上代表着共济会的理性主义倾向。
1777年,诺维科夫出版了俄国第一份哲学和道德期刊《晨光》。与后来由诺维科夫出版,但实为施瓦茨主编的《晚霞》不同,《晨光》所刊载的均为诺维科夫的文字。这份杂志上发表的最重要文章之一,即他的《试论人在与上帝和世界之关系中的尊严》 [22] 。这篇文章暗含着对一种流行的神秘主义观点的抨击,那种观点认为,人类是堕落的造物,在上帝面前只是一粒尘埃,是“盛满原罪的腐烂容器”。诺维科夫则针锋相对,给出一个地道的文艺复兴式观点,即人是“宇宙的创造者”。他认为,人和最小的蛆虫一样均由上帝用尘土造出,但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模样被创造出来的,且被赋予理性,人的本性中即已包含神性因素。因此,人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连接纽带。人性的本质是相互矛盾的:人是蛆虫,与此同时也具有神性;人是奴隶,与此同时又是统治者。他必须对造物主谦卑,但他也有权作为尘世上帝的真正代表而感到骄傲。 [23]
从这一理论可得出几个具有实践意义的结论。诺维科夫赞扬人类理性的神圣属性,比如他提出,用理性征服世界就是献给上帝的最合适供奉。此外,由于人的本质具有神性,因此每一个人都应得到尊重,无论其出身或社会地位。他还以人的尊严的名义,呼吁人们积极参与为共同利益而进行的事业。他在该文结论部分写道,人本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他是目的,因为无人有权把另外一个人当作手段,他又是手段,因为每个个体都应致力于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事业。他总结道,谁若仅把自己视为目的,他就是寄生虫,就是毫无用处的雄蜂。
诺维科夫并非一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但是他在俄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不依赖于独创性。他本质上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他可被称为他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他代表了当时所有主流的(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思想倾向:既有启蒙运动的普世主义,又有对传统民族价值的捍卫;既有理性主义,又有反理性主义的宗教意识。不过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不懈的改革家,他以其一生证明,教育的传播仅为专制政体之特权的时代已一去不返。
俄国共济会运动拥有众多富有且具有影响力的成员,是当时唯一独立于政府的强大组织。诺维科夫认为它可在社会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作用,这并不奇怪。早在1777年,他就用《晨光》的销售收入在圣彼得堡为中产阶级子女开办了两所学校。然而在都城,在女皇本人的眼皮底下,他的计划几乎无望获得成功。因此在1779年,他移居莫斯科,租下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开始活跃于教育领域。1784年,他抓住允许设立私人印刷所的法令出台之良机,创建了他著名的印刷所(使用学术联谊会中富有的共济会成员们的资本)。其出版活动的规模在俄国前所未有。他不仅是编辑,也是发行商,努力确保他的书能抵达帝国的最边远地区,其中包括西伯利亚。仰仗诺维科夫,中产阶级,还有一些农民,方才接受到那些步入俄国的新思想。于1781—1790年间在俄国出版的所有书籍中,由诺维科夫出版的书约占28%(即2 585种图书中的749种) [24] ,但其中只有相对较少的书籍是介绍正统共济会思想、神秘学或神秘主义的。事实上,诺维科夫并不愿意出版此类作品,施瓦茨也经常指责他对共济会事务缺乏适当热情。他甚至因此与那些富有的玫瑰十字会成员发生公开争吵,后者威胁要撤出他们的资本。他的大部分出版物均为历史图书或教育图书(包括俄国第一部儿童文选),他出版的主要作家和学者包括弥尔顿、莎士比亚、杨、莱辛、克洛普施托克、菲尔丁、斯特恩、高乃依、拉辛、培根、洛克、门德尔松、卢梭,甚至伏尔泰和狄德罗,另有一套单独的、精心编选的俄国作家选集丛书。在那些忙碌的岁月里,诺维科夫发现自己依然有精力去从事其他活动。1787年饥荒发生后,他利用其杰出的组织才能为饥饿的农民提供了大规模帮助。
诺维科夫的活动很难得到叶卡捷琳娜的赞同。如此大规模的、不受她监督的教育行动和公民行动令她深感不安。在她与这位对手的战斗中,她巧妙利用了对方与玫瑰十字会的联系,以便在公众眼中把他诋毁为一个愚昧的神秘主义者,而她自己则是启蒙运动理性理想的捍卫者。1780年代,她发起一场针对共济会的全面战争,她自己也写了几部嘲讽该运动的喜剧(《西伯利亚萨满》《骗子》等)。她还匿名出版一本小册子,标题意味深长,即《荒谬社团之秘密》,她还试图说服都主教普拉东把诺维科夫指为异端。她推出这些措施并不仅仅因为她不喜欢诺维科夫的热情,而且还因为她担心,共济会的那些分会正在密谋推翻她,用王位继承人(王储保罗)来取代她。
法国大革命使叶卡捷琳娜意识到必须实施更严厉的制裁。1792年,她下令逮捕诺维科夫,后者未经审判就被监禁于施吕瑟尔堡,刑期长达15年。诺维科夫的印刷所被解散,在那里印制的许多书籍和期刊也被焚毁。4年后,诺维科夫在沙皇保罗即位时获释。他健康状况不佳,生活环境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在宗教神秘主义中寻求安慰。他和加马列亚一同,把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用于编纂一本庞大的有关神智学、神幻术和神秘哲学的文选。
在19世纪前25年,共济会经历过一次短暂的复兴,其突然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即位,他无法容忍任何秘密或半秘密社团,尤其憎恶共济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