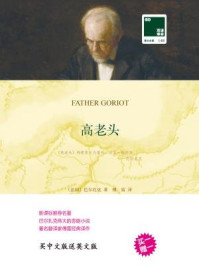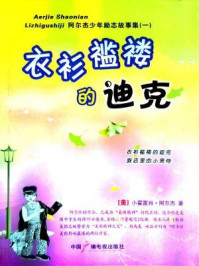“我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计划,”当我的生命之光提着大大小小的爱马仕购物袋走进家门时,我激动地说道。她的几张信用卡因为频繁摩擦,现在还冒着热气。“我们打车到布鲁克林,去彼得·卢格牛排馆奖励自己一顿雪花牛肉,怎么样?他们家的西冷牛排鲜嫩多汁,我已经馋了一整天了,更别说再配上西红柿、洋葱和薯饼。如果威廉斯堡大桥堵车了,我们可以下车跑过去。”
“控制一下你的肾上腺素,”我不朽的爱人搪塞道,给我踩下了刹车,“我在市中心的生鲜超市买了一对鳐鱼翅。我觉得可以加点新鲜的酸豆进去炖个浓汤,再把我们在易趣网上买的那瓶爱斯基摩葡萄酒开了。”在钦定此事后,她开始夸夸其谈,根据一个古老的家传秘方用语言烹制出一桌大餐,其中包括一款酷似胶水的酱汁。
“别傻站着啊,”家里的女主人对我嚷道,仿佛我是帕里斯岛
 的新兵,“把我买的鱼拿出来,我来除味。”在意识到一块厚切西冷牛排及其配菜注定要升华为一首有关求而不得的辛酸俳句后,我开始拆开夫人买的用《每日新闻》包裹着、长得像蝙蝠的主菜。正是在这几张报纸上,我像尼俄伯
的新兵,“把我买的鱼拿出来,我来除味。”在意识到一块厚切西冷牛排及其配菜注定要升华为一首有关求而不得的辛酸俳句后,我开始拆开夫人买的用《每日新闻》包裹着、长得像蝙蝠的主菜。正是在这几张报纸上,我像尼俄伯
 般正流泪不止的眼睛看到了一篇令我格外感兴趣的报道。
般正流泪不止的眼睛看到了一篇令我格外感兴趣的报道。
报上说迈克·泰森正在出售他的豪宅,而那家伙的府邸说是人间仙境也不为过。它拥有十八间客房,我想就算两支棒球队突然到访也能被安排得妥妥当当——以及三十八个卫生间,显然泰森不喜欢边捶门边大喊:“你到底还出不出来了?”此外它还带了七间厨房、一座瀑布、一个船库、一间迪斯科舞厅、一个巨大的健身房以及一座大剧院。房子最初的报价是两千一百万美元,结果活生生被砍到了四百万,我觉得要么买家是一个功力深厚的催眠师,要么就是这房子有什么硬伤,比如缺少一个导弹发射井。
这篇报道让我想起自己多年前经历的一桩与房产交易有关的小惨剧。尽管并未达到如此惨绝人寰的地步,但也曾让我的血压一度飙升到足以触发自动灭火系统的程度。
此事说来话长,围绕着我们的合作社
 公寓展开。因为我夫人看上了一栋联排别墅,其最新装修完美吻合了她钟爱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风格,她决定把我们的公寓挂牌出售。于是她,我的小闪电泡芙,在运用了包含普朗克常数在内的数学算式后推断,只要我们卖掉这套位于公园大道的经典六号
公寓展开。因为我夫人看上了一栋联排别墅,其最新装修完美吻合了她钟爱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风格,她决定把我们的公寓挂牌出售。于是她,我的小闪电泡芙,在运用了包含普朗克常数在内的数学算式后推断,只要我们卖掉这套位于公园大道的经典六号
 公寓,再耍些手段,便可以使这次换房行动接近收支平衡。
公寓,再耍些手段,便可以使这次换房行动接近收支平衡。
“房产中介灰鲭鲨小姐和大白鲨太太说我们家能卖好大一笔钱。”夫人颤抖地说道。“那栋别墅要价八百万。如果我们不吃不喝,断掉医疗保险,再把为孩子们上大学存的教育基金取出来,也许能凑够首付。”见她的双眼有如救世主马赫迪般射着金光,我握拨火棍的手攥得更紧了。她显然已铁了心要搬家,就像希特勒站在波兰地图前摩拳擦掌时那样,她连哄带骗,直到我同意将我们宽敞的高层爱巢卖给任何一个手头有一千万闲钱的人。
“听好了,”我正告那两位中介女妖,“不先卖掉旧房,我就绝不会考虑买新房。”
“那是自然,伊格纳兹。”背鳍更大的那位一边说,一边用史丹利牌锉刀锉她的第三排牙齿。
“我不叫伊格纳兹。”我没好气地回道,对她的自来熟感到火大。
“不好意思,”她说,“我看你长得就像个伊格纳兹。”她朝同伙咧嘴一笑,接着说,“你家就标价四百万吧。后面想降总是可以的。”
“四百万?”我尖声叫道,“我家怎么也值八百万。”灰鲭鲨用法医般狡黠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番。
“这种空手套白狼的事交给我们就行,”她说,“你只管继续玩你的魔方,不久你就能弄到足够的钱,无缝衔接地搬进你的新窝,还能剩点零钱把自来水通上。”
我做预算时没有考虑过翻新的费用,但显然老婆大人已经想好了新房的改造方案,且所有人都觉得这笔开销完全可以通过我去黑市卖肾解决。那栋联排别墅的中介,巴拉库德尼克太太,告诉我夫人,有好几个买家看上了那栋古色古香的别墅,随时可能出手,谨慎起见,我们最好先发制人。她建议的出价相当于一位沙特王子的零花钱。我决定硬碰硬,但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个潜在买家来看我们的房子,我夫人开始加大了抗焦虑药的剂量。
“我们最好把要价降一降,”夫人说,“灰鲭鲨小姐说,如果不这样漫天要价的话,我们的公寓会好出手很多。”
“四百万怎么能算漫天要价?我们十年前买的时候,整整花了两百万呢。”我解释道。
“两百万买蟾蜍宫
 ?”大白鲨太太一口饮尽我仅剩的那点金宾威士忌,说道,“你大麻抽多了吧?”在把要价降到三百万的那一刻,我仿佛在时隔多年以后,终于明白了开膛手杰克的作案动机。所幸总算有人来看房了:一对俄罗斯夫妇,他们以为我的报价是三百美元;还有一位在玲玲兄弟马戏团工作的马戏怪人,但我听说他不可能通过合作社公寓董事会的买家资质审核。与此同时,巴拉库德尼克太太说,近来对那栋别墅感兴趣的人数激增,一位名人意欲出价。
?”大白鲨太太一口饮尽我仅剩的那点金宾威士忌,说道,“你大麻抽多了吧?”在把要价降到三百万的那一刻,我仿佛在时隔多年以后,终于明白了开膛手杰克的作案动机。所幸总算有人来看房了:一对俄罗斯夫妇,他们以为我的报价是三百美元;还有一位在玲玲兄弟马戏团工作的马戏怪人,但我听说他不可能通过合作社公寓董事会的买家资质审核。与此同时,巴拉库德尼克太太说,近来对那栋别墅感兴趣的人数激增,一位名人意欲出价。
“你们要买的那栋房子刚有人出价,演员乔希·梅投瑙想要。坊间传闻,他正认真考虑要和珍妮弗·布高幸步入婚姻的殿堂。如果你诚心要买,”巴拉库德尼克太太残忍地笑道,“你就得出个价盖过他。”
“可我们的公寓还没出手呢,”我尖叫得像蝴蝶夫人。
“去办个过桥贷款,”这位中介脸上露出了浮士德熟悉的微笑,“我在贷款公司有熟人。在你卖掉那个大累赘之前,足够你渡过难关了。”
“大累赘?过桥贷款?我们的公寓要是能卖两百五十万就好了。”我卑微地说道。
“或者不亏本卖就行。”我的另一半说道。再说下去她可能就要提议把我们家捐给市里作为产房,只要能抵税就行了。打砸抢贷款公司的高俄力稀先生有如传教士献祭般,拔出我胳膊上的针头,用酒精棉签擦了擦我的动脉。
“按一会儿,”他说,“不然会有血肿。我就抽了一点血——你可以分期还。”
“十九个点的利息是不是有点粗暴了?”我嘟囔道,“何况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
“嘿,新泽西的那帮吸血鬼可是要二十五个点,而且要是你还钱不利索,他们会一枪崩碎你的膝盖骨。我们只会没收你的抵押物。”考虑到我已经艰难地讨价还价过一番,并且坚决拒绝了抵押孩子去套现,我有理由为自己感到欣慰和骄傲。在签协议时,高俄力稀像饿狼般看着我,他看到的分明是一份穿着拉夫劳伦粗花呢大衣的羊排。
“我们现在有两个家了。”我向夫人嘟囔着,掏出了会计师专为我遇到这种情况而准备的毒药。
“我有信心,我们一定能卖掉那个火坑,”灰鲭鲨小姐安慰我道,“可能我们要再降一次价,没准要再搭上家具。”想到破产的情景,想到我们的退休生活可能要在纸箱里度过,我把报价一降再降。与此同时,爱挑毛病的家伙们纷纷前来检阅我家,把每块地板和每道踢脚线都视察一遍,然后便永远地消失在了这座不夜城的八百万个五花八门的故事里。接着有一天,我正向当铺打听我的心脏起搏器能抵押多少钱时,我们那两位食肉的房产中介带着一个年约五十、衣冠楚楚的人走进了家。此人叫内斯特·莱钱快,拥有迈克·托德
 那样的进取精神,以及恺撒·罗摩洛
那样的进取精神,以及恺撒·罗摩洛
 那样英俊的欧陆风情长相。他似乎对我们的公寓诚心感兴趣,带着几个建筑师和一个家装设计师来看了好几次。我听到他们几个聚在一起开会,计划着把墙拆了,加装几个卫生间、一个健身房和酒窖。他们时不时瞥我一眼,有一次我听到莱钱快悄声说:“真是稀奇,有些人原来还能这样活着,真适合让玛格丽特·米德
那样英俊的欧陆风情长相。他似乎对我们的公寓诚心感兴趣,带着几个建筑师和一个家装设计师来看了好几次。我听到他们几个聚在一起开会,计划着把墙拆了,加装几个卫生间、一个健身房和酒窖。他们时不时瞥我一眼,有一次我听到莱钱快悄声说:“真是稀奇,有些人原来还能这样活着,真适合让玛格丽特·米德
 来做研究。当然,在让我的人碰任何东西之前,我要先请人做一次全屋烟熏消毒。”尽管我用朱红之舌一舔便能让他们灰飞烟灭,但早日还债好过逞匹夫之勇,我决定不和他们计较。毕竟莱钱快有钱,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有着无可挑剔的资质。简言之,他是一位理想的业主,尽管我们的合作社董事会在筛选潜在业主时,并不比门格勒
来做研究。当然,在让我的人碰任何东西之前,我要先请人做一次全屋烟熏消毒。”尽管我用朱红之舌一舔便能让他们灰飞烟灭,但早日还债好过逞匹夫之勇,我决定不和他们计较。毕竟莱钱快有钱,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有着无可挑剔的资质。简言之,他是一位理想的业主,尽管我们的合作社董事会在筛选潜在业主时,并不比门格勒
 医生心慈手软,但他们绝对挑不出莱钱快的毛病。我甚至怀疑他可能是骷髅会
医生心慈手软,但他们绝对挑不出莱钱快的毛病。我甚至怀疑他可能是骷髅会
 的成员,就和董事会的新任主席L.L.豆包先生一样。而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基本都是一本正经的詹姆斯二世党人,面对莱钱快大方自信的魅力,他们绝无抵挡之力。住在10A的西尼罗太太、拥有顶层公寓的阿提拉·韦恩纳里勃,以及美洲原住民住户萨姆·掩护马,都会欢迎像莱钱快这样的邻居。莱钱快的金融资产配置包含了大量的蓝筹股,他的正式推荐人包括比尔·盖茨和科菲·安南。要是灰鲭鲨和大白鲨更有眼色的话,我想她们在读到这样一封推荐信时就该反应过来了:“内斯特·莱钱快这家伙挺靠谱,不酗酒,不吹牛,不乱搞男女关系——雷茵霍尔德·尼布尔
的成员,就和董事会的新任主席L.L.豆包先生一样。而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基本都是一本正经的詹姆斯二世党人,面对莱钱快大方自信的魅力,他们绝无抵挡之力。住在10A的西尼罗太太、拥有顶层公寓的阿提拉·韦恩纳里勃,以及美洲原住民住户萨姆·掩护马,都会欢迎像莱钱快这样的邻居。莱钱快的金融资产配置包含了大量的蓝筹股,他的正式推荐人包括比尔·盖茨和科菲·安南。要是灰鲭鲨和大白鲨更有眼色的话,我想她们在读到这样一封推荐信时就该反应过来了:“内斯特·莱钱快这家伙挺靠谱,不酗酒,不吹牛,不乱搞男女关系——雷茵霍尔德·尼布尔
 签字推荐。”但可惜,对高额佣金的渴望冲昏了她们的头脑。后来,我听说了在哈维·内克塔尔的公寓里举行的那次业主面试,虽不免有夸张成分,但属实非同凡响。起初还都挺顺利的,莱钱快明白公寓里不能养宠物,发誓不会举办扰民的派对,说自己喜欢清心寡欲的生活,还聘请了一位叫“水肿”的清洁女工。哈佛毕业的5D房间业主赫尔曼·博瑞里斯故作严肃地拿耶鲁和莱钱快开玩笑,结果发现他俩刚好都穿齐默利牌的内衣。就在面试即将完美收官时,走廊突然传来了一阵喧哗。
签字推荐。”但可惜,对高额佣金的渴望冲昏了她们的头脑。后来,我听说了在哈维·内克塔尔的公寓里举行的那次业主面试,虽不免有夸张成分,但属实非同凡响。起初还都挺顺利的,莱钱快明白公寓里不能养宠物,发誓不会举办扰民的派对,说自己喜欢清心寡欲的生活,还聘请了一位叫“水肿”的清洁女工。哈佛毕业的5D房间业主赫尔曼·博瑞里斯故作严肃地拿耶鲁和莱钱快开玩笑,结果发现他俩刚好都穿齐默利牌的内衣。就在面试即将完美收官时,走廊突然传来了一阵喧哗。
“快开门,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门外人在大喊,大门的铰链被撞锤击落。莱钱快在看到一大群联邦探员破门而入时一下愣住了。“他在那儿!别让他跑了!”一位身穿防弹服的探员吼道。“要当心,这可是个武装抢劫犯。”只见莱钱快飞身越过钢琴,与萨姆·掩护马撞了个满怀,把那位阿拉帕霍人
 的头饰都给撞掉了。且不论真假,据说在追捕过程中枪声大作,其中有几颗流弹射进了哈维·内克塔尔为妻子贝雅所作的模仿天后赫拉的肖像画中。直到六个月后,我才把公寓卖给了信奉教友派的一家人,售价刚够付我那笔过桥贷款的利息——好多次,我都想从那座桥上跳下去。
的头饰都给撞掉了。且不论真假,据说在追捕过程中枪声大作,其中有几颗流弹射进了哈维·内克塔尔为妻子贝雅所作的模仿天后赫拉的肖像画中。直到六个月后,我才把公寓卖给了信奉教友派的一家人,售价刚够付我那笔过桥贷款的利息——好多次,我都想从那座桥上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