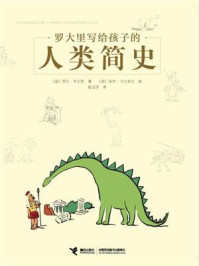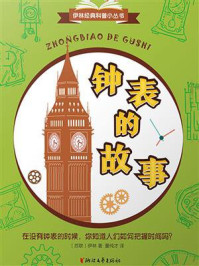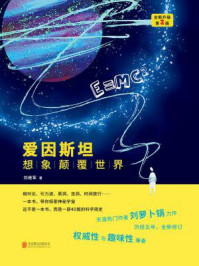战国时期,秦国年轻的将领白起临危受命,在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龙门镇)迎战韩魏联军,此战史称“伊阙之战”。白起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敌众我寡,必须“计利形势”。他利用韩魏联军各怀鬼胎、貌合神离的弱点,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他把军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采用疑兵之计,佯装与韩军精锐交锋,以牵制韩军;另一部分则秘密集结到魏军后方,全力打击魏军。战役开始后,白起的策略大获成功,韩魏联军准备不足,一时间溃不成军。最终,初出茅庐的白起展露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华,采用的战术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中原大地,一代“战神”崛起。在人类的抗癌史上,同样也有一位“战神”。我们的故事,就从他开始吧!
他,早在1913年就提出了“魔法子弹”(Magic Bullet)的设想:将毒素(子弹头)安装在能精确瞄准癌细胞的载体上,便可实现精准“投毒”,而不伤害正常细胞。他的思想,成为近百年后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简称ADC)的底层逻辑,为克服传统化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弱点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位先驱就是德国科学家、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埃尔利希(Paul Ehrlich)。
1878年,在德国莱比锡,年轻的医学生埃尔利希正在准备毕业设计。与其他同学的思路不同,埃尔利希似乎对细胞染色情有独钟。他计划用服装染料(苯胺及其他有色衍生物)对动物组织染色,以便在显微镜下观察被染色的动物组织。埃尔利希的兴趣让学院的教授们大为恼火,在他们眼里,埃尔利希不务正业,“玩物丧志”,沉迷细胞染色而根本无暇学习更有用的技能,前途堪忧。
让教授们“颇为失望”的是,“玩物丧志”的埃尔利希却搞出了大名堂。埃尔利希发现,与布匹被均匀染色不同,苯胺这种有机化合物染料只对细胞的部分区域染色,十分“挑剔”,也就是说,苯胺只能与细胞的部分特殊结构结合。那这些特殊结构又有什么蹊跷呢?
随着研究的深入,埃尔利希发现,不同的细胞简直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些细胞“好酸”(酸性),有些“馋碱”(碱性),还有些细胞“口味寡淡”(中性)。这些初步研究成果为检测不同的免疫白细胞提供了工具:在正常情况下,被酸性染料上色的为嗜酸性粒细胞,占人体免疫系统中白细胞总数的0.5%—5%,中性粒细胞则“家大业大”,是免疫系统中含量最丰富的白细胞(占比40%—60%),而相比之下嗜碱性粒细胞就显得形单影只,占比不到1%。看到这些专业词汇,是不是有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没错,这就是体检报告中血常规检测的部分指标。
当然,免疫细胞研究只是故事的序幕,埃尔利希同时也朦朦胧胧地形成了细胞特异性结合分子的模糊概念。也就是说,每个细胞好比一把锁,每一把锁都有一把对应开启的钥匙。
埃尔利希将钥匙和锁之间的结合称为“亲和力”,它不仅存在于染料和细胞之间,也存在于其他化学物质和细胞之间。埃尔利希提出,药物要发挥作用,必须被绑定结合,这是现代医学靶向疗法的理论基础。
既然染料能特异性地结合细胞,一个奇思妙想就诞生了:如果某种染料既能特异性地结合病原体,又恰好有毒性,那岂不是能“毒死”病原体,成为灵丹妙药?
1891年,埃尔利希开始研究针对疟疾病原体的染料。测试几十种染料后,他发现一种叫亚甲蓝的染料,不仅能染色疟疾病原体,还有一定的毒性,完全符合他寻找药物的标准。于是,埃尔利希迫不及待地在几位疟疾患者身上进行测试,并成功治愈其中两人。至此,世上第一款完全经由人类设计的药物问世,出乎所有人意料,它竟然是一款深蓝色的化学染料。
亚甲蓝的研发成功,给了埃尔利希巨大的鼓舞和底气,于是,他向人类历史上最恶毒的顽疾之一——梅毒,发起了进攻。
15世纪,梅毒在法国军队中暴发,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暴发。之后,梅毒席卷整个欧洲,成为传染性最强的顽疾之一,上百万欧洲人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
梅毒还没被正式命名前,欧洲各国互相“甩锅”,意大利人称之为“法国病”,法国人则叫它“意大利病”。浩劫面前,各种离奇的治疗方案层出不穷:异想天开地希望蒸桑拿将梅毒蒸出去,江湖骗子兜售含有水银的巧克力饮料来治疗梅毒。虽然水银能杀死梅毒病原体,使得症状缓解,但众所周知,水银对人体也有毒。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巨大的痛苦面前,患者不得不饮鸩止渴,因而当时坊间流行一种说法,“一夜风流情,一生水银伴”。
1899年,埃尔利希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法兰克福实验医疗研究所所长。当时,埃尔利希正带领一批专家寻找治疗非洲昏睡症的药物。研究发现,这种病的病原体是锥体虫,而锥体虫也可以感染老鼠。埃尔利希和实验助手、年轻的日本细菌学家秦佐八郎合成、筛选了数百种砷苯化合物(有毒),对上万只老鼠进行实验,最终在1909年发现,第606号化合物洒尔佛散(Salvarsan,又称砷凡纳明)能杀死老鼠血液中的锥体虫。有说法称,是由于之前遭受了605次实验失败,这个化合物才取“606”为代号,这一说法也成为科学家不畏失败、锲而不舍的经典案例,曾被多次引用。但是,也有说法表示,“606”的命名与此无关。
早在四年前的1905年,美国生理学家霍夫曼(Erich Hoffmann)就发现了梅毒的病原体梅毒螺旋体。秦佐八郎进一步找到了梅毒螺旋体感染兔子的方法。于是,埃尔利希指导秦佐八郎去测试洒尔佛散能否治疗梅毒。
1909年,在治疗梅毒患者的临床试验中,洒尔佛散效果显著,一夜成名。埃尔利希称其为“魔法子弹”。1910年,洒尔佛散上市,成为第一个治疗梅毒的有机药物,开化学疗法之先河。
洒尔佛散上市后迅速成为世界上处方最为广泛的药物之一。然而,皮疹、肝损伤等副作用的报道也随之而来,埃尔利希因此遭受了侮辱性指控。但是他化压力为动力,在1912年推出了改良版洒尔佛散(Neosalvarsan),代号“914”。
“606”和“914”两款药物一直保持着治疗梅毒的重磅药物的地位,直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首个抗生素盘尼西林(又称青霉素)问世。巨大的成功让埃尔利希成为公众英雄,好莱坞还紧跟节奏拍了一部电影——《埃尔利希博士的魔法子弹》。这部影片在第1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原创剧本”提名。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埃尔利希声名鹊起后,一小群持不同观点的人宣称洒尔佛散是一种危险药物,又指责埃尔利希是个牟取暴利的骗子,甚至从其他研究人员那里窃取荣誉。埃尔利希的朋友们坚持认为,这场学术圈内的“洒尔佛散之战”损害了埃尔利希的健康,并最终导致他于1915年去世,享年61岁。
因为洒尔佛散的巨大成功,20世纪早期最大的几个药物研发实验室,特别是莱茵河畔的几家德国公司,对合成药物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埃尔利希也得以继续推广他的“魔法子弹”概念,并将目光转向了癌症。
借鉴以往的成功模式,埃尔利希的目标就是找到和癌细胞亲和力高的化合物。然而问题来了:针对病原体的化合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病原体和宿主细胞差异甚大。但在埃尔利希生活的20世纪初,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的差异化认知并不明确,因此埃尔利希的探索没有理论指导,完全是大海捞针,很难找出区分敌我的“魔法子弹”,因此他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埃尔利希去世后,学术界对治疗癌症“魔法子弹”的追寻却从未停止。先是针对癌细胞旺盛繁殖的特性,大量化疗药物走上历史舞台。紧接着,伴随着癌症生物学的迅猛发展,癌细胞与正常细胞的差异化特征也慢慢被揭示出来,至此,靶向药隆重登场。
抗原和抗体是我们了解免疫系统必须掌握的概念。抗原是指能诱发免疫反应的物质。抗体则是机体由于抗原刺激,而产生的具有保护作用的蛋白质。抗体特异性高,是导航的一把好手,可将化疗药物护送到癌细胞的表面,最终成为靶向药的主将。有了抗体的导航,化疗不再盲目发射,而是更有针对性地狙击。虽然子弹(化疗药物)是一样的,但有了靶向的属性,因此属于靶向化疗的范畴。于是,真正意义上的“魔法子弹”终于梦想照进现实,ADC的概念进入成熟期。
ADC由三部分组成:特异性识别癌细胞的抗体、杀伤力极强的毒素(比如化疗药物),以及将两者串(偶联)起来的连接子。对比埃尔利希的“魔法子弹”,抗体的功能就是实现特异性结合(亲和力高),而毒素就是有毒的化合物。
ADC有一套非常严谨规范的工作流程:抗体带着毒素自由飞翔,用火眼金睛发现癌细胞后便牢牢抓住(特异性结合)。癌细胞被ADC攻击后,直接启动胞吞作用,自以为将ADC“吃”进肚子就可以高枕无忧。然而,被癌细胞吞食的毒素,就像潜入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等在癌细胞内部亮出金箍棒,搅得天翻地覆。

方到此时,癌细胞才后知后觉,原来吃了个祸害,只好自取灭亡!
很显然,ADC比普通化疗更强大、更精准,但它的研发之路特别曲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限于技术,ADC只停留在概念阶段,毕竟再高明的魔法,如果抗体和毒素没有备齐,也“憋”不出什么大招来。20世纪50年代,法国免疫学家马特(G. Mathe)等首次将从老鼠体内提取的抗鼠白细胞免疫球蛋白和甲氨蝶呤(毒素)偶联用于治疗人类白血病患者,拉开了ADC的研究序幕。然而,动物来源的抗体会引起人体免疫反应,使得疗效减弱,副作用也大。因此,ADC研究刚一启动就直接“卡壳”了。
好在这次停滞并不算久。20世纪80年代,抗体人源化技术诞生,ADC用于治疗癌症患者的临床试验才正式开启,不过早期的ADC基本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在2007年,《纽约时报》公开点名了几家“僵尸”生物技术公司追求单一技术路线,“烧起钱”来不客气,却长年不见盈利,其中就有两家ADC研发企业Immunomedics和ImmunoGen。庆幸的是,这些“僵尸”咬紧牙关不放弃:2020年,Immunomedics研发的ADC获得美国监管部门认可后,总算修得正果,后该公司被美国知名的一线药物研发公司吉利德以210亿美元巨额收购;而ImmunoGen也是一路披荆斩棘,经历了大幅裁员、贷款求生等挫折后,2023年5月30日宣布,其治疗卵巢癌的药物Elahere在临床Ⅲ期获得积极的关键数据。消息一出,该公司股价当天暴涨。
如今,回首ADC的研发之路,我们会更深刻地理解药物研发的艰辛与本质。
第一代ADC在2000年登上历史舞台,名为Mylotarg,用于治疗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大多新技术的第一代产品很容易因为各种缺陷成为“炮灰”,Mylotarg也没能逃脱这个魔咒,因为安全隐患以及上不了台面展示的临床益处,它只能在2010年灰头土脸地退市。
按照ADC的理念,乍一看去,Mylotarg的设计并没有什么问题。Mylotarg选择了CD33抗原和卡奇霉素(毒素)偶联,两者分工非常明确:CD33抗原遍布在85%—90%的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癌细胞表面,CD33抗体负责导航并瞄准CD33抗原,抗体和抗原特异性结合后,卡奇霉素乘虚而入,发挥其药效。拿放大镜仔细瞅瞅,发现原来是貌似不起眼的连接子坏了好事。
就ADC而言,一个优秀的连接子必须懂得收放自如:进入癌细胞前,要经受住血液循环洪流的考验,一手拽紧抗体,一手牵好毒素,但凡松懈一点,就好比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没能拉住的毒素会漫无目的地瞎捣乱,误伤正常细胞,引发副作用。这就是第一代ADC的致命问题,连接子不牢固,结果自己还没到癌细胞跟前,走一路,毒素就掉一路,祸害一路。
如果ADC能顺利遇到癌细胞,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届时,ADC被癌细胞内吞后,途经内体这个中转站,再抵达溶酶体。这个时候,连接子经受不住溶酶体内部水解酶的拆散(分解),该放手时就放手,和毒素就此告别。毒素终于变身孙悟空,完成自己的终极使命,快、准、狠地给癌细胞致命一击。
当然,在选择抗体和毒素上也有不少学问,比如抗体亲和力并不是简单粗暴地越高越好,而是需要有个最优的平衡点。对于毒素来说,大前提就是要足够“彪悍”,至少要比传统化疗药强上几百上千倍,毕竟癌细胞的内吞能力有限。此外,经营抗体和毒素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很微妙,难度甚至不啻于处理两性关系。
吸取第一代ADC的研发教训后,十年磨一剑,第二代ADC维布妥昔单抗(商品名安适利)在2011年出现。安适利在连接子上有明显的进步。其间,单克隆抗体以及毒素的开发也没闲着,继续平行发展,取得的成果包括提高了抗体的癌细胞靶向性,减少了和健康细胞的交叉反应等。随后不久,在癌细胞,比如靶向乳腺癌细胞上高表达的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简称HER2)靶向的ADC曲妥珠单抗(商品名赫赛汀)在2013年顺利获批,开启了ADC向实体瘤挑战的新篇章。新偶联物思美曲妥珠单抗与 HER2 单抗单独治疗的复发风险比,下降了50%,这一结果让人振奋。
当然,第二代ADC也并不完美,比如毒素和抗体上的结合比例过于随机。从理论上说,每个抗体能连上的数量在0—8。如果太过随性,有些抗体没有连接任何药物,不仅“裸”着上战场寡不敌众,还会和其他装着真枪实弹的ADC竞争。反过来,要是抗体承载的药物太多,容易引起ADC聚集并被快速清除。至于药物和抗体的黄金比例还处在小马过河的阶段,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核心就是优秀的ADC设计讲究的就是一个平衡和优化。
因此,第三代ADC追求的便是实现可控的特定位点偶联,以此进一步提高治疗窗口,比如2017年和2019年相继获批的奥加伊妥珠单抗(商品名贝博萨)和德曲妥珠单抗(商品名优赫得)等。
至此,老、中、青三代ADC齐聚一堂。
如今,特定位点偶联成为第三代ADC的标配。不少企业还在继续追求卓越,时不时抖了个小机灵,琢磨着怎么利用旁观者效应来进一步提高ADC的疗效。
说起旁观者效应,那绝对是撒手锏。开发抗癌药物面对的很大挑战就是肿瘤组织的异质性。所谓异质性,指的是肿瘤内部像个万花筒,聚集着形形色色的癌细胞。以乳腺癌为例,有些癌细胞携带高水平的 HER2 ,有些水平很低,有些甚至没有。对于没有 HER2 的癌细胞来说,靶向 HER2 的ADC如果只是有的放矢,自然没什么威慑力。
既然ADC自带子弹,是不是可以让子弹飞久一点?于是旁观者效应隆重登场:ADC进入癌细胞后,如果毒素能穿透 HER2 阳性癌细胞跑到外面去巡视一圈,那么,对于附近的癌细胞,管它有没有 HER2 ,都得伏法,这就是旁观者效应。也就是说,看热闹的旁观者,如果离被攻击癌细胞很近,很容易被一并“干掉”。
要想淋漓尽致地发挥旁观者效应,有三个前提:第一,连接子可以裂解,这样毒素才能被释放;第二,毒素有很好的细胞膜穿透能力;第三,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脱离连接子的毒素半衰期(药物浓度下降一半所需要的时间)不能太长,也就是说,毒素不能撒腿跑太远,否则容易误伤健康细胞。
近些年,把旁观者效应琢磨得最透彻的公司当数日本的跨国原研制药集团的第一三共(Daiichi Sankyo)。2022年,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的年会上,第一三共研发的药物优赫得的数据公布后,因为太过亮眼,会场罕见出现了全体起立鼓掌的盛况。优赫得作为靶向 HER2 的明星药物,其成绩斐然众所周知,且更为惊喜的是,优赫得对 HER2 低表达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也有效,和传统化疗比较,死亡风险降低了36%。要知道, HER2 低表达患者在整个乳腺癌中占比45%—55%,优赫得的出现给这些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优赫得强悍的旁观者效应。
除了ADC研发内部精益求精,“外卷”也持续升级。行业里有句话叫“万物皆可偶联”,其中一马当先的就是多肽偶联药物(Peptide Drug Conjugate,简称PDC)。PDC和ADC只有一字母之差,原理也差不多,就是将抗体换成多肽。
多肽和抗体相比,最大优势是小巧玲珑。分子量小,意味着来去更自如,穿透力就更强。目前国际上已经有几款PDC上市,比如2021年2月加速获批的美氟苯甲酰胺(PEPAXTO,商品名美氟芬),用于治疗复发/难治多发性骨髓瘤,国内也有部分企业正蓄势待发。
当然,PDC也有它的软肋,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个头小,稳定性就会较弱,半衰期也短,不过PDC领先企业,比如Bicycle Therapeutics,有独创一套技能,通过双环肽化学修饰加以改善。多肽被打了个环,也就稳定多了。
和PDC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抗体前体偶联药物(Probody-Drug Conjugate)。为示区别,暂且叫它PBDC。PBDC的设计理念就是给抗体加个遮蔽肽口罩(Mask)。神奇之处在于,只有等PBDC抵达肿瘤微环境,癌细胞相关的蛋白酶才能将口罩掀开(切割),这样脱掉口罩的抗体就能大展拳脚地攻击癌细胞。健康组织没有此类蛋白酶,口罩拿不下来,PBDC就没有攻击性,因此有了口罩,就相当于上了双保险。
既然“万物皆可偶联”,那化疗并肩作战的兄弟放疗又该如何入场?没错,放疗也紧跟步伐,进行了更新换代,有了抗体放射性核素偶联(Antibody Radionuclide Conjugates,简称ARC)的初步探索。也就是说,抗体连接的不是毒素,而是放射性核素。更有意思的是,放射性核素兼具诊断和治疗的双重功能,其潜力不可小觑。
如果将抗体类药物研发比作爬树摘水果,那以ADC为代表的“魔法子弹”则是高高挂在树顶的那个,想拿下并不容易,必须得解锁各种技能和用上创新思维。不仅得配对好子弹和导航,还得处理好它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什么时候合、什么时候分,都需要谨慎设计。
挑战虽大,但“魔法子弹”带来的可能性和前景也不可限量。除癌症以外,“魔法子弹”在风湿病治疗的探索也已进入临床阶段。一代代ADC推陈出新,PDC也不甘示弱,PBDC虽有待临床验证,但在理论上给“魔法子弹”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实,药物研发说复杂确实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单之处就在于只要逻辑正确,能不能实现,只需要等待技术的发展。这也是“魔法子弹”历经百年还能焕发青春的原因。
跨越一个世纪的“魔法子弹”,期待它飞得更久更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