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孕有多容易呢?毕竟,焦虑的父母经常对青春期的孩子强调:“只需要一次!”在一个年轻人生活中的某个时期,他们可能会通过避孕或者禁欲来尽量避免怀孕。而当你终于想组建一个家庭,把另一个生命带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和伴侣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尝试,但是你们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成果。性教育课程和父母经常告诉我们,怀孕是很容易的,这是避孕行业的骗局吗?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给定的一个月里,怀孕的机会有多大?这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迄今为止,最好的尝试来自挖掘夫妇在试图怀孕时提供的详细记录。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一项研究涉及221对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夫妇,研究者记录了他们何时进行性行为,以及女性何时排卵——这是通过黄体生成素的激增来标记的,对应着卵泡释放卵子。在另一项于1993—1997年间在意大利进行的研究中,193名女性记录了她们何时进行性行为,以及她们对宫颈黏液的观察结果(将其分为4类):(1)干燥,(2)湿润或湿感,(3)浓稠、奶油状白色黏液,(4)湿滑、可拉伸的清水状黏液。
20世纪90年代最大的一项研究——欧洲每日生育能力研究,追踪了782名欧洲女性试图怀孕的情况。研究人员收集了超过7 200个月经周期的数据,其中女性记录了她们何时进行性行为,以及她们对所谓的基础体温(静息状态下)和宫颈黏液的描述。在追踪女性基础体温的情况下,排卵时体温会上升不到0.5摄氏度,这可以用足够灵敏的温度计检测到。所有的研究都捕捉到了关键的参数:经过所有这些努力,是否达到了怀孕的目的。
这些调查提供了大量数据,但科学家需要用一种方法来挖掘其中的趋势。问题在于,在一个受孕周期中,可能几天都有性行为,所以很难知道是哪一次性行为导致受孕。幸运的是,通过使用简单的概率规则,可以对每一天的可能性进行一些估计。第一次尝试应用这些技术是在1969年,美国的研究人员使用了241对英国已婚夫妇收集的数据,其中女性记录了她们的基础体温,并记录下来她们何时进行性行为。 [1] 使用统计技术来确定一个周期中可能导致成功怀孕的概率之后,研究者发现性行为的理想时间是排卵前两天,受孕概率为30%,而排卵后的受孕概率几乎为零。这个“可能性”模型在其他研究中得到了改进,包括1980年的一项研究,该研究使用了相同的数据,发现当每天进行性行为并至少持续6周时,怀孕的概率为49%。 [2]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杜克大学统计学家戴维·邓森和他的同事采取了一种略有不同的方法。他们使用了一种强大的技术——贝叶斯统计
 ,来分析女性的月经周期和怀孕的最佳时间。众所周知,不同女性的月经周期长度不同,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月份也有所不同。但是统计分析显示,即使是月经周期为规律的28天的女性,排卵日也可能会变化。通过检查,北卡罗来纳州研究数据中大约700个长度为28天的周期,只有10%的周期是在第14天排卵的——这是你通常期望排卵发生的日子。
[3]
他们还发现,一个周期中的受孕期为6天——排卵前5天和排卵当天。
,来分析女性的月经周期和怀孕的最佳时间。众所周知,不同女性的月经周期长度不同,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月份也有所不同。但是统计分析显示,即使是月经周期为规律的28天的女性,排卵日也可能会变化。通过检查,北卡罗来纳州研究数据中大约700个长度为28天的周期,只有10%的周期是在第14天排卵的——这是你通常期望排卵发生的日子。
[3]
他们还发现,一个周期中的受孕期为6天——排卵前5天和排卵当天。
如早期研究所示,排卵后第一天的受孕概率几乎为零,所以在那个时候试图怀孕没有多大意义。这项研究也证实了时间的关键性,排卵前一天怀孕的概率高达30%。北卡罗来纳州研究的另一个有趣发现是,夫妇之间的性行为频率在排卵期达到高峰。邓森和同事发现,6个受孕日的性行为频率比所有其他非经期日高24%。然后,性行为频率在排卵后一两天急剧下降。 [4]
由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布鲁诺·斯卡尔帕领导的对意大利研究的贝叶斯统计分析发现,如果夫妇忽略了宫颈黏液的指标以及月经日历,只是每周进行一次性行为,那么平均怀孕等待时间为4个周期。 [5] 然而,如果他们观察黏液,但只在它处于第4种类别时且在第13天到第17天之间进行性行为,那么受孕所需的性行为天数平均为2.42,受孕概率为35%。这意味着平均需要3个周期能怀孕。至于那些对黏液得分不那么挑剔的夫妇,他们在第13天到第17天之间、黏液处于第3或第4种类别时进行性行为,受孕概率为47%,这意味着只需要等待两个周期。所以,对那些关注日历的人来说,每隔一天进行一次性行为就够了。但是贝叶斯统计分析显示,如果你真的想优化受孕所需性行为的次数,那么关注宫颈黏液的迹象和日历是快速怀孕的有效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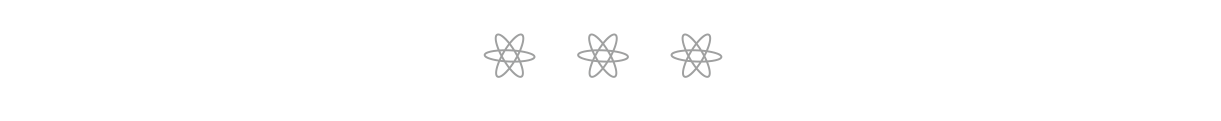
你可能经常在新闻中听到关于“人口定时炸弹”的问题,你那些渴望有孙子孙女的父母也可能经常提起这个问题。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35岁以后甚至40岁出头才生孩子,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吗?毕竟,你仍然可以看到年纪较大的父母推着婴儿车——只是在评论祖父母和孙子孙女共度美好时光有多棒之前,你要确认他们是不是父母。
根据欧洲的一项研究数据,邓森和他的同事发现,如预期的那样,19~26岁的女性怀孕概率明显高于27~34岁的女性,而35~40岁的女性怀孕概率进一步下降。 [6] 至于在12个周期内无法怀孕的女性(如果她们每周进行约两次性生活)的怀孕概率,19~26岁的女性为8%,27~34岁的女性为13%,35~39岁的女性为18%。所以,虽然怀孕概率确实随年龄增大有所下降,但与20岁出头时相比,到了40岁并不会断崖式下跌。
这项研究还探讨了男性的年龄对生育力的影响,发现年龄对35岁以下男性的生育力并无影响,但对35岁以上男性存在影响。如果男性和女性都是35岁,那么,如上所述,12个周期内无法怀孕的概率是18%;但如果男性年龄是40岁或者更大,这个比例就会变成28%——这对仅仅5年的年龄差距来说是一个大幅度的跳跃。无法生育的夫妇的比例是1%,不随年龄变化,这表明生育力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衰退。这项研究还表明,一对夫妇不太可能无法生育,他们可能只是很难自然怀孕。所以,医生可能会说在考虑生育治疗前要坚持尝试怀孕12个月,这是经过贝叶斯统计分析结果证实的。
现在,强大的贝叶斯统计技术正被用在孕期应用程序中,这些应用程序声称只需每天输入基础体温,就能准确地识别出排卵期。然后,这些知识可以用来指导在哪一天或那一天之前进行性行为,或者作为避孕的一种方式。反过来,这些应用程序也在产生大量可供研究的数据。2019年,Natural Cycles应用程序的开发者对近12.5万名用户的超过60万个周期进行了分析。
 他们发现,用户的平均月经周期长度为29.3天,随着年龄从25岁增长到45岁,每增长一岁,平均月经周期长度就减少0.19天。
[7]
对于体重指数(BMI)大于35的女性,月经周期长度的平均偏差是0.4天,比被归类为“正常”(BMI为18.5~25)的女性高出14%。这些应用程序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分析结果,不仅可以进一步揭示月经周期相关信息,还可以揭示生育能力,即在一个月经周期内怀孕的可能性。
他们发现,用户的平均月经周期长度为29.3天,随着年龄从25岁增长到45岁,每增长一岁,平均月经周期长度就减少0.19天。
[7]
对于体重指数(BMI)大于35的女性,月经周期长度的平均偏差是0.4天,比被归类为“正常”(BMI为18.5~25)的女性高出14%。这些应用程序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分析结果,不仅可以进一步揭示月经周期相关信息,还可以揭示生育能力,即在一个月经周期内怀孕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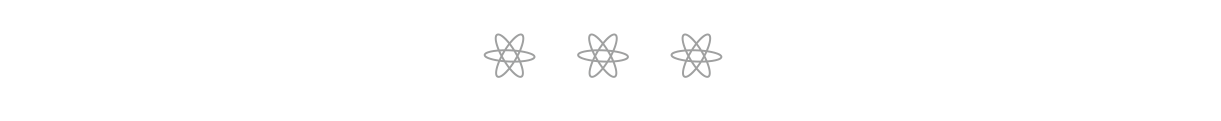
一旦你和你的伴侣开始尝试怀孕的旅程,第一站就是检测是否成功。当我和妻子克莱尔发现自己即将迎来第一个孩子时,我们欣喜若狂。我仍然记得那个早晨,我凝视着验孕试纸上淡淡的蓝线,难以置信。我越看那个标记,它的颜色就变得越深,尽管它仍然比旁边的“对照线”要淡得多。这次测试是在预期的月经前几天做的,所以我们怀疑是不是臆想在捉弄我们。考虑到超市里验孕试纸的“买一送一”优惠,我的妻子在第一次测试之后又做了几次后续测试。我们看到线条变得更加明显,虽然有点儿花钱,但这是一种无害的乐趣。毕竟,这让我们接受了怀孕的事实,所以,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以计划在9个月后的凌晨3点看什么录像带了。
第一次测试是在12月初完成的,圣诞节期间,我们和家人住在一起,我的妻子决定再进行一次测试。毕竟,一条漂亮的蓝线会是一个很好的圣诞礼物。这个程序在圣诞节晨尿时正确地进行了,对照线开始变蓝。我们等待另一条线出现。等待……又等待。什么都没有。过了一会儿,一条颜色非常浅的线出现了,就像我们一个月前做的那次测试一样,但是这条线的颜色没有继续变深。我和妻子两个人看着对方,没有说一句话。我们的脑中思绪翻涌。在之前出现过所有那些明显的线条之后,我们怀疑会不会正在或已经失去了这次怀孕机会?我们很崩溃。这是一个糟糕的圣诞节早晨。
但是,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都要归功于现代验孕试纸的一种特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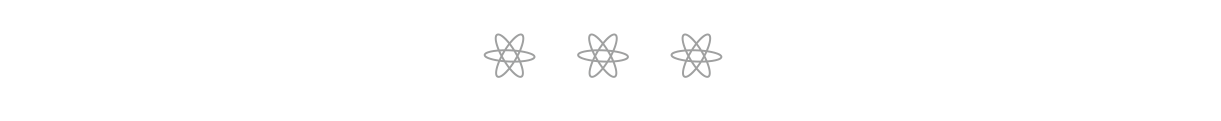
当今的妊娠试验非常简单,几分钟就能得出结果。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人们认为,最早的妊娠试验约在公元前1350年由古埃及人进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考古学家发现了用象形文字写的记录,其中详细记载了这种试验的规则。几天内,女性会在大麦和小麦等各种谷物上小便。如果有一粒种子发芽并生长,就意味着这个女人怀孕了,而且这种方法甚至可以预测孩子的性别。如果大麦发芽,那就是男孩;如果小麦发芽,那就是女孩。
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研究试图用怀孕女性的尿液重复这种方法,结果显示,这种种子测试的准确率大约为70%。对这种原始的方法来说,这个准确率并不差(尽管它无法准确预测孩子的性别,所以不要对你的下一次性别揭晓派对抱有任何期待)。 [8] 这种测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怀孕女性尿液中雌激素的含量升高,刺激了谷物发芽。
从女性在小麦和大麦上小便到出现更准确的测试方法,用了数百年的时间。这次,它依赖于检测另一种关键的妊娠激素: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现在我们知道,使用这种激素进行检测要好得多,因为它在妊娠期间由囊胚外表面的滋养层细胞产生——这些细胞之后会形成胎盘。
 在胚胎植入子宫内膜后,HCG水平最初每隔几天就会翻倍,大约在受孕后10周达到峰值。
在胚胎植入子宫内膜后,HCG水平最初每隔几天就会翻倍,大约在受孕后10周达到峰值。
最初,这种激素是在1928年由德国妇科医生塞尔马·阿什海姆和伯恩哈德·桑德克在怀孕女性的尿液中发现的。他们每天两次向5只雌性小鼠体内注射3毫升怀孕女性的尿液,持续注射三天,发现这样可以刺激小鼠的卵巢,使它们进入发情期。小鼠卵巢增大表明怀孕;如果卵巢保持正常大小,那么可能没有怀孕。不幸的是,为了检测是否有反应,必须杀死小鼠,解剖并检查卵巢。这种以研究者姓名首字母命名的“A–Z测试”是对发芽种子测试的一大改进,准确率大约为98%。 [9]
大约在同一时期,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美国医生、生殖生理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在兔子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反应。通常,他会使用两只兔子进行测试,将大约8毫升的人类HCG注入它们的耳静脉。HCG的存在会在兔子的卵巢组织中形成被称为黄体和血体的结构。黄体是一个小的黄色团块,它会释放孕酮等激素,并在排卵后的卵泡附近形成。血体则在排卵后形成,在卵泡塌陷并充满血液后形成血凝块。
遗憾的是,就像A–Z测试中一样,为了检测是否发生了这种变化,必须杀死兔子并检查它们的卵巢。但这种方法比小鼠身上进行的测试快,只需要一天就能完成。
 “这非常可靠,”弗里德曼告诉《纽约时报》,“唯一更可靠的测试就是等待九个月。”
[10]
“这非常可靠,”弗里德曼告诉《纽约时报》,“唯一更可靠的测试就是等待九个月。”
[10]
大量屠杀兔子和小鼠的行为总让人感觉不必要,人们开始寻求更人道的方法。英国动物学家兰斯洛特·霍格本登场了。20世纪20年代末,他在开普敦大学研究非洲爪蟾,主要关注这种动物的激素产生过程。当霍格本于1930年返回英国时,他带回了一些非洲爪蟾,并将其中一些送给了他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同事弗朗西斯·克鲁。在一系列实验中,克鲁将孕妇的尿液注射到非洲爪蟾的背淋巴囊(位于其身体的顶部),发现大约12个小时后非洲爪蟾产生了卵或精子。这种方法在确定怀孕方面非常准确,成功率达到99.8%。
[11]
它比之前的方法更快速,关键是不涉及杀死非洲爪蟾,让它们得以重复使用。“谢谢你关于某女士妊娠试验的报告。你可能会感兴趣的是,一位有多年经验的全科医生、一位妇科专家和一只非洲爪蟾,只有非洲爪蟾的判断是正确的。”一位医生写信给霍格本,赞扬这种新方法。

然而,非洲爪蟾测试也有阴暗的一面。由于其速度快且可重复使用,数以万计的非洲爪蟾在几十年里被测试过,当它们变得多余时,它们就被简单地遗弃在野外,并形成自己的群落。更大的问题是,它们带来了一种致命的真菌——蛙壶菌,这种真菌影响了以前从未接触过这种病原体的本土蛙种。据估计,由于真菌入侵,全球多达200种蛙类灭绝。 [12]
使用动物进行妊娠试验的时代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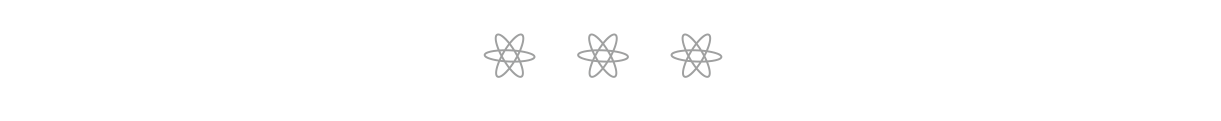
有小孩的人都知道,孩子们在吸引各种病菌方面的效率如何之高,然后他们会慷慨地将这些病菌带回家,感染其他人。在冬季,孩子会不断打喷嚏,或者黏液分泌旺盛,因为他们发育中的免疫系统正在抵抗疾病。当感染发生时,身体的免疫系统会遭遇入侵的病毒,并设法将其排出。一种防御方式是产生抗体,这些小的叉状蛋白质会与病毒的受体结合,抑制其活性。有时候,病毒消失后这些蛋白质还会在血液系统中停留一段时间,如果病毒在短时间内第二次出现,那么抗体会迅速识别出来并警告免疫系统,使免疫系统占据优势,这就是一些疫苗的工作原理。
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开始开发用于检测尿液中HCG的妊娠试验,他们使用了能与HCG分子结合进而检测HCG的抗体。通过抗体检测某种分子是否存在的测试被称为“免疫分析”(又称免疫测定),这种方法在1959年首次用于检测胰岛素,从那时起就被用来检测癌症、非法药物、病毒和其他微生物等。
 将免疫分析用作妊娠试验,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在含有HCG抗体的溶液中加入尿液。20世纪60年代初的试验中,使用了在实验室中涂覆HCG抗体的兔红细胞(所以,此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动物产品)。试验用到的另一种主要成分是涂有HCG的绵羊红细胞。这两种组分被放在一起,如果女性的尿液中不含HCG,那么来自兔血的抗体会与绵羊血上的HCG结合,形成血块。如果女性的尿液中含有HCG,那么HCG会与兔抗体结合,导致绵羊的红细胞从溶液中脱落——脱落的绵羊红细胞会在容器底部形成一个红褐色的环。和古埃及的大麦苗是怀孕的象征一样,到了20世纪中叶,一圈绵羊血成了怀孕的象征。
将免疫分析用作妊娠试验,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在含有HCG抗体的溶液中加入尿液。20世纪60年代初的试验中,使用了在实验室中涂覆HCG抗体的兔红细胞(所以,此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动物产品)。试验用到的另一种主要成分是涂有HCG的绵羊红细胞。这两种组分被放在一起,如果女性的尿液中不含HCG,那么来自兔血的抗体会与绵羊血上的HCG结合,形成血块。如果女性的尿液中含有HCG,那么HCG会与兔抗体结合,导致绵羊的红细胞从溶液中脱落——脱落的绵羊红细胞会在容器底部形成一个红褐色的环。和古埃及的大麦苗是怀孕的象征一样,到了20世纪中叶,一圈绵羊血成了怀孕的象征。
考虑到任何对容器的移动都会破坏结果,这些试验最初是在精心控制的实验室环境中进行的。技术人员会将装有血尿混合物的容器排列好,并将它们直接放在镜子上方,以便他们轻松看到是否有血环出现。这个试验需要大约两个小时才能完成,如果在预计排卵日后的22天进行,其准确率大约为99.8%。 [13] 唯一的缺点是,它需要你去看医生并提供尿液样本,然后等待一两周才能拿到结果。
20世纪60年代的一场妊娠试验革命始于玛格丽特·克兰的努力,她被新泽西州的欧加隆医药科技公司聘为自由平面设计师,负责为新的化妆品线设计包装。当她参观公司进行妊娠试验的实验室时,她见到了一排排悬挂在镜子上方的试管。了解到其中进行的是妊娠试验后,克兰确信这个过程可以被小型化和标准化,足以在家中完成。她开始设计一个包含所有实验室测试基本元素的家用妊娠试验。她向欧加隆的管理层推销这个设想,最终公司接受了这个想法,并在1971年获得了专利,将克兰列为发明人。
 尽管当时有些医生对在家中进行此类试验表示反对,但第一个家用试验套件于1978年在美国药店售卖,价格约为10美元。
尽管当时有些医生对在家中进行此类试验表示反对,但第一个家用试验套件于1978年在美国药店售卖,价格约为10美元。
 欧加隆的研究显示,家用版本的准确率约为97%,虽然不如实验室版本高,但至少可以在自家的卫生间里完成。
欧加隆的研究显示,家用版本的准确率约为97%,虽然不如实验室版本高,但至少可以在自家的卫生间里完成。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科学家开始研究不涉及动物血液的试验,通过改进合成抗体的设计,使其能够检测到HCG。现代妊娠试验的准确性在于,它们利用了HCG分子上的两个特定区域(表位),抗体可以附着在这两个区域。这两个HCG亚基分别是α亚基和β亚基,是1970年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的。 [14] HCG分子的α亚基与其他激素的α亚基相同,如脑垂体前叶产生的黄体生成素,这是男性和女性生殖功能相关的重要激素。然而,β亚基是HCG独有的。
最终,科技的进步使得试验所需组分可以放在一种简单的条带材料上。1988年,联合利华推出了它的“一步式”HCG夹心免疫分析法。条带的一端吸收尿液(通过浸入尿液或使用者直接在条带上排尿),首先进行过滤,以确保只有尿液通过。尿液渗透到条带的另一端,到达“反应区”。这部分区域包含能连接到HCG的α亚基的活动抗体。这些抗体还附着有染成蓝色的乳胶珠。然后,HCG–抗体组合随着尿液流向下一个区域——测试区
 ,这里是所有反应发生的地方。固定在这个区域的是更多的抗体,但这些抗体与HCG的β亚基结合。这种抗体是不动的,所以HCG的轨迹在此终止。随着越来越多的抗体被捕获,它们携带的乳胶珠开始积聚,这就是产生蓝线的原因。HCG分子被两种抗体夹在中间,解释了夹心免疫分析法的名称由来。
,这里是所有反应发生的地方。固定在这个区域的是更多的抗体,但这些抗体与HCG的β亚基结合。这种抗体是不动的,所以HCG的轨迹在此终止。随着越来越多的抗体被捕获,它们携带的乳胶珠开始积聚,这就是产生蓝线的原因。HCG分子被两种抗体夹在中间,解释了夹心免疫分析法的名称由来。
如果尿液中没有HCG,带有乳胶珠的抗体就会继续前进,不会与固定的抗体连接,也就不会出现蓝线。现在,抗体进入控制区,这个控制区包含不可移动的抗体。然而,这些抗体被设计成可以黏附于活动抗体而不是HCG分子。它们与抗体连接,然后乳胶珠再次积累,产生蓝色的对照线。所以,无论活动抗体是否吸附HCG,对照线都应该至少呈淡蓝色。如果不是这样,试验就出了问题。夹心免疫分析法是最快速、最简单的测试方法,而HCG至今仍然是我们检测早孕的最好方法。
 正如2006年某款早孕测试笔的一则电视广告所说:这是“你会尿在上面的最先进的科技产品”。
正如2006年某款早孕测试笔的一则电视广告所说:这是“你会尿在上面的最先进的科技产品”。

一些公司声称,他们的现代验孕棒可以早在预期中的月经缺席前6天就预测怀孕。尽管他们如此声称,但是事情总归是有限度的。月经来潮前4天的HCG平均水平约为0.5微克/升,这太低了,无法产生可靠的信号,因此即使使用现代验孕棒,准确率也只有55%。一天后,准确率提高到86%;到了本该月经来潮的当天,准确率达到99%,此时HCG的平均水平约为10微克/升。
 错过月经后4天,HCG水平为80微克/升。因此,无论你多么迫切地想看到结果,都应该稍稍等待一下。
错过月经后4天,HCG水平为80微克/升。因此,无论你多么迫切地想看到结果,都应该稍稍等待一下。

图4-1 现代妊娠试验示意图,显示尿液中存在HCG时会发生什么(改编自文献
 )
)
而且,怀孕后期进行测试的过度热情也可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让我们说回2014年圣诞节那天的妊娠试验。在克莱尔和我参加节日活动之前,我们通过“谷歌医生”进行了快速咨询。那时,我们了解到可能影响免疫分析的“钩状效应”。在妊娠试验中,这是指血液中的HCG水平过高,以至于超过了试纸的检测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有太多的HCG结合抗体,它们挤满了测试线上的不动抗体,因而无法正确地附着。这就像一群人试图冲向一扇门,结果只会陷入僵局。由于许多HCG抗体无法与不动抗体正确地形成夹心结构,乳胶珠无法正确传输,因此测试线比以前的颜色更淡。这种形成“正确的夹心结构”的需求,对于对照线上的抗体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因此这部分测试仍然有效。
从那一刻起,我们承诺不再进行更多的试验,而是尽量享受圣诞节。毕竟,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会有终极证据来证明即将有一个宝宝,那就是超声检查结果。
[1] Barrett, J.C., and Marshall, J.“The Risk of Conception on Diferent Days of the Menstrual Cycle.” Population Studies 23 (1969): 455–461.
[2] Schwartz, D., Macdonald, P.D.M., and Heuchel, V.“Fecundability, Coital Frequency and the Viability of Ova.” Population Studies 34, no.2 (1980): 397–400.
[3] Wilcox, A.J., Dunson, D.B., and Baird, D.D.“The Timing of the‘Fertile Window’in the Menstrual Cycle: Day Specific Estimates from a Prospective Stud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21 (2000): 1259–1262.
[4] Wilcox, A.J., Baird, D.D., Dunson, D.B., et al.“On the Frequency of Intercourse Around Ovulation: Evidence for Biological Influences.” Human Reproduction 19,no.7 (2004): 1539–1543.
[5] Scarpa, B., Dunson, D.B., and Giacchi, E.“Bayesian Selection of Optimal Rules for Timing Intercourse to Conceive by Using Calendar and Mucus.”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88, no.4 (2007): 915–924.
[6] Dunson, D.B., Baird, D.D., and Columbo, B.“Increased Infertility with Age in Men and Women.” Age and Infertility 103, no.1 (2004): 51–56.
[7] Bull, J.R., Rowland, S.P., Berglund Scherwitzl, E., et al.“Real-World Menstrual Cycle Characteristics of More Than 600 000 Menstrual Cycles.” NPG Digital Medicine 83 (2019). doi.org/10.1038/s41746-019-0152-7.
[8] Ghalioungui, P., Khalil, S.H., and Ammar, A.R.“On an Ancient Egyptian Method of Diagnosing Foetal Sex.” Medical History 7, no.3 (1963): 241–246.
[9] Herbert, E., and Simpson, M.“Aschheim-Zondek Test for Pregnancy—Its Present Status.” California and Western Medicine 32 (1930):145–148.
[10] Howe, M.“Dr. Maurice Friedman, 87, Dies: Created Rabbit Pregnancy Test.” New York Times , March 10, 1991.
[11] Well, G.R.“Lancelot Thomas Hogben, 9 December 1985–22 August 1975.”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 24 (1978): 183–221.
[12] Vredenburg, V.T., Felt, S.A., Morgan, E.C., et al.“Prevalence of 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 in Xenopus Collected in Africa (1871–2000) and in California(2001–2010).” PLOS One 8, no.5 (2013): e63791. doi.10.1371/journal.pone.0063791.
[13] Wide, L.“Inventions Lea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agnostic Test Kit Industry—From the Modern Pregnancy Test to the Sandwich Assay.” Upsala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110, no.3 (2005): 193–216.
[14] Swaminathan, N., and Bahl, Om.P.“Dissociation and Recombination of the Subunits of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40, no.2 (1970): 42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