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自然充满了图案。想象一下完美的、可复制的花瓣排列,幼儿在墙上用永久记号笔绘制的复杂的螺旋图案,或者斑马身上重复的条纹。即使只是伸出你的手臂,你也会看到双手各有5根形状几乎相同的手指。

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对自然界中所有这些不同的模式如何形成感到着迷。他并不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生物学家,而是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然后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数理逻辑博士学位。然而,当图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返回英国参加布莱切利园的密码破译活动时,他声名鹊起,那里的许多男人和女人夜以继日地工作,破译德国海军用于加密无线电通信的恩尼格玛密码机产生的通信编码。
在这些不畏艰难的密码破译努力之后,图灵继续了他对计算和人工智能的热情。他也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的兴趣:胚胎学。图灵这样做的灵感来自苏格兰生物数学家达西·温特沃斯·汤普森的工作,汤普森于1917年在邓迪大学学院(当时隶属于圣安德鲁斯大学)出版了经典著作《生长和形态》。 [1] 这本书研究了许多不同的主题,从树木的发育到骨骼结构和骨骼动力学。它还包含对形态发生的数学描述,形态发生是赋予生物形状的生物过程。尽管汤普森的一些想法当时遭遇了反对,但他坚信数学可以解释动物和植物等生物体的形成。 [2] 图灵同样确信这一点。正如计算机遵循一组代码指令一样,同样的基本逻辑也必然适用于生物体。
基于汤普森的思想,图灵专注于研究形态发生素(其分布控制组织发育模式的物质)如何在限定的空间中扩散。换句话说,从纯粹的理论角度来看,他寻找的是导致我们在自然界中看到的各种模式的展开机制。
图灵理论的主旨涉及在某个空间(比如发育中的胚胎)中扩散的两种竞争行为。一种是激活剂开启某些物质的产生过程,例如色素;而另一种是抑制剂阻止该过程的发生。图灵理论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当激活剂移动时,它不仅会复制自身,还会产生抑制剂。另一个特征是抑制剂的移动速度比激活剂更快。
这一理论简单而优雅,但它仍然带有一些看起来低劣的数学运算。1948年,图灵到了曼彻斯特大学,当时一台新计算机“Ferranti Mark 1”刚刚抵达,可以帮助他进行模拟,直观地展示他的数学理论的实际应用。图灵通过大量处理方程式表明,如果你从一点儿激活剂开始,通过调整激活剂和抑制剂的传播速度,就可以创造出无数种不同的模式,从简单的斑点、条纹到更复杂的排列,比如环状、斑驳的团状或迷宫图案。 [3] 扩散的几何形状也创造了它自己的可能性,例如,猎豹身上的斑点状图案在尾巴这样较薄的部分可以显示为条纹——动物身上本就如此。

图3-1 各种图灵模式的示意图
图灵的想法代表了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通常如何处理问题,那就是将其分解为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因此,他没有将该理论应用于生物学中的特定问题,并承认该理论有许多缺点。“这个理论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假设,”他在1952年的论文中写道,“它只是表明某些众所周知的物理定律足以解释许多事实。”遗憾的是,图灵无法进一步发展它。他因与同性伴侣的关系,被捕并被定以“严重猥亵”的罪名(20世纪50年代初,同性恋在英国是非法的,图灵是公开的同性恋者)。图灵被处以化学阉割的惩罚。1954年,就在他的理论发表两年后,41岁的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因此,他没有将该理论应用于生物学中的特定问题,并承认该理论有许多缺点。“这个理论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假设,”他在1952年的论文中写道,“它只是表明某些众所周知的物理定律足以解释许多事实。”遗憾的是,图灵无法进一步发展它。他因与同性伴侣的关系,被捕并被定以“严重猥亵”的罪名(20世纪50年代初,同性恋在英国是非法的,图灵是公开的同性恋者)。图灵被处以化学阉割的惩罚。1954年,就在他的理论发表两年后,41岁的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其他人继续了图灵的研究。1988年,当时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工作的苏格兰应用数学家詹姆斯·默里进一步发展了图灵的理论,并使用计算机建模表明反应扩散理论可以解释自然界发现的大多数动物的外表。 [4]
尽管图灵拥有天才般的想法,但生物学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看到它的可能性。即便如此,许多人也仍然怀疑一个相对简单的理论能否解释如此复杂的结果。相反,许多发育生物学家都被在伦敦大学学院工作的英国胚胎学家刘易斯·沃尔珀特20世纪60年代末设计的模型所吸引。该理论表明,细胞可以感知它们与胚胎中分子信号的潜在图谱有关的位置,这将导致不同结构的产生。它有点儿类似于儿童涂色书,一张轮廓图上的某些区域用数字来代表不同的颜色。轮廓图就是潜在图谱,当形态发生素扩散时,它会在每个区域沉积正确的“颜色”,从而构成整幅五彩斑斓的图画。
沃尔珀特的模型在现实系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个例子是果蝇身体的生成。果蝇是生物学家研究的模式生物,因为许多控制果蝇发育的基因与控制脊椎动物的基因相似。果蝇的身体不是由反应扩散机制产生的,而是由不同浓度的形态发生素(特别是 bicoid 基因对应的蛋白质)在全身扩散时产生的。
但是,图灵的模型并没有完全失败。2006年,瑞士生物学家在毛囊的位置排布中找到了图灵理论的明确证据。 [5] 事实证明,手上或爪子上的手指数可以完美地展示图灵模式。2012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基因组调控中心的生物学家詹姆斯·夏普和他的同事证明了用图灵的方法在小鼠身上产生手指的有效性。他们去除了一组被称为 Hox 的基因,这组基因是涉及许多发育领域的基因大家族的一部分,功能包括制订身体计划。当他们一一敲除39个 Hox 基因时,小鼠的手指越来越多,最多达到15个。 [6] 这种基因改变不会导致小鼠的爪子大小发生变化,相反,爪子的大小相同,但手指的间距减小了。
这项研究是图灵模式的经典例子——当斑点被塞进更小的空间时就会变成条纹,研究人员根据图灵方程进行的计算再现了他们在实验中看到的模式。两年后,夏普和他的同事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想法,发现三种不同分子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可以解释为什么手指会在原来的地方生长。他们发现,一种被称为SOX9的蛋白质会发出在特定位置构建骨骼的信号,另一种蛋白质会开启SOX9对应基因的表达,而第三种蛋白质会在手指之间的缝隙处关闭该基因的表达。 [7]
大自然结合反应扩散和形态发生素梯度机制来创建身体计划,这似乎是合理的。然而,图灵模式本身仍然可以解释一系列现象,从肺部分支的产生到口腔顶部的嵴——当你咬下馅料过热的馅饼时,嵴会被烫伤。图灵的洞见还得到了胚胎发育之外的应用,例如解释星系形成和生态学中捕食者与猎物关系的各个方面,甚至揭示了城市中的犯罪热点地区。但是,汤普森和后来的图灵等人开创的是一种严格的数学和物理方法,用以理解生物学问题,特别是胚胎发生和形态发生过程。尽管生物学家近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基因如何塑造我们,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仅靠这一点是不够的。对胚胎发育过程中物理力的更深入了解,正在提出关于我们如何形成的更多问题并促成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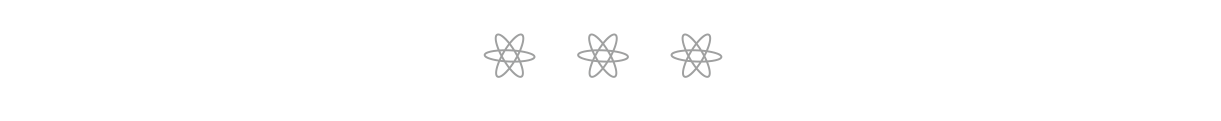
当两个互补的人相遇时,我们常说火花四溅,而这正是卵子和精子相遇时所发生的情况——或者至少是“锌花四溅”。2016年,芝加哥西北大学的科学家使用高速摄像机拍摄了人类精子和卵子结合时发生的“烟花”。他们发现,当一个精子进入卵子时,它会导致卵子中的钙含量激增,从而引发锌的释放。当锌射出时,研究人员使其与小分子结合并发光,以便检测到锌。他们发现卵子会对锌的分布进行调整,来控制健康胚胎的发育。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释放的锌越多,闪光就越亮,从胚胎到胎儿的过渡就越可行。 [8]
当这种火花出现时,合并的遗传物质制造出第一个细胞——受精卵,它开始在被称为有丝分裂的过程中分裂。第一次细胞分裂发生在受精后约24个小时,到第4天结束时,受精卵已经含有大约16个细胞。胚胎沿着输卵管向下移动,与精子进入子宫的方式相反。当它这样做时,帮助精子到达卵子的生物力学机制(第2章中描述的精子尾部的微管)现在也帮助引导胚胎返回子宫。
除了帮助精子和其他微生物游动的鞭毛,还有其他伸出细胞的毛发状结构——纤毛。纤毛通常比精子的鞭毛小,直径约为0.25微米,长度为6微米(大约是精子头部的长度),并且可以锚定在固定的细胞上,带动它们周围的液体移动。它们也存在于身体的多个器官中。例如,在肺部,纤毛推动气道内的黏液层。纤毛也排列在输卵管上,它们不像在肺部那样分布均匀,看起来更像一片森林,到处都有一些空地。
鉴于纤毛的尺寸很小,其雷诺数与精子相同,因此当涉及往复运动以对液体产生单向推动力时,它们会遇到相同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输卵管中的纤毛具有与精子相同的“9+2”微管组结构,这使得它们能够进行复杂的运动(见图3–2)。它们利用这一点,通过“单手蛙泳”来移动细胞周围的液体,其中“动力行程”不同于“复原行程”。纤毛的长度针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很好的优化。任何较短的、流量不足的行程会被创建;而如果行程太长,它们就会太“松散”,无法再次向流体施加必要的力。

图3-2 固定细胞体上的纤毛可以通过执行不同的“动力行程”(虚线所示)和“复原行程”(实线所示)来移动它们所沐浴的液体
纤毛尽管体积不大,但仍能在液体中产生足够的流量来移动一个卵子或胚胎。1982年,当时在伍伦贡大学工作的澳大利亚数学家约翰·布莱克
 表明,纤毛引起的流体流动足以推动输卵管中的卵子,即使人们普遍认为,输卵管中的肌肉收缩至少具有相同的效果(不是更大的话)。
表明,纤毛引起的流体流动足以推动输卵管中的卵子,即使人们普遍认为,输卵管中的肌肉收缩至少具有相同的效果(不是更大的话)。

当胚胎以这种方式被推进子宫时,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现在,胚胎中的细胞开始移动和分化,因此约到第5天,它看起来就不再像一个光滑的细胞球了。这个“囊胚”有两种特征明显的细胞:一种是位于胚胎外表面的滋养层,有助于形成胎盘(见第8章);另一种是内细胞团,最终形成婴儿。剩余的空间是一个充满液体的隔室,被称为囊胚腔。
然而,要进入囊胚阶段,胚胎需要从光滑对称的细胞球转变为滋养层和内细胞团区域。换句话说,胚胎的球对称性必须被打破。毕竟,人体可不仅仅是一个由数万亿个细胞组成的大球。 [9] 虽然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胚胎对称性破缺的遗传和化学控制,但直到2019年的发育研究成果取得之前,其机械或物理方面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未知的。该研究成果由法国巴黎居里研究所的细胞生物物理学家让–莱昂·迈特尔及其同事取得。通过对小鼠胚胎进行超快成像,他们首次发现细胞之间存在数百个微小水泡(每个水泡大小约为1微米)。这些水泡转瞬即逝,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以前人们没有看到它们。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发现这种水泡可以分解将细胞结合在一起的蛋白质。
这些单独的水泡被认为起源于胚胎外部的液体,当它们在细胞之间流动时,它们会聚集在一起产生一个充满水的大空腔,被称为内腔。 [10] 当液体在内腔中积聚时,它将组建胎儿的细胞推向一侧聚集。这个过程不仅在帮助囊胚植入子宫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开始了定义方向(胚胎的正面和背面)的过程。迈特尔团队的工作是在小鼠胚胎中进行的,他们计划对人类胚胎进行类似的研究,看看是否有相同的机制在发挥作用。鉴于胚胎无法植入子宫是导致妊娠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这项研究可能有助于辅助生殖诊所确定哪些胚胎最有可能植入。

图3-3 受孕后,胚胎中的细胞继续分裂(左);约到第5天,它变成囊胚,具有内细胞团和滋养层
一旦胚胎分化发生,约到第6天,囊胚就开始“孵化”。实际上,它是从透明带中破壳而出,
 并开始将自身植入子宫内膜
并开始将自身植入子宫内膜
 。然后,它开始锁定母体的血液供应,就像一个口渴的吸血鬼(第8章中有更多介绍)。一旦进入子宫内膜,胚胎就开始形成身体的轴线和轮廓。滋养层紧贴在子宫内,停留在胚胎的外部区域;但内细胞团现在开始了自己的迁移和分化,因此到第12天它形成了两个圆盘(被称为上胚层和下胚层)——位于胚胎的中部,有点儿像“8”的形状,底部的“o”是下胚层,顶部的“o”是上胚层。它们在中段相触,有点儿像三明治中的面包,只不过暂时没有馅料。下胚层将产生卵黄囊,在胎盘接管之前最初滋养婴儿。另一侧是婴儿将居住的羊膜腔的起点。
[11]
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已经发生,而且在人们知道自己怀孕或进行妊娠测试之前,更多的转变即将发生。约第14天,上胚层和下胚层的两个夹层状圆盘开始打破对称性,胚胎的头轴和尾轴从而开始发育。这也标志着可以在人类胚胎上进行实验的终点,主要是因为此时胚胎开始发育中枢神经系统,并且从法律定义来看代表着一个人的形成,而不仅仅是一个细胞盘。
。然后,它开始锁定母体的血液供应,就像一个口渴的吸血鬼(第8章中有更多介绍)。一旦进入子宫内膜,胚胎就开始形成身体的轴线和轮廓。滋养层紧贴在子宫内,停留在胚胎的外部区域;但内细胞团现在开始了自己的迁移和分化,因此到第12天它形成了两个圆盘(被称为上胚层和下胚层)——位于胚胎的中部,有点儿像“8”的形状,底部的“o”是下胚层,顶部的“o”是上胚层。它们在中段相触,有点儿像三明治中的面包,只不过暂时没有馅料。下胚层将产生卵黄囊,在胎盘接管之前最初滋养婴儿。另一侧是婴儿将居住的羊膜腔的起点。
[11]
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已经发生,而且在人们知道自己怀孕或进行妊娠测试之前,更多的转变即将发生。约第14天,上胚层和下胚层的两个夹层状圆盘开始打破对称性,胚胎的头轴和尾轴从而开始发育。这也标志着可以在人类胚胎上进行实验的终点,主要是因为此时胚胎开始发育中枢神经系统,并且从法律定义来看代表着一个人的形成,而不仅仅是一个细胞盘。

在原肠胚形成的过程中,上胚层中开始形成一种被称为原条的结构。它开始在圆盘的边缘形成,然后生长到圆盘中,看起来就像国际象棋中的卒躺在圆盘的中心(见图3–4)。棋子的“头”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原结,细胞开始聚集在那里,然后穿过上胚层,在两个圆盘之间形成一个新的层,有点儿像在三明治的面包片中间注入一些果酱。这最终让胚胎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最上面是外胚层,它将形成神经系统和皮肤的上皮层。新形成的中间层称为中胚层,产生结缔组织、心脏和肌肉组织。最后,底层即内胚层,有助于形成胃肠道和呼吸道。

图3-4 到第12天时,胚胎包含两层(左图)——上胚层和下胚层;几天后,原肠胚形成过程帮助胚胎制订身体计划,其中原条和原结开始形成(右图)
在胚胎发生这场“旋风之旅”中,胚胎在几周的时间内形成了身体的轴线。它已经区分了正面和背面、头部和尾部,还有一种主要的对称性需要打破——左右对称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外表看起来是对称的。如果你站在镜子前,在身体中间画一条假想的分界线,将你从头到脚切成两部分(这个切面被称为矢状面),你会看到相对完美的对称性。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人体内部不对称占主导地位,心脏向左倾斜,胰腺、胃和脾脏也向左倾斜,而肝脏则位于右侧。器官的这种偏手性非常一致,但也有不一致的情况。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人体内部不对称占主导地位,心脏向左倾斜,胰腺、胃和脾脏也向左倾斜,而肝脏则位于右侧。器官的这种偏手性非常一致,但也有不一致的情况。
第一个发现事情可能有所不同的人是达·芬奇。尽管达·芬奇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但他并没有完全正确理解性交过程的内部细节。不过,他有一些怪癖。他创造了自己的速记法,甚至将书写过程镜像处理,从页面的右侧开始向左移动。即使是他,在15世纪的某一天,当他研究一个死去的女人的躯干时,也感到惊讶。在解剖过程中,他发现这个女人的心脏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向左倾斜,而是向右倾斜。就像他的书写习惯一样,这是一个“正常”人心脏的镜像。现在,这种情况被称为右位心,影响着不到1%的人口——这些人仍然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心脏的这种情况。
虽然这对像达·芬奇这样好奇的人来说一定很有趣,但他不知道,还有一种比右位心更极端的情况——体内所有内脏器官都是镜像的。这是由苏格兰医生马修·贝利首先发现的,他于1788年发表了解剖一具器官镜像的尸体的详细记录。 [12] “打开胸腔和腹腔后,内脏的不同情况是如此惊人,以致立即引起正在解剖它的学生注意。”贝利写道。
这种情况被命名为“镜面人”(内脏反位, situs inversus ),源自拉丁语“ situs ”(位置)和“ inversus ”(相反)。据估计,这种疾病的发生率为万分之一,有这种情况的名人包括西班牙歌手安立奎·伊格莱西亚斯和美国歌手唐尼·奥斯蒙。与右位心的人一样,这种疾病的患者完全有可能过着正常的生活,甚至不知道自己患有这种疾病。那么,问题是自然为什么(以及如何)如此多地选择左侧作为心脏的倾斜方向?毕竟,如果这是随机现象,那么你会预测1/2的人的心脏向左倾斜,另外1/2的人的心脏向右倾斜。事实证明,这个问题非常适合用流体动力学工具来解决,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些小纤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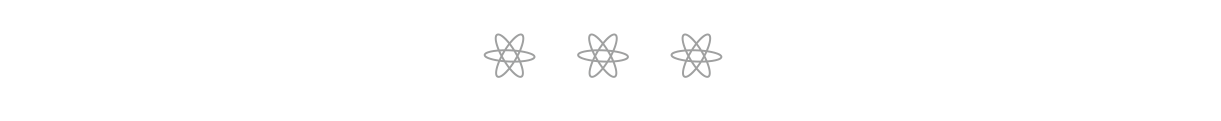
回想发育中的胚胎,你会记得原条上的结点恰好包含200~300根长度约为5微米的纤毛。它们沐浴在一层胚胎液薄膜中,该薄膜的黏度类似于盐水,存在于发育中胚胎的所有三层细胞之间。然而,这些纤毛的内部结构与我们遇到的输卵管纤毛和精子鞭毛的内部结构略有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具有“9+0”结构,即环中具有相同的9个微管结构,但没有中心对。这意味着它们无法执行与精子鞭毛相同的复杂运动,例如弯曲。相反,它们只是绕细胞上的固定点旋转,有点儿像将一根棍子的一端放在地上,然后将另一端绕圈移动,从而画出一个假想的圆锥体。
大约20年前,在小鼠身上进行的实验证实了这些纤毛对于破坏体内对称性的重要性。科学家发现,如果结点上的纤毛无法移动,那么一些小鼠的心脏会向左倾斜,而另一些小鼠的心脏会向右倾斜——结果似乎是随机的。 [13] 因此,虽然纤毛的这种圆周运动显然是造成胚胎左右对称性被破坏的原因,但目前尚不清楚纤毛的这种圆周运动如何导致流体向左流动。
2004年,在西班牙格林纳达晶体学研究实验室工作的数学家朱利安·卡特赖特领导的数学分析取得了突破。纤毛旋转的频率为10~20赫兹,类似于空转汽车发动机的转速。卡特赖特及其同事进行流体动力学模拟,探究如果纤毛向已建立的后部倾斜约35度 [14] ,然后沿顺时针方向围绕这个固定点旋转,会产生什么现象。研究小组发现,在这种设置之下,可以产生左偏流,因为向左运动比向右运动对流体产生的影响更大。

图3-5 原结细胞上的纤毛以特定方式旋转,产生更大的左偏流,从而打破了体内的左右对称性
这就像从快艇后面直视螺旋桨一样。由于纤毛指向后方并顺时针旋转,因此当向假想圆锥的底部移动时,它们会将液体扫向左侧。当它们向圆锥顶部移动时,纤毛将液体扫到右侧。纤毛向圆锥顶部的运动并不那么有效,因为纤毛靠近细胞表面(类似船的底部),所以细胞表面会抵抗该运动。然而,在圆锥的底部,纤毛的末端距离细胞最远,因此没有任何障碍,并且沿这个方向的扫掠更有效。
拥有一个模型固然很好,但与图灵理论一样,它必须经过实验证实。一年后,日本的研究小组在一项更大规模的实验中模拟了这种纤毛的定向。 [15] 他们使用6毫米长的导线模拟纤毛,并将它们放置在高黏性流体中以确保维持低雷诺数。实验表明,当导线倾斜约30度旋转时,流体中会产生左偏流。随后,这一发现在对小鼠和兔子胚胎的实验中得到支持,这些实验清楚地勾勒出纤毛会向后倾斜,其尖端描绘出一个椭圆形。 [16] 这是低雷诺数状态下发生的,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习惯的背景下思考这种流畅的运动会不太对劲。事情有点儿违反直觉。
“在低雷诺数状态下,结纤毛产生的流体流动并不像你想象的恒定向左,更像是前进两步又后退一步。”伯明翰大学数学家戴维·史密斯向我解释道。史密斯研究肺部纤毛和胚胎结纤毛,
 于2005年在伯明翰大学获得了生物数学博士学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流体向左流动,再稍微向右流动,然后更多地向左流动——产生使其中的“材料”更多沉积到左侧的净效应。
于2005年在伯明翰大学获得了生物数学博士学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流体向左流动,再稍微向右流动,然后更多地向左流动——产生使其中的“材料”更多沉积到左侧的净效应。
人们认为,结细胞底部会产生蛋白质,其中一种蛋白质因其起源被称为“Nodal”。这是一种强大的信号分子,可以影响基因表达,从而开启发育过程的某些方面。 [17] 蛋白质在发育中的胚胎周围移动,开启基因以形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例如心脏、脊柱、肝脏和肺。关于左右对称性,我们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这超出了对其如何发生的基本描述,但现在我们很清楚,这些微小的结纤毛在器官的定向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心脏和肝脏。就像大约50年前关于形态发生素的图灵模式的例子一样,胚胎中左右对称性如何被打破是数学正确预测生物系统行为的力量的另一次完美证明,尽管它们很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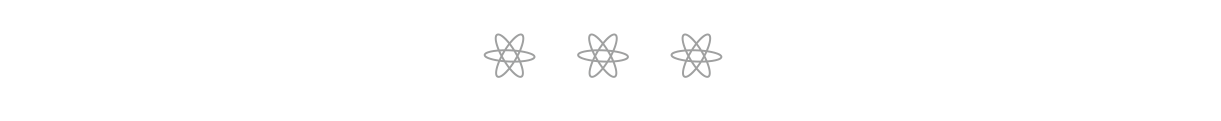
在过去的10年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生物物理学家奥特格·坎帕斯一直在研究与胚胎体如何延长(所有结构就位后的下一阶段)有关的一些力。通常,测量细胞或组织中的力需要在体外的培养皿中进行,这可以提供一些信息。但为了对发育如此迅速的活体动物进行精确测量,坎帕斯必须发明一种新技术。他没有研究小鼠胚胎,而是研究了斑马鱼。出于多种原因,斑马鱼恰好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模型。一来它们是脊椎动物,二来它们丰富且便宜,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几乎完全透明,这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内部结构的发展。
21世纪头10年快结束的时候,当坎帕斯在哈佛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时,他提出了通过在斑马鱼尾巴的细胞之间注射油滴来测量力的想法——斑马鱼尾巴的长度可以在5小时内翻倍。在进行了一些初步调查(其中涉及超市购买的简单橄榄油)后,坎帕斯转到圣芭芭拉建立了自己的团队。然后,他开始进一步开发这项技术,这次使用了生物相容性油。他涂覆液滴并学习如何将磁性纳米颗粒加载到其中,所有这些花了大约8年的时间才实现。
为了推进研究,研究团队将单个油滴注入斑马鱼尾巴细胞之间的空间,每个油滴都装有磁性纳米颗粒。然后,他们施加磁场使液滴变形,这反过来又使组织变形。研究人员研究了液滴是否可以恢复到球形,以及需要多大的应力才能使组织永久变形。所有这些信息使他们能够生成展示斑马鱼细胞和组织机械特性的图片。通过分析颗粒被压扁的程度,他们可以测量施加在液滴上的压力,并且通过将液滴放置在不同的位置,绘制出尾巴的应力情况,以测量细胞的密集程度。
坎帕斯和同事发现,生长中的尾巴末端的细胞就像液体一样,它们可以自由地流动,并且组织更容易变形。他们认为,细胞沿着尾巴表面向尖端移动,然后“重新进入”尾巴,以带来更多的材料来拉长它。然而,细胞从尾部向头部移动时变得更加固定和坚硬,正是在这里开始形成最终成了动物椎骨的结构。 [18] 当细胞聚集在一起时,它们像在固体中一样被锁定到位,有点儿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车突然接近交通堵塞处。这被称为“堵塞”转变,会在其他生物系统中突然出现,例如伤口愈合和癌组织形成时。
研究团队还在尾巴的细胞之间添加了荧光染料,发现尾巴尖端的细胞与另一端的细胞相比有更多的空间,细胞在尾巴尖端比在头部“摇晃”得更多。这种“堵塞”转变和头部“摇晃”不足结合起来,共同使尾巴固化,坎帕斯将其比作玻璃吹制过程中液化需要雕刻的部分,然后让它凝固。“尽管当时没有任何证据,但达西·汤普森描述的形态发生正是这个过程。”坎帕斯说,“然而,这就是我们在斑马鱼尾巴的形成过程中发现的。”尽管这项工作仅在斑马鱼胚胎中进行,但目前在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工作的坎帕斯预计,从液体到固体的转变将被认可为脊椎动物(包括人类)形态发生过程的一个普遍特征。“在接下来的20年内,我们将了解很多有关生物物理学的知识,”坎帕斯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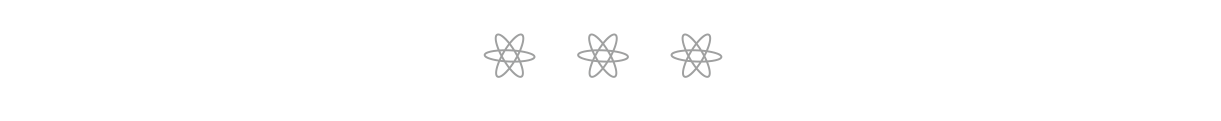
在几周的时间里,人类胚胎从第6天时的一团细胞发展出身体的最初轮廓,这样当你知道自己怀孕时(可能是通过妊娠试验,我们会在下一章中讨论),身体计划的基础已经形成。这种快速发育仍在继续,因此到了妊娠第6周,就可以在阴道超声检查中看到胚胎心跳的早期迹象;到妊娠第12周结束时,胚胎身体的主要轮廓几乎完全形成。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过程,无论是在人类还是其他动物模型中,都需要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之间的合作。物理学在帮助阐明这些奥秘方面的重要性现在已不再受到质疑,并且成为研究生物体塑造过程的强大工具。正如汤普森100多年前在《生长和形态》中所写的那样:“对于(人类)身体的构造、生长和运作,就像地球上的所有事物一样,以愚见,物理学是我们唯一的老师和向导。”
[1] D’Arcy, W.T. On Growth and Fo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7), Cambridge.
[2] Jarron, M.“Cell and Tissue, Shell and Bone, Leaf and Flower—On Growth and Form in Context.” Mechanisms of Development 145 (2017):22–25.
[3] Turing, A.“The Chemical Basis of Morphogenesi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237 (1952): 37–72.
[4] Murray, J.“How the Leopard Gets Its Spots.” Scientific American 258, no.3 (1988):80–87.
[5] Sick, S., Reinker, S., Timmer, J., et al.“WNT and DKK Determine Hair Follicle Spacing Through a Reaction-Difusion Mechanism.” Science 314 (2006):1447–1450.
[6] Sheth, R., Marcon, L., Bastida, M.F., et al.“Hox Genes Regulate Digit Patterning by Controlling the Wavelength of a Turing-Type Mechanism.” Science 338 (2012):1476–1480.
[7] Raspopovic, J., Marcon, L., Russo, L., et al.“Digit Patterning Is Controlled by a Bmp-Sox9-Wnt Turing Network Modulated by Morphogen Gradients.” Science 345 (2014): 566–570.
[8] Duncan, F.E., Que, E.L., Zhang, N., et al.“The Zinc Spark Is an Inorganic Signature of Human Egg Activation.” Scientific Reports 6 (2016): 24737. doi:10.1038/srep24737.
[9] 关于对称性如何在细胞水平上被打破的精彩描述,请参阅Zernicka-Goetz, M.,and Highfield, R. The Dance of Life (London: W H Allen, 2020)。
[10] Dumortier, J.G., Le Verge-Serandour, M., Tortorelli, A.F., et al.“Hydraulic Fracturing and Active Coarsening Position the Lumen of the Mouse Blastocyst.” Science 365 (2019): 465–468.
[11] 有关人类胚胎发育过程的更全面描述,请参阅《生命的成形》:Davies, J. A. Life Unfolding: How the Human Body Creates Itsel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 Baillie, M.“An Account of a Remarkable Transposition of the Viscera.” Philosoph 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78 (1788): 350–363.
[13] Nonaka, S., Shiratori, H., Saijoh, Y., et al.“Determination of Left-Right Patterning of the Mouse Embryo by Artificial Nodal Flow.” Nature 418 (2002): 96–99.
[14] Cartwright, J.H.E., Piro, O., and Tuval, I.“Fluid-Dynamical Basis of the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Left-Right Asymmetry in Vertebr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101 (2004): 7234–7239.
[15] Nonaka, S., Yoshiba, S., Watanabe D., et al.“De Novo Formation of Left-Right Asymmetry by Posterior Tilt of Nodal Cilia.” PLOS Biology 3, no.8 (2005): e268.doi:10.1371/journal.pbio.0030268.
[16] Okada, Y., Takeda, S., Tanaka Y., et al.“Mechanism of Nodal Flow: A Conserved Symmetry Breaking Event in Left-Right Axis Determination.” Cell 121 (2005):633–644.
[17] Smith, D.J., Montenegro-Johnson, T.D., and Lopes, S.S.“Symmetry-Breaking Cilia-Driven Flow in Embryogenesis.” Annual Review of Fluid Mechanics 51(2019): 105–128.
[18] Mongera, A., Rowghanian, P., Gustafson, H.J., et al.“A Fluid-to-Solid Jamming Transition Underlies Vertebrate Body Axis Elongation” Nature 561 (2018):4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