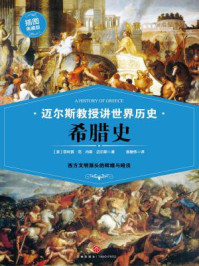THE RULERS AND THE RULED

可能是波瓦坦(Powhatan)酋长穿过的鹿披风,1607年。17世纪中叶,这件披风被牛津一家博物馆收藏。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布里奇曼图片社
他们用石头做成的刀具把鹿皮剥离下来,用一根肋骨把皮上的鲜肉和废油都刮干净。他们把鹿皮浸在木灰和玉米屑中,在木头架子上抻开,然后用筋把鹿皮缝在一起。在这些缝好的熟鹿皮上,镶着数百枚风干并清空的海蜗牛壳,在一个由34个圆形组成的图案中间是一个人,两侧分别是一只白尾小鹿和一头山狮。
这个人就是他们的统治者,动物是他的精灵,圆圈是他统治的村庄。他有一个名字叫瓦浑苏纳科克(Wahunsunacock),但英国人都叫他波瓦坦。他可能把这件鹿皮衣当披风穿,也可能用它来表示对祖先的尊重。当英国国王詹姆斯在1608年送给他一件红色长袍和一顶铜制王冠作为礼物时,他可能把这件披风作为礼物送给了英国人——一袍换一袍。还有种说法是,英国人可能偷走了披风。某人通过某种办法用船将它运到了英格兰。1638年,一个英国人在英格兰的一座博物馆见到了它,把这件缀有蜗牛壳、用筋缝制的鹿皮称为“弗吉尼亚王袍”,但它也是波瓦坦王国的一张地图。 [1]
英国人称波瓦坦为“国王”是外交辞令,而英国国王宣称自己是弗吉尼亚的国王:詹姆斯把波瓦坦看作他的臣民。两位国王统治的本质和历史说明了一些英格兰殖民者为此纠结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问题:是谁在统治?凭借什么权力来统治?
波瓦坦大约生于1545年,父亲死后,他继承了统治权,掌管着六个邻近的部族,16世纪90年代,他开始扩大自己的统治。在大洋的另一侧,詹姆斯生于1566年,第二年,他的母亲玛丽一世被废黜后,他成为苏格兰国王。1603年,他的表亲伊丽莎白去世,詹姆斯加冕为英格兰国王。英国教会与罗马教会的分离提升了君主政体的地位,因为国王不再听从教皇,詹姆斯坚信他(像教皇一样)是君权神授。他在一部名为《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则》( 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 )的论著中写道:“质疑上帝的所为是一种亵渎,所以争论国王该做什么同样是在煽动叛乱。”似乎他不仅是绝对正确的,而且是高于法律之上的。 [2]
詹姆斯是个教皇式的国王,事实证明,他在新世界建立殖民地的决心比伊丽莎白更坚决。1606年,他发布了一条特许令,授权一家公司或一群人在“美洲通常被称为弗吉尼亚的地方”建立殖民地。他宣称这里是他的财产,因为如特许令所言,这些土地“事实上不归基督教君主或人民所有”,而且那里的原住民“生活在黑暗之中”,这意味着他们根本不知道基督。 [3]
与西班牙人(他们出发的目的是征服)不同,英国人的目的是要在美洲安家立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最初是和波瓦坦进行贸易,而不是和他开战。詹姆斯授权殖民地定居者“挖掘、开采、探寻各种金矿、银矿和铜矿”,这与西班牙最初的目的是一样的,但他同时要求他们将原住民转化为基督教徒,因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应通过“宣扬基督教”,“将居住于此的无信者和野蛮人带入人类文明,带入安定和谐的政府” [4] 。他坚信,他们的目的不是带来暴政,而是带来自由。
詹姆斯的特许令就像波瓦坦的鹿皮披风一样,同样是一种地图。(特许令“charter”和拉丁文的“chart”是同一词根,意思是“地图”)詹姆斯的特许令将土地赐给“弗吉尼亚公司”和“普利茅斯公司”两个公司:“我们将赐予他们建设住宅、开垦种植并发展为一个殖民地的许可证……在上述弗吉尼亚或美洲海岸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他们认为恰当方便的地方。” [5] 在那个年代,弗吉尼亚的范围从现在的南卡罗来纳一直延伸至加拿大:英格兰主张对这些地方拥有所有权。
英格兰帝国将会具备与西班牙和法兰西帝国不一样的特色。天主教可以通过受洗的方式令人皈依,但新教让皈依者阅读《圣经》,这意味着永久定居,意味着拥有家庭、社区、学校和教堂。而且,大英帝国会成为一个海上帝国——它的海军是它最强大的力量,它还会成为一个商业帝国。而且,对将从这些定居点发展出的那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殖民者是自由人而不是家臣,他们的“英国自由民”身份要得到保障。 [6]
詹姆斯的殖民者天高皇帝远,虽仍是国王的臣民,但他们将自治自理。他在1606年的特许令中称,国王将在英格兰指定一个由13人组成的委员会对殖民地进行监督。但对地方事务来说,定居者应该建立他们自己的13人委员会来“管理和安排所有事由”。最重要的是,殖民者将作为英国臣民保留他们所有的权力,就像他们从未离开英格兰一样。如果国王保证殖民者作为英国人的自由、特权和豁免权,如同他们将来返回英国后应得的自由、特权和豁免权,那么这些殖民者将会认为他们的上述权利在殖民地也得到了保障。 [7]
17世纪至18世纪初期这段时间,英国建立了二十多个殖民地,构成了一个由海岸定居点组成的海上帝国,从纽芬兰的渔港到佐治亚的稻田,从牙买加和安提瓜到百慕大和巴巴多斯。自弗吉尼亚特许状开始,有关帝国臣民享受英国自由的想法根植于美洲大地,并且,英国国王对此拥有统治权。这一主张的理由是,像波瓦坦及其人民这样的人生活在黑暗里,且不具备政府组织,尽管英国人将他们的领袖称作国王。
然而,英国自身的政治秩序却岌岌可危。在英国殖民化初期,国王在大洋两岸的臣民都相信,人生来是不平等的,上帝已授权国王治理他们。这些是过去的真理,到17世纪末,约翰·洛克设想美国的诞生并借鉴了基督教神学的观点后认为,所有人生而“平等,所有的权力和管辖权在此状态下都是对等的,没有人比别人享有更多”,每个人“都拥有最大限度的平等,不受任何人支配” [8] 。到1776年,国王在多个殖民地的很多臣民都完全同意洛克的观点,以至他们接受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朴素的真理”,即“所有人生而平等”,上帝授权某人和他的继承人去统治其他人的想法,完全是荒唐至极。“大自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潘恩坚信,“否则的话,大自然不会频频嘲弄国王,向人们揭露‘驴披狮皮’ [9] 的真相。” [10] 这些成为他们的新真理。
在弗吉尼亚特许状与使那么多人相信“人生而平等”和“政府的权力完全是在被管理者同意的情况下产生的”《独立宣言》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答案隐藏在鹿皮披风的红色长袍这种完全不同的人造制品中,隐藏在相去甚远的古堡废墟与缠绕着嘎嘎作响的铁链的奴隶船的船身之中。

新不列颠,1609年。弗吉尼亚公司通过广告雇用殖民志愿者,许诺殖民者将得到“伊甸园”式的奖赏
弗吉尼亚第一特许状是在首席检察官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的办公室写就的,科克是个刻薄的人,下巴尖尖的,他思维清晰,但经常口不择言。科克在弗吉尼亚公司有投资,是英国普通法(依几世纪以来的习俗和案例形成的不成文法律)的头号理论家,他一直寻求将理性主义规则纳入普通法。“理性是法律的生命”,科克写道,而且“普通法本身除理性之外别无他事”。1589年,37岁的科克成了一名议员。5年后,伊丽莎白任命他做首席检察官。1603年,在詹姆斯国王将沃尔特·雷利爵士打入伦敦塔之后,科克起诉雷利因谋害国王而犯有叛国罪。“你毒如蛇蝎,”科克在法庭上对雷利说,“你长着一副英国人的脸,但有一颗西班牙人的心。”雷利在监狱遭受了13年的折磨,在被斩首前一直书写他自己的世界史。与此同时,他的定罪放开了人们定居弗吉尼亚的权限(伊丽莎白授予雷利的权限)——在科克的审视下由詹姆斯重新宣布。殖民地特许状发布两个月之后,詹姆斯任命科克为普通诉讼法院的首席法官。 [11]
为占据新的殖民地,弗吉尼亚公司组织了一群渴望赚取财富的人,以及曾经在反天主教及伊斯兰教的英国宗教战争中作战的士兵。26岁的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健壮勇敢,在法兰西和荷兰与西班牙人打过仗,也曾在匈牙利和奥地利军队一起与土耳其人作战。他后来被穆斯林抓获,被当成奴隶卖掉,不过最终逃脱了。他的盾徽上刻着三个土耳其人的头像,还有他的座右铭:征服就是生命(vincere est vivere)。 [12] 乔治·桑迪斯(George Sandys)是弗吉尼亚公司的财务主管,他曾骑着骆驼前往耶路撒冷,写下了很多关于伊斯兰的文章;殖民地大臣威廉·斯特雷奇(William Strachey)曾到伊斯坦布尔旅行。与西班牙人非常相似,这些人和他们的投资人要在新世界建立殖民地,寻找金矿以资助击败旧世界的穆斯林的战争,尽管他们承诺不会对美洲原住民实施“西班牙式的残忍” [13] 。
1606年12月,105名英国人(没有女人)登上了三艘船,带着一个装有一张弗吉尼亚公司指定的统管殖民地的人员名单的箱子,“不许打开,这些管理者在抵达弗吉尼亚之前也不可以知道。”在航行期间,史密斯被关在甲板之下,戴着手铐脚镣,罪名是发动“自立为王”的兵变。 [14] 1607年5月,当探险队最后在一条以国王名字命名的半咸水河岸登陆时,箱子打开了,人们发现上边写的是“史密斯”——尽管当时他还是个囚徒。 [15] 他身上的锁链被全部打开。
无论公司的商人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和谐政府”,殖民者们都是无法管束的。他们建造了一个要塞,然后开始寻找金子。但一群士兵和一些绅士、探险家不愿开荒或种植和收获庄稼;相反,他们从波瓦坦的人那里偷窃食物,将其视为粮仓。史密斯非常生气,他抱怨公司几乎什么也没给他,只给了一些没用的定居者。他清点出一个木匠、两个铁匠和一群男仆,其他人则被标注为“绅士”“商人”“下人”“浪荡汉”等,他们足可以搞砸一个国家十次,但却不能创建或维持一个国家。 [16]
1608年,史密斯当选为殖民地总督,他定了一条规则:“不干活就别吃饭。” [17] 他利用外交手法举办了一场精心安排的加冕仪式,加冕波瓦坦为“国王”,还把詹姆斯国王赠送的红袍披在后者的肩上。无论这一举动对波瓦坦来说意味着什么,英国人的本意是将此作为一个承认他们主权的行为,坚信如果波瓦坦接受这些礼物,就算接受了英国的统治:“波瓦坦,他们的大国王自愿接受王冠和节杖,并完全认可他的职责和归顺。” [18] 但英国人仍在挨饿,他们仍在掠夺当地人的村庄。到1609年秋,殖民者发起叛乱——这是此后众多叛乱的开端——他们把史密斯送回了英格兰,称在他的领导下,弗吉尼亚已经成为“悲惨、毁灭和死亡之地”。 [19]
真正的地狱还没有出现。1609年至1610年冬天,殖民者没有很好地从事农耕、渔业和狩猎,除了把邻居变成了敌人,所收甚微,人数也从500人减少到了60人。“很多人由于极度饥饿,爬下那些没有铺盖的床,瘦骨嶙峋,如同骨架,哭喊着‘我们要饿死了’,‘我们要饿死了’”,殖民地副总督乔治·珀西(George Percy)——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伯爵的第八个儿子——报告说,“我们的一个士兵杀死了他的妻子,把婴儿从子宫里揪出来扔进河里,然后把他妻子剁成肉块,撒上盐,做成自己的食物。” [20] 他们相互蚕食。
这种惨绝人寰的消息迅速传到英格兰,像大洋彼岸传来的所有消息一样,点燃了人们的思想。在弗吉尼亚公司董事会任职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持续关注殖民地陷入无政府状态的过程。1622年,波瓦坦去世四年之后,原住民奋起反抗,试图将英国人逐出他们的领土,在英国人所谓的“弗吉尼亚大屠杀”中杀死了数百人。通过演绎自然的原始状态从而得出了一个有关公民社会起源理论的霍布斯,对弗吉尼亚的暴力事件进行了反思。“美洲许多地方的野蛮人……根本没有什么政府,至今仍以那样的粗野方式生活。”之后他在专著《利维坦》中总结说,自然的状态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 [21]
殖民地奇迹般地恢复了生命力,人口在增长,经济随着一种新作物的种植兴旺发展:烟草——一种仅新世界有的、原住民长期种植的作物。 [22] 烟草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带来了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殖民者自治,然后再统治其他人。1619年7月,11个殖民地中,每个殖民地推选出两名殖民者(共22人)为代表,组成了一个立法机构,即“市民议会”(House of Burgesses),这是殖民地第一个自治政体。一个月之后,20名非洲人抵达弗吉尼亚,这是英属美洲的第一批奴隶,来自恩东戈(Ndongo)王国,操金邦杜语(Kimbundu)。他们在安哥拉(Angola)总督指挥的袭击行动中被抓,然后步行到海边,登上了一艘叫“施洗者圣约翰号”(São João Bautista)的开往“新西班牙”的奴隶船。在海上,一艘启航于“新荷兰”的英国私掠船“白狮号”袭击了“施洗者圣约翰号”,抓住了全部20人,并把他们带到弗吉尼亚出售。 [23]
20名英国人被选入市民议会,20名非洲人被贬为奴隶。美国建国史书的另一章开始了:自由和奴役成为美国的亚伯和该隐。 [24]
海浪冲击着船舷,如鼓槌在敲响。妈妈在哄孩子睡觉,男人则不停地哀号,唱着忧伤的歌。“欧洲人买来的黑鬼常常会发疯,”一个奴隶贩子写道,“很多人都死于这种状态。”其他人则是自杀,纵身跳入大海,希望大海能让他见到祖先。 [25]
跨越大洋的英国人承受风险的情形虽然截然不同,但航行中的危险也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印迹,风险留在了他们的身上,也留在了回忆录的故事里,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中。1620年夏天,即“白狮号”登陆弗吉尼亚海岸一年后,“五月花号”(一艘排水量为180吨的三桅横帆商船)停靠在英国普利茅斯城位于普利姆河口的港口。它很快就开始接收乘客,约60名探险者,加41名男子——英格兰教会的异见者——带着妻子、孩子和仆人登船。宗教异见者编年史家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称这些人为“朝圣者”。 [26]
布拉德福德将会成为这些异见者所建立的殖民地的总督,也将成为该殖民地的主要史官。他说,写作“要用简单的风格,特别关注所有事情中的简单事实”。布拉德福德解释说,10年以前,朝圣者离开英格兰前往荷兰,定居在莱顿(Leiden),这是一个大学城,以其学术气氛好、宗教容忍度高而闻名。流亡10年之后,他们决定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他们考虑的地方是美洲某处地域广阔、人烟稀少的乡野,”布拉德福德写道,“那里地多丰产、适于居住,没有一个文明人,只有散居四处的未开化的人和粗俗的人,比起野兽强不了多少。”尽管他们对此远行充满恐惧,但他们把信仰寄托在慈悲的上帝身上,起航奔赴弗吉尼亚。“所有人都挤在了一条船上,”布拉德福德写道,“好运之风再次把他们吹到了海上。”
船在布拉德福德所谓“浩瀚而狂暴的大海”上航行了66天(原预测并不准确)。在此期间,一个人曾坠入水中,最后靠抓住一条帆绳捡回性命;船漏水了;一根横梁开裂了;一条桅杆弯了,几乎折断。有两天,风刮得太猛,人只能聚集在船舱里,在椽下紧紧地挤在一起。风暴平息之后,人们忙着堵塞甲板,加固桅杆,再次升起船帆。伊丽莎白·霍普金斯(Elizabeth Hopkins)在这条摇摆的船上生了孩子,她给儿子起名为奥西那斯(Oceanus)。这条船被海风吹得严重远离了航线,没能在弗吉尼亚登陆,而是停靠在大风肆虐的科德角(Cape Cod)海岸。不愿再在海上冒险的朝圣者停船上岸,去寻找希冀中的一个新的、更好的英格兰,一个新的起点。但是,布拉德福德写道:“除了一片奇形怪状、渺无人烟、到处都是野兽和野人的荒原,他们还能看到什么?”他们跪在地上,赞美上帝他们还活着。他们抵达的当天,在遭遇了布拉德福德所谓的“巨大挫折”之后,在一条他们想象的所有人同舟共济的国家之船上,签署了一份文件,承诺“立约并将大家结合成一个公民政体” [27] 。他们以船的名字给协议命名,称《“五月花号”公约》。
在弗吉尼亚定居的人们得到过国王的特许状,但定居在他们称为“新英格兰”的地方的那些男人、女人和孩子没有任何特许状,他们是为了摆脱他的统治而逃出来的。17世纪,英格兰的宗教异己分子同样也是政治异己分子,他们面临着被监禁和处决的惩罚。但如果詹姆斯神圣的统治权受到逃离他权威范围的异己分子的挑战,那么议会也会质疑他的统治。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斗争将会使另外几万人流亡大洋彼岸,到殖民地那里去寻求政治自由。冲突同样会激发人们心中对专制统治深刻而持久的反叛精神。
正当新英格兰的异己分子在他们命名为“普利茅斯”的殖民地的第一个冬天苦苦挣扎时,议会议员开始挑战过去的传统,即只有在国王召唤的时候才会召开议会。1621年,爱德华·科克在雷利1618年被斩首后逐渐成为詹姆斯最狡猾的对手。他宣称议会有权讨论所有国家大事。国王将科克抓了起来,把他关进伦敦塔并解散了国会。雷利在监狱里写了一部世界史,科克将写就一部法律史。
为了收集反抗国王的法律依据,科克翻出了一本尘封多年、几乎被遗忘的古代法律文件,名为《大宪章》( Magna Carta )。1215年,约翰国王在《大宪章》中向贵族们承诺将遵守“国内法律”。《大宪章》的文本与科克整理的结果相比,重要性相差甚远。《大宪章》没有科克所说的那么重要,但通过论述它的重要性,科克使它变得重要,不仅是为了英国历史,也是为了美国历史,它将英格兰殖民地上每个人的政治命运,与中世纪一个坏国王的怪异行为联系在了一起。
约翰国王生于1166年,是亨利二世最小的儿子。年轻的时候,他师从父亲的首席大臣雷约夫·德·格兰维尔(Ranulf de Glanville)。格兰维尔曾致力于撰写一部有关英国法律的最早期评论,试图处理“法律如果没有被人写下来能否成为法律”这一相当微妙的问题。 [28] 格兰维尔承认,将国内所有法律和法规都变成文字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认为,这就意味着不成文法依然是法律,它们是大量先例和习俗的纪实,共同构成了“普通法” [29] 。
格兰维尔的深思将他引入了另一个更微妙的问题:如果法律没有书写下来,或即便书写了下来,我们靠什么理由或力量来约束一位国王遵守这些法律?自公元前6世纪起,国王们一直以书面形式强调他们的统治权。 [30] 而至少从公元9世纪开始,他们一直以宣誓的形式接受司法的监督。 [31] 1100年,在《大宪章》中,“征服者”威廉的儿子亨利一世承诺要“废除所有使英格兰王国受到不公正压迫的邪恶习俗”,这(他并未遵守这一承诺)是一个先例,格兰维尔可能希望借此来限制亨利一世的重孙子约翰国王。 [32]
不幸的是,国王约翰是个专制君主,无视《大宪章》的存在。他比以往任何一位国王征税都更高,而且他把大量的货币要么运出国境,要么放在他的城堡里,这样任何人都难以用钱来支付税款。当他的贵族成为他的债务人,他就把他们的儿子作为人质。他曾把一个贵妇和她的儿子饿死在地牢里。传言说他还下令砸死了一个办事员。 [33] 必须要做些什么了。
1215年,发动叛乱的贵族们占领了伦敦塔。 [34] 当约翰同意面见他们进行和平谈判时,他们聚集在伦尼米德(Runnymede,泰晤士河畔的草场),贵族们向约翰提交了一份长长的,后来被重写为宪章的要求清单。国王在宪章授予王国的“所有自由人”——也就是说,不是全国人民,只是贵族——“余等及余等之子孙后代,下面附利之各项自由。” [35] 这就是《大宪章》。
《大宪章》几乎从成文之日起就被废除,到詹姆斯国王和难以管制的爱德华·科克产生争端之时,它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但科克是个聪明的政治策略家兼法律学者,他在17世纪20年代复活了它,并开始称之为英格兰的“古宪法”。当詹姆斯国王强调君权——君主高于法律的古老权力时,科克以他的古宪法予以反击,坚持认为法律高于国王。“《大宪章》是这么个家伙,”科克说,“它没有君主。” [36]
科克复活《大宪章》充分解释了为什么在将来的某一天,英国殖民者会相信国王无权统治他们,为什么他们的后代会相信,合众国需要一部成文宪法。但《大宪章》还扮演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它在真理的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英格兰的历史进程与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
《大宪章》所确立的最关键的权利是陪审审判权。多少世纪以来,在整个欧洲,有罪和无罪或是由神判法(水审、火审)决定的,或是由决斗来裁定的。神判法和决斗既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证词和审问。其结果本身就是证据,而且是唯一可接受的司法证据,因为终审权在上帝手里。不过,这种审判很容易被滥用,因为牧师很可能受到贿赂。于是到1215年,教皇取缔了神判法。在欧洲,神判法被一种新的神圣审判体制所替代:法庭拷问。但在英格兰(那里有一种召集陪审团来公审民间争执的传统,如邻里间房产地界争端),神判法不是由法庭拷问而是由陪审审判制所取代的。这种局势的出现有一个理由:就在教皇废除神判法的当年,约翰国王在《大宪章》中承诺:“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审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 [37] 在英格兰,不论是民间争执或者是犯罪调查,真相都是由人,而不是由上帝决定的,不是由刀剑之战决定的,而是由事实之争决定的。
这一转折标志着人类知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需要一套新的证据原则和新的调查方式,并最终催生了这样一种观点:被观察到或被目睹的行为或事物——事实的本体和内容——是真相的基础。法官判断法律,陪审团判断事实。神秘事物属于信仰问题,是一种不同的、只有上帝知道的真相。但是在宗教改革期间,当英格兰教会脱离罗马天主教会、反对教皇的权威并在《圣经》中寻找真理时,教会的奥秘被揭开,牧师的秘密也被揭露出来。神秘时代开始远去,很快,事实文化从法律层面进入了政府层面。 [38]
在17世纪的英格兰,国王与议会之间问题的实质是对知识本质的争论。秉持君权神授观念的詹姆斯国王坚持认为他的权力不能受到质疑,而且不属于事实的范畴。他说:“讨论与王权神秘性有关的问题是不合法的。” [39] 争论国王的神圣权力,是要从神秘、宗教和信仰领域中移除王权,将这种权力纳入事实、证据和审判的领域。授予殖民地特许状,就是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建立法律,是对神秘统治的否认。
国王凭什么权力进行统治?议会怎样才能约束他?1625年,詹姆斯死后,他的儿子查理加冕为王,查理同样坚信君权神授。3年后,科克(已76岁)回到了议会。他反对查理利用王权将士兵驻扎在臣民家里,未经审判将抗税的人关入监狱。科克宣称国王的特权应该受《大宪章》的制约。 [40] 在科克的建议下,议会起草并向国王提交了一份《权利请愿书》,其中引用了《大宪章》,坚持认为国王无权在未经陪审团审判的情况就关押臣民。如果科克在英国取得了成功,英格兰在美洲的殖民地就不会是后来的样子了。但事实相反,1629年,国王禁止科克出版他对《大宪章》的研究成果,并解散了议会。正是这一行动,使成千上万的国王臣民横渡那浩瀚而狂暴的大洋逃离英国。
1630年到1640年间,即国王查理在没有议会存在的统治期,一批2万多异见分子横渡大洋,逃离英国来到新英格兰定居。其中有一个叫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的,他不苟言笑,但意志坚定,留着范戴克式的胡子,身着浆硬褶裥衣领衬衣。他决定加入在马萨诸塞湾建立殖民地的一次新远征。与布拉德福德想脱离英格兰教会的朝圣者不同,温斯罗普属于一群被称为“清教徒”的宗教异见者(因为他们想净化英格兰教会,但因议会解散而失去了职位)。1630年,温斯罗普(后来成为马萨诸塞的首任总督)给同行的殖民者写了一篇讲话,叫《基督教慈爱之典范》(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五月花号”公约》将普利茅斯的殖民者联盟描述为一个政治团体,而温斯罗普将他的人描述为以爱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基督的身体。“由于他们必须分享彼此的力量和软弱、喜悦和悲伤、幸福和痛苦,因此在这一特殊关系里的这具身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他引用《多林哥前书》第12章的第一段经文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他说,在这里,在他们的新英格兰,他们将在山上建一座城,如同基督在《山上宝训》( Sermon on the Mount )(《马太福音》,5:14)中所要求的那样:“建造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盖起来的。” [41]
殖民地沿大西洋海岸迅速涌现,如香蒲草一样沿池塘边生长。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曾做过科克的速记员,也加入了马萨诸塞湾远征,尽管他于1635年因支持宗教宽容而被驱逐。第二年,他创建了罗得斯。1624年,荷兰人已定居于“新阿姆斯特丹”(后成为纽约);1638年,瑞典殖民者建立了“新瑞典”,这是由后来的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州的一部分构成的殖民地,它甚至不是清教徒的殖民地,也是由这种或那种宗教异见分子建立的。以查理一世的天主教夫人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命名的马里兰,作为天主教徒的避难所出现于1634年。康涅狄格和罗得斯一样建于1636年。纽黑文建于1638年,新罕布什尔建于1639年。

1629年,马萨诸塞湾启用了一枚殖民地印章,以此来美化殖民行为。印章上刻有一名几近裸体的印第安人,正乞求英国人“快来帮助我们”。马萨诸塞文档库版权
英国移民通常是举家移民,有时甚至是整个镇子移民,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同体,一个与所有人的共同福祉相关、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宗教社区。“对公众事务的关注必须支配私人事务的方方面面,”温斯罗普说,“因为这是一条真理:个人财产无法存在于公共利益的废墟中。”他们期待着全世界的关注。“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温斯罗普说。他们的世界是一个有序的世界,一个等级和服从的世界。他们把家庭看作“小国”,父亲是领袖,如同大臣是会众的领导,国王是臣民的头儿。他们在饲养动物的公共用地周围修建城镇。他们并不认为对公共利益的承诺与追求富贵的渴望是矛盾的。他们相信天意:凡事有因,决于上帝。
财富是上帝恩宠的标志,为财富积累财富是一项大罪。新英格兰人期望通过农业和贸易而兴旺发达。“在美洲,宗教和利润同台共舞。”爱德华·温斯洛(Edward Winslow)在谈到普利茅斯时说道。 [42] 他们通过城镇会议自我管理。他们的生活以教堂或会议室为中心:在定居的前20年中,他们修建了40多座这样的建筑。在英格兰时,他们筹集资金,许诺将用于“传播福音”,就是说,用于劝说印第安人改信基督教。马萨诸塞启用了一枚殖民地印章,刻着一个近乎裸体的印第安人,高喊“快来帮助我们”,借用了《圣经》中期盼基督的马其顿人的典故。1636年,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为教育英国和印第安青年在剑桥创建了一所学校:哈佛学院。第二年,在康涅狄格,殖民者和佩科特(Pequot)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爆发。战争结束时,殖民者决定将被俘的印第安人贬为奴隶,卖给加勒比地区的英国人。1638年,新英格兰的第一批非洲奴隶被装在“欲望号”上运到了塞勒姆(Salem),这艘船曾经将佩科特战俘运往西印度群岛。据温斯罗普的日记记载,这些战俘换来了“棉花、烟草和黑人”。新英格兰的非洲人不多,但新英格兰人的确在加勒比海的遥远海岸设有奴隶种植园。 [43]
殖民地的英国人认为他们作为自由人的权利源自保证了即使是国王也要遵守当地法律的古宪法。卖掉印第安人并买下非洲人的是同一批人。他们凭借什么权力在山上的城市里统治其他人?当地法律是什么样的?
英属美洲的非洲人特别多。英格兰在建立殖民地的进程中来晚了,在非法交易奴隶的进程中也晚了。但它一旦进入这种贸易,便开始占据统治地位。1600年至1800年,有100万欧洲人移民到了不列颠美洲,同期有250万非洲人被强行运到这里,运奴船一只接着一只,日夜不停。 [44] 非洲人死得很快,但作为移民人口,他们的人数超过了欧洲人,比例是2.5∶1。

奴隶市场,插画,选自尚邦(Chambon)《美国商业通论》( Traite General du Commerce de l’Amerique )。欧洲奴隶贩子在检查准备购买的奴隶时,有时会舔一下他们的皮肤,他们相信通过汗液的味道能够判断奴隶是否健康。法国南特市图书馆(PRC BW)
英国人曾经讲述美洲“西班牙人残忍”的血腥故事,他们也一直谴责葡萄牙人在非洲的奴隶贸易。一个叫理查德·乔布森(Richard Jobson)的英国商人在1621年告诉某个想卖给他奴隶的冈比亚人,“葡萄牙人和我们不一样。”葡萄牙人像买卖动物一样买卖人口;但乔布森说,英国人“不会进行这种商品交易,我们不买卖他人,或者和我们有着同样外形的东西” [45] 。
但到了17世纪40年代,当英国殖民者开始在巴巴多斯种植甘蔗时,他们将这条长期坚持的信条弃之如敝屣。种植甘蔗比种植烟草需要更多的人力。为种植这种难以生长但利润巨大的新作物,巴巴多斯种植园主总是从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那里买进非洲人。1663年,英国进入奴隶贸易业不久,他们成立了“英国皇家探险者非洲贸易公司”(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rs of England Trading With Africa)。在17世纪的最后25年里,由英国船长掌舵、英国水手服役的英国海轮将500多万戴着镣铐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铐在船上的把手上)运到大洋彼岸。 [46] 他们的船不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的国家之船,不是另一艘缔结契约的“五月花号”。他们的船是奴役之船,捆绑他们的是锻造的镣铐。他们低语、哭泣;他们尖叫、沉默;他们生病;他们悲伤;他们死去;他们忍耐。
英国奴隶商购买的许多非洲人讲班图语,他们来自今天的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地区;有些人讲阿肯语,他们来自今天的加纳;其他人讲伊博语,来自今天的尼日利亚。在前往非洲海岸的过程中,在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中,在加勒比海的群岛上,在美洲大陆上,尤其在那些船舱里,他们的死亡人数相当惊人。他们相信人死后还活着。他们用阿肯语说“Nyame nwu na mawu”,意思是“神明不会死,所以我也不会死” [47] 。
英国人到底有什么权力把这些人变成奴隶?和在1550年与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在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进行辩论的胡安·塞普尔韦达一样,他们同样也指望古代专家,然而发现这些专家并不能胜任。按照罗马法,所有人生而自由,只有国家法律才能在少数情况下判他们为奴隶,比如,当他们成为战俘,或为了还债而出售自己。亚里士多德曾反对罗马法,他坚信有的人生来就是奴隶。因为有关蓄奴制的法律与蓄奴制本身,这些古代传统没能为试图使他们的蓄奴制合法化的英国殖民者提供很大帮助,在14世纪就从普通法中消失了。巴巴多斯的一个英国人在1661年说,现在“无路可以引导我们朝哪里走,也没有规则告诉我们怎样管理这些奴隶” [48] 。在无路或无规则引导的情况下,殖民议会(Colonial Assemblies)采取了一些新措施,设计出一些新法,以此为基础,试图以此在“黑人”和“白人”之间设定一条界线。早在1630年,弗吉尼亚的一个英国人因“和黑人躺在一起而玷污了自己的身体”,遭到当众鞭笞的惩罚。 [49] 采取这些措施并通过这些需要颠覆英国法律,因为现有的英国法律中的很多内容损害了奴隶主的诉求。1655年,一个母亲为非洲人、父亲为英国人的人援引英国普通法要求获得自由,因为普通法规定,孩子的身份跟随父亲而不是母亲。1662年,弗吉尼亚市民议会回答了“英国男人和黑人妇女所生的孩子是奴隶还是自由人”的问题。他们找到了一条古代罗马规则:partus sequitur ventrem(随你母亲)。自此之后,奴隶妇女所生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将继承母亲的身份。 [50]
美国历史上令人感到相当不适的讽刺之一是,为奴隶制和管理奴隶而辩护的法律中,也写入了自由和自由人政府的新观念。1641年,为了给以佩科特人换非洲人的交易提供法律依据,马萨诸塞立法机构通过了《各类自由之主体》( The Body of Liberties ),这是一份清单,列举了100项权利,其中许多出自《大宪章》(一个半世纪之后,其中的7条权利出现在美国的《人权法案》中),《各类自由之主体》包括此条禁令:“我们不允许奴隶、农奴或拘役的存在,除非是在正义之战中获取的合法战俘,并且这些陌生人自愿卖身或由他人卖给我们。”取自罗马法的这一奴隶条款为殖民者出售1637年佩科特战争中被俘的佩科特人和阿尔冈昆人提供了特定的法律保护,也为买卖非洲人提供了保护——他们被描述成“陌生人”,即“被卖给我们”的外国人——所以这里没有需要讨论的法律问题。 [51] 再过一个半世纪,新英格兰人才愿意重新将蓄奴制的合法性拿出来争论。
船只穿梭的航线将殖民者与英格兰、加勒比和西非紧密相连,他们借此推动了自己的法律进程。当英格兰殖民者为蓄奴辩护,并坚持他们拥有不受限制的统治权时,这些国王的臣民仍在争取限制国王的权力。在什么条件下某些人才能有统治权,或反叛权,而其他人却没有这些权力?1640年,国王查理终于召集了一次议会大会,希望能筹集到资金去镇压苏格兰叛乱。新议会否决了国王的提议,通过了一条进一步限制国王权威的法律,要求议会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大会,无论是否经皇家召集。国王支持者和议会支持者之间的战争最终于1642年爆发。在这场争战中,国王神圣权力的法律拟制让位于另外一个法律拟制:人民的主权。 [52]
这种将乘风破浪抵达大洋彼岸的思想,其基础是代表的观念。英国议会于13世纪首次召开,当时国王将贵族们召集到宫中谈话,要求他们承诺服从他的法律并向他缴纳税款。没过多久,这些贵族推说他们的这些承诺并非为了他们自己,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们“代表”了其他人,即他们家臣的利益。这些在17世纪40年代参与谈判的贵族——现在叫“议会”——挑战国王,以他们自己的统治权来对抗国王的统治权:他们宣称代表人民,人民才是君主。他们这么说,是因为在远古的某个时候,人民就授权他们作为代表。保皇党人指出这纯属荒唐。在此刻“还是人民的,下一分钟就可能不是人民的人”,怎么可能行使统治权呢?人民到底是谁?还有,到底什么时候他们曾赋予议会代表他们的权利?1647年,平等派抱着解决这一细小问题的希望,起草了一份《人民公约》( An Agreement of the People ),希望每个英国人都在上面签字,授权议会的代表们具有代表自己的权力。 [53] 这项提议没有实现。而在1649年,国王因叛国罪受审,并被砍了头。
诞生于同一争论的是有关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的前提被中世纪的教会视为异端,在自由和真理之间并无冲突。1644年,清教徒诗人约翰·弥尔顿——后来《失乐园》的作者——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攻击了一条议会通过的法律,即要求印刷商发表任何东西都要获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这一要求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宗教法庭。弥尔顿争辩说,任何书在出版前都不应经过审查(尽管书在出版后可能受到指责),因为只有允许和谎言搏斗,真理才能确立起来。“让她和谎言去搏斗吧”,因为“在自由和公开的碰撞中,谁曾见真理落于下风”。这个观点是基于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认识。弥尔顿认为,人民并不“愚钝,而是思维敏捷、聪明灵巧、精神敏锐、善于发明、微妙健谈,绝不低于人类最高能力的任何一点”。 [54]
在罗得斯,罗杰·威廉姆斯专注于“良心的自由”的成因,其观念是人们思考得越自由,就越有可能接触到真理。在一封写于1655年的信中,威廉姆斯借鉴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想法:政治社会如同船上的乘客,这是一个深受渡过了极其危险的大洋的人喜爱的比喻。“有很多船入海,每条船上有数百个灵魂,他们的幸福和伤痛是共同的。这是一个共同体、人类联合体或社会的真实图景,”威廉姆斯写道,“有时天主教徒和清教徒、犹太人和土耳其人可能登上的是同一条船。”威廉姆斯强调说,船长应该保护他们以他们想要的方式进行祈祷的自由,确保“没有一个天主教徒、清教徒、犹太人、土耳其人被迫参加船上举行的祈祷活动,也不能排斥他们自己特定的祈祷活动(如果他们信教的话)” [55] 。
在宗教异己分子和政治异见分子日渐增长的年代,威廉姆斯在他的理想王国里的引人注目之处不仅包含了天主教徒和所有的新教徒,还包含了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他想象出的是一艘气势宏大的航船。在1649年到1660年间,英格兰没有国王,成为一个共和国,人们认真地对待共和国的概念,在同一条船上的每个人都和他人一样,也更容易假装这世间的确存在“人民”这样一种事物,而且他们是……他们自己的君主。在英格兰,新的宗派开始兴起,从浸礼会到贵格会。掘地派主张土地公有制。平等派呼吁政治平等。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殖民地数量不断增长,殖民者也逐渐将自己看作人民。毋庸置疑,大部分英属美洲殖民地本身就是宗教叛逆和政治反叛的结果,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人民统治和言论自由的实践。大多数殖民地成立了议会(公众选举的立法团体)并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到1640年时,已有8个殖民地有了自己的议会。巴巴多斯(英国人于1627年开始定居)在1651年宣布,英国议会无权干涉其内部事务(不管怎样,这主要是关于蓄奴法)。
1660年君主政体的复辟和查理二世的加冕代表了对宗教宽容进一步的承诺,新国王保证“任何人不得因宗教见解的差异遭到骚扰和质询”。这种精神扩散到大洋对岸,特别是那六个复辟殖民地——那些在查理二世当政期间创建或纳入英国统治的殖民地。纽约和新泽西成为贵格会、长老派和犹太人的宗教避难所,1681年,查理二世赐给贵格派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宾夕法尼亚亦然。佩恩把宾夕法尼亚称作他的“神圣的试验”,并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国家的种子”。1682年,他在《宾夕法尼亚政府体制》(新殖民地宪法)规定了民选大会和崇拜自由,规定“生活在本省的任何人,只要他认可并承认一个全能永恒的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维持者和统治者,而且承认自己在良心上有义务和平、公正地生活在公民社会之中,就应该在任何情况下不因他们在信仰和崇拜方面的宗教派别和惯例而受到骚扰或歧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强迫人们经常性地参与或维持任何宗教活动,无论在什么地方,由什么牧师主持” [56] 。和平依赖宽容。

威廉·佩恩手迹。1681年,查理二世将后来成为宾西法尼亚洲的土地赐给了英国贵格会议员佩恩,后者在这块殖民地上展开了一场“神圣实践”。美国国会图书馆
英属美洲的殖民者以新的章程、新的宪法、新的奴隶法推翻了假设,并重写了规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法律。在一个世纪的有关内部事务的争吵中,英格兰和美洲之间的水域成了某种镜子:起草新法规的人在他们的反思中看到了政治哲学家;政治哲学家在他们的反思中看到了殖民地立法者。没有几个人能像约翰·洛克那样对这种关系进行深思熟虑。他是政治哲学家,同时又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洛克是牛津基督教堂学院的指导教师,他双颊凹陷,鼻子很长,看上去像是一只猛禽。他从未结过婚。他有一个学生是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的儿子。伯爵任英国财务大臣,病得不轻。1667年,洛克离开牛津,任沙夫茨伯里的私人秘书,同时还负责照顾伯爵的身体。他搬进了沙夫茨伯里的埃克塞特府。沙夫茨伯里恰好忙于殖民地事务,负责成立各种贸易和种植园会,包括卡罗来纳殖民地业主董事会(查理把这块殖民地特许给议会的八个曾经帮助他复辟的议员)。洛克成为殖民地大臣。
作为大臣,洛克在写完《论宽容》后不久,在撰写《政府论》( Two Treatises on Civil Government )的同时,起草并随后修订了殖民地宪法,这些著作后来对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7] 洛克从未到过大洋彼岸,但他对殖民地的土地挖掘至深,并埋下了微如他笔尖的革命种子。
与洛克《论宽容》的观点一致,他的《卡罗来纳基本法》(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为宗教言论自由奠定了基础。“不承认上帝的、不公开而庄严地崇拜上帝”的人将不得定居并拥有土地,但除此之外,任何信仰都可以接受,宪法严格规定“异教徒、犹太人和其他对基督教的纯洁性持异见的人士也不得受到恐吓和疏离”。秉承同一种精神(加入到了始于1492年,并统治西班牙王室大半个世纪的论争之中),卡罗来纳宪法还规定原住民的异教教义不足以成为抢夺他们土地的基础。“那个地方的原住民,”宪法强调,“对基督教完全陌生,他们的偶像崇拜、愚昧或过错,并未赋予我们驱赶和虐待他们的权力。” [58] 那么,英国有什么权力占据他们的土地呢?
回答这个问题要靠洛克的哲学。基本法中建立的政府是一种实践,但在《政府论》中,洛克试图从哲学的高度解释政府是如何出现的。他从设想一个自然状态开始,即政府出现之前的状态:
为了正确地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源头,我们必须考究人类原来自然地处在什么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
这不仅是一种思想试验,也是一个已知地点,他写道:“在最初,全世界都像美洲。”
在洛克看来,这种自然状态就是“完全自由”,“同时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洛克的平等主义,部分来自他的基督教理念,以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最为明显的是,人们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完全平等的状态下,人们创造了公民社会——政府——为的是维护秩序、保护财产。
要想理解政府是怎么产生的,就需要理解人们是怎样拥有财产的。在洛克看来,这需要借鉴美洲的例子。洛克《政府论》中有一半关于美洲的参考资料都在“论财产”这一章里。 [59] 例如,他考察过波瓦坦国王,洛克很可能把这位国王的鹿皮披风拿在手里把玩,并触摸上面的蜗牛壳,因为这件披风就存放在牛津的一家博物馆里。“美洲的印第安国王,不过是他们军队里的将军”,而这些印第安人没有财产,也“根本就没有政府”。波瓦坦这样的国王也不拥有主权,据洛克分析,因为他们不耕种土地,他们只是住在那里。“上帝将土地赐予人类所共有”,洛克写道,但“他的意图不是土地永远都是公有的,永远都是荒废的。他将土地赐予勤劳而富有理性的人(而‘劳作’使这些人取得所有权)”。那些浪费了“巨大面积的土地”——未曾开垦——和那些土地公有的人,可以说还尚未“加入人类的大家庭”。一个不相信土地可以被拥有的族群不仅不能立约出售土地,也不能说他们拥有政府,因为政府只因保护财产而存在。
这种想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奇之处。1516年,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 Utopia )中就写过,从那些“不会利用土地而任其闲置和荒废”的人手中夺走土地,是“战争最正义的理由”。 [60] 但洛克一面在不断推动宗教宽容度,一面又在极力区分英国的殖民与西班牙的征服,他觉得强调土地的缺乏开垦比强调宗教的差异更具说服力,更能为占有土地提供更好的理由,这种观点影响深远。
在《卡罗来纳宪法》和《政府论》中,洛克不仅探讨了财产,还探讨了奴隶制。事实上,《政府论》开篇第一个词就是“奴隶制”。他写道:“奴隶制是一种可恶而悲惨的人类状态,直接违背我们民族的宽宏性格与英勇气概,一个英国人(别说是绅士了)会去为它辩护,这几乎令人难以想象。”这是对罗伯特·菲尔默(Sir Robert Filmer)爵士的驳斥,后者在他的《君权论》( Patriarcha )中认为,国王的神圣权力来源于上帝赐予亚当的统治权,不可置疑。在洛克看来,相信这些,无异于相信国王的臣民无非都是奴隶。洛克辩解道,国王的臣民应该是自由人,因为“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作为他的准绳”。洛克还说,人人生而平等,有天然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为了保护这些权利,他们一致同意组建政府。在洛克看来,奴隶制既不属于自然状态,又不属于公民社会。奴隶制是国家的法律问题,“仅仅是合法征服者和被俘者之间的持续战争状态。”因此,将奴隶制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础引入卡罗来纳,即建立一种与洛克所理解的公民社会不一致的制度。宪法中称,“卡罗来纳的每个自由人对他所拥有的黑人奴隶具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这就是说,尽管洛克强烈肯定人的自然自由权,宣称绝对权力就是专制,但在美洲,一个人可以占有另一个人的权利——在自然状态下或在公民政府下难以想象,在其他任何制度安排(除非是战争状态)下也难以想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法的。 [61]
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即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生来自由而另一些人则不是,乃是播撒另外一粒种子:种族观念。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生长,需要更长的时间才枯萎。
美洲革命并非始于英国的殖民者,而是始于他们所统治的人。早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枪声响起之前,在乔治·华盛顿穿越特拉华之前,在人们还没有想到美国独立之前,革命的传统就已成形,塑造此传统的不是美洲的英国人,而是发起战争的印第安人,以及发动造反的奴隶。造反、起义和叛乱接连不断。他们的革命行动一浪高过一浪,不断冲击着这块土地。他们不断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凭什么遭受奴役?终有一天,这些殖民者自己也会发出同样的疑问。
英格兰殖民者似乎常认为这些叛乱属于一种阴谋,特别是,如1675年和1676年,叛乱接踵而来,这些都远在这群英国人为自身独立而战的一个世纪之前。1675年6月,一个由米塔科姆(Metacom)酋长(英国人叫他“菲利普王”)领导的、由新英格兰的阿尔冈昆人组成的同盟试图赶走他们土地上所有的外国人,他们向一座座城镇发起了进攻。“全国的印第安人都在起义。”一个英国人写道。战争尚未结束,新英格兰半数以上的城镇不是被毁,就是被弃。米塔科姆被击中、被开膛、被肢解、被斩首,他的头颅被挂在普利茅斯的柱子上——遭受国王式的惩罚。他九岁大的儿子被当作奴隶卖掉,运往加勒比海,那里的巴巴多斯奴隶叛乱正好爆发。巴巴多斯的英国人认为这些非洲人“企图杀死所有的白人”,他们的“宏伟构想是为自己选择国王”。(岛上的立法者颇感惊恐,他们迅速通过了一条法律,禁止购买从新英格兰运来的印第安人奴隶,唯恐会加剧暴乱。)其实新英格兰和巴巴多斯“尝到的是同一个杯子里的苦水”,一个新英格兰殖民者评论说。
这个“杯子”里的水洒了。新英格兰的战争持续升级,巴巴多斯被叛乱者占领,原住民开始攻击英国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城镇,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被迫宣布,“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传染病”已经向南扩散。伯克利拒绝对印第安人进行报复,这导致了一个叫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的殖民者煽动叛乱。培根带领一支约500人的队伍冲入詹姆斯敦,将其焚为平地。若不是伯克利总督下台和培根患痢疾而死,肯定会有更多的混乱接踵而至。 [62]
战争、反叛以及各种谣言充斥了殖民地的信件和报刊。消息传播得广阔遥远必然产生这样的效果,即种族分界线更加分明。在“菲利普王战争”开始前,新英格兰的大臣们曾试图让原住民改信基督教,教他们学英语,希望他们最终能和英国人生活在一起。战争之后,人们基本上放弃了这些努力。培根叛乱加深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隔阂。在培根率兵火烧詹姆斯敦之前,贫穷的英国人基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跨洋来到殖民地的英国男女,每四人中就有三人是负债人或是契约奴;他们不算奴隶,但也不是自由人。 [63] 选举权有财产要求,这意味着并非所有自由白人都可以投票。与此同时,奴隶可能被主人释放,这意味着黑人可能是自由人,而白人却可能是非自由人。培根叛乱之后,自由的白人男性获得了选举权,黑人男女则几乎不可能获得自由。到1680年,有位观察家指出,“黑人和奴隶这两个词”已“逐渐具有同等性质,可以互换”——你是黑人,你就是奴隶。 [64]
对战争和叛乱的恐惧萦绕在英国殖民地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成了恐怖之地,政治动荡,令人担忧,物质条件十分脆弱。1692年,在马萨诸塞的萨勒姆城,19名男女因玩弄巫术而被治罪。不过,所谓的巫术,似乎是印第安人袭击的余波,是难以抹去的痛苦经历和恐怖记忆。在巫术审判过程中,莫西·肖特(Mercy Short)说魔鬼用火烧她,让她备受折磨,她描述这个魔鬼是一个“矮个子黑人……但不是非洲黑人,皮肤为深茶色,或印第安人的肤色”。魔鬼和他的女巫开始折磨莫西·肖特的两年前,她曾被阿贝内基人俘获,阿贝内基人洗劫了她在新罕布什尔的全家,杀害了她的父母和三个兄妹。莫西·肖特被迫步行到加拿大。在路上,她目睹了一桩桩暴行:一个5岁的男孩被剁成了几段,一个年轻的女孩被剥去了头皮,同时被俘的另一个人成为“残暴的牺牲品”——他被绑在桩子上用火烧,阿贝内基人从他身上一点一点地切肉。女巫称这魔鬼为“黑人”,波士顿总督考顿·马瑟(Cotton Mather)说:“他们通常说他像个印第安人。”马瑟据此推测,黑人和印第安人是同一种魔鬼,是某种邪恶的工具。但折磨莫西·肖特的东西并非巫术,而是恐怖。 [65]
即便在没有受到攻击的年代和地方,也常有它们的消息,这些消息都带着恐怖色彩。起义遍地都是,即便没有起义,也有对起义的恐惧。定居者们一直怀疑、猜测、镇压的阴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想象出来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一群奴隶或印第安人在计划推翻现政府并建立自己的政府。
战争、叛乱和传言:其实殖民者最害怕的是革命。1733年,90名非洲奴隶占领了丹属圣约翰岛,并将其控制了半年。1736年,在安提瓜岛(Antigua),一群黑人“筹划并展开行动,将岛上的白人全部杀死,在奴隶群中建立新政权,他们将完全拥有该岛”,他们的领袖是一个叫科特的人,他“在他的乡民中……承担国王的角色”。 [66] 有时候,反叛者会面临庭审,但通常情况下并没有审判。在对印第安人发动战争时,英国人倾向于放弃他们早先持有的关于战争在什么情况下是正义的观点;他们倾向于先发动战争,然后再为战争辩护。在镇压和惩罚奴隶起义方面,他们放弃了陪审团审判和禁止严刑拷打的规定。在安提瓜岛,根据新法律的条款,被指控犯有阴谋罪的人会受到酷刑,而且这项法律规定,各式各样的惩罚是合法的:黑人男子被车裂、被饿死、被慢火烤死、被活活绞死。1738年,在楠塔基特(Nantucket),英国殖民者认为他们发现了岛上印第安人的阴谋,这些人“要消灭所有英国人,先在夜间烧掉他们的房子,然后持枪进攻”。印第安人对此计划的解释是“英国人先强行抢走了他们祖先留下的土地,还永久占有”。 [67]
征服永远是脆弱的,奴隶制永远不稳定。在牙买加,黑人和白人的比例是20∶1。有个叫库乔的人,逃出了种植园,自己在岛屿的内陆山区建立了若干小镇(英国人称之为Maroon,即“逃亡黑人”镇)。“第一次逃亡黑人战争”结束于1739年,停战条约的内容是英国人同意承认五个“逃亡镇”,并给予库乔及参战者自由和1500英亩土地。这曾是一场独立战争。
牙买加和安提瓜叛乱的消息在几个星期内就传到了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几天后又传到新英格兰。大陆上的英国殖民者在这些岛上有家属——他们的奴隶在那里也有亲人。奴隶和他们的主人一样,焦急地在每一艘到港的船上打听消息,互换传闻。1739年,南卡罗来纳发生了一场“史陶诺动乱”。那里黑人和白人的比例是2∶1,100多名黑人发动了武装起义,杀死了20多个白人。“卡罗来纳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黑人地区,而不是白人的定居地。”一名参观者写道。 [68] 叛乱者希望前往西属佛罗里达,那里的西班牙人已经承诺给逃奴自由。他们在行军途中高声呼喊着“自由!自由!”。他们的领袖叫杰米,生于安哥拉,会讲刚果语、英语和葡萄牙语,而且像其他叛乱领袖一样,他能读会写。 [69]
什么样的法律能平息这些叛乱?什么样的惩罚能避免奴隶革命?这是殖民地立法者在砖瓦木石混合构建的会堂里争论的问题,尽管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威胁要拆毁这些会堂。1740年,“史陶诺动乱”之后,南卡罗来纳立法机构通过了《黑人与奴隶安顿和管理法》,其中包括一套新的处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条款。它严格限制奴隶运动,确定了他们的待遇标准,设立了奴隶犯罪的惩罚制度,解释了他们的起诉程序,规定了审判他们的证据规程:在极刑案例中,起诉需由两名法官和一名陪审员(最少三人)在场听证。为防下一个杰米出现,像他那样教奴隶读懂书籍并宣扬自由,此法还规定,教授奴隶读书写字是犯法行为。 [70] 塞缪尔·帕切斯说,英国人相对于他们所统治的人民享有“文字优势”,他们要保持这种优势。
反叛的消息在殖民地传播迅速,这是因为尽管奴隶被限制学习,但殖民者自身的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殖民者开始印刷他们自己的册子和书籍,特别是发行自己的报纸。第一个成立于不列颠殖民地的出版社是在波士顿,于1639年成立。不列颠美洲殖民地的第一张报纸——《国内外公共事件报》( Publick Occurrences )于1690年在同一城市创刊。迫于审查,这张报纸只发行了一期,但创刊于1704年的第二张报纸《波士顿新闻通讯》( Boston News-Letter ),却坚持了下来。这张报纸的印刷车间在狭窄拥挤的波士顿城的一条狭窄拥挤的街道上,离公共用地不远,在公共用地上能看到羊在吃草,时常能听到母牛的哞叫,在教堂钟声的映衬下发出无尽的嗡鸣。 [71]
起初,殖民地印刷商报道最多的是欧洲的消息,但后来越来越多地开始报道相邻各殖民地实时发生的事情。他们还开始质疑权威,捍卫自身的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这一观念最激烈的倡导者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1706年出生于波士顿,是一个清教徒兼蜡烛和肥皂制造商的儿子。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父亲十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妹妹珍生于1712年,是父亲七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本杰明·富兰克林自学读书、写字,然后在家教妹妹。那时的女孩就像奴隶一样,几乎没人教她们写字(不过还是要教她们阅读,这样她们可以读《圣经》)。本杰明想当作家,父亲说可以,但只能负担得起他两年的学费(根本不送珍去上学)。他的哥哥詹姆斯在16岁时成为一名印刷匠,本杰明就当他的学徒。此时詹姆斯·富兰克林(James Franklin)开始发行一份挑战权威的报纸,叫《新英格兰报》( New-England Courant )。 [72]
《新英格兰报》不接受新闻界审查,它是新英格兰各殖民地中第一份“无执照”的报纸,意思是殖民政府没有给它颁发执照,也不在出版前审查内容。詹姆斯·富兰克林决定利用他的报纸批评政府和教会(当时二者基本上是一回事,而马萨诸塞奉行神权政治)。“你报纸的设计很简单,就是在取笑和辱骂上帝的神职人员。”考顿·马瑟生气地告诉他。1722年,詹姆斯·富兰克林因煽动性言论被捕。他入狱的时候,他弟弟这个勤奋的学徒接手报纸工作,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字首次出现在报头。 [73]
当他的小妹妹在家中浸蜡烛、熬肥皂的时候,年轻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决定将矛头指向政府。他刊登了《加图信札》( Cato’s Letters )这本书的一些选段。本书由两位激进派作家所著,一位是英国人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另一位是苏格兰人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全书收录144篇有关自由本质的文章,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没有自由的思想,就不会有智慧;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公众自由。这些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权利。”特伦查德和戈登写道。 [74] 珍·富兰克林也读到了这些文章,她在一个有叛逆思想的家庭中成长和学习,也开始考虑应该属于每一位女性的权利。
詹姆斯·富兰克林抗拒指控,出了狱,继续从事印刷出版,但在1723年,年轻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对哥哥嗤之以鼻,他放弃了学徒生涯,这也意味着他抛弃了妹妹珍。此后不久,15岁的珍结婚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了他“从碎布到富人”的崛起。这个短语在当时既有比喻的含义,也有字面的含义:纸张是由碎布制造的,而富兰克林作为美洲第一个纸币印刷商,把碎布变成了财富。珍有12个孩子,其中11个死掉了,她过着远不如18世纪美洲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的生活,她生得贫穷:从碎布到碎布。
本杰明·富兰克林把妹妹留在波士顿,而他最终定居在一个干净整洁的贵格会小镇费城,于1729年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宾夕法尼亚公报》( Pennsylvania Gazette )。在报纸上,他仍为出版自由而奋战。在1731年的一篇弥尔顿式的名为《印刷商的辩护》的文章里,他指出“人的见解如同他们的面孔一样千差万别”,但“印刷商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虽然人的见解不同,但争议的双方都有让公众听取他们见解的平等优势,当真理和谬误公平竞争时,前者将永远胜过后者”。 [75]
事实文化已从法律扩散到政府的经验主义理念,但还没有广泛散播到报纸上。报纸上满是船运的消息和抓获逃奴的广告,也有奴隶叛乱、印第安战争、议会最新会议的消息。报纸对真理感兴趣,但也确立真理,如富兰克林所说,通过发表各方意见,让他们去争议。印刷商并不认为他们有责任只印刷事实,他们认为有责任通过富兰克林所说的“人们的见解”来确立真理,让最佳者获胜:真理自然彰显。
虽然事实文化尚未扩散到报纸,但它已经渗透到历史中。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写道:“关于事实知识的记录就是历史。” [76] 美洲人从自己的历史事实中学到的一条教训与出版自由的限度有关,这些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实,是他们决定捍卫的自由。
詹姆斯·富兰克林在波士顿陷入官司之后,下一场争取出版自由的战斗又在纽约打响。纽约是北美大陆最繁忙的港口,荷兰人的非洲奴隶曾在城边修筑了一堵墙,英国人手下的非洲奴隶又把墙拆掉,留下了华尔街。1732年,新总督抵达纽约,进驻市政厅办公室,市政厅是由非洲奴隶用拆墙的石头建造的。
威廉·科斯比(William Cosby)是个讲究体面的乡巴佬。与大陆所有殖民地总督(四个除外)一样,他也是由国王钦定的。他既没有任何特殊资质担当这一职位,也和他统辖的人没有任何联系。这个人贪婪、腐败。为了推翻他的统治,纽约的一个律师,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朋友詹姆斯·亚历山大(James Alexander)雇用了一个叫彼特·曾格(Peter Zengger)的德国移民,于1733年创立新报纸,名为《纽约周报》( New-York Weekly Journal )。报纸的大部分内容是《加图信札》的文章选登,以及主旨相近的文章,这些均由亚历山大所写,但匿名发表。“从古至今,没有哪个民族失去过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但他们因为成为奴隶而失去全部自由。”亚历山大写道。他说的“奴隶”用的是洛克的原意:屈从于绝对专制统治暴君的人。他明显指的不是在他自己家居住和干活的非洲人。纽约人中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奴隶,奴隶建造了这座城,建造了城里巨大的石屋以及用木头和铁钉构筑的码头。他们挖土修路,也在黑人墓园挖好了自己的坟坑。他们挑泡茶的水,扛烧火的木,装船卸船,铺设奴隶市场的阶梯。但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属于他们。 [77] 科斯比冷漠霸道,像许多飞扬跋扈、性情暴烈的后任统治者一样,不能容忍任何批评意见。他下令烧掉曾格发行的所有报纸,并以煽动性诽谤罪将曾格这个给别人打工的穷商人逮捕。
当所有人都认为政党破坏政治秩序的时候——“党派是多数人疯狂,几个人受益。”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在1727年说——两个政治派别在乱哄哄的纽约城出现:宫廷党支持科斯比;国家党反对科斯比。“我们处在党派之争的烈焰当中。”丹尼尔·霍斯蒙登(Daniel Horsmanden)哀叹道。他是由科斯比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但是个心胸狭隘、尸位素餐之人。但伦敦距此3000英里之外,需几个星期的航行时间,纽约什么时候才能从暴政总督的统治下得到解脱?纽约人开始相信,党派也许“不仅有必要存在于自由政府之中,而且会极大地有助于公众服务”。正如一个纽约人在1734年所写:“政党之间是相互制约的,通过将彼此的野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来维护公共自由。” [78]
第二年,曾格在殖民地最高法院开庭受审,就是在那座石头建造的市政厅。人们并不知道报纸上的政论文章是由亚历山大所写,他担任曾格的辩护律师,直至科斯比任命的首席法官取消了他的辩护资格。后来是由费城精明老练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为他辩护。汉密尔顿并不认为曾格印发批评总督的文章涉嫌诽谤。相反,他说曾格所发表的文章内容是真实的——科斯比的确是一个十分恶劣的总督——相信陪审团不会不同意。在他的结束语中,汉密尔顿不仅借用了《加图信札》的素材,而且将此纽约的争议提高到史诗意义的层面,他雄辩的修辞手法到18世纪60年代已成常态,因为有更多的殖民地越来越痛恨英国的统治。汉密尔顿告诉陪审团,你们在此审理的“不是这位可怜的印刷商的事业,也不仅仅是纽约的事业。这是最重要的事业,是自由的事业” [79] 。
陪审团成员一致做出曾格无罪的裁决。科斯比于第二年羞愧地死去。但纽约人对党派之争的热情并未减退。一段时间内,甚至出现过有关内战的谈论。国家党继续对饱受争议的科斯比继任者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e)提出质疑。克拉克向伦敦汇报说,他惊讶地发现纽约人的一种信念,“如果总督不称职,他们可以罢免他,再换一个” [80] 。
人民可以罢免暴君,并用自己人替代暴君统治的想法当然并不令人吃惊:它隐藏在每一次奴隶反叛的背后。曾格审判事件后的几年里,他们担心这种阴谋会成为城市奴隶心中的恐惧,变成奴隶主自身难以摆脱的恶魔。1741年,全城燃起大火,克拉克的大宅——总督官邸——被焚为平地,许多纽约人坚信,大火是城中的奴隶点燃的。他们在计划一场反叛运动,除了更暴力些,就像18世纪30年代发生在安提瓜、巴巴多斯、牙买加和南卡罗来纳的反叛一样,而且与国家党掀起的反科斯比的叛乱并不完全相像。这些难道不是更可怕的党派之争的烈焰吗?
“黑人要起义了!”街头巷尾的纽约人高喊。城里的许多奴隶都是从加勒比地区来到纽约的;不少人来自发生过叛乱的岛屿。恺撒是一个荷兰面包师的奴隶,他同杰米(南卡罗来纳“史陶诺动乱”领袖)一样能读会写。恺撒还和一个白人女性生了孩子,是另一个跨越种族界线的例子。他是在纽约被捕的第一批奴隶之一,随之而来的是小道传言和他被屈打成招的消息。丹尼尔·霍斯蒙登觉得“城里的大多数黑人都是坏人”,他们计划杀害所有的白人,并选举恺撒为他们的总督。
纽约在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的事情在美洲政治史上奠定了一种格局。在霍斯蒙登的鼓动下,城里有150多名黑人被捕入狱,并遭到审讯。许多人遭受过折磨。曾格审判和恺撒等人的审判结果迥异。纽约白人认为,他们可以忍受党派之火的炙烤,可以容忍报纸上的政治异见,也可以忍受反对王室任命总督的政党,但以奴隶叛乱的形式出现,他们无法忍受。曾经裁定曾格无罪的法庭审讯定罪了30个黑人,判决13人绑在柱子上烧死,另外17人(与4个白人一起)被绞死。一个殖民者说1741年的处决行动是“一团黑人的篝火”。但这些也是党派的火焰。剩下的大多数被捕的黑人被迫离家,被卖到了加勒比海,这是一种被很多人看作比死亡更悲惨的命运。恺撒在绞刑架上拒绝认罪,被绞死在铁链上,他的尸体在街上示众达几个月之久,这样的处决是希望他的“例子和惩罚能够瓦解其他团体并引诱某些人披露邪恶的秘密” [81] 。但邪恶的秘密并不是什么阴谋,而是蓄奴制本身。
反叛的浪潮冲击着英国的大西洋海岸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从波士顿到巴巴多斯,从纽约到牙买加,从卡罗来纳又折回到伦敦。“统领大不列颠,统领巨潮;不列颠人从不做奴隶。”1740年出现在英格兰的一首诗成了帝国国歌,也是美洲的圣歌。谁也没有感到迷惘,早期现代世界里最强劲的自由呼喊来自这个世界的那块完全依赖蓄奴制的地方。
蓄奴制并非存在于政治领域之外。蓄奴制是一种政治形式,奴隶反叛是政治异见的一种暴力形式。“曾格审判”和“纽约奴隶阴谋”的意义远不止一场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争论和一场被挫败的奴隶叛乱:它们是一场关于政治反对派本质的辩论的一部分,它们共同确立了政治反对派的界限。据说科斯比的反对派和恺撒的拥护者都在计划罢免总督。一种反叛受到称赞,另一种叛乱受到镇压——这种分裂将一直持续下去。在美国历史上,自由和奴役之间的关系立即变得阴暗和深邃:黑人反叛的威胁给白人的政治反对派以可乘之机。美洲的政治传统是由哲学家和政治家缔造的,由印刷商和作家缔造的,但也是由奴隶们缔造的。
1754年5月9日,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公报》上发表了一张木刻图,标题是《要么联合,要么死亡》。画面上是一条蛇,被切成了八段,从头到尾用殖民地名称缩写标注: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

《要么联合,要么死亡》,木刻版画,1754年,本杰明·富兰克林作。该作品既可以看作一张政治漫画,又可以看作一张殖民地地图。美国国会图书馆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国王和女王一直为如何瓜分北美而争斗,好像北美土地是一块可以分切的蛋糕。他们标注自己的领土,给城镇起名,然后发动战争;他们在地图上标注主权,通过画线、着色来划分区域。1861年,一张名为《北美主要部分分区图,分别标明属于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若干州》的地图被插进了伦敦印刷的一本地图集中,颜色是手工加上的。地图只简略地标注了土著人的土地,在靠近新墨西哥处模糊地写着“阿帕奇”(Apache)。像很多地图一样,它很快就过时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707年结成了联盟,并继续与法国和西班牙进行断断续续的战争,战争蔓延到北美大陆,英国和法国都与印第安人结盟。殖民者以战时当政的国王或女王给这些战争命名:威廉国王战争(1689—1697)、安妮女王战争(1702—1713)和乔治国王战争(1744—1748)。北美最初分成了几大块,然后再继续分。
富兰克林的木刻画是一篇文章的插图,文章由富兰克林所写,内容是这些殖民地需要形成共同防御体系——对抗法兰西和西班牙,对抗印第安人的战争和奴隶的反叛。这时富兰克林48岁,已是一个有财富、有成就的人。他比其他贵格会市民穿着整洁,讲话温和有力。1754年4月,宾夕法尼亚总督任命他为专员,参加一个6月在纽约奥尔巴尼(Albany)举行的由各殖民地代表参加的会议,他们将与易洛魁联盟协商一项条约。易洛魁联盟即所谓的“六部族联盟”,包括莫霍克人、奥奈达人、奥农达加人、卡尤加人、瑟内萨人和塔斯卡洛拉人。“我们的敌人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们在同一个方向上,拥有一套行政体系和财务体系。”富兰克林写道,说明这种完整性是英国的美洲殖民地所缺乏的。 [82]
自从1723年富兰克林从波士顿放弃学徒离开之后,他考虑过许多关于北美殖民地公民意识的计划,这些计划伴随北美殖民地的向西扩展远离海岸、远离群岛、远离伦敦,也远离彼此而生。其中许多计划主要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来拉近各殖民地之间的距离。
作为新闻出版自由的斗士,富兰克林以各种方式推动知识的传播。1731年,他创建了美洲的第一个借阅图书馆——费城图书馆公司。1732年,他开始印刷出版《穷理查历书》( Poor Richard’s Almanack )。此书遍及各个殖民地,给美洲人提供了一个共有的箴言商店,甚至成为一部可以共享的政治史。如6月的那一页,富兰克林加了这样一些话:“公元1215年的本月15日,约翰国王签署了《大宪章》,宣布并确立英国自由。”1736年,富兰克林被选为宾夕法尼亚省议会文书;第二年,他就任费城邮政局局长,之后开始改进邮政服务。“建立新殖民地的最初艰辛任务(将人们的注意力仅限于必需品)现已圆满完成。”他在1743年的小册子《在英属美洲种植园中推广有益知识的提议》( Proposal for Promoting Useful Knowledge Among the British Plantations in America )中写道。美洲到处都有“思考之人”,他们投身实验、记录观察、勇于发现。“但考虑到土地幅员辽阔,这些人过于分散,很难见面、对话或相识,因此许多有益的细节知识仍得不到交流,随着发现者的离去而消失,永远不为人知。”所以他成立了美洲哲学协会——殖民地的第一个学者协会。 [83]
本着和创立图书馆与哲学协会同样的精神,富兰克林致力于邮政局局长的事业:他想让思想得到循环,如同血液在殖民地的血脉中流动一样。他巡游各殖民地,检查邮政通路。他计算它们之间的距离,以及从农场到农场,从城镇到城镇所需的时间。他还做了某种人口普查,计算人口并测算他们之间的距离。
到1750年,尽管绝大多数移居英国殖民地的移民都去了加勒比海地区,但生活在英属美洲的五分之四的人都去了13个大陆殖民地的其中之一居住。这个比例与不列颠美洲帝国不同地区的人口死亡率有关,移民到加勒比海的人成群成堆地死去。在新英格兰,英国定居者都比较长寿。南方殖民地与加勒比海地区有更多的共同点:黑人多,死亡率高。中部地区的殖民地比较混杂,混合居住着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非洲人,人口的健康情况优于加勒比,但劣于新英格兰。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大陆殖民地在18世纪中叶变得越来越相似:“从我走过的不同省份来看,我发现人们的行为举止和性格特征基本上大同小异。”苏格兰医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44年写道。这是他带着非洲奴隶卓莫骑马从马里兰巡游至缅因后的发现。 [84]
让美洲大陆殖民地变得更加相似的一个方法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专注于进行一次宗教复兴,产生一种更具表现力的宗教,对牧师的敬畏更少,多了精神的引力和天下所有灵魂的平等。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是一个来自英国的满腔热情的福音派牧师,他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信徒。怀特菲尔德苛刻且狂热,但同时也患有对眼病——不太友好的人送他个外号叫“斜眼博士”(Dr. Squintum)。怀特菲尔德由寡居的旅店老板养大,是一个出身极为普通的平民,但在美洲殖民各地,他吸引了各个城镇的社会各个阶层的“见证者”。他告诉他的信众,他们可以再生,进入耶稣的身体,并催促他们尽早摒弃保守牧师的各种信条。他说:“我情愿为你们入狱,为你们而死,但没有你们陪伴,我不愿进入天堂。” [85]
这也代表着一种革命:怀特菲尔德以失去牧师权威为代价,强调普通百姓同样神圣。1739年,费城的一个正统教牧师聚会决定,所有牧师必须拥有哈佛、耶鲁、英国或欧洲大学的学位。但怀特菲尔德是百姓的布道者,他的信众是农夫、工匠、水手和仆人。 [86]

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布道,1740年,约翰·科利特(John Collet)绘。怀特菲尔德的布道震撼了美洲的普通人,让他们心醉神迷,但他的布道也激发了人们的学习热情和思想独立,图中左下角戴着眼镜学习经文的女性便是一例。私人收藏/布里奇曼图片社
富兰克林对怀特菲尔德抱有怀疑,但对宗教,还有许多其他事情,他都有自己的判断。用他的话说,“反宗教的言谈等于是放虎归山”。在其他事情上,他有更多的言论。他巡视过众多的殖民地,测量过它们的面积,试图统计过人口数量,1751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人口规模的文章,叫《关于人口增长及区域人口增加等问题的一些见解》。
富兰克林想知道的是:如果殖民地的规模增长到比他们原居住地还大,其命运将会如何。殖民地的土地便宜,“便宜到一个懂农业、爱干活的人可以在短期内攒下足够的钱,买一块足够建一个种植场的新地。”如果这个人结了婚,有了孩子,他和妻子相信他们的孩子也会有广阔的地产。富兰克林猜测美洲大陆殖民地全部人口大约是“100万英国人”,而他推算,这个数字每25年将会翻一番。按这个速度,只需一个世纪,“海水的这一边将会成为英国人最多的地方”。
富兰克林的数字并不准确,他的估算不是太高,而是太低。当时,住在英属美洲大陆13个殖民地的人数是150万。这些殖民地的定居点比新法兰西或新西班牙的定居点人口更为密集。只有6万法国定居者生活在加拿大,路易斯安那还有1万多。新西班牙的定居点人口更分散、更稀少。在新法兰西和新西班牙,将定居者和原住民分开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因为太多人在那里组建了家庭。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这种类型的家庭常不被认可,大多数是主动保密。
富兰克林像后来很多美国人一样,在遇到肤色问题时失去了一贯的冷静。西属美洲殖民地是混血儿的地方,奴隶主在他们的遗嘱中释放奴隶为自由人,至1775年,自由黑人的人数已超过黑人奴隶。类似情形也出现在新法兰西,在那里,法国贸易商和印第安人组成的家庭叫“梅蒂斯”。那里和新西班牙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异族通婚,一同生养孩子已经有了几代人的历史。肤色在很多情况下标志着身份,但并未在奴隶人和自由人之间画线,而且肤色就是肤色:红色、棕色、粉色和黄色等。英国本土殖民地建立了一种截然不同且更加野蛮的种族制度,该制度只设想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只设想两种身份,奴隶和自由人。法律禁止跨种族通婚,规定奴隶母亲的孩子也是奴隶,并阻碍或禁止解放奴隶。奴隶主经常会和女性奴隶生孩子,但奴隶主并不把这些孩子当亲生的抚养,不会赐他们自由,或干脆不认这些孩子。他们把这些孩子看作奴隶,叫他们“黑人”。考虑到种族界限,富兰克林在关于人口的文章中又加了一些观察和见解,他写了一个新种族——“白种人”。
“世界上,纯白人的人数相对来说非常少。”富兰克林以此开头。在他看来,非洲人是“黑色”;亚洲人和美洲本土人是“黄褐色”;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俄国人、瑞典人和德国人是“黝黑色”。剩下的那些以英国人为主的少数人是世界上独有的“白人”。“我愿意看到他们的人数增加,”富兰克林犹疑地补充道,“但也许我偏爱我国家人种的肤色,因为这种‘偏爱’是人类的自然状态。” [87]
富兰克林在他“偏爱”自己人的“肤色”上卡壳了。这真的是“自然”吗?也许是。他显然对此感到困惑。但以其惯有的机警,他还是全写了下来,然后转向其他话题,即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纽带:要么联合,要么死亡。
在1754年奥尔巴尼会议(Albany Congress)上,富兰克林提出了一个“联盟计划”。联盟由“总主席负责,总主席由皇家任命和支持;联盟设大议会(Grand Council),由各殖民地人民代表各会议,选举产生”。联盟包括他在“蛇图”中标注的7个殖民地——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以及图中以“新英格兰”表示的4个殖民地——马萨诸塞、罗得斯、康涅狄格和新罕布什尔。
富兰克林的计划是按11个殖民地的人口多少分配代表人数(人口稀少的新罕布什尔和小小的罗得斯,每地2名;人口众多的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每地7名)。政府在费城开会,有权通过法律、签署协议、征款征兵“来保卫任何一个殖民地”,并保卫整个海岸线。奥尔巴尼会议的参会代表批准了联盟计划,并呈送他们的殖民地议会。殖民地议会担心这样会失去自己的权威,表示拒绝,英国政府也没有批准。如富兰克林所说,“计划被认为过于民主” [88] 。
富兰克林的联盟计划失败了。留存下来的是那幅木刻画,它和一个半世纪前缝制的波瓦坦鹿皮披风有许多共同之处。《要么联合,要么死亡》其实是张地图,但它是一张特殊的地图,被称作“分割的地图”。分割的地图是一种古老的拼图游戏,是用纸粘在木头上做的。最早的一张分割地图叫《以王国分裂的欧洲》,18世纪60年代出现在伦敦,制作者是个制图匠,曾给国王的地理顾问当学徒。那是个玩具,目的是教孩子们地理,同样教他们怎样理解王国的性质,以及统治的本质。
富兰克林的《要么联合,要么死亡》也有这等功效,他讲授了一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课,讲述了政治团体的性质。他对所有殖民地宣告:它们是整体中的部分。
[1] Gregory A. Waselkov,“Indian Maps of the Colonial Southeast,”in Powhatans’ Mantle: Indians of the Colonial Southeast , ed. Waselkov et al.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6) ,453–57 .
[2] James Stuart, The True Law of Free Monarchies i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I , ed.Charles Howard McIlwa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598] 1918) ,310. And see Glenn Burgess,“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Reconsidered,”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7 (1992) :837–61 .
[3] “The First Charter of Virginia, April 10, 1606,”in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Colonial Charters, and Other Organic Laws , ed. Francis Newton Thorpe, 7 vols. (Washington,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9) ,3:3783. On Jamestown, see James P. Horn, Adapting to a New World: English Society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and Karen Kupperman, The Jamestown Project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The First Charter of Virginia, April 10, 1606.”
[5] Ibid.
[6] 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Linda Colley, Captives: Britain, Empire and the World, 1600 – 1850 (London:Jonathan Cape, 2002); David Armitage and Michael J. Braddick, eds.,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1500 – 180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7] Daniel J. Hulsebosch,“English Liberties Outside England: Floors, Doors, Windows, and Ceilings in the Legal Architecture of Empire,”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w and Literature, 1500 – 1700 , ed. Lorna Hut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ch. 38.
[8] John Locke in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and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 ed. Mark Goldie (16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4, 63.
[9] 出自《伊索寓言》,驴子披着狮子的皮,但是一叫就露馅儿。——译者注
[10] Paine, Common Sense , 12.
[11] Edward Coke, The First Part of the Institutes (1628; London, 1684) ,97b. On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charters, see Ken MacMillan, Sovereignty and Possession in the English New World: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Empire, 1576 – 164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79–86. On Coke, see Daniel J. Hulsebosch,“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Expanding Empire: Sir Edward Coke’s British Jurisprudence,”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1 (2003) :439–82.For a dissenting view on Coke’s contribution to the 1606 charter, see Mary S. Bilder,“Charter Constitutionalism: The Myth of Edward Coke and the Virginia Charter,”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94 (2016) :1545–98, especially 1558–60.
[12] John Smith, Complete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 ed. Philip L. Barbour, 2 vol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1: lⅷ. I discuss Smith and the Jamestown colony in The Story of America: Essays on Orig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 1.
[13] Kupperman, The Jamestown Project , 58, 64–68.
[14] John Smith, Captain John Smith , ed. James Horn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7) ,44.
[15] Ibid. , 42; Smith, Complete Works , 1:207.
[16] Edmund S.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 Norton, 1975), chs. 3 and 4.
[17]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 78.
[18] A True Declaration of the Estate of the Colonie in Virginia (London, 1610) ,11.
[19] Smith, Complete Works , 2:128–29.
[20] Smith, Captain John Smith , 1100–1101; Smith, Complete Works , 1:ⅹⅳ.
[21]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165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9) ,96–97. On Hobbes and the Virginia Company, see Noel Malcolm,“Hobbes, Sandys, and the Virginia Company,”in Aspects of Hobb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3–79.
[22]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 108–9, 158–59.
[23] Martha McCartney,“Virginia’s First Africans,” Encyclopedia Virginia , Virginia Foundation for the Humanities, July 5, 2017.
[24] 该隐(Cain)是《圣经》中的杀亲者,因为憎恶弟弟亚伯(Abel)而把亚伯杀害,后受上帝惩罚。——译者注
[25] Sowande’M. Mustakeem, Slavery at Sea: Terror, Sex and Sickness in the Middle Passag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6), introduction and ch. 5 (quotation, 117). Also see Marcus Rediker, The Slave Ship: A Human History (New York: Viking, 2007).
[26] Samuel Morison, introduction to William Bradford, Of Plymouth Plantation, 1620 – 1647 (New York: Knopf, 1952) ,ⅹⅹⅵ–ⅹⅹⅶ.
[27] Bradford, Of Plymouth Plantation , 3, chs. 9 and 10.
[28] Stephen Church, King John: And the Road to Magna Carta (New York: Basic Books,2015) ,21.
[29] Quoted in Nicholas Vincent, ed., Magna Carta: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5–16. And on the general question, see R. C. van Caenegem, 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2–3.
[30] Vincent, Magna Carta , 12.
[31] David Carpenter, Magna Carta (New York: Penguin, 2015) ,252.
[32] Quoted in Carpenter, Magna Carta , ch. 7.
[33] Church, King John , 148; Carpenter, Magna Carta, 81; Nicholas Vincent, ed., Magna Carta: The Foundation of Freedom, 1215 – 2015 (London: Third Millennium Publishing, 2015) ,61–63.
[34] Church, King John , 210.
[35] Magna Carta, 1215, in G. R. C. Davis, Magna Carta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63) ,23–33 .
[36] Quoted in The [Cobbett’s]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 ed. William Cobbett and J.Wright, 36 vols. (London, 1806–20) ,2:357.
[37] On this transformation, see Leonard W. Levy, The Palladium of Justice: Origins of Trial by Jury (Chicago: I. R. Dee, 1999); John H. Langbein, Torture and the Law of Proof (1977;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aul R. Hyams,“Trial by Ordeal: The Key to Proof in the Early Common Law,”in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 Essays in Honor of Samuel E. Thorne, ed. Morris S. Arnold et al.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Robert Bartlett, Trial by Fire and Water: The Medieval Judicial Orde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38] Barbara J. Shapiro,“The Concept ‘Fact’: Legal Origins and Cultural Diffusion,” Albion 26 (1994) :227–52; Barbara J. Shapiro, A Culture of Fact: England, 1550 – 172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See also Lorraine Daston,“Marvelous Facts and Miraculous Evid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ritical Inquiry 18 (1991) :93–124; Mary Poovey,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Fact: Problems of Knowledge in the Scieuces of Wealth and Socie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Lorraine Daston,“Strange Facts, Plain Facts, and the Texture of Scientific Experience in the Enlightenment,”in Proof and Persuasion: Essays on Authority, Objectivity, and Evidence ([Tournai]: Brepols, 1996) ,42–59.
[39] James I, Speech in the Star Chamber, June 20, 1616, in J. R. Tanne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Reign of James I: 1603 – 16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19.
[40] Vincent, Magna Carta , 4, 90. Vincent, Magna Carta: The Foundation of Freedom , 108.
[41] John Winthrop, A Modell of Christian Charity (Boston: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1630] 1838) ,31–48. See also Edmund S. Morgan, The Puritan Dilemma: The Story of John Winthrop (Boston: Little, Brown, 1958).
[42] Quoted in Karen Kupperman, Providence Island, 1630 – 1641: The Other Puritan Colon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8.
[43] Winthrop, A Modell of Christian Charity ; Edward Winslow, Good News from New England , ed. Kelly Wisecup (1624;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4), 114; John Winthrop, February 26, 1638, Winthrop’s Journal“History of New England,”1630 – 1649 , ed. James Kendall Hosmer (New York: Scribner, 1908) ,260. On the conversion mission, see Lepore, The Name of War . On New England and slavery, see Wendy Warren, New England Bound: Slavery and Colonization in Early America (New York: Liveright, 2016) .
[44] John Harpham,“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American Slavery,”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2018, ch. 2.
[45] Quoted in Harpham,“Intellectual Origins of American Slavery,”28, 32.
[46] Harpham,“Intellectual Origins of American Slavery,”34.
[47] Quoted in Vincent Brown, The Reaper’s Garden: Death and Power in the World of Atlantic Slave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5. For slavery, broadly, see also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 ; Winthrop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 – 181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8) ;Peter Kolchin, American Slavery 1619 – 1877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3); Ira Berlin, Many Thousands Gone: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 Slavery in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8] Quoted in Stanley Engerman, Seymour Drescher, and Robert Paquette, eds., Slave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5–13.
[49] Quoted in A. Leon Higginbotham Jr., Shades of Freedom: Racial Politics and Presumptions of the American Legal Proc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8–27.
[50] Annette Gordon-Reed, The Hemingses of Monticello: An American Family (New York: Norton, 2008) ,45.
[51] “Massachusetts Body of Liberties of 1641,”in The Colonial Laws of Massachusetts , ed.W. H. Whitmore (Boston, 1890), clause 91 on 53.
[52] Edmund S. Morgan, 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1988), chs. 3 and 4.
[53] Ibid., 72–87.
[54] John Milton, Areopagitica: A Speech of Mr. John Milton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d Printing, to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London, 1644) ,30.
[55] Roger Williams to the Town of Providence, January 15, 1655, in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Roger Williams , 7 vols.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3) ,6:278–79.
[56] William Penn, The Frame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ovince of Pennsilvania [ sic ] in America (London, 1682) ,11.
[57] Although the Second Treatise was not published until 1689–90, Locke wrote parts of it in or around 1682, including the chapter“Of Property,”at a time when he was revising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 David Armitage,“John Locke, Carolina, and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 Political Theory 32 (2004) :602–27.
[58] “Charter of Carolina and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in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Colonial Charters, and Other Organic Laws , 5:2743, 2783–84.
[59] Armitage,“John Locke, Carolina, and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
[60] Sir Thomas More, Utopia , ed. Edward Sur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76.
[61] Armitage,“John Locke, Carolina, and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And,broadly, see also John Dun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Argument of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and Jeremy Waldron, God, Locke, and Equality: Christian Foundations of John Locke’s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2] Great Newes from the Barbadoes, or, A True and Faithful Account of the Grand Conspiracy of the Negroes Against the English (London: Printed for L. Curtis, 1676) ,9–10;Nathaniel Saltonstall, A New and Further Narrative of the State of New-England (London, 1676) ,71–74; Lepore, The Name of War , 167–68. And see also Stephen Saunders Webb, 1676: The End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Knopf, 1984).
[63] Christine Daniels,“‘Without Any Limitacon of Time’: Debt Servitude in Colonial America,” Labor History 36 (1995) :232–50.
[64] Quoted in Berlin, Many Thousands Gone , 97.
[65] Mary Beth Norton, In the Devil’s Snare: The Salem Witchcraft Crisis of 1692 (New York:Knopf, 1998), quotations on 58–59.
[66] “A Full and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Negro Plot in Antigua,” New-York Weekly Journal ,March 28, April 4, April 11, April 18, April 25, 1737. And see David Barry Gaspar, Bondmen and Rebels: A Study of Master-Slave Relations in Antigu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 ,3–62. I discuss some of these episodes and write, broadly, on fears of Indian wars and slave rebell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 in Jill Lepore, New York Burning: Liberty, Slavery, and Conspiracy in Eighteenth-Century Manhattan (New York: Knopf, 2005).
[67] New-York Weekly Journal , March 28, 1737; Pennsylvania Gazette , October 19 and 20, 1738.
[68] Quoted in Alan Taylor, American Colonies (New York: Viking, 2001) ,238.
[69] On Stono, see Peter Wood, Negroes in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from 1670 through the Stono Rebellion (New York: Norton, 1974); Peter Charles Hoffer, Cry Liberty: The Great Stono River Slave Rebellion of 17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ck Shuler, Calling Out Liberty: The Stono Slave Rebellion and the Universal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9).
[70] “An Act for the Better Ordering and Governing Negroes,”1740, in David J. McCord,ed., The Statutes at Large of South Carolina , 22 vols. (Columbia, SC: A. S. Johnston, 1840) ,7:397.
[71] Most usefully, see Charles E. Clark, The Public Prints: The Newspaper in Anglo-American Culture, 1665 – 174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72] On Jane Franklin, and on her relationship with her brother, see Carl Van Doren, Jane Mecom, the Favorite Sister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Viking, 1950), and Jill Lepore, Book of Ages: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Jane Franklin (New York: Knopf, 2013). Much of their correspondence is reproduced in The Lett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and Jane Mecom , ed. Carl Van Dor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but here I instead cite the online PBF . Van Doren refers to Jane Franklin throughout, by her married name, Jane Mecom; but for clarity I here refer to her throughout as Jane Franklin.
[73] Cotton Mather quoted in J. A. Leo Lemay, The Life of Benjamin Franklin , 3 vols.(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6) ,1:114. And see Perry Miller, introduction to The New-England Courant: A Selection of Certain Issues (Bosto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1956) ,5–9; and Thomas C. Leonard, The Power of the Press: The Birth of American Political Report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 1.
[74] John Trenchard and Thomas Gordon, Cato’s Letters: Or, Essays on Liberty , 4 vols. (4th ed.; London: W. Wilkins et al., 1737), Letter No. 15, 1:96.
[75] Benjamin Franklin,“Apology for Printers,” Pennsylvania Gazette, June 10, 1731.
[76] Hobbes, Leviathan , 64.
[77] Lepore, New York Burning , preface. My brief discussion here of Zenger’s trial and the 1741 slave conspiracy follows this earlier, book-length account of these same two signal events.
[78] Ibid.,–ⅹⅶ.
[79] Ibid., ch. 4.
[80] Ibid.,–ⅹⅵ.
[81] Ibid.,–, 89–90.
[82] Benjamin Franklin to Richard Partridge, May 9, 1754, and The Albany Plan of Union,1754, PBF . See also Taylor, American Colonies , 424–28.
[83] Benjamin Franklin,“A Proposal for Promoting Useful Knowledge,”May 14, 1743, PBF .
[84] Alexander Hamilton, Gentleman’s Progress: The Itinerarium of Dr. Alexander Hamilton, 1744 , ed. Carl Bridenbau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48) ,199.
[85] Quoted in Albert David Belden, George Whitefield, the Awakener (New York: Macmillan,1953) ,4–5.
[86] Gilbert Tennent, A Solemn Warning to the Secure World, from the God of Terrible Majesty (Boston, 1735) ,102.
[87] Benjamin Franklin,“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Peopling of Countries, &c.,”1751, PBF .
[88] Benjamin Franklin,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 PB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