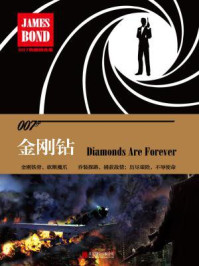明月从窗棂处照耀进来,灯烛晃动,月光也跟着晃动,所有人的影子都变形,摇曳。庭院清晰传来那巨狼的四足踩在地面上的“咔咔”之声。
大堂内一片寂静,众人神色各异。
“原来,你来青墩戍是在设一个局!”令狐瞻苦涩,“是以奎木狼为饵,吸引我们来。”
玄奘无言地望了他半天:“也不算设局。贫僧知道你们会来,也知道奎木狼会来,只是以自身为饵,四方碰撞,碰撞出真相罢了。”
“四方?还有一方是谁?”令狐瞻问。
玄奘转头望着林四马:“自然便是这位林戍主。”
“我……”林四马倒退了几步,目露惊恐。
“如今你还要说,自己在鬼魅碛中斩杀了吕晟吗?”玄奘问。
林四马身子一软,彻底崩溃在地。他魁梧粗豪,身负横推四马之力,勇冠三军,可如今刀就在手边,却拿不动了。
鱼藻愤恨地冷笑:“你既然知道我是谁,便很清楚此事不可能擅了,除非你能把我们所有人杀得干干净净,否则你身为大唐边将,私纵胡商走私,与人勾结谋害监军吕晟,受人良田大宅,一桩桩一件件,足够你抄家灭门!”
“我没有错!”林四马双眼血红,坐在地上惨笑,“八大士族统治敦煌近千年,农家为其耕作园囿,打窟人给他们凿山造窟,牧人给他们放牧牛马羊,其他百工各业各有行会,石匠打石头,画匠、塑匠作壁画,铁匠、木匠、泥匠各有所司,这千年来我贫家百姓就是这样过的,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人都在为士族效力,谁都不能脱离这张巨网。少年时在子亭镇的山上放牧,我也曾仰望过天空,我也曾站在山顶,朝着山脚下看过一眼的。可是我又能如何?我家只是最卑贱的锅子匠,祖祖辈辈以修补锅釜为生,敦煌从来就没有一个寒素之人能穿上丝绸做的袍子,能进入泮宫摸一摸书卷。”
“那是你们自己不努力!”令狐瞻冷冷地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书卷人人可读,我们士族又不曾禁绝诗书。”
“我不努力?”林四马一跃而起,怒不可遏地扯开衣袍,露出疤痕交错的胸口,“老子在大唐边疆厮杀多年,多少次险死还生,这叫不努力?你们的确不曾禁绝诗书,可我们一家三个男丁,中原地多,每个男丁授田百亩,敦煌这里每一户只能均田六十亩。农田亩产两石,每一户收成一百二十石,脱壳后收成七十二石,我们六口之家每年自用四十五石,要缴纳租六石,一年下来只能存储二十一石粟麦,除了换盐巴、酒醋、农具铁器等日常所需,还要备用灾荒、疾病、人事等应急,还要缴纳绢二丈、绵三两,承担杂徭和色役,官府和士族还要征丁修渠。一家人终日劳作尚且忙碌不堪,谁家敢让子孙脱产去读书?”
令狐瞻张口结舌,半晌才道:“这并非是我敦煌士族压榨,整个大唐天下都是如此。”
“是啊!”林四马黯然,“所以人啊,一旦仰望过天空,就没法再容忍卑贱了。这个牢笼覆盖了敦煌,覆盖了大唐,既然谁都挣不脱,我只好另辟蹊径。当年你们令狐氏来找我,要我出卖吕晟来换取大宅、良田、正八品下的宣节副尉,我想也没想便同意了。哈哈——”林四马惨笑,“为何不同意?这是我期待一生的机遇啊!”
林四马疯狂地大笑着,魁梧的汉子像个娃娃般乐不可支。
“林戍主,”玄奘叹息,“你在陷害吕晟的局中,都做了些什么事?”
林四马擦擦眼泪,笑道:“其实我也没做什么。之前与法师讲的句句属实,只是最后有所欺瞒。那一日我们逃进鬼魅碛中,我只是把吕晟打晕了,捆绑起来交给了令狐德茂,另外烧焦一具袍泽的尸体,斩掉脑袋冒充吕晟,交给了官府。”
“交给了令狐德茂?”玄奘盯着令狐瞻,“你们真是胆大包天,竟然敢私下囚禁一位大唐状头,西沙州录事参军!”
“法师猜错了。”令狐瞻冷冷地道,“事已至此,我也不隐瞒,吕晟并非我们私下囚禁,而是经过刺史杜予和州长史商议,将他关押在敦煌县衙的地牢中,并且还行文秘奏朝廷。”
“胡说!”鱼藻喊道,“你们明明是陷害吕晟,又用焦尸假冒他被杀,怎么还敢把他交给官府?”
令狐瞻冷笑:“十二娘子,这是两件事。有没有人陷害吕晟是一件事,吕晟通敌叛国是另一件事。如果是区区一个西沙州录事参军叛国倒罢了,可是一个大唐双科状头叛国,便是连皇帝陛下都承受不起。我们令狐氏做的,便是掩盖朝廷的颜面,拿一只头颅来宣称吕晟已诛。至于真正的吕晟,则交由官府秘密处置。”
玄奘恍然:“原来竟然是皇帝亲自盖棺定论的。令狐德茂真是谋算缜密,如此一来,他不但让令狐氏脱身事外,还让吕晟彻底身败名裂。”
“倒也不算皇帝盖棺定论,”令狐瞻道,“奏疏报上去之后,陛下并无只言片语的回复,留中不发。这其实也在我父亲预料之中,皇帝承受不起这种屈辱,故作不知。后来陛下褫夺了杜予等人的官职,对牢狱中的吕晟却是不闻不问,显然就是希望他自己瘐毙于狱中,不要再张扬此事。”
鱼藻泪水婆娑。
玄奘问道:“后来吕晟如何从狱中出来,变成了奎木狼?”
“不知。”令狐瞻坦然道,“我迎亲那日,他突然出现,在长街上掳掠杀人。后来我们去狱中查看,铁枷脱落,两名狱吏死于狼爪之下。到底是吕晟化作了狼,还是狼化作吕晟,我实在不知,但无论他们是谁,都是我要猎杀的仇敌!”
“当年本尊在天庭时,无数次透过亿万里尘埃遥望下界,众生如蚁,朝来夕死。天人一闭眼,一打盹,便是你们的一生。你们的恩仇在本尊看来极为可笑,本尊酒后睡一夜,那恩仇便随着你们的生命消散掉了,所以毫无意义。”庭院中忽然响起“咔咔”声,似乎是奎木狼来到大堂门口,口吐人言,“法师,你要本尊等到何时?”
李澶喊道:“你要怎么样?”
“本尊此来是为了夺取天衣,”奎木狼淡淡地道,“这些天本尊想了个法子,天衣乃是不散不灭之物,若是把玄奘焚烧成灰烬,天衣自然便会重现。所以,法师就跟随本尊去一趟玉门关吧。我已准备好了三昧真火台,保准你刹那成灰。”
“休想!”李澶大怒。
玄奘阻止他,淡淡道:“贫僧只问一个问题,便随你去玉门关——吕晟在何处?”
“到了玉门关,本尊让你见到他,”奎木狼道,“方才有一件事你猜错了,在莫高窟时我之所以没杀你,是因为吕晟交代过,不得害你性命,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他放过你两次。玄奘,你走是不走?”
“好,我跟你走。”玄奘道。
鱼藻和李澶大吃一惊,一起道:“不可——”
连李淳风也劝道:“法师,在长安时我就听说过您的名头,您是佛门千里驹,承载着佛门振兴的希望。您出关西游,路上虽然艰险,却是为求证大道,何必把有为之躯抛在此处呢?”
玄奘笑道:“多谢李博士。不过对于贫僧而言,出长安便是西游路,路上的一灾一劫,一饮一啄都是大道坎坷,贫僧不敢逃避。何况,”玄奘望着门外,神情忧伤,“当年我与吕晟有过约定,要携手求证心中大道,我们道不同,路也不同,可是我们要共创的那个未来世界却相同。如果他倒在中途,我想知道他为何而败,那条路为何走不通。这样我才会知道,我的路该如何走。”
“无论是敌是友,是善是恶,贫僧感念各位装点这大千世界,璀璨人间。”玄奘坦然地望着众人,深深鞠躬,双手合十,右手顿时被扎得鲜血淋漓。他脸上却含着温和的笑容。
玄奘转身走到大堂门口,正要拉开门,手臂却被人拽住,回头一看,是索易。
“法师稍等,且让我为法师开道!”索易笑了笑,拉开门走出去,然后把门轻轻合上。
门并没有关严,微微露出缝隙。从大堂里望出去,白色的狼身占据了视野,索易似乎和奎木狼面对面站着。
索易不知说了什么话,奎木狼口吐人言,声音沉闷:“你这是何苦?”
“也没什么苦不苦的。”索易道,“老朽这辈子沉溺术数,虽然窥视天道,却拿这些东西来替人占卜、堪舆——相痣、称骨、解梦、占婚嫁,直到吕晟把我驳得一败涂地,我才发现自己这辈子窥探天机竟然只为赚人钱财。那时起,曾经的敦煌大术士索易便已经死了。今夜再死,也无非死一个躯壳而已。当初我为了救你,哪怕自绝于家族,也从未想过回报,今日却想要你回报我。我不管你是奎木狼还是吕晟,你都要答应我一件事,让玄奘法师西游天竺,求证大道。”
“你做什么?”奎木狼怒吼。
众人一惊,一起从门缝里往外看,也不知索易做了什么动作,门缝里只看见奎木狼身躯一点点后退,最终索易的身躯定格在门缝中,只见奎木狼的一只利爪插在索易胸口,索易一步一步向前走,那利爪在他体内越陷越深,最终抓穿了心脏。
“我不会答应你的!”奎木狼怒道。
索易口角流血,朝门缝看了一眼,身子一软,胸口从狼爪处拔出,带出一蓬鲜血,摔倒在地。他脸上仍然含着笑容,喃喃道:“《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索老丈!”玄奘惊叫一声,正要冲出去,林四马拦在他身前。
林四马从旁边抄起一把七尺长的陌刀,叹道:“法师,索易已经是必死之人,求死得死。今夜还有一个必死之人,便是末将。”
“林戍主,不可轻生!”玄奘急了。
林四马弹击着陌刀,慨然道:“末将为了一己之私,做过很多错事,纵容走私,收取贿赂,陷害吕晟,勾结马匪,一桩桩一件件说也说不完,论唐律也是一个斩首之刑。可老子当年既然仰望过天空,如何甘心像条狗一般,死在那臭烘烘的刑狱之中?”林四马霍然拽开门,大吼,“老子是大唐边将,且让我为法师开辟那西游大道!”
奎木狼蹲踞在庭院中,巨大的身躯傲然屹立。旁边是索易的尸体。
林四马挥着七尺陌刀,冲向奎木狼,一声怒吼,凛冽的刀光疾如奔雷闪电。奎木狼冷冷一笑,身子一闪即逝,已经到了林四马身后,利爪抓向他脖颈。林四马身子一拧,陌刀反转,斩向奎木狼。“当”的一声巨响,陌刀和利爪碰撞,火星四射,一人一兽都踉跄一步。
“好大的蛮力。”奎木狼冷笑。
玄奘、李澶、鱼藻、令狐瞻和李淳风等人纷纷来到庭院中,紧张地盯着庭院中的缠斗。那奎木狼身形飘忽,快如闪电,时隐时现,而林四马刀长臂长,刀光纵横,周围一丈二尺的虚空仿佛充斥着刀光,将整个空间都剿得粉碎。陌刀不时劈砍在四周的胡杨、墙垣和车辆上,挡者无不披靡,杀得烟尘滚滚,木屑纷飞。
林四马口中大呼酣战,这贪腐成性的边将仿佛将积年的勇悍之气彻底激发,一人一刀竟然杀出千军辟易的惨烈,但仍然抵不住奎木狼的神通秘术,乌沉沉的狼爪似乎随时在虚空中出现、隐没,每一次都会在林四马身上撕裂出一条血口,片刻之间,林四马身上血肉横飞,遍体鳞伤,有些地方甚至连白骨都露了出来。
林四马却毫不在意,甚至哈哈大笑着,唱起大唐的军中歌谣:“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
一个“人”字出口,血光之中利爪一闪,林四马的脖颈被撕裂,人头落地,颈血冲天而起。只有无头的尸体仍然握着陌刀,屹立半晌,最终轰然倒地。
玄奘泪流满面,他仍然记得,林四马口中所唱的歌谣乃是当年秦王扫平王世充之后,吕晟以旧曲填入新词,在长安城外万人齐唱,迎接凯旋的将士,遂成大唐军中之乐。
卯时日始。一轮红日起于大漠之上,边城如血。昨夜死伤的尸体仍未收殓,到处可见残肢断臂,尸体枕藉。
令狐瞻、李淳风等人站在城墙上沉默地送别。
玄奘走出青墩戍,骑着一匹马,背着朝阳向西而行,鱼藻和李澶骑着马跟随在他身后,马背上载着干粮、饮水和毡毯。远处沙碛中,一头巨狼蹲踞在马背上,正等待着玄奘。
玄奘转过马头:“十二娘,李琛,你们还是回去吧,贫僧此去注定会死,没办法保证你们的安全。”
鱼藻淡淡道:“法师,我从来不需要任何人保护。哪怕死了,我也要得见真相。”
“何苦如此,”玄奘明白她的心意,“那玉门关如今已经是妖窟魔巢,你便得见真相又如何?”
“心总是不甘吧。”鱼藻道,“我准备好接受最残酷的真相,可是不亲眼看到,我想我永远会在这大漠上兜兜转转。生和死,跟有些事情比起来,不算最大。”
玄奘没再说什么,转向李澶:“你呢?”
“我——”李澶看了看鱼藻,“师父,其实这些天我一直不明白,您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去西游,到底要找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哪怕找到了,万里流沙,您若回不来又有何意义?现在我有一些明白了。”
“哦?”玄奘倒感兴趣了。
“师父,”李澶笑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也不是合格的……少东家,眼见家里生意不好,父亲日夜忧愁,却没有丝毫热血去分担这份职责,也不知道该如何做。可是如今我爱上一人,我愿意追随她到地老天荒,我不知道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可是我愿意这么千难万险地走下去,不计生死。因为这让我感受到自己还活着,还有血能燃烧。”
鱼藻冷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追花逐蝶的纨绔之行说得如此豪迈……嗯?”她猛然回过味,眉毛顿时竖了起来,“你说的是我?”
“是啊!”李澶微笑地望着她,“你大可以拿刀斩了我。”
鱼藻怒气勃发,却无可奈何,恨恨地不搭理他。
三人正要策马疾驰,忽然两名部曲搀扶着令狐瞻从青墩戍中走了出来:“法师!”
玄奘勒住马匹:“令狐校尉。”
令狐瞻推开部曲,挣扎着走到玄奘旁边道:“法师可否到这边说话?”
玄奘下马,随着令狐瞻走到一旁。
令狐瞻低声:“法师,我来是想拜求您一件事。”
“请说。”玄奘道。
令狐瞻凝望着远处的奎木狼,咬牙切齿:“法师,在这之前我想让您知道,我令狐瞻不是懦弱之人。原本我也应该像那林四马一样,纵然不敌而死,也无怨无悔。可是……可是……”
令狐瞻露出难言的痛苦,脸上肌肉扭曲。
“贫僧知道。”玄奘温和地道,“贫僧此去便是为了解除奎木狼之祸,不希望再死人。”
“可是我真的想抽出这把刀……”令狐瞻喃喃地道,“昨夜原本还有一个必死之人,那便是我。我来时发过誓,不杀奎木狼,不收骸骨,不葬祖坟。可是我如今这模样,不敢轻易言死。”
“我知道。”玄奘道,“令狐校尉,死者已矣,活着的人若不能破那贪嗔痴,烦恼障,你便也如同这奎木狼一般,起于我见,坠堕边邪,轮回生死。”
“烦恼障,贪嗔痴……”令狐瞻念着,“痴为何也称为一障?”
“痴又称作无明,痴者,便是痴愚,众生心性迷暗,迷于事理。所以佛家说,诸烦恼生,必由痴故。”玄奘解释道。
“迷于事理……迷于事理……”令狐瞻喃喃地道,“从武德九年翟纹被掳到现在,我执着于猎杀奎木狼,三年中与他交手八次。世人都认为我与翟纹相爱太深,要为她复仇。可是法师知道吗,其实我与翟纹见面不过两次,如今我连她的模样都记不清了。”
“哦?”玄奘倒有些吃惊了,“她不是你的妻子吗?”
“是啊!”令狐瞻苦涩,“虽然说令狐氏和翟氏世代交好,五服之内有多人通婚,可是不论令狐氏还是翟氏,都是千年汉家士族,讲究礼法门风,尤其是五胡乱华以来,胡风侵袭,我们士族更加恪守礼法,我和翟纹婚前根本没有见过。唯一见过的两次,一次是在她十三岁那年上巳日,在水渠边举行祓禊之祭,一次是她十六岁那年在我族中一位翟氏夫人去世的葬礼上。我们的婚事也是族中长辈安排的,他们说,令狐氏和翟氏这一代必须联姻,于是我们就成亲了。”
玄奘怜悯地看着他,出身士族,联姻其实是作为一个士族子女必须尽到的义务。自古以来,士族门阀最讲究的有两条:一是婚姻,二是仕宦。便是靠官位来维持高门大族的政治地位,靠联姻来保持士族和寒族的界限。
一个士族门阀往往是历经几百上千年形成的,哪怕改朝换代之后政治上并未得势,依靠强大的社会认同感,几十上百年也不会掉品。真正打击士族的,反而是来自婚姻——士族绝不能与杂姓寒族联姻。北魏《氏族志》便规定: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婚。如有犯者,剔除士籍。
而士族真正的礼崩乐坏,便是北朝时滥觞的为了索取高额聘财,嫁女给寒庶杂姓,如同商贾一般讨价还价,甚至明码标价。这直接导致士族标榜几百年的礼法门风开始崩塌。
敦煌士族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地处边疆,胡风盛行,那些胡人莫说是门第,便连汉人的日常礼法也并不遵循。在敦煌城外一些胡人归化的乡里,婚姻上仍然盛行收继婚制,夫丧之后嫁给其弟或其子。
敦煌士族要维持其赫赫门阀,就必须更古板地遵循礼法门风。
另有一点便是敦煌处于商贸中枢之地,自北朝到隋唐,大量寒族杂姓通过商贸攫取巨额财富,或者通过改朝换代骤然得了高官显职,而这些家族一旦在财富或官位上立足,必然挑战士族的社会地位。前者如百年前的吕氏,后者如今日的刺史王君可。因此在敦煌这种远离中原,相对孤立和半封闭的地域,士族们的联姻更加迫切。
“虽然我和翟纹并不相熟,也还没洞房,可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那一夜,奎木狼在敦煌长街上掳走翟纹,不但是我令狐氏的奇耻大辱,更是我令狐瞻的奇耻大辱。”令狐瞻道,“若是她当时被杀倒也罢了,于贞洁无碍,可她是被掳……一个青春貌美的女子被人掳走,会遭遇什么,法师想必很清楚。昨夜法师推测我当时杀人是为了掩盖吕晟出现的消息,这当然重要,其实就我而言,我杀人是因为他们一口咬定翟纹是被人掳走,而不是被狼掳走!”
这“人”和“狼”两字令狐瞻咬得很重,玄奘顿时便明白了。对士族的家风名誉而言,这的确有本质的区别。被狼掳走,无非是做了肉食,被人掳走,却会贞洁有失。无论令狐氏还是翟氏,都承受不起这种侮辱。
“我当时真的是慌了,第一个念头不是新婚妻子的生死,而是别人会如何看待我。我并非嫡长子,却从小聪慧,家族调动最好的资源来栽培我,二十一岁便做了正八品上的宣节校尉,二十三岁做了从七品上的翊麾校尉,品秩一年一叙,如今更是正七品上的致果校尉、西关镇将,敦煌州城的兵力都掌握在手。按照家族的安排,我将来不会去外地任官,要替令狐家在瓜沙镇守住根基。我从小顺风顺水,有无数人嫉妒我,我却从不与他们争,总是做出清冷散淡的样子。可是我内心极为介意,因为我无法容忍别人超越我,更无法容忍自己有瑕疵,成为那些人窃笑暗嘲的对象。”
令狐瞻滔滔不绝地说着,似乎要把一生的积郁都倾倒出来。
“可是那一夜,我彻底毁了。我杀掉了所有敢于说出‘人’字的仆役和部曲,可是平民百姓我能掩盖,八大士族却皆知真相。法师,两家共同的羞辱聚集在我一人身上了。这三年来,我苦心孤诣猎杀奎木狼,把自己装得穷凶极恶,满脸杀戮之气,只是想让人人惧怕,不敢提及翟纹二字。这三年来,我装作对翟纹情深义重,为新婚妻子誓死复仇,只是要让别人知道我是因为夫妻情谊,而不是为了自身羞辱。”
令狐瞻忽然泪流满面,双手捂着脸。他脸上仍有鲜血,掌中一片殷红。玄奘默默地听着,一句话没说。佛家说,诸烦恼生,必由痴故。
“敦煌每个人都知道,我对翟纹情爱深重,有时候连我夜半醒来都不禁苦涩,仿佛盲人瞎马,行走在深渊之外。”令狐瞻喃喃道,“翟纹未过门而死,令狐氏与翟氏的婚约其实已经结束,可是因为我这般行径,两家至今仍然得维持这场虚假的联姻。而我自己也被困于其中,不能有心爱之人,不能再订婚约,娶妻生子。三年来我猎杀奎木狼八次,每次都无功而返,其实我已经疲惫不堪,却不得不在人前装模作样,一听到奎木狼三字就做出怒发冲冠、鲁莽冲动的模样。”令狐瞻苦笑地望着他,“法师,我为自己打造了一座囚狱。”
玄奘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令狐瞻人才智慧皆是上上之选,对自身情势也看得透彻分明,却自造牢狱,困锁其中。佛法度人,更需自度。
“听说佛家有忏悔一词,在佛与师长面前告白追悔过去之罪,以期灭罪?”令狐瞻问道。
玄奘点点头:“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
“一切我今皆忏悔……”令狐瞻默默地念着,神情寥落,“这些话法师且当作我忏悔之言吧。至于拜求法师的事……这次去玉门关,法师能否帮我问一问那奎木狼,翟纹尸骨葬在何处?若我能找到她尸骨收敛,归葬祖坟,也算了结了这三年的痛苦。”
“此事贫僧一定办好。”玄奘点点头,“只是此去玉门关,贫僧十有八九要被烧死在那里,消息如何能报给你听?”
“若法师得到消息,便在玉门关的城门口土墙上用白石灰画圈,自然有人找寻法师。”令狐瞻道。
玄奘恍然,令狐氏和奎木狼斗了这么多年,想来自然会安插一些耳目。玄奘没再说什么,双手虚合,转身策马离去。
令狐瞻沉默地站着,神情萧瑟沧桑,回头吩咐部曲:“我们回敦煌吧!”
处理完青墩戍的善后事宜,令狐瞻和李淳风带着咒禁科众人以及幸存的部曲们返回敦煌。令狐瞻归心似箭,第一日便疾行百里,戌时日落时,土窑子驿便遥遥在望。
去时七十名部曲,返回时只有四十多人,加上咒禁科众人,在沙碛道上拉出长长一列马队。李淳风原本在队伍中间,这时催促马匹疾行,追上了令狐瞻,两匹马并辔而行。
“令狐兄,”李淳风道,“这次下官没能降服奎木狼,致使死伤惨重,深感抱愧。”
“李博士不必过谦。”令狐瞻不以为意,“我和奎木狼斗了三年,深知其厉害之处。你是这些年唯一能在他面前全身而退,且不落下风之人。若是摸熟了他的法门,未必不能降服他。”
李淳风脸上带着散淡的笑:“似乎你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
令狐瞻两眼一缩,警惕地打量着他。
“在令狐乡临出发之时,令狐兄慷慨陈词,死不归葬,颇有易水萧萧,一去不回之悲壮。而事败之后却仓促返回,归心似箭,这让我实在不解。”李淳风言辞锋锐。
令狐瞻脸色沉了下来:“李博士是在讥笑我吗?”
李淳风笑着摆手:“哪里,哪里。令狐兄是个做大事的人,我只有敬佩。”
“此话怎讲?”令狐瞻冷冷地盯着他。
“因为整个青墩戍一役,就是个局。”李淳风淡淡地道,“如今人死够了,局已成了,令狐兄自然要返回敦煌主持大局。”
令狐瞻猛一勒马匹,战马长嘶一声,骤然停了下来。李淳风的马匹跑出去几丈远才勒住,转回马匹,和令狐瞻马头相对。两人就这么默默地对视着,彼此之间似乎有风雷涌动。
随行的众骑也察觉到异状,纷纷减速,在远处观望着。
“这些年敦煌八大士族围剿奎木狼屡屡失败,前些天你甚至调动了镇兵在莫高窟大战一场,仍然没能诛杀奎木狼,反而受到军法处置,丢掉了西关镇将一职。”李淳风神情冷静从容,一字一句地道,“所以对你们而言,拿下奎木狼的唯一办法就是出动大军!可是想出动大军却不是你们说了算,是刺史王君可说了算。王刺史看来并不想出兵,所以你们就必须逼得他不得不出。”
令狐瞻静静地望着他,一言不发。
李淳风也不介意,继续说着:“此前莫高窟狼祸,虽然军民死伤不少,却达不到逼迫王君可出兵的程度,所以你们便谋划了这场青墩戍之战。哼,奎木狼攻入青墩戍,屠杀戍卒十余人,甚至戍主林四马都死了,这可是对军方实打实的挑衅!王君可再不出兵,莫说西沙州军方众将不答应,恐怕朝廷也不答应。令狐兄,你这般急匆匆地返回州城,就是想接手军队的吧?”
“李博士,你的确天资聪颖,可是你说的这些我不会承认。”令狐瞻心中暗暗吃惊,沉着脸道,“你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究竟想做什么?”
“令狐兄爽快。”李淳风大笑,“我来敦煌,是受阴妃和阴侍郎所托,要降服奎木狼,与你们敦煌八大士族目标一致。我李淳风初入官场,官职虽然低微,却并非没有上进之心,若能降服奎木狼,使得朝野瞩目,便是豁出性命又有何不可?可是令狐兄,我却不愿做他人手中的玩偶,白白送了性命!”
令狐瞻神色不动:“这话怎讲?”
李淳风冷笑:“你们跟我讲述的奎木狼,只是区区山精野怪,可没有这等深不可测的神通!前日一番较量,他精通金丹大道,天罡三十六般变化,这等妖孽哪里是我这般仓促上阵便能降服得了的?没有把命丢在青墩戍,已经是邀天之幸!所以令狐兄,若你们想真心请我降妖伏魔,就推心置腹,不要有所欺瞒。若你们只是想利用我一番,如今青墩戍一役已经结束,你们也达成了目的,我便抽身走人,返回长安。再要设局坑害,便是欺我李淳风背后师门软弱可欺!”
令狐瞻双手抱拳,诚恳地道:“淳风兄,我令狐瞻以及令狐氏,绝无设局坑害你的心思!这中间或许有些误会,想来也是对你我、对敌手的实力估测有误。前日夜间你力抗奎木狼,实在是神通了得,法术精熟,这三年来我们请来的术士高人不知凡几,您淳风兄的实力首屈一指!等回到敦煌,我自会向父亲和各位家主分说,竭诚以待,共克奎木狼,还请淳风兄助我一臂之力!”
李淳风深深地看着他,似乎在判断他的诚意。
“我们八大士族只想要它死,镇杀奎木狼的声誉,全归淳风兄!”令狐瞻道。
“好!”李淳风伸出了手,两人双手相握,一泯所有的不快。
令狐瞻心情大好,此时众人已经到了土窑子驿前,众人放慢马速,朝着戍驿门口而行。
正要入驿休息,忽然间一匹快马从南而来,马上之人身穿胡服,头上戴着幂篱,黑色罗纱覆盖了半身,身上到处是灰土和沙尘。马快风疾,有风吹起,身材极为纤细,似乎是个女子。
令狐瞻看了一眼,忽然就是一怔。那骑士看见令狐瞻,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疾驰而来,喊道:“九郎!”
声音清脆,果然是个女子。
令狐瞻看了李淳风一眼:“李兄,您请先到驿站内休息,我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好。”李淳风含笑点头,和咒禁科众人以及部曲们进入土窑子驿。
令狐瞻急忙策马迎过去,两匹马在荒凉的驿道上交会,那女子挑起幂篱的罗纱,露出一张清丽无双却颇有憔悴的面孔,含情脉脉地望着令狐瞻。
“窕娘,果然是你!”令狐瞻吃惊。
原来这女子便是张敝的嫡女,窕娘。
令狐瞻急忙扶着她下马,发现窕娘整个身子都僵硬了,显然经历了长时间的奔波之苦。
“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会来这里?”令狐瞻一迭声地问。
窕娘泪眼盈盈地望着他:“九郎,昨日青墩戍烽火急警,有军中羽檄把发生的事情传到了敦煌,奎木狼杀了那么多人,我都担心死你了,便想到青墩戍找你,却万幸在这里遇到你。”
“你——”令狐瞻心中一阵揪痛,却万般无奈。
自从武德九年翟纹被奎木狼掳掠之后,令狐氏和翟氏对外便宣称翟纹已死,两家的婚姻事实上就已经结束。令狐瞻是令狐氏新一代的翘楚,自然不可能不成亲,连翟昌也默认了事实。张氏和令狐氏这几十年颇有些疏远,这些年令狐氏势大,张敝也有心联姻,窕娘对令狐瞻更是芳心暗许,只是令狐瞻却因为翟纹被掳之辱,仍视翟纹为妻子,窕娘只好将一腔深情藏于心中。
令狐瞻并非不知,却也只好辜负美人之恩。
“九郎,你……你受伤了?”窕娘忽然发现令狐瞻一条腿微瘸,缠着的绷带上隐隐渗出鲜血,当即花容失色。
“挨了一刀而已,不重。”令狐瞻道,“你是私自到这里的吗?你的身份却不能让人知道,且放下幂篱,跟我到驿站里歇息一下。”
“无妨,我是从城外的别业来的。”窕娘道,“我们张氏出了大事,父亲眼下也顾不得我。”
令狐瞻一怔:“张氏出了什么大事?”
“你还不知……”窕娘这才醒悟,顿时露出愤怒之色,“九郎,那刺史王君可,对我张氏动手了!”
令狐瞻吃了一惊,详细询问,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原来奎木狼杀人那天晚上,青墩戍的戍卒便点燃了烽火,戍副连夜赶往敦煌发出急警。戍主林四马被杀,戍卒死伤惨重,这可是大事。王君可详细盘问戍副。
戍副虽然不敢提吕晟和各士族的恩怨,可林四马勾结马鬃山马匪,纵容走私聚敛钱帛的事却不敢隐瞒。八大士族的谋划取得了成功,王君可怒不可遏,一方面派出镇兵赶往青墩戍支援,另一方面调动西沙州兵力集结,做出剿灭奎木狼的姿态。
然而就在八大士族弹冠相庆,等着王君可出兵的当口,王君可却突然出手,严厉彻查涉嫌走私的商队!
自大唐开国以来,便实行禁边令,非但普通国人禁止出关,连唐人的商队也不能出关贸易,《唐律》规定:“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
这实质上便将丝路的贸易权拱手交给了胡人,虽然对胡人商贸限制也颇为严厉。
可商贸之暴利,仍然吸引了大批的豪族参与其中,只是一则有唐律所限制,二则商贾地位低贱,士族官员乃是清流,不得兼职经商,商贾之家也不得入仕,所以不少为暴利所动心的士族就以旁系的名义组建商行,暗中与胡人合股,让胡人出入关隘行走丝路去行商,商行则作为坐商,承销货物。
这些大士族盘踞敦煌数百年,势力分布西沙州的各行各业,各个关卡,比如执掌市场交易的敦煌县市令,就是张氏族人。敦煌乃是边境丝路重地,历来商贸之风就重,朝廷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譬如莫高窟竞买会上,李氏商队手中的汗血宝马,就是这种来历,众人也不以为奇。可是有些士族过于贪婪,暗中买通林四马之类的边将进行走私,这就是朝廷要严厉打击的行为。
如今王君可就是借着林四马一案掀起了打击走私的风暴。
首当其冲的就是张氏。因为张氏有两点过于瞩目,一则敦煌县市令是张氏族人,二则敦煌张氏与高昌国张氏同出一脉。高昌国乃是西域中唯一的汉人之国,王室姓麴,张氏与麴氏历来休戚与共,十几年前高昌国发生义和政变,麴氏失国出奔,正是张氏力挽狂澜,三年后协助麴氏复国,如今大将军张雄更是执掌高昌国的兵权。因此敦煌张氏与高昌张氏之间的商贸极为密切,顺着矟竿道北上虽然是伊吾国,但伊吾国小,丝毫不敢得罪高昌。也就是说只要敦煌张氏的货物出了大唐国境,便畅通无阻直达高昌、焉耆。
敦煌八大士族中,于商贸之中获利最巨的,便是张氏和李氏。
“青墩戍林四马纵容走私的消息传来,给了那王君可一个借口,他一出手便拿下了市令张克之,随即查抄几家胡人和高昌张氏的商行,通过账簿和钱帛流向,直接抓获了我敦煌张氏商行的六名主事。”窕娘说道,“如今王君可正在拷问那些主事,一心要把我张氏牵连进走私大案。”
窕娘满脸疲惫和愤恨,却又露出惶恐。令狐瞻默默地望着她,不知该如何安慰。
“九郎,”窕娘眼中慢慢流泪,“我知道,那王君可如此疯狂,是因为我父亲拒了他婚事,是我连累了父亲,连累了家族。父亲不让我忧心,送我到城外别业暂住,可是……可是我心里真的好怕。”
窕娘慢慢抱住了令狐瞻,泪盈盈的两眼望着他,似乎想得到一份慰藉,一份承诺。令狐瞻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透过朦胧的幂篱罗纱,看着漫漫黄沙,第一次觉得无力和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