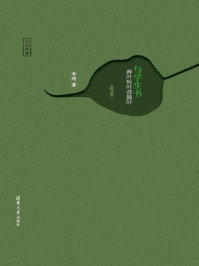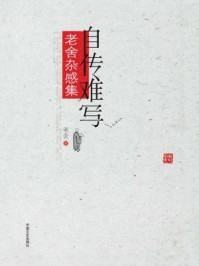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又无时不处在枷锁之中。人类向来认为自己是万物的主宰,但事实上,他们比其他任何事物所受的奴役都要多。”
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芒万丈,有人一身锈。千万种不同的境遇,自然也有千万种不同的心境。因为我们对未来有所期许,所以总要于困苦中寻求一种可贵的精神支撑。有了这种信念的铺垫,即便你真的身处陋室、深沟,都会因为心系高堂而跃出谷底。生而为人虽然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有很多禁锢。有人为贫穷所限,有人因残疾受阻,也有人被认知圈定,无论怎样都迈不出自己眼前的小世界。
第一次读余秀华的诗,就震惊于她大胆激烈的言辞,从诗行里的字句看她,有时候是一位意气风发的侠女,有时候又是一位柔情似水的姑娘,有时候也是一位形单影只的闲者。仿佛她有千百个灵魂,化身在不同的诗句里,每一句诗都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而这些味道,就是她寄身于世的安乐之所。
人们读到一篇动情的诗歌,总会联想一下作者的样子。当余秀华的故事细节还没有被发掘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在脑海中对于她的第一印象总是倔强又傲气、独立于世的豪放诗人形象。但是,在读到她的故事以后,心里树立的这种形象就轰然倒塌,不禁心头一颤:原来她的经历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余秀华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由于是逆产,脑部严重缺氧,让她一出生便患了脑瘫。在她长大成人以后,生活行动也因此变得不便,说起话来也不像正常人那样口齿清晰,从小遭受了很多人异样的目光。单单是这一段经历,就很难让人把她和诗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作是一座房子,那么这座房子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灵魂。 有时候,世间的风雨磕碰 会让这座房屋受损,但灵魂的栖息并不会因为受损的房屋而枯竭 凋萎。
对于正常人来说,两岁的孩子大都走路已经很稳了,但余秀华却是在六岁的时候才学会走路。走路这件在旁人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对于六岁以前的她来说,却异常艰难。那时候,她都是在院子里爬过来爬过去。家人为了帮助她学会行走,特意给她打造了一个学步车。在学步车里待过一段时间后,家里人又帮她把学步车换成了拐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她终于能自己独立行走。虽然是摇摇晃晃地,但已经让她相当开心了。
我们或许并不能真正体会到她在学步期间的辛酸,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残损坏破的身体里住着的,是一个高贵而向往自由的灵魂。 越是被否定,就越是想要证明自己;越是被阻拦, 就越是想要飞得更高。 当她支撑着身体摇摇晃晃站起来的时候,就是她挣脱禁锢的第一步。虽然身患残疾,但这并不影响她心生期盼。
在很多人的人生经历中,高中似乎是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尤其是高中毕业的那段日子,告别紧张高压力的昨天,迎接崭新又充满希望的明天。但余秀华高二都没有上完,更别说踏入大学。辍学以后,她就赋闲在家,等着母亲给她寻找一个靠谱的婆家,然后结婚成家,生孩子,干农活。那一年,她才十九岁,就在家里人的安排下和同村的一个比她大十二岁的男人结了婚。余秀华称这段婚姻为“非自由恋爱下的婚姻”。她坦言自己的婚姻并不幸福,虽然两个人有了孩子,但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大多数的日子里,他们都在吵架,丈夫看余秀华写诗不顺眼,而余秀华看丈夫也不顺眼。两个人没有一点共同话题,一点也不能理解对方的世界。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彼此都不开心。
这段婚姻对余秀华而言就是一片苦海,她在苦海里煎熬,始终不得上岸。余秀华很早就萌生了离婚的念头,只不过在沉重的世俗观念面前,这种想法想要实现是很难的。首先站出来反对的便是家里的长辈,在他们看来,余秀华本身身体有缺陷,现在能找到一个老公,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应该踏踏实实地过日子,离婚实在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选择。这重重的阻碍,让她一次又一次将这个念头压了下去,继续将自己沉入那片苦海之中。
有一次,她脑海里突然萌生了出去乞讨的念头。她到市里面的一个天桥上,看到桥两旁很多跪着行乞的人,她看得出了神。想到自己的将来一片迷茫,想要养活自己必须得有一个出路。自己能不能和他们一样,往天桥上一跪,再放个碗,等着别人施舍一点零碎的钱财呢?当时这种想法在她的脑子里特别强烈,她甚至找来了一个碗,寻了一块“风水宝地”,还刻意装扮了一下自己的形象,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个真实的乞丐。但是,最终她没有成功,因为她实在是跪不下去。扔掉碗,她不再执着于此,而是寄情于笔,转念于诗。
都说生活的不如意十之八九,对于余秀华,那仅剩的一二乐事也不能幸免。身体和生活都是打击,婚姻和未来都是苦闷。但好在,她有诗。她用诗来修补生活的种种残缺,当周遭像死水一样寂静时,她的诗就是她波澜不惊的生活里的歌谣。在走不出去的封闭农村里,她和别人不一样。他人有健全的四肢和健康的身体,但却平淡寡味,一天又一天,只是从日子的这一头挪动到了另一头。而余秀华则在生命这方水塘里尽力拍打水花,在她写下的诗句里,有愤恨,有忧愁;有悲伤,有喜悦;有回忆,有展望;有亲情也有爱情。高兴的时候写几句,不高兴的时候也写几句;空闲的时候写几句,忙碌的时候抽时间再写几句。只有在这些诗篇中,她才能彻底摆脱自己身体残疾的现实,以及让人窒息的封建和闭塞。
从出生到学会走路,从学会走路到上学,从上学到高中肄业,从高中肄业到结婚,从结婚到想要离婚,余秀华似乎更加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没有靠写诗成名之前,她的博客已经积累了很多自己平时写下的诗歌,虽然也有一些读者,但从没有让她对“用诗歌来改变生活”抱有一点希望。直到有一天,网络上疯狂转发她的诗《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夜之间,余秀华也随着她的诗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红”。为此,她颇感自豪,看来,用写诗来养活自己这件事情慢慢变得靠谱了。
网络上的走红让她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专程跑到村里去采访她。余秀华瞬间被包围在一片聚光灯之下,对每一位来访者重复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一点都没有了往日的平静。一边觉得烦恼,一边又觉得享受,但她并没有迷失在这种金光闪闪的包围之中。当外来的潮水退却之后,她仍然自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电脑,敲下几行来自生活的文字。除此之外,她还干着和从前一样的农活,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扫地做饭,最大限度地接近生活。
后来,她拿奖了,“农民文学”特别奖。颁奖典礼上的那段诗一样的颁奖词带给她的幸福感溢于言表。自此,余秀华写下的诗,已经有两千多首。当人们在同情她的遭遇、可怜她的身世的时候,她却说,正是这样的环境,给了她和常人不一样的心境。既然抱怨没有用,那何不尝试改变呢?农闲的时候,周围的邻居总爱聚在一起,除了打麻将还是打麻将。而余秀华则说,其实,我写诗和他们打麻将一样,也是会上瘾的,哪怕是一天不写,我心里都直痒痒。
看来,上帝还是公平的,在从你身边拿走一样东西时,总会再赐予你另一样东西。余秀华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上帝就给了她诗歌,让她以此为杖,从此站得直、走得稳。不沉湎于悲伤,不哀叹于失去,不执着于过往,这才能有所改变,有所得到,有所进步。
一个有趣味的灵魂,本身就自带发光发热的属性,它不仅能照亮自己,也能将余光传递给他人。在夜晚的茫茫大海上,她就是穿透黑暗的光,坚定有力,温暖安详。
诗集出版以后,余秀华拿到了一笔钱。她做了一件很久以前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情——离婚。虽然婚姻受挫,但她对爱情依然心怀期待。就像她在诗里写的:“这人间情事,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而光阴皎洁,我不适宜肝肠寸断。”这就是她的向往和期待,哪怕只是干巴巴地活着,在心里也要为自己设定一种最美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