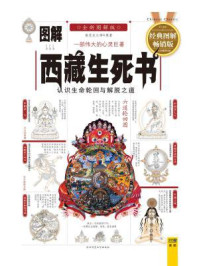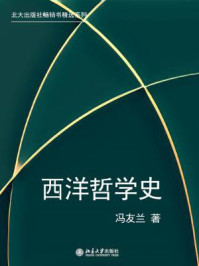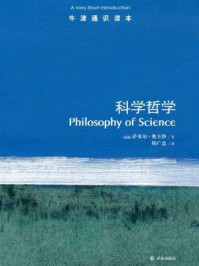只有明白了《老子》不是老子出关之时应关尹之请的即兴书写,而是老子精思密虑的毕生著作(详见第一章),才有可能把《老子》视为体大思精的哲学体系,进而探索《老子》哲学体系的源代码。假如误以为《老子》是老子出关之时应关尹之请的即兴书写,就会像旧老学那样把《老子》视为即兴书写的格言集锦,就不可能把《老子》视为体大思精的哲学体系,也就不可能探索《老子》哲学体系的源代码。
老子之道的源代码之所以是伏羲之道,是因为伏羲之道是中古夏商周两千年的文化基因。上古四千年的伏羲之道之所以成为华夏文化的总基因,第一原因是中古夏商周两千年的“三易”《连山》、《归藏》、《周易》,核心都是伏羲六十四卦,第二原因是精通夏商周“三易”的东周史官老子于春秋晚期撰著《老子》,把伏羲之道的天文科学体系,转化为道家之道的人文哲学体系,实现了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开启了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而诸子百家的人文哲学思想,全面影响了秦汉至今的近古两千年。
伏羲之道的核心,就是伏羲六十四卦及其卦象合成的伏羲太极图。《礼记·礼运》用天文术语“太一”描述伏羲太极图:“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吕氏春秋·大乐》也用天文术语“太一”描述伏羲太极图:“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周易·系辞上》则用历法术语“太极”描述伏羲太极图:“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老子后学所撰《太一生水》,用“太一成岁”的“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阐释整部《老子》。庄子后学所撰《庄子·天下》,用“主之以太一”概括整部《老子》。两者共同认为:《老子》的源代码是“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
《老子》的“道”和“一”,分别对应伏羲之道的两大天文范畴:“道”是上古伏羲族之“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一”是上古伏羲族之“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老子》“道生一”的真义是:“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道”,产生并总摄“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这是理解《老子》“主之以太一”的终极起点。
由于人类难以尽知“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道”,所以《老子》反复申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知不知,上矣”,“道,可道也,非恒道也”。由于人类可以略知“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所以《老子》以“道生一”为第一基石,一方面说“唯道是从”,另一方面说“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执今之道”,亦即教诲天下侯王绝对信仰“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道”,然后顺从宇宙局部的太阳系规律“太一”,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
本文梳理《老子》“主之以太一”的三大系统证据,即《老子》“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内涵,《老子》“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内涵,《老子》“礼必本于太一”的数术结构,论证伏羲之道是《老子》之道的源头,“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是《老子》的源代码。
“太一”是伏羲之道的固有名相,通用于上古伏羲时代至中古夏商周的华夏天文、华夏历法、华夏宗教,所以《老子》“主之以太一”中的“太一”共有四义:伏羲之道固有的“太一”天文义、“太一”历法义、“太一”宗教义,以及《老子》新增的“太一”哲学义。
伏羲之道固有的“太一”三义,全都植根于天象,所以互有联系,略有差异。

▲地球自转轴指向太一帝星
“太一”天文义,即地球自转轴北端所指、永居天球中心不动的“太一”帝星(小熊座β)。此星发出紫光,亮度低微,所以又称“紫微星”。“紫微星”所在中央天区,即称“紫微垣”。《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即取“太一”天文义:“太一”帝星。
“太一”历法义,即太阳围绕“太一”帝星旋转的“太极”体系,专指太阳围绕“太一”帝星旋转而形成的圭表测影图,亦即用于计算一年历法的伏羲太极图(详见拙著《伏羲之道》)。《礼记·礼运》描述伏羲太极图:“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吕氏春秋·大乐》描述伏羲太极图:“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均取“太一”历法义:“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
“太一”宗教义,即“太一”帝星神格化的“太一”上帝。《史记·封禅书》:“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屈原《九歌》首篇《东皇太一》,均取“太一”宗教义:“太一”上帝。由于“太一”帝星又称“紫微星”,所以“太一”上帝又称“紫微大帝”。汉后道教把“太上老君”视为“紫微大帝”化身,宗教义移用于神化教祖老子,所以道教神话叙述“老子出关”:关尹夜观天象,发现“紫气东来”,预示老子即将来到函谷关。秦汉以后人“王”僭用天“帝”之号,宗教义又移用于神化君主,所以皇宫称为“紫禁城”。
地球自转轴的陀螺式摇摆,导致中宫天极星不断改变(永居天心不动仅是小年错觉)。上古伏羲族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创立华夏天文体系,当时的中宫天极星是“太一”帝星(小熊座β),但是数千年后的西汉时期,中宫天极星已经变成了“勾陈一”(小熊座α),即今日俗称的“北极星”。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天官书》,为什么不说“中宫天极星”是“勾陈一”,仍说“中宫天极星”是“太一”帝星(紫微星)?因为《史记·天官书》不是“天文”书,而是“天官”书,“天官”体系是“天文”体系神格化的宗教体系。宗教信仰必须具有神圣性,永远不能改变至高神,所以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华夏宗教的至高神永远是中宫天极星“太一”帝星神格化的“太一”上帝、“紫微大帝”。但是宗教信仰又必须具有兼容性,包括兼容中宫天极星之大年变化,所以汉代以后的道教神谱,把新的中宫天极星“勾陈一”神格化为“勾陈大帝”,作为辅佐“太一”上帝的次要天帝。而华夏天文学为了兼容中宫天极星的大年变化,把地球自转轴的摇摆区域命名为“紫微垣”,即把“紫微星”永居天心不动,修正为“紫微垣”范围,正如皇帝可以住在紫禁城的任何一处。秦始皇每晚改变寝宫的表层原因是躲避刺客,深层原因是对位天象,因为秦始皇以“王”僭“帝”之后,不再像夏商周之“王”那样对位北斗星君,而是对位“太一”上帝。
伏羲之道固有的“太一”三义,均见于“主之以太一”的《老子》。
“主之以太一”的《老子》,首先蕴涵伏羲之道的“太一”天文义:“太一”帝星。
上古伏羲族创立的华夏天文体系,包含两大天文范畴:宣夜说,浑天说。
“浑天说”是上古伏羲族在仰韶时代(前5000—前3000)创立的初级天文理论,用于阐释以地球、太阳、“太一”帝星为中心的太阳系规律。“浑天说”取象于“鸡子”(鸡蛋),认为地球如蛋黄而居于中,天球如蛋清而包于外。《老子》“道生一”之“一”,“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之“一”,“载营魄抱一”之“一”,“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之“一”,“有生于无”之“有”,均指“浑天说”范畴的“太一”(太极)之道。
“宣夜说”是上古伏羲族在龙山时代(前3000—前2000)创立的终极天文理论,用于阐释不以地球、太阳、“太一”帝星为中心的宇宙总体规律。“宣夜说”超越了“浑天说”的“太极”体系,认知了地球、太阳、“太一”帝星均非宇宙中心;宇宙没有中心,亦即没有极星,所以谓之“无极”。《老子》“道生一”之“道”,“有生于无”之“无”,“复归于无极”之“无极”,均指“宣夜说”范畴的“无极”之道。
中古夏商周史官执掌天文历法,熟知上古伏羲时代创造的两大天文理论。东周史官老子所撰《老子》,用“道生一”和“有生于无”,表述“道”的两大天文层级:“道”和“无”均指“宣夜说”范畴的“无极”之道,“一”和“有”均指“浑天说”范畴的“太一”之道(太极之道)。
《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庄子·逍遥游》“无极之外,复无极也”,《庄子·大宗师》“夫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北宋周敦颐《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无不继承作为《老子》第一基石的两大天文层级:“道”,“易”,“无极”,均指“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一”,“太一”,“太极”,均指“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
“主之以太一”的《老子》,同样蕴涵伏羲之道的“太一”历法义:“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
“太极”之“太”即太阳,“太极”之“极”即“太一”极星。“太极”名相的精确内涵是:太阳围绕“太一”极星旋转一年(实为地球自转轴指向“太一”极星,每日自转一周,每年围绕太阳公转一周),所以伏羲太极图是太阳围绕“太一”极星旋转一年的“太一”历法图,包含阴阳、两仪、四象、八节、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等等。
《道生一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之道”,“一”以下是“浑天说”范畴的太阳系规律“太一之道”,对应“太一”历法图,亦即伏羲太极图:“一”即天文术语“太一”,等价于历法术语“太极”。“二”即阴阳两仪。“三”即阴爻、阳爻构成的三爻八卦。“万物”即伏羲六十四卦对应的万物(参看《周易·说卦》)。
《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礼记·礼运》:“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吕氏春秋·大乐》:“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这些先秦古籍,或用历法术语“太极”,或用天文术语“太一”,一切描述全都符合伏羲太极图,所以“太一”历法图正是伏羲太极图。
“主之以太一”的《老子》,同样蕴涵伏羲之道的“太一”宗教义:“太一”上帝。
天文存在是能指描述的受指,不可能错。历法知识是描述受指的能指,有可能错。所以历法知识之神圣性,依附于天文存在之神圣性。华夏阴阳合历所含太阳历二十四节气之神圣性,依附于天文层面的冬至圭影最长、夏至圭影最短、春分秋分昼夜等长。华夏阴阳合历所含太阴历每月十五之神圣性,依附于天文层面的每月十五月圆。中古夏商周为了把天文存在、历法知识的神圣性,转化为君主统治的神圣性,于是“神道设教”,把“太一”帝星神格化为“太一”上帝,先把天文存在、历法知识的神圣性,转化为宗教体系、神话体系的神圣性,再把宗教体系、神话体系的神圣性,转化为君主统治的神圣性:用君王颁布的历法符合天文,证明“君权神授”。
由于观星制历的并非夏商周君王,而是夏商周史官,所以“神道设教”的“君权神授”论,仅对不通天文历法的人们有效,对执掌天文历法的史官无效。东周史官老子深知,历法符合天文无法证明君王之神圣性,证明君王之神圣性的唯一通途是君王效法天道治国。
东周史官老子同样深知,“太一”上帝是“太一”帝星的神格化,所以《道冲不盈章》对“太一”上帝进行了哲学祛魅:“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帝”即“太一”帝星神格化的“太一”上帝。“象帝之先”,还原了“太一”上帝的产生过程:先有天文义的“太一”帝星,后有宗教义的“太一”上帝。点破“道”先于“帝”,是以上古伏羲之道,对中古夏商周之神道设教的哲学祛魅。苏格拉底对上古希腊神话之神道设教,释迦牟尼对上古婆罗门教之神道设教,耶稣对上古犹太教之神道设教,全都进行了类似于老子的哲学祛魅。一个民族若未完成对神道设教的哲学祛魅,就不可能实现哲学突破。上古部落文化进入中古国家的初级文明,必然经历神道设教,即把天文体系神格化为天神体系,建构统一信仰。中古国家的初级文明进入近古国家的中级文明,必然经历哲学突破,即对初级文明的神道设教予以哲学祛魅。一个民族假如没有实现哲学突破,就不可能从中古国家的初级文明升级为近古国家的中级文明。事实上仅有极少数民族实现了哲学突破,从中古国家的初级文明升级为近古国家的中级文明。
《老子》“象帝之先”四字,对夏商周宗教的“太一”上帝之神圣性,以及自封“太一”上帝之子、自称“君权神授”的夏商周君主之神圣性,予以哲学祛魅,标志着中国文明实现了“以道代帝”的哲学突破。
《老子》一方面用“象帝之先”四字,实现了“以道代帝”的哲学突破;另一方面又借用了夏商周宗教的“太一”上帝,称其为“教父”,亦见《道生一章》:“故‘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强梁者不得其死”并非老子之言,而是引用镌刻于东周太庙“太一”上帝神像背部的神谕《金人铭》。《老子》引用《金人铭》,所取正是“太一”宗教义“太一”上帝,故称“太一”上帝为“教父”。
老子并未彻底否定中古夏商周宗教的“太一”上帝,仅是予以哲学祛魅,并且借用“太一”上帝的神谕《金人铭》,教诲天下侯王。正如苏格拉底并未彻底否定希腊宗教的奥林匹亚众神,而是借用德尔斐神庙的阿波罗神谕“认识你自己”,教诲希腊民众;释迦牟尼并未彻底否定婆罗门教的印度众神,而是改造婆罗门教的信仰,传播佛学智慧;耶稣并未彻底否定犹太教的上帝,而是借用犹太教上帝的旧约“十诫”,传播基督教的新约“福音”。四大民族的四大哲人,所处民族环境虽异,所处历史时段则同,所以因应外境的方式大同小异,殊途同归。
对于华夏古道固有的“太一”三义,《老子》的哲学处置不尽相同:对于华夏古道固有的“太一”天文义、历法义,《老子》是顺势继承并予哲学提炼;对于华夏古道固有的“太一”宗教义,《老子》是顺势扬弃并予哲学祛魅。所以《老子》全书的一切表述,无不围绕“哲学突破”的两大使命:一是认知人类的永恒无知,二是对于宗教的哲学祛魅。认知人类的永恒无知,则是《老子》的第一教诲。
“主之以太一”的《老子》,除了蕴涵华夏古道固有的“太一”三义(天文义、历法义、宗教义),又新增了“太一”第四义:哲学义,亦即道家义。
首先,老子把“道生一”之“道”,亦即“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之道”,称为不可知、不可得、不可抱、不可执、不可道的“恒道”,见于《道可道章》:“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所以《知不知章》说:“知不知,上矣。不知不知,病矣。”
其次,老子把“道生一”之“一”,亦即“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之道”,称为可知、可得、可抱、可执、可道的“常道”,见于《含德之厚章》:“和曰常,知常曰明。”又见于《守静知常章》:“知常,明也。不知常,妄作凶。”所以《侯王得一章》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抱一爱民章》则说:“载营魄抱一。”《曲则全章》又说:“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
“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之道”,“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之道”,都是老子之前的伏羲之道固有的,但把“无极之道”称为不可知、不可得、不可抱、不可执、不可道的“恒道”,把“太一之道”称为可知、可得、可抱、可执、可道的“常道”,则是《老子》新增的“太一”哲学义。
老子新增“太一”哲学义之前,“太一生两仪,两仪生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属于神创宇宙论。“太一”为宗教义,即“太一上帝”,意为:太一上帝创造了全部宇宙。
老子新增“太一”哲学义之后,“太一生两仪,两仪生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不再是神创宇宙论,而是自然宇宙论。老子首先把“太一”宗教义还原为“太一”天文义、“太一”历法义。“太一”天文义是:“太一”帝星是太阳系一切天体绕之旋转的中宫天极星。“太一”历法义是:“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揭示了太阳系天体围绕“太一”帝星旋转的周期规律。所以“太一”宗教义的神创宇宙论“太一上帝创造了全部宇宙”,在“太一”哲学义的自然宇宙论中,仅是“太一上帝创造了局部宇宙太阳系”。
老子在把“太一”宗教义还原为“太一”天文义、“太一”历法义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揭示了自然宇宙论的“太一”哲学义:“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之道,仅是人类可知的次级天道“太一常道”;“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则是人类不可知的顶级天道“无极恒道”。所以《道生一章》之“道生一”意为:不可知的无极之道,生可知的太一之道。《道冲不盈章》之“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意为:不可知的无极之道,先于可知的太一之道;天文历法的太一之道,先于宗教神话的太一上帝。
正是老子新增的“太一”哲学义:“道”是不可知的“无极恒道”,“一”是可知的“太一常道”;“道”先于“一”,“一”先于“帝”,“帝”是“一”的神格化;把伏羲天文之道突破为道家人文之道,把神创宇宙论突破为自然宇宙论,实现了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突破。
《老子》除了把对应华夏天文学两大范畴“宣夜说”、“浑天说”的“道生一”作为第一基石,又严格区分了天文存在和历法知识:譬解天文存在为“父”,譬解历法知识为“母”。
《老子》初始本两见“父”字,分别譬解“宣夜说”范畴、“浑天说”范畴的天文存在。《唯道是从章》之“众父”,譬解“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尊之为顶级天文存在的“众父”。《道生一章》之“教父”,譬解“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尊之为次级天文存在的“教父”。
《老子》初始本七见“母”字,全都譬解“浑天说”范畴的历法知识,亦即“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天下有始章》“天下母”,“既得其母”,“复守其母”,《治人事天章》“有国之母”,《道可道章》“有,名万物之母也”,《敬天畏人章》“贵食母”,《有状混成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无一例外均指“浑天说”范畴的历法知识“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
“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人类仅知其天文存在,不知其历法知识,所以《老子》仅仅譬解其天文存在为“众父”,不譬解其历法知识为“众母”。“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人类既知其天文存在,又知其历法知识,所以《老子》既譬解其天文存在为“教父”,又譬解其历法知识为“天下母”、“天地母”、“万物之母”、“有国之母”。
厘清了上述诸多名相分别属于两大天文范畴“宣夜说”、“浑天说”,就能精确理解《有状混成章》: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状混成章》首先标举“宇宙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人”是宇宙第四大,属于“浑天说”范畴的“万物”层级。“人亦大”,是因为“人是万物之灵长”。
“地”是宇宙第三大,属于“浑天说”范畴的“地球”层级。“地大”,是因为“人”居于地球。
“天”是宇宙第二大,属于“浑天说”范畴的“天球”层级。“天大”,是因为地球从属于天球,即地球以“太一”帝星为“道枢”,以“太一”上帝为“教父”,以“太一”历法为“天下母”。
“道”是宇宙第一大,属于“宣夜说”范畴的“宇宙”层级。“道大”,是因为地球人只能略知“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无法尽知“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在“宣夜说”范畴的全部宇宙中,“浑天说”范畴的“太一”帝星不是全部宇宙的“道枢”,“太一”上帝不是主宰宇宙的“众父”,“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不是宇宙万物的“天下母”。
《有状混成章》随后标举“宇宙四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法地”是宇宙第四法,即“浑天说”范畴的万物效法地球。地球自转导致日出之昼和日落之夜,“人法地”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球公转导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人法地”即“春耕夏种,秋收冬藏”。
“地法天”是宇宙第三法,即“浑天说”范畴的地球效法天球。太阳系的天球,以“太一”帝星为“道枢”,所以地球人以“太一”上帝为“教父”,以“太一”历法为“天下母”。
“天法道”是宇宙第二法,即“浑天说”范畴的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效法“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
“道法自然”是宇宙第一法,即“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仅仅效法自己。因为“无极恒道”是全部宇宙的最高主宰,没有更高的效法对象,只能效法自己。
《老子》“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内涵,以“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内涵为前提。“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内涵,是指《老子》以“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为源代码。“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内涵,是指《老子》教诲天下侯王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所以贯穿《老子》全书的价值五阶“道↘德↘仁↘义↘礼”,侯王四境“德↘仁↘义↘礼”,以及“扬泰抑否”的“君人南面之术”,无不源于“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
《老子》首章《上德不德章》,开宗明义曰: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老子》首章《上德不德章》的价值五阶:道↘德↘仁↘义↘礼,源代码正是“太一”历法图,即伏羲太极图。

▲伏羲太极图(伏羲族方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伏羲太极图的中心,对应“太一”帝星。伏羲太极图是《太一生水》所言“太一成岁”的历法图,因为太阳系一切天体无不围绕“太一”帝星旋转(此为地球观测者的直观),所以伏羲太极图是“太一”历法图。《老子》把伏羲太极图揭示的“太一常道”,提炼为价值五阶的第一价值“道”。
《老子》又把伏羲太极图开辟“四时”的外圈四卦,提炼为价值五阶的后四价值:春分泰卦
 ,提炼为“德”。夏至乾卦
,提炼为“德”。夏至乾卦
 ,提炼为“仁”。秋分否卦
,提炼为“仁”。秋分否卦
 ,提炼为“义”。冬至坤卦
,提炼为“义”。冬至坤卦
 ,提炼为“礼”。
,提炼为“礼”。
提炼自伏羲太极图的价值五阶:道↘德↘仁↘义↘礼,见于《老子》初始本首章,贯穿《老子》全书。
由于人类不可能尽得“天道”,所以剔除价值五阶的第一价值“道”,后四价值即为“人道四境”:德↘仁↘义↘礼,对应伏羲太极图开辟“四时”的外圈四卦:泰↘乾↘否↘坤,亦即《太一生水》所言“太一成岁”之“四时”。
由于《老子》的教诲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侯王,所以《老子》初始本首章《上德不德章》,又把“人道四境”落实为“侯王四型”: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上德”侯王顺道“无为”,以“德”治国。“上仁”侯王悖道“有为”,以“仁”治国。“上义”侯王悖道“有为”,以“义”治国。“上礼”侯王悖道“有为”,以“礼”治国。
《老子》初始本首章的“人道四境”和“侯王四型”,应用于《出生入死章》,即为“侯王摄生四境”: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生而动,动皆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之厚也。
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避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
以“德”治国的上德侯王顺道“无为”,善于统摄民生,所以民众“无死地”。以“仁”治国的下德侯王悖道“有为”,较不善于统摄民生,所以民众“生之徒,十有三”。
以“义”治国的下德侯王悖道“有为”,很不善于统摄民生,所以民众“死之徒,十有三”。
以“礼”治国的下德侯王悖道“有为”,极不善于统摄民生,所以民众“动皆之死地,亦十有三”。
《老子》初始本首章的“人道四境”和“侯王四型”,应用于《太上不知章》,即为“侯王四境”: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
以“德”治国的上德侯王顺道“无为”,所以民众“不知有之”。
以“仁”治国的下德侯王轻度悖道“有为”,所以民众“亲而誉之”。
以“义”治国的下德侯王重度悖道“有为”,所以民众“畏之”。
以“礼”治国的下德侯王极度悖道“有为”,所以民众“侮之”。
提炼自伏羲太极图外圈四卦的侯王四境:德↘仁↘义↘礼,见于《老子》初始本首章,贯穿《老子》全书。
《老子》初始本首章《上德不德章》,又按照顺道“无为”、悖道“有为”,把“侯王四型”分为“上德”和“下德”两类: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以“德”治国的“上德”侯王,仅有一型,独有标志是顺道“无为”,所以《老子》把“上德”侯王对位于伏羲太极图外圈正东的春分泰卦
 。
。
以“仁↘义↘礼”治国的“下德”侯王,共有三型,共同标志是悖道“有为”,所以《老子》把“下德”侯王对位于伏羲太极图外圈正西的秋分否卦
 。
。
但是这一提炼并非《老子》首创的私见,而是夏商周政治制度的建构原理,所以《老子》全书援引夏商周的四大政治制度,即太庙神谕制度、明堂月令制度、侯王谦称制度、泰否左右制度,阐明夏商周政治制度的建构原理是“礼必本于太一”,夏商周政治制度的核心是“扬泰抑否”。
夏商周政治制度的基本理念是“人文效法天文”,证见《周易·易经·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见《周易·系辞上》:“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圣人象之。”又见《周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落实基本理念“人文效法天文”的建构原理是“礼必本于太一”,所以“礼必本于太一”贯穿于夏商周的一切政治制度,包括《老子》援引的夏商周四大政治制度:太庙神谕制度、明堂月令制度、侯王谦称制度、泰否左右制度。
《老子》援引“礼必本于太一”的夏商周太庙神谕制度,教诲天下侯王顺从“太一”之父、母、子。
首先,《老子》教诲天下侯王顺从“太一”之“父”,亦即信仰天道。见于《道生一章》、《唯道是从章》。
人之所教,亦我而教人。故“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道生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父。(唯道是从章)
《道生一章》先言“人之所教,亦我而教人”,阐明夏商周政治制度的建构原理是“礼必本于太一”;后引镌刻于东周太庙“太一”上帝神像背部的神谕《金人铭》“强梁者不得其死”,称颂“太一”上帝为“教父”。
《唯道是从章》进而言高于“教父”的“众父”,教诲天下侯王:顺从可知、可得、可道的“浑天说”范畴之太阳系“教父”,即为顺从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的“宣夜说”范畴之宇宙“众父”。
其次,《老子》教诲天下侯王顺从“太一”之“母”,亦即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见于《道可道章》、《有状混成章》、《天下有始章》、《治人事天章》、《敬天畏人章》。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道可道章)
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有状混成章)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殁身不殆。(天下有始章)
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治人事天章)
我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敬天畏人章)
《道可道章》之“恒道”,即“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其天文存在可知,其历法知识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不能被人类拥有,故称“无”。可道的“常道”,即“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其天文存在可知,其历法知识可知、可得、可道,能被人类拥有,故称“有”。天文存在属“父”,历法知识属“母”,故称“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为“万物之母”。
《有状混成章》之“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即“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太一”为因,“天地”为果,故言“先天地生”,故称“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为“天地母”。
《天下有始章》之“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即言夏商周政治制度“礼必本于太一”,故称“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为“天下母”。
《治人事天章》之“有国之母,可以长久”,亦言夏商周政治制度“礼必本于太一”,故称“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为“有国之母”。
《敬天畏人章》之“我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亦言夏商周政治制度“礼必本于太一”,故称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为“贵食母”。
最后,《老子》教诲天下侯王顺从“太一”之“子”,即遵循“泰道”治国。见于《道生一章》、《天下有始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生一章)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殁身不殆。(天下有始章)
“道生一”之“道”,即“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道生一”之“一”,即“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关键词,是连言四次的“生”,所以后续两句阐明道“生”万物之基本原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两句均言“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标示春分的泰卦:“负阴而抱阳”,即言泰卦之卦象
 ,上卦背负三阴,下卦抱持三阳;“冲气以为和”,即言泰卦之卦义,上卦阴气下行,下卦阳气上行,阴阳二气相冲而和。
,上卦背负三阴,下卦抱持三阳;“冲气以为和”,即言泰卦之卦义,上卦阴气下行,下卦阳气上行,阴阳二气相冲而和。
由于“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以春分泰卦标示道“生”万物之基本原理,以秋分否卦标示道“杀”万物之基本原理,所以《老子》教诲天下侯王首先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其次效法春气“生”物的基本原理“泰道”,不能效法秋气“杀”物的基本原理“否术”。
《老子》称天文存在“太一”帝星及其神格化的“太一”上帝为“教父”,称历法知识“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为“万物之母”、“天地母”、“天下母”、“有国之母”,所以称“泰道”为“太一”父母之“子”。
《天下有始章》之“既得其母”,义同《侯王得一章》之“侯王得一”,因为“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揭示的太阳系规律,是地球生物圈的万物之“母”。“以知其子”,“子”即“太一”父母“生”万物的基本原理“泰道”。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意为:侯王既然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就应知晓春气“生”物的基本原理“泰道”,乃是“太一”父母之“子”。“泰道”之“母”是作为历法知识的“太一”历法图,亦即“有国之母”。“泰道”之“父”是作为天文存在的“太一”帝星及其神格化的“太一”上帝,亦即“教父”。
“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殁身不殆”意为:侯王既已知晓春气“生”物的基本原理“泰道”是“太一”父母之“子”,只要遵循“泰道”治国,就能国泰民安,“殁身不殆”,“长生久视”,“子孙祭祀不绝”。
由于《老子》初始本以“太一”上帝为“教父”,所以《老子》初始本的文体是宗教神话时代的神谕体兼先知体,其第一人称“我”和“吾”,或为“太一”上帝的神谕口吻,或为作为宗教祭司的先知口吻、圣君口吻。神谕体、先知体其实都是祭司体,祭司代表自己说话就是先知体,祭司代表上帝说话就是神谕体。由于《老子》的教诲对象是侯王,所以先知体兼神谕体是教诲侯王的恰当文体。神谕体兼先知体决定了《老子》的极简主义文风,省略成分极多。只有充分了解史官老子熟知的上古至中古知识背景,同时充分了解《老子》的教诲对象和思想宗旨,才能正确理解《老子》大量省略的究竟是什么。
《老子》援引“礼必本于太一”的夏商周明堂月令制度,教诲天下侯王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见于《不出于户章》、《上善若水章》。
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不出于户章)
居善地……动善时。(上善若水章)
理解《不出于户章》和《上善若水章》,必须了解夏商周的王城结构、明堂结构、式盘结构全都效法“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之伏羲十二辟卦。
夏商周的王城十二门、明堂十二室、式盘十二支,全都效法伏羲太极图之十二辟卦。夏商周侯王每月所居明堂之室,对应北斗七星之斗柄:每月初一,侯王移居斗柄所指明堂之室。夏商周的明堂月令制度,详见《礼记·月令》,《吕氏春秋》之十二纪,《逸周书》之《明堂解》、《月令解》,蔡邕《明堂月令论》等,参看拙著《玉器之道》第九章《昆仑台传播史》。

▲伏羲十二辟卦→王城十二门、明堂十二室、式盘十二支
夏商周侯王所居明堂,四方各三室,合计十二室,对应北斗斗柄所指十二月:春季三月(寅月、卯月、辰月),侯王逐月移居东方三室(寅室、卯室、辰室)。夏季三月(巳月、午月、未月),侯王逐月移居南方三室(巳室、午室、未室)。秋季三月(申月、酉月、戌月),侯王逐月移居西方三室(申室、酉室、戌室)。冬季三月(亥月、子月、丑月),侯王逐月移居北方三室(亥室、子室、丑室)。闰年之闰月,侯王移居明堂中间的太室。
道家出于史官,史官执掌伏羲天文象数易。夏商周的明堂月令制度,按照天文“本数”,制定人文“末度”,合称“数度”(《庄子·天下》)。“度”之本义,即“天有三百六十度”之“度”。“制度”之本义,即“人”之“制”合于“天”之“度”。所以《周礼·春官宗伯·大史》曰:“大史(太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说文解字》释“闰”曰:“余分之月,五岁再闰,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闰月居门中。从‘王’,在‘门’中。《周礼》曰:‘闰月,王居门中。’”“王居门中”之“门”,正是明堂之“门”,亦即《不出于户章》“不出于户”之“户”。
《说文解字》所言“告朔之礼”,即侯王每月初一移居明堂某室之时的祭天仪式。老子作为《周礼·春官宗伯·大史》所言主持“告朔之礼”的东周太史,深知夏商周明堂月令制度的建构原理是“礼必本于太一”,所以据此教诲天下侯王:
侯王居于“礼必本于太一”的明堂,“不出”明堂之“户”,就能“知天下”;“不窥”明堂之“牖”,就能“知天道”。侯王只要顺道“无为”,亦即不干扰农时,“天下”百姓就能顺应“天道”,遵循“自然”节令,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于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
《老子》所言“稽式”、“天下式”,均用本义“式盘”(见上页第6图),“稽式”意为“稽古之式盘”,“天下式”意为“治理天下之式盘”。正因夏商周式盘效法“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所以又称“法式”。汉后注家不知“稽式”、“天下式”均指效法“太一”历法图的夏商周式盘,望文生义地空泛阐释“稽式”、“天下式”,不可能读懂《老子》。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周易·彖传·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论语·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文子·道原》:“调其数而合其时,时之变则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所言“与时迁移”、“与时消息”、“使民以时”、“调其数而合其时”,均与侯王逐月移居北斗斗柄所指明堂之室有关,亦即《上善若水章》之“动善时”,“居善地”。
孔子两次问“礼”于老子(详见第一章),“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必闻老子“礼必本于太一”之教。所以战国儒家所撰《礼记·礼运》遂言:“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
《老子》初始本援引的夏商周明堂月令制度,以及侯王所居明堂之室对应北斗七星之柄,北斗七星指向太一帝星等,不仅是准确理解《不出于户章》、《上善若水章》的必备知识,而且是准确理解《老子》初始本之象数结构的必备知识(详见本章第三节)。
《老子》援引“礼必本于太一”的侯王谦称制度,教诲天下侯王遵循“泰道”,自损自弱。见于《侯王得一章》、《道生一章》。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此其贱之本邪?(侯王得一章)
人之所恶,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名也。是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道生一章)
《侯王得一章》先言“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即侯王“既得其母,复知其子”,得到“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之后,必须以春气“生”物的基本原理“泰道”为治国正道;后言“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即言侯王遵循“泰道”,自损自弱而用谦称。
《道生一章》先言侯王谦称“孤、寡、不穀”,然后援引镌刻于东周太庙“太一”上帝神像背部的《金人铭》贬斥“否术”之言“强梁者不得其死”,点破“教父”(“太一”上帝)之神谕,正是褒扬春气“生”物的基本原理“泰道”,贬斥秋气“杀”物的基本原理“否术”,亦即“扬泰抑否”。
《老子》援引“礼必本于太一”的夏商周泰否左右制度,教诲天下侯王效法“太一”,“扬泰抑否”。见于《天道左右章》、《兵者不祥章》、《以正治国章》、《柔之胜刚章》。

▲夏商周“太一”历法图(黄帝族方位:上南下北,左东右西)
道泛兮,其可左右。(天道左右章)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以吉事尚左,丧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兵者不祥章)
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柔之胜刚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正治国章)
《天道左右章》之“道泛兮,其可左右”,对应夏商周“太一”历法图之左右
 :左为春气“生”物的泰卦
:左为春气“生”物的泰卦
 ,右为秋气“杀”物的否卦
,右为秋气“杀”物的否卦
 。天道生杀万物,既有春气“生”物的“泰道”,也有秋气“杀”物的“否术”。
。天道生杀万物,既有春气“生”物的“泰道”,也有秋气“杀”物的“否术”。
《兵者不祥章》之“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即言夏商周按照“礼必本于太一”的政治理念,建构了泰否左右制度。
明白了夏商周的泰否左右制度,就能正确理解《柔之胜刚章》、《以正治国章》。
《柔之胜刚章》之“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亦言夏商周的泰否左右制度,以春气“生”物的泰道治国,不以秋气“杀”物的否术治国。
《以正治国章》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亦言夏商周的泰否左右制度,以春气“生”物的泰道治国,以秋气“杀”物的否术用兵。
春分泰卦
 位于“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正东,东方属木,主生,东方苍龙七宿同样主生。侯王的历法对位是东方春分泰卦,侯王的天文对位是东方苍龙七宿,冠冕、服饰、器物、仪仗均用龙形,所执权柄为“左契”,所以侯王的治国正道是春气“生”物的“泰道”。
位于“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正东,东方属木,主生,东方苍龙七宿同样主生。侯王的历法对位是东方春分泰卦,侯王的天文对位是东方苍龙七宿,冠冕、服饰、器物、仪仗均用龙形,所执权柄为“左契”,所以侯王的治国正道是春气“生”物的“泰道”。
秋分否卦
 位于“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正西,西方属金,主杀,西方白虎七宿同样主杀。将军的历法对位是西方秋分否卦,将军的天文对位是西方白虎七宿,冠冕、服饰、器物、仪仗均用虎形,所执兵符为“虎符”,所以将军的用兵奇术是秋气“杀”物的“否术”。
位于“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正西,西方属金,主杀,西方白虎七宿同样主杀。将军的历法对位是西方秋分否卦,将军的天文对位是西方白虎七宿,冠冕、服饰、器物、仪仗均用虎形,所执兵符为“虎符”,所以将军的用兵奇术是秋气“杀”物的“否术”。
与马王堆帛书《老子》同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乃是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而亡佚两千年的《黄帝四经》。《黄帝四经》继承了《老子》所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故其《称》篇曰:“奇从奇,正从正。奇与正,恒不同廷。”故其《十大经·前道》亦曰:“名正者治,名奇者乱。正名不奇,奇名不立。正道不殆,可后可始。乃可小夫,乃可国家。小夫得之以成,国家得之以宁。小国得之以守其野,大国得之以并兼天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古伏羲族的伏羲太极图采用伏羲族方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故其泰卦居右,否卦居左。中古夏商周的“太一”历法图采用黄帝族方位: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故其泰卦居左,否卦居右。因此《天道左右章》之“道泛兮,其可左右”,意为“道泛兮,其可泰否”;《兵者不祥章》之“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丧事尚右”,意为“君子居则贵泰,用兵则贵否……吉事尚泰,丧事尚否”;《以正治国章》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意为“以泰治国,以否用兵”。
个别学者明白《老子》所言“左右”,源于夏商周政治制度之“左右”。
比如高亨《重订老子正诂》曰:“《逸周书·武顺》篇:‘吉礼左还,顺天以立本。武礼右还,顺地以利兵。’《诗·裳裳者华》:‘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传:‘左阳道,朝祀之事。右阴道,丧戎之事。’并与《老子》此文相合。”

再如高明《帛书老子校注》曰:“‘左’为阳位属吉,‘右’为阴位属丧。《礼记·檀弓上》‘二三子皆尚左’,郑玄注:‘丧尚右,右阴也。吉尚左,左阳也。’”

又如徐志钧《老子帛书校注》曰:“春秋时贵族日常生活中以左为上。无论宾主席位,马车乘坐,器物执着,都是这样。《礼记·曲礼下》:‘执主器,操币、圭、璧,则尚左手。’注:‘谓以左手为尊也。’”
 参看郑玄注:“上左,上右,拱手时左手在上或右手在上也。”
参看郑玄注:“上左,上右,拱手时左手在上或右手在上也。”
高亨、高明、徐志钧虽已明白《逸周书》、《诗经》及毛传、《礼记》及郑注所言左阳右阴,合于《老子》所言左阳右阴,然而不知《老子》所言左阳右阴,植根于夏商周政治制度之左阳右阴,更加不知夏商周政治制度之左阳右阴,植根于夏商周“太一”历法图之左阳右阴、左泰右否。因为在拙著《伏羲之道》之前,伏羲太极图之初始卦序及其上古伏羲族方位、中古黄帝族方位已经失传两千多年。
尽管汉后两千多年的历代学者不再了解老子熟知的伏羲太极图初始卦序及其两种方位,然而稍后于春秋老子的战国诸子,仍然了解老子熟知的伏羲太极图初始卦序及其两种方位,所以继承《老子》的战国“黄帝之书”、稷下“黄老学派”以及诸子百家,全都明白《老子》所言“泰否左右”源于夏商周泰否左右制度。
比如《黄帝四经》之《十大经·雌雄节》,继承《老子》而阐明了“夏后氏”开创的泰否左右制度,乃是效法“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
皇后历吉凶之常,以辨雌雄之节,乃分祸福之向。……
凡人好用雄节,是谓妨生。大人则毁,小人则亡。以守不宁,以作事不成。以求不得,以战不克。厥身不寿,子孙不殖。是谓凶节,是谓散德。
凡人好用雌节,是谓承禄。富者则昌,贫者则[康]。以守则宁,以作事则成。以求则得,以战则克。厥身[长生,子孙不绝。是谓吉]节,是谓绛德。
故德积者昌,[刑]积者亡。观其所积,乃知祸福之向。([]内缺字为笔者补入。)
“雌雄节”之名,承于《老子》“知其雄,守其雌”。“雌”指“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春分泰卦之上卦三阴,“雄”指“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秋分否卦之上卦三阳,因为侯王对位上卦,民众对位下卦。“节”指“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春分泰卦之节气、秋分否卦之节气。
“皇后”指开创夏商周泰否左右制度的夏代侯王,“皇”训古,“后”即“夏后氏”之“后”,商代盘庚迁殷之前,酋长、君王均称“后”。
“皇后历吉凶之常,乃分祸福之向”,意为“夏后氏”开创了效法“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的夏商周泰否左右制度: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之吉凶常道,分辨祸福之趋向。
“凡人好用雄节,是谓妨生”一节,阐明夏商周泰否左右制度之“抑否”,因为侯王奉行秋气“杀”物的否术必将“妨生”。
“凡人好用雌节,是谓承禄”一节,阐明夏商周泰否左右制度之“扬泰”,因为侯王遵循春气“生”物的泰道方能“承禄”。
“故德积者昌,刑积者亡”一节,阐明“泰道”为“德政”,积久必昌;“否术”为“刑政”,积久必亡。
稷下“黄老学派”的第一经典《管子》,也继承了《老子》所言“左右”:
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管子·版法解》)
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出者而不伤人,入者自伤也。(《管子·白心》)
《管子·版法解》之“版法”,意为图版之法,亦即“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之图法。故其所言“文事在左,武事在右”,承于《老子》“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对应夏商周“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之左阳右阴、左泰右否。故其所言“生长之事”,亦即“春生夏长”,对应夏商周“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左面的阳仪。故其所言“收藏之事”,亦即“秋收冬藏”,对应夏商周“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右面的阴仪。故其所言“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即言夏商周泰否左右制度的建构原理“礼必本于太一”。
《管子·白心》之“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即言“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左面为东,是日出月出之方;右面为西,是日入月入之方。“出者而不伤人,入者自伤也”,即言东方泰道不伤人,西方否术伤人。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老子》提炼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的对词“泰/否”及其宗旨“扬泰抑否”,被老子弟子范蠡创造性转化为对词“德/刑”及其宗旨“扬德抑刑”,见于范蠡所撰《范子·计然》:“德取象于春夏,刑取象于秋冬。”(《太平御览》卷二二引)范蠡明言“德”(即春气生物的泰道)取象于“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阳仪之春夏二季,“刑”(即秋气杀物的否术)取象于“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阴仪之秋冬二季。
战国“黄帝之书”继承了范蠡对《老子》的创造性转化,所以对词“德/刑”及其宗旨“扬德抑刑”大量见于《黄帝四经》。比如《十大经·雌雄节》:“德积者昌,刑积者亡。”再如《十大经·观》:“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而盈屈无匡。”又如《十大经·姓争》:“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
稷下“黄老学派”又继承了战国“黄帝之书”,所以对词“德/刑”及其宗旨“扬德抑刑”,也见于《管子·势》:“不犯天时,不乱民功。秉时养人,先德后刑。顺于天,微度人。”又见于《管子·四时》:“阳为德,阴为刑。”
经过春秋末年老子弟子范蠡、战国“黄帝之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持续传播,对词“德/刑”最终成为诸子百家的通用术语,大量见于战国秦汉文献。
比如战国道家著作《鹖冠子·王》:“天者诚其日,德也。日,诚出诚入,南北有极,故莫弗以为法则。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终则有始,故莫弗以为政。天者明其星,稽也。列星不乱,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
再如大量吸收《老子》的韩非所著《韩非子·二柄》:“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
又如《春秋繁露·阳尊阴卑》:“阳为德,阴为刑。”均据“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而言“德/刑”。
还有《淮南子·兵略训》:“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体圆而法方,背阴而抱阳,左柔而右刚,履幽而戴明,变化无常,得一之原,以应无方,是谓神明。”(《文子·自然》略同)“背阴而抱阳”,即“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左面的春分泰卦:“背阴”即泰卦上卦三阴,“抱阳”即泰卦下卦三阳。“左柔”即泰卦居“左”而“柔”,“右刚”即否卦居“右”而“刚”。“履幽而戴明”,即“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右面的秋分否卦:“戴明”即否卦上卦三阳,“履幽”即否卦下卦三阴。“变化无常,得一之原,以应无方,是谓神明”,即言得到“变化无常”的“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可以因应无方,上应神明之道。《淮南子·精神训》专言“背阴抱阳”、“以正治国”之泰道,《淮南子·兵略训》专言“履幽戴明”、“以奇用兵”之否术,深明《老子》宗旨“扬泰抑否”。
综上所论,夏商周政治制度的基本理念“人文效法天文”和建构原理“礼必本于太一”,导致泰否左右制度合于“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之泰否左右。由于夏商周的泰否左右制度植根于“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之泰否左右,所以《老子》第一宗旨是“扬泰抑否”。由于《老子》第一宗旨是“扬泰抑否”,所以战国“黄帝之书”、稷下“黄老学派”才会“扬德抑刑”。所以“扬泰抑否”并非《老子》的新创私见,而是源于夏商周政治制度的建构原理“礼必本于太一”,所以《柔之胜刚章》才说:“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所处春秋晚期,天下侯王“莫不知”夏商周政治制度的建构原理是“礼必本于太一”,天下侯王“莫不知”夏商周政治制度的第一宗旨是“扬泰抑否”,却又“莫能行”,所以老子“见周之衰”而撰著《老子》,抉发夏商周政治制度的建构原理“礼必本于太一”和第一宗旨“扬泰抑否”。
《老子》援引夏商周四大政治制度,阐明其建构原理“礼必本于太一”和第一宗旨“扬泰抑否”,《汉书·艺文志》称为“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夏商周四大政治制度共同遵循的“泰道”,《太一生水》称为“天道贵弱”,《庄子·天下》称为“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汉书·艺文志》称为“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战国“黄帝之书”,稷下“黄老学派”,不仅全都继承《老子》提炼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的对词“泰/否”及其宗旨“扬泰抑否”,而且全都明白《老子》哲学体系的源代码是“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后人假如不知“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是《老子》哲学体系的源代码,不仅不能正确理解《老子》,也不能正确理解继承《老子》的战国“黄帝之书”、稷下“黄老学派”以及诸子百家,因为老子不仅是百家之祖,而且是百家之源。
《老子》援引夏商周的太庙神谕制度、明堂月令制度、侯王谦称制度、泰否左右制度,意在阐明“人之所教,亦我而教人”,亦即“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内涵、“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内涵均非老子的个人私见,而是夏商周政治制度的建构原理和一贯传统。但是夏商周的另一政治传统“绝地天通”,亦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导致夏商周政治制度的建构原理“礼必本于太一”,长期成为庙堂内部的隐秘知识。经由《老子》援引夏商周四大政治制度并阐明其建构原理“礼必本于太一”,“礼必本于太一”才在战国时代传播天下,成为华夏文明的公共知识。
按照夏商周政治制度的基本理念“人文效法天文”和建构原理“礼必本于太一”,秋气“杀”物之时,方能用兵用刑。所以邦国开战须在秋后,谓之“秋后算账”。处决死囚也在秋后,谓之“秋后问斩”。罗马帝国处决死囚则在二月,所以罗马太阳历的二月天数最少。
道家祖师老子提炼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的“泰道/否术”以及《老子》第一宗旨“扬泰抑否”,是轴心时代中国哲学突破的核心内容。此后战国“黄帝之书”、稷下“黄老学派”、诸子百家无不继承发挥老子的哲学突破。各家的继承发挥虽有差异,但其共同源头是“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因为“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是伏羲六十四卦的卦象合成,而伏羲六十四卦见于夏代《连山》、商代《归藏》、周代《周易》,是上古华夏(前6000—前2000)至中古夏商周(前2000—前221)的华夏文化总基因。
《老子》“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内涵,“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内涵,全部提炼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所以《老子》教诲天下侯王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见于《侯王得一章》、《抱一爱民章》、《唯道是从章》、《执今之道章》、《知雄守雌章》。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侯王得一章)
载营魄抱一,能毋离乎?……爱民治国,能毋以知乎?(抱一爱民章)
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唯道是从章)
一4 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执4 今之道……以为道纪。(执今之道章)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贷,复归于无极。(知雄守雌章)
《侯王得一章》之“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抱一爱民章》之“载营魄抱一”和“爱民治国”,《唯道是从章》之“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执今之道章》之“执今之道”,都是教诲天下侯王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
或问:既然“道生一”意为“宣夜说”范畴的“道”产生并总摄“浑天说”范畴的“一”,那么《老子》为什么不主张侯王“得道”、“抱道”、“执道”,把“宣夜说”范畴的“道”作为治国正道,却主张侯王“得一”、“抱一”、“执一”,把“浑天说”范畴的“一”作为治国正道?
因为《老子》反复申言“知不知,上矣。不知不知,病矣”,“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亦即人类难以尽知“宣夜说”范畴的“道”,只能略知“浑天说”范畴的“一”。所以侯王不可能“得道”、“抱道”、“执道”,不可能把“宣夜说”范畴的“道”作为治国正道;只能“得一”、“抱一”、“执一”,只能把“浑天说”范畴的“一”作为治国正道,亦即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
《执今之道章》所言“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意为:“无极恒道”人类不知,“太一常道”人类已知。所以“执今之道”、“以为道纪”意为:“侯王执一以为天下牧”,即执今人已知的“太一常道”,奉为永难尽知的“无极恒道”之纲纪。
《知雄守雌章》所言“为天下式”,即言侯王把“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作为治理天下的“法式”,但要时刻铭记自己不知“无极恒道”,所以必须“恒德不贷,复归于无极”。
《老子》把“道生一”作为哲学体系的第一基石,教诲天下侯王:信仰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不可有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遵循可知、可得、可道、可有的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彻悟人类的永恒无知,永不自居全知全能,永不悖道“有为”,永不任意“妄作”。
《老子》把“宣夜说”范畴的“道”称为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的“恒道”,把“浑天说”范畴的“一”称为可知、可得、可道的“常道”,所以《天下有始章》把侯王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称为“袭常”。
《老子》称天文存在为“父”,称历法知识为“母”,所以《治人事天章》把“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称为“有国之母”,《敬天畏人章》把侯王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称为“贵食母”。
或问:《老子》为什么以“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为源代码,一切重要价值全都从中提炼而出?
答曰:因为“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是华夏文化、中国文明的总基因,而《老子》哲学体系的宗旨是“人文效法天文,人道效法天道”,亦即“以人合天,顺天应人”,所以《老子》以“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为源代码,建构其哲学体系。
老子以“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为源代码,建构《老子》哲学体系,纳入“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内涵和“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内涵,所以老子自定了《老子》初始本的“太一”象数结构:全书七十七章,对应北斗七星;上经《德经》四十四章,对应斗魁四星;下经《道经》三十三章,对应斗柄三星。
《老子》初始本之七十七章对应北斗七星,可举内部证据、外部证据、考古证据各三。
内部证据一,上古伏羲时代创立的华夏天文体系,由北斗七星领衔二十八宿,围绕“太一”帝星旋转。华夏天文体系转化为华夏历法体系,合为伏羲天文象数易的“太一”象数体系:“象”即天象,“数”即历数。老子身为执掌天文历法的东周史官,精通伏羲天文象数易之“太一”象数体系,所以把《老子》初始本之总章数,定为对应北斗七星的七十七章,总摄“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内涵和“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内涵。
内部证据二,《老子》援引的太庙神谕制度,是“太一”帝星神格化的“太一”上帝之神谕。老子以“太一”上帝为“教父”,所以把《老子》初始本之总章数,定为对应北斗七星的七十七章。
内部证据三,《老子》援引的明堂月令制度,侯王随着北斗七星旋转而移居斗柄所指明堂之室。所以老子把《老子》初始本之总章数,定为对应北斗七星的七十七章。
外部证据一,道家集大成者庄子,明白《老子》的“太一”象数结构,明白《老子》七十七章对应北斗七星而仿效之,所以撰写了对应北斗七星的《庄子》内七篇。
外部证据二,与庄子同时的孟子,同样明白《老子》的“太一”象数结构,同样明白《老子》七十七章对应北斗七星而仿效之,所以撰写了对应北斗七星的《孟子》内七篇。
今人假如囿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门户之见,可能感到奇怪:孟子是儒家,不是道家,为什么像庄子一样仿效《老子》?因为“太一”象数体系是华夏公共知识,并非道家私有知识。战国之时尚无后世的百家分类,更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门户之见,所以战国诸子百家共尊“黄老”,把老子尊为诸子百家之元祖。孔子曾经师事老子、问道于老子(见于《论语》、《礼记》、《孔子家语》、《庄子》、《史记》等大量古籍),也使孟子仿效《老子》毫无心理障碍。何况孟子作为齐国稷下学宫的学士,广义上也属于稷下“黄老学派”的成员,所以孟子只反“杨墨”,不反老子。孟子仿效《老子》,相当于现代学者遵从主流学术界的学术规范,只会为孟子加分,不会为孟子减分。
外部证据三,西汉道家传人刘安,曾与九大门客共同编纂了抉发伏羲天文象数易的《淮南道训》(汉后久佚,今存少量佚文),所以同样明白《老子》的“太一”象数结构,同样明白《老子》七十七章对应北斗七星,同样明白《庄子》内七篇对应北斗七星,所以按照《老子》的“太一”象数结构,把《庄子》初始本扩充为《庄子》大全本:“内篇七”对应北斗七星,“外篇二十八”对应二十八宿,“杂篇十四”对应东方苍龙七宿、西方白虎七宿;三项合计七七四十九篇,对应《老子》七十七章。另附刘安自撰的“解说三”,不属象数结构。
考古证据一,北大收藏的西汉中期汉简本《老子》,早于西汉晚期成书的《老子》传世本之祖本(详见第三章),属于《老子》初始本系统,全书七十七章,上经《德经》四十四章,下经《道经》三十三章。这是《老子》初始本总章数和上经《德经》章数、下经《道经》章数的考古证据之强证。
考古证据二、三,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期帛甲本、西汉早期帛乙本,均为上经《德经》四十四章连抄,下经《道经》三十三章连抄,各章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章标志,但其上经《德经》四十四章和下经《道经》三十三章的经文,与汉简本基本相当。这是《老子》初始本总章数是七十七章、上经《德经》是四十四章、下经《道经》是三十三章的考古证据之弱证,即对强证不构成反证。
《老子》四大出土本中,仅有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期楚简本是摘抄本,不能作为《老子》初始本总章数、上经《德经》章数、下经《道经》章数的考古证据。
以上九大证据,充分证明《老子》七十七章对应北斗七星。
上古伏羲族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创立的华夏天文体系,以北斗七星领衔二十八宿围绕“太一”帝星旋转,所以北斗七星共有三大天文功能。
北斗七星的第一天文功能是揭示全部天体围绕“太一”帝星旋转,作为四季北斗合成符的万字符是夏商周天文历法的“斗建”符号:天盘万字符卍标示天球之顺时针旋转,地盘万字符卐标示地球之逆时针旋转。所以中古夏商周祭祀“太一”上帝的乐舞称为“万舞”,意为“万字符之舞”。商代甲骨文之“卍舞”,正是《诗经》、《墨子》、《左传》、《史记》等大量古籍所言“万舞”,“万”是“卐”的秘藏写法(详见拙著《玉器之道》)。所以战国道家著作《鹖冠子·环流》曰:“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史记·天官书》则曰:“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北斗七星的第二天文功能和第三天文功能,分别属于斗魁四星(斗勺四星),斗柄三星(斗杓三星)。
斗魁四星的天文功能是指认北极星:新石器时代中期是以天玑星、天权星的延长线指认“太一”帝星,秦汉以后是以天璇星、天枢星的延长线指认“勾陈一”(参看本章第一节之图)。所以华夏神谱除了对应北斗七星的北斗星君,另有对应斗魁四星的斗魁星君。遍布华夏全境的“魁星阁”,供奉之神并非北斗星君,而是斗魁星君。
斗柄三星的天文功能是指认二十八宿之第一宿“角宿”:开阳星、摇光星的延长线指向二十八宿之第一宿,亦即苍龙七宿之第一宿“角宿”,所以《史记·天官书》曰:“北斗七星,杓携龙角。”
老子自定的《老子》初始本之“太一”象数结构,分别对应北斗七星、斗魁四星、斗柄三星的天文功能:全书七十七章,对应围绕“太一”帝星旋转的北斗七星;上经《德经》四十四章,对应指向“太一”帝星的斗魁四星;下经《道经》三十三章,对应指向“龙角”的斗柄三星。
老子按其自定的《老子》“太一”象数结构,先把天文层面之“象”,转化为历法层面之“数”,表达“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内涵;再把天文历法之“本数”,转化为政治制度之“末度”,表达“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内涵。
老子自定的《老子》初始本之“太一”象数结构,再次证明《老子》不是老子出关之时应关尹之请的即兴书写,而是老子精思密虑的毕生著作。
明白老子自定的《老子》初始本之“太一”象数结构,不仅有助于理解《老子》初始本援引的夏商周四大政治制度:太庙神谕制度、明堂月令制度、侯王谦称制度、泰否左右制度,也有助于理解上经《德经》“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内涵,有助于理解下经《道经》“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内涵,更有助于理解“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是《老子》初始本的源代码。
《老子》初始本的源代码是夏商周“太一”历法图(即夏商周伏羲太极图),并非我的个人私见,而是战国道家的共识和常识,证见老子后学所撰《太一生水》,庄子后学所撰《庄子·天下》。
与郭店《老子》同墓出土的《太一生水》,撰者是老子后学,宗旨是解密《老子》“太一”象数结构的源代码是“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两节分别阐释《老子》“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内涵和“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内涵。
《太一生水》第一节,阐释《道生一章》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言曰: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寒热。寒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
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寒热之所生也。寒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
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
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埋,阴阳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谓圣,不知此之谓冥。
《太一生水》第一节,解密《老子》“太一”象数结构的源代码是“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阐释《老子》“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内涵,分为四层。
第一层,主词是“成”,即伏羲天文象数易之“成数”,乃言“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是《老子》的源代码。要义是“太一成岁”,因为“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是计算一岁“成数”的历法图。始于最初之因“太一”,中间过程是“成天地”,“成神明”,“成阴阳”,“成四时”,“成寒热”,“成湿燥”,结于最终之果“成岁而止”。
第二层,主词是“生”,即伏羲天文象数易之“生数”,仍言“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是《老子》的源代码。要义是“岁生于太一”,因为一岁生于太阳围绕“太一”帝星旋转一周。始于最终之果“岁”,中间过程是“湿燥之所生”,“寒热之所生”,“四时之所生”,“阴阳之所生”,“神明之所生”,“天地之所生”,结于最初之因“太一之所生”。
上古伏羲时代至中古夏商周的伏羲天文象数易,以“成数”表示由因推果的顺推过程,以“生数”表示由果推因的逆推过程。所以第一层、第二层的要素全同,顺序互逆,“太一”是最初之因,“成岁”是最终之果。
第三层,概括第一层、第二层,解密《老子》“太一”象数结构的源代码是“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太一藏于水”,对应《老子》“上善若水”。“行于时”,对应《老子》“动善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对应《老子》“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第四层,把前三层所言“天道”,移用于“人道”:“君子知此之谓圣,不知此之谓冥。”因为《老子》把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的“侯王”称为“圣人”:“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
《太一生水》第二节,解密《道生一章》之“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老子提炼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春分泰卦的“泰道”。其言曰:
下,土也,而谓之地。上,气也,而谓之天。道亦其字也,青昏其名。
以道从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长。圣人之从事也,亦托其名,故功成而身不伤。
天地名字并立,故化其方,不思相尚。
天道贵弱,削成者,以益生者;伐于强,积于弱。何谓也?天不足于西北,其下高以强;地不足于东南,其上厚以壮。不足于上者,有余于下;不足于下者,有余于上。
《太一生水》第二节,阐释《老子》“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内涵,也分四层。
第一层,“下,土也,而谓之地。上,气也,而谓之天”,是以伏羲六十四卦之上卦、下卦对位天地、君臣,上卦对位天与君,下卦对位地与臣。“道亦其字也,青昏其名。”对应《老子》“字之曰道”。此“道”是太阳围绕“太一”帝星旋转的“太一常道”。
第二层,先言“以道从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长”,这是泛言人类之“泰道”。后言“圣人之从事也,亦托其名,故功成而身不伤”,这是专言侯王之“泰道”,即“君人南面之术”。
第三层,“天地名字并立,故化其方,不思相尚”。“天地名字并立”,比拟君臣并立。“故化其方”,意为侯王选择天道之一端“泰道”。“不思相尚”,意为天不以“否术”灭地,地亦不以“否术”灭天;君不以“否术”杀臣,臣亦不以“否术”杀君。
第四层,“天道贵弱”,对应《老子》“柔弱胜刚强”之泰道:天道既然贵弱,对位于天的侯王,也应效法“天道”而“贵弱”。
“天道贵弱”之“泰道”,是“削成者,以益生者;伐于强,积于弱”,这是阐释《道生一章》第二节的泰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君位居上“成”而“强”,必须削其“成”而伐其“强”,使之不太强;臣位居下“生”而“弱”,必须益其“生”而积其“弱”,使之不太弱。
然后以华夏地理大势为喻,对应《老子》“人法地”。“天不足于西北,其下高以强”,以华夏西北之天低地高,隐喻君弱臣强的“泰道”。“地不足于东南,其上厚以壮”,以华夏东南之天高地低,隐喻君强臣弱的“否术”。其潜台词是:文王八卦对位君道之乾卦,位于西北;所以侯王必须效法华夏西北之天低地高,遵循君弱臣强之“泰道”。
最后小结,“不足于上者,有余于下”,对应《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阐释《老子》主张的“以正治国”之“泰道”。君位居上“成”而“强”,是“有余”者,宜“损之又损之”。臣位居下“生”而“弱”,是“不足”者,宜“益之又益之”。“不足于下者,有余于上”,对应《老子》“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益有余”,阐释《老子》反对的“以奇用兵”之“否术”。
综上所言,《太一生水》全文,解密《老子》初始本的“太一”象数结构。第一节阐释《老子》初始本“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内涵,即《老子》以“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为源代码。第二节阐释《老子》初始本“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内涵,即《老子》以“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之“泰道”为治国正道。
《庄子·天下》,撰者是庄子再传弟子魏牟,宗旨是总论天下道术、方术。
《天下》第一章,专论老子之道承于伏羲之道,亦即解密《老子》“太一”象数结构的源代码是“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第一层,总论伏羲之道是老子之道的源代码。
“古之人”,即上古伏羲氏。“其备乎”,即“古之道术”伏羲太极图之完备。
“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展开“古之道术”伏羲太极图之“完备”以及“其运无乎不在”:“本数”,即伏羲太极图计算一年历法的天文象数。“末度”,即按照伏羲太极图之天文象数而创建的夏商周人文制度。
“六通”,即伏羲六十四卦之六爻。“四辟”,即伏羲太极图外圈开辟四时之卦。
“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即中古夏商周之人文制度,效法“旧法”伏羲太极图之天文象数,“世传”于夏商周史官,最后传至东周史官、道家祖师老子。
第二层,总论孔子问道于老子。“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即儒家祖师孔子问道于道家祖师老子,然后创立了儒家“方术”。
第三层,总论老子“道术”是百家“方术”之祖。“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即百家“方术”称道“古之道术”伏羲之道、老子之道。
《天下》第二章至第四章,是百家“方术”三章,详尽展开百家“方术”称道“古之道术”伏羲之道、老子之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悦之。……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
《天下》第五章,专论关尹所传老子“道术”,继承了“古之道术”伏羲之道: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
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
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于物,不削于人。
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此章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概括关尹所传《老子》初始本之宗旨。
“古之道术”,即伏羲之道。“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即关尹所传老子之道,继承伏羲之道。
“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阐释《老子》第一基石“道生一”:前句对应“宣夜说”范畴之“无极恒道”,后句对应“浑天说”范畴之“太一常道”。乃言《老子》哲学体系“建之以”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不可有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主之以”可知、可得、可道、可有的“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侯王首先必须信仰不可知的“无极恒道”,然后必须遵循可知的“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
“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乃言《老子》第一宗旨“扬泰抑否”,教诲天下侯王遵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之春气“生”物的“泰道”治国。
第二部分,引用《关尹子》、《老子》要义,并予点评,论证第一部分之概括。所引老言“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等,均属《老子》第一宗旨“扬泰抑否”之名言。
《天下》第六章,亦即最后一章,专论庄子之道传承伏羲之道、老子之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因为庄子是道家集大成者,撰者是庄子再传弟子魏牟。
综上所言,由于伏羲之道的本质是天文象数,老子之道的本质是人文制度,老子之道承于伏羲之道的本质是人文制度效法天文象数,所以《庄子·天下》揭示《老子》的“太一”象数结构,称天文象数为“本数”,称人文制度为“末度”,合称两者为“数度”。由于老子人文之道承于伏羲天文之道,所以《老子》人文之道以伏羲天文之道的最高结晶伏羲太极图为源代码,实现了从天文之道到人文之道的哲学突破。
老子后学所撰《太一生水》和庄子后学所撰《庄子·天下》,均以“太一”概括《老子》宗旨,全都兼及“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内涵和“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内涵,全都抉发了《老子》的“太一”象数结构,全都解密了“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是《老子》的源代码。证明“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是《老子》的源代码,既非两者之私见,亦非两者之巧合,而是得自老子真传的先秦道家之共识和常识。
这一得自老子真传的先秦道家之共识和常识,西汉时代仍有传承。
比如西汉早期,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是《庄子·天下》之后总论天下道术、方术的名篇,也像《庄子·天下》一样批评百家“方术”,独赞道家“道术”:“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证明司马谈仍然明白伏羲天文之道是道家人文之道的源代码,仍然明白《老子》宗旨是“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内涵和“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内涵。
再如西汉末期,严遵弟子扬雄的《太玄经》,内容是抉发伏羲天文象数易,书名也取自《老子》“太一”、“玄之又玄”,既认为“伏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又认为“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转引自桓谭《桓子新论·闵友》),证明扬雄得到严遵真传,仍然明白伏羲天文之道是道家人文之道的源代码,仍然明白《老子》宗旨是“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内涵和“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内涵。
然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夏商周“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失传,夏代《连山》、商代《归藏》亡佚,《老子》初始本降维为《老子》传世本,后人再也不可能明白伏羲天文之道是道家人文之道的源代码,也不可能明白《太一生水》、《庄子·天下》共同解密了“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是《老子》“太一”象数结构的源代码,更看不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对道家的评论、扬雄《太玄经》对《老子》的评论,于是得自老子真传的先秦道家之共识和常识,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两千多年,再也无人知晓。
正因《老子》的“太一”象数结构,并非《太一生水》撰者和《庄子·天下》撰者之私见,亦非两者之巧合,而是得自老子真传的先秦道家之共识和常识,所以战国道家《子华子》的“人生四境”,战国道家《庄子》的“生命四境”,全都继承《老子》的“侯王四境”,全都对应夏商周“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的外圈四卦。
战国中期的道家后学子华子,把《老子》的“侯王摄生四境”,转换为《子华子》的“人生四境”:“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
《子华子》把《老子》的“善摄生”、“无死地”,转换为“全生为上”。意为:以“德”治国的上德侯王顺道“无为”统摄民生,民众循德“自为”而“无不为”,得以“全生”。
《子华子》把《老子》的“生之徒,十有三”,转换为“亏生次之”。意为:以“仁”治国的下德侯王悖道“有为”统摄民生,三成的民众陷入“亏生”。
《子华子》把《老子》的“死之徒,十有三”,转换为“死次之”。意为:以“义”治国的下德侯王悖道“有为”统摄民生,三成的民众被诛而死。
《子华子》把《老子》的“民之生生而动,动皆之死地,亦十有三”,转换为“迫生为下”。意为:以“礼”治国的下德侯王悖道“有为”统摄民生,三成的民众陷入“迫生”。
战国中期的道家集大成者庄子,一方面把《老子》的“侯王四境”发展为《庄子》的“生命四境”:“至知—大知—小知—无知”(详见拙著《庄子奥义》);另一方面把《老子》的“侯王四境”,按照《老子》的本意分为“两类侯王”,发展为《庄子·大宗师》的相忘江湖寓言:“泉涸,鱼相与处于陆;与其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相忘于江湖”对位“侯王四境”之第一境,即“太上不知有之”的上德侯王一型;“鱼相与处于陆”对位“侯王四境”之后三境,即“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的下德侯王三型。
由于夏商周“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既是《老子》的源代码,也是《子华子》、《庄子》的源代码,所以《老子》的“侯王四境”,《子华子》的“人生四境”,《庄子》的“生命四境”,全都对应“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的外圈四卦。
夏商周“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属于“天道”,道家祖师老子在春秋晚期把“天道”转化为“人道”,建构了“人文效法天文,人道顺应天道”、“以人合天,顺天应人”的道家哲学体系。战国的道家后学子华子和道家集大成者庄子继承老子,进一步发展、丰富、完善了道家哲学体系。所以老子是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人,《老子》是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书;庄子是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突破集大成者,《庄子》是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突破集大成之书。
本文最后,将伏羲太极图(“太一”历法图)是《老子》的源代码,《老子》四境是《子华子》四境、《庄子》四境的源代码,列为二表。
表1 伏羲太极图是《老子》的源代码

表2《老子》四境是《子华子》四境、《庄子》四境的源代码

表1直观呈现了伏羲太极图(“太一”历法图)是《老子》价值五阶、人道四境、侯王四型、侯王四境、侯王摄生四境的源代码。表2直观呈现了《老子》的侯王四型、侯王四境、侯王摄生四境是《子华子》人生四境、《庄子》生命四境的源代码,所以伏羲太极图(“太一”历法图)是道家通用的源代码。华夏八千年道术,伏老庄一脉相承。
《老子》的“侯王四境”,把伏羲“天道”转化为侯王“人道”,是第一次视线下移,教诲天下侯王“人文效法天文,人道效法天道”,“以人合天,顺天应人”。
《子华子》的“人生四境”,把侯王“人道”转化为民众“人道”,是第二次视线下移,教诲天下民众“人文效法天文,人道效法天道”,“以人合天,顺天应人”。
《庄子》的“生命四境”,把《老子》的侯王“人道”和《子华子》的民众“人道”予以综合,并非视线下移,而是充类至尽,教诲全体人类“人文效法天文,人道效法天道”,“以人合天,顺天应人”。
读过《伏羲之道》的读者,曾经有过疑问:天文宇宙如此广大,如此繁复,难道可用伏羲六十四卦及其卦象合成的伏羲太极图简单概括?我复原的伏羲太极图,是否符合伏羲原意?
读过《庄子奥义》的读者,也曾有过疑问:庄学宇宙如此广大,如此繁复,难道可用《庄子》首篇《逍遥游》的“庄学四境”简单概括?我概括的“庄学四境”,是否符合庄子原意?
阅读《老子奥义》的读者,或许也有疑问:老学宇宙如此广大,如此繁富,难道可用《老子》首章《上德不德章》的“价值五阶”及其派生的“侯王四境”简单概括?我概括的“老学四境”,是否符合老子原意?
其实正如牛顿用极其“简单”的三大定律,概括了经典物理学,建构了“浑天说”范畴的科学体系;爱因斯坦用极其“简单”的质能转化公式,概括了非经典物理学,建构了“宣夜说”范畴的科学体系。伏羲、老子、庄子的伟大之处,正是不像普通人那样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是通过“大道至简”的极简表达,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伏羲用极其“简单”的阴阳二爻,概括了太阳的周年运动,实现了华夏天道的开天辟地;老子用极其“简单”的伏羲四时卦象,建构了道家哲学体系,实现了华夏人道的哲学突破;庄子用承于老学四境而极其“简单”的庄学四境,完善了道家哲学体系,实现了华夏真道的终极登顶。华夏真道的三大巨人伏羲、老子、庄子,都是“大道至简”的至高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