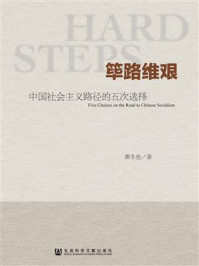我所掌握的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纠纷发生在家庭之内,其中以兄弟之间的纠纷最为典型,其次是夫妇间的纠纷,偶尔也有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纠纷。纠纷的焦点通常是但并不总是物质利益。
根据村民向“满铁”调查者的讲述,已婚而未分家的兄弟间的争吵是村庄中最为常见的纠纷,通常的解决办法则是分家。正如一位村民所说,十户中八户分家是因为争吵,剩下两户分了家而未吵是因为他们把争吵藏在心里(《惯调》,1:189;参见《惯调》,1:137,153;3:32;4:359;5:70—71)。在沙井的寺北柴,13件分家纠纷构成了所有记录在案的纠纷的1/3以上。
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村民们是生活在这一矛盾中的:一方面是上层社会的理想对他们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日常生活的实际对他们的压力。正统儒家的理想是父母和兄弟们合家而居,这一理想在《大清律例》中得到维护:“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律八十七)在这种文化理想的影响之下,几乎每一个家庭都试图合家共居。分家被看作应该努力避免的事,分家纠纷的调解人通常首先试图说服当事人和解不分(例如,《惯调》,5:424)。
而生活的实际是,几对夫妇住在一个屋檐之下,不少是处在严重的财务困境中。按照一个男性村民的意见,婚姻是兄弟间发生摩擦的最主要因素。尽管兄弟们是一块儿长大的,大多能和睦相处,但他们的妻子则是外来人,不大容易和睦相处。妻子们之间的争吵通常会变成兄弟间的纠纷。这个意见当然可能反映了一种女人是祸水的意识,但下面的意见大致是符合实际的。那就是经济上的困境,譬如年成不好,会加剧兄弟间的摩擦。如果一个家庭没有足够耕作的土地,因而一个或几个兄弟必须佣工或负贩,这样兄弟间的收入和对家庭的贡献就会不同,那么兄弟间的关系也就会特别紧张。一个懒惰、无能或挥霍的兄弟也是冲突的原因,而当家庭处在经济压力之下时这种冲突就会更甚(《惯调》,1:241,251;5;70—71,424)。
事实上,父母在世而兄弟分家是频繁发生的。这一事实在清律中也得到了反映。附于禁止分家律文后的一条例文说:“其父母许令分析者听。”(例第八十七条之一)在现实中,只要父母无异议,父母在世而兄弟分家是合法的。不仅如此,这条例文也意味着一旦父母去世,兄弟分家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1929—1930年民国的民法摒弃了反对分家的禁律,但传统上层文化的理想和社会生活实际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村庄之中。尽管大多数已婚兄弟都分家析居(其中很多人是父母在世就已分家),但村民们仍视未分家的大家庭为理想:在与日本调查者的访谈中,没有人提到新民法及它在这方面包含的新意识形态。
分家的基本原则是家庭财产在兄弟间平均分配,这在清律中说得很明白(例第八十八条之一)。
 尽管民国的民法赋予女儿和儿子同等的权利(第1138条),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村庄里财产继承的原则还是原来的一套。这一原则适用于土地和几乎所有的其他不动产(特别是住宅),以及所有的动产如农具、家具、耕畜。只有明确属于个人所有物的东西除外,如妇女的嫁妆和她个人的零花钱,夫妇的卧房用品和个人的衣物。
尽管民国的民法赋予女儿和儿子同等的权利(第1138条),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村庄里财产继承的原则还是原来的一套。这一原则适用于土地和几乎所有的其他不动产(特别是住宅),以及所有的动产如农具、家具、耕畜。只有明确属于个人所有物的东西除外,如妇女的嫁妆和她个人的零花钱,夫妇的卧房用品和个人的衣物。

分家过程是充满潜在冲突的。分家时最大宗的财产一般是土地。经过许多代人的分割,土地通常已变成许多小块。其中大一点的还可以平均分割,但小块的常要根据大小、质量、离家远近等因素来搭配考虑以便公平分配(例如《惯调》,1:290—292)。住宅的分割也有同样的困难。如果家境富裕,遇到婚娶或添丁时能盖新房,则事情比较简单。但一般情况是要分割老宅。厢房、堂屋、院子,甚至猪圈都在平均分割之列。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遵循“半斤八两”的公平原则以避免日后的冲突和争执。单件物品如车、农具、犁、水车都要遵照这样的原则来分割。
农村中产生了一套细致的惯行来处理这一过程,为的是减少可能的冲突。分家习惯上要有几个中间人在场(“中间人”又称为“说合人”“中保人”“中说人”等:《惯调》,1:290—292,319;3:93,96,102,103),这些中间人通常是宗亲、姻亲、邻居和社区领袖。
 哪怕是为了很小的一宗财物的分割,要取得兄弟间的同意也常需讨论上大半天。分一个家花上两个整天的工夫算是比较快的(《惯调》,3:96)。
哪怕是为了很小的一宗财物的分割,要取得兄弟间的同意也常需讨论上大半天。分一个家花上两个整天的工夫算是比较快的(《惯调》,3:96)。
在兄弟间对财产的公平分割达成协议之后(譬如,一辆车被等同于一小块土地,一张桌子或凳子等于一件小农具),就通过拈阄来分配财产(参见《惯调》,3:96;1:290—292)。为了防止日后可能发生的争执,一旦达成协议,就由在场作证的族人和中间人拟成一份分家单(参见《惯调》,1:290—292,319;3:93,95—96,102,123。上面载有真实的分家单)。

在我所见的有详细记录的13件分家案中,有两件最后上了法庭。其中一件涉及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弟,两兄弟中的一个已过继给他的舅舅,但在其舅破产之后他又回来要求分得他病逝父亲的一半财产(《惯调》,3:153—154)。另一件则是一个再嫁的寡妇和她两个女儿告她前夫的兄弟。这位寡妇要为她的两个女儿争取她们父亲所应得之其祖父财产的一半。这样的案件独此一件,反映了对村庄传统的挑战,因为新的民国民法赋予了她们这种权利(《惯调》,3:155)。
根据县法庭的资料,关于分家的诉讼相当少。在宝坻的35件有关田产和继承的案件中只有一件与分家有关,而且情况非常特殊。三位花甲之年的兄弟已议定分家多年,因母亲健在故仍住在一起。其母死后,他们才根据多年以前的协议正式丈量分地。由于产生了争议,弟兄们最终只好对簿公堂(宝坻,104,1867.8)。更为显著的是,1916—1934年间顺义县72件涉及田产和继承的案件中没有一件与分家有关。事实上现今中国档案学者对清代档案进行分类时并不用“分家”这一范畴。
19世纪台湾地区的淡新案件也反映了相同的情况,在142件与田产和继承有关的案件中只有两件涉及分家(表4)。其中一件涉及两兄弟间的分家,族中长老们反对他们分家,因为弟弟是个鸦片烟瘾者。于是他们决定让兄长每月付给弟弟一笔生活费。当弟弟以没有拿到生活费为由打官司要求分家时,县官拒绝了他的状子,理由是“同胞兄弟,理应敬事,何得因月费细故遽行兴讼。不准”(《淡新档案》,22524,1891.223[土-104])。在另一件案子里,一个家庭的财产被其叔父吞并了。当该户的继承人向法庭提起诉讼时,他的状子也同样被县官所拒绝。县官命令他们的族人自己去处理这个案子,并说:“须知同室操戈有讼,则终凶之戒。”(《淡新档案》,22522,1891,2.11[土-1021])
按照清代的理想,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家庭等级制度之上的,法律通过惩罚破坏这一制度的行为来维护社会秩序,但并不直接干预这一制度的正常运作。分家被看作应由宗亲组织按常规惯行去处理的事务。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案件资料,清代法庭确实尽量把分家纠纷推给宗亲组织去处理。由兄弟阋墙所引起的分家纠纷可能是村庄中最常见的纠纷,但它们并不构成县法庭诉讼案件的主要来源。
除了兄弟阋墙导致分家,夫妻争执显然是村庄调查中反映出来的最常见的一种纠纷。接受日本调查者访问的村民们把这种争执归咎于丈夫的懒惰或挥霍(《惯调》,1:239),娘家和婆家之间收入的差别,丈夫对媳妇丑陋的不满等(《惯调》,4:63)。但是仅有很少的夫妻争执会导致离婚这种最极端的结局,即使在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虽然在清代离婚对男子来说相对容易,对一个不幸的妻子却并不是一个实际的选择。清律规定,一个女人只有当她被丈夫离弃三年以上(例第一百一十六条之一),或强迫她与别人通奸(律第三百六十七条),或把她卖给别人(律第一百零二条),或将她牙齿、手指、脚趾或四肢打断(律第三百一十五条),才允许同丈夫离异。至于受公婆虐待,她必须受“非理”毒打致残方允离异(律第三百一十九条)。在19世纪宝坻的32件婚姻案中,只有一件是由一个妇女提出的离婚案,其理由是丈夫的遗弃:她已13年未得到丈夫的任何消息(宝坻,162,1839.6.1[婚-7])。
因此,事实上那些不幸的农民妻子唯一求助的是返回娘家。在宝坻的32件婚姻案件中有13件牵涉妻子的“出逃”。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其中6件是妻子返回娘家长住,而被丈夫控告为出逃,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她们的行为在县官面前显得有罪(例如宝坻,170,1814.6[婚-16];166,1837.5.22[婚-4])。同样地,在民国时期的顺义,33件婚姻案中有10件牵涉妻子“出逃”。其中五件是妻子不顾丈夫的反对跑回娘家居住。
在理论上,民国的民法赋予了妇女较大的离婚权,包括通奸和虐待也成了可以接受的离婚理由(第1052条;参见白凯,1994)。侯家营的村民提到由一位妇女提出的离婚案。这位妇女的侯姓丈夫于十多年以前离村出外谋生,但从未给家里捎过信,也无人知道他的去向。该妇女最后回自己娘家居住,并和李宝书同居怀孕。她的娘家于是向她的公公提出让她同其子离婚以便她和李结婚,但遭到她公公的拒绝。她娘家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惯调》,5:139—140)。
另外两件发生在侯家营的纠纷,一是通过当事人协议而非诉讼解决的,赵洛和的儿子结婚已五年,其妻子与一村民通奸。赵报告了警察,但警察未予以处罚。结果双方家庭协议离婚(《惯调》,3:125—126)。另一纠纷是侯小单与其妻子无法和睦相处,终日争吵。他们未曾生育,婚姻显然很不美满。在结婚八年之后,双方同意悄然离婚(同上)。
顺义县的案件记录包括了城镇和村庄的案件,这些案件反映了在离婚问题上更为广泛的变化。在33件婚姻案件中有12件涉及离婚,而其中八件是由妻子主动提出的,其理由为虐待(6件)、遗弃(1件)、重婚(1件)。但是民国的法律改革对村庄生活的影响是缓慢的。更大的变化要等到共产党革命胜利以后,那时,妇女离婚权的扩大才成为通过法律推进社会变革的前导。
在一个没有亲生子嗣的家庭,继承会成为纷争的焦点。按照清律所认可的村庄惯例,该家庭应从最近的父系亲属中过继一个嗣子(例第七十八条之一)。但是,如果一个拥有财产的户主未能在活着时确立自己的继承人,继承纠纷就很容易发生。
这里,寺北柴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在一个三兄弟的家庭,长兄没有子嗣,两个弟弟都要求他们各自的一个儿子继承大哥的财产。由于村庄社区的调解失败,这个案子只好上诉法庭(《惯调》,3:88)。
从宝坻的案件记录中可以看到同样的纠纷和其他由过继子嗣所引起的纠纷。有一个案子讲到四兄弟争相要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他们的一个没有儿子的兄弟(宝坻,182,1874.12.2[继-12])。在另一个案子里,父亲和继子的关系恶化,导致财产纠纷并最终诉诸法庭(宝坻,182,1859.9.10[继-8])。在第三个案例里,一个过继出去的儿子陷入穷困而回原家要求得到生父的财产(宝坻,183,1904.5[继-3])。
在顺义县30件与财产继承有关的案件中有12件牵涉宗祧纠纷。其中7件源于要求过继者之间的争执,3件发生于养父母和继子之间,剩下2件则发生于继子和宗亲之间。
一个重要并相关的问题是寡妇的财产权。虽然村庄资料中没有这方面的例子,但在宝坻的12件和顺义的30件财产纠纷中,前者有5件后者有3件是关于寡妇与其夫家父系亲属的财产纠纷。
养赡与宗祧和财产继承密切相关。根据一个村民的意见,如果只有一个儿子,一般不会有养赡纠纷。只有当一个家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儿子,关于谁应当负多少养赡责任才会成为纠纷。这位村民告诉我们的两个例子,是几个兄弟为了其父母的养老地的耕种责任问题发生的争执(《惯调》,4:189—190)。按照理想的惯例,儿子们应平均分摊父母养赡的责任。例如,寺北柴村长郝国梁和他的四个兄弟平均负担老母的供养,包括每年两石小米、两石麦子和每月两吊零花钱。这是一个口头协议,是当初分家时通过族长调解所达成的(《惯调》,3:93)。在另一个例子中,三兄弟每人耕种一亩他们母亲的养老地,而老母则五天一轮流在三兄弟家里吃饭(《惯调》,3:79)。
清代和民国法律都规定了赡养老年父母是儿子的责任。清律是从惩罚的角度出发:儿孙若不赡养他们的父母重责一百(律第三百三十八条),而民国的民法则强调长辈有“权利”让晚辈来赡养(第1114—1116条)。无论如何,成文法律和村庄惯行之间的契合,在村庄社区内形成了一种对子女的道德压力,使他们负担起对年老父母的责任。
村庄资料中有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个贫穷的寡妇和她已婚的儿子之间的养老纠纷。徐老太太要卖断家中一亩已经出典的地,她的儿子徐福玉作为户主不同意,母亲于是告到法院说她的儿子不赡养她(《惯调》,3:153)。在19世纪宝坻的12件和民国时期顺义的30件财产继承案中,各有3件和7件案子也涉及养老,其中四件牵涉寡妇的财产继承(宝坻和顺义各两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