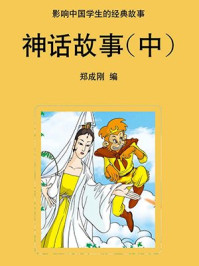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为什么祁老太爷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呢?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理上,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了的。不信,你看吧,祁老太爷会屈指算计:直皖战争有几个月?直奉战争又有好久?啊!听我的,咱们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
七七抗战那一年,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对家务,他早已不再操心。他现在的重要工作是浇浇院中的盆花,说说老年间的故事,给笼中的小黄鸟添食换水,和携着重孙子孙女极慢极慢的去逛大街和护国寺。可是,卢沟桥的炮声一响,他老人家便没法不稍微操点心了,谁教他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爷呢。
儿子已经是过了五十岁的人,而儿媳的身体又老那么病病歪歪的,所以祁老太爷把长孙媳妇叫过来。老人家最喜欢长孙媳妇,因为第一,她已给祁家生了儿女,教他老人家有了重孙子孙女;第二,她既会持家,又懂得规矩,一点也不像二孙媳妇那样把头发烫得烂鸡窝似的,看着心里就闹得慌;第三,儿子不常住在家里,媳妇又多病,所以事实上是长孙与长孙媳妇当家,而长孙终日在外教书,晚上还要预备功课与改卷子,那么一家十口的衣食茶水,与亲友邻居的庆吊交际,便差不多都由长孙媳妇一手操持了;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老人天公地道的得偏疼点她。还有,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习目染的和旗籍人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儿媳妇见了公公,当然要垂手侍立。可是,儿媳妇既是五十多岁的人,身上又经常的闹着点病;老人若不教她垂手侍立吧,便破坏了家规;教她立规矩吧,又于心不忍,所以不如干脆和长孙媳妇商议商议家中的大事。
祁老人的背虽然有点弯,可是全家还属他的身量最高。在壮年的时候,他到处都被叫作“祁大个子”。高身量,长脸,他本应当很有威严,可是他的眼睛太小,一笑便变成一条缝子,于是,人们只看见他的高大的身躯,而觉不出什么特别可敬畏的地方来。到了老年,他倒变得好看了一些:黄暗的脸,雪白的须眉,眼角腮旁全皱出永远含笑的纹溜;小眼深深的藏在笑纹与白眉中,看去总是笑眯眯的显出和善;在他真发笑的时候,他的小眼放出一点点光,倒好像是有无限的智慧而不肯一下子全放出来似的。
把长孙媳妇叫来,老人用小胡梳轻轻的梳着白须,半天没有出声。老人在幼年只读过三本小书与六言杂字;少年与壮年吃尽苦处,独力置买了房子,成了家。他的儿子也只在私塾读过三年书,就去学徒;直到了孙辈,才受了风气的推移,而去入大学读书。现在,他是老太爷,可是他总觉得学问既不及儿子——儿子到如今还能背诵上下《论语》,而且写一笔被算命先生推奖的好字——更不及孙子,而很怕他们看不起他。因此,他对晚辈说话的时候总是先愣一会儿,表示自己很会思想。对长孙媳妇,他本来无须这样,因为她识字并不多,而且一天到晚嘴中不是叫孩子,便是谈论油盐酱醋。不过,日久天长,他已养成了这个习惯,也就只好教孙媳妇多站一会儿了。
长孙媳妇没入过学校,所以没有学名。出嫁以后,才由她的丈夫像赠送博士学位似的送给她一个名字——韵梅。韵梅两个字仿佛不甚走运,始终没能在祁家通行得开。公婆和老太爷自然没有喊她名字的习惯与必要,别人呢又觉得她只是个主妇,和“韵”与“梅”似乎都没多少关系。况且,老太爷以为“韵梅”和“运煤”既然同音,也就应该同一个意思,“好吗,她一天忙到晚,你们还忍心教她去运煤吗?”这样一来,连她的丈夫也不好意思叫她了,于是她除了“大嫂”“妈妈”等应得的称呼外,便成了“小顺儿的妈”;小顺儿是她的小男孩。
小顺儿的妈长得不难看,中等身材,圆脸,两只又大又水灵的眼睛。她走路,说话,吃饭,做事,都是快的,可是快得并不发慌。她梳头洗脸擦粉也全是快的,所以有时候碰巧了把粉擦得很匀,她就好看一些;有时候没有擦匀,她就不大顺眼。当她没有把粉擦好而被人家嘲笑的时候,她仍旧一点也不发急,而随着人家笑自己。她是天生的好脾气。
祁老人把白须梳够,又用手掌轻轻擦了两把,才对小顺儿的妈说:“咱们的粮食还有多少啊?”
小顺儿的妈的又大又水灵的眼很快的转动了两下,已经猜到老太爷的心意。很脆很快的,她回答:“还够吃三个月的呢!”
其实,家中的粮食并没有那么多。她不愿因说了实话,而惹起老人的啰嗦。对老人和儿童,她很会运用善意的欺骗。
“咸菜呢?”老人提出第二个重要事项来。
她回答的更快当:“也够吃的!干疙疸,老咸萝卜,全还有呢!”她知道,即使老人真的要亲自点验,她也能马上去买些来。
“好!”老人满意了。有了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就是天塌下来,祁家也会抵抗的。可是老人并不想就这么结束了关切,他必须给长孙媳妇说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日本鬼子又闹事哪!哼!闹去吧!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连皇上都跑了,也没把我的脑袋掰了去呀!八国都不行,单是几个日本小鬼还能有什么蹦儿?咱们这是宝地,多大的乱子也过不去三个月!咱们可也别太粗心大胆,起码得有窝头和咸菜吃!”
老人说一句,小顺儿的妈点一次头,或说一声“是”。老人的话,她已经听过起码有五十次,但是还当作新的听。老人一见有人欣赏自己的话,不由的提高了一点嗓音,以便增高感动的力量:“你公公,别看他五十多了,论操持家务还差得多呢!你婆婆,简直是个病包儿,你跟她商量点事儿,她光会哼哼!这一家,我告诉你,就仗着你跟我!咱们俩要是不操心,一家子连裤子都穿不上!你信不信?”
小顺儿的妈不好意思说“信”,也不好意思说“不信”,只好低着眼皮笑了一下。
“瑞宣还没回来哪?”老人问。瑞宣是他的长孙。
“他今天有四五堂功课呢。”她回答。
“哼!开了炮,还不快快的回来!瑞丰和他的那个疯娘们呢?”老人问的是二孙和二孙媳妇——那个把头发烫成鸡窝似的妇人。
“他们俩——”她不知道怎样回答好。
“年轻轻的公母俩,老是蜜里调油,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真也不怕人家笑话!”
小顺儿的妈笑了一下:“这早晚的年轻夫妻都是那个样儿!”
“我就看不下去!”老人斩钉截铁的说。“都是你婆婆宠得她!我没看见过,一个年轻轻的妇道一天老长在北海,东安市场和——什么电影院来着?”
“我也说不上来!”她真说不上来,因为她几乎永远没有看电影去的机会。
“小三儿呢?”小三儿是瑞全,因为还没有结婚,所以老人还叫他小三儿;事实上,他已快在大学毕业了。
“老三带着妞子出去了。”妞子是小顺儿的妹妹。
“他怎么不上学呢?”
“老三刚才跟我讲了好大半天,说咱们要再不打日本,连北平都要保不住!”小顺儿的妈说得很快,可是也很清楚。“说的时候,他把脸都气红了,又是搓拳,又是磨掌的!我就直劝他,反正咱们姓祁的人没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侮到咱们头上来!我是好意这么跟他说,好教他消消气;喝,哪知道他跟我瞪了眼,好像我和日本人串通一气似的!我不敢再言语了,他气哼哼的扯起妞子就出去了!您瞧,我招了谁啦?”
老人愣了一小会儿,然后感慨着说:“我很不放心小三儿,怕他早晚要惹出祸来!”
正说到这里,院里小顺儿撒娇的喊着:“爷爷!爷爷!你回来啦?给我买桃子来没有?怎么,没有?连一个也没有?爷爷你真没出息!”
小顺儿的妈在屋中答了言:“顺儿!不准和爷爷讪脸!再胡说,我就打你去!”
小顺儿不再出声,爷爷走了进来。小顺儿的妈赶紧去倒茶。爷爷(祁天佑)是位五十多岁的黑胡子小老头儿。中等身材,相当的富泰,圆脸,重眉毛,大眼睛,头发和胡子都很重很黑,很配作个体面的铺店的掌柜的——事实上,他现在确是一家三间门面的布铺掌柜。他的脚步很重,每走一步,他的脸上的肉就颤动一下。作惯了生意,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团和气,鼻子上几乎老拧起一旋笑纹。今天,他的神气可有些不对。他还要勉强的笑,可是眼睛里并没有笑时那点光,鼻子上的一旋笑纹也好像不能拧紧;笑的时候,他几乎不敢大大方方的抬起头来。
“怎样?老大!”祁老太爷用手指轻轻的抓着白胡子,就手儿看了看儿子的黑胡子,心中不知怎的有点不安似的。
黑胡子小老头很不自然的坐下,好像白胡子老头给了他一些什么精神上的压迫。看了父亲一眼,他低下头去,低声的说:“时局不大好呢!”
“打得起来吗?”小顺儿的妈以长媳的资格大胆的问。
“人心很不安呢!”
祁老人慢慢的立起来:“小顺儿的妈,把顶大门的破缸预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