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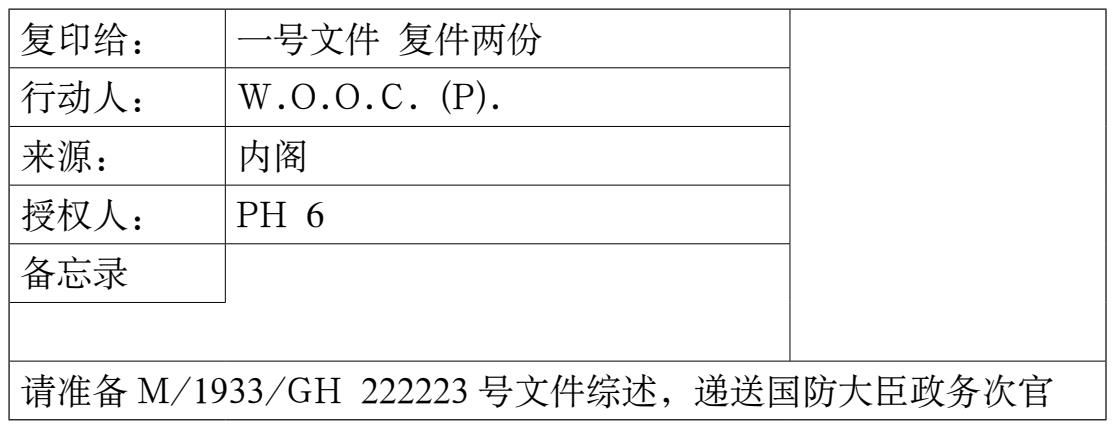
下午两点半,内线电话
 传来消息,说国防大臣不太理解结语里的某些部分。我可能要和国防大臣见一面。
传来消息,说国防大臣不太理解结语里的某些部分。我可能要和国防大臣见一面。
可能吧。
国防大臣的公寓就在特拉法尔加广场边上,从那里能俯瞰整个广场,装潢风格像奥斯卡·王尔德的私宅,繁复又浮华。国防大臣坐在一把朴素规整的谢拉顿式木椅上,而我坐的只是一把精巧舒适的赫伯怀特式椅。两把椅子中间摆着盆一叶兰,我们便透过宽大的叶片窥视彼此。
“老兄,从你自己的角度讲讲整个故事就行。抽烟吗?”
我还在想不然我能从谁的角度,他就把他那薄薄的金烟盒连同叶片递了过来。不过,我先掏出了一包皱皱巴巴的高卢烟,婉拒了他。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说,“档案里的第一份文件……”
国防大臣冲我摆了摆手。“别管档案的事,兄弟。你就告诉我你看到的东西。先说说你跟这家伙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吧……”他低头看了看手上摩洛哥山羊皮封面的小笔记本,“这家伙叫……杰伊。他的事,你知道多少?”
“杰伊。他的代号换成四号盒子了。”我说。
“为什么?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国防大臣一边问,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些什么。
“整个故事就很让人摸不着头脑,”我对他说,“我干的,就是个没头没脑的营生。”
国防大臣说“确实”,说了好几次。我掸了掸撞手上四分之一英寸长的烟灰,烟灰落在脚下泛蓝的卡尚地毯上。
“我第一次见杰伊时,是个周二上午。我当时在莱德尔咖啡馆,时间差不多是十二点五十五分。”
“莱德尔咖啡馆?”国防大臣问,“在哪儿?”
“要是一边叙述一边回答问题就有点困难,”我说,“长官,如果不是特别急的问题,我更希望您能记下来,等我讲完一起问。”
“兄弟,你讲,我不问了。我保证不插嘴。”
就这样,在我讲述的过程中,他果然一次都没有再插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