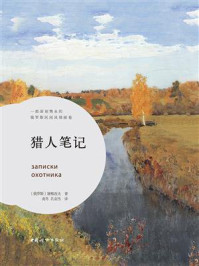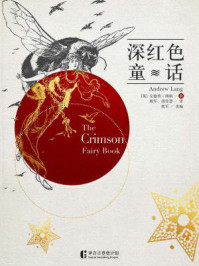我在这儿要讲述的事情,别人本可以由此著书了;然而,光是经历它,我就已经竭尽了所有心力与品德。因此,我将简单写下我的回忆,如果有些地方显得支离破碎、不成章法,我也无意用任何虚构的情节对其加以修补完善;画蛇添足或许只会阻碍我从讲述中得到最后一点儿乐趣。
父亲去世时,我还不满十二岁。在他曾经从医的城市勒阿弗尔,母亲失去了牵念,便决定移居巴黎,她认为我在那儿能更好地完成学业。她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租了一间小公寓,阿什布通小姐来与我们同住。佛洛拉·阿什布通小姐已无亲故,她曾是我母亲的小学老师,后来成了她的女伴,不久后成为她的挚友。我与这两位神态温和而忧愁,且久着丧服的女士一起生活。在父亲去世很久之后的某天,母亲将清晨软帽上的黑丝带换成了一根淡紫色丝带。我惊叫道:
“哦,妈妈!这个颜色真不适合你!”
隔天,她又换上了黑丝带。
我身体羸弱。母亲和阿什布通小姐为此十分操劳,唯恐我累着。这份关心没有将我变成一个懒汉,那是因为我对学习的确很感兴趣。一到风和日丽的季节,她们俩便认为是时候让我离开巴黎了,因为这座城市让我的脸色黯淡无光。大约六月中旬,我们动身前往勒阿弗尔附近的冯格兹马尔,舅舅布克兰每年夏天都在那里接待我们。
布克兰家白色的两层房子与两个世纪前的许多乡村住宅相似。它坐落在一个面积不大,也算不上漂亮的花园里,与其他大多数诺曼底花园没什么区别。房子朝东,正对着花园那面开了二十几扇大窗户,房子背面也有同样多的窗户,两侧无窗。大窗户由小块玻璃组成,有几块新换的玻璃在周围灰绿色的旧玻璃中显得过于明亮。一些玻璃有瑕疵,我们的亲戚把这些瑕疵叫作“气泡”;透过它们向外看,树木都变形了;邮递员从它们前面经过,也会突然长出驼背来。
花园是长方形的,四周有围墙。屋前有一块被绿荫覆盖的、面积还算大的草坪,一条沙石小道环绕着它。这一侧的围墙稍矮,人们可以看见花园周围的农场院子。一条山毛榉大道以当地的划界方式隔开了花园与农场院子。
屋后西侧的花园更为舒展。朝南的果树前,一条繁花似锦的小径在郁郁葱葱的葡萄牙月桂和几棵树木的荫蔽下,得以免受海风的蹂躏。另一条小径沿北墙延伸,直至消失在树丛中。我的表姐妹们叫它“黑道”,谁都不愿在暮色四合之后去那儿冒险。这两条小径都通向菜园,菜园是花园在低处的延伸,向下走几级台阶就能到。菜园尽头的另一侧围墙上,开了一扇小小的暗门,门外是一片矮树林,山毛榉大道从左、右两侧收束于此处。自西侧台阶远眺,目光越过树丛就能看到高原,可以欣赏遍野的丰收盛况。在地平线上,能看见一个相距不远的小村庄的教堂,夜色悄寂时,炊烟袅袅,几点人家。
在每个清朗的夏夜,我们晚饭后便会到“下花园”去,从暗门出去,来到大道上的那张长椅旁,从那里差不多可以俯瞰整片区域;在一座废弃泥灰岩矿场的茅屋顶旁,我的舅舅、母亲和阿什布通小姐坐了下来;在我们眼前,小山谷雾气缭绕,远处树林上方的天空一片金辉。随后,我们在早已暗下来的花园深处闲逛。回到家,舅母坐在客厅里,她几乎从不与我们一同出去……对于孩子们而言,夏夜活动就此结束,但我们常常还会在各自的房间里看书,更晚些时候,能听到大人们上楼的声音。
一日之内所有不在花园里度过的时刻,我们几乎都泡在“自习室”里。那是舅舅的书房,里面放了几张小学生的课桌。我和表弟罗贝尔并排坐着,后面是朱丽叶特和阿莉莎。阿莉莎长我两岁,朱丽叶特小我一岁,罗贝尔在我们四人当中最年幼。
我在这里要写的并不是最初的回忆,而是与此事相关的回忆。可以说,此事确实是从父亲去世那年开始的。可能我因丧事——如果不是因我自身的悲伤,至少也是因为目睹了母亲的悲痛而变得更为敏感,这使我更容易生发出一些新的感情:我过早地成熟了。这一年,我们重回冯格兹马尔,我觉得朱丽叶特和罗贝尔显得更年幼了,但重见阿莉莎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们都已不再是孩子了。
是的,的确是父亲逝世的那一年。我们到达冯格兹马尔后,母亲与阿什布通小姐的谈话更让我确信没有记错。当时,我猛地走进房间,母亲和她的朋友正在谈论我的舅母。母亲对于舅母并未服丧或者她过早地脱掉丧服而深感不满(老实说,布克兰舅母穿黑色的衣服,就像我母亲穿亮色裙装一样难以想象)。我记得,露西勒·布克兰在我们到达的那天穿着一条薄纱裙。向来随和的阿什布通小姐竭力安抚我母亲,她小心翼翼地为舅母开脱道:
“说到底,白色也算服丧吧。”
母亲大喊:“那她肩上的红披巾算什么,你管这个也叫‘服丧’吗?佛洛拉,你太让我生气了!”
我只在假期那几个月见到舅母。大概是因为夏季的酷热,她总穿着轻薄的低领上衣;比起她裸露的肩膀上的鲜红披巾,这种袒胸露肩更令我母亲难堪。
露西勒·布克兰美艳动人。我保存了一张她的小画像,这幅画像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她的美貌。画中,她以惯常的姿势倾身坐着,看起来如此年轻,仿佛是她女儿们的姐姐。她垂首于左手上,小指略带刻意地弯向嘴唇,浓密的鬈发由一个粗孔发网拢着,半搭在颈上;在衬衣的开领处,松松地系着一条黑丝绒质地的项链,上面挂着一枚有着意大利嵌画的椭圆形颈饰。黑丝绒腰带打了一个飘动的大结,宽边软草帽用帽带挂在椅背上,这一切都为她增添了几分稚气。她的右手自然垂下,拿着一本合上的书。
露西勒·布克兰是克里奥人,很早就失去了父母,或者说她压根儿就没见过他们。母亲后来告诉我,伏提耶牧师夫妇收养了这个弃女或孤女,他们当时还没有自己的孩子。不久后他们就离开了马提尼克岛,将小露西勒带到了勒阿弗尔。布克兰一家也住在那儿,并且与伏提耶家的人经常来往。我舅舅当时在国外的一家银行供职,三年后他重回家人身边,这时才见到小露西勒。舅舅爱上了她,并且立刻向她求婚。他父母和我母亲为此愁眉不展。露西勒那时十六岁。在这期间,伏提耶夫人生下了两个孩子,她开始担心这个性格日益古怪且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会带坏他们,再加上这对夫妇收入微薄……母亲告诉我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伏提耶夫妇会欣然同意舅舅的求婚。此外,我猜想,可能年轻的露西勒逐渐让这对夫妇非常为难。我足够了解勒阿弗尔的社交界,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这个极具魅力的女孩受到了怎样的欢迎。后来,我认识了温文尔雅的伏提耶牧师,他审慎又天真,对抗阴谋诡计时无计可施,面对邪恶时更是完全无能为力——这个仁慈的人当时一定走投无路了。至于伏提耶夫人,我没什么可说的,第四个孩子降生时,她因难产而去世。这个孩子差不多与我同龄,后来成了我的朋友……
露西勒·布克兰很少参与我们的生活。她只在午饭后从房间走下楼,立马又躺到沙发或吊床上,直至入夜,她才有气无力地站起来。有时,她在干燥的前额搭上一方手帕,像是为了擦拭轻微的汗;这方手帕做工精细,似乎散发着一阵果香而非花香,令我赞叹不已。有时,她从腰间拿出一面银质滑盖的小镜子,与各式小物件一同挂在她的表链上;她照着镜子,用一根手指轻触嘴唇,蘸一点儿唾沫润湿眼角。她经常拿着一本书,但书几乎总是合上的,书页中夹着一枚玳瑁书签。当有人走近,她也并不会将目光从白日梦中移出看向对方。从她或散漫或倦怠的手中,从沙发的扶手上,从裙子的褶皱中,经常掉落一方手帕,或是一本书,几朵花,抑或是一枚书签。给大家讲一段儿时的回忆,有一天,我将被她遗落的书捡起来,读了数行诗句,便脸红了。
晚饭后,露西勒·布克兰从不靠近家人围坐的桌子,而是坐在钢琴前,怡然自得地弹奏着肖邦的慢板《玛祖卡舞曲》;有时,她会停在某个音符上,断了拍子……
在舅母身边时,我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局促不安,爱惧交织的情感搅得我心绪不宁。可能有某种无法言明的本能使我对她心生反感。此外,我觉得她瞧不起佛洛拉·阿什布通和我母亲,阿什布通小姐害怕她,而我母亲不喜欢她。
露西勒·布克兰,我多想放下对您的怨恨,多想,哪怕只有片刻能忘却您的诸多恶行……至少在谈及您时,我将尽量心平气和。
这年夏天的某日——或是之后的那个夏天,因为场景年年相同,层叠交错的记忆有时难免混淆——我进客厅找一本书,见她在那儿,便赶紧退了出来。这个平日对我视若无睹的女人竟叫住了我:
“你为什么那么快走开?杰罗姆!我让你害怕了?”
我靠近她,心脏怦怦直跳,克制地挤出一丝笑容,并向她伸出手。她一只手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轻抚我的脸颊。
“你母亲给你穿得多难看呀,我的小可怜……”
那时我穿着一件大领水手服,舅母开始摆弄起它来。
“水手服的衣领可要敞开得多呢!”她说着便扯掉了衬衫上的一颗扣子,“瞧!你这样是不是好看多了!”她拿出小镜子,将我的脸拉过去贴住她的脸,裸露的手臂绕上我的脖子,手落进我半开的衬衫里,一边嬉笑着问我是否怕痒,一边将手摸向深处……我猛地惊跳起来,连衬衫都撕破了,面如火烧。她喊道:
“呸!大傻瓜!”
我落荒而逃,跑到花园深处。我把手帕放进菜园的小池子中浸湿,敷在前额上,擦洗脸颊、脖颈,以及所有被那个女人碰过的地方。
某些日子里,露西勒·布克兰会“发病”。这病将她骤然攫住,闹得全家不得安宁。阿什布通小姐急忙将孩子们领走,给他们找些别的事儿做;但从卧房或客厅传来的那骇人的叫喊声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孩子们听见了。舅舅惊慌失措,只听他在走廊里小跑着寻找毛巾、古龙水、乙醚。晚餐时,舅母仍旧没有露面,舅舅的面色焦灼而苍老。
等病差不多过去了,露西勒·布克兰把孩子们叫到她身边,至少罗贝尔和朱丽叶特会在场,阿莉莎从来不去。在那些阴郁的日子里,阿莉莎闭门不出,她父亲有时会去找她,父女俩常常闲聊。
舅母的频繁发病让仆人们大为震惊。一天晚上,她的病发作得特别厉害。我待在母亲身边,被禁止离开房间,所以对客厅里发生的一切知之甚少,只听见厨娘在走廊里边跑边喊:
“先生可得快点儿下来,可怜的太太就要死啦!”
原来舅舅去阿莉莎房间了,我母亲出去跟他会合。一刻钟后,他们俩从我待着的房间前经过,并未留意敞开的窗户。我的耳边传来母亲的声音:
“我的朋友,恕我直言:这一切都是装腔作势。”她一字一顿地重复了好几遍——“装、腔、作、势。”
这件事发生在我们服丧两年后的那个假期末。此后,我很长时间没再见到舅母。有件悲伤的事将我们全家搅得天翻地覆,在此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将我对露西勒·布克兰复杂未定的情感化为纯粹的仇恨。但在讲述那件悲伤的事情之前,我必须先与你们谈谈我的表姐。
阿莉莎·布克兰多美呀!我那时竟然还没有意识到。吸引我留在她身旁的是另一种与世俗之美无关的魅力。毫无疑问,她长得非常像她的母亲,但她的神情却如此不同,以致很久之后我才发觉她们相貌相似。我无法描绘她的容貌,她脸庞的轮廓甚至眼睛的颜色于我的记忆而言都转瞬即逝,唯有她近乎悲伤的笑容,以及她眉毛的线条,令我牵肠挂肚。她的眉毛在眼睛上方高高扬起,形成两个大圆弧。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见过这般眉眼……不,我在但丁时代佛罗伦萨的小雕像上见过;我情不自禁地想象,童年时的贝特丽丝
 也该有这般弯弯的眉毛。它们给予目光、给予整个存在,一种焦虑又自信的、探询的神色——不错,炽烈的探询。在她身上,一切都只是疑问和等待……我将告诉你们这种探询是如何占据我,耗尽我的生命的。
也该有这般弯弯的眉毛。它们给予目光、给予整个存在,一种焦虑又自信的、探询的神色——不错,炽烈的探询。在她身上,一切都只是疑问和等待……我将告诉你们这种探询是如何占据我,耗尽我的生命的。
朱丽叶特那时候看起来似乎更漂亮,欢乐与健康使她容光焕发。但相较于姐姐的优雅,她的美貌显得肤浅,让人一眼就能看透。至于我的表弟罗贝尔,他没什么特点,仅仅是一个与我年龄相近的男孩。我与朱丽叶特和罗贝尔一起玩耍,与阿莉莎谈心,她从不参与我们的游戏。不论我追忆多么久远的往事,记忆中的阿莉莎总是举止庄重,温和地微笑着,若有所思。我们聊些什么呢?两个孩子有什么可说的?我会尽快告诉你们,但为了之后不再谈及舅母,我先把与她有关的故事讲完。
父亲去世两年后,母亲和我去勒阿弗尔过复活节。因为布克兰家在城里的住处有些拥挤,我们没住在那里,而是去了母亲的一位姐姐家,她的住宅更宽敞。姨妈普兰迪耶已孀居许久,我很少有机会见到她,也几乎不认识她的孩子们。他们都比我年长,而且与我性格迥异。勒阿弗尔人称作“普兰迪耶之宅”的地方不在城内,而是坐落在可以俯瞰城市的半山腰上,人们叫它“山坡”。布克兰一家住得更靠近商业区,两个宅子间有一条斜坡近道,我每天都要上下坡跑很多次。
那天,我在舅舅家吃午饭,饭后不久他就出门了。我陪他走到办公室,接着又上坡走到普兰迪耶家找我母亲,结果得知她和姨妈出门了,晚饭时才回来。我马上返回城里,毕竟我很少有机会能在那儿自由闲逛。我来到港口,海雾使它看起来阴沉沉的。我在码头上游荡了一两个小时,然后我突发奇想:再去拜访刚刚分别的阿莉莎,准会吓她一跳……我小跑着穿过城市,按响布克兰家的门铃,我早已迫不及待地要奔向楼梯了。开门的女仆拦住了我:
“请别上楼,杰罗姆先生!请别上楼,太太犯病了。”
但我充耳不闻:“我不是来看舅母的……”阿莉莎的卧室在四楼。二楼是客厅和饭厅,三楼是舅母的房间,里面传出说话声。房门开着,我必须从门前经过;一束光线从房间里透出来,将楼梯平台一分为二。由于害怕被发现,我犹豫片刻后便躲了起来,然而眼前的一幕令我目瞪口呆:房间里,窗帘都已拉严实,两架枝形大烛台上烛火欢跃,舅母躺在房间中央的长椅上,罗贝尔和朱丽叶特在她脚边;她身后是一个穿着中尉制服的陌生年轻男人。今日回想,让两个孩子在场简直伤天害理,但我当时天真无知,他俩在场竟让我感到安心。
他们笑着看着那个陌生人,他尖着嗓子重复道:
“布克兰!布克兰!……如果我有一头羊,一定叫它布克兰。”
舅母放声大笑。我看见她递给那个年轻男人一支烟,他将其点燃后,舅母吞云吐雾了几口。烟掉在地上。男人一个箭步去捡,却假装被一条披巾绊住,在舅母面前跪倒……多亏了这场可笑的情景戏,我得以趁机溜走而未被发现。
我在阿莉莎的房门前等了一会儿。也许是从楼下传来的笑闹声盖过了我的敲门声,因为我没有听见回应。我轻轻一推,门就悄无声息地开了。房间里很暗,我没有立刻看到阿莉莎:她跪在床边,背对窗户。窗外白日将尽。当我靠近她时,她转过头,却没有起身,低语道:
“啊,杰罗姆,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我俯身吻她。她满面泪水……
那个瞬间决定了我的一生,如今回想起来,我依然无法放下忧虑。或许我对阿莉莎忧虑的缘由不甚了解,但我强烈地感受到,那小小的、颤动着的灵魂,那纤弱的、因抽噎而发抖的身体,经不住如此剧烈的悲痛。
我站在她身边,她依然跪着。我不知该如何表达内心这份崭新的激情,我将她的头抵在心口,我的嘴唇贴上她的前额,灵魂从唇间汩汩而出。醉于爱,醉于怜惜,醉于一种暧昧不明的复杂情感——狂喜、牺牲、美德。我用尽全力呼唤上帝,我将献出自己,此生不为别的,只求能保护这个孩子,使她远离忧惧与邪恶,免受生活的摧残。我跪下虔心祈祷,让她倚靠在我怀中。隐约间,我听见她说:
“杰罗姆!他们没看见你吧?啊,快走!别让他们看见你。”
接着,她的声音更轻了:
“杰罗姆,别告诉任何人……可怜的爸爸并不知情……”
所以我对母亲什么都没说,但普兰迪耶姨妈与母亲无休止地窃窃私语,她们表情神秘、慌忙又痛苦。每当我在她们密谈时靠近,她们便将我支开——“孩子,你去远一点儿的地方玩儿吧!”一切都表明,她们对于布克兰家的秘密并非毫不知情。
我们刚回到巴黎,一封快信把母亲叫回了勒阿弗尔——舅母消失了。
母亲将我托付给阿什布通小姐,我问道:“和谁一起?”
这位亲爱的老友说:“我的孩子,你之后问你母亲吧,我什么也回答不了。”此事令她无措。
两天后,我们启程去与母亲会合。那是一个周六,第二天我将在教堂里见到表亲们,这是我唯一惦记的事;因为在我那孩童的脑袋里,这次圣洁的重见意义非凡。总之,我毫不在乎舅母;为了体面,我也没有向母亲打听。
那天早晨,小教堂里人不多。伏提耶牧师无疑是有意选了基督的这句话作为冥想祷文: “请务必竭尽全力进入窄门。”
阿莉莎隔着几个座位坐在我前面。我看着她的侧脸,忘我地定睛凝视,仿佛我狂热倾听的圣言是自她而来。舅舅坐在母亲身旁哭泣。
牧师先诵读了整节经文: “请务必竭尽全力进入窄门,因为引到堕落,那门是宽的,路是阔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接着,他进一步讲解各个部分,首先谈到阔路……我精神恍惚,如在梦中,仿佛又看见舅母的房间,她笑容满面地躺着,英俊的军官也跟着笑……此时,欢笑的念头都变得伤人又带有侮辱性,仿佛成了罪孽那卑鄙无耻的夸张形态!……
“进去的人也多” ,伏提耶牧师重提这句并加以描绘时,我看见盛装打扮的一群人,笑闹着前进。我觉得自己不能,也不愿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与他们同行的每一步都将使我远离阿莉莎。伏提耶牧师又回到这段经文的开头,我看见那扇需要竭尽全力进入的窄门。我沉入梦中,它像一台轧机,我费劲地挤进去,感受到超乎寻常的剧痛中夹杂着将至的天福之乐。这扇门又变成了阿莉莎的房门。为了进去,我放低自己,清空身上残存的私心……伏提耶牧师继续说:“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 ”——在所有苦修与忧伤之上,我遐想着,预感到另一种欢乐,它纯粹、神秘又高洁,令我的灵魂久久渴求。这欢乐好似一首尖锐又温柔的小提琴曲,好似那熊熊烈火,令我和阿莉莎的心脏燃烧、衰竭。我们身穿《启示录》中的白衣,牵着手朝同一个目标前进……倘若这些孩童的幻想令人发笑,那又如何呢?我原封不动地加以叙述。倘若其中有混乱的地方,也仅仅是因为词语的局限和意象的不完美,使我没能精准地表达情感罢了。
“ 找着的人也少 ”,伏提耶牧师最后说。他解释了如何找到窄门……“ 人也少 。”——我将是这些少数人中的一个……
布道临近尾声,我的精神已经无比紧张,以至于布道一结束,我就立刻离开了,没有去找她——出于骄傲,我想让我的决心(因为我已下定决心)经受试炼,而且我以为,只有立即远离她,才能更配得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