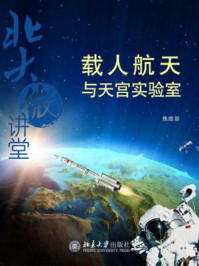根据界面治理理论,治理变革的动因要么来自外部环境,要么来自内部需要,其变革表现为界面层面变革、功能层面变革和内部结构变革。对于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而言,他们会将治理变革归因于外部环境,强调治理变革作为一种适应性策略,遵循规则逻辑,演化治理理论构成了这一视角下最主要的研究结论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他们会将治理变革归因于内部结构,强调治理变革是一种主观选择的结果,遵循理性选择逻辑,治理机制选择理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他们会将治理变革归因于内部结构,强调治理变革是一种主观选择的结果,遵循理性选择逻辑,治理机制选择理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从界面治理理论的视角看,治理变革意味着打破原有治理界面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是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平衡和变革是一体两面,这与间断—均衡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
。从界面治理理论的视角看,治理变革意味着打破原有治理界面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是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平衡和变革是一体两面,这与间断—均衡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
 。
。
对于治理变革,除了考虑动因,还可以考虑变革的机制。借鉴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变迁区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分类方法
 ,我们可以将治理变革区分为强制性治理变革和诱致性治理变革,前者是由外部力量强制推动,后者是由自身推动。同样,这种区分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很多变革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以变革动因和变革机制两个维度为基础,界面治理理论将治理变革区分为四种模式,即外部环境驱动的强制性变革、外部环境驱动的诱致性变革、内部结构驱动的强制性变革和内部结构驱动的诱致性变革(见表1-1)。
,我们可以将治理变革区分为强制性治理变革和诱致性治理变革,前者是由外部力量强制推动,后者是由自身推动。同样,这种区分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很多变革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以变革动因和变革机制两个维度为基础,界面治理理论将治理变革区分为四种模式,即外部环境驱动的强制性变革、外部环境驱动的诱致性变革、内部结构驱动的强制性变革和内部结构驱动的诱致性变革(见表1-1)。
表1-1 治理变革的类型

外部环境驱动的强制性变革意味着治理变革是由外部环境强制推动,自上而下是其典型特征,治理界面没有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治理界面可以作为更大治理界面的一个内部结构,更高层次的治理界面主导了作为内部结构的治理界面的变革。以欧盟为例,欧盟是成员国的外部环境,当成员国将权力让渡给欧盟时,成员国的变革可能是由作为外部环境的欧盟推动的
 。外部环境驱动的诱致性变革则强调治理界面在变革中拥有主动性,自下而上是其典型特征,治理主体因为感知到来自环境的信息而主动采取变革策略。在政策扩散研究中,很多主体实施新政策主要是因为其他主体实施了类似政策,他们觉得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以获得合法性。内部结构驱动的强制性变革意味着治理变革是因为内部结构不能满足治理功能需求,治理主体通过强制方式来推动变革。各国政府推行机构改革多遵循这一变革方式,中国2018年推行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内部结构驱动的诱致性变革意味着治理变革是自下而上的主动性变革,治理行动者意识到传统方式不能够解决问题,于是通过变革来解决问题。中国的地方实验,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内部结构驱动的诱致性变革
。外部环境驱动的诱致性变革则强调治理界面在变革中拥有主动性,自下而上是其典型特征,治理主体因为感知到来自环境的信息而主动采取变革策略。在政策扩散研究中,很多主体实施新政策主要是因为其他主体实施了类似政策,他们觉得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以获得合法性。内部结构驱动的强制性变革意味着治理变革是因为内部结构不能满足治理功能需求,治理主体通过强制方式来推动变革。各国政府推行机构改革多遵循这一变革方式,中国2018年推行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内部结构驱动的诱致性变革意味着治理变革是自下而上的主动性变革,治理行动者意识到传统方式不能够解决问题,于是通过变革来解决问题。中国的地方实验,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内部结构驱动的诱致性变革
 。
。
根据上面的治理变革分类框架,中国城市治理变革存在多样性路径,它是外部环境和内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城市治理变革面临着不同的环境和需求,从而产生了差异化演化路径。如果不考虑变革的来源,只考虑变革的机制,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强制性变革和诱致性变革这两种典型的变革路径。当然,现实中变革都是混合型变革,无论是变革动因,还是变革机制,都具有混合特点,是多种因素结合的产物。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以首都治理变革和长三角城市治理变革为例,讨论中国城市治理变革,它们分别是强制性变革和诱致性变革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这两个地方的城市治理变革都发生了转化,成为混合型变革模式。首都治理变革始于强制性变革,随后逐渐向一种自觉性行动转化。长三角城市治理变革始于诱致性变革,随后上升为国家战略从而转化为一种强制性行动。
新时代的首都治理变革主要是由外部环境驱动,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强制性变革范畴。首都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会受到国家治理逻辑的影响,国家对首都治理的战略定位会引发首都治理的界面重构和内部结构变革。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有三次讲话对首都治理的战略定位、主要措施和核心思路提出了具体要求(见表1-2)。
表1-2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讲话精神

在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系列讲话的指引之下,京津冀协同构成了首都治理最大的环境,国家战略引领首都治理变革,首都治理需要适应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的双重变革需要。内部功能重组是要求首都治理聚焦核心功能,围绕“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展开,疏解非首都功能是战略定位实施的主要途径,前者是从肯定性方面发挥作用,后者是从否定性方面发挥作用。于是,我们可以厘清首都治理变革的基本逻辑: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了首都治理功能定位变化,首都治理功能定位变化最终需要通过首都治理界面和内部结构重组来实现。当然,最初的强制性变革也可能引发诱致性变革,使得变革成为一种自觉。首都治理主体越是感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越可能推动首都治理变革;首都治理主体越是认同变革要求,越可能推动首都治理变革。
长三角城市治理变革,更多的是一种诱致性变革,它是城市之间相互学习、借鉴、模仿和相关实践经验扩散的结果。最能代表外部环境驱动的诱致性变革的是浙江省嘉兴市通过对标上海而引发的城市治理变革,而随后这一变革从自发行为上升为浙江省战略和国家战略,实现了从诱致性城市治理变革向强制性城市治理变革转变。早在1992年,嘉兴市就提出了全面接轨上海的发展思路,并且于1996年将全面接轨上海作为首选战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调研嘉兴时强调:嘉兴作为全省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承接上海辐射的“门户”,要在全省“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中发挥更大作用。2017年,嘉兴市全面接轨上海正式成为浙江省的战略,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嘉兴市创建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实施方案》。在该方案中,浙江省对嘉兴市全面接轨上海进行了具体部署,提出将嘉兴市全面接轨上海的目标定位为:打造上海创新政策率先接轨地、上海高端产业协同发展地、上海科创资源重点辐射地、浙沪一体化交通体系枢纽地、浙沪公共服务融合共享地。2017年7月25日,嘉兴市印发《嘉兴市创建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行动计划(2017—2020年)》,这为嘉兴市全面接轨上海提出了行动指南。从2017年开始,嘉兴市每年至少率党政代表团对沪考察一次,促进全面接轨的双向互动,推动行动计划的落实。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调研嘉兴时强调:嘉兴作为全省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承接上海辐射的“门户”,要在全省“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中发挥更大作用。2017年,嘉兴市全面接轨上海正式成为浙江省的战略,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嘉兴市创建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实施方案》。在该方案中,浙江省对嘉兴市全面接轨上海进行了具体部署,提出将嘉兴市全面接轨上海的目标定位为:打造上海创新政策率先接轨地、上海高端产业协同发展地、上海科创资源重点辐射地、浙沪一体化交通体系枢纽地、浙沪公共服务融合共享地。2017年7月25日,嘉兴市印发《嘉兴市创建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行动计划(2017—2020年)》,这为嘉兴市全面接轨上海提出了行动指南。从2017年开始,嘉兴市每年至少率党政代表团对沪考察一次,促进全面接轨的双向互动,推动行动计划的落实。
2019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意味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被纳入国家战略,开启了强制性城市治理变革。该纲要的出台,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指明了具体的目标和路径,从而对各个城市治理界面和内部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前,不同城市是否选择一体化战略,更多地出于城市的自主选择,而在前述纲要出台之后,各个城市都需要按照一体化战略来重新规划自身的城市定位、发展路径和进行治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