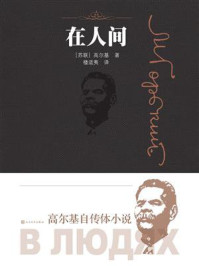几年前,当早晨的阳光洒进卧室,帕蒂·奈斯利已经打开了电视,阳光让人无法从某些角度看清屏幕上的画面。帕蒂的丈夫塞巴斯蒂安那时还在世,她正忙着准备去上班。早些时候,她一直在确认他能否应付这一天。那时他刚生病,她不确定——他们都不确定——最终会是什么结果。电视上像往常一样在播放晨间节目,帕蒂在卧室里走来走去,偶尔看上两眼。她正把一只珍珠耳环穿进耳垂,这时听见女主持人说:“稍后我们将请到露西·巴顿。”
帕蒂朝电视走过去,眯起眼看着,几分钟后露西·巴顿——她写了本小说——出现了,帕蒂喊了声:“噢,我的天啊。”她走到卧室门口叫道:“西比?”塞巴斯蒂安走进卧室,帕蒂说:“噢,亲爱的,噢,西比。”她帮他在床上躺好,抚摸着他的额头。她如今想起这件事——露西·巴顿上过电视——是因为她当时给塞巴斯蒂安讲了这个女人的事。露西·巴顿出身极为贫寒,就在附近伊利诺伊州的阿姆加什。“我不认识他们,因为我是在汉斯顿上的学,但人们谈到他们家孩子时总会说,喔,一群虱子!接着便跑开。”她向丈夫解释说。帕蒂知道这些是因为:露西的母亲以前给人做衣服,帕蒂的母亲曾经找她做裁缝。有几次,帕蒂的母亲带帕蒂和她的姐妹们去过露西·巴顿家。巴顿家很小,而且散发着一股臭味!但看看现在的露西·巴顿:喔,她已经成为一名作家,住在纽约。帕蒂说:“看啊亲爱的,她好漂亮。”
塞巴斯蒂安来了兴趣。这个故事他听得津津有味,她都看在眼里。几分钟之后他问了几个问题,比如,露西看上去是不是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不一样?帕蒂说她不知道,她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真的。但是,有件事很奇怪:露西的父母曾经被邀请参加帕蒂的大姐琳达的婚礼,帕蒂一直不理解这件事,她想象不出露西的父亲怎么会有一套正装,他们为什么会去参加她姐姐的婚礼。塞巴斯蒂安说,也许你母亲在那个时候找不到别人说话,帕蒂意识到他完全说对了。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帕蒂的脸变得红通通的。甜心,塞巴斯蒂安边说边去拉她的手。
几个月后,塞巴斯蒂安去世了。他们将近四十岁时才认识,只在一起度过了八年。没有孩子。帕蒂从没见过比他更好的男人。
*
今天她开车时,把车里的空调开得很大。帕蒂身体超重,因而很怕热,而现在已经是五月末了,天气很好——所有人都在说天气很好——但对帕蒂而言,实在是有点太暖和了。她驶过一片田,玉米还只有几英寸
 高,另一片田里大豆绿油油的,紧贴着地面。接着她穿过镇子,在街上拐来拐去,有些房子的门廊边,芍药正在怒放——帕蒂喜欢芍药——之后她开到了学校,她是高中部的一名辅导员。她把车停好,在后视镜里检查了下嘴唇上的口红,用手把头发抓得蓬松些,费力地从车里钻出来。停车场那头,安吉丽娜·芒福德正在下车,她是教公民课的初中部老师,丈夫最近离开了她。帕蒂朝她使劲挥了挥手,安吉丽娜也挥手回应。
高,另一片田里大豆绿油油的,紧贴着地面。接着她穿过镇子,在街上拐来拐去,有些房子的门廊边,芍药正在怒放——帕蒂喜欢芍药——之后她开到了学校,她是高中部的一名辅导员。她把车停好,在后视镜里检查了下嘴唇上的口红,用手把头发抓得蓬松些,费力地从车里钻出来。停车场那头,安吉丽娜·芒福德正在下车,她是教公民课的初中部老师,丈夫最近离开了她。帕蒂朝她使劲挥了挥手,安吉丽娜也挥手回应。
帕蒂的办公室里有很多文件夹,还有一堆装在小相框里的外甥和外甥女的照片,加上一些大学的小册子,这些都整齐地摆放在她的档案柜上方和桌子上。日程簿也放在桌上。莉拉·莱恩错过了昨天的约谈。有人敲门——门是开着的——一个高个子漂亮女生站在那里。“进来,”帕蒂说,“是莉拉吗?”
不安感和女孩一起走进了办公室。她没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看向帕蒂的眼神让帕蒂感到害怕。女孩留着金黄色的长发,当她伸手把头发撩起来搭到肩膀另一侧时,帕蒂看见了贯穿她手腕的文身——就像一道小小的铁丝护栏。帕蒂说:“莉拉·莱恩,很美的名字。”女孩说:“本来是要用我姨妈的名字的,但最后关头我妈说,见她的鬼去吧。”
帕蒂拿起试卷,在桌子上摞齐。
女孩坐直身子,出其不意地说:“她是个婊子。她觉得自己比我们任何人都强。我甚至都没见过她。”“你从没见过你姨妈?”
“没有。她父亲,也就是我母亲的父亲死后,她回来过这里,之后又走了,我从来没见过她。她住在纽约,她觉得自己拉的屎都是香的。”
“噢,让我们看看你的分数吧。分数挺高的。”帕蒂向来不喜欢她的学生说粗话,她觉得很无礼。她朝女孩望过去,又转头看着试卷。“你的总体成绩也不错。”帕蒂补充道。
“我没上三年级。我跳级了。”女孩没好气地说,但帕蒂似乎听出了她语气里的骄傲。
帕蒂说:“你很棒。这么说的话,我猜你一直是个好学生。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允许你跳级的。”她愉快地朝那个女孩扬起眉毛,但莉拉正在四下打量她的办公室,仔细地研究那些小册子和帕蒂的外甥及外甥女们的照片,最后她的目光在墙上的一幅海报上停留了很久。海报中一只小猫正悬在一根树枝上,猫的下方用印刷体印着“坚持住”几个字。
莉拉回头看着帕蒂。“什么?”她说。
“我说,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允许你跳级。”帕蒂重复。
“他们当然不会。老天爷。”女孩把她的一双长腿挪了个方向,但她仍旧瘫坐着。
“好吧。”帕蒂点点头,“那你将来怎么打算?你的成绩很好,分数都不错——”
“这些是你的孩子吗?”女孩眯起眼,手一挥指着照片问。
“他们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女。”帕蒂说。
“我知道你没有孩子,”女孩坏笑着说,“你怎么会没有孩子呢?”
帕蒂的脸微微一红。“就是没有罢了。现在来聊聊你的前途吧。”
“因为你从来没跟你丈夫做过?”女孩大笑着说,露出一口坏牙,“你知道,大家都这么说。胖子帕蒂从来没跟她丈夫伊戈尔做过,从来没跟任何人做过。人们说你还是个处女。”
帕蒂把试卷平放在桌子上。她感觉脸火辣辣地烧着。有一瞬间,她的视线模糊了,她听见墙上挂钟的嘀嗒声。即使在最疯狂的梦中,她也不曾预料到即将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话。她死死盯着女孩,她听见自己说:“马上从这儿滚出去,你这个脏东西。”
女孩似乎吃了一惊,但很快又说:“嘿,哇哦。他们说对了。噢,我的天啊!”她捂着嘴,发出一阵愈加持久而深沉的笑声,帕蒂感觉那笑都要从她的嘴里溢出来了,就像恐怖电影里某种生物吐出的胆汁。“对不起,”过了一会儿女孩说,“对不起。”
不知怎的,帕蒂突然知道了这个女孩是谁。“你姨妈是露西·巴顿。”帕蒂说。她又添了一句:“你看起来很像她。”
女孩站起来走出了房间。
帕蒂关上办公室的门,打电话给姐姐琳达,琳达住在芝加哥郊外。汗水润湿了帕蒂的脸,她觉得腋窝也被汗弄得黏糊糊的。
她姐姐接起电话,说:“琳达·彼德森-科内尔。”
“是我。”帕蒂说。
“我猜到了。电话上显示的是你的学校。”
“噢,那你怎么会——听着,琳达。”她告诉了姐姐刚刚发生的事。帕蒂说得很急,没提她对女孩说的那句话。“你敢相信吗?”她最后说。她听见姐姐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琳达说她永远也想不通帕蒂是怎么做到天天和青少年打交道的。帕蒂回答说她没领会重点。
琳达说:“不,我不是没领会。重点就是莉拉·莱恩、露西·巴顿,莉拉这个,露西那个,但谁在乎她们呢?”短暂的沉默后,琳达接着说:“说真的,帕蒂,露西·巴顿的外甥女这么浑蛋,这一点儿也不意外,我是认真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
“没有为什么。你不记得他们了吗?他们就是人渣,帕蒂。上帝啊,我刚想起来他们有个——什么来着?表兄弟,我想是吧?那个男孩叫艾贝尔。上帝啊,他可真了不得。他有次站在查特温蛋糕铺后面的垃圾箱里翻垃圾,想找些吃的。他有那么饿吗?他为什么要那样?而且我记得他这么做时一点儿也没觉得不好意思。我记得露西那时跟他在一块儿。那让我浑身发抖。坦白说,我现在想到还是会发抖。他妹妹叫多蒂,一个皮包骨头的女孩。多蒂·布莱恩和艾贝尔·布莱恩。我还记得他们,这有点不可思议。但我怎么会忘呢?我之前从没见过有人在垃圾箱里找吃的。他还是个帅气的男孩子。”
“天啊。”帕蒂说。她脸上的热度开始消退。她问:“露西的父母不是去参加过你的婚礼吗?你第一次结婚的时候。”
“我不记得了。”琳达说。
“你明明记得。他们怎么会去参加你的婚礼?”
“因为她邀请了他们,这样才有人跟她说话。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帕蒂,忘了这些吧。我已经忘了。”帕蒂说:“行吧,也许你忘了,但你还保留着他的姓。彼德森。你们结婚才一年。”
琳达说:“我到底为什么要把姓改回奈斯利?我无法理解你干吗一直留着。奈斯利家的小美人儿。被别人叫作奈斯利家的小美人儿,这太可怕了。”
帕蒂心想:这并不可怕。
琳达接着说:“你最近去看我们那位还没升天的母亲了吗?她这些日子又干什么傻事了?”
帕蒂说:“我打算下午去那儿看看。有些天没去了。我得确保她一直在坚持吃药。”
“我才不关心她吃没吃呢。”琳达说。帕蒂说她知道这一点。
帕蒂又说:“你心情不好吗,还是怎么了?”
“不,没有。”琳达说。
*
这天是星期五,下午在镇子上,帕蒂拿着工资支票去了趟银行,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她往书店里看了一眼,瞅见了——就摆在展台正前方——露西·巴顿的一本新书。“我的天啊。”帕蒂说。查理·麦考利在书店里,帕蒂看到他后差点走了出去,因为他是除了塞巴斯蒂安之外她唯一爱的男人。她真的爱他。她并不是特别了解他,但她喜欢他很多年了,小镇上的人都是这样,互相认识但也互相不了解。在西比的葬礼上,当她转头看见他独自坐在后排,她立刻——立刻——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他,自那以后她就一直爱着他。他带着他的孙子,小男孩在上小学,当查理抬头看见帕蒂时,他的面容舒展了,点了点头。“嗨,查理。”她说。随后她问了店主露西·巴顿新书的事。
是一本回忆录。
回忆录?帕蒂拿起书翻了翻,但查理离得这么近,她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帕蒂拿着书去收银台结账。她出门时瞥了查理一眼,他冲她挥挥手。查理·麦考利老得够当她父亲了,不过如果她父亲还在世的话,他应该比她父亲年轻些。但查理至少比帕蒂大二十岁,他年轻时参加过越南战争。帕蒂说不清她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他的妻子相貌平平,而且骨瘦如柴。
帕蒂的房子和镇中心隔着几条街。房子不大,但也不小,是她和西比合伙买的,有一个前门廊和一个小小的侧门廊。侧门廊边上种的芍药花头硕大,还有一些鸢尾也开花了。透过厨房的窗户能看见那些鸢尾,她从橱柜里拿出一盒饼干——是尼拉牌威化饼干,还剩半盒——接着走进起居室,坐下来一块接一块地吃掉。之后她又回到厨房,喝了一杯牛奶。她打电话给母亲,说她大概一小时后过去,她母亲说:“噢,好呀。”
楼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走廊里。地板上到处都是结成小团的灰尘。“天哪。”帕蒂说。她坐在床上,说了好几遍。“噢,天哪,噢,天哪。”
到汉斯顿镇的车程是二十英里,帕蒂开车经过田野时,阳光依旧耀眼。有些田里种着玉米幼苗,有些田地是棕色的,还有一块田在她驶过时正在翻耕。随后她来到了风力涡轮机所在的地方,地平线上排列着一百多台,这些巨大的白色风车近十年前就竖立在这片土地上了。它们令帕蒂着迷,一直如此,它们白色的、长长的胳膊以同样的速度搅动着空气,然而却并不同步。她想起眼下的一起诉讼,经常有这类案子——关于风车对鸟类、鹿和农田的危害,但帕蒂喜欢这些白色的大家伙,它们细长的臂杆以略显古怪的动作对抗着天空,产生能源——很快它们落在了她身后,眼前再次只剩种满玉米幼苗和油亮大豆的农田。就是在这些玉米地里——在它们茎叶繁茂的夏季——在她十五岁时,她让男孩们压在她的身上,他们的嘴唇肥大,充满弹性,他们的家伙在裤子里鼓起,她喘息着,把脖子露出来让他们亲吻,在他们身上摩擦,但——是真的吗?——她无法忍受,她无法忍受,她无法忍受。
帕蒂开进镇子,这里自她长大之后就几乎没什么变化。样式过时的黑色街灯,灯泡装在顶部的灯箱里。还有那两家餐厅、礼品店、投资公司、服装店——都有着同样的绿色雨篷和黑白招牌。要去母亲的住处,她必须经过童年时期的那个家,一座漂亮的红房子,有黑色的百叶窗和一条宽敞的门廊,上面挂着一架秋千椅。很小的时候,帕蒂和母亲在秋千椅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她蜷缩在母亲肚子边,弄皱了母亲的连衣裙,头顶上方传来母亲的笑声。她的父亲在那座房子里一直住到去世,就在西比去世的前一年。现在的房主是儿女众多的一大家子,帕蒂每次开车经过时,总是扭头看另一个方向。穿过镇子再开一英里,就到了母亲的小白房子。帕蒂开上车道时,看见母亲透过前门的帘子盯着外面,接着,帕蒂打开侧门进屋,听见她的拐杖重重地敲在地板上。帕蒂长大了多少,母亲就变小了多少,这是她如今每次见到母亲时的想法。“嘿。”帕蒂俯身亲吻母亲脸旁的空气。她站直身子说:“我买了些吃的给你。”
“我不要吃的。”母亲穿着一件毛巾布睡袍,她拉了一下睡袍带。
帕蒂拆开烘肉卷、凉拌生菜丝和土豆泥,把它们放进冰箱。“你得吃点东西。”帕蒂说。
“我一个人坐着就什么也不想吃。你能留下来陪我吃吗?”母亲透过她硕大的眼镜抬头看着她,眼镜已经从鼻梁上滑下来了一点。“求你了。”帕蒂快速地闭了下眼睛,点了点头。
帕蒂布置餐桌时,母亲坐在椅子里,两腿在睡袍下叉开,她抬头看着帕蒂。“见到你真是好极了。我好久没见你了。”
“三天前我刚来过这里。”帕蒂说。她朝案台转过身去,母亲稀疏的头发——头皮清晰可见——停留在她的思绪中,她感到自己崩溃了。回到餐桌边,她拉过一把椅子,说道:“我们得谈谈你去‘金树叶’福利院的事。还记得我们谈过这事儿吗?”母亲的脸上似乎显出了困惑,她缓缓摇头。“你今天穿好衣服了吗?”帕蒂问。
她母亲低头看着腿上的睡袍,又抬头看看帕蒂。“没有。”她说。
*
在圣路易斯的一次会议上,帕蒂认识了她的丈夫。会议讨论的是如何解决低收入家庭孩子的相关问题,但塞巴斯蒂安与此无关。他的宾馆房间挨着帕蒂的,他来参加的是另一场会议,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又见面啦!”他们走出各自的房间时帕蒂说。晚上他俩各自回房时她就见过他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还无法确定,但他让她感觉十分舒服。她当时因为服用抗抑郁药物已经开始发胖,她先前在距自己的婚期仅仅几周时,中止了那场婚礼。最初的几次交谈,塞巴斯蒂安甚至都不看她。但他是个英俊的男人,瘦高,面庞瘦削,头发偏向一边。他的眉毛很粗,像在额头上连成了一条线,双眼凹陷在眉骨下方。她就是喜欢他。会议结束时,她要到了他的邮箱地址,她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之间的邮件往来。短短几周内他写道: 如果我们要做朋友的话,帕蒂,有些关于我的事应该让你知道。几天之后他又写道:我遇到过一些事。可怕的事。它们让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住在密苏里州,她写信让他来伊利诺伊州的卡莱尔时他同意了,这让她很意外。自那之后,他们就在一起了。她怎么会知道——她从不知道——他小时候曾一次又一次地被继父玩弄?塞巴斯蒂安很难忍受和别人相处,但一开始他就看着她,详细地告诉了她自己经历的事,他对她说,帕蒂,我爱你,但我做不了。我就是做不了那个,我希望我可以。她说:“没关系,我也忍受不了那个。”
在他们的婚床上,他们手牵着手,但从未更进一步。尤其在头几年里,他经常做可怕的梦,他会踢被子并发出尖叫,声音骇人。她注意到,每当这时他都很亢奋,而她总是确保只触碰他的肩膀,直到他平静下来。然后她替他擦拭额头。“没事的,亲爱的。”她总是说。他则盯着天花板,双手握拳。谢谢你,他说。他转过脸看她,谢谢你,帕蒂,他说。
“告诉我,告诉我。跟我说说。你怎么样?”她母亲把一叉子烘肉卷塞到嘴里。
“我挺好的。明天晚上我要去看安吉丽娜。她丈夫把她甩了。”帕蒂把土豆泥抹在烘肉卷上,再把黄油涂在土豆泥上。
“我不知道你在说谁。”她母亲把叉子放在餐桌上,疑惑地看着她。
“安吉丽娜,芒福德家的女孩之一。”
“哈。”她母亲缓缓点着头,“噢,我知道了。她的母亲是玛丽·芒福德。肯定是。她这人不怎么样。”“谁不怎么样?安吉丽娜是个很好的人。我一直觉得她母亲很和善。”
“喔,她是挺和善。她只是不怎么样。我记得她是密西西比人。她嫁给了那个芒福德家的男孩,他很有钱,之后她就有了那几个姑娘和一大堆钱。”
帕蒂张开嘴。她想问母亲还记不记得,玛丽·芒福德几年前离开了那个有钱的丈夫,在七十多岁的时候,母亲还记得吗?但帕蒂不会问的。她不会告诉母亲她和安吉丽娜成为朋友的原因:她们的母亲都离开了。
“我想杀了他,”塞巴斯蒂安曾对帕蒂说,“我真的想杀了他。”“你当然会这么想。”她说。“我还想杀了我母亲。”他说。帕蒂说:“你当然会这么想。”
帕蒂四下打量着母亲的小厨房。厨房里一尘不染,这都是奥尔加的功劳,她是个比帕蒂年长的女人,每周过来两次。她身旁的桌子是油布面的,边角已经开裂,蓝色的窗帘严重褪色。从帕蒂坐着的地方,顺着走廊到起居室的角落,能看见那张蓝色的豆袋椅,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母亲一直不让扔。
她母亲正在念叨过去的事——这些天来她经常这样。“俱乐部里跳的那些舞,我的天啊,多有意思。”她顿了顿,难以置信地摇着头。
帕蒂又在土豆上放了厚厚的一块黄油,她吃掉土豆,把盘子推到一边。“露西·巴顿写了一本回忆录。”她说。
她母亲说:“你说什么?”帕蒂又重复了一遍。
“我现在想起来了,”她母亲说,“他们之前住在一间车库里,后来那个老男人死了——是个什么亲戚,我不知道——他们搬到了房子里。”
“一间车库?我记得去过的地方就是那儿?一间车库?”
她母亲沉默片刻后说道:“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但她非常便宜,所以我雇了她。她干得特别出色,而且几乎不收一个子儿。”又过了好一阵子,她母亲又说:“几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过露西。大人物啊。她写了本书什么的,住在纽约。大摇大摆的,派头挺足。”
帕蒂不安地深吸了一口气。她母亲伸手去够凉拌生菜丝,睡袍敞开了一点点,帕蒂看见了——一闪而过——睡袍下面干瘪的小乳房。几分钟后帕蒂站起身,把桌子收拾干净,飞快地洗完盘子。“我们来检查一下你的药。”她说。她母亲鄙夷地挥了挥一只手。帕蒂走进卧室,找到装着每日固定剂量的药盒,她发现从她上次来之后,母亲就没吃过一片药。帕蒂把药盒拿到母亲面前,又解释了一遍每一片药的重要性,她母亲说:“好吧。”她服下帕蒂递给她的药片。“你需要吃这些药,”帕蒂告诉她,“你总不想中风吧?”至于延缓痴呆的药,她提都没提。
“我才不会中风。中风个鬼。”
“行,回头见吧。”
“你长得最漂亮了,”她母亲站在门口说,“可惜那些能让你开心的药令你发胖了,真糟糕,但你还是很漂亮。你确定你真的要走了吗?”
帕蒂沿着车道朝她的车走去,她大声说了一句:“噢,我的天啊。”
*
太阳刚落山,帕蒂离家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已经路过了风车——满月正从天边升起。她父亲死的那天晚上也是满月,在帕蒂心里,每当月圆之时,她都感觉父亲正在看着她。她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摇了摇,当作和他打招呼。爱你,爸爸,她轻声说。她也是在对西比说,某种程度上,他们在她心里合二为一。他们在上面看着她,她知道月亮不过是一块岩石——岩石!但看到满月总让她感觉她的男人们就在那里,就在上面。等着我,她轻声说。因为她知道——她几乎可以确定——等她死了,她会和父亲还有西比团聚。谢谢你,她轻声说。因为她父亲刚刚告诉她,她能照顾母亲真是太好了。他现在这么宽容,是死亡改变了他。
回到家,她走时留着的灯光让房子显得很温馨。让灯一直亮着,这是她在独居生活中学到的许多事情之一。然而,当她放下皮包,穿过起居室时,一种可怕的感觉袭来。她度过了糟糕的一天。莉拉·莱恩让她大受震动,假如这个女孩举报她,告诉校长帕蒂骂自己是脏东西怎么办?她做得出来,莉拉·莱恩。她很擅长这一套。帕蒂的姐姐帮不上忙,打电话给另一个姐姐也没有意义,她住在洛杉矶,她们从来都聊不到一起,她的母亲——噢,她的母亲……
“胖子帕蒂。”帕蒂大声说出这几个字。
帕蒂在沙发上坐下,环顾四周。这座房子看上去有点陌生,而她已经明白,这是个不祥之兆。她的嘴里还有烘肉卷的味道。“胖子帕蒂,准备去睡觉吧。”她大声说着,站起身,用牙线剔牙,接着刷牙洗脸。她抹上面霜,这让她感觉稍微好了点。翻皮包找手机的时候,她看到了之前塞进去的露西·巴顿的那本小书。她坐下来端详着封面。封面上是黄昏时的都市建筑,灯火辉煌。接着,她开始读起来。“天啊,”看了几页后她说,“我的天啊。”
*
第二天早上,星期六,帕蒂用吸尘器把楼上楼下打扫了一遍,换了新床单,洗了衣服,仔细检查了邮箱,把商品目录和广告传单都扔了出去。然后帕蒂进城买了些杂货,还买了一些花。她已经很久没有给家里买过花了。整整一天,她都感觉嘴里塞了一块黄色的糖果,也许是奶油硬糖,她知道这份隐秘的甜蜜来自露西·巴顿的回忆录。帕蒂不时地摇着头,响亮地发出一声“哈”。
下午她给母亲打电话,是奥尔加接的。帕蒂问她能不能每天都来,而不是一周来两天,奥尔加说她要考虑一下,帕蒂说自己能理解。然后帕蒂请她让母亲接电话。“谁啊?”母亲问。帕蒂说:“是我,帕蒂,你女儿。我爱你,妈妈。”
她母亲立刻说:“噢,我也爱你。”
这之后,帕蒂不得不躺下。她说不上来她上次告诉母亲她爱她是什么时候了。小时候她经常这么说,甚至在母亲同意帕蒂不用再参加女童子军的那个早上可能也说过。当时帕蒂刚上高中,她母亲说:“噢,帕蒂,没事的,你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决定。”母亲站在厨房里,把装在纸袋里的午餐递给她,那才是她,帕蒂的母亲。当天中午,帕蒂因为痛经——帕蒂曾有严重的痛经——从学校回到家,她听见父母的卧室里传来最骇人的声音。她的母亲在哭泣、喘息、尖叫,还有拍打皮肤的声音,帕蒂跑上楼,看见母亲正骑在德莱尼先生——帕蒂的西班牙语老师身上,母亲的乳房晃来晃去,那个男人拍着她母亲的屁股,他的嘴伸上去含住她母亲的乳房,她的母亲哀号着。帕蒂永远忘不了她母亲的眼神,那么疯狂。她母亲无法抑制地哭喊,这就是帕蒂看见的,母亲的乳房和母亲看她的眼神——但母亲却无法阻止从自己口中发出的声音。
帕蒂转身跑进了自己的卧室。几分钟后,她听见德莱尼先生下楼的脚步声,母亲走进她的房间,裹着一件家居袍,说道:“帕蒂,我向上帝发誓,你绝不能告诉任何人,等你长大一点,你会明白的。”
帕蒂想象不到她母亲的乳房有那么大,她看见它们无拘无束地在那个男人上方晃荡。
几天之内,曾经宁静平凡的家庭发生了如此可怕的事,帕蒂甚至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种事。事实上,帕蒂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看到了什么,她不知道该如何措辞,但她再也没有去上德莱尼先生的课,后来——噢,这太突然了!——母亲在一次告解时爆发了,之后她搬进了镇上的一间小公寓里。帕蒂只去看过她一次,公寓的角落里有一把蓝色的豆袋椅。整个镇子都在谈论她母亲和德莱尼先生的韵事,对于帕蒂,她感觉像是自己的头被砍掉了,正在远离她的身体。这感觉真的极为怪异,而且持续不断。她和姐姐们看着父亲哭泣。她们看着他咒骂,变得神情冷漠。他之前从来不是这样,他不哭,不咒骂,神情也不冷漠。而他就变成了这样的人,这个家不复存在了——就好像他们不过是无辜地坐在湖上的一艘小船里——变成了从未想象过的样子。镇子上议论不休。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帕蒂只得忍受最漫长的等待,直到一切过去。到圣诞节的时候,德莱尼先生已经离开了镇子,留下帕蒂母亲一人。
当帕蒂开始和班上的男生去玉米地,甚至在很久之后,当她有了真正的男朋友,她和他们干那事的时候,她母亲的形象总是浮现出来,没穿上衣,没戴胸罩,乳房晃来晃去,那个男人抓住一只放到嘴里——不,帕蒂无法忍受这一切。她自己的兴奋感带来的,永远是痛苦而可怕的羞耻。
*
安吉丽娜还是那么苗条,看着很年轻,虽然她比帕蒂还要大几岁。但当帕蒂在“萨姆家”餐厅的镜子里瞥见她们俩,她觉得自己看上去更年轻——安吉丽娜则略显憔悴。帕蒂正要告诉安吉丽娜有关露西·巴顿出书的事,但她们刚坐下来,安吉丽娜的绿眼睛中就泪水涟涟,帕蒂越过桌子抚摸着朋友的手。安吉丽娜举起一根手指,过了一会儿她才开口。“我简直恨死他们俩了。”安吉丽娜说,帕蒂说她都懂。“他对我说,‘你爱上你母亲了’,我惊讶极了,帕蒂,我就那么盯着他——”
“天啊。”帕蒂叹了口气,靠坐在椅子上。
几年前,安吉丽娜的母亲在七十四岁的时候,离开了镇子——离开了她丈夫——去意大利嫁给了一个比她小将近二十岁的人。这件事让帕蒂十分同情安吉丽娜。但她现在想说:听听这个!露西·巴顿的母亲对她非常差,她父亲——噢,上帝啊,她父亲……但露西爱他们,她爱她母亲,她母亲也爱她!我们都是一团糟,安吉丽娜,我们拼尽所能,爱得不完美,安吉丽娜,但这没关系。
帕蒂一直迫切地想把这些告诉她的朋友,但此时她感觉这些话听起来是那么无谓——简直是愚蠢。于是帕蒂听安吉丽娜说起她的孩子们,他们在上高中,即将离开家远走高飞,听她说起她母亲在意大利,给所有女儿们——安吉丽娜有四个姐妹——写电子邮件,而安吉丽娜是其中唯一一个没去看过母亲的,但她正在考虑这件事,也许她今年夏天会去。
“噢,去吧,”帕蒂说,“一定要去。我觉得你应该去。我是说,她老了,安吉丽娜。”
“我知道。”
帕蒂意识到安吉丽娜很想聊她自己的事,不过这并没有令帕蒂困扰,她只是注意到了而已。她也能理解。她明白,每个人大多数时候都只对自己感兴趣。也有例外,西比就对她感兴趣,她对他也怀有强烈的兴趣。这份对与你共度一生之人的爱,是一层保护你不受外界伤害的皮肤。
过了一会儿,喝到第二杯白葡萄酒时,帕蒂跟安吉丽娜说了莉拉·莱恩的事,但她只说了“胖子帕蒂”的部分,以及他们都认为她是个处女。接着她说:“你知道,露西·巴顿写了——”
“噢,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安吉丽娜说,“你还是这么漂亮,帕蒂,千真万确,别听那种鬼话,没人那么说你,帕蒂。”
“有可能说过。”
“我从没听过,我可是整天听小孩们说话的。帕蒂,你还会遇到别的男人的。你很美,真的。”
“查理·麦考利是唯一让我感兴趣的男人。”帕蒂说。酒后吐真言。
“他老了,帕蒂!你知道,他这人不正常。”
“哪方面不正常?”
“我是说,他以前参加过越南战争,而且他——你知道的,他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真的吗?”
安吉丽娜微微耸了耸肩。“我听说的。我不知道是谁说的,但很多年前我就听说了。我不知道,真的。他妻子——唔,你有机会,帕蒂。”
帕蒂笑了。“他妻子看上去人很好。”
“噢,得了吧,她是个整天提心吊胆的老家伙。我是认真的,去跟查理兜兜风吧。”
帕蒂觉得要是自己什么都没说就好了。
但安吉丽娜似乎没注意到。她只想谈论自己——还有她丈夫。“那天晚上我在电话里直接问他,你要开始走离婚程序了吗?他说不,他不想那么做。我就不问了。我不懂他既然要走,为什么又不想离婚。噢,帕蒂!”
在停车场,安吉丽娜用双臂环住帕蒂,她们拥抱了一会儿,紧紧地搂在一起。“我爱你。”帕蒂上车后安吉丽娜喊道。帕蒂说:“我也爱你。”
帕蒂小心地开着车。白葡萄酒让她情绪敏感,虽然服用抗抑郁药期间不应该喝酒。此时她感到思绪开阔,很多事在脑海中交错。她想起塞巴斯蒂安,想知道是否有人在他告诉她之前,就知道了那些她不知道的事——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不可言说的事。她现在怀疑事情早已暴露。早已暴露,肯定的。她想起有一天在服装店里,她和塞巴斯蒂安正要离开,听见一个年轻的店员对另一个店员说:“她就像养了一条狗一样。”
在露西·巴顿的回忆录里,露西写道,人们总是希望感觉高人一等,帕蒂觉得正是如此。
今晚,月亮几乎跟在帕蒂身后,她从后视镜里看到它,冲它眨了眨眼。她想起了姐姐琳达。琳达说她不明白帕蒂怎么能忍受和青少年打交道的工作。帕蒂开着车,摇了摇头。好吧,那是因为琳达从来就不懂。除了塞巴斯蒂安没有人懂。西比死后,帕蒂去看过心理治疗师。她本来打算告诉这个女人,但这个女人穿了一件海军蓝的夹克,坐在一张大书桌后面,她问帕蒂对父母离婚有什么感受。很糟,帕蒂说。帕蒂不知道怎样才能找个理由不去见这位心理治疗师,最后她说了谎,说她付不起钱了。
此时,当帕蒂开进家里的车道,看见她走时留下的灯光,她意识到露西·巴顿的书理解了她。就是这样——那本书理解了她。黄色糖果的甜味还留在她的口中。露西·巴顿也有自己的羞耻,噢,那是怎样的羞耻啊。而她很快就从中挣脱了。“呵。”帕蒂说,一边熄灭引擎。她在车里坐了片刻,然后下车进了屋。
*
星期一早上,帕蒂给班主任留了一张便条,让莉拉·莱恩去她的办公室,但当女孩在下一节课出现时,她还是吃了一惊。“莉拉,”帕蒂说,“进来。”
女孩走进帕蒂的办公室,帕蒂说:“坐吧。”女孩警惕地看着她,但立刻开口说:“我打赌你想让我道歉。”
“不,”帕蒂说,“不是。我今天让你来,是因为上次你在这儿的时候,我骂你是脏东西。”
女孩一脸困惑。
帕蒂说:“你上周在这里的时候,我骂你是脏东西。”
“你骂了吗?”女孩问。她缓缓坐下。
“我骂了。”
“我不记得了。”女孩不是在怄气。
“在你问我为什么没有孩子,说我还是个处女并叫我‘胖子帕蒂’之后,我骂你是个脏东西。”
女孩狐疑地盯着她。
“你不是脏东西。”帕蒂停了停,女孩等着,帕蒂接着说,“我在汉斯顿长大的时候,我父亲是一座饲用玉米农场的经理,我们有很多钱。衣食无忧,可以这么说。我们的钱够多了。我实在没必要骂你——骂任何人——是脏东西。”
女孩耸耸肩。“我确实是。”
“不,你不是。”
“噢,我猜你当时是生气了。”
“我当然生气了。你对我真的很粗鲁。但那并不意味着我可以说那种话。”
女孩看上去很疲惫,她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我不会被这个困扰,”她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再想这件事了。”
“听着,”帕蒂说,“你的分数很高,成绩优异。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去上大学。你想去吗?”
女孩流露出些许惊讶。她耸耸肩。“我不知道。”
“我丈夫,”帕蒂说,“他觉得自己是个脏东西。”
女孩看着她,过了一会儿说:“他真这么想?”
“是的。因为他身上发生过的事。”
女孩用那双忧伤的大眼睛看着帕蒂。最后她长叹一声。“噢,天啊,”她说,“好吧。我很抱歉说了关于你的那些蠢话。你的那些事。”
帕蒂说:“你才十六岁。”
“十五岁。”
“你才十五岁。我是个成年人,我才是那个做错事的人。”
帕蒂吃惊地发现,泪水开始从女孩的脸庞上滚落,她用手擦拭着。“我只是累了,”莉拉说,“我只是太累了。”
帕蒂起身关上办公室的门。“亲爱的,”她说,“听我说,甜心。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我能让你进一所大学。有地方可以弄到钱。我说过,你的成绩很优秀。看到你的成绩单我都惊呆了,你的分数真的很高。我的成绩不如你,可我也上了大学,因为我父母出得起钱。但我也能让你进大学,你可以的。”
女孩头枕着胳膊趴在帕蒂的书桌上。她的肩膀颤抖着。过了几分钟,她抬起目光,脸上湿湿的,她说:“对不起。每当有人对我好——上帝啊,我真受不了。”
“没事的。”帕蒂说。
“不,不是的。”女孩又哭了,出声地哭个不停。“噢,上帝啊。”她说,一边抹着脸。
帕蒂递给她一张纸巾。“没事的。我是说真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
那天下午,艳阳当空,阳光泼洒在邮局的台阶上,帕蒂从上面走过。查理·麦考利正在邮局里。“嗨,帕蒂。”他说,点了点头。
“查理·麦考利,”她说,“这些日子在哪儿都能见到你。你好吗?”
“还活着。”他朝门口走去。
她检查了邮箱,把信件拿出来,然后意识到他已经走了。但她走出去时发现他正坐在台阶上,让她吃惊的是——尽管并不那么出乎意料——她挨着他坐了下来。“哇哦,”她说,“我这一坐下可能就起不来了。”台阶是水泥的,虽然有阳光洒下来,她透过裤子仍然感到一丝凉意。
查理耸耸肩。“那就别起来。我们就这么坐着吧。”后来的很多年里,帕蒂都会在脑海中回味这件事,他们坐在台阶上,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街对面是五金店,再过去是一座蓝房子,下午的阳光照亮了房子的一侧。她想起了高大的白色风车。它们纤细的长臂全部转动起来,却从不同步,只是偶尔有两台风车会齐齐转动,它们的手臂在空中悬停于同一个位置。
最后,查理说:“你最近还好吗,帕蒂?”
她说:“是的,我挺好。”她转向他。他的眼睛好像永远地退了回去,它们是那么深邃。
过了会儿查理说:“你是个中西部姑娘,所以你总说挺好的。但事情可能并不总是那么美好。”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他。她看见他喉结正上方有一小片忘刮了,那儿有几根白胡子。
“你当然不用告诉我有什么不好的事,”他说,直直地看着前方,“我也肯定不会问。我只是想说,有时候,”他转而望向她的眼睛,她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暗蓝色的,“有时候事情没那么好,一点儿也不好。事情并不总是美好的。”
她想说,哦,她渴望伸手触碰他的手。因为他说的正是他自己,她才想到了这个。哦,查理,她想说。但她安静地坐在他身边,一辆汽车从主街上开过,接着又是一辆。“露西·巴顿写了本回忆录。”帕蒂终于开了口。
“露西·巴顿。”查理盯着正前方,眯起眼睛。“巴顿家的孩子,天啊,那个可怜的男孩,最大的那个。”他轻轻摇了摇头。“老天爷。可怜的孩子们。我的老天爷。”他看着帕蒂,“我猜那是一本悲伤的书?”
“不是。至少我不这么认为。”帕蒂想了想。她说:“那本书让我感觉好多了,让我觉得没那么孤单了。”
查理摇摇头。“哦不。不,我们总是孤单的。”
他们在一种友善的沉默中坐了很久,阳光罩在他们身上。随后帕蒂说:“我们并不总是孤单的。”
查理转头看着她。他什么也没说。
“我能问问你吗?”帕蒂说,“大家都觉得我丈夫很奇怪吗?”
查理顿了一会儿,似乎在考虑。“也许吧。在这里我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别人在想什么的人。塞巴斯蒂安在我看来是个好人。很痛苦。他很痛苦。”
“嗯。是的。”帕蒂点点头。
查理说:“对此我很遗憾。”
“我知道。”阳光明晃晃地洒在蓝房子上。
又过了很久,查理再次转过去看着她。他张开嘴好像要说什么,但随即摇了摇头,又一次闭上了嘴。帕蒂感觉——虽然并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她明白他要说的话。
她飞快地碰了一下他的胳膊,他们就这样坐在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