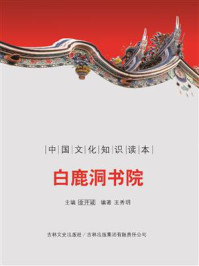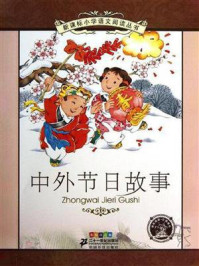多说无益,因为禁海令被严令执行了。
从弘治十三年(1500)起,无论何人,只要被发现建造超过两个桅杆的船只,就要被判处死刑。而在嘉靖三十年(1551),就连乘坐这种船出海都是犯罪行为。有一个故事说,成化十三年(1477),当大臣们重提宝船航行这个想法时,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派人烧毁了郑和的航海日志,刘大夏的理由是:“郑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费了上百万的金钱和谷物,而且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此……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行动,大臣们本应予以强烈反对。即使这些旧资料现在还保存着,也应该被烧毁。”对此,兵部尚书余子俊大为愤怒,但皇帝朱见深没有任何反应。
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句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结束国家航海项目的决策贯彻得畅通无阻,巨大的远洋船无所事事地停泊在港口里,很快就成了廉价木材,被拆卸一空。铁工厂被废弃,航海仪器和资料缺乏管理,船队人员或者受雇于大运河的小船,或者被投入建筑和交通行业。不久,大明就不再拥有海洋主导地位,虽然朝贡使团仍在流入,但已是乘坐外国船只而来。到了15世纪中期,印度洋周边国家的使团,一般都远离中国水域了。

大明船队不再独霸海疆半个世纪后,葡萄牙、西班牙船队才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洋,进而走遍世界,成为海上商业与殖民帝国。在此之前,以印度洋为中心,西起红海,东到日本海的整个亚洲大陆南缘的长弓形的海上通道,才是世界贸易的中心,更是世界的活力中心。在此之后,欧洲主宰的大航海时代,使得大西洋成为世界动力的源头。中国的“退守内陆”与欧洲的“海上扩张”,是划分世界史的依据。

与郑和远航的主旨是和平,基础是和谐与宽容大相径庭的是,欧洲人的每一次远航都带有经济掠夺、军事征服甚至地理占有的目的,都夹杂着对当地人的矮化与压制。如1768年英国皇家派出一支远航队,公开宣称前往塔希提岛观察金星凌日,以便准确地测出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船上载有多名天文学家、科学家和画家,船长是航海家、制图师、海军中尉詹姆斯·库克。他们不仅观察到了金星凌日,而且抵达了澳大利亚东海岸和被荷兰人发现但未登陆的新西兰,然后宣称这些岛屿归英国所有。就连1798年拿破仑进攻埃及时,都随队带着165名学者,一大成就是建立了一个名叫埃及学的新学科,长远目的则是为法国占领埃及奠定语言、文化、法理基础。
西方人认为,中国在15世纪初放弃海权是一个“千年之谜”。因为其他航海大国往往经过百年争斗,受到对方的驱逐而成为悲惨的输家,不得不离开这一蓝色的舞台。而大明从蓝色的舞台退出,根本没有任何外力的干扰,纯属自主选择。这一点,是令拥有殖民主义思维的外国探险家和政治家匪夷所思的。
答案,应该与地理、政策和文化有关。
一是地理因素。中国的海岸线长度达到3.2万公里,而陆地边界线仅有1.8万公里,但这道陆地边界线是它与它不稳定和好斗的邻国共享的,尽管明代来自倭寇的骚扰和19世纪来自海上的侵略使得中国数度蒙羞,但它没有被这些侵略者推翻,而来自陆上的侵略者则屡次做到这一点。
二是政策因素。回望中国二十四史,强盛的王朝总是把精力集中在陆地上,土地和人口一直是它的首要问题。只有分裂时期的偏远和弱小政权,才会把目光投向海洋。譬如春秋战国时期,注重发展水产和水师的,是相对边远的齐国、吴国和越国;三国鼎立时期,最重视水军建设的,是相对弱小的东吴;宋辽金元并立时期,发展海上贸易最积极的,是武力羸弱的南宋。虽然中国与海洋存在长期而重要的关系,但历代中国统一王朝本质上都是大陆国家,海洋从来不是国家政策和国家身份的核心。它更关心内部稳定,而不是对外关系,它担心对外贸易会引发不安定,因为这会在世俗和精神层面上引入外国思想,并使商人集聚起个人财富,而这些人是在儒家社会体系中居于最下层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重农抑商”,是除宋朝之外其他所有王朝的国家政策,商人在古代中国人眼里几乎就是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代名词,挣再多的钱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想着捐一个官做。道理很简单,当中华帝国对海外无欲无求,国内又能做到太平、富庶、风调雨顺、衣食无忧,人的举止端庄优雅,能够按照儒家学说组织社会、礼遇那些皓手穷经的人,朝廷为什么还需要更多地注意海外的世界呢?正如亚当·斯密分析的那样,中国主动放弃了海权,没有“鼓励对外商业活动,因此失去了比较优势和国际劳动分工带来的优势”,使得经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只能听任那些毫不起眼的西欧小公国在殖民扩张之路上狂奔。
三是文化因素。在中国人的传统性格里,一向缺乏向外的张力。“安土重迁”,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守业守成”,是历代君主共同的选择。千年前的秦始皇虽然纵横六合,但他建造的长城,本质上与农夫的篱笆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他的院子更大一点罢了。因此我们看到,永乐除了下西洋、编纂《永乐大典》外,还有一项同样引人注目的盛举——把国都从长江南岸的南京迁移到靠近长城的北京,并重修被冷落数百年的长城。明朝科举主要考核举人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但朱元璋最讨厌孟子,认为孟子“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思想不利于君主专制,因此科举所用的经典删去了不利于皇权的章节,经典的解释也以朱熹的注疏为主,以保证纲常不变。这样选取的举人,当然都是些循规蹈矩者,对皇帝只有效忠,不敢怀疑。儒家思想的僵化,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以人性为主、强调人格和公平正义的孔孟学说,从此被阉割为统治者维护专制权威的工具。

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从海洋倒退的关键因素,是信奉儒家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因为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而加强了。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儒家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重视。达官贵人对陆军和水军厌恶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商人和商业资本的疑虑与不满。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眼里就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到他们控制。

此外,大多数知识分子目睹了方孝孺、于谦等人的悲惨结局,不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卷入政治斗争,也不再愿意将目光投向未知的世界,便选择了安于现状。一些人设坛讲学,却拒绝为科举考试培养学生;一些人注重为村庄和家庭制定规则,女子裹脚的习俗随之形成;还有一些人倾向自省,通过静坐与沉思来完善自己,勠力实践朱熹所倡导的:“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更有一批人以中庸为人生信条,一再标榜和推崇老子的那句话:“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大清名臣张廷玉在专制君王乾隆登基后,只能黯然致仕,并一再感叹:“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一个印度老牌政治家对明清时期的中国和欧洲做了一个比喻:中国是一个有教养的中年人,喜欢平静的生活,不热衷于新的冒险,不喜欢打乱规律的生活,忙于研究古典文化和艺术;而欧洲则是个毛头小伙儿,桀骜不驯,富有激情和探求精神,渴望到各处去冒险。中国不乏美妙动人之处,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固守住疆界,笼络住人口,成为明清实行海禁的真正目的。特别是到了清代,顺治帝发布了两次“禁海令”,要求商船一律不准私自出海;为了对付郑成功,顺治帝和康熙帝又发布了三次“迁海令”,勒令沿海居民一律内迁30里。连续三次强制性的“迁海”,波及范围北起山东半岛,南到珠江三角洲,不但造成了滨海千里荒无人烟的历史悲剧,而且使得“隆庆开禁”后稍有复苏的外贸业又遭到毁灭性打击。即便是大清后来放松“海禁”,也是有条件、有地点、以收税为目的、在朝廷主导下的放松。所有的海上民间贸易,都被视为“海盗”,都属于禁止的范围;所有远洋的华商海船,无论运送了多少中国商品,都不受大清保护。与此相反,西方国家一直用武力支持商人开拓市场,争夺航线,甚至武装殖民。西方商人在仗剑经商,而中国商人却是非法经营。如此说来,中国民间商船屡屡被外国公司劫持,香料基地和贸易航线全被西方控制,也就怪不得别人了。
在朝廷眼中,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与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一样,不过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免费长城。那漫长的海岸线,是他们无法逾越的精神边界。直到用蒸汽机驱动的、用钢铁打造的、用火炮武装起来的西方舰队逼近中国海岸,尤其是英国炮舰“康华丽号”大摇大摆地游弋在南京下关江面,将火炮对准谈判中的静海寺,用人造的闪电和雷鸣向对方示威的时候,大清官员们才猛然醒悟:大洋原来也是路,而且是最快捷、最宽阔的路——当然只是洋人而非自己的路。
我只有发出一声长叹:郑和下西洋就这样成了一个传奇,也仅仅是一个传奇。
这一声叹息,是萦绕在曾经盛极一时的海上强国心头的噩梦。
难怪梁启超说,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历史也说,郑和之后,再无太仓。明末,娄江上游水利失修,刘家港走向衰落,其枢纽地位被新兴的上海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