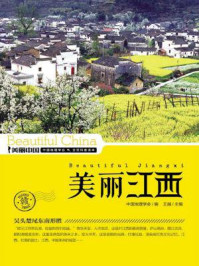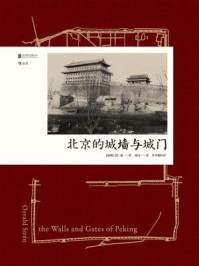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巴蜀文化”概念,在抗战时期提出和形成。“巴渝文化”概念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对近八十年来“巴蜀文化”研究概况和学术史的梳理研究,已有系列成果
 ,但对“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的提出、形成的界定,则歧义纷呈。从“巴蜀文化”到“巴蜀文明”和“巴渝文化”的嬗变研究,则相对阙如。本文拟就此专题做系统梳理和探讨。
,但对“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的提出、形成的界定,则歧义纷呈。从“巴蜀文化”到“巴蜀文明”和“巴渝文化”的嬗变研究,则相对阙如。本文拟就此专题做系统梳理和探讨。
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有三种说法:一是以卫聚贤于1941年发表《巴蜀文化》一文为标志
 ;二是郭沫若“是提出巴蜀文化研究概念的第一人”
;二是郭沫若“是提出巴蜀文化研究概念的第一人”
 ;三是认为卫聚贤、王国维二人提出了“巴蜀文化”概念
;三是认为卫聚贤、王国维二人提出了“巴蜀文化”概念
 。具体考察从郭沫若到卫聚贤关于“巴蜀文化”概念提出的实际情况,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和形成呈现出一个渐进明晰的历程。
。具体考察从郭沫若到卫聚贤关于“巴蜀文化”概念提出的实际情况,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和形成呈现出一个渐进明晰的历程。
近代“巴蜀文化”的学术研究,发轫于1929年四川广汉县太平场燕氏宅旁大批玉器的发现,以及此后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D.C.Graham)及林名钧对该玉器坑的科学发掘和研究。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旅居日本的郭沫若于1934年7月9日致林名钧的信中提出,“西蜀文化很早就与华北、中原有文化接触”,推论“四川别处会有新的发现,将展现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
 ,谭继和正是据此提出,郭沫若是提出巴蜀文化概念和课题的第一人
,谭继和正是据此提出,郭沫若是提出巴蜀文化概念和课题的第一人
 。显然,郭沫若提出的文化概念是“西蜀文化”,而不是“巴蜀文化”。不过,他已从考古发现的视域将四川作为一个“文化分布”的文化区域,已有“巴蜀文化”的区域认识和意识。但是,“西蜀文化”的概念毕竟不同于“巴蜀文化”。在卫聚贤1941年明确提出“巴蜀文化”之前,除郭沫若对四川具有明显文化区域认识和意识外,徐中舒1940年3月的《古代四川之文化》
。显然,郭沫若提出的文化概念是“西蜀文化”,而不是“巴蜀文化”。不过,他已从考古发现的视域将四川作为一个“文化分布”的文化区域,已有“巴蜀文化”的区域认识和意识。但是,“西蜀文化”的概念毕竟不同于“巴蜀文化”。在卫聚贤1941年明确提出“巴蜀文化”之前,除郭沫若对四川具有明显文化区域认识和意识外,徐中舒1940年3月的《古代四川之文化》
 、顾颉刚1941年5月的《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
、顾颉刚1941年5月的《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
 ,同样是把四川或巴蜀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加以研究。以至当代学者(林向、段渝等)评价顾颉刚一文,首次提出了“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但是,该文并无“巴蜀文化”概念的术语和称谓。文章有“蜀的文化”,甚至以嘲讽的口气评价汉唐以来建构的巴蜀与中原的关系云“简直应该说巴蜀就是中原,而且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了”
,同样是把四川或巴蜀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加以研究。以至当代学者(林向、段渝等)评价顾颉刚一文,首次提出了“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但是,该文并无“巴蜀文化”概念的术语和称谓。文章有“蜀的文化”,甚至以嘲讽的口气评价汉唐以来建构的巴蜀与中原的关系云“简直应该说巴蜀就是中原,而且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了”
 ,全文都是讨论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却不明确称道“巴蜀文化”,可谓有“巴蜀文化”之实,而未正其名。
,全文都是讨论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却不明确称道“巴蜀文化”,可谓有“巴蜀文化”之实,而未正其名。
《说文月刊》3卷4期刊出“巴蜀文化”专号,卫聚贤于该期发表《巴蜀文化》一文,1942年又以《巴蜀文化》之名再次发表。前后两文均以巴蜀青铜器(主要是成都白马寺坛君庙青铜器)为其材料研究巴蜀文化,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卫聚贤在《巴蜀文化》的开篇谈到该文命题的变化,是从《蜀国文化》拓展为《巴蜀文化》:
今年四月余到成都,在忠烈祠街古董商店中购到兵器一二,其花纹为手与心,但只有一二件,并未引起余注意。六月余第二次到成都,又购到数件,始注意到这种特异的形状及花纹,在罗希成处见到十三件,唐少波处见到三件,殷静僧处两件,连余自己搜集到十余件,均为照、拓、描,就其花纹,而草成《蜀国文化》一文。
八月余第三次到成都,又搜集到四五件,在赵献集处见到兵器三件,残猎壶一。林名钧先生并指出《华西学报》第五期(1937年2月出版)有𬭚于图。其花纹类此,购而读之,知万县、什邡(四川)、慈利(湖北)、长杨(湖北)峡来亦有此特异的花纹兵器出土,包括古巴国在内,故又改此文为《巴蜀文化》。

从这两小段叙文可知,卫聚贤在1941年4—8月间三次到成都搜集巴蜀青铜器,在前两次搜集到的约三十件青铜器的基础上已写成《蜀国文化》一文。文章命名的变化缘于卫聚贤第三次到成都,特别是在林名钧引导下得阅《华西学报》一文,始知此类青铜器分布不限于蜀地,也见于古代巴国之地,实为巴蜀青铜器,遂改名《巴蜀文化》。郭沫若于1934年针对广汉出土的玉器提出“西蜀文化”概念,卫聚贤1941年在巴蜀青铜器的搜集、研究基础上提出“巴蜀文化”概念。从郭沫若的“西蜀文化”到卫聚贤的“蜀国文化”进而“巴蜀文化”的提出,直接的导因无疑是玉器、青铜器等新的出土材料,为巴蜀区域文化的认识提供了可信的佐证。而这一概念提出的认识背景,也呈现出从郭沫若到徐中舒、顾颉刚对四川、巴蜀整体文化区域的认识。卫聚贤在《巴蜀文化》开篇中专门谈到1940年4月重庆江北汉墓的发现以及重庆各地的崖墓
 。而该期《巴蜀文化》之后的文章,则是郭沫若《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文中详叙与卫聚贤一同赴江北培善桥发现汉墓的经过。由此可知,郭沫若的关于四川文化区域的认识对卫聚贤“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应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明确提出“巴蜀文化”概念的,毕竟是卫聚贤,而不是郭沫若,也不是顾颉刚。
。而该期《巴蜀文化》之后的文章,则是郭沫若《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文中详叙与卫聚贤一同赴江北培善桥发现汉墓的经过。由此可知,郭沫若的关于四川文化区域的认识对卫聚贤“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应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明确提出“巴蜀文化”概念的,毕竟是卫聚贤,而不是郭沫若,也不是顾颉刚。
当明确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提出的实际情况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这一概念形成和确立的标志是什么?
学界对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更多的是关注卫聚贤《巴蜀文化》一文对于这一概念的提出,往往忽略刊载该篇论文,并以“巴蜀文化专号”命名的先后两期《说文月刊》。而深入探讨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不仅要关注《巴蜀文化》一文,更须全面深入研究《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所蕴涵的“巴蜀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以及它们对于“巴蜀文化”概念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作用和意义。
《说文月刊》第一期“巴蜀文化专号”出版,是在1941年10月的上海。而第二期“巴蜀文化专号”的出版,则是《说文月刊》西迁重庆后于1942年8月复刊的首期,故特别注明“渝版”。前后两期“巴蜀文化专号”,共刊载25篇文章(零散小文、随笔类不计),另有一篇《冠词》、一篇《复刊词》。显然,这批文章的内容和它们所蕴涵的《说文月刊》编辑思想,应是我们深入考察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基本内涵的主要研究对象。
“巴蜀文化专号”这批文章所反映的“巴蜀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五个基本的要素:巴蜀文化的地位、巴蜀文化的空间内涵、时间内涵、民族内涵和文化内涵。关于巴蜀文化的地位,金祖同在第一期“巴蜀文化专号”刊载的《冠词》中评价:巴蜀文化“于中华文化,实多所贡献。巴蜀之于中国,虽地近边陲,而于学术文物有与中原、吴越相长相成者,安可不加注意者乎”
 ?不仅肯定其历史地位,更将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与下游的吴越文化、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相提并论,在中国区域文化中确立其特定的独到地位。傅振伦《巴蜀在中国文化上之重大供(贡)献》指出:巴蜀“历史上,均有特殊的供(贡)献,而自成一系统”,文章从石经、雕版、陶瓷、织造、钱币交子等九个方面论述巴蜀古代文化的贡献和地位
?不仅肯定其历史地位,更将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与下游的吴越文化、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相提并论,在中国区域文化中确立其特定的独到地位。傅振伦《巴蜀在中国文化上之重大供(贡)献》指出:巴蜀“历史上,均有特殊的供(贡)献,而自成一系统”,文章从石经、雕版、陶瓷、织造、钱币交子等九个方面论述巴蜀古代文化的贡献和地位
 ,与金祖同的《冠词》两相呼应。
,与金祖同的《冠词》两相呼应。
第二,巴蜀文化地理空间的范围。《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刊载的文章,就其所涉地理空间范围而论,除少数专类文章外(如葬制、汉墓、汉砖三文),其主要文章为古代四川历史文化研究,也有少量文章扩展到西康、云南、湖北相邻地区。1941年上海出版的“巴蜀文化专号”有数篇巴蜀汉墓文章。此外,又刊载张希鲁《云南昭通的汉墓》一文。1942年重庆出版的第二期“巴蜀文化专号”,载有郑德坤《华西的史前石器》,该文研究的石器分布范围,除以四川为主外,尚有湖北的宜昌(巴东列入四川)、云南元谋、西康雅安和道孚至泸河
 。可见,《说文月刊》“巴蜀文化”的地域范围,是四川省(今四川省、重庆市)和邻省的邻近地区。
。可见,《说文月刊》“巴蜀文化”的地域范围,是四川省(今四川省、重庆市)和邻省的邻近地区。
第三,关于巴蜀文化历史阶段和时限的划分,则多种说法并存。金祖同《冠词》将巴蜀文化划分为“巴蜀古文化”和当代“巴蜀新文化”,并立足抗战“中华新文化”和国家“复兴”的视角,就巴蜀文化的当代意义提出:
溯自抗战军兴,国都西徙……巴蜀一隅,遂成复兴我国之策源圣地,政治、经济、人文学囿,蔚为中心……中华崭然新文化当亦将于此处孕育胚胎,植其始基,继吾辈研究巴蜀古文化而发扬滋长……使巴蜀新文化衍而为中华新文化。

金祖同在《冠词》的开首部分,追述了《华阳国志》《春秋》《蜀王本纪》等文献所记巴蜀两国及两族历史,继而接以两汉、三国、唐宋巴蜀历史文化。显然,金祖同所谓“巴蜀古文化”,就是巴蜀古代历史文化,而“巴蜀新文化”,则是与之相对应的巴蜀现当代文化。可见,金祖同以第一期“巴蜀文化专号”《冠词》名义发表的“巴蜀文化”概念,是包容古今巴蜀地域文化的总称。“巴蜀文化”概念提出的伊始,就包含了“学术文物”之“古文化”和复兴国家民族之“新文化”两种涵义。这是《说文月刊》要担当的历史使命,也是编辑两期“巴蜀文化专号”,提出“巴蜀文化”概念的当代意义。金祖同对“巴蜀古文化”的认识,全面体现在《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的编辑思想之上。第一期“巴蜀文化专号”刊载了11篇论文,除卫聚贤《巴蜀文化》一文以出土青铜器研究为主外,其余9篇为汉代历史、考古方面的文章,《蜀胜志异录》则由先秦秦汉至隋唐。1942年渝版“巴蜀文化专号”刊载14篇文章,专论先秦巴蜀历史考古的文章共计8篇,除汉代研究及一篇记叙文外,其余数篇如《四川古迹之调查》《巴蜀在中国文化上的重大贡献》《钓鱼台访古》均为巴蜀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全不受先秦秦汉的时代限制。可见,抗战时期《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的“巴蜀文化”概念,在其“巴蜀古文化”的内涵之中,是包容了整个古代巴蜀的历史文化,不限于巴人、巴国或蜀人、蜀国的石器、青铜时代。
此外,以先秦秦汉巴蜀历史考古为“巴蜀文化”概念内涵的认识,在《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中也有较为充分、明晰的体现。1942年渝版“巴蜀文化专号”以“说文月刊社”名义发表的《复刊词》云:“三卷四期为巴蜀文化—成都白马寺的兵器,与重庆江北的汉墓。”
 从巴蜀青铜器时期下延至东汉汉墓时代,这应是“说文月刊社”对1941年上海出版的“巴蜀文化专号”关于“巴蜀文化”概念的较为明晰的表述。对于渝版“巴蜀文化专号”(第二期)的具体约稿、编辑工作,缪凤林《漫谈巴蜀文化》开首语云:
从巴蜀青铜器时期下延至东汉汉墓时代,这应是“说文月刊社”对1941年上海出版的“巴蜀文化专号”关于“巴蜀文化”概念的较为明晰的表述。对于渝版“巴蜀文化专号”(第二期)的具体约稿、编辑工作,缪凤林《漫谈巴蜀文化》开首语云:
《说文月刊》迁川继续出版,第一期为“巴蜀文化专号”,专考秦汉以前的巴蜀文物,聚贤一定要我为该专号写一篇论文。我说:“历史上对于巴蜀文化的记载,始于汉人,近世发现的巴蜀文物,我所见所知的,亦以汉代者为多,我不能凭空恣论汉前的巴蜀文化,我只能据汉代的记载和遗物,对于古代的巴蜀文化作一个合理的推测。”因草成这篇漫谈。

从这一段说明可以看到,缪凤林的“巴蜀文化”概念在其历史阶段的划分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卫聚贤《巴蜀文化》一文为代表的,“专考秦汉以前的巴蜀文物”的“汉前的巴蜀文化”,这是与《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中关于广汉玉器、巴蜀青铜器、华西史前石器等系列文章相对应的特定内涵;二是除先秦时期外,也包括秦汉的巴蜀文化。缪凤林《漫谈巴蜀文化》一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秦灭巴蜀以降战国秦汉时期的巴蜀历史文化。此类划分,与该期“说文月刊社”发布的《复刊词》对巴蜀文化时段的认识,最为接近。
第四,关于“巴蜀文化”概念的民族(族群)与文化内涵。缪凤林从民族的视角将巴蜀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他说:“狭义的巴蜀,指的是‘巴人’‘蜀人’或‘巴国’‘蜀国’”,“广义的巴蜀,则除巴人蜀人或巴国蜀国外,《史记》和《汉书》西南夷所列举的西夷南夷,亦皆计入”
 。这与《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将四川相邻的少数民族地区,如西康、云南等地作为同一文化区加以研究,在民族和族群内涵的认识应相一致。“巴蜀文化”概念的文化内涵,《说文月刊》分为两类:一是具学术意义的“巴蜀古文化”,二是当代现实意义的“新文化”。金祖同在《冠词》中呼吁:中华新文化“继吾辈研究巴蜀古文化而发扬滋长……使巴蜀新文化衍而为中华新文化”
。这与《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将四川相邻的少数民族地区,如西康、云南等地作为同一文化区加以研究,在民族和族群内涵的认识应相一致。“巴蜀文化”概念的文化内涵,《说文月刊》分为两类:一是具学术意义的“巴蜀古文化”,二是当代现实意义的“新文化”。金祖同在《冠词》中呼吁:中华新文化“继吾辈研究巴蜀古文化而发扬滋长……使巴蜀新文化衍而为中华新文化”
 。显然,金祖同的巴蜀“古文化”和“新文化”具有不同的涵义。巴蜀“古文化”是“学术文物”的传统文化,它在“发扬滋长”“中华新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彰显了极为重大的当代意义;巴蜀“新文化”当与抗战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华新文化”相衔接,即赋予了极为神圣的时代使命。
。显然,金祖同的巴蜀“古文化”和“新文化”具有不同的涵义。巴蜀“古文化”是“学术文物”的传统文化,它在“发扬滋长”“中华新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彰显了极为重大的当代意义;巴蜀“新文化”当与抗战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华新文化”相衔接,即赋予了极为神圣的时代使命。
综而言之,“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从郭沫若、徐中舒、顾颉刚到卫聚贤,有一个渐进发展和明晰的进程,但明确提出“巴蜀文化”的是卫聚贤;而“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的形成,则以1941年和1942年两期《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系列文章的出版为标志。抗战时期形成的“巴蜀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丰富而宽广,包括诸多要素:在构成中华文化的各主要地域文化中,巴蜀文化具有独特的地位;巴蜀文化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仅限于古“巴国”“蜀国”和“巴人”“蜀人”,广义的除四川、重庆外,也包括相邻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巴蜀文化包容古今,可分为巴蜀“古文化”和“新文化”。巴蜀“古文化”主要为“学术文物”意义,其时间划分三说并存:先秦时期“专考秦汉以前的巴蜀文物”;包容秦两汉,从先秦迄两汉;由先秦迄明清,跨越整个古代。在抗战“国府西迁”,巴蜀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背景下,研究巴蜀“古文化”,对于“发扬滋长”巴蜀“新文化”和“中华新文化”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巴蜀文化的研究和发扬,在抗战特定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考古发掘和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以及巴蜀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巴蜀文化”概念的嬗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指向性。以“文革”十年为限,“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为一阶段,“文革”后的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为一阶段。“巴蜀文化”概念嬗变的指向性呈现出两个趋向:一是在抗战时期形成的概念内涵基础上深化、丰富和拓展;二是以成渝两地学者群为主体,分别由“巴蜀文化”向“巴蜀文明”“巴渝文化”新的区域文化概念提升和衍展。
抗战时期对于卫聚贤等人提出“巴蜀文化”概念的质疑和争议,在20世纪50年代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等同类青铜器出土的科学发掘证据前而销声匿迹。顾颉刚在抗战时提出的“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得到坚实的支持。正是在50年代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巴蜀文化”研究在60年代出现了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邓少琴、缪钺、任乃强“第一次学术群体性创获”
 ,形成一批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巴蜀文化”概念予以明确的界定,从这时期的研究成果范畴可知,先秦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历史文化是他们主要的研究领域。
,形成一批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巴蜀文化”概念予以明确的界定,从这时期的研究成果范畴可知,先秦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历史文化是他们主要的研究领域。
对“巴蜀文化”予以科学界定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童恩正撰的“巴蜀文化”条目:
巴蜀文化—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巴、蜀两族先民留下的物质文化。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境内。其时代大约从商代后期至战国晚期,前后延续上千年。从考古学上确认巴蜀族的物质文化,是建国以来商周考古的一大收获。

林向对童恩正的这一界定评价:“这是第一次对‘巴蜀文化’的科学界定,大致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巴蜀文化’的主流看法……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特别是成都平原及长江三峡诸多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对上述‘巴蜀文化’的表述,应该有所改观了。”他做出修正后的界定如下:
“巴蜀文化”应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巴蜀文化”,即中国西南地区以古代巴、蜀为主的族群先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邻近地区,其时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前后延续上千年。“广义的巴蜀文化”是指包括四川省与重庆市两者及邻近地域在内的、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的、包括地域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

从以上二人的界定中可以看到,“巴蜀文化”概念的内涵有四个最为基本的要素:时间(历史阶段的划分)、空间(地理范围的界定)、族群、文化范畴。
就“巴蜀文化”概念狭义、广义的内涵而论,两位学者的界定均包含了两个极端:狭义之最,童恩正仅限巴蜀二族的物质文化,林向仅限春秋战国时期;而广义之最,以林向“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为其代表。时间是“由古至今”,空间是川、渝两省市及邻近地域,族群是巴蜀两族及各少数民族,文化范畴则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地区文化的总汇”。
林向对“巴蜀文化”狭、广二义划分的方法
 ,受到袁庭栋1991年狭义、广义“两种含义”
,受到袁庭栋1991年狭义、广义“两种含义”
 和段渝“三概念说”即“狭义的巴蜀文化”(“小巴蜀文化”)、“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广义巴蜀文化”(“大巴蜀文化”)
和段渝“三概念说”即“狭义的巴蜀文化”(“小巴蜀文化”)、“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广义巴蜀文化”(“大巴蜀文化”)
 的影响。从童恩正20世纪80年代首次对“巴蜀文化”概念的界定到林向2006年全面修正的二十余年间,是抗战以来“巴蜀文化”概念发展、演变最丰富多样,也最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就“狭义巴蜀文化”而论,有赵殿增从新石器晚期到西汉前期早、中、晚三段划分
的影响。从童恩正20世纪80年代首次对“巴蜀文化”概念的界定到林向2006年全面修正的二十余年间,是抗战以来“巴蜀文化”概念发展、演变最丰富多样,也最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就“狭义巴蜀文化”而论,有赵殿增从新石器晚期到西汉前期早、中、晚三段划分
 ,有袁庭栋“秦统一巴蜀之前”
,有袁庭栋“秦统一巴蜀之前”
 (战国晚期之前)的界定,还有段渝“先秦巴蜀文化”的断定
(战国晚期之前)的界定,还有段渝“先秦巴蜀文化”的断定
 ,也有林向的“春秋战国秦汉的划分”;就“广义巴蜀文化”的划分,袁庭栋提出“广义的是指整个四川古代及近代的文化”
,也有林向的“春秋战国秦汉的划分”;就“广义巴蜀文化”的划分,袁庭栋提出“广义的是指整个四川古代及近代的文化”
 ,谭洛非认为,“巴蜀文化,是指四川省地域内,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包括省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
,谭洛非认为,“巴蜀文化,是指四川省地域内,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包括省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
 。谭继和在“泛巴蜀文化”(即广义巴蜀文化)基础上于2002年提出,“一般说来,巴蜀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巴蜀地区人群生活方式的总和,它包含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史前时代,也包含整个文明时代”
。谭继和在“泛巴蜀文化”(即广义巴蜀文化)基础上于2002年提出,“一般说来,巴蜀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巴蜀地区人群生活方式的总和,它包含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史前时代,也包含整个文明时代”
 。显然,林向于2006年对于“巴蜀文化”的界定,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余年间关于“巴蜀文化”概念研究和界定的一次综合与提炼,具有明确的时代代表性。
。显然,林向于2006年对于“巴蜀文化”的界定,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余年间关于“巴蜀文化”概念研究和界定的一次综合与提炼,具有明确的时代代表性。
将最近这二十多年学术界对于“巴蜀文化”概念的界定和论述与抗战时期的研究比较,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关于“巴蜀文化”概念研究的丰硕成果和极大进步,对“巴蜀文化”概念的科学界定更明晰、规范,其基本内涵构成的主要要素内容的研究更深入、系统,对“巴蜀文化”概念的认识更丰富、多样,从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状态。但是,这些成果的主要论点与抗战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明显的沿袭关系。
对“巴蜀古文化”划分的三种类型的前两种:“专考秦汉以前”历史,与童恩正、段渝的界定相类;而新石器至两汉的研究,则与林向、赵殿增关于“狭义巴蜀文化”的划分相近。金祖同在《说文月刊》“冠词”中将巴蜀文化划分为“古文化”和“新文化”,当应是“广义巴蜀文化”的滥觞。袁庭栋、段渝、林向对巴蜀文化狭义、广义的界定,谭继和对巴蜀文化由古至今六大发展阶段的划分
 ,近十年来四川学界《巴蜀文化通史》的编撰,就其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的思想渊源,均肇始于抗战时期关于“巴蜀文化”的学术思想。
,近十年来四川学界《巴蜀文化通史》的编撰,就其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的思想渊源,均肇始于抗战时期关于“巴蜀文化”的学术思想。
“巴蜀文化”概念嬗变的标志,是“巴蜀文明”和“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与传播,这是近三十年来川渝学术界对于“巴蜀文化”概念最具时代意义的创新和贡献。据段渝的梳理,“巴蜀文明这个概念,是80年代中叶三星堆考古重大发现以后提出来的”
 。自此以后的三十年间,巴蜀文明的探讨成为当代巴蜀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议题和方向,逐步拓展和深入,呈现出一系列学术性、创新性明显的论题,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概念的创新和探索,对巴蜀文化学术研究的推动,起到了尤为关键和重要的作用。
。自此以后的三十年间,巴蜀文明的探讨成为当代巴蜀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议题和方向,逐步拓展和深入,呈现出一系列学术性、创新性明显的论题,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概念的创新和探索,对巴蜀文化学术研究的推动,起到了尤为关键和重要的作用。
“巴蜀文明”提出以后,在其文明概念与巴蜀文化的研究方面,最具学术意义的应是关于长江上游文明起源和区域文明中心的研究。
赵殿增认为,巴蜀文明有一个孕育于石器时代,形成于青铜时代,融合于铁器时代的完整发展过程,是长江上游古文明中心
 。林向在1993年提出,巴蜀文化区以古蜀文明为中心,巴蜀文化区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
。林向在1993年提出,巴蜀文化区以古蜀文明为中心,巴蜀文化区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
 。此后,他分别就“蜀文明”和“巴文明”指出:“夏商周时期的四川盆地和邻近地区是以‘蜀’为核心的‘古蜀文明’的范围。东周时期……‘巴文化’和‘蜀文化’一起,共同构成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古代文明中心—‘巴蜀文化区’。”
。此后,他分别就“蜀文明”和“巴文明”指出:“夏商周时期的四川盆地和邻近地区是以‘蜀’为核心的‘古蜀文明’的范围。东周时期……‘巴文化’和‘蜀文化’一起,共同构成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古代文明中心—‘巴蜀文化区’。”
 巴蜀文明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意义,赵殿增明确提出是中华汉文化的又一源头。林向认为,这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段渝《酋邦与国家的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一书利用“酋邦理论”的方法,将长江上游的巴蜀文明纳入整个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比较研究
巴蜀文明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意义,赵殿增明确提出是中华汉文化的又一源头。林向认为,这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段渝《酋邦与国家的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一书利用“酋邦理论”的方法,将长江上游的巴蜀文明纳入整个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比较研究
 。四川的考古发现成果和四川学者的这些研究成就,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同。2005年10月,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中心主办的“巴蜀文化研究新趋势国际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美国、韩国、日本和国内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五十余位学者参会。巴蜀文化与国家及文明起源是这次会议最为主要的议题。段渝在这次会议论文集《前言》中提出:“近年来,巴蜀文化研究提出了‘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发源地’的崭新论断。”李学勤最近总结:“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可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四川的考古发现成果和四川学者的这些研究成就,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同。2005年10月,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中心主办的“巴蜀文化研究新趋势国际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美国、韩国、日本和国内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五十余位学者参会。巴蜀文化与国家及文明起源是这次会议最为主要的议题。段渝在这次会议论文集《前言》中提出:“近年来,巴蜀文化研究提出了‘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发源地’的崭新论断。”李学勤最近总结:“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可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河北学者沈长云、张渭莲的《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其主题内容均为夏商周黄河流域的国家起源,唯一例外,是专章讨论的《三星堆与古蜀文明—上古中原以外早期国家的探讨》
河北学者沈长云、张渭莲的《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其主题内容均为夏商周黄河流域的国家起源,唯一例外,是专章讨论的《三星堆与古蜀文明—上古中原以外早期国家的探讨》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原以外”的探讨,是以“古蜀文明”为其代表。该著所依托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三星堆考古发掘材料,二是赵殿增、段渝等四川学者的研究成果。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原以外”的探讨,是以“古蜀文明”为其代表。该著所依托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三星堆考古发掘材料,二是赵殿增、段渝等四川学者的研究成果。
关于“巴蜀文化”和“巴蜀文明”两概念的关系,谭继和认为,“巴蜀文化是比巴蜀文明广泛得多的概念”。“但它(巴蜀文明)是比巴蜀文化更高一个层次的概念。”“巴蜀文明”概念的定义很难界定,“大体说来,巴蜀人行为的作用方式,思维的体验方式,知识的积累方式和智慧的创造方式,应该是巴蜀文明史研究的范畴”。所以,他在2002年提出编撰《巴蜀文明史》,并将巴蜀文化的发展划分为六大阶段:一是巴蜀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诞生和形成的阶段,大体包括从距今4500年的宝墩文化时期直到三星堆文化一、二期;二是巴蜀文明初步发展的古典期,商周至战国时期;三是秦汉至唐宋,巴蜀文明出现两次鼎盛时期;四是明清时期巴蜀文明的蜕变和沉暮;五是近代巴蜀文化的式微和开新期;六是巴蜀文化的现代化时期
 。在2013年举办的“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上,谭继和《巴蜀文化概说》将“巴蜀文明”划分为“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巴蜀“农业文明”发生于岷山河谷,开始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三角地带。“巴蜀城市文明形成于4500年前”,它的形成和发展,“同巴蜀山水有直接的关系”。巴蜀四塞的盆地封闭环境,激励、培育了巴蜀人冲出盆地,“开拓与开放,兼蓄与兼容”的“集体文化性格”。所以,巴蜀文化基本性质的形成和发展,是巴蜀“这两种城乡文明基因与方式长期对立统一和矛盾运动的结果”
。在2013年举办的“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上,谭继和《巴蜀文化概说》将“巴蜀文明”划分为“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巴蜀“农业文明”发生于岷山河谷,开始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三角地带。“巴蜀城市文明形成于4500年前”,它的形成和发展,“同巴蜀山水有直接的关系”。巴蜀四塞的盆地封闭环境,激励、培育了巴蜀人冲出盆地,“开拓与开放,兼蓄与兼容”的“集体文化性格”。所以,巴蜀文化基本性质的形成和发展,是巴蜀“这两种城乡文明基因与方式长期对立统一和矛盾运动的结果”
 。谭继和对“巴蜀文明”的界定,主要偏向于精神文明层面,“巴蜀文明”的内涵应更为宽广。但是,他对巴蜀文化历史发展六大阶段的划分颇具创见,特别是对长达三千余年的农业文明四个阶段的界定,基本符合巴蜀文化和巴蜀文明发展的实际。此外,谭继和认为文化是比文明“广泛得多的概念”和“巴蜀文明”是比“巴蜀文化更高一个层次的概念”的认识,在中国文化史和文明史研究中有充分的依据。“巴蜀文化”和“巴蜀文明”无疑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构成部分,二者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的共性。就中华文化和“巴蜀文化”的起源而论,均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而中华文明和“巴蜀文明”的起源,受文明概念诸要素(城市、文字、金属器、大型礼仪)和社会政治组织演进的限定,长时期与国家加以联系。正是“酋邦理论”的运用,使文明起源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国家”时期。所以,谭继和对“巴蜀文化”和“巴蜀文明”关系的界定,前者为“广”,后者则“高”,二者紧相联系而又有所区别,可谓把握住了两个概念的实质。
。谭继和对“巴蜀文明”的界定,主要偏向于精神文明层面,“巴蜀文明”的内涵应更为宽广。但是,他对巴蜀文化历史发展六大阶段的划分颇具创见,特别是对长达三千余年的农业文明四个阶段的界定,基本符合巴蜀文化和巴蜀文明发展的实际。此外,谭继和认为文化是比文明“广泛得多的概念”和“巴蜀文明”是比“巴蜀文化更高一个层次的概念”的认识,在中国文化史和文明史研究中有充分的依据。“巴蜀文化”和“巴蜀文明”无疑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构成部分,二者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的共性。就中华文化和“巴蜀文化”的起源而论,均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而中华文明和“巴蜀文明”的起源,受文明概念诸要素(城市、文字、金属器、大型礼仪)和社会政治组织演进的限定,长时期与国家加以联系。正是“酋邦理论”的运用,使文明起源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国家”时期。所以,谭继和对“巴蜀文化”和“巴蜀文明”关系的界定,前者为“广”,后者则“高”,二者紧相联系而又有所区别,可谓把握住了两个概念的实质。
“巴蜀文明”概念的提出,在许多方面推动了巴蜀文化研究的发展,扩大了巴蜀文化的影响。区域文明中心、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等重大课题研究,超越了地域局限,而具全局性的独特意义。
“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迄今已近三十年。以“巴渝文化”名目发表的论著,对于“巴渝文化”的研究和讨论,从未间断。
对于“巴渝文化”概念,有文章提出质疑,可概括为三点:一是认为一个文化概念的形成是严肃、科学的,而“巴渝文化”概念不是诞生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而是重庆设立直辖市以后,适应政治需要和市民心态需要,由重庆媒体的“煽惑”而提出;二是巴渝文化源远流长是一个“虚假命题”,“源”与“流”并不一致,巴族、巴国灭于秦而融入中华文化,已终止于秦;三是“巴渝文化”概念提出后的影响仅限于重庆或川东范围,域外应者寥寥
 。显然,讨论“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对以上质疑无从回避。
。显然,讨论“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对以上质疑无从回避。
关于“巴渝文化”概念提出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问题。追溯“巴渝文化”概念提出、形成的客观历史状况,它与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提出的方式相同,都是历史考古学术界以严肃、科学的精神和态度,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提出。时间不是1997年设立直辖市以后,而是1989年。提出“巴渝文化”概念的,不是重庆媒体的记者,而是重庆历史、考古学界的一批学者。提出这一概念的背景和目的,不是迎合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政治需要,也不是适应什么市民心态,而是“巴蜀文化”“巴文化”学术研究内在发展与三峡文物抢救性保护的社会推动双重因素的结果。
从1989年重庆市博物馆编辑的第一辑《巴渝文化》论文集正式出版(重庆出版社,1989年),到1999年第四辑《巴渝文化》的出版
 ,在10年时间内,一百一十余篇关于“巴蜀文化”和“巴渝文化”的历史考古类学术论文以《巴渝文化》刊名连续出版四辑专集,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是重庆“巴渝文化”概念提出的集合方式,也是这一概念形成的学术基础和标志。设立直辖市之后媒体与相关方面推动的“巴渝文化”的宣传,无论其理性的探讨,或其他方式的报道,都根植于此前近十年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成果。
,在10年时间内,一百一十余篇关于“巴蜀文化”和“巴渝文化”的历史考古类学术论文以《巴渝文化》刊名连续出版四辑专集,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是重庆“巴渝文化”概念提出的集合方式,也是这一概念形成的学术基础和标志。设立直辖市之后媒体与相关方面推动的“巴渝文化”的宣传,无论其理性的探讨,或其他方式的报道,都根植于此前近十年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成果。
关于“巴渝文化”的“源”与“流”是否一致的问题,这是中国区域文化,特别是长江流域及整个中国南方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共通性问题。中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在秦汉时期的形成,就是建立在先秦诸多方国、民族的融合之上。除中原黄河流域华夏文化区外,长江流域的巴蜀、荆楚、吴越都经历了由先秦方国文化和民族文化向秦汉大一统下的地域文化的转型,这不是源与流不一致问题,而是民族文化融合趋势下的转型问题。“巴渝文化”在其源与流的关系中,与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有着相同的历史轨迹。作为长江流域一个特定地理单元的地域文化,“巴渝文化”的源远流长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熊笃认为,“如果重庆文化要寻找一个能贯通古今历史源流的、代表主流而又具有地域文化个性特色的文化,那就非‘巴渝文化’莫属”
 。可见,“巴渝文化”命题,没有“虚假”,唯有真实。
。可见,“巴渝文化”命题,没有“虚假”,唯有真实。
“巴渝文化”概念的域外影响问题。这一概念提出伊始,在其形成过程中就逐渐为重庆之外的中国学术界所认同,并积极参与相关学术论题的研究和探讨。从出版的四辑《巴渝文化》论文著者的地域和单位构成,我们可以看到“巴渝文化”概念提出的早期,有一个由文博系统向其他学术领域,由市内向市外及全国扩展的过程。1989年出版的第一辑《巴渝文化》刊载近三十篇论文,其作者均为重庆市博物馆或重庆文博系统的研究人员。1991年春,第二辑《巴渝文化》出版,作者除以重庆市博物馆为其主体外,收入西南师大两文(黎小龙、蓝勇)、四川大学一文(张勋燎)。这应是高校和四川成都学者参与《巴渝文化》文集的开端。1993年秋,中国先秦史学会、西南师大历史系(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博物馆等数家单位主办“首届全国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重庆巴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来自北京、河北、四川、山东、陕西等省市历史、考古学专家与重庆学者共计六十余人参会。西南师大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的《巴渝文化》第三辑,即是这次参会论文的特辑。该辑刊载文章34篇,重庆市博物馆和文博系统仅9篇,外地学者15篇,重庆各高校为10篇。其中有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的《巴史的几个问题》。而以“巴渝文化”命名的两篇文章,作者均为外地学者:一是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孟世凯的《巴渝文化琐论》,另一篇则是南京大学张之恒的《巴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这些文章,多为巴渝历史和文化本源性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见,“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在重庆之外的全国学界,其影响绝非质疑者所谓的“应者寥寥”。
应当说,1989年出版的首辑《巴渝文化》,即是“巴渝文化”概念正式提出的标志。从1989年到1994年第三辑《巴渝文化》的出版,5年间先后有八十余篇论文在《巴渝文化》发表。特别是1993年秋“首届全国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对巴渝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和交流。这一系列的成果和学术活动,标志着“巴渝文化”这一概念在重庆设立直辖市以前已正式形成和确立。
在这四辑《巴渝文化》的编撰基础上,刘豫川、杨明在1999年发表《巴渝文化》一文,对“巴渝文化”概念的内涵予以明确的界定:
所谓“巴渝文化”,是指以今重庆为中心,辐射川东、鄂西、湘西这一广大地区内,从夏商直至明清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

对于“巴文化”和“巴渝文化”的关系,文章概括了巴地青铜器、陶器和文字系统“巴人图语”的特点,提出:
这些特点,构成了先秦时期考古学上所谓的“巴文化”。实际上,这一“巴文化”的概念主要是物资(质)的,如果将这一文化概念扩展到当时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诸领域,并经与秦汉汉文化交融,传承发展到隋唐以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巴渝文化”。

以上两小段的概括,应是自“巴渝文化”概念提出以来,最为全面、明确的界定和概括。它们对“巴渝文化”概念基本内涵的诠释极为全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空间、时间、文化。空间,除“今重庆”为中心外,辐射川东、鄂西、湘西,这一地区是古代巴族、巴文化的分布地,已超出了先秦巴国及秦汉巴郡的地理范围;时间,夏商至明清,并不包括民国以来的近现代,“巴渝文化”在其时间内涵上界定为巴渝之地的古代文化;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全都包括在这一文化内涵的界定之中。不过,“巴渝文化”之中还包括了考古学上,仅限先秦时期物质文化的“巴文化”。
1989年第一辑《巴渝文化》出版时,该著正文之前刊登了以“重庆市博物馆《巴渝文化》编委会”名义发布的《编者的话》,摘要如下:
两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重庆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进而广之,一百八十万年前,川东巴渝之地上,就站立着我们的原始先民。其后,部落纷争,王国兴衰,朝代更迭,历史演进,石器、铜器、铁器、大机器渐次发展,乃有今日之川东与重庆。由于地域、人群、历史发展不均衡性等诸多原因,形成了巴渝有个性的文化氛围,蕴于浩茫的历史烟云中。

“巴渝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在这一段“前言”类的说明中,已完全呈现了出来:地理范围,是川东重庆;历史阶段,跨越了石器、铜器、铁器、大机器时代,应是包容古今;文化内涵,由地域、人群、历史发展不均衡等原因形成的,具有“个性”的文化,民族、地域和物质、精神全都包容在内,这里彰显的无疑是大文化的概念。将刘豫川、杨明10年后的“巴渝文化”概念与之比较,区别在两方面:地理空间有所扩大,除川东重庆外,扩展至鄂西、湘西;时间划分加以收缩,仅限铜器、铁器时代(商周至明清)。以“编委会”名义在《巴渝文化》第一辑出版时表述的关于“巴渝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的认识,较为完整地贯彻到以后10年间对于《巴渝文化》4辑的编辑之中。
贯通古今的大文化概念,在《巴渝文化》第一辑的编辑中,即已显现。该辑共刊载28篇论文,大致可划分为重庆古代历史、近现代历史、考古与文物、民族史几类。就时间内涵而论,纵贯古今。《古代重庆》一文的时间上限,追溯至23000年前旧石器晚期的“铜梁文化”。而该辑的时间下限,不仅刊载有一组近现代文章,如《周恩来与郭沫若》《周恩来与抗战时期重庆的话剧运动》等,更有当代传统民间艺术研究,如《四川皮影戏艺术》《蜀艺漫话》。该期唯一一篇以“巴渝文化”命名的,也是“巴渝文化”概念正式提出以后第一篇以之命名的文章,是刘豫川《璀璨的巴渝文化遗迹—重庆市文物普查收获综述》。该文记录的文化遗迹的上限,同样是始于远古旧石器时代的铜梁遗址,继而是新石器时代的江津王爷庙遗址、合川沙梁子遗址、巴县干溪沟遗址等。而遗迹的下限,古遗址和古墓葬注明为1840年,古建筑则下延至清末光绪年间;“近现代重要史迹及近现代代表性建筑”,扩展至“近代开埠到抗战期间作为国民政府陪都及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驻地”所遗留下的“遗址、旧居、纪念地及名人墓葬”
 。显然,该文所蕴涵的“巴渝文化”的时限,是从远古的石器时代,经历铜器、铁器,直至近现代“大机器”时代,这与《巴渝文化》编委会对“巴渝文化”的界定,应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0年后第四辑《巴渝文化》的出版。该辑近三十篇文章分编为5个栏目,在其《目录》分别注明:“巴蜀历史考古”“本土文化研究”“城市文化与近代化”“陪都史研究”“文物保护与研究”,依然是由石器时代至近现代,包括巴渝地区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的综合研究。可见,1989年第一辑《巴渝文化》出版时,编委会表述的“巴渝文化”概念,在这10年先后4辑的《巴渝文化》编辑中,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
。显然,该文所蕴涵的“巴渝文化”的时限,是从远古的石器时代,经历铜器、铁器,直至近现代“大机器”时代,这与《巴渝文化》编委会对“巴渝文化”的界定,应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0年后第四辑《巴渝文化》的出版。该辑近三十篇文章分编为5个栏目,在其《目录》分别注明:“巴蜀历史考古”“本土文化研究”“城市文化与近代化”“陪都史研究”“文物保护与研究”,依然是由石器时代至近现代,包括巴渝地区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的综合研究。可见,1989年第一辑《巴渝文化》出版时,编委会表述的“巴渝文化”概念,在这10年先后4辑的《巴渝文化》编辑中,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
但是,深入探究这4辑一百一十余篇文章,与《巴渝文化》编委会关于“巴渝文化”概念不同的认识和界定,集中出现在1993年“首届全国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综合这次学术研讨会关于“巴渝文化”概念的讨论,有以下数种观点:一是“巴渝文化”与“巴文化”的关系,以及“巴文化”有微观、宏观划分说法的提出。管维良提出:“巴渝文化是否就是巴文化?……现在所论的巴渝文化与古代巴渝地区的文化是否是一回事。”并认为,“宏观巴文化是……一种具有大跨度时间,大跨度空间的大文化”。从时间角度,应由古迄今;“从空间上,凡出有巴文物的地方,或文献记载巴人活动过的地方;从内容上讲,凡与巴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皆属于巴文化的范畴”
 。这一界定,大体与《巴渝文化》编委会的表述相近。不过,管维良的着眼点是古代的巴,而编委会的着眼点是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川东、重庆)的地域文化。二是“巴渝文化”历史阶段划分出现与编委会截然不同的观点。孟世凯认为,巴渝文化“有一个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巴渝历史文化是颇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是“古代巴渝先人所创造的历史文化”
。这一界定,大体与《巴渝文化》编委会的表述相近。不过,管维良的着眼点是古代的巴,而编委会的着眼点是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川东、重庆)的地域文化。二是“巴渝文化”历史阶段划分出现与编委会截然不同的观点。孟世凯认为,巴渝文化“有一个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巴渝历史文化是颇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是“古代巴渝先人所创造的历史文化”
 。显然,孟世凯是将“巴渝文化”界定为巴渝地区的古代文化。此外,有将“巴渝文化”界定为先秦两汉时期的。张之恒《巴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考古发掘材料和考古学方法为主,辅以文献记录,认为巴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从新石器时期至商周秦汉,可分为三个阶段:前巴渝文化、早期巴渝文化、晚期巴渝文化
。显然,孟世凯是将“巴渝文化”界定为巴渝地区的古代文化。此外,有将“巴渝文化”界定为先秦两汉时期的。张之恒《巴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考古发掘材料和考古学方法为主,辅以文献记录,认为巴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从新石器时期至商周秦汉,可分为三个阶段:前巴渝文化、早期巴渝文化、晚期巴渝文化
 。
。
可见,刘豫川、杨明在1999年对“巴渝文化”概念的界定,应是建立在“巴渝文化”概念提出10年以来,对各种观点的综合与概括之上,既是对《巴渝文化》编委会表述的修正,也是对这时期有关“巴渝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思考、认识的概括。
不过,《巴渝文化》四期专辑所奠定的,关于“巴渝文化”历史阶段的界定,逐渐成为具有主流概念的认识,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余楚修在2000年提出,“巴渝文化……指孕育于巴山渝水间,伴随着这一地区人类语言的产生而产生,在历史长河中发展演变的相对独立的文化”
 。熊笃于2001年将“巴渝文化”归纳为“十大系列”:“巴渝文化源远流长,巫山原始文化、巴族巴国文化、三国文化、丰都鬼神文化、巴渝竹枝词民间文艺、大足石刻艺术、宋末抗元军事文化、明玉珍大夏文化、辛亥革命文化、陪都及红岩文化等构成了巴渝文化的完整系列。”
。熊笃于2001年将“巴渝文化”归纳为“十大系列”:“巴渝文化源远流长,巫山原始文化、巴族巴国文化、三国文化、丰都鬼神文化、巴渝竹枝词民间文艺、大足石刻艺术、宋末抗元军事文化、明玉珍大夏文化、辛亥革命文化、陪都及红岩文化等构成了巴渝文化的完整系列。”
 2005年《论“巴渝文化”是贯通重庆古今的主流文化》进一步诠释其大文化观概念
2005年《论“巴渝文化”是贯通重庆古今的主流文化》进一步诠释其大文化观概念
 。2006年6月,在由重庆市社科联、重庆师范大学主办的“巴渝文化研讨会”上,曾繁模对“巴渝文化”作了最为简要的概括,“巴渝文化应是指以今重庆为中心包括周边地区从古至今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
。2006年6月,在由重庆市社科联、重庆师范大学主办的“巴渝文化研讨会”上,曾繁模对“巴渝文化”作了最为简要的概括,“巴渝文化应是指以今重庆为中心包括周边地区从古至今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
 。此外,薛新力
。此外,薛新力
 、胡道修
、胡道修
 均在这时期著文,阐释和认同巴渝文化贯通古今的大文化观。
均在这时期著文,阐释和认同巴渝文化贯通古今的大文化观。
在“巴渝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讨论的同时,“巴渝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另一个议题。2000年春,余楚修《巴渝文化刍议》指出:“巴蜀文化”仅指“华阳地区的一种地域性的青铜文化”,“其亚文化只能是巴文化、蜀文化,决不是巴渝文化”
 。薛新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巴渝文化与蜀文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化”,“巴渝文化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地区文化”
。薛新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巴渝文化与蜀文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化”,“巴渝文化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地区文化”
 。熊笃系统梳理了巴与蜀3000年间的“文明进程史”,认为“巴与蜀在行政区划上经历了九分九合。分,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个性;和,产生了交融的文化共性”。“‘巴蜀文化’这个概念就其共性而言固可成立;而‘巴渝文化’这个概念就其个性而言,同样可以成立”
。熊笃系统梳理了巴与蜀3000年间的“文明进程史”,认为“巴与蜀在行政区划上经历了九分九合。分,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个性;和,产生了交融的文化共性”。“‘巴蜀文化’这个概念就其共性而言固可成立;而‘巴渝文化’这个概念就其个性而言,同样可以成立”
 。进入21世纪初期的关于“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关系的讨论,应是对前10年“巴渝文化”概念提出和形成的深化与拓展,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巴渝文化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初期的关于“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关系的讨论,应是对前10年“巴渝文化”概念提出和形成的深化与拓展,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巴渝文化的研究。
近十年来,四川、重庆分别确立和开展“巴蜀全书”和“巴渝文库”的重大文化工程,对巴蜀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指导和影响这两项文化工程的,则是“巴蜀文化”和“巴渝文化”的概念和基本内涵。在“巴渝文库”的第一个项目《巴渝文献总目》的开展和研讨进程中,与“巴渝文化”概念直接相关的议题,就是对巴渝历史阶段和地理空间的界定。经多次讨论,该著《凡例》将地理范围确定为:古代以秦汉时期的巴郡、晋《华阳国志》所指“三巴”为限,民国时期以重庆直辖后的行政区划为基础,根据民国时期的地理建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张弛;时间范围:上溯先秦,下迄民国
 。在《巴渝文献总目》的讨论和审定中,系统梳理抗战以来关于“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的形成及嬗变,成为大家的共识。最终由蓝锡麟撰写的“总序”中,关于“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关系的论述,颇具新意。他提出:“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种属关系,彼此间有同有异,可分可合……自古及今,巴蜀文化都是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同一层级的长江流域的一大地域历史文化,巴渝文化则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巴渝文化之于巴蜀文化具有某些异质性……就构成了巴渝文化的特质性。以此为根基,在尊重巴蜀文化对巴渝文化的统摄地位的前提下,将巴渝文化切分出来重新观照,合情合理,势在必然。”
。在《巴渝文献总目》的讨论和审定中,系统梳理抗战以来关于“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的形成及嬗变,成为大家的共识。最终由蓝锡麟撰写的“总序”中,关于“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关系的论述,颇具新意。他提出:“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种属关系,彼此间有同有异,可分可合……自古及今,巴蜀文化都是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同一层级的长江流域的一大地域历史文化,巴渝文化则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巴渝文化之于巴蜀文化具有某些异质性……就构成了巴渝文化的特质性。以此为根基,在尊重巴蜀文化对巴渝文化的统摄地位的前提下,将巴渝文化切分出来重新观照,合情合理,势在必然。”
 这些观点和认识,可谓近十年“巴渝文化”研究最具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论述。
这些观点和认识,可谓近十年“巴渝文化”研究最具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论述。
1989年提出的“巴渝文化”概念,在重庆设立直辖市以后在社会广为传播,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仅直接推动文化的繁荣,也为学术发展带来活力。学术思想的创新,可谓意义非凡。
探究1989—1999年期间,“巴渝文化”概念提出和形成的原因,可归结为“巴蜀文化”“巴文化”研究发展的内在学术推动,以及三峡工程和三峡文物保护的紧迫性带来的区域文化意识的增强。正是在这内外两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和影响下,“巴渝文化”概念在这时期得以提出和确立。
抗战以来的“巴蜀文化”研究,对于巴、蜀两个在历史和自然地理上紧相联系,又各具特色、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的探讨,已是每个时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共通现象。除综合性问题的讨论外,凡需深入研究,均有“巴文化”“蜀文化”的专题性讨论。此类现象,从抗战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前期。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重庆继徐中舒、冯汉骥、邓少琴之后的第二代学者,如董其祥、管维良、彭伯通等将主要努力集中于“巴文化”的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成果。当三星堆、十二桥遗址等新的考古发现推动四川学者的巴蜀文化研究步入“古蜀文明”“巴蜀文明”的探讨时,重庆历史考古学界则从“巴文化”逐渐向“巴渝文化”研究嬗变。成渝两地学者关于“巴蜀文化”研究中的地域文化概念的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这一时段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流。这一学术现象的内在推动因素,仍然植根于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发展和学术研究。
就外在社会因素而论,三峡工程与三峡文物的保护,对于重庆“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和推动。1989年首辑《巴渝文化》的近三十篇文章中,载有刘豫川《璀璨的巴渝文化遗迹—重庆市文物普查收获综述》
 ,这篇文章内容是根据1987年以来一年多全市文物普查,对重庆市文物遗迹的总结性综述。但用名“巴渝文化遗迹”,足见“巴渝文化”的提出,与重庆的文物保护有直接的关系。而这时期的文物普查,在重庆和三峡地区,随着三峡工程的论证,文物的抢救性保护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10年后,当《巴渝文化》第四辑于1999年出版时,第一篇文章是王川平的《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重庆文博事业》,所列重庆下一步的文物工作中的第二项,即是“继续抓好三峡文物抢救工作”。文章指出,“世界的舆论在看着我们,全国人民在关注着三峡文物”
,这篇文章内容是根据1987年以来一年多全市文物普查,对重庆市文物遗迹的总结性综述。但用名“巴渝文化遗迹”,足见“巴渝文化”的提出,与重庆的文物保护有直接的关系。而这时期的文物普查,在重庆和三峡地区,随着三峡工程的论证,文物的抢救性保护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10年后,当《巴渝文化》第四辑于1999年出版时,第一篇文章是王川平的《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重庆文博事业》,所列重庆下一步的文物工作中的第二项,即是“继续抓好三峡文物抢救工作”。文章指出,“世界的舆论在看着我们,全国人民在关注着三峡文物”
 。重庆文博界和学术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使命和文化责任下,强化重庆和三峡的区域意识,提出“巴渝文化”的概念。这既是学术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三峡文物保护这个特定时期社会和区域发展的需要。
。重庆文博界和学术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使命和文化责任下,强化重庆和三峡的区域意识,提出“巴渝文化”的概念。这既是学术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三峡文物保护这个特定时期社会和区域发展的需要。
当我们系统梳理了近三十余年关于“巴蜀文化”概念的嬗变之后,我们必须不无遗憾地指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前期“巴蜀文化”概念的衍展、嬗变最为丰富多彩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川渝两地学界所关注的焦点,不仅出现明显的分流,而且各自坚守自己研究的命题,双方甚少交流互动。四川学界专注于“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重庆学界则热衷于“巴渝文化”。四川的学者,即便追溯抗战以来“巴蜀文化”的研究,以至近来“巴蜀文明”的探讨,却共同忽略了同一时期重庆学界热烈讨论的“巴渝文化”。重庆的学者,即便三峡考古取得丰硕成果,成都学者在“巴蜀文明”研究中运用三峡考古材料探讨“峡江流域文明的起源”
 ,也没有参与诸如巴蜀区域文明中心、长江上游文明起源和文明进程的研究及讨论。在近二十多年时间内,当四川、重庆以外的全国不少学者积极参与“巴蜀文明”和“巴渝文化”的研究和讨论时,相形之下,川渝两地学界在巴蜀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却呈现高度默契的分离。这样奇特的学术现象,可谓“巴蜀文化”和“巴渝文化”学术史上的奇葩,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也没有参与诸如巴蜀区域文明中心、长江上游文明起源和文明进程的研究及讨论。在近二十多年时间内,当四川、重庆以外的全国不少学者积极参与“巴蜀文明”和“巴渝文化”的研究和讨论时,相形之下,川渝两地学界在巴蜀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却呈现高度默契的分离。这样奇特的学术现象,可谓“巴蜀文化”和“巴渝文化”学术史上的奇葩,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新的资(材)料的发现、学术研究的发展以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通常会带来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的创新。抗战时期“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都学者关于“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的探讨、重庆学者关于“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研究,都是学术发展和社会推动双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学术理念和概念的创新,如“巴蜀文化”“巴蜀文明”和“巴渝文化”的提出和传播,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和繁荣,扩大和提高了地域文化的影响,更成为川渝两地促进社会进步,推动社会文化繁荣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