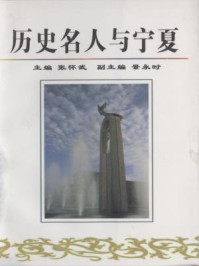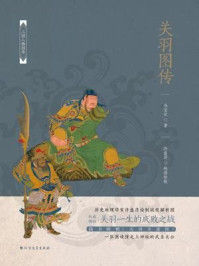以苏轼的个性,心里有话必得一吐为快,如若不然,就像吃了苍蝇一般难受。对陈公弼的不满,他终于逮着了一个尽情发泄的机会。
治平元年(1064),陈公弼在凤翔建的凌虚台落成,请苏轼写一篇文。这对苏轼当然不是难事,他洋洋洒洒写下一篇《凌虚台记》,文中暗藏机锋,讽刺陈公弼想凭建凌虚台扬名于世、自我满足。
让苏轼意外的是,这篇《凌虚台记》陈公弼居然不改一字,当即命人刻于石上,立在凌虚台处。后来,苏轼才明白,陈公弼原来是一个面冷心热之人,他之所以这样对苏轼,实则是出于爱护之心,担心他年纪轻轻、才名太盛而过于自满张扬。
原来,笑容不全是友善,冷脸也不全是恶意,就如同白天并不全是光明,夜晚也不等同于黑暗。这就是世道人心的真相。多年以后,极少给人写传记与墓志的苏轼,为陈公弼写下一篇长长的传记,文中表达了因自己当年不懂陈公苦心而愧疚的心情。
苏轼与陈公弼,都是真君子,他们之间并无大是大非的根本性矛盾。苏轼的才干、品性都令陈公弼深为欣赏,而陈公弼为官也令苏轼深感钦敬。他从这位上司身上,看到了丰富的人性,更学到了正直为官之道。
时光流逝中,苏轼对陈公弼的了解日渐加深,但他的三年任期已满,要另派别处。
离开前,苏轼带着满满的怀恋,回望自己的凤翔岁月。这三年中,他努力工作,从两位上司身上学到了许多为官之道,为民众做了很多实事,卓越的政绩背后,劳苦与幸福交杂。繁重公务之余,他在凤翔四处观览古迹,除了“石鼓”,还有秦碑“诅楚文”、王维和吴道子的画、唐代著名雕刻家杨惠之塑的维摩像、真兴寺阁、李氏园、秦穆公墓,他为这六处文物古迹各写下一首诗,与《石鼓歌》《东湖》合称《凤翔八观》。
在凤翔,苏轼也收获了新的友情。苏轼从京城到凤翔上任时,在京结识的朋友马梦得一路追随。旧友固然值得珍惜,新友也值得期待。
嘉祐七年(1062)秋天,苏轼到长安负责进士考试事务时,意外地遇到了当年与他同榜中礼部进士的章惇。两个人年纪相当,才华、志气都非同一般,通过这次考务工作而变得熟悉起来,很快成了好友。
据说两人一同出游时,章惇曾毫无惧色地走过万丈深渊上的独木桥,也曾若无其事地近距离敲响铜锣吓退老虎。他笑话苏轼胆小,苏轼却开玩笑说他将来会杀人,章惇听后哈哈一笑。章惇与苏轼个性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友情。
新结交的另一位朋友,其实可算旧识。
嘉祐五年(1060),苏洵在京城为官时与文同是同事。苏轼与文同早就听说过彼此,但一直未见面。直到四年后,文同为父守丧期满,赴汉州(今四川广汉)任职,途经凤翔,才有了与苏轼见面订交的机会。二十九岁的苏轼与四十七岁的文同,个性相契、情趣相投,两人都天真随性、乐观幽默,爱好文学、绘画。他们初见对方便似遇见了另一个自己,很快成了忘年知己。
还有一个人——陈公弼的第四子陈季常,在苏轼后来的人生中也颇为重要。
一次在西山,苏轼见陈季常策马一箭射中飞鸟,深为陈季常身上的侠气所动,便与他在马上谈起了用兵之道与古今成败之事。其时与陈公弼的关系,并未影响到苏轼与陈季常的交往。苏轼用坦荡广阔的襟怀,无意中为未来储蓄了一份福泽。
每一段友情,都是人生变幻的伏笔。友谊的走向,无法预知,也无从掌控。有的人,相伴终生,不离不弃;有的人,中途离散,悄无声息;有的人,是上苍珍贵的馈赠;有的人,成了命运莫名的暗涌。
于热爱交友的苏轼来说,马梦得、章惇、文同、陈季常,会在他未来的人生中扮演什么角色,目前还不得而知。他只知道,友情是人生中重要的部分之一。
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回到京城。新皇帝宋英宗本想召苏轼入翰林院任自己的机要秘书,却遭到了韩琦等重臣的反对,理由是苏轼年纪太轻、资历太浅,需要多多磨炼。英宗于是改任苏轼为直史馆,负责编修国史。
正当苏轼在朝中准备大展其才,想要有所作为时,天大的不幸接连降临——这一年五月,陪伴了苏轼十一年的妻子王弗,在京突然染疾离世,年仅二十七岁。丧妻之痛还未复原,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又与世长辞。不到一年,痛失两位至亲之人,苏轼内心的悲伤可想而知。
在苏辙的陪伴下,苏轼护送父亲和妻子的灵柩回眉州安葬。故乡风物清美依旧,但在苏轼眼中却有些苍凉。母亲离开以后,这个家就显得空荡了许多,如今又少了两个人。
熙宁元年(1068),因为年幼的苏迈无人照顾,守孝期满的苏轼续娶了二十一岁的王闰之。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眉州青神人。她身上虽少了些书卷气,但柔顺活泼、聪明干练又体贴周到,对苏迈视若己出。虽心底仍不能忘怀王弗,但苏轼选择面对现实,努力去呵护与王闰之的感情,很快再度拥有了和美的家庭。
丧服已除,继室已娶,苏轼和苏辙离开眉州赶往京城。如果苏轼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看见家乡的山水,如果他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会不会选择留下来,去实现多年前心底那个归隐山林的梦?
然而,人生不能未卜先知,人生也没有如果,这条漫长又短暂的单行道上,处处峰回路转、花明柳暗。此时的苏轼,满身才华还未完全放射光华,致君尧舜的最高理想还未实现,他只能坚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