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形象描绘了六朝佛教的繁盛景象;而作为“六代帝王都”的建康城,在佛法东传中土的最初几百年里,一直是包括魏晋般若学在内的几大佛学思潮的重镇;加之,梁武帝在中国佛教制度上的诸多首创,以及活跃于建康的“六朝四大家”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都从不同侧面彰显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京佛教文化的中心地位。
佛教在南京的传播,最早可溯至东吴黄龙元年(229)支谦在建业翻译佛经、传授佛教。东吴赤乌十年(247),孙权为康僧会建造有“江南第一寺”之称的建初寺。东晋义熙九年(413),法显西行取经归来,抵达建康,写成《佛国记》一书。宋泰始年间,明僧绍于摄山结庐念佛,取名“栖霞精舍”。刘宋末年,僧绍舍宅为寺,以奉来自北燕黄龙之法度禅师,遂有“栖霞寺”。此外,梁武帝于南朝梁天监十二年(513)撰《断酒肉文》,并先后四次下诏,强令僧尼一律遵守,由此形成僧侣素食的传统。梁大同四年(538),梁武帝设盂兰盆会,后逐渐形成汉传佛教重要之礼仪风俗。梁武帝与达摩祖师因“功德”之论,话不投机,遂一苇渡江至长芦寺、定山寺,后驻锡定山寺,定山寺遂成“达摩第一道场”。在谈论中国佛教史时绕不过去的这些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建业、建康。说六朝时的南京是全国佛教的中心,诚非过言。
中国佛教史上曾有“南义北禅”一说,即南方注重义理,北方强调禅定。而佛学“义理”之重镇或中心,则非南京莫属。作为佛教义理两大流派之“中观学”与“涅槃学”,都曾经以建康为舞台,上演了一场堪称波澜壮阔的论辩与弘阐。齐永明七年(489),僧朗法师自辽东来,大弘“三论”,世称江南三论之祖;僧诠、法朗诸师继之,其学益盛,遂成“三论宗”之祖庭。涅槃师依据《大般涅槃经》,阐发弘扬涅槃佛性论,至竺道生倡“众生有性”和“顿悟成佛”而达到一个新高潮。其中尤以竺道生的涅槃佛性论对于整个中国佛教往后发展的影响至深至巨。隋唐佛教的几大宗派(尤其是天台、华严与禅宗)之所以均倡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以顿悟为极致,都与竺道生的佛性理论有密切的关联。另外,六朝的成实学派、毗昙学派也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因此,赵朴初先生曾有“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和南京有关”一说。
创建于陈隋之际的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宗派。它的实际创始人是“智者大师”。陈光大元年(567),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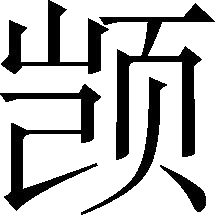 赴建康讲经说法、弘扬教观,受到了朝野僧俗的欢迎与敬重。太建元年(569),智者大师被朝廷迎请住进瓦官寺,前后长达八年。在瓦官寺,智
赴建康讲经说法、弘扬教观,受到了朝野僧俗的欢迎与敬重。太建元年(569),智者大师被朝廷迎请住进瓦官寺,前后长达八年。在瓦官寺,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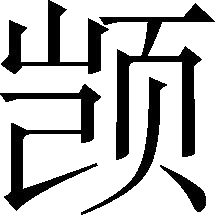 讲经说法,标立宗义,判释经教,为天台宗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讲经说法,标立宗义,判释经教,为天台宗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随着南北割据的结束和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南北文化的交融汇合造成中国佛教思想文化亦呈融合发展之大趋势,天台宗始倡统合南北禅观的“定慧双修”。而佛教般若学由于栖霞三论宗的弘扬再次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李唐盛世时期,中国佛教诸宗并起。有“东夏达摩”之称的法融禅师,在金陵牛首山创立了以“虚空为道本”的牛头宗。牛头宗因其浓厚的老庄化、玄学化特色,曾被印顺长老誉为“中华禅的代表”。后期禅宗在金陵清凉山另开一叶,创立了法眼宗。法眼宗创始人文益禅师被中主迎至金陵讲经说法,后被谥为“大法眼禅师”。在禅宗“五家七宗”中,法眼宗是最后成立的一个宗派,也是思想最具融合性的宗派。
唐五代之后,禅宗一改六祖慧能以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传统,而大兴“公案”“灯录”甚而“颂古”“评唱”,出现了文字禅;之后,随着大慧宗皋焚毁刻板,提倡“看话禅”,禅门又重新走上了“须是悟得”的道路。在禅教关系上,宋元佛教逐渐走上禅教一致、禅净合流的道路。不论是“一枝独秀”的禅宗,还是成为时代潮流的禅教融合,宋元时期的南京佛教,都出现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大德、禅师,他们或于提倡禅教并重方面多有建树,或在延续禅门慧灯方面屡放新光,如圆通法秀、长芦宗赜之于禅净双修,圆悟克勤之于文字禅,云峰妙高、中峰明本之于“看话禅”,宏智正觉之于默照禅,凡此等等,都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大明王朝定都南京,加之开国皇帝朱元璋与佛教的诸多因缘,决定了大明王朝与佛教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明代诸帝所制定的一系列佛教政策,对于明代及明之后中国佛教的影响至为深远。明代几部大藏经的编纂与刊刻,在汉藏大藏经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从“国初第一高僧”楚石梵琦的“禅净并弘”,到雪浪洪恩对华严的阐发弘扬;从宋濂的三教融通,到阳明学的儒释交融;全室宗泐天台华严融通并弘,古心如馨则中兴南山律宗;复兴晚明佛教的四大高僧,均主禅净融通,又多以净土为归趣。朱明一代的中国佛教从总体上讲虽然已呈衰颓之势,但在南京地区却仍不乏扬名于佛教史的大德高僧。而且修建于永乐年间并成为“全国第一大寺”的大报恩寺,即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大报恩寺塔,更是当时南京作为全国佛教中心的一个象征。
清代佛教的一大特点,是喇嘛教的兴盛。相形之下,汉传佛教则着实有点“乏善可陈”。其中的一个“亮点”,是居士佛教的崛起,遂至于在“三宝”之外,有“四宝”之说。杨仁山创设的金陵刻经处,当是近代佛教复兴所露出的一缕曙光。由金陵刻经处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支那内学院,汇集了诸如欧阳竟无、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一大批教内外的时代精英,使南京不仅成为当时汉传佛教的中心,甚而成为时代启蒙思想的重要发祥地。民国初期,中国佛教协进会等全国性佛教机构在南京的建立,使得南京成为当时汉传佛教的大本营。20世纪上半叶,太虚大师等一大批佛教思想家在南京等地所倡导的“人生佛教”,揭开了现当代佛教改革的序幕。近几十年内,由“人生佛教”进一步演化而成的“人间佛教”,已发展成为整个汉传佛教的主流。
鉴于佛教思想义理的发展变化与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关系十分密切,《南京佛教通史》对佛教与各个时代的王朝政治、佛教政策、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等也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揭示和论述。另外,由于佛教寺院和佛教文化艺术在南京佛教史上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史》按三个发展时期(即六朝、隋唐宋元和明清民国)分别列有专章,力求以较翔实的史料和更宽广的视野,多视角、多层面地再现南京佛教的全貌和发展历程。
佛教讲因缘,《南京佛教通史》的编撰也是“众缘和合”的产物。始倡者是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复有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的发心资助,之后又列入江苏省教育厅和江苏省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最终由一批长期致力于南京佛教研究的专家学者,经过近五年的通力合作,遂有此三卷四册,总二百余万字,始自东吴,讫于20世纪40年代之《南京佛教通史》的编撰。值此《通史》付梓之际,由衷感谢上述有关单位的鼎力加持!并向所有参加《通史》编写的学者致以最真挚的谢意!
《通史》是个集体攻关项目,由于各编写者学术专长的差异和写作风格的不尽相同,全书在体例和风格上很难整齐划一,虽经统稿的多次磨合与修润,但其中之印痕仍在所难免。就主编而言,因时间、精力和学识所限,现在提供给读者的这部《通史》,肯定还存在着不少疏漏和错讹,对此,我除竭诚期待着方家大德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外,今后仍会将《通史》的修订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以期《通史》能够不断得到完善。
赖永海
2019年秋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