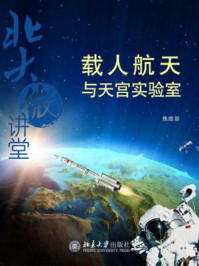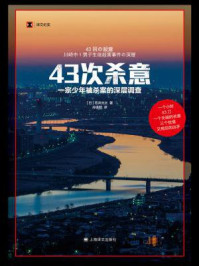“海洋命运共同体”既是理论又是方法,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视角,考察海域问题具有客观实用性。它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海域问题的方法,具有方法论价值。换言之,以“东亚历史海域”为场域,探讨这一海域“海洋命运共同体”发生、衍变、异化及未来走向等问题,可能会有新的学术发现。
众所周知,以海洋为介质展开的交流、交往以及不同族群共享海洋资源等活动,在古代来说很难想象。因为发明海上交通工具和开辟海上通道,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远古时代,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可以断言,海上交通工具与海上通道,对于“海洋命运共同体”本身而言,具有发生学的意义。“共同体”何以发生?在此,我们可以假设以下前提是成立的:有了不同族群的接触才有共同体发生的可能;有了不同族群以海洋为介质的接触才会有命运共同体发生的前提;有了克服海洋险阻后相接触的族群间的交好与抗争,才会有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诞生。在这个意义上,“海洋命运共同体”发生学,应该将讨论的内容集中到东亚历史海域相关的回顾与阐释上来。
从方法论观之,“海洋命运共同体”之于东亚历史海域,不仅可以成为观察古代中国海运交通问题的工具,还可以成为判断俄罗斯远东海域及美国阿拉斯加与周边海域以及东南亚海域进行互动的全新视角。
中国古代早期港口的兴起,呈现出“从中国沿海的南北两端向中部延伸”的特点,即“南方有广州、徐闻、合浦,北方有碣石、登州”。而四明(句章)和椒江(章安)等则属于浙东海域的名港,通过吴越人的航海活动,将中国东部沿海与中国台湾、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东南亚联系起来。可以认为,在太平洋海域范围内,中国古代先民的足迹已经远至美洲,南至东南亚,东部已达朝鲜半岛和日本,这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探讨东亚历史海域古代先民的海外交流本身,就已赋予“海洋命运共同体”以方法论价值。
同样,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视角,判断俄罗斯远东海域、美国阿拉斯加以及东南亚何时进入共同体时,能够再次展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价值。这一价值体现在,它可以超越相互争论的问题,重在关心这一海域何时形成互动及其互动的方式方法。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楚科奇半岛以及阿留申群岛的爱斯基摩文化所独有的平底船与金属鱼叉的广泛存在,便可说明北极人与萨哈林岛屿的土著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使得东亚历史海域北部的海洋文化得到了发展。
在分析阿拉斯加所代表的美国部分于太平洋海域是如何参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时候,美国考古学家根据上述“平底船与金属鱼叉”被萨哈林岛民所用的事实,断定岛上的部族可能来自北极或准北极民族。而北极民族的源头又是阿拉斯加半岛西南的民族。也就是说,萨哈林的先民来自美国阿拉斯加。这也说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在白令海、阿拉斯加湾、鄂霍次克海以及日本海等“海+岛”之间,形成了利用海洋资源的文化交流以及松散的共同体。
当我们将视域转向被称为“风下之地”的东南亚海域时,起初的共同体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国礼仪之邦以和平交往为特征)为表现形式,及至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到来,打破原有的域内平衡,将殖民主义移植到这一片海域。现在中国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得到许多国家赞同,认为“海洋命运共同体”将这一海域共同体建设的思想与实践向前推进了一步。
综上所述,“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海上安全稳定、推进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它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倡导相关各国共护海洋和平、共谋海洋安全、共促海洋繁荣、共建海洋环境与共兴海洋文化。同时它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富含中国古代先贤特别是孟子学说的哲学元素,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可以发挥“概念工具”的作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和合共生”特点,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现代阐释,还是新时代“利益观”的完美表达。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阐释出发,以“东亚历史海域”为视角进行考察,对于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