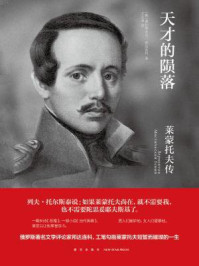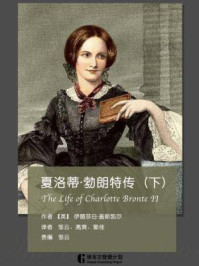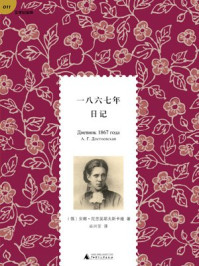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是美国新闻研究的文化路径(cultural approach)的代表学者。她现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嫩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教授和危机媒体研究中心(DCMR)主任。泽利泽是犹太人,曾在1976年和1981年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0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
进入学界之前,泽利泽曾长期在耶路撒冷从事新闻记者工作,这段经历不仅促使她走上新闻研究的道路,也使她对危机传播产生了强烈兴趣。此外,她曾担任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等多家媒体机构的评论员,在2009年至2010年间担任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ication Association, ICA)的主席。
泽利泽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她开拓、丰富了新闻研究的文化研究和解释学路径。在具体研究中,她尤为关注新闻权威、集体记忆以及危机时期的新闻图像等问题。1992年,由泽利泽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报道总统之躯:肯尼迪刺杀案、媒体与集体记忆的塑造》(Covering the Body: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the Media, 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的出版,为业已僵化的主流新闻研究范式注入了清新的空气。在这部著作中,泽利泽勾勒出新闻从业者如何通过阐释历史事件、塑造集体记忆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性。此后,泽利泽一直在新闻研究领域深耕,目前已出版十几部著作,发表了超过150篇论文与书籍章节,包括屡获殊荣的《濒死:新闻图像如何感动公众》(About to Die:How News Images Move the Public)和《记得只为遗忘:镜头里的大屠杀记忆》(Remembering to Forget:Holocaust Memory Through the Camera’s Eye)等。她于2017年出版的《新闻的潜能》(What Journalism Could Be)关注了新闻业的重要性,以及新闻适应21世纪不断变化的技术和文化背景的过程。
泽利泽是当今具有洞察力与创造力的新闻研究学者之一,她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新闻研究的“文化转向”。她最有贡献的学术观念在于启示人们聚焦新闻中的文化传统,通过解释的路径弥合新闻研究领域的观点冲突,追求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新闻理论,探寻新闻背后的社会语境与知识脉络。此外,她在界定新闻研究的领域与边界、梳理传统的新闻学术概念、考察新闻从业者的观念与行为、探索媒体在危机事件中构建公众的集体记忆的功能等方面也做出了理论贡献。
当前,面对日益多元的文化环境和不断迭代的技术环境,新闻实践逐渐走向多样化与复杂化。新闻从业者、新闻教育者与新闻研究者的工作也在数字时代呈现出新的特征。泽利泽的研究告诉我们,从文化路径中探寻新闻领域内的基础性问题的答案,或许是新闻研究实现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
面对数字技术的冲击,芭比·泽利泽将影响新闻行业的诸多要素置于制度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综合考量,从中提炼出自己对于数字新闻业的独特认识。具体来说,她在研究中主要通过对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受众的日常行为和价值观进行剖析,自下而上地阐释新闻业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的发展趋势。
常江:眼下,新闻似乎再一次成为传播研究领域的焦点。有很多新闻研究学者和新闻从业者都在热烈地讨论新闻的内容、新闻的价值以及新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您认为对于新闻业而言,这种探讨是否预示着一种潜在的创造性变革?
泽利泽: 确实如此。新闻从业者们总是倾向于思考自身、探索自身、凝视自身。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比以往更多生产和散播自我倾向的作品,至少表面上如此。我一贯将新闻从业者视作一个“解释的社群”,所以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新闻从业者在本质上就是聚集在一起、共享相似的世界观与社会规则意识的乡民。因此,有关新闻和新闻从业者的话语激增,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到达一个需要进行对话的关键节点。很多观点需要被讨论、被争辩,进而为我们探求新闻从业者的不同工作路径带来新思路。在研究新闻业的时候,将新闻从业者的行为与其他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综合考虑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我试图表明的:在不同的行动者、不同的意图、不同的规范与信念之外,总是有一种制度性文化在发挥作用。在美国,在特定情况下,政府当局与新闻从业者之间可能会产生对抗,这种对抗的来由可能是政府长期对媒体的不信任。新闻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很难辨别,但毫无疑问,当多疑的公众并不是真心想参与到涉及新闻从业者或新闻生产过程的行为中时,新闻从业者与政府的关系就变得紧张起来,这种紧张的关系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新闻业的怀疑。但这种关系并不鲜见。这种紧张关系如今在美国之所以受到关注,并不是因为公众对媒介普遍的怀疑,而是因为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过于越界,他的行为远比尼克松、约翰逊、罗斯福乃至肯尼迪等人激进。因此我们需要直面问题:每个总统都或多或少与新闻从业者有龃龉;新闻面对的关切自身的问题和构建自身权威性的问题都因它们与不同总统(一种制度性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同而各异。
常江:在数字时代,新闻的来源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也越来越去权威化。您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吗?
泽利泽: 关于新闻源的问题,总体上我认为“越多越好”。但我不太喜欢一种说法,那就是:我们现在拥有更丰富的信息来源,就等于拥有了更多、更好的信息。数量的多寡和品质的高低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更何况,如今的情况已经表明,即使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信息、更多元的信息源,也并不必然拥有更优质的信息。重要的是,我们要弄清楚导致变化的深层原因。我们不仅为这种变化高兴,也要明白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或许我们因此而陷入了一种含混的状态,但我们期待新闻为我们做些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新闻媒体?无论新闻是否可被替代,也无论新闻机构是否被旁观者或公民记者或建制化新闻组织所运营。我是十分敬佩Buzzfeed(美国的一个新闻网站)这类新兴媒体的,我觉得它们有勇气去打破固有的习惯。它们可能会犯错,但并不惮于进入旁人不愿踏足的领域。现在它们拥有显而易见的政治优势——既然长篇新闻难以就政治事件获得足够的信息,不如深耕一些边缘性的具体事件。在某些领域,新兴新闻平台往往做得更好。即使是在传统媒体中,《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在这方面也已远远超过《纽约时报》,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情况。这很值得我们思考。总之,在我们将所有的民主化的潜力归功于“越多越好”时,需要更谨慎一些。
常江:在新闻业的发展革新方面,您一直比较重视机构层面的举措。那么您对作为新闻消费者的个体有什么建议吗?是不是应该鼓励人们通过付费订阅的方式去支持好的新闻媒体?
泽利泽: 我建议,一定要成为优质新闻媒体的订阅会员。如果消费者不用行动支持专业媒体的话,这些媒体就无法立足。如果你有意向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的话,那么媒体一定是最值得资助的。对此,有两点需要强调。首先,这是一个让我们重新思考个体媒介素养的机会。由于教育系统的失职,大量美国人并不知道如何参与新闻。如果我们在小学至高中阶段开设媒介素养课程,这将会对教育产生巨大的系统性影响,以及不可估量的效果。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媒介素养教育不仅是口头和文字形式上的,而且是关乎视觉系统的。视觉媒介教育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环节,但长久以来,我认为视觉媒介教育是缺失的。其次,作为个体,我们应该意识到接触多渠道信息来源是一件平常事。这对于像我一样的“新闻粉丝”来说很简单:如果不能将每天要看的几份报纸浏览一遍的话,我到夜里就会辗转反侧。我也会随时上网检索,随时活跃在社交网站上,随时保持对当前热点事件的追踪。个体需要做的就是随时保持活力,从不同的渠道和媒体上获取信息。你始终应该清楚,没有一家媒体会向你讲述完整的故事。作为一个新闻消费者,我们的任务是从不同新闻来源中发现有用的信息,越早觉察到这一点越能从中获益。
泽利泽的新闻研究理念在她对数字新闻业的观察和剖析中展现无遗:在探索新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到新的媒介平台所带来的新闻来源的多样性以及这一变化为整体的新闻文化所提供的新的想象潜力。而作为新闻的阅读者与支持者,她认为用户对新闻的态度或许指引着新闻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方向。
在数字时代,新闻从业者的日常工作不仅面临着新的技术环境与工作内容的挑战,而且经受着一系列来自媒体之外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这一切都不断塑造着有别于以往的新闻职业认同。公众对于新闻从业者的信任,与新闻从业者的表现、新闻实践与政治行为的关系、新闻从业者的道德水准,乃至危机事件的报道情况等,都息息相关。
常江:请问您如何理解新闻从业者在数字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依旧坚守着基于共享技能和知识的旧职业认同吗?还是出现了值得我们关注的新现象?
泽利泽: 从定义上来说,新闻从业者就是从事新闻实践的人。新闻是指与新闻制作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报道、编辑以及对事件的评判。新闻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长期以来它一直是社会讨论的焦点,没有任何人会认为新闻是无关紧要的。当下的情况更证明了新闻作为一系列实践、作为个体的集合、作为一种职业乃至作为一种机构的不可替代性。在每一种情境下,新闻的重要性都呈指数增长。新闻也在帮助人们理解日常生活和政治机构的问题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并不是上述所有的观点都能在实践中得到证实。我们知道,现下的新闻从业者被无数人抨击。在当下的新闻从业环境下,经济要求和政治压力都迫使新闻成为一个利益导向的社会领域,因而新闻从业者变得更加多元化,并以前几代从业者未曾见过的方式处理多重任务。在政治上,他们同时受到左派和右派政客的攻击,这些政客在所谓的“新闻从业者的素质”的不同定义上争论不休。同时,政治环境也在不断削弱新闻从业者以旧的方式从业的能力。他们与政府部门、地方利益甚至军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新闻从业者总是遵循着不同的实践模式,但没有任何一种模式能够完全适应当今复杂的政治环境。
常江:还有传播技术的影响。
泽丽泽:对,从技术的角度看,新闻从业者面临着来自博客、推特等在线社群的新挑战,这种挑战削弱了机构媒体的工作的重要性。在美国,主流报纸和广播新闻节目(早间节目除外)正在失去它们的受众;与此同时,族群媒体、在线媒体以及深夜电视喜剧节目、博客与在年轻人中流行的网站正在迎来受众的增长。这或许说明旧的新闻生产系统的消亡并不代表新闻本身的消亡。最后,发生在英美等国的不少丑闻都引发了公众对新闻从业者的道德质疑。这也为自媒体和公民新闻的发展壮大铺平了道路。因此,新闻从业者在讨论“新闻应该如何去做”时的发声效力就越来越弱。记者的定义是否发生了改变?哪些技术(比如手机和博客)是制造新闻的真正手段?新闻业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简单地提供信息还是更积极地塑造社群和公民身份?这些之所以会成为问题,部分原因在于界定新闻时其实始终存在诸多彼此冲突的传统。新闻从业者的自我定义到底是一门手艺,一种专业技能,一种商业模式,一个社区集合,还是一种思维模式?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些定义的一部分的集合。这需要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定义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对抗的关系。
常江:除了技术之外,还有哪些因素是我们在思考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时忽略了的?
泽利泽: 图像是新闻的一个被忽视的方面。我们往往将图像与新闻标题、新闻真实和文本分割开来,这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即使我们不去充分地考虑它,视觉元素也在危机报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像在伊拉克战争或“9·11”事件之后,我们可以在《纽约时报》之类的报纸头版上看到比和平时期数量多达2.5倍的图像。因为图像的“正确使用”方式还没有被研究透彻,所以图像的呈现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当图像刺痛了人们的神经时,他们就会潸然泪下,这就意味着新闻在无法唤醒人们的感情时,会将这一功能转交给以图像形式呈现的各种角色:政客、游说者、公民、失孤父母,甚至军人。同样被低估的还有我们需要将危机事件纳入新闻规则的程度,而非将其排除在新闻之外。在新闻报道中,有太多新闻是出自灵光一现、纯粹的好运或厄运,甚至是我们不愿承认的上天的恩赐。但是,若将这些因素都排除在外的话,我们就可以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新闻感,这种新闻感将新闻置于一种更可预测、可管理的地位。综合考量所有这些因素,新闻从业者在公众信任程度列表中垫底就不足为奇了。有报道称,在美国只有50%的人信任他们的当地报纸,对于广播和有线电视台的信任也在大幅度降低。所有上述因素都导致新闻从业者成为一个与社会脱节的群体,因此观众的需求、新闻制作环境革新的需求、新闻编辑室对灵感和创造力的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
在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进行考察时,泽利泽继承了新闻生产的社会学传统,主张在复杂的社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中思考这一问题。此外,从自身的研究兴趣出发,她提出对“图像”和“危机”的忽视是新闻职业身份难以实现自洽、新闻从业者难以赢得公众认同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甚至是一个学科),新闻研究(新闻学)究竟要解决哪些基本问题一直饱受争议。泽利泽的研究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她在长期的实证研究经验中,尝试建立新闻学的某种共享的文化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新闻实践、新闻教育与新闻研究的协同促进。
常江:您可以为我们描绘一下新闻研究在当下的版图吗?
泽利泽: 虽说只要公众对关于外部世界的中介性信息仍有需求,新闻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但新闻本身的确面对着这样或那样的争议。当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将报纸上的报道作为他的第一本书的引注,批评家便讽刺他“将一本好书变成了新闻”。尽管人们对新闻有着强烈的依赖,但这种对新闻的不屑一顾或吹毛求疵的态度始终存在。这些反应不仅鞭策我们形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也促使我们将这种情况视作认同自身、理解世界的新的起点。
关于新闻研究应该怎么做,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他认为任何研究的成功都建立在共识的建立和共享范式的发展上,也就是以群体认知的方式对一个研究领域相关的概念进行命名、描述和考察的程序。一旦共识被建立起来,我们对新现象的分析就有现成的框架可以参考了。如今,我们对新闻研究这个领域的理解,已远远超出库恩的思考范畴。涂尔干、罗伯特·帕克、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等人的观点都被纳入进来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建立探知世界的方式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最早由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提出,并由我和其他学者加以发展的“解释性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将共享知识的过程作为知识的组成部分”。正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所认为的那样,真正的群体只有在个体分享他们不同的思想时才可能存在。因此,研究不只是一种认知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解释性社群”的概念不仅适用于理解新闻从业者,也适用于理解新闻研究者。
常江:这些观点对于新闻研究者意味着什么?
泽利泽: 上述思想和观点鼓励我们重新思考社会群体在形塑新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新闻研究中的每一种观点都没有比其他观点更好、更权威,自然也不会存在任何归一化的新闻研究视角。相反,不同的观点以多样、激烈的方式协商着新闻的定义,而每一种观点都建立在一系列阐释的关键因素与作用方式的基础上。大家关注的核心应当是新闻研究到底该如何实现真正的发展,但这一问题目前被搁置了,因为每个人都试图在众声喧哗中寻找那个“最有力”的观点。在有能力进行新闻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面临着“谁最有能力发声”以及“谁占据了发声的最有利的地位”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综合思考一下新闻研究中这些纷杂的声音。当我们反思新闻和新闻研究时,每一种声音都有其长处,也有其劣势。每一种声音都会构成一种解释性社群,这种群体依据其自身目标来定义新闻,并将认识新闻的策略与其目标结合起来。
常江:新闻学学科变化如此之快,研究对象也似乎变得越来越暧昧,新闻研究者应该做些什么来适应当前的局面呢?
泽利泽: 新闻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在传播研究、媒介研究、新闻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也被历史学、英语研究、美国研究、社会学、城市研究、政治学、经济学和商业管理所关注。这也就意味着,新闻的研究者往往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边界之内去考察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所以他们的观点便不得不通过各学科所遵从的研究范式呈现出来。总体而言,我认为新闻学应当是一门解释的学科,因此,历史学和社会学,即我所认知的最有效的解释性学科,会比其他学科更加有助于我们界定新闻的内涵及其存在方式、决定什么类型的研究可以进行。而现状却是,新闻已经被学者们装到了不同的“口袋”里,每一个口袋都将新闻的一个方面与其他方面分割开来。这种分割并不利于从整体上界定新闻是什么,而是将新闻的局部放大并加以阐释。其结果是新闻研究内部互相攻讦,进而导致新闻教育者与新闻研究者分离,人文主义取向与社会科学取向分离。新闻研究在不同学科产生了一系列分散的学术影响,但我们至今无法归纳关于新闻的至关重要的共享知识。
常江:国别和文化的差异也是新闻作为研究对象的模糊性的一个来源。
泽利泽: 对,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即使新闻实践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形态,但大部分新闻研究都关注美国的新闻实践,因此几乎所有的新闻研究项目都自然而然带有美国色彩。这些研究当然无法回答全球视野下的诸多问题。同样重要的是,虽然新闻的历史长期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但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很难说这种关系仍然在发挥作用。我们很容易承认全球化的一个关键影响就是它消减了民族国家的中心性,但我们始终没有搞明白是否还有一些“替代性的动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新闻业发展的规律。所有的这些情况都表明,新闻研究者未能采取足够的行动在新闻与各种社会形式之间建立联系。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即使我们有充分的知识用以说服那些皈依者,也不能创造出关于新闻的定义和新闻业的运作方式的共识。我们应该想办法更加有效地解决与新闻学发展相关的三大群体(新闻从业者、新闻教育者、新闻研究者)之间的紧张与龃龉,并提供一种有效的方式提升公众对新闻的兴趣。
常江:您曾提出五种研究新闻的视角,即社会学、历史学、语言研究、政治研究和文化分析。您能阐释一下一个优秀的研究者应该选择其中某一种,还是综合运用这些取向吗?
泽利泽: 需要澄清一点:并不是只有这五个学科或领域在研究新闻,而是这些研究的视角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系列的观点,让我们借此对新闻进行概念化。值得一提的是,每一种框架在其对新闻的阐释之中都暗含着一些基本假设。每一种框架都为解决“新闻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方案:社会学解释了新闻本身的重要性;历史学解释了新闻运作过程的重要性;语言研究通过语言或视觉分析的手段解释新闻的重要性;政治研究解释了为何新闻是重要的;文化分析解释了如何对新闻的重要性实现多元化理解。回到研究的大环境中,这些答案都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为何要首先解决新闻重要性的问题?
常江:在可预见的未来,究竟应该如何使新闻研究的各部分联系得更加紧密,您能给出一些明确的建议吗?新闻研究者和新闻学院应当怎么做?
泽利泽: 首先,我们需要弄明白如何将新闻实践、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三项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洞悉这三者的共生关系有助于使新闻与公众的想象相契合。新闻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囊括各方力量的框架,无论新闻实践、新闻教育还是新闻研究本身,都应该置身其中。其次,我们应该促进新闻教育跟更广泛的大学教育紧密结合。我们要明白,新闻是一种与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表达艺术,也是一种与社会科学结合紧密的社会活动。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再次,我们要意识到,每一种观点都只提供了浩如烟海的思想中的某一个,并以此来解释新闻的运作规律,只有综合考量这些观点,我们才能最好地统筹全局,洞察新闻如何运作,以及其中的问题缘何产生。最后,我们不仅应该解释我们对新闻的共识,而且应解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共识。时刻保持跨学科的敏感性并以此检视新闻,或许我们可以找到新的方法以反思现有的新闻研究,对于跨地区和跨时期的研究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我们要去不断思考如何在保持新闻学的学科想象力的基础上,努力使其成为一个整体、一个真正的学科。
总而言之,回答“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取决于我们对新闻业发展的预测、我们对新闻业发展方向的把握,以及我们在观察新闻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视野拓展和方法创新。新闻太重要了,以至于仅从其自身出发根本无法解决我们所讨论的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新闻研究的未来就会十分黯淡。很久以前,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曾说过:“新闻让我们以他者的眼光看问题,以他者的耳朵听问题,以他者的思想思考问题。”在思考新闻学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时,或许我们也能得到同样的启发。
芭比·泽利泽通过提出“解释性社群”这个概念,为新闻研究的未来设计了方向:打破不同学科和范式对新闻研究的分割,建立各个局部研究之间的关联,建立新闻从业者、新闻教育者和新闻研究者的共识机制。她对“解释性的新闻学”的倡导对于新闻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有着不容忽视的推动力。
(资料整理及翻译:田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