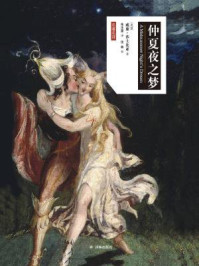先从海顿(F.J.Haydn,1732—1809)谈起。因为从巴洛克时期到古典时期,海顿是一个关键的过渡人物。
1750年,亦即巴赫去世的那一年,海顿18岁,写出了他第一部作品《F大调短小弥撒曲》。而贝多芬出世和莫扎特去世的时候,长寿的海顿还活在世上,他一脚横跨两条河流,理所当然地衔接起了巴洛克和古典主义两个时期。
海顿与莫扎特、贝多芬共同生活的18世纪下半叶,正处于欧洲巨大变革的前夜,没落的封建专制正在被废除,新生的资本主义正在兴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人权宣言》的威力,启蒙运动的深入人心,一大批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的风起云涌,搅动得时代翻天覆地,使得音乐艺术在内容上也随之发生了与巴洛克时期截然不同的变化。这一变化,是以宗教音乐进一步世俗化,音乐离开宫廷、离开教堂,到民间去、到自然中去为标志的。音乐开始进入酒馆、进入旅店、进入市民的家庭里,成为普通百姓放纵情感与思想,尽情参与那个时代狂欢的最好方式。“此时音乐的作用不再像巴洛克时期那样去教育去感动听众,而更多的是愉悦。” [20] 据说,那时在威尼斯这样的城市里,如果看到两个人边走边交谈,都像是在唱歌,而且是用二重唱的方式。
如果从音乐形式的发展脉络来看,文艺复兴时期以帕勒斯特里那为代表的声乐艺术占据了主要地位,到了巴洛克时期经过巴赫的努力,器乐已经和声乐平分秋色,那么,到了新的时期,也就是18世纪下半叶的古典时期,器乐发展到了历史最重要的阶段,它对于那个时代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器乐的新品种——交响乐。
当然,那是经过了北德乐派(指当时活动于德国柏林的音乐家,代表人物有巴赫的二儿子)和曼海姆乐派(指当时活动于德国西南部曼海姆地区的音乐家,其中包括来自波西米亚的音乐家),一直到以海顿为代表的维也纳乐派(当时维也纳已经成为整个欧洲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音乐的中心也转移到了这里,维也纳被称为“音乐之都”)三派的共同努力才结出的丰硕果实。“交响乐”(symphony)一词源于古希腊,意思是“一起发声”。交响乐便是管弦乐乐队一起演奏的新的样式。无可争议的是,海顿是交响乐创作的先驱,正是他的探索和努力,使得古典奏鸣曲和交响曲套曲的形式逐渐完整完美,曲式、结构不断充实,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了交响乐的基本规范程式:第一乐章为快板奏鸣曲,第二乐章为慢板的抒情性的三部曲或变奏曲,第三乐章为三部曲式的小步舞曲,第四乐章为快速的回旋曲或奏鸣曲。交响乐成为横亘几个世纪绵延至今、长盛不衰的音乐形式,成为如今音乐会上的必备节目。称海顿为“交响乐之父”,是不为过的。
我们可以看出莫扎特在音乐旋律上和上一代的巴赫、在歌剧创作上和上一代的格鲁克的关系,也可以看出贝多芬与亨德尔的某种渊源。而莫扎特和贝多芬在音乐中与海顿的血缘关系,是一目了然的。可以说,没有海顿就没有贝多芬的交响乐,22岁的贝多芬正是由于海顿的赏识并听从了海顿的劝告,才乘车走了一个星期,从故乡波恩跋涉了500英里来到维也纳,迈出了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到了维也纳,贝多芬已经囊中羞涩,但他还是拿出所剩无几的钱,给海顿买了一杯咖啡,以简单的形式和虔诚的心情拜海顿为师。尽管贝多芬也敬重巴赫和莫扎特,他的祖父和父亲也都是他的老师,尽管耿直倔强的贝多芬和温驯的海顿脾气秉性不同,导致后来发生争执,贝多芬拂袖而去,但他还是承认自己一直受业于海顿,他的第二交响乐可以明显看出海顿的痕迹。莫扎特就更不用说了,他干脆称海顿是自己的爸爸,极其虔诚地把自己的弦乐四重奏献给了海顿。
因此,我们可以说,交响乐是经过海顿的奠基而由莫扎特和贝多芬尤其是贝多芬最后完成的,是他们两代三人的共同努力,使交响乐成为古典主义音乐的旗帜,用划时代的音乐新形式辉映并呼应着18世纪后半叶那个变革时代汹涌的浪潮和粗犷的呼吸。
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莫扎特(W.A.Mozart,1756—1791)和贝多芬(L.V.Beethoven,1770—1827)。在这里,主要说的是他们的交响乐。
说起莫扎特,就不能不说到他早年的聪慧和婚后的拮据。
没错,没有人能够比莫扎特更具有天才的能力了。他3岁就开始弹奏钢琴,4岁就能够写钢琴协奏曲,5岁开始公开演出,9岁创作了第一部交响乐,仅仅在少年时期就有16部交响乐问世……当然,还应该提及莫扎特6岁时在维也纳的百泉宫里摔倒,被7岁的玛丽公主扶起,他对这位后来成为法国路易十六之妻的小公主说的话首先不是感谢,而是口气颇大的命令一般的言辞:“你真好,等我长大了,我一定娶你!”所有这些无不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
莫扎特生活的窘迫,似乎从来就没有缓解过。婚后九年,他的日子越来越艰难,这九年中,他搬了12次家,有六年是妻子生养孩子或产后休养,一直处于负债累累的状态,而且由于他妻子的大手大脚使得艰辛的日子雪上加霜,以至到了冬天连买烤火的炭的钱都没有,饥寒交迫之中他只好抱着带病的妻子围着空壁炉跳舞取暖。
或许,以上可以作为关于莫扎特的一幅生动的画像,如果再加上莫扎特独有的处变不惊、一贯乐天、自尊自爱、自由放纵的表情,画像就更生动清晰了。如此贫寒又如此乐观,莫扎特就是这样一个人!罗曼·罗兰说:“他的所有心理功能好像都十分平衡;他的灵魂充满情感却又能很好地自我控制;他的心灵十分镇定,情绪稳健……这种心理上的平衡在天生充满激情的人当中实属罕见,因为所谓激情就是指感情过度。莫扎特什么情感都有,但他没有激情——他有的其实是极端的高傲和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有天才。” [21] 莫扎特就是以这样独一无二的心理平衡能力,平衡着自己并不如意的生活和如日中天的音乐,他在不如意的生活中体现着一颗不屈心灵的高贵和高傲,在如意的音乐中表达着精神的理想与寄托。
莫扎特为我们留下的音乐作品实在浩繁得和他三十五年的短促人生不成比例,其数量之多可以说在音乐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仅交响乐就有48部,歌剧20部,钢琴协奏曲27部,其他还有弥撒曲、奏鸣曲和各种重奏曲,以及最后没有来得及完成的重要作品《安魂曲》。应该说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后宫诱逃》是他极重要的作品,但我们还是暂时把它们放在一旁,删繁就简,集中精力,主要先说说莫扎特的交响乐。在莫扎特留存下的48部交响乐中,我们主要说说他在1788年夏天最后完成的三部交响乐,即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乐、g小调第四十交响乐、C大调第四十一朱庇特交响乐。
这三部交响乐,莫扎特仅仅用了六周的时间就一挥而就。他确实是一个天才,音符与旋律就好像是揣在他衣袋里,随时都可以尽情抛洒。三年后,他就撒手西归了。去世之前这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正是他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刻,因此,可以说这三部交响乐是他人生最后喷突出的精华,是他生命末尾的杜鹃啼血之作。当时,为了能够尽快挣得一点现金以解燃眉之急,他才以如此快的速度写完,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卖给了出版商,但是直到他死后,这三部最重要的作品才得以出版。
这确实是三部最为重要的作品,英国研究莫扎特的学者从交响乐纯粹的调式意义上这样认为:“莫扎特为他最后三部交响曲所选择的调性在他的音乐中具有强烈的相关意义:正如我们多次所见,C大调与典礼仪式有关,常有军乐性质,有小号和鼓参与;降E大调具有抒情的暖意和富丽的音响,有时还透出一定的高贵隆重的气息;g小调与所有小调一样,能产生急切感、戏剧效应,或许还有悲怆之情。” [22] 以这样有益的提示来听这三部交响乐,也许是我们走近莫扎特的一条捷径。
我们先来听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乐,舒缓的引子,号角般富丽堂皇的音乐开始了第一乐章,大提琴和低音提琴雍容华贵地落在高音的木管乐上,优雅的小提琴出场了,的确有那么一点高贵隆重。第二乐章行板的质朴中流溢出典雅,抒情性很强的弦乐,吟唱般显得格外韵味悠长。第三乐章的小步舞曲充分体现了舞曲欢快的性质,那样健康,阳光灿烂,泥土芬芳。一般人们都认为这部交响乐最像海顿,但细听之后,我们会觉得它比海顿要机敏,那种舞曲流淌出的诗情画意,是莫扎特独有的。
g小调第四十交响乐,确实有一种悲怨的调子,写这部交响乐的时候,莫扎特正住在远离维也纳市中心的郊外,经济紧张,境遇悲惨,心境郁闷。不过,莫扎特音乐的悲怨不是那种落木萧萧的凄凉,只是有些如怨如诉、细雨淅沥。即使是悲怨,也被莫扎特化为一种异样的美,犹如落叶飘零在枝头迎风摇曳却迟迟不落的样子,雨水在上面淋漓,那样楚楚动人。在这部交响乐中,莫扎特没有用小号、定音鼓之类的乐器,而只用了弦乐、木管乐,加上柔和的法国号,那种温柔就如轻纱拂面一般。木管听起来那样的明亮,第一乐章中弦乐有时有些急促,没有了弦乐的缠绵,仿佛铜管乐的效果,显得有些硬朗,就像他妻子的小拳头爱意绵绵的敲打。直到第二乐章,细雨初歇,明月绽露,弦乐才又恢复了雨后空气所弥散的清新,莫扎特特有的歌唱性和抒情性一下子如同温柔的手伸出来重新把你揽在怀中。
C大调第四十一朱庇特交响乐,被誉为莫扎特交响乐的里程碑,那种气势恢宏、变化多端,在莫扎特的音乐里确实是少有的。小号和鼓响起蓝天般的晴朗和高远寥廓,巴松和长笛奏出晚霞柔美的色调和飘曳的情绪,小提琴穿梭在它们之间,宛若高飞云天之上的大雁,翅膀上闪烁着天光云影,游弋出蜿蜒的线条,有那样一种凄楚之美。最后一个乐章,小号、法国号和定音鼓齐上,一股英雄蓬勃之气氤氲蒸腾,特别地壮观,光彩夺目。“小号、法国号和定音鼓的号角花彩给予《朱庇特》一个非常配称的雄伟结局,也是为莫扎特的交响乐作品作了总结。这个乐章确实像在诉说最后的话语:悲伤得使我们永远也无法猜测莫扎特本来还会继续走向何方,美满得使我们永远也不能想像他还能创作任何超过它的东西。” [23]
我们再来看贝多芬。这是一位不仅在古典时期而且在整个音乐史上都属于重量级人物的音乐家,在音乐家的排兵布阵表中,他肯定处于中锋的位置。
罗曼·罗兰这样描述贝多芬的样子:“他由得到加固的坚固材料筑成;贝多芬的心灵因而有了力量的基础。他的身材魁梧,肌肉发达;个头矮小粗壮,肩膀厚实,长着一张黑红的脸,一看便知是风吹日晒使然。他有一头又黑又硬、长而密的头发,草丛一样的眉毛,连鬓胡子向上长到眼角,前额和头盖骨宽阔而高昂,‘像圣殿的拱顶’;有力的下颚‘像能把坚果咬碎’;凸出的口鼻部像头狮子,嗓音也似狮吼。认识他的所有人都对他体力充沛深感吃惊。诗人卡斯泰利(Castelli)就说他‘是力量的化身’。塞伊弗里德(Seyfried)也写道:他是‘一幅力量的画’。” [24]
朗多尔米则这样描述他:“他身材矮壮,有着红褐的面色,饱满而凸出的前额;长着一头浓黑而乱蓬蓬的头发,还有一双深灰兰色、看上去好象是黑色的眼睛。宽而短的鼻子上长着‘狮子似的鼻尖和骇人的鼻孔’,下巴有些歪。他的微笑是慈祥的,大笑时却似怪物,神情总是忧郁的。他的一位同时代人说:‘他那双柔和的眼睛里含有一种令人伤心的痛楚。’在即兴演奏时他的模样全改变了,‘面部的肌肉抽搐着,静脉鼓胀起来,嘴也发抖了。’人们说,这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人物——李尔王!” [25]
他们的描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突出了贝多芬性格愤世嫉俗和强悍怪异的一面。这和我们如今在许多地方常常见到的那种贝多芬的雕像是一样的,无论见没见过贝多芬,贝多芬都约定俗成地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其实,无论罗曼·罗兰还是朗多尔米,都不是贝多芬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没有见过贝多芬,他们所描述的贝多芬只是想象中的贝多芬而已。应该说,贝多芬的样子和他的音乐一样,并不是固定一种版型。二百年来,贝多芬一直存活在不同人的想象之中。正所谓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人眼中和心中有不同的贝多芬,这也正是贝多芬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对于一般人来讲,知道得更多或更为关心的是贝多芬这样几点:耳聋、爱情和音乐里命运的敲门声。
没错,贝多芬26岁开始耳聋,到38岁双耳完全失聪,对于一个格外需要听力的音乐家来说,这确实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但是,贝多芬许多重要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打击之下写出来的,他确实不是一个凡人,他的作品具有一般音乐家所难以达至的不同凡响的品质和力量。
贝多芬和亨德尔一样终生未婚,但和亨德尔不一样的是,他一生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恋爱之中,只是一直都没有赢得爱情。所有的爱情开始时都盛开着美丽的勿忘我,结束的时候却只结无花果。这种生命的痕迹明显地留在他的音乐中,他的《月光奏鸣曲》是献给初恋情人朱丽塔·吉采尔荻的;他根据歌德的诗编写的歌曲《我想念你》是献给布鲁思维克姐妹俩的;而他的78号钢琴奏鸣曲和美丽得无与伦比、也是他唯一一首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都是献给姐姐苔莱泽·布鲁思维克的。他所钟情的其他女人还可以说出许多,一直可以说到他最后痴痴暗恋着的、跟随他学习钢琴并成为当时著名钢琴家的多罗西娅·冯·艾特曼,贝多芬一直藏在抽屉里、被后人发现的那封《致永久爱人书》就是写给她的。贝多芬一生都在爱情的向往和失落中生活,都在灵与肉的苦闷中度过,他自己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那时的女人:“要么有灵魂没有肉体,要么有肉体没有灵魂。”这话听起来像是哈姆雷特说的“是死是生,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充满着天问般的苦楚。他于是把他那终生不可得的爱情梦想幻化在他的音乐之中,将苦楚的悲剧化为甜美的音符。因此,罗曼·罗兰和朗多尔米所描述的贝多芬的样子,并不全然可信,起码贝多芬不是什么时候都如狮子如李尔王一样吓人。他的音乐也不尽是命运的敲门声一样深刻和恐惧,如果我们听他的那首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会感受到他敏锐而善感的动人一面。
贝多芬一生创作的作品数量无法和多产的莫扎特相比,他只有9部交响乐、16首弦乐四重奏、32首奏鸣曲、2首弥撒曲、1部歌剧、1部轻歌剧和一些协奏曲、室内乐以及歌曲。数量即使没有莫扎特那样多,要一一尽数贝多芬的作品也是困难的,我们主要来说贝多芬的交响乐。这样来谈,不仅同前面谈莫扎特一样是为了避轻就重容易集中,更重要的是贝多芬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具有交响性,他的交响乐更集中体现了他一生的这种追求。是贝多芬将古典主义时期的海顿和莫扎特的交响乐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之前一个多世纪蒙特威尔第到巴赫的器乐梦想在他的9部交响乐中得到了最灿烂圆满的实现。同时,他也将从帕勒斯特里那到亨德尔戏剧中的特点与长处引进他的交响乐中,他的交响乐以前所未有的戏剧性开创了新的篇章,使得交响乐的创作有了更为丰富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知道,一部音乐史其实就是声乐和器乐这两支力量此起彼伏相互交融的发展史,器乐经过了漫长历史的发展,到19世纪初在贝多芬的交响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步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这一在音乐史上承上启下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曾有美国学者这样说:“器乐在整个十九世纪余下的时间的发展都是在他的符咒之下,但是没有一个音乐领域的真正灵魂不是归功于贝多芬。贝多芬赋予纯器乐以最强烈的和最富于表现力的戏剧性的特点,这种表现特点又反过来影响到戏剧音乐本身。这里完成了一个循环。……瓦格纳认为贝多芬的最伟大的影响应归于他打破了器乐的界限……” [26]
让我们先从他的第三交响乐说起。第一和第二交响乐,还不是我们后来看到的贝多芬的样子,明显有着莫扎特和海顿的影子。1804年完成的第三交响乐,对于贝多芬的创作极为重要,它是贝多芬甚至整个古典音乐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交响乐的标题原来是写着献给拿破仑的,但当贝多芬后来听到拿破仑称帝的消息后立刻撕掉了那页标题,重新写上“英雄交响乐”的字样。这一情景被赋予了传奇的色彩,和贝多芬的这部交响乐一起辉映在那个动荡革命的时代乃至今日的传说之中。这部完全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大潮中被激荡起的交响乐,洋溢着一代人的革命激情。拿破仑曾经是那场革命中激励着一代人的英雄,他的称帝打破了一代人心中的偶像与梦想。贝多芬在这部音乐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英雄的渴望以及对英雄的精神和理想的呼唤,远远地超越了一个拿破仑泡沫的升腾与破灭。
这部交响乐以传统的四个乐章的形式构成,乐思辽阔,结构缜密,气势如虹。但第二乐章却是一个特例,与传统的模式不尽相同。第二乐章是一个缓慢的柔板,名为《葬礼进行曲》,以其慷慨悲壮和肃穆庄严为伟大的英雄送葬。这一般应该放在末乐章,贝多芬这样反常的处理,第一次打破了古典交响乐的传统。他在这段进行曲中加入了回旋曲的效果,后来渐渐地便成了一段行板,这曾经被许多人分析为是用进行曲为英雄送葬,行板则代表英雄的灵魂飞进了天国。
英国学者Robert Simpson则与众不同地认为:“贝多芬的英雄概念并不是浪漫主义的概念;他按照从自身所感受到的来表达人类潜力的真理。拿破仑被远远抛在后面。这段行板音乐不是天堂的景象——如果它是天堂的话,为什么在最终的急板部分像英雄决心的最后一个浪头那样涌现之前,人类经受的强大压力、强烈疑惑、甚至恐惧都在不知不觉之中从音乐中出现,英雄主义甚至在瓦尔哈拉宫都不需要,就莫说天堂了。不——这些最后的辉煌的乐段的意义肯定是:在经历了斗争、悲剧、欢乐并且了解了力量之后,英雄以一种正当的、越来越强的尊严意识来审视过去……然后,磨练人的终极认识出现了:他永远不会缺少恐惧和斗争的理由。他坚强不屈地面对着真理,交响曲以激昂的反抗结束。贝多芬是客观的现实主义者,即使在这里,在他毫无疑义地绘着一幅自画像的时候也是如此。” [27] 他说得很有道理,他特别突出了音乐中所呈现的英雄的悲剧色彩,并且阐释了这部交响乐的自传性质。
贝多芬1808年完成的第五交响乐的主题无疑是“命运”,随着第一乐章开始的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那四个音,恐怕是音乐史上音乐主题最精要短促却包含着最强悍力量的音响了,那种突如其来的严酷却坚定的命运,从天而降一般响当当地突兀地摆在贝多芬的面前(那时,贝多芬在自己耳聋、病重等厄运面前燃起过自杀的念头,并写下过遗书),也同样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人生不如意多于如意、痛苦多于欢乐的命运是相同的)。据说,从总谱上来看,那四个音的最后一个音的延长,是后来特意加上的,有意延长的效果,反映了贝多芬潜意识里对命运本能的敬畏。那四个音的快慢速度和强弱程度,日后成为衡量指挥家的一块试金石,反映了不同指挥家和不同听众对它的理解。“命运就是来敲门的。”贝多芬这样解释这四个音。这四个音极具抽象的哲理,它们说明了命运的宿命性,命运自身不可更易的意志。“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贝多芬的这句话不仅演绎着命运的抗争性,而且表达了人类自身锲而不舍的意志。表现这样两种意志的搏斗,就是对这部交响乐最通俗的解释。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乐队都把这四个音演奏得雷一般炸响,也并非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贝多芬的坚强与伟大,以及自己和贝多芬的接近。有的乐队将这四个音演奏得如同从遥远地平线上隐隐滚过的风,吹响了连天的绿草和树木的飒飒心音,在辽阔的四野悠悠地回荡,不能说这就不是命运,不是贝多芬。紧接着的双簧管如泣如诉,整个弦乐响起的时候,并不都是一味地孔武有力,也可以是低沉回旋,极其节制,哪怕是再微弱的音节也处理得如同羽毛飘浮在空中又轻轻地落在地上或我们身上那样踏实、感人。然后,是弦乐此起彼伏地响起,如同花开一样的缤纷,让我们嗅到芬芳;如同星星一下子亮起来布满我们的头顶,璀璨得让我们的眼睛和心灵一起明亮起来。
因此,在我看来,第五交响乐可以是强硬的,也可以是柔软的;可以震撼我们,也可以温暖我们;可以是戏剧性的,也可以是诗性的。Robert Simpson不无嘲讽之意地提醒我们:“《第五交响曲》的戏剧性,使它经常遭到表演过火的浪漫派指挥们的虐待。谨防那种以慢速用力敲出开头几小节的蠢人,然后他又像躁狂症者一样从第6小节起拼命赶;我们可以确信,他会在每一个类似的时刻表演相同的、令人发狂的把戏,来显示……他像训狮员一样地控制了交响乐团……” [28] 在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时,要特别提防这样的“驯狮员”。
第九交响乐《欢乐颂》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如果说第三交响乐是一个英雄的诞生,第五交响乐是一个英雄的成长,这部交响乐则是英雄的涅槃。这三部交响乐让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贝多芬或者说贝多芬心目中的一个英雄的心路历程,从恐惧、绝望,到奋争、欢乐,热情的快板和如歌的柔板早已经为英雄扫清了道路,最后的大合唱《欢乐颂》是英雄的涅槃。为了这一感情和理想的需要,贝多芬把传统交响乐四乐章的所谓完整性的组合顺序打破了,增加了演奏的时间,扩展了结构的规模,并有史以来第一次增加了独唱和大合唱,这为以后马勒的交响乐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贝多芬就是这样以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开创了交响乐史诗性的先河。
只要想一想这部创作于1824年的交响乐是贝多芬完全失聪的情况下的作品,就会明白这绝对是音乐史上的奇迹。据说,这部交响乐在维也纳成功首演的时候,尽管台上有指挥,贝多芬在舞台的一旁还是激动得像醉汉、疯子一样,不停地挥舞着手臂,踏动着脚步,风摆柳枝一样前仰后合,好像指挥着也操练着所有的乐器,并像歌手一样不顾一切地在唱在跳。这样可笑的样子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嘲笑,相反,大家只是更加认真地听,而且在演出结束后向他报以雷鸣般热烈的掌声。可惜,此时的贝多芬什么也听不见,还是一位女演员推了推他,他才回转过身来,看到了台下那无数只手在无声地扇动着鼓掌。这确实是非常感人的场景,是只有在贝多芬的时代才有可能出现的场景。
在听完上面三部交响乐之后,我们还应该听一下第四交响乐和第六交响乐。
1806年写的第四交响乐的调子与前三部截然不同,它是明快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爱情的活力。舒曼曾经说它“像两位北欧巨人之间的一位纤弱的希腊少女”。都说贝多芬的第四和第七交响乐是最难以描绘的,舒曼这样的比喻也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但柔板乐章中的细腻与神秘,以及轻柔的幻想,希腊时代那种古典味道确实更浓郁些,这都是在贝多芬的交响乐里不多见的。那一年,贝多芬正在和苔莱泽恋爱(后来,贝多芬终生未娶,苔莱泽则终生未嫁),苔莱泽把刻有自己面容的雕像送给了贝多芬,贝多芬则将这份爱情寄托在他的这部交响乐里。
1808年创作的第六交响乐,是贝多芬9部交响乐中难得的柔板,贝多芬表白它是“到达乡间时愉快的感受”,是“溪边景色”,是“乡民的欢聚”,是“暴风雨”,是“慰藉和感恩的情绪”。他还说:“我虽然失聪,但那里的每一棵树都跟我说话。”这部交响乐精美的配器,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了管弦乐的潜力,真的好像每一棵树都在和贝多芬说话,乡间的田野和溪水覆盖着美妙的旋律,就连明媚的阳光都闪烁着绿色的光斑,暴风雨也充满着牧歌般的温馨。需要注意的是,无论第四还是第六交响乐,无论爱情还是田园,贝多芬所诉诸音乐的都不是描绘性的,而是他心中的感觉和感受,因此,如果说他的音乐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幅画的话,那也不是那种须眉毕现的写实派,而是感觉派的点彩。
如果说前三部交响乐是贝多芬的一面,即英雄、命运和欢乐,那么第四和第六则是贝多芬的另一面,即青春、爱情和自然。前者呼应着那个时代革命与英雄的主题,后者回荡着那个时代回归人性与自然的回声;前者是贝多芬的理想,后者则是贝多芬的幻想。如此阴阳契合,方才是立体的贝多芬。
下面,我们把莫扎特和贝多芬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他们音乐的不同特色。在音乐史或有关音乐评述的文章中这样的比较屡见不鲜:许多人爱把他们两人进行对比,仿佛他们是一对性格迥异的亲兄弟。这确实是一种有意思的现象。
比如柴可夫斯基就多次进行这样的对比:“莫扎特不像贝多芬那样掌握得深刻,他的气势没有那样宽广……他的音乐中没有主观性的悲剧成份,而这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是表现得那么强劲的。” [29] 他还说:“我不喜欢贝多芬。……我对他怀有惊异之感,但同时怀有恐惧之感。……我爱莫扎特却有如爱一位音乐的耶稣。莫扎特……的音乐充满难以企及的美,如果要举出一位与耶稣并列的人,那就是他了。” [30]
丰子恺这样表述他的对比:“贝多芬……是心的英雄,他的音乐,实在是这英雄心的表现。在莫扎特(Mozart),音乐是音的建筑,其存在的意义仅在于音乐美。至于贝多芬,则音乐是他的伟大的灵魂的表征,故更有光辉。即莫扎特的音乐是感觉的艺术,贝多芬的音乐则是灵魂的艺术。” [31]
写《音乐的故事》的作者保罗·贝克这样进行他的对比:“人们有时把莫扎特和贝多芬称作音乐界的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前者注重结构的完美,后者则喜欢气势的恢宏。人们有时也把莫扎特和贝多芬比作歌德和席勒,前者的作品纯朴自然,而后者的作品感情浓烈、内涵丰富。诸如此类的比较对于人们理解他们的艺术风格可能具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似乎缺乏深度,而且没有触及他们艺术创作内在的共同特征。纵观艺术发展的历史,我认为伦勃朗是惟一一位可与贝多芬媲美的人物。贝多芬和伦勃朗的作品都具有一种摄人心魄的表情力量,情感表现的力度和深度以及乐观昂扬的精神都无与伦比。” [32]
很少有人拿莫扎特和其他音乐家对比。拿莫扎特和贝多芬对比,说明他们两人地位旗鼓相当,也说明了拿二者对比的人的心目中对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态度以及对艺术人生的态度。
我更愿意从这样一点来对比莫扎特和贝多芬,即他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态度及其在音乐中的表现。之所以选择人生苦难这一点来作为比较的基点,是因为这一点是他们两人共有的,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都是他们共有的磨难,也是他们共有的财富。
难道不是这样吗?疾病、贫穷、孤独、嫉妒、倾轧……如黑蝙蝠的影子一样紧紧跟随着他们。谁会比他们更悲惨呢?只不过,贝多芬比莫扎特多了耳聋和一辈子没有爱情的悲惨,而莫扎特则比贝多芬多了早逝的悲惨。而且,同样生活在维也纳,莫扎特要贫寒得多,贝多芬虽然有过贫穷的童年,但到维也纳不久就得到了宫廷顾问官勃朗宁夫人的资助,生活在富丽堂皇的顾问官家中,苦难离他远去。此后这样欢迎他的贵族宅邸对于贝多芬来说屡见不鲜,甚至曾经有一位公爵慷慨地提供一支管弦乐队专门为他作曲实验用。虽然贝多芬与这样的贵族气氛并不相容,但他还是不客气地享用了,莫扎特哪里有这样的福气?同样死在维也纳,莫扎特的葬礼比起贝多芬由维也纳政府出面举办的2万人参加的壮观葬礼,则显得凄凉万分,他没钱去买埋葬自己的墓地,只是被随便埋在了一个贫民的公墓里,由于下葬的那天下起了冬雨,连亲戚朋友都没有什么人来,他的妻子正病重爬不起来,以致她之后再来找他的墓地都找不到,从此以后他到底埋在哪里也就无人说得清楚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此深重的苦难,表现在他们的音乐之中却是那样的不同。傅雷曾经说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透露他的痛苦的消息,非但没有愤怒与反抗的呼号,连挣扎的气息都找不到……音乐史家都说莫扎特的作品所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是的,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反抗的工具,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使般的温柔。” [33] 他评价说:“没有一个作曲家的音乐比莫扎特的更近于‘天籁’了。” [34]
一个“天使”,一个“天籁”,傅雷特意用了这样两个词来形容莫扎特的音乐,这是他对莫扎特的独特认识和理解。这确实是莫扎特对于苦难的态度,他的音乐因此才显得那样与众不同。在莫扎特所有的作品里,我们找不到一点他对生活的抱怨,对痛苦的咀嚼,对不公平命运的抗击,对别人幸运的羡慕,或是对世界故作深沉的思考以及自以为是的所谓哲学的胡椒面……他的欢快,他的轻松,他的平和,他的和谐,他的优美,他的典雅,他的幽邃,他的单纯,他的天真,他的明静,他的清澈,他的善良……都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情不自禁的流露。他不是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恬淡,不是“闲云不作雨,故傍青山飞”式的超然,不是“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式的宁静,不是“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式的喜悦,也不是“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式的安然……他对痛苦和苦难不是视而不见的回避和如禅家般的超脱,而是把这痛苦和苦难嚼碎化为肥料重新撒进土地,不是让它们再长出痛苦带刺的仙人掌,而是让它们开出芬芳美丽的鲜花——这鲜花就是他天使般的音乐。傅雷说莫扎特的音乐表现了他天使般的温柔,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自己得不到抚慰,却永远在抚慰别人。……他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幸福,他能在精神上创造出来,甚至可以说他先天就获得了这幸福,所以他反复不已地传达给我们。” [35] 傅雷说得真好!我还没有看到别人将莫扎特说得这样淋漓尽致,这样深入骨髓,这样充满着发自内心的理解和感谢。傅雷是莫扎特的知音。
贝多芬和莫扎特不同,他对于苦难反抗之心很强烈,这明晰地刻印在他的行为轨迹和他的乐思之中。
当得知自己患病将致耳聋的消息后,他便极其痛苦地诉说不已:“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一切心爱的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 [36] (1801年致阿门达牧师)“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 [37] (1801年致魏格勒)我们很难从莫扎特那里听到这样悲观和激愤的话语。当贝多芬看到别人可以听到,而自己却听不到时,他感到无比的痛苦和屈辱,甚至多次想以自杀结束生命,这样颓败的心情与极端的方式,在莫扎特那里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只要想想在那冬天没钱买炭的饥寒交迫的日子里,莫扎特所采取的抱着妻子跳舞取暖也要活下去的乐天态度,便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看待生命及处世的态度是如何的不同。
当然,贝多芬最终以自己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这一切苦难,但是,他是经过了激烈的内心冲突,以起伏跌宕的姿态勾勒出自己的行为曲线的,他犹如一棵暴风雨中的大树,抖动着浑身摇摆的枝叶,在大地与天空之间为人们留下了激动甚至狂躁的身影。如此的性格和态度,一定会在他的音乐里留下同样澎湃的心理谱线。也许,这就是我们在听他的《命运》、听他的c小调钢琴奏鸣曲《悲怆》、听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等时所感受到的对命运不屈抗争的心声。
贝多芬明确地主张:“音乐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出火花。” [38]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渗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 [39] 因此,在他的音乐里,听得到他明确的主观意图,他棱角鲜明的性格,他抽象的哲学意义,和他史诗般宏大叙事的胸怀。因此,在他的音乐里,他把苦难演绎得极其充分、淋漓尽致,不是渲染它或宣泄它,而是重视它超拔它,以此反弹于他的乐思中乃至他对传统音乐创作规范的突破上。因此,即使在苦难的深渊中也有对欢乐的讴歌,如第九交响乐末乐章的《欢乐颂》,给予我们的是从天而降的欢乐,和所经历的那些苦难一样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那力量,是大众的,是你我都具有的。莫扎特的欢乐是个人化的,是甜蜜的,是潺潺的小溪;贝多芬则是欢乐的大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莫扎特更像巴赫,而贝多芬更像亨德尔。
贝多芬和莫扎特在生活经历上有那样多的共同点,但在音乐的表现上却是那样的不同,其中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是由于莫扎特短暂的一生都沉浸在音乐之中,音乐融化了他,他自己也化为了音乐;而贝多芬却从小就喜爱哲学和文学,年轻时爱读莎士比亚、莱辛、歌德、席勒的作品,曾经专门拜访过歌德两次,并把自己根据歌德的诗《大海的寂静》谱写的康塔塔总谱献给了歌德,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还专门到波恩大学听哲学课,他比莫扎特吸收了更多的营养。这些滋润着他的音乐,也使他的音乐比莫扎特更为丰腴,气势更磅礴,思想的力度也更强悍。如果说他们两人都是天才的话,莫扎特是上帝造就的天才,具有先天性,而贝多芬是后天造就的天才。
贝多芬曾经说过:“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 [40] 在这一点上,贝多芬和莫扎特是一致的,他们的音乐在这一交叉点上汇合。所以,我们在贝多芬的某些音乐中听到莫扎特的影子,比如第一交响乐,比如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便不会感到奇怪。
说到这里,我们又在不由自主地对莫扎特和贝多芬两人进行比较了。说起这样的比较,让我想起傅雷和傅聪父子,他们对莫扎特和贝多芬也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只是说的话不尽相同。
傅雷这样说:“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末莫扎特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信心。” [41]
傅聪这样说:“我爸爸在《家书》里有一篇讲贝多芬,他讲得很精彩,就是说,贝多芬不断地在那儿斗争,可是最后人永远是渺小的,所以,贝多芬到后期,他还是承认人是渺小的。……贝多芬所追求的境界好象莫扎特是天生就有的。所以说,贝多芬奋斗了一生,到了那个地方,莫扎特一生下来就在那儿了!” [42]
傅聪这话讲得很有意思,比父亲讲得要通俗,却更形象,也更能让我们接受;比丰子恺讲得更深沉;比柴可夫斯基讲得更实在。傅雷更多地还是从传统的思想意义上来比较莫扎特和贝多芬,多少带有阶级斗争时代的味道,这和他以前所讲的莫扎特音乐“天使”和“天籁”的特点相去甚远,因为一个“信心”是无法涵盖“天使”和“天籁”的内涵的。
我常常想起傅聪讲的这句话:贝多芬奋斗一辈子好不容易才到达的地方,原来莫扎特一出生就站在那里了。这对于贝多芬来说是多么残酷的玩笑和现实!贝多芬和莫扎特之间的距离竟然拉开了这样长(是整整一辈子)!
在中国,一般而言,更多的人知道贝多芬,对贝多芬更为崇拜,莫扎特的地位要在贝多芬之下。我们一直崇尚的是战斗的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忽略了无论与天与地还是与人,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和谐关系、相濡以沫的关系、相互抚慰的关系。如果说前者有时是生活和时代必需的,那么后者在更多的时候一样也是必需的。如果说前者要求我们锻炼一副外在的钢铁筋骨,那么后者则要求我们有一颗宽厚而和谐的心灵。锻炼外在的筋骨不那么困难,但培养一颗完美的心灵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一般运动员可以从小培养,音乐家尤其是像莫扎特和贝多芬这样的,却很难从小培养,他们大多是天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天生只崇拜贝多芬式的不向命运屈服的英雄,我们一样崇拜温柔如水、天使天籁般的莫扎特,尤其是在日复一日单调而庸常的日子里,我们离后者更近,也更向往,更觉其亲切。
傅聪在解释父亲上面讲过的那句话“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末莫扎特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信心”时,又特意补充说:“我觉得中国人传统文化最多的就是这个,不过我们也需要贝多芬。但中国人在灵魂里头本来就是莫扎特。” [43] 我不知道傅聪这样解释是否符合傅雷的本意,但这话很让人深思。中国人在灵魂里头本来就是莫扎特,我们本来应该很容易接近莫扎特,可是,我们却离莫扎特那么遥远。我们很容易轻视莫扎特,以为莫扎特只有旋律的优美。
德沃夏克在布拉格音乐学院执教的时候,不允许他的学生轻视莫扎特。他曾经在课堂上向一个学生提问:莫扎特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学生回答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当时,德沃夏克非常恼火,抓住这个学生的手,把他带到窗子旁边,指着窗外的天空厉声问他看到了什么东西。学生莫名其妙,异常尴尬。德沃夏克气愤异常地反问他:“你没有看见那太阳吗?”然后严肃地对全班学生讲:“请记住,莫扎特就是我们的太阳!” [44]
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回溯历史,莫扎特和贝多芬不同的风格很像是上一个世纪的巴赫和亨德尔,他们是新世纪的双子星座。莫扎特在室内乐、交响乐、协奏曲和歌剧几个方面全方位出击,将他对社会的理解融入和谐美丽的音乐之中,他是以自己的痛苦化为温柔的音符来抚慰这个世界的。而贝多芬则是以他横空出世的交响乐震响着这个世界,将器乐的理想发挥到那个时代的极致,直面人生且挥舞着时代的大旗。
莫扎特的音乐是一派天籁,贝多芬的音乐是一片浪潮。
莫扎特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心中粗糙坚硬的东西变得柔软,贝多芬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心中柔弱淡薄的东西变得强硬。
莫扎特的音乐是把痛苦点石成金化为美的境界,贝多芬的音乐是把痛苦碾碎成药滋养着人生升华为崇高的境界。
莫扎特的音乐是含有抚摸性质的,贝多芬的音乐是具有破坏力量的。
莫扎特给我们以信心,贝多芬给我们以勇气。
贝多芬站在遥远的前方,莫扎特就站在我们的面前。
在世界上所有的音乐家中,没有谁比他们两人更适合于我们中国人了。
他们两人的音乐也是抚慰和激励世界所有人的艺术,至今拥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莫扎特个人化的抒情风格,影响着以后的舒伯特和门德尔松,而贝多芬晚期作品所呈现出的对个性与自由的张扬,已经打开了通往浪漫派音乐的大门,他的宏大叙事风格则影响着以后更多的人,包括马勒、瓦格纳和布鲁克纳,甚至我们的冼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