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禄时期(1688—1704)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町人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在社会上日益显示出重要地位。与此相应的,反映城市居民生活的“町人文化”兴起,出现了一批以描写町人生活为主要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主要反映了町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两面:发财致富和生活享乐,特别是情欲方面的享乐。井原西鹤(1642—1693)的作品集中描写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其中《好色一代男》、《好色二代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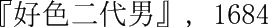 )、《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人女》(
)、《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人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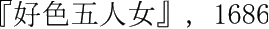 )等浮世草子生动地再现了町人追求情欲享乐的生活。
)等浮世草子生动地再现了町人追求情欲享乐的生活。
《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等作品的好色部分是不容回避的,但是井原西鹤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作家,他不是为了作为消费目的把好色部分呈现出来吸引大家的眼球,而是有非常深入的对社会的批判和思考,同时,也有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伦理思想要表达,在这个前提下他写了这样一部书。“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去,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
 如果不将“浮世草子”这一特殊文体放置于17世纪前后日本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环境中去考察,如果不联系日本近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草子中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实际上,通过阅读书中的“好色”描写,我们发现井原西鹤要呈现的“好色”不仅仅包括色情,还有很多物质性的欲望,通过写作他试图把欲望看破,要分析欲望到底是什么,然后一方面肯定欲望的正面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要反思时人对欲望无止境的追逐,所以某种过程的呈现是必要的。同时《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就这一方面而言,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是非常好的范本,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小说,通过还原作者的道德立场来重新构建文学写作跟当时社会时代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将“浮世草子”这一特殊文体放置于17世纪前后日本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环境中去考察,如果不联系日本近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草子中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实际上,通过阅读书中的“好色”描写,我们发现井原西鹤要呈现的“好色”不仅仅包括色情,还有很多物质性的欲望,通过写作他试图把欲望看破,要分析欲望到底是什么,然后一方面肯定欲望的正面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要反思时人对欲望无止境的追逐,所以某种过程的呈现是必要的。同时《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就这一方面而言,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是非常好的范本,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小说,通过还原作者的道德立场来重新构建文学写作跟当时社会时代之间的关系。
《好色一代男》开篇这样写道:“樱花很快就要凋零,会成为人们感叹的题目。月亮普照大地之后,很快又没于山际。唯独男女之间的恋情绵绵无尽。”
 这一段从日本文学中的传统意象“樱花”和“月亮”开始,感叹“樱花”和“月亮”易逝,美的短暂和难以持久,转而引入该书的主旨——赞颂恋情,不过从后文的阅读中我们发现赞颂的并非爱情,而是好色、风流,书中人物追求的不是精神层面的超脱,而是官能层面的享受。《好色一代男》首先介绍了主人公的父亲梦介,他出生在但马国一个有银矿的村落,不必为生计所苦,一味地逐香猎艳,在京都与最红的三位日本妓女厮混,过着醉生梦死、放浪形骸的生活,并与其中的一个妓女生下世之介。
这一段从日本文学中的传统意象“樱花”和“月亮”开始,感叹“樱花”和“月亮”易逝,美的短暂和难以持久,转而引入该书的主旨——赞颂恋情,不过从后文的阅读中我们发现赞颂的并非爱情,而是好色、风流,书中人物追求的不是精神层面的超脱,而是官能层面的享受。《好色一代男》首先介绍了主人公的父亲梦介,他出生在但马国一个有银矿的村落,不必为生计所苦,一味地逐香猎艳,在京都与最红的三位日本妓女厮混,过着醉生梦死、放浪形骸的生活,并与其中的一个妓女生下世之介。
《好色一代男》以世之介的男性视角讲述故事,小说中所有的男性无论富贵贫穷,不问出身,只看重好色的体验。整部小说以世之介的冶游之旅为中心线索,纵观世之介的一生,无论是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落魄贫穷的青年时代还是富庶无忧的后半生,其唯一的追求就是好色体验的满足。世之介年仅8岁就懂得托请僧人代写情书,尚未成年便开始和各种女人厮混,即便因行为放荡被父亲逐出家门依然毫不悔改,即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仍然贪恋一夜忘形之欢。贫困潦倒之际,从九州的小仓、下关,流浪到佐渡的金山,北国的酒田,凡娼妓麇集之处,无不尽情狎游。从19岁到33岁的15年间,世之介不是通过勤俭创业而是冶游学得通达世故。及至父亲去世,世之介继承遗产后更加放浪形骸,从35岁起,历27年,遍游京都、江户、大阪三大都市的妓院,以各地的一流名妓为对象,过着渔色无度的生活。
与《好色一代男》形成对应,《好色一代女》以女性在好色场的生活为中心线索,用女性视角去讲述好色故事。与世之介相似,一代女出生富贵之家,美貌好色,她始终渴求爱情与色欲的满足,一生辗转于形形色色的男性之间,上至大名诸侯下至仆从梳头匠,在欲望的过度放纵中逐渐耗尽了青春颜色,最终隐居深山孤独终老。与世之介形成对照,随着年龄增长,一代女的生命轨迹是向下的抛物线,从宫廷、官家堕入娼门,在妓馆又来客日稀,迫不得已,典质为下等娼妓。历经13年的苦难,典质期满,却无家可归,更无以谋生,只得做寺院杂役、商家女佣、卖唱女尼、梳头师傅、女佣佣人、茶饭女侍、私娼、伴旅女佣等等,在颠沛流离之中苦熬岁月,及至老年,在孤寂忏悔中度过余生。
世之介的足迹遍布日本关东、东北、九州各地,从繁华的都市江户、京都、大阪、奈良到偏僻的长崎、博多等地,在地理空间的迁移中读者得以阅尽世俗生活百态。与世之介相比,一代女的活动范围则比较狭窄,主要局限于京都、东京、大阪三地,但在社会各阶层摸爬滚打的过程中她结识了身份地位不同的男性,在一代女与这些男性的纠缠中读者同样看到了社会世俗生活的全景。通过一代男和一代女的人生轨迹,井原西鹤既写了乡村,也写了城市,人们要么勤恳经商要么辛苦耕种,然而无论贫穷还是富庶,他们的人生理想毫无例外都是纵情声色,在所有人身上我们感受到的都是难以遏制的欲望。不难看出,与将来、来世相比,他们更为重视现在、现世的生活与享受,信奉的是及时行乐、抓住今天。西鹤在创作好色物时,逐年记叙主人公的事迹,不侧重心理描写和抒发感情,而是着重叙事状物,刻画情状和行动;强调的是彻底的性享乐,把佛教信仰和儒家伦理,一概斥之为平庸的说教,抛于九霄云外。
世之介,与其说是一个好色浪子的个体,不如说是当时千千万万出生于商家子弟的集合体,他的生活经历集中体现了当时市井商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很显然,世之介的道德观与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相违背。他无视他人眼光,完全听任自己的内心欲望驱使,也正是这种生存方式,反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物内心,更清晰地认识当时的日本社会。世之介不是被教化的对象,通过他的行为,真实的人和社会被展现于读者面前。而一代女则是一个本能性的女性,她生为贵族闺秀,由于不能抵制欲望的诱惑,逐步堕落,酿成一生的悲剧。这里也反映出,即便是追求享乐的町人,对男性和女性仍然有双重道德标准,相较于对男性的宽容,女性的欲望是难以得到社会承认的。这种倾向在《好色五人女》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好色五人女》包括五个根据当时实事写成的短篇,所叙多为女人因争取爱情而遭遇厄运的悲惨故事。无论女性的身份如何,是女佣还是小姐,都因爱欲私情,无法见容于社会,最终走上绝路。唯一一篇有美满结局的则是为了赞美少女对爱情的纯真坚定。
作者将“好色”作为人际关系的纽带,在好色物所描述的伦理社会中,父子之反目,友朋之结交,生意之往来,娼门之游狎,所有的人际关系均围绕好色展开,好色弥漫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刻。“好色”是汉语词汇,随着中日交流很早就传到了日本。这个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无疑是个贬义词,但是在日本,“好色”却是个中性词,到了近世则演变为一个褒义词,在意义上接近中文的“风流”“风雅”,剔除了汉语中否定的道德价值判断。“日本固有的文化则淡化伦理思想,不以伦理道德的善恶来审视‘好色’,而从情感、审美出发,采取以真、美为主的判断、审美基准。”

基于这样的理解,好色物无关道德价值判断,井原西鹤只是客观地呈现市井生活,所以“好色”主要是在世俗伦理的层面上展现,经由好色看破和揭穿的,是世俗的人情。这种世俗伦理,涉及父子、夫妇、友朋等诸多方面,涵盖了亲族关系、家庭伦常、朋友往来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而对好色无条件、无止境的追逐,正是伴随着日本近世商业社会的兴起而出现的基本人情世态。这种世俗伦理肯定欲望,将毫不加以掩饰的好色表现在日常交往中,脱离了伪善,表露出真善的一面。因此,客观上,好色物表现的世俗伦理就与江户时代的刻板儒家伦理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冲突。
井原虽然没有刻意去渲染市井世俗伦理与儒家礼教伦理的冲突,或者说他主观上也不是为了反映这种冲突,但是他在写好色的时候,带有明显的弱道德化的冲动。在井原的笔下,无论是世之介,还是一代女,又或者是那些只是过客的男男女女,他们都被置于同一个价值层面。这些人物身上的道德自律感均被作者弱化,以世之介为例,他与无数女子海誓山盟,可是一旦身陷困境便毫不犹豫地弃她们于不顾。
之所以称为弱道德化而非去道德化,因为井原并非滤除是非善恶,他只是渲染了人的本能中趋向现世享乐(被感官所确认)的一面,其书中的人物仍然有是非观念,也没有摒除道德观。因此,荒唐的梦介在面对儿子的荒唐时把他逐出家门,世之介也不怨恨父亲,认为这是干了坏事应受的惩罚。在“出乎意料的女人”一节,世之介勾引一位有夫之妇被设计惩罚,头上重重挨了一劈柴却并未报复,反而自称这是不道德恋爱导致的后果,同时感慨“人世间的确有这样谨守贞操的女子”
 。
。
在世之介的眼里,最重要的是现在,是抓住今天、及时行乐。借由世之介的内心活动他明确表达出这种现世哲学观:“信佛毫无乐趣,来世如何,谁也没有看见过,最终还是觉得以往那种既不近鬼神、也不见佛院的人间俗世更好些。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呜呼哀哉,他认为这才是考虑人生的主要依据。”
 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来世,而在现世的感官世界中,“好色”是首要的动力和最后的目的。井原以弱道德化的立场把人的是非观念放得很松,客观上助长了社会的伦理混乱,更重要的是给读者留下了需要考量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道德?是诚与真、忠于自己内心的欲望是道德,还是压抑自己才是道德?井原显然不是要把世之介只写成淫棍、坏人,他某种意义上是不道德的,书中也有世之介被拒绝、被斥责不道德的时候,但作者的意思是,世之介也好,晚年忏悔的一代女也罢,他们只是被欲望所羁绊的人,深陷在欲望里的人,在欲望中不知道克制的普通人,这里体现出作者悲悯的地方。
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来世,而在现世的感官世界中,“好色”是首要的动力和最后的目的。井原以弱道德化的立场把人的是非观念放得很松,客观上助长了社会的伦理混乱,更重要的是给读者留下了需要考量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道德?是诚与真、忠于自己内心的欲望是道德,还是压抑自己才是道德?井原显然不是要把世之介只写成淫棍、坏人,他某种意义上是不道德的,书中也有世之介被拒绝、被斥责不道德的时候,但作者的意思是,世之介也好,晚年忏悔的一代女也罢,他们只是被欲望所羁绊的人,深陷在欲望里的人,在欲望中不知道克制的普通人,这里体现出作者悲悯的地方。
好色物中的“好色”,固然有为读者所诟病的专意于色的一面,但也写到了作为性风俗和性文化的一面。实际上,井原的小说诚实地反映了町人生活,生动刻画出町人生活的甘苦不一。小说虽以花街柳巷为活动舞台,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冶游场中放浪形骸的肉欲行为,但同时他是将好色作为一种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的社会交往和娱乐方式,所以既辅之以弹琴、吟唱谣曲、射箭等游戏名目,又穿插了盂兰盆节、过年、无神月等节庆,还极尽笔力描写与时令相应的服装。由此,好色既是俗事,又是雅事。通过叙事者的眼光,浮世草子的主题涉及社会的商业、经济、市井文化、道德及文化观念等众多主题。因此,井原的好色物虽然处于色情泛滥的文化系统之中,但他与纯粹的色情小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也是井原的后继者无法企及之处。那么,井原的“好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或者说是有意义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要思考:为何日本的好色物创作,会在德川幕府时期发生。
回到井原西鹤创作《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的伦理现场,一方面,德川幕府初期的三代将军实行武力统治和集权政治,建立了牢固的封建体制。在此基础上,从第四代将军家纲开始,经纲吉、家宣、家继,在近65年左右的时间(1651—1716)是礼教政治的时代。“这种礼教文化政治的开始,不仅是国民文化昌盛的具体表现,而且大部分是以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勃兴为基础的。”
 实行礼教政治的目的是按照儒教的政治理想教化人民,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缓和幕府初期的武力杀伐之风,促进社会的和平与安定。另一方面,以藤原惺窝(Seika Fujiwara)为代表的京学和继承了土佐的南学是儒学的核心。他们要求严格道德自律,以南学为例,其特点是要恢复和弘扬朱子学中的伦理道德思想。山崎闇斋(Ansai Yamazaki)为了重新回归于朱子学的根本精神——人伦道德思想,主张倡明伦、重正名、论正统。但是,礼教政治、严格的道德自律与实际社会生活商业化、欲望化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隙缝。对人们而言,一方面必须遵循维护基本上排斥欲望的“礼”,另一方面却又难以剥离自己的欲望和功名利禄之心。很多人自然地在追求自己欲望的过程中,将儒教变成一种“伪装”。
实行礼教政治的目的是按照儒教的政治理想教化人民,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缓和幕府初期的武力杀伐之风,促进社会的和平与安定。另一方面,以藤原惺窝(Seika Fujiwara)为代表的京学和继承了土佐的南学是儒学的核心。他们要求严格道德自律,以南学为例,其特点是要恢复和弘扬朱子学中的伦理道德思想。山崎闇斋(Ansai Yamazaki)为了重新回归于朱子学的根本精神——人伦道德思想,主张倡明伦、重正名、论正统。但是,礼教政治、严格的道德自律与实际社会生活商业化、欲望化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隙缝。对人们而言,一方面必须遵循维护基本上排斥欲望的“礼”,另一方面却又难以剥离自己的欲望和功名利禄之心。很多人自然地在追求自己欲望的过程中,将儒教变成一种“伪装”。
从文学上来看,礼教政治的实施一方面帮助人们从贵族、僧侣的文学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在儒教道德的训诫之下人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欲望,面对色欲问题,不管是言论还是行为,都慎之又慎。然而实际上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圣人,这时候大家就进入伪装,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即直接来肯定自己的欲望,还是把自己打扮成道学家,这是井原西鹤在好色物中思考的问题。在井原的笔下,好色物所反映的世俗社会中,欲望尤其是色欲的泛滥,使得处于其对立面的儒家伦理和价值观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以此为出发点,井原西鹤的好色物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拒绝说谎,也就是说,井原通过文学创作引入了道德生活的一个新纬度——真诚或者说真实。真诚问题作为道德的要素之一,在日本近世出现,有极其复杂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比如说历经战国之乱后封建秩序的重建和社会重组,但是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最为根本的原因是自17世纪开始的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明显增加。在17世纪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增长的现实中,社会中的个体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武士地位开始走向衰落,市民阶层地位提升,尤其是以商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快速崛起。问题在于,这种阶层地位变动的内在需要,与儒教恒定的道德束缚之间构成了矛盾冲突。“士农工商”等级位序的变动,固有的儒家礼教伦理模式与新生的市井世俗伦理产生了尖锐冲突,这样一来,就为新的伦理思想预留了位置。
井原观察和剖析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肯定他们的享乐与营利行为,并亲自投身其中,用充满俳谐风格的文章描写了这一切。对新兴阶层町人来说,好色是唯一能摆脱封建道德和等级制度,凭借金钱就可以自由享乐的世界。“好色”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说明市民至此才有了提倡自己的世界观、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的有力支柱。井原的受欢迎,恰恰表现出蓬勃向上的市民阶级的力量。所以,究其根源:其一,德川幕府统治中期,富庶稳定的社会中人们似乎很容易纵情于男女好色;其二,井原所写的好色,源于当时的社会风气本身的好色,小说不过是对伦理现场的一种记录而已。
当然,井原西鹤写作好色物的目的显然不止于记录、还原伦理现场。应该指出好色物也不是对现有道德秩序的批判和动摇,作家也没有重建善恶及道德秩序的主观意图。因为在好色背后起作用的,是个人的欲望,按照这样的观察和逻辑,井原西鹤把对道德的区分问题,压缩为受欲望控制的程度问题;把对恶的批判,转变为对欲望的批判。所以,他的“好色物”在客观上体现出对好色本身的反思。
当我们把时间放在17、18世纪的大背景之下,会发现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巧合,在西方已经经历了宗教变革,文学方面则已经迎来了文艺复兴的高潮,在中国有儒家思想从程朱到阳明的思想转折,他们几乎同时产生。在日本,15至16世纪战乱频仍,经过了长达100多年的内乱才终告统一,如果说在乱世中人们更多地渴望稳定的秩序,那么江户时期的人们虽然仍为谋生所苦,但已经从关注外部世界转向个人的内心世界,个人欲望的满足便成了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所以,从欲望角度来说,东西方差不多同时出现对欲望管理的松动,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再排斥欲望,只能是虚伪。那么怎么看待欲望,在中国,从王阳明开始,欲望就开始纳入思想史的讨论,阳明学的初衷,是为了重构崩溃中的社会伦理秩序,不过他对“心”的强调,在客观上却加速了社会体制的崩溃。“他时时刻刻强调天理,却最终走向了人欲。至王船山,‘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矣’这样的经典表述至终于被堂而皇之地提了出来,成为了明末清初的主流思想。”
 在日本,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儒家思想内部也出现了批判和改造它的动向,如阳明学、古学派及国学。在研究日本古典文学——和歌的基础上,力求从宋明理学和佛教道德中解放出来,试图从日本的传统文学中探求大和民族固有的精神,抒发真实的感情。所以,当时从东西方看,大家都面临相似的转折问题。具体到情色文学的出现,东西方出现的时间也差不多,中国是16世纪,西方的高峰在18世纪,日本则是17世纪。
在日本,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儒家思想内部也出现了批判和改造它的动向,如阳明学、古学派及国学。在研究日本古典文学——和歌的基础上,力求从宋明理学和佛教道德中解放出来,试图从日本的传统文学中探求大和民族固有的精神,抒发真实的感情。所以,当时从东西方看,大家都面临相似的转折问题。具体到情色文学的出现,东西方出现的时间也差不多,中国是16世纪,西方的高峰在18世纪,日本则是17世纪。
在这个观念变革中,传统礼仪结构开始变化,在《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里可以看到儒教与现世享乐观念之间的角力,虽然儒教的忠孝节义没有被摧垮,但也不是理想的出路。在日本传统文学中,佛、道历来是人物、也是社会的一个归宿,是对现实世界否定的动力,平安时代紫式部(Shikibu Murasaki)的《源氏物语》、室町时代的军记物语、松尾芭蕉(Basho Matsuo)的俳句都是这样,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同样把佛、道作为出路。所以他对于男女之情的描写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世俗色情的层面,而是由对好色的描摹走向对虚无的体悟。
在《好色一代男》的结尾,已经年老体衰,逐渐走向死亡的世之介并没有如传统文学中的人物(比如光源氏)那样幡然悔悟、遁入空门,而是把剩余的家产6000两黄金埋于东山深处,造一只船,取名“好色丸”,用曾经欢好的妓女遗下的贴身裙做了船的风帆,邀约了6位同道中人,扬帆出海向着传说中的“女护岛”而去,从此音信杳然。品味这一幕,荒唐之余又觉出一种虚无,女护岛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一代女和一代男又大不相同,如果说井原西鹤以戏谑嘲弄的态度写世之介,那么对一代女他给予了更多的同情,世之介一直以主动的态度对待性,一代女却有身不由己的凄惶。作为男性,世之介不停地抛弃女性,而一代女始终被男性抛弃,世之介在贫穷时可以出卖劳力,一代女作为女性却只能出卖色相,随着年龄增长,青春不再,她的社会地位一降再降,从女官、诸侯妾、艺妓、娘姨、佣人一路堕落,最后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去做野妓。当世之介乘船出海寻找传说中的“女护岛”时,后者则隐居山林,清心寡欲,在佛教中寻找心灵的归宿。65岁时,某天顺路去佛殿参拜,但见500罗汉个个都像与她交往过的男人。在结尾处,主人公抚今追昔,无限感慨地说:“冬日的黄昏,山上万木凋零,樱树梢头积满了白雪,一片凄凉景象。但是季节循环,还有迎来鲜花开放的春朝时刻,唯有人类一旦上了年纪,就失去了任何乐趣。尤其像我这样的人,回顾自身的一切,真是令人羞愧难当。”
 临近生命的终点,一代女忏悔自己的过去,也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年轻人不要沉迷好色。
临近生命的终点,一代女忏悔自己的过去,也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年轻人不要沉迷好色。
“西鹤的‘好色物’,从《好色一代男》到《好色二代男》,再到《好色一代女》,都有一个从好‘色’的沉溺到‘好色’的解脱的过程,贯穿其中的就是‘色道’。‘浮世’的快乐莫过于‘好色’,但‘好色’须有‘道’,‘色道’就是将‘好色’加以特殊限定,就是要‘好色’者领悟到‘好色’的可能与不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成为有‘色道’修炼、有人生修养的‘帅人’,最终洞察人生、超脱浮世,使‘好色’有助于悟道和得道。这就是西鹤‘好色物’的真义。”
 井原西鹤好色物的立足点,不在对社会现实的全方位批判,所以小说并不严厉,只是在《好色一代女》中通过女主人公的沉痛忏悔和世之介的扬帆出海引入佛、道的价值纬度。作者并没有将好色视为社会的阴暗面,好色只是人性本然的一部分,所以大可不必把它视作洪水猛兽,无需对现实与社会状况过于悲观,但是井原毕竟看到了好色走入极端之后的可能性,所以在《好色一代男》中他只是将佛眼置于世之介的身后,若隐若现,体现出看透之后的空,但是在《好色一代女》中他则退回到彻底的佛教立场。井原根据这个立场对欲望本身展开终极性的反思。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佛眼又对人世间好色的煎熬以及沉湎于好色的昏昧与愚蠢,给予了无条件的慈悲和爱恋。佛对于一代女的宽宥和哀怜形成了一种屏障和保护,一代女理所当然获得了一种正面描述色欲的道德勇气。所以,《好色一代女》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依据一代女的自我忏悔的心理逻辑,娓娓道来之中她获得了道德的正当性,给后来者提供了某种道德上的警示和庇护。
井原西鹤好色物的立足点,不在对社会现实的全方位批判,所以小说并不严厉,只是在《好色一代女》中通过女主人公的沉痛忏悔和世之介的扬帆出海引入佛、道的价值纬度。作者并没有将好色视为社会的阴暗面,好色只是人性本然的一部分,所以大可不必把它视作洪水猛兽,无需对现实与社会状况过于悲观,但是井原毕竟看到了好色走入极端之后的可能性,所以在《好色一代男》中他只是将佛眼置于世之介的身后,若隐若现,体现出看透之后的空,但是在《好色一代女》中他则退回到彻底的佛教立场。井原根据这个立场对欲望本身展开终极性的反思。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佛眼又对人世间好色的煎熬以及沉湎于好色的昏昧与愚蠢,给予了无条件的慈悲和爱恋。佛对于一代女的宽宥和哀怜形成了一种屏障和保护,一代女理所当然获得了一种正面描述色欲的道德勇气。所以,《好色一代女》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依据一代女的自我忏悔的心理逻辑,娓娓道来之中她获得了道德的正当性,给后来者提供了某种道德上的警示和庇护。
一代女在晚年顿然彻悟,深感人世无常,便一心皈依佛法,在深山中结一庵舍,题名好色庵。早晚青灯木鱼,诵经念佛,追悔过去。《好色二代男》中的世传在33岁时大往生了,即使是在描写好色更为彻底的《好色一代男》中,也仍然流露出把佛教作为最后出路的意味。在“睡梦中的刀光剑影”一节,世之介在半睡半醒之际见到被他抛弃的四个女子的恶灵,她们咬牙切齿地轮番向他报复,世之介深感命丧于此,“于是,口诵佛经,抛下腰刀,伏拜西方净土”。在他得救之后发现这四个女人写的表示爱情的誓文均被撕得粉碎,“但是,其中请神降临的句子却完好无损”
 。好色物引入佛教思想,透过佛教的真妄纬度,历尽千帆后来回望人世间的欲望,其中的“性真”,这里的真,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是在佛教真妄意义上的真假,用以穿透世间诸相的虚诞与幻妄。正如一代男、一代女,遍历色之一道之后反而抵达空之彼岸。无论是寻找女护岛这个世外乌托邦,还是避居深山,可以清楚地看到井原的出世情愫。井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对好色展开了反思与批判。其次,在世俗人情的判断和态度上,好色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尺度,与传统的道德论并驾齐驱。井原对好色的推崇,显然是为了给真情率性和放达自由预留位置。由此可见,井原对于“真”的追求,实际上主导了对于俗世是非道德的评价。好色观的提出,作为对善恶道德观的补充,拓展了日本文学的文化视野和价值空间,在日本文学史上,这无疑是一件重要的事件。
。好色物引入佛教思想,透过佛教的真妄纬度,历尽千帆后来回望人世间的欲望,其中的“性真”,这里的真,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是在佛教真妄意义上的真假,用以穿透世间诸相的虚诞与幻妄。正如一代男、一代女,遍历色之一道之后反而抵达空之彼岸。无论是寻找女护岛这个世外乌托邦,还是避居深山,可以清楚地看到井原的出世情愫。井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对好色展开了反思与批判。其次,在世俗人情的判断和态度上,好色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尺度,与传统的道德论并驾齐驱。井原对好色的推崇,显然是为了给真情率性和放达自由预留位置。由此可见,井原对于“真”的追求,实际上主导了对于俗世是非道德的评价。好色观的提出,作为对善恶道德观的补充,拓展了日本文学的文化视野和价值空间,在日本文学史上,这无疑是一件重要的事件。
综观日本近世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阶层流动性增加、新兴商业伦理初步形成,以幕府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加强,依靠旧有的道德、伦理,已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控。在新旧交替的背景下,伦理秩序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所有这些内容,在井原西鹤的好色物中都有着明确的反映。因此,思想的变革主要在道德的领域内展开。好色物正是对道德展开讲述,并对市民阶层的人情伦理进行全面展示的作品。好色物对“好色”的发现,构成了反道德主义的一个重要参照,它包括了佛、道的本然与世俗的本能两个方面。好色物所强调的回到“本然”,主要还是回到心灵的空寂、澄明和无,很显然,那是一个欲望已尽的空寂。因此,虽然不相信来世,但是回复本然的观念,既提供了社会道德批判的动力,同时也暗示了出离世间的可能归宿。按照传统的道德观,世之介绝不是一个好人,但井原在好色物中有用真伪纬度来取代道德纬度的倾向。或者说,好色物在价值和道德层面上,真正关注的与其说是善恶问题,还不如说是真伪问题。这固然是好色物的局限所在,但真伪观的确立,也为了解日本近世伦理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