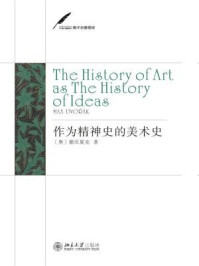“叙事一直是并且继续是历史著作中的主导性模式,任何有关历史著作的理论的首要问题,因而就不是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问题,而是要对叙事在历史学中的持久存在作出说明。一种历史话语的理论必须关注叙事在历史文本的生产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问题。”
 叙事乃是历史话语理论所首要关注的问题,对历史话语的叙事结构各个层面的分析,由此就构成为海登·怀特那套颇具形式主义色彩的理论框架的主要部分。
叙事乃是历史话语理论所首要关注的问题,对历史话语的叙事结构各个层面的分析,由此就构成为海登·怀特那套颇具形式主义色彩的理论框架的主要部分。
怀特在《元史学》一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其篇幅并不很大的导论部分。他在这里援引当代语言哲学、文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等多方面的学术资源,将叙事性话语结构分析为这样几个层面:(1)编年;(2)故事;(3)情节化(emplotment)模式;(4)论证(argument)模式;(5)意识形态蕴涵(ideological implication)模式。
与大多数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过去”不能直接呈现在研究者的面前,人们只能通过“过去”遗留到现在的种种“痕迹”(traces)来接近“过去”本身。这些“痕迹”中,包括考古发现、历史遗址、活生生的传统遗存等,而其中最主要的乃是各种文字记载。文字记载了过去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我们可以设想,过去发生的事件浩如烟海,不可胜数,得以通过留下“痕迹”而有可能为人们所知晓和了解的,只是其中极其微小的部分。事件发生而得到记录,才有可能成为历史事实。
 将历史事实纯然按照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记录下来,所产生的就是历史著作最简单和最初级的层面——编年(chronicle)。编年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它们只开始于编年史家开始记录之时,而结束于编年史家结束记录之时。在怀特看来,编年中所记载的各种事件,需要被编排进入一个有着意义和内在关联的话语结构,才能成其为故事。在许多文化及这些文化存续的很多时期内,都有编年的存在,但并不是在任何文化中都出现了将编年转化为故事的情形。
将历史事实纯然按照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记录下来,所产生的就是历史著作最简单和最初级的层面——编年(chronicle)。编年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它们只开始于编年史家开始记录之时,而结束于编年史家结束记录之时。在怀特看来,编年中所记载的各种事件,需要被编排进入一个有着意义和内在关联的话语结构,才能成其为故事。在许多文化及这些文化存续的很多时期内,都有编年的存在,但并不是在任何文化中都出现了将编年转化为故事的情形。
 编年中所描述的一些事件分别依据初始动机、过渡动机和终结动机被编排进入故事。故事有可辨认的开端、中段和结局,各种事件由此就在故事里进入到一种意义等级之中,共同构成为一个可以为人们所理解的过程。而故事的编排和叙事话语的最终完成,是与呈现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不同种类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编年中所描述的一些事件分别依据初始动机、过渡动机和终结动机被编排进入故事。故事有可辨认的开端、中段和结局,各种事件由此就在故事里进入到一种意义等级之中,共同构成为一个可以为人们所理解的过程。而故事的编排和叙事话语的最终完成,是与呈现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不同种类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在将从编年中选择出来的事件编排为故事时,就会出现历史学家在建构其叙事的过程中必须预料到并且要回答的此种性质的问题,诸如“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那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最终会是什么样?”等等,这些问题决定了历史学家在建构他的故事时所必须采纳的叙事策略。然而此种涉及各事件之间的关联并使得它们成其为一个可追踪的故事中的要素的问题,要区别于另一类问题:“总合起来是什么样?”“全部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与被视为一个完整故事的全部系列的事件的结构相关联,并且要求就某一特定故事与在编年中可能“找到”“辨识”或“发掘”出来的其他故事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全面的判断。可以有若干种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我将这些方式称之为(1)情节化的说明,(2)论证的说明,以及(3)意识形态蕴涵的说明。

由怀特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说,鲜明的问题意识是所有历史叙事话语赖以形成和展开的基础,因而那种将叙事史学区别于问题史学的观点未必就站得住脚。在编排故事这样一个构建叙事性历史话语的比较初级的阶段,历史学家关心的问题,是个别事件之间所可能具有的在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上的关联。而一旦要对整个历史构图进行把握,要将特定的历史事件与某个更大的整体关联起来而赋予其意义,要体验对于同一历史对象(或者同一些历史事件)所可能具有的不同历史构图之间所可能具有的关系,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就是更为宏观的、与历史叙事作为一个整体的特性相联系的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了。柯林武德的哲学强调的是一套问答逻辑,认为任何哲学思考都是对于特定的哲学问题的解答。不了解特定的哲学思考所企图去解答的问题,就无法达成对于该思想的真正理解。与此相关的是,在史学理论领域内,历史学家的研究归根结底乃是试图回答某些问题,没有鲜明的问题呈现在面前并致力于有效地解答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产生富有意义的史学(包括考古学)的学术成果。
 柯林武德在史学理论领域中所强调的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乃是历史学家在史学实践中应该自觉意识到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致力于解决特定的问题。勘定史实、重演历史行动者的思想、通过想象和逻辑推论重建各种事件之间内在和外在的关联,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按照常识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后者不过是在前者完成(或阶段性地完成)之后的文字记录,前者是“胸有成竹”,后者则是泼墨作画,将胸中之竹表现于实际画面。那么,从这样的常识观点出发,柯林武德心目中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提出并解决问题的程序,似乎主要地就是与历史研究的过程相关。与此相比较,上述引文中怀特所提出的对第二类问题的解答方式,则显然更多地与历史写作相关,与历史著作作为一种文学产品所具有的显著特征相关。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历史写作就表现得不像在传统和常识的观点之下那样居于一个附庸和次要的地位了。这是下文还要进一步探讨的内容。
柯林武德在史学理论领域中所强调的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乃是历史学家在史学实践中应该自觉意识到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致力于解决特定的问题。勘定史实、重演历史行动者的思想、通过想象和逻辑推论重建各种事件之间内在和外在的关联,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按照常识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后者不过是在前者完成(或阶段性地完成)之后的文字记录,前者是“胸有成竹”,后者则是泼墨作画,将胸中之竹表现于实际画面。那么,从这样的常识观点出发,柯林武德心目中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提出并解决问题的程序,似乎主要地就是与历史研究的过程相关。与此相比较,上述引文中怀特所提出的对第二类问题的解答方式,则显然更多地与历史写作相关,与历史著作作为一种文学产品所具有的显著特征相关。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历史写作就表现得不像在传统和常识的观点之下那样居于一个附庸和次要的地位了。这是下文还要进一步探讨的内容。
情节化、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是历史著作作为一种叙事话语所具有的三个基本层面,它们中的每一种又各有四种主要模式,可表示如下
 :
:

情节化是一种将构成故事的事件序列展现为某一种特定类型的故事的方式。人们可以通过辨识出被讲述的故事的类别来确定该故事的意义,情节化就这样构成为进行历史解释的一种方式。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是情节化的四种主要模式。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如果史学家赋予它一种悲剧的情节结构,他就是在按悲剧的方式来解释故事;倘若他赋予故事的是一种喜剧的情节结构,他就是在按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故事了。
在历史学家对故事进行情节化的层面之外,他还要致力于解释和说明故事“全部的意义”和“总和起来是什么样”。这就是情节化之外的论证的层面。论证是要通过援引某些人们认作历史解释的规律的东西,来表明故事中究竟发生的是什么。在这个层面上,历史学家要通过建构起某种规则—演绎性的(no-mological-deductive)论证,来对故事中的事件(或者是他通过某种模式的情节化而赋予事件的形式)做出说明。严格缜密者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理论立场,暧昧俗常者如“有兴盛就有衰落”这样的老生常谈,都可以作为论证所要援引的规律。论证模式直接关系到我们是以何种方式来看待历史世界。形式论的论证(formalist argument)
 是要通过辨识出历史领域内某一对象的独特性,来达到对于对象的说明。在理论阐发和史学实践中强调历史现象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和独特性(uniqueness)的赫尔德、蒙森等人,当是这一模式最恰当的体现者。有机论论证模式的特点则在于,将单个实体视作它们所构成的整体的部分,而整体不仅大于部分之和,在性质上也与之相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过程视为精神逐步实现自身的一个辩证过程,兰克的史学认为人类历史体现了某种人们虽然无从直接把握但却确定无疑地存在着的神意,他们的历史观都是有机论论证模式的样板。机械论则认为历史领域内的对象都存在于部分与部分的关系形态之中,表明了支配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规律的具体运作,研究对象就得到了说明。以种族、气候和环境作为解释历史现象的根本因素的泰纳以及实证主义史家如巴克尔都是典型例证。情境论的(contextualist)论证模式则强调,将事件置于它所发生的“情境”之中,通过揭示它们与在同一情境之下发生的其他事件的具体关系,就可以对该事件(或事件序列)何以如此发生进行解释。布克哈特的历史著作中的论证模式就是情境论的。
是要通过辨识出历史领域内某一对象的独特性,来达到对于对象的说明。在理论阐发和史学实践中强调历史现象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和独特性(uniqueness)的赫尔德、蒙森等人,当是这一模式最恰当的体现者。有机论论证模式的特点则在于,将单个实体视作它们所构成的整体的部分,而整体不仅大于部分之和,在性质上也与之相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过程视为精神逐步实现自身的一个辩证过程,兰克的史学认为人类历史体现了某种人们虽然无从直接把握但却确定无疑地存在着的神意,他们的历史观都是有机论论证模式的样板。机械论则认为历史领域内的对象都存在于部分与部分的关系形态之中,表明了支配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规律的具体运作,研究对象就得到了说明。以种族、气候和环境作为解释历史现象的根本因素的泰纳以及实证主义史家如巴克尔都是典型例证。情境论的(contextualist)论证模式则强调,将事件置于它所发生的“情境”之中,通过揭示它们与在同一情境之下发生的其他事件的具体关系,就可以对该事件(或事件序列)何以如此发生进行解释。布克哈特的历史著作中的论证模式就是情境论的。
意识形态蕴涵是情节化和论证之外历史叙事概念化的第三个层面,这个层面反映的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知识的性质是什么,以及研究过去对于理解现在而言具有何种意义这样一些问题的立场。而所有意识形态都无一例外地号称自身具有“科学”或“现实性”的权威。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蕴涵来进行历史著述。晚近以来,大多数史学家总是要或隐或显地表白自己在史学实践中摆脱了意识形态的侵扰(即便其中很多人并不讳言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立场),史学史家们则经常为在过往史学家客观表现过去的努力中渗入了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扼腕痛惜,“然而更经常的情形是,他们是在为那些表达了不同于他们自身意识形态立场的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而感到惋惜。正如曼海姆所言,在社会科学中,一个人的‘科学’在别的人来说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立场关系到人们对于当前社会实践的现状如何评判,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是(急剧地或渐进地)改变它还是维持现状——等问题的观点。这些立场和观点中主要的模式乃是这样四种: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
意识形态的立场关系到人们对于当前社会实践的现状如何评判,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是(急剧地或渐进地)改变它还是维持现状——等问题的观点。这些立场和观点中主要的模式乃是这样四种: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
如果说,历史话语所生产的乃是历史解释的话,历史叙事概念化的这三个层面,就分别代表了历史解释所包含的审美的(情节化)、认知的(论证)和伦理的(意识形态蕴涵)三个维度。在怀特看来,这三个层面所各自具有的四种模式之间并非可以任意随意组合的,它们之间具有一种“选择的亲和性(selective affinity)”,如前面列表所示。比如,在喜剧的情节化模式、有机论的论证模式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之间,或者,在讽刺剧的情节化模式、情境论的论证模式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之间就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然而,史学大师的作品的特质,却往往在于它们独具一种辩证的张力,将看似并没有亲和关系的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结合在一起,将一致性和融贯性赋予这些看似不甚协调的模式,而这恰恰构成了史学大师经典之作的魅力之所在。
 这种融贯性和一致性的基础何在,就成了由历史文本出发进行理论探讨的历史哲学所必须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怀特看来,“这种基础本质上乃是诗性的、具体而言是语言学的”。
这种融贯性和一致性的基础何在,就成了由历史文本出发进行理论探讨的历史哲学所必须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怀特看来,“这种基础本质上乃是诗性的、具体而言是语言学的”。
 这样,我们就触及怀特理论中至为重要而又最为含混和困难的转义理论。
这样,我们就触及怀特理论中至为重要而又最为含混和困难的转义理论。

在怀特看来,历史意识有一种深层的结构。历史学家在将表现和解释历史领域的各种概念化(情节化、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的各种)模式施展于历史领域中的材料之前,必须先将作为他研究对象的历史领域预构为一个精神感知的对象。这种预构行为乃是诗性的,它决定了历史学家表现和解释特定历史领域的言辞模型,“而且也构成了这样一些概念,被他用来辨识占据那一领域的对象,并描述它们彼此之间所维系着的关系。在先于对该领域的正式分析的诗性行为中,历史学家既创造了他的分析对象,又预先决定了他将用来解释对象的概念化策略的模式。”
 可能的解释策略的数量并不是无限的多,而是与诗性语言的四种转义(trope)相对应的。这种在先的语言和思维的转义模式,正是构成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并赋予历史学家的各种概念化层次以一致性和融贯性的基础。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怀特在别的地方所做的解说:
可能的解释策略的数量并不是无限的多,而是与诗性语言的四种转义(trope)相对应的。这种在先的语言和思维的转义模式,正是构成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并赋予历史学家的各种概念化层次以一致性和融贯性的基础。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怀特在别的地方所做的解说:
……倘若我所提出的情节化、解释和意识形态蕴涵的模式相互之间的关联是有效的话,我们就必须考虑这些模式在意识的某些更根本层次上有着其基础的可能性。……那一基础就是语言本身,它在诸如历史学这样的领域中可以说是在转义的方式上发挥着作用,以便在某种特殊的关系模式中预构出一个感知领域。……(倘若我们要在发展出来了一套专门的技术性术语的学科如物理学,和那些尚未产生出类似的有着确定语义和句法规则的学科之间作出分别的话),我们就看到历史学显然属于后一类领域。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当中的分析,不仅发生在事实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也发生在它们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而意义反过来,又是以自然语言本身的可能样态、并且具体而言就是那些经由不同的转义性运用而给未知的和陌生的现象赋予意义的主导性的转义策略来领会的。如果我们认为主导性的转义乃是四种: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和反讽(irony),那么很显然,在语言本身当中、在起源性的和先于诗性的层面上,我们就很可能找到产生那些必定会出现在任何尚未被完全驯服(学科化,disciplined)的研究领域中的解释类型的基础。

怀特在这里所着重指出的就是,历史学的这种诗性的层面、这种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是与历史著作本身作为言辞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分不开的:那就是它所使用的不是一套有着严格的语义规定、在某一知识共同体内几乎不会造成歧义的专业技术性术语,而是以日常有教养的语言为其基本的语言工具。历史叙事的语言不是透明的中介,而是有着所有诗性语言所共有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征,即便在表述事实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超出事实之外的蕴涵,此种语言在人们,包括职业历史学家们所注意到的“传达”(communicative)功能之外,还有着往往为人所忽视但对于历史叙事话语而言却至关紧要的“表情”和“达意”(expressive, conative)的功能。
 在《元史学》和随后的一些论著中,怀特都不断地或明或暗地表示,正是历史语言和历史意识所普遍具有的转义特质,使得转义的主要模式成为历史著作和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正是依赖转义性的预构行为而赋予其研究领域和概念化层次以一致性和融贯性。
在《元史学》和随后的一些论著中,怀特都不断地或明或暗地表示,正是历史语言和历史意识所普遍具有的转义特质,使得转义的主要模式成为历史著作和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正是依赖转义性的预构行为而赋予其研究领域和概念化层次以一致性和融贯性。

怀特在他的《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一文中,谈到过促使他发展出这套转义理论的契机,颇有助于我们来把握这一理论的作意。一次文学史会议上,怀特听到文学理论家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评论说,他不大能够确定文学史家们想要做的是什么,但他可以确信,写作一部历史就意味着要将某一事件置入一个语境之中,将其作为部分而与某个可以设想得到的整体关联起来。而在他看来,将部分与整体关联起来的方式只有两种,那就是转喻和提喻。
 在对于维柯诗性智慧的逻辑和当代转义理论已潜心研究多时的怀特听来,这无异于验证了他的设想:转义性话语的类型决定了历史研究素材的基本形式。
在对于维柯诗性智慧的逻辑和当代转义理论已潜心研究多时的怀特听来,这无异于验证了他的设想:转义性话语的类型决定了历史研究素材的基本形式。
历史学家运用语言要做到的,在很大程度上和文学家一样,是要将原本无法理解的变为可理解的,将原本陌生的变为熟悉的。转义就是达到这一目的必不可少而又无可回避的手段。“隐喻本质上是表现的(representational),转喻是还原的(reduc-tionist),提喻是合成的(intergrative),而反讽则是否定的(nega-tional)。”
 我们可以这样大致地来理解隐喻的四种类型在历史意识和历史写作中的实际体现
我们可以这样大致地来理解隐喻的四种类型在历史意识和历史写作中的实际体现
 :(1)隐喻——它所建立的是两个对象之间的类比关系。我们在历史著作中常常看到,以植物的生长、繁茂和衰败来类比一个民族或文化的兴衰起落,或者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意象来表述个体或民族经历危机而重新焕发活力的历程。(2)转喻——其特征是把部分视作代表了整体,如将对殖民主义的个别抵抗行为视作给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赋予了意义,视作某种普遍现象的代表;又如以伏尔泰一生言行作为启蒙运动的人格化身。(3)提喻——与转喻相反,其运作方向不是从部分到整体,而是从整体到部分。由“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或“一切历史都是贵族的灵床”(帕雷托)这样对全部历史的意义做出判断的命题出发,一切个别事件或事件组合都由此得到理解并获得其意义。(4)反讽——对于某种关于历史的判断采取怀疑主义或犬儒主义的否定态度,以展示出与之相反的意涵。
:(1)隐喻——它所建立的是两个对象之间的类比关系。我们在历史著作中常常看到,以植物的生长、繁茂和衰败来类比一个民族或文化的兴衰起落,或者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意象来表述个体或民族经历危机而重新焕发活力的历程。(2)转喻——其特征是把部分视作代表了整体,如将对殖民主义的个别抵抗行为视作给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赋予了意义,视作某种普遍现象的代表;又如以伏尔泰一生言行作为启蒙运动的人格化身。(3)提喻——与转喻相反,其运作方向不是从部分到整体,而是从整体到部分。由“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或“一切历史都是贵族的灵床”(帕雷托)这样对全部历史的意义做出判断的命题出发,一切个别事件或事件组合都由此得到理解并获得其意义。(4)反讽——对于某种关于历史的判断采取怀疑主义或犬儒主义的否定态度,以展示出与之相反的意涵。
从这样的理论立场出发,转义性的诗性预构行为先于任何概念化的层面,而决定了历史学家看待和建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基本方式。
 创造、建构、想象这样一些往往受到历史学家排斥(或者即便是接受,也往往将其限制在比较狭隘和低下的范围内)的因素,以及历史著作中认知层面以外的审美和伦理的概念化层面,就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在新的视野下进入了历史哲学的核心地带。
创造、建构、想象这样一些往往受到历史学家排斥(或者即便是接受,也往往将其限制在比较狭隘和低下的范围内)的因素,以及历史著作中认知层面以外的审美和伦理的概念化层面,就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在新的视野下进入了历史哲学的核心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