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学向以“记住”为职志,然而有时候它丢失了更多。
近代以来,延绵数千年的中华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几近“解体”。
 移植过来的“西方/现代”学科体制,替换了国人对传统的结构性认知,奠定了当代中国学术的基本模式——人们转而在新的学科框架下
移植过来的“西方/现代”学科体制,替换了国人对传统的结构性认知,奠定了当代中国学术的基本模式——人们转而在新的学科框架下
 展开对传统的“科学”研究,进行艰难的文化“重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他而自觉为我”
展开对传统的“科学”研究,进行艰难的文化“重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他而自觉为我”
 ,反复讨论“中华文化有什么特点”,并在这个总问题下形成诸如“中国哲学思想特点”“中国文学特点”“中国传统史学特点”“中国艺术精神”之类子门类的“特质论”论说。
,反复讨论“中华文化有什么特点”,并在这个总问题下形成诸如“中国哲学思想特点”“中国文学特点”“中国传统史学特点”“中国艺术精神”之类子门类的“特质论”论说。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史学”领域
 ,有关“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特点”的讨论作为一个子命题照理应该和“中国文化特质说”全面契合,但实际上,在一个很大范围内——我们概略地将之称为“美”“诗性”“艺术性”的领域——它却几乎没有参与“特性论”的消费:在“中国文化特质说”话语圈定的那些特质中,有一部分史学没有去分享。这个现象独见于史学,在哲学艺文论中是不存在的(为集中论述,这里主要以“文史哲艺”四科为“传统文化”的代表)。
,有关“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特点”的讨论作为一个子命题照理应该和“中国文化特质说”全面契合,但实际上,在一个很大范围内——我们概略地将之称为“美”“诗性”“艺术性”的领域——它却几乎没有参与“特性论”的消费:在“中国文化特质说”话语圈定的那些特质中,有一部分史学没有去分享。这个现象独见于史学,在哲学艺文论中是不存在的(为集中论述,这里主要以“文史哲艺”四科为“传统文化”的代表)。
“中国哲学艺文特质”论述的相互渗透 那些从总体上去概括“中国哲学特点”和“中国文学特点”的论说,常常相互呼应:哲学界讨论所谓的“传统哲学特点”时,总能拉上艺文论,炫耀自己的影响力;而文艺圈讨论“传统诗学、美学特点”,也习惯请出哲学这个靠山,显示底气。
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首的“中国文学”词条(周扬、刘再复撰写)就采用了这个叙述策略。该词条分别考察了儒家思想、老庄思想对传统文学的影响,从“善”与“美”两个层面去概括中国文学的特点。文称,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
以诗文为教化的文学功用说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文学观念。中国的文学在内容上偏于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经国之大业”“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说法,一方面固然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一方面也不恰当地将文学视为政治的附庸,说教的倾向一直被当作一种无可非议的倾向。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宦海的升沉、战争的成败、国家的兴亡、人生的聚散、纲常的序乱、伦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

此外,与儒家并列,老庄思想则给予中国文学艺术另外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章》)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文艺含蓄精炼的艺术表现形态上的特点;二是“大制不割”(《老子·二十八章》)、“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观点,使得古人强调自然的纯朴、素朴、浑朴,使得中国艺术家向来把刻苦的技巧训练与不露刀斧之痕的无技巧境界结合起来。
“中国文学”这一词条,为“中国文学的特质”这个大话题建构了一个清晰的解释框架:(1)在“善”的层次上,强调儒家的影响;(2)在“美”的层次上,强调道家的影响。在艺文研究中,这是一个惯常的套路。曾有人总结,一部西方的艺术思想史,不过是记载着“善的帝国主义”和“美的帝国主义”的相斫书
 ,“善”和“美”,是艺文最常规的两大主题。而在中国传统语境下,它们分别被配给了儒家和道家,形成一个“儒—善/道—美两维影响论”的框架:一维以儒家哲学为基础,强调文学艺术的济世化人功能,承载强烈的入世精神,突出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如“诗言志”“文以载道”“兴观群怨”等观念可归入此类;另一维以道家哲学为基础,强调文学家审美体验的深化,带有一抹出世情怀,取内心观照的进路,推崇直觉思维,如“气韵”“空灵”“意境”等观念可归入此类。
,“善”和“美”,是艺文最常规的两大主题。而在中国传统语境下,它们分别被配给了儒家和道家,形成一个“儒—善/道—美两维影响论”的框架:一维以儒家哲学为基础,强调文学艺术的济世化人功能,承载强烈的入世精神,突出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如“诗言志”“文以载道”“兴观群怨”等观念可归入此类;另一维以道家哲学为基础,强调文学家审美体验的深化,带有一抹出世情怀,取内心观照的进路,推崇直觉思维,如“气韵”“空灵”“意境”等观念可归入此类。
很多出色的著作都采用了这个叙述结构。例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在回答“中国诗学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时,就循轨上述两维给出答案:儒家的“人道(仁道)”精神和道家的宇宙意识(佛学理论则强化了道家哲学的影响)。儒家的影响“在于对诗济世化人等方面的价值和功用的实现”;道家的影响“在于对诗人审美体验的深化和诗的审美境界的开拓昭示了无限光辉的前景”。
 前者作用于外,后者作用于内,内外协调,豁然贯通;也有学者从批评的角度出发,态度虽然相反,却依然从这两维入手,例如郭绍虞这句概括:“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主要问题,不是乌烟瘴气闹什么‘文以载道’的说法,便是玄之又玄玩一些论神论气的把戏,前者是儒家思想之发挥,后者是道家思想之影响。”
前者作用于外,后者作用于内,内外协调,豁然贯通;也有学者从批评的角度出发,态度虽然相反,却依然从这两维入手,例如郭绍虞这句概括:“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主要问题,不是乌烟瘴气闹什么‘文以载道’的说法,便是玄之又玄玩一些论神论气的把戏,前者是儒家思想之发挥,后者是道家思想之影响。”

虽然把哲学思想、政治伦理和文学艺术一一对应,有简单化之嫌。但这个解释框架的普遍存在,确使我们可以承认,在哲学史和文论史研究中所得出的中国文化“特质”,一般都能同条共贯。
那么,史学呢?
我们权且按照上述“儒道(善/美)两维影响论”的视角,可以确认的是,中国史学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在“善”层面上呈现的特点,已经被大家充分注意到了。如在不少西方人那里,中国史学被泛称为“儒家史学”:
(一般的西方史家)认为中国史学受到儒教的深切影响,把重点放在褒贬上,沦为道德工具,而历代中央政权雇佣史官,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又沦为政治工具。

如果我们把上引“中国文学”词条中描绘儒家对文学影响的那段话中的“文学”两字,全部替换为“史学”。我们会发现,除了个别文字略有滞碍外,这段话基本符合一般中国史学史著作对传统史学的概括。这可以证明,在“善”的层次上,我们总结的“中国文化特质”“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儒家思想的特点”“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等和“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特点”,是相当一致的。
然而,移视“美”的层面,我们会发现,其他文化门类依然一团和气地互吹互擂、相互验证,中国传统史学,却似乎被疏远了,独处在角落中。史学史的研究者,当看到“诗言志”“文以载道”这类传统哲学艺文、政治伦理的共享观念的时候,会有亲切感,因为这些念头,变身到历史领域大略也就是“史以解经”“以史翼经”“义理史学”“经世史学”之类理念。可是当我们看到如“气韵”“空灵”“意境”“性灵”之类,怕是不会有什么熟悉感(除非讨论到历史文学的修辞层面)。
大家普遍认可“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完整凝一”
 的整体,而文史哲等分科只是近代现象;常言中国传统文化以“美善合一”为特点,向己求善,自诚而自得,自主而自由,仁之境界便是乐之境界,善之境界便是美之境界。反观史学中,在“善”的层面上,传统史学重视历史的伦理教化功能;在“经世”路向上,传统史学强调历史为政道资鉴,这些都已是史界常谈。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可否追问,在“美”的层面上,传统史学是否也具备一些特点,使其和传统哲学艺文论相契合呢?诗性思维、艺术性思维作为中国文化的整体特点,难道没有表现到史学中来吗?我们或许可以提问:
的整体,而文史哲等分科只是近代现象;常言中国传统文化以“美善合一”为特点,向己求善,自诚而自得,自主而自由,仁之境界便是乐之境界,善之境界便是美之境界。反观史学中,在“善”的层面上,传统史学重视历史的伦理教化功能;在“经世”路向上,传统史学强调历史为政道资鉴,这些都已是史界常谈。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可否追问,在“美”的层面上,传统史学是否也具备一些特点,使其和传统哲学艺文论相契合呢?诗性思维、艺术性思维作为中国文化的整体特点,难道没有表现到史学中来吗?我们或许可以提问:
中国传统史学在“美”的层面上的特点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忘了它?)
“中国文化特质”论述中史学的有限参与 以上对“特质”论的观察,乃就中国文化各门类内部的相互比较而言。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特质”讨论,还有一个整体的比较对象:“西方”。当我们把视眼抬高,从中西比较的外部观察,仍可以得出同于上节问题。
我们且于汗牛充栋的中西文化对比论述中信摭数例以概其余。金耀基曾经讲:
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之异于西方文化者,在中国文化之基本性格是艺术的、道德的,而西方文化之基本性格是哲学的、科学的。

这个高度概括的判断是近代以来众多文化比较研究者的共识,相似的说法很多,如钱穆多次说西方文化是科学性的,中国文化是艺术性的,并素来倡议“由中国艺术窥中国文化”
 ;如唐君毅曾区分“宗教—道德”“科学—艺术”四种(两对)精神,认为:西洋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发达,中国是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发达,他所谓道德艺术精神和宗教科学精神之不同,是“主客观之和谐融摄”和“主客观之紧张对待”之不同。
;如唐君毅曾区分“宗教—道德”“科学—艺术”四种(两对)精神,认为:西洋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发达,中国是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发达,他所谓道德艺术精神和宗教科学精神之不同,是“主客观之和谐融摄”和“主客观之紧张对待”之不同。

显然,金耀基、唐君毅这里讲“中国文化之基本性格是艺术的、道德的”,论据和上文的各种引述是一致的:中国哲学思想是艺术的、道德的,中国文学思想是艺术的、道德的,等等。不过,如果我们看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子类“中国传统史学”,会发现说“中国史学基本性格是道德的”不会有太大异议,但是,人们似乎通常不会说“中国史学思想基本性格是艺术的”。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企图概括中西文化区别的好事者众多,美国学者艾恺在用中文写成的著作《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中
 ,做了巧妙地汇总。艾恺敏锐地指出,所有非西方地区以西方为“他者”而进行的文化比较,都有相似的模式,这些比较以经常出现的系列二分概念为基本结构:像上引金耀基、唐君毅所构建的“宗教—道德”“科学—艺术”二分,类似的二分还有很多,艾恺在书中一口气举出了九十六对。他认为,那些从事文化比较的非西方思想家,通常不过是择取这一总表中某部分的二分项而已。
,做了巧妙地汇总。艾恺敏锐地指出,所有非西方地区以西方为“他者”而进行的文化比较,都有相似的模式,这些比较以经常出现的系列二分概念为基本结构:像上引金耀基、唐君毅所构建的“宗教—道德”“科学—艺术”二分,类似的二分还有很多,艾恺在书中一口气举出了九十六对。他认为,那些从事文化比较的非西方思想家,通常不过是择取这一总表中某部分的二分项而已。
艾恺这个操作颇有智巧,他列的清单可谓幅广思深,讨论这些“民族文化特质”话语的得失,并非本文目的。但只要对此一瞥而过,就能发现,可以从这些二分观念中圈出某些项组成“善”的一箩筐集合,圈出另一些组成“美”的一箩筐集合,这两箩筐反抗武器是“落后”地域“抵御”西方文化时的常用备选,形成“西方虽然比我更强、更科学,但我比西方更善、更美”之类的习见套话。
在“中国哲学艺文特点研究”中,我们会发现艾恺这个表中的各项二分普遍被采用。但是,在“中国史学特点研究”中,情况却有所不同。“善”一类的对立构造,人们在做“中西史学思想(以及中西历史)比较”时,通常也是采用的。如(序号延用艾恺原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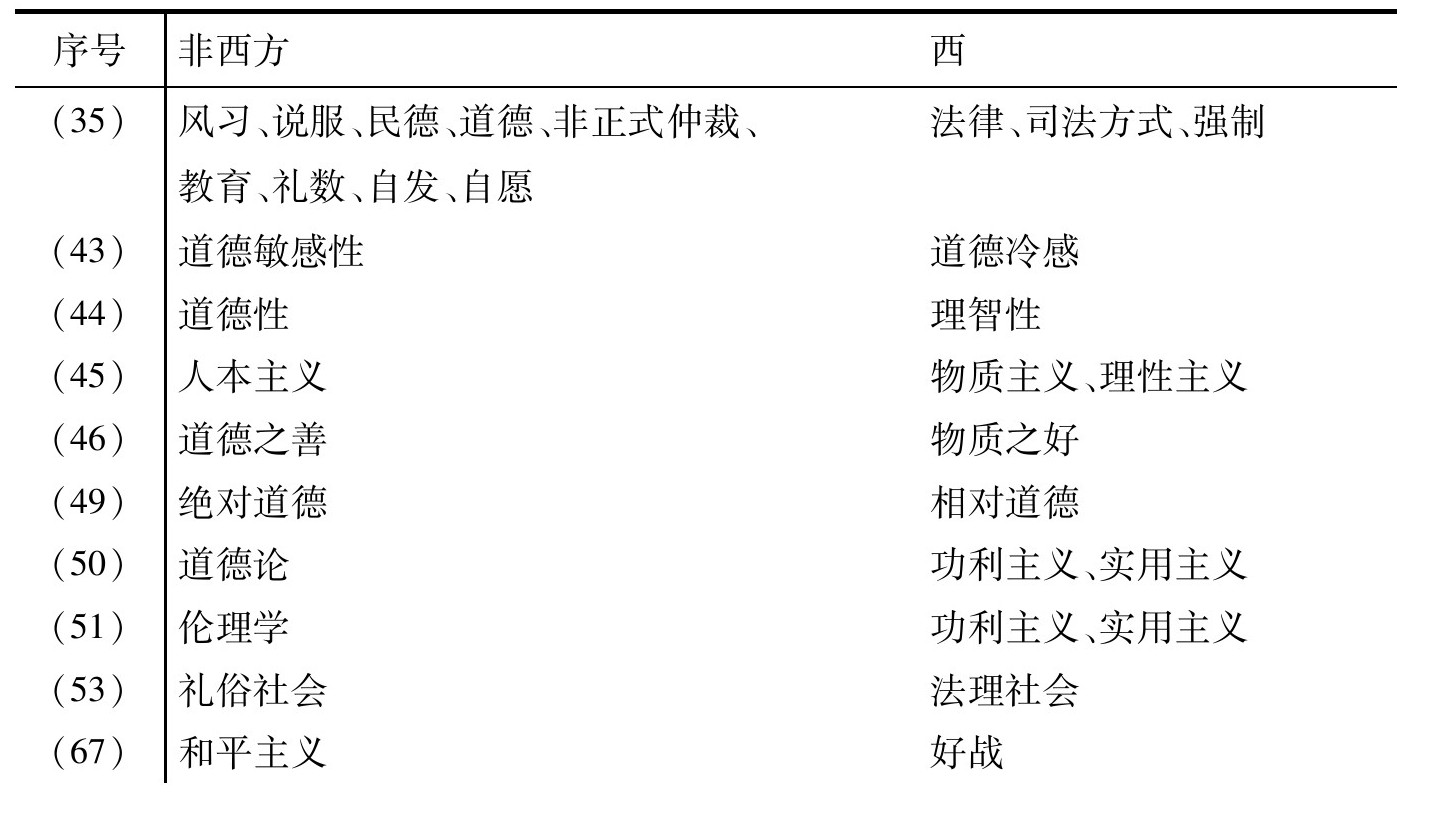
选取上表中的某些二分,形成中西比较论述如:“西方史学思想是理智主义的、中国的史学思想富有伦理道德性”“西方史表现为力量、中国史表现为情感”“西方史于斗争中著精神,中国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这类说法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艾恺所列举的关于“美”一类的对立构造,在“中国史学特质”研究中却较少见到,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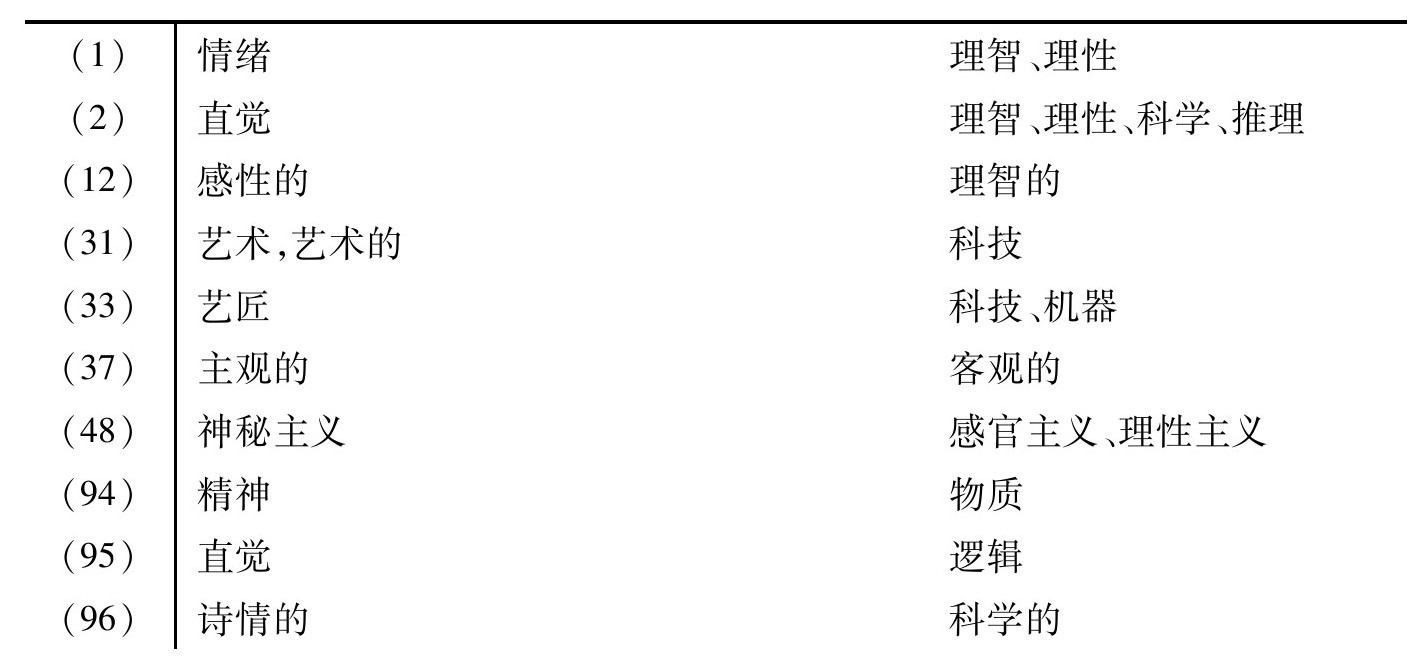
我们当然不是说,该表右边的概念,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从不出现,这个表只是一个大体的概括,其选词首先追求的是涵盖性而不是严谨性。但是一般而论,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以往的“中国史学特质”论,在“美”的层面上,基本上没有参与那些概括“中国文化特质”的标志性词语的消费。
最后,我们再留意一个现象:很多把“中国文化特质”判定为“美”、为“艺术性”的整体性论断,常常是在史学缺位的情况下得出。例如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和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
 等以“中国”为书名、以传统文化整体“美”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其论却罕及史学;彭锋的《诗可以兴》,副标题为“古代宗教、伦理、哲学与艺术的美学阐释”,并不包括史学
等以“中国”为书名、以传统文化整体“美”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其论却罕及史学;彭锋的《诗可以兴》,副标题为“古代宗教、伦理、哲学与艺术的美学阐释”,并不包括史学
 ;杨义的《感悟通论》把感悟思维看成“中国智慧的优势所在”,论域遍及哲学、宗教、文学、书画琴棋诸艺,唯独没有谈到史学。
;杨义的《感悟通论》把感悟思维看成“中国智慧的优势所在”,论域遍及哲学、宗教、文学、书画琴棋诸艺,唯独没有谈到史学。
 事实上,通过一些“哲史艺文”的共享概念,去概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普遍的特征,完全是可行的
事实上,通过一些“哲史艺文”的共享概念,去概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普遍的特征,完全是可行的
 ,只是一到“美”的层面,我们看到史学出场并不多。
,只是一到“美”的层面,我们看到史学出场并不多。
至此我们发现,“史学之美”
 是一个失落的话题,乃是近人对传统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时造成的“消耗性转换”。
是一个失落的话题,乃是近人对传统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时造成的“消耗性转换”。
 不过我们到此为止只是间接证明,只是通过“中国史学特质”和“中国文化特质”这个总论断比较和“中国哲学艺文论特质”这些分论断比较,间接得出“中国传统史学带有‘美、艺术性、诗性’的特质”这个设想。我们认为,对一个著名史学思想家的再研究,能直接证实上述设想,他就是章学诚(1738—1801年)
不过我们到此为止只是间接证明,只是通过“中国史学特质”和“中国文化特质”这个总论断比较和“中国哲学艺文论特质”这些分论断比较,间接得出“中国传统史学带有‘美、艺术性、诗性’的特质”这个设想。我们认为,对一个著名史学思想家的再研究,能直接证实上述设想,他就是章学诚(1738—1801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