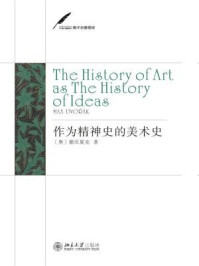笔者在《张九龄“丁父忧”准确时间考辨》
 (见本书)中已经考得张九龄之父张弘愈或逝于长安二年(702)正月或二月。但是,张弘愈及其妻卢氏的出生年月、年寿与张弘愈的仕历尚未明确。本节拟对此问题进行考证。然而,破解张九龄之父张弘愈出生年月之谜,证据极少。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唐徐浩《张九龄神道碑》所载:“列考讳弘愈,新州索卢县丞,赠太常卿,广州都督”
(见本书)中已经考得张九龄之父张弘愈或逝于长安二年(702)正月或二月。但是,张弘愈及其妻卢氏的出生年月、年寿与张弘愈的仕历尚未明确。本节拟对此问题进行考证。然而,破解张九龄之父张弘愈出生年月之谜,证据极少。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唐徐浩《张九龄神道碑》所载:“列考讳弘愈,新州索卢县丞,赠太常卿,广州都督”
 ,唐萧昕《张九皋神道碑》
,唐萧昕《张九皋神道碑》
 记叙略同。《旧唐书》卷一百三“张九龄传”载:“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别驾,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父弘愈,以九龄贵,赠广州刺史。”
记叙略同。《旧唐书》卷一百三“张九龄传”载:“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别驾,因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父弘愈,以九龄贵,赠广州刺史。”
 《新唐书》对此无载。后来的研究者如李世亮、李锦全、顾建国、熊飞等,对于张九龄之父张弘愈的生平事迹也是依据以上说法,对于张弘愈的出生年龄、年寿及任索卢丞的始任时间未能给出具体答案。
《新唐书》对此无载。后来的研究者如李世亮、李锦全、顾建国、熊飞等,对于张九龄之父张弘愈的生平事迹也是依据以上说法,对于张弘愈的出生年龄、年寿及任索卢丞的始任时间未能给出具体答案。
其实,根据以上材料,加上张九龄丁卢氏太夫人忧的记载和嘉靖《始兴县志》《新兴县志》
 等记载,再结合唐代尤其是唐初法令规定,还是可以对张弘愈的大致年龄和经历做出推断。
等记载,再结合唐代尤其是唐初法令规定,还是可以对张弘愈的大致年龄和经历做出推断。
查《旧唐书》卷一百三“张九龄传”:“寻丁母丧归乡里。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迁中书令,兼修国史。”
 徐浩《张九龄神道碑》:“(九龄)迁中书侍郎。丁内忧,中使慰问,赐绢三百匹。奔丧南讣……”
徐浩《张九龄神道碑》:“(九龄)迁中书侍郎。丁内忧,中使慰问,赐绢三百匹。奔丧南讣……”
 ,对张九龄母卢太夫人之去世,萧昕《张九皋神道碑》
,对张九龄母卢太夫人之去世,萧昕《张九皋神道碑》
 亦有同样记载。根据张九龄《让起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表及唐玄宗御批
亦有同样记载。根据张九龄《让起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表及唐玄宗御批
 、《旧唐书·玄宗纪》
、《旧唐书·玄宗纪》
 等材料所记和后人的研究,可以确定,卢太夫人在开元二十一年(733)秋末去世,是年张九龄56岁。
等材料所记和后人的研究,可以确定,卢太夫人在开元二十一年(733)秋末去世,是年张九龄56岁。
张九龄是张弘愈长子,出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按照唐代尤其是唐初官方礼制规定与婚俗,士人当二十而冠,成为成年人即可以成婚了。而女子则十五而笄,可以成婚。男子二十而婚,女子十五而嫁,是唐初的法律规定,也是家族繁衍的强烈的内在需求。因为男女成婚是增加人口的前提,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要求成年男子要为家族增加人口,为家族人丁兴旺、增强家族势力、延续家族血脉适时而婚。对于家族长辈而言,对成年子侄以及女性晚辈的婚事自然高度重视,而成年男子也自然将婚姻大事和后代的养育视为一件关系家族实力、荣誉与自身地位的一件大事来对待。
此外,适时而婚还有经济上的动因。《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规定:“凡天下之田,五尺为步,二百有四十为亩。亩百为顷。度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丁男、中男以一顷……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又规定:“凡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已下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其口分永业不与焉。”李林甫等注曰:“若京城及州、县郭下园宅,不在此例。”
 也就是说,人口多者,可以多分得土地,口分田和永业田都会增加,而京城、州、县郭下的土地则不授予或不按此标准授予。在农耕社会,土地对于人民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各家族均十分重视。新增丁口还可以分得园宅用地,就是今天所说的宅基地,这个政策是很有吸引力的,也可以理解为朝廷为了增加人口而采取的带有鼓励性的土地政策。
也就是说,人口多者,可以多分得土地,口分田和永业田都会增加,而京城、州、县郭下的土地则不授予或不按此标准授予。在农耕社会,土地对于人民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各家族均十分重视。新增丁口还可以分得园宅用地,就是今天所说的宅基地,这个政策是很有吸引力的,也可以理解为朝廷为了增加人口而采取的带有鼓励性的土地政策。
同时,历代开国君王在天下平定之初以及其后一段时间里,都高度重视人口的增长。初唐时期,因为天下大乱初定,人口急剧减少,必须加速繁殖人口,以扩大税赋、兵员的来源。因此,男子二十而婚,女子十五而嫁,就不仅仅是一种家庭或者家族的要求,而成为一种刚性的政策法律要求了。早在唐太宗贞观元年(627)正月,即发布《令有司劝庶人婚聘及时诏》。诏书先讲一番儒家婚嫁的道理:“昔周公治定制礼,垂裕后昆。命媒氏之职,以会男女,每以仲春之月,顺行时令,蕃育之理既弘,邦家之化斯在。及政教陵迟,诸侯力争,官失其守,人变其风,致使谣俗有失时之讥,鳏寡无自存之术汉魏作教,事非师古,道随世隐,义逐时乖,重以隋德沦胥,数钟屯剥,五教俱覆,万方咸荡。暨参墟奋旅,救彼艰危,区县削平,总斯图籍。顾瞻禹迹,提封尚存,乃眷周余,扫地咸尽。痛心疾首,寤寐无忘。唯上玄之大德曰生,蒸民以最灵为贵。一经丧乱,多饵豺狼。朕夙奉天命,为人父母,平定甫尔,劬劳求康。厚生乐业,尚多疏简,永言亭育,实切于怀。若不申之以婚姻,明之以顾复,便恐中馈之礼斯废,绝嗣之憾方深。有怀怨旷之情,或至淫奔之辱。宪章典故,实所庶几,宜命有司,所在劝勉”;再规定“庶人男女之无家室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取,皆任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命其好合。”对于家庭贫困者,还要求“仰于其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裒多益寡,使得资送”。还下令将管内是否及时婚配、增加户口作为对于地方官员考核的指标。“刺史、县官已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就是连鳏夫、寡妇也要及时再婚、再嫁。反之,官员“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口减少,以附殿失”
 ,也就是说,如果地方刺史、县令执行不力,方法不妥,致使该娶未娶,该嫁未嫁,则等同于“户口减少”,在考课中就是过失,自然不能得到较高等次,还要承担责任,予以处罚。
,也就是说,如果地方刺史、县令执行不力,方法不妥,致使该娶未娶,该嫁未嫁,则等同于“户口减少”,在考课中就是过失,自然不能得到较高等次,还要承担责任,予以处罚。
可见在唐初统治者心中,繁育人口是国家治理极其重要的方面,是正风俗、稳定社会的重要因素。实际上,人口的增加还是朝廷治理国家重要的资源。由此,可以看出这道诏书是为了增加人口采取的带有强制性的严厉政策措施。实际上,有唐一代,人口增加与否,历来是朝廷考核地方官员如刺史、县令的重要指标。《唐大诏令集补编》中多有相关诏令的记载。如《刺史县令政绩委所在节度观察闻奏分别奖贬诏》就把“增多户口”列为重要指标,《太守县令廉能者赐中上考制》《长吏县令增加户口广辟田畴者优于处分制》等,均有明确规定。不仅如此,为防止刺史、县令属官懈怠,还下达敕令《喻诸道州考察所属官敕》提出要求。
 在这样严格的政令要求之下,各地方官吏必然会千方百计予以贯彻落实,而各地官宦世族之家必然成为政策落实的重点。
在这样严格的政令要求之下,各地方官吏必然会千方百计予以贯彻落实,而各地官宦世族之家必然成为政策落实的重点。
对于婚龄的规定和对于官员“劝庶人婚聘及时”的成效列入对于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予以考核,可谓奖惩双管齐下。那么唐代尤其是唐初对于朝廷这一诏令的要求,在各地执行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尚未发现直接史料证明。但根据李斌成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整个唐代男子女子十五岁成婚者最多。
 他引用《唐会要》的数据说:“唐初,承隋末大乱之后,经济萧条,社会残破,人口大量死亡,‘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又指出:“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人口在农业生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恢复被战乱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唐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鼓励百姓及时婚嫁,以增殖人口,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提供尽可能多的劳动力。”“唐人的实际婚龄,文献和考古资料关于男子婚龄记载较少,大抵年二十成人而婚者居多。”“唐代女子的实际婚龄,比法律规定的要复杂得多。”
他引用《唐会要》的数据说:“唐初,承隋末大乱之后,经济萧条,社会残破,人口大量死亡,‘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又指出:“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人口在农业生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恢复被战乱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唐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鼓励百姓及时婚嫁,以增殖人口,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提供尽可能多的劳动力。”“唐人的实际婚龄,文献和考古资料关于男子婚龄记载较少,大抵年二十成人而婚者居多。”“唐代女子的实际婚龄,比法律规定的要复杂得多。”
 他根据《唐代墓志汇编》所载3200余人(不包括女尼、女冠和宫人)中,女子出嫁情况的统计,制成表格,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见表1和表2)
他根据《唐代墓志汇编》所载3200余人(不包括女尼、女冠和宫人)中,女子出嫁情况的统计,制成表格,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见表1和表2)
表1

表2

注:中国古代女子至15岁,将发用簪束起,表示成年,可以出嫁。登笄、既笄、逮笄和始笄与笄年年龄基本相仿。《谢小娥传》云:“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笄”。弱笄、幼笄、将笄、近笄和副笄大体也属此年龄。实际上,以上两类笄年很难区分。
根据上表统计分析,李斌成等得出结论:
“以上二表显示,唐代部分女子出嫁的年龄是:
1.年龄最小的11岁,最大的27岁,相差16岁。
2.13岁以下的,20岁以上的,均为少数。
3.14岁至19岁出嫁者居多。
4.在14岁至19岁者中,又以14、15岁者居多。
5.在14、15岁者中,15岁者居首位。”

李斌成等的研究还说:“唐朝在政局稳定,天下太平时,人们婚姻以时。而在国家多事之秋,百姓不用说了,就是皇亲国戚的婚嫁,也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至于为何14岁出嫁者也占较大比例,这极有可能与唐玄宗二十二年(734)的敕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
至于为何14岁出嫁者也占较大比例,这极有可能与唐玄宗二十二年(734)的敕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
 相关,更何况地方官员和士族家庭为了完成增加户口的刚性指标,也还可能采取早婚的办法。
相关,更何况地方官员和士族家庭为了完成增加户口的刚性指标,也还可能采取早婚的办法。
由以上统计数据,可知,在唐朝时期,凡是在政局稳定天下太平之时,人们的婚嫁是及时的,也就是说,人们的婚嫁年龄与朝廷的法令要求基本吻合。这是因为朝廷法令与百姓需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换言之,朝廷的法律与士民自身的利益要求高度一致,所以朝廷法律得到了较为严格、有效的执行。只有在天下大乱之时,人们的婚嫁才受到影响,具体体现就是不能及时而婚、及时而嫁。在唐朝建立之安史之乱爆发前,尽管唐朝朝廷中发生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从全国范围而言,政治局势是稳定的。这就为人们及时而婚、及时而嫁提供了政治和社会保障。
张弘愈家族是韶州的官宦之家,衣冠之族,若张弘愈无极其特殊的原因,无论从朝廷政令的贯彻、落实还是家族自身的要求哪个方面来说,都必然会适时而婚。从张九龄出生十三年之后,张弘愈连生三子来看,张弘愈和卢氏绝对不会有个人身体方面的原因不能及时成婚、生子的。而且当地的刺史、县令也因为考核的压力,必然会督促、要求适时而婚。因此基本可以认定,张弘愈应该是在成人礼之后适时而婚的。
这是张弘愈一方的情况。李斌成等的研究表明了唐朝在天下太平时女子出嫁年龄大都集中在十五岁左右。相信卢太夫人与张弘愈成亲时也应该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即是相差,也不会太远。
如此,如考虑张弘愈夫妇均为成年后即由家人操持婚礼,一年后生九龄,即16岁时生张九龄,从仪凤三年(678)上推16年即张母卢太夫人的出生时间。这个推测与徐安贞撰《张九龄阴堂志铭》、徐浩所撰《张九龄墓碑》中所记张九龄逝于开元二十八年(740)五月七日,即逝年63岁相合,可以成立。由此可知,张九龄母卢氏夫人应生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下半年或麟德元年(664)上半年。九龄母卢太夫人去世之年即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由此可知,卢太夫人逝年已达71岁或72岁。
如果考虑唐朝初期朝廷男女婚嫁年龄的规定能够得到有力执行,又考虑民间生育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其实不待政府法令的督促,而张弘愈又无极其特殊情况的话,在张九龄出生之年的仪凤三年(678)上推21年,或者在卢太夫人的出生时间往前推5年,则应该为张弘愈的出生时间。由此可知,张弘愈应该出生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或显庆四年(659)。由此,也可推知,如笔者所考证,张弘愈在长安二年(702)去世,则其去世时应为42至43岁左右。
下面考察张弘愈任职索卢县丞的始任时间。张弘愈始任索卢县丞,应在张九龄出生后数年内。按:张九龄出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如此,张弘愈任索卢县丞应该在此后数年内,他始任索卢丞时,年龄应在21岁之后,即张九龄出生之后数年之内,亦即唐高宗仪凤四年或调露元年(679)至永淳二年或弘道元年(683)间。
可以肯定,张弘愈任索卢县丞,并非由于科举出身。既非科举出身,又确实担任过索卢县丞,则必然是经过“南选”而入仕。所谓“南选”,即朝廷从岭南、黔中、闽中诸地实际出发,在官员选授的科举制度之外设立的一种地方官员选授制度。《唐六典》卷第二“尚书吏部”“其岭南、黔中三年一置选补使,号为‘南选’。”李林甫等注曰:“应选之人,各令所管勘责,具言出身、由历、选数、作簿书预申省,所司具勘曹名、考第、造历子,印署,与选使勘会,将就彼诠注讫,然后进申以闻。”
 《旧唐书·职官志》所载与此完全相同。在此之前,为了适应对于岭南、闽中等新定地区统治的需要,大约在高祖武德后期或太宗贞观时即实际上存在由州都督拣选县令、刺史等官吏的做法,但是也存在着“任官简择,未甚得所”的问题。所以唐高宗才于上元三年(676)八月七日下达敕令谓:“桂、广、交、黔等州都督府,比来所奏拟土人首领,任官简择,未甚得所。自今已后,宜准旧制,四年一度,差强明清正五品以上官,充使选补,乃令御史同往注拟。其有应任五品以上官者,委使人共所管督府,相知具条景行艺能,政术堪称所职之状,奏闻。”
《旧唐书·职官志》所载与此完全相同。在此之前,为了适应对于岭南、闽中等新定地区统治的需要,大约在高祖武德后期或太宗贞观时即实际上存在由州都督拣选县令、刺史等官吏的做法,但是也存在着“任官简择,未甚得所”的问题。所以唐高宗才于上元三年(676)八月七日下达敕令谓:“桂、广、交、黔等州都督府,比来所奏拟土人首领,任官简择,未甚得所。自今已后,宜准旧制,四年一度,差强明清正五品以上官,充使选补,乃令御史同往注拟。其有应任五品以上官者,委使人共所管督府,相知具条景行艺能,政术堪称所职之状,奏闻。”
 “南选”由此形成制度,并长期执行。一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才改为科举选授和南选并行。即在京师应选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七月二十七日敕:“如闻岭南州县,近来颇习文儒,自今已后,其岭南五府管内白身,有词藻可称者,每至选补时,任令应诸色乡贡,乃委选补使准其考试。有堪及第者具状闻奏,如有情愿赴京者亦听。其前资官并常选人等有词理兼通才堪理务者,亦任北选及授北官。”
“南选”由此形成制度,并长期执行。一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才改为科举选授和南选并行。即在京师应选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七月二十七日敕:“如闻岭南州县,近来颇习文儒,自今已后,其岭南五府管内白身,有词藻可称者,每至选补时,任令应诸色乡贡,乃委选补使准其考试。有堪及第者具状闻奏,如有情愿赴京者亦听。其前资官并常选人等有词理兼通才堪理务者,亦任北选及授北官。”

这里有个问题,按照《唐六典》《旧唐书》所载,“南选”是三年一置,而高宗敕书说是“四年一度”。这应该是后来发现“南选”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既采取委任补选使的办法加强监督,同时也延长了每届“南选”举行的时间。也就是说,“南选”在高宗时应是先四年一度,后改为三年一度。
考虑到在唐高宗上元三年(676)时,张弘愈尚未行成人之礼,不可能参与南选。按照四年一度的制度规定,张弘愈应该是参加680年亦即唐高宗调露二年、永隆元年的“南选”得中,成为索卢县丞的,时年23岁左右。这与高宗时“南选”四年一度举行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或许有疑者会认为,张弘愈23岁何以能成为县一级的官员?是否年龄太小一些了?这可以从当时岭南官吏缺少,治理人才难得,而张弘愈经“南选”考试又比较优秀。而且张弘愈家族来源北方世家,并非是岭南土著;又出身于数代官宦之家,必然饱读经书,在家中耳濡目染,对于出仕为官的规矩有较全面了解;对于岭南民风习俗比较了解,从这些原因中得到解释。何况在唐时也有一些虽然年轻但经科举考试而入仕的情况。最为切近的例子,是张九龄于长安元年(701)即入京参加科举考试,时年23岁,竟然一举得第。虽然未曾得官,但那是回乡“丁父忧”的个人原因。如无此原因,他必然就在长安二年(702)入仕了,其年龄正是24岁。由此可见,张弘愈23岁任索卢县丞,是完全可能的。
《新兴县志》说:张弘愈于“嗣圣元年(684)从新州辞官,返回韶州。”
 如果可信,则他任新州索卢县丞一共四年时间。由此可以大致确定,张弘愈辞官时年龄应在27岁至28岁之间。据明嘉靖刻本《始兴县志》卷之下“人物·张九龄”条记:“父宗振”。
如果可信,则他任新州索卢县丞一共四年时间。由此可以大致确定,张弘愈辞官时年龄应在27岁至28岁之间。据明嘉靖刻本《始兴县志》卷之下“人物·张九龄”条记:“父宗振”。
 据清人郝玉麟《广东通志》卷四十四《人物志》,张弘愈字宗振,还任过新州等地刺史。
据清人郝玉麟《广东通志》卷四十四《人物志》,张弘愈字宗振,还任过新州等地刺史。
 新修《新兴县志》也说:“张弘愈,生卒年不详,字宗振,韶州曲江人(今广东省韶关市),唐丞相张九龄之父,曾任新州索卢县丞、知新州军州事,赠太常寺卿广州都督。嗣圣元年(684)从新州辞官,返回韶州。”
新修《新兴县志》也说:“张弘愈,生卒年不详,字宗振,韶州曲江人(今广东省韶关市),唐丞相张九龄之父,曾任新州索卢县丞、知新州军州事,赠太常寺卿广州都督。嗣圣元年(684)从新州辞官,返回韶州。”
 但是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张弘愈字“宗振”,细研“宗振”二字,作为张宏愈的“字”,与其名“弘愈”还是有着比较紧密的内在联系的。古人字号,往往与其名的内涵相联系、相承接或者相辅助,“弘愈”作为名,蕴含着张大、复兴家族的含义,与“宗振”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也符合古人命名赋字的传统习俗。因此,这个“宗振”作为张弘愈的字,是没有太大疑问的。从《广东通志》《新兴县志》记载看,张弘愈还可能任过新州刺史。
但是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张弘愈字“宗振”,细研“宗振”二字,作为张宏愈的“字”,与其名“弘愈”还是有着比较紧密的内在联系的。古人字号,往往与其名的内涵相联系、相承接或者相辅助,“弘愈”作为名,蕴含着张大、复兴家族的含义,与“宗振”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也符合古人命名赋字的传统习俗。因此,这个“宗振”作为张弘愈的字,是没有太大疑问的。从《广东通志》《新兴县志》记载看,张弘愈还可能任过新州刺史。
笔者则认为张弘愈不可能任过新州刺史。如果真正任过新州刺史,则他在任新州刺史之前,还应该任过县令、司马、别驾等职务。因为唐时授官也是严格按照等级来升迁的。按照《唐六典》规定:“下州(原注:户不满二万为下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别驾一人,从五品上;司马一人,从六品上,”“诸州下县,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
 张弘愈以一个索卢县丞的正九品下的官阶,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跃升为正四品下的高级官吏?如果是逐级升迁的,只有经过十考以上,才有可能隔品授官,《唐六典》规定:“若都畿、清望、历职三任,经十考以上者,得隔品授官。不然则否。”
张弘愈以一个索卢县丞的正九品下的官阶,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跃升为正四品下的高级官吏?如果是逐级升迁的,只有经过十考以上,才有可能隔品授官,《唐六典》规定:“若都畿、清望、历职三任,经十考以上者,得隔品授官。不然则否。”
 可见,他没有足够的任职时间。张弘愈出身于“南选”,非清流、清望之官,又任职于岭南下州、下县,也不可能隔品授官,更不可能短时间即升至刺史。按照《唐六典》规定:从正九品下的县丞到正四品下的下州刺史,其间隔着十八个官阶。在官场历练,又非处于清流正途,如果没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是不可能达到正四品下这个官阶的。
可见,他没有足够的任职时间。张弘愈出身于“南选”,非清流、清望之官,又任职于岭南下州、下县,也不可能隔品授官,更不可能短时间即升至刺史。按照《唐六典》规定:从正九品下的县丞到正四品下的下州刺史,其间隔着十八个官阶。在官场历练,又非处于清流正途,如果没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是不可能达到正四品下这个官阶的。
 《新兴县志》不是明确说他“嗣圣四年”就辞官返回韶州了吗?那他在新州所辖的索卢县任职一共也才四年时间,官阶不可能达到如此级别的。
《新兴县志》不是明确说他“嗣圣四年”就辞官返回韶州了吗?那他在新州所辖的索卢县任职一共也才四年时间,官阶不可能达到如此级别的。
再考徐浩《张九龄神道碑》、萧昕《张九皋神道碑》,均无关于张弘愈曾任新州刺史的记载。须知,碑文的写作,其生平事迹是由其家属后人提供给撰写者的。如果张弘愈任过新州刺史,其家属后裔必然是知道的,也会作为张弘愈任职的一大亮点提供给碑记撰写者的。而张九龄、张九皋兄弟二人的碑记均无张弘愈任新州刺史的记载,则说明并非偶然漏记,而是张弘愈确实未曾任过新州刺史。可能是《新州志》编撰者认为,张弘愈死赠太常卿、广州都督官衔太高,需要中间有个过渡官衔,才加上去的。按:新州旧志,最早由元代新州尹薛里吉思于至元元年(1335)所编撰;其后,明代由新州官员主持编撰的有三志;清代由新州官员主持编撰的共七志。最早的《新州志》编撰之时,距唐已远,史料遗失,诸多人物事迹多靠传说甚至推测,是过去时代地方志编撰中常见的事情。综合以上情况,新州诸志中记张弘愈曾任新州刺史的记载并无根据,可以否定。
下面讲一下对于张弘愈侨寓广州的看法。《广东通志》卷四十四《人物志》、光绪《始兴县志》、《羊城古钞》
 以及今人李世亮《张九龄年谱》都认为“弘愈尝侨南海生九龄”,《广东通志》等书不知何据。因书晚出未能引起学界关注。对此,顾建国在《张九龄年谱》中引《旧唐书》张九龄本传:“(九龄)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曰:此子必能致远”和徐浩《张九龄神道碑》类似说法,指出“我们似可推测,九龄当生于广州,且幼亦长于广州。否则,曲江、始兴皆远离广州,一个十三岁的孩童是不大可能远涉上书的。”
以及今人李世亮《张九龄年谱》都认为“弘愈尝侨南海生九龄”,《广东通志》等书不知何据。因书晚出未能引起学界关注。对此,顾建国在《张九龄年谱》中引《旧唐书》张九龄本传:“(九龄)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曰:此子必能致远”和徐浩《张九龄神道碑》类似说法,指出“我们似可推测,九龄当生于广州,且幼亦长于广州。否则,曲江、始兴皆远离广州,一个十三岁的孩童是不大可能远涉上书的。”
 今人李世亮《张九龄年谱》认为:“因为张九龄父亲时为索卢县丞、并知新州等州事。索卢县位于现广东省新兴县南,邻近广州,弘愈侨寓,当有可能。”
今人李世亮《张九龄年谱》认为:“因为张九龄父亲时为索卢县丞、并知新州等州事。索卢县位于现广东省新兴县南,邻近广州,弘愈侨寓,当有可能。”

关于张弘愈是否任过新州刺史,笔者前文已有辨证。但这里还有三个问题:一是张弘愈是否曾侨寓广州;二是张九龄是否生于广州;三是张九龄幼年是否长于广州。
笔者认为张弘愈在辞去索卢县丞后可能曾经侨寓广州一段时间,以谋求仕途的进一步发展。须知,当时新州在广府管内,
 广州都督府即驻节广州,是“南选”的举办地。张弘愈辞去索卢县丞,在回韶州居住一段后,再独自到广州侨居,在广府管辖范围之类谋取升迁,有地利之便,也是在情理之中。之所以独自,可能是因为张弘愈家境其实也不太宽裕,如果携其妻共居广州,在经济上也难于承受。张弘愈寓居广州谋求仕途发展,或者因为并不顺利,因而断了继续做官的念头,遂返回曲江,也未可知。
广州都督府即驻节广州,是“南选”的举办地。张弘愈辞去索卢县丞,在回韶州居住一段后,再独自到广州侨居,在广府管辖范围之类谋取升迁,有地利之便,也是在情理之中。之所以独自,可能是因为张弘愈家境其实也不太宽裕,如果携其妻共居广州,在经济上也难于承受。张弘愈寓居广州谋求仕途发展,或者因为并不顺利,因而断了继续做官的念头,遂返回曲江,也未可知。
这也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张九龄二弟张九皋的出生与张九龄出生间隔竟达十三年之久。即张弘愈居官索卢四年,嗣圣元年(684)任满不再任索卢县丞,又侨寓广州数年,长期在外,很少回家或者回家时间短的缘故。这也可以解释张九皋之生,或许与张弘愈已经弃官,居于韶州家中相关。此后又有三弟张九章、四弟张九宾出生,也是由于张弘愈已经返回韶州,长期与妻子共同生活。同时也证明,张弘愈此时应该是正当壮年,至少年岁不会过大。由此分析,我认为,张弘愈侨寓广州是很有可能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嗣圣元年(684)辞去索卢县丞返归韶州之后,一直到武后载初元年(689)。按照萧昕《张九皋神道碑》,张九皋逝于天宝十四年(755)四月二十日,终年66岁。如此计算,则张九皋当于武后天授元年(690)生于韶州。这一说法也被历来张九龄研究者所确认。
 在张九皋出生之前一年的689年春,或当在3月之前,张弘愈必然已回韶州。
在张九皋出生之前一年的689年春,或当在3月之前,张弘愈必然已回韶州。
至于张九龄是否出生于广州,现在亦无可靠材料可以证明。笔者认为,既然张九龄生于广州之说并无可靠材料依据,以推翻新旧《唐书》之说,还是维持新旧《唐书》的说法为好。同时,唐时考进士,需要向户部申报关于自身情况的材料。“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
 这里说“既至省”,就是到尚书省去缴纳地方的推荐公文,缴纳个人家庭父祖三代履历、身貌、家庭状况、学业状况等,还要与其他贡士联名结保。程序是很严格的。如果互保之人中出现不实问题,其他参保之人要受到处分的。因此,张九龄赴京考试和吏部铨试也必然会走这一程序,他的出生地也必然要向尚书省报告。如果报告,官方档案必有张九龄出生地的记载,其后代也应该十分清楚,不至于出现大的错误。同时,张九龄首次被封为曲江县男,后又被封为始兴县开国子、始兴县开国伯,也可以看出一些信息来。唐代封赏赐爵,大都与被封者的祖居或者里贯相关。从封爵地大致可以看出被封者的籍贯、出生地或者长期职任地。但是却无广州的封爵,由此可见,张九龄未必生于广州。还有就是现在更无证据证明张弘愈曾携带其夫人卢氏共同侨寓与广州的材料。所以说张九龄出生于广州之说,并无理据,不可遽然采信。
这里说“既至省”,就是到尚书省去缴纳地方的推荐公文,缴纳个人家庭父祖三代履历、身貌、家庭状况、学业状况等,还要与其他贡士联名结保。程序是很严格的。如果互保之人中出现不实问题,其他参保之人要受到处分的。因此,张九龄赴京考试和吏部铨试也必然会走这一程序,他的出生地也必然要向尚书省报告。如果报告,官方档案必有张九龄出生地的记载,其后代也应该十分清楚,不至于出现大的错误。同时,张九龄首次被封为曲江县男,后又被封为始兴县开国子、始兴县开国伯,也可以看出一些信息来。唐代封赏赐爵,大都与被封者的祖居或者里贯相关。从封爵地大致可以看出被封者的籍贯、出生地或者长期职任地。但是却无广州的封爵,由此可见,张九龄未必生于广州。还有就是现在更无证据证明张弘愈曾携带其夫人卢氏共同侨寓与广州的材料。所以说张九龄出生于广州之说,并无理据,不可遽然采信。
至于顾建国在《张九龄年谱》中提出的疑问,张九龄如不在广州,何能远涉广州向王方庆献书?实际上很好理解。一是“献书路左”事不一定只能发生在广州。韶州是唐代两都南下岭南广州的大道,南来北往的赴任、离任官员必经之地。张氏家族作为当地的书香门第、衣冠士族,当然有机会接触王方庆。由此观之,张九龄“献书路左”也可能发生在韶州。二是即使是张九龄献书王方庆是在广州,因为张弘愈曾较长时期寓居广州,张九龄探视其父或者被其父携带到广州居住过一段时间,也是情理之中,作为一个曾任县丞的官员,尽管已经辞职,自然也可以找到接触王方庆的理由。因此,即使张九龄在广州献书也不能证明就一定出生于广州。
根据以上考证,我们可以为张弘愈的生平行事列出一个简略时间表。
张弘愈,韶州人,名弘愈,字宗振。大约生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或显庆四年(659);
其妻卢氏生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下半年或麟德元年(664)上半年。
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左右,张弘愈与卢氏成婚,时年20岁,卢氏时年15岁;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张弘愈、卢氏生张九龄;张弘愈时年21岁,卢氏时年16岁;
唐高宗调露二年、永隆元年(680),张弘愈参加“南选”,得授索卢县丞,时年23岁;卢氏时年18岁;
唐高宗嗣圣元年(684)从新州索卢县丞任满,返回韶州;不久南下广州,此后数年,或侨寓广州,谋取仕途进展。期间,或可能携张九龄在广州居住;
唐武则天载初元年、天授元年(690),本年初,张弘愈或返回韶州。此前,张九龄或于韶州,也或于广州献书于当时的广州都督王方庆,受到称赞。
本年,张弘愈生二子张九皋。其后数年,连生三子张九章、四子张九宾兄弟。
武周长安元年(701),张九龄赴长安参与科举考试。出发之时,张弘愈尚在世。
武周长安二年(702),张弘愈或于本年正月逝世。终年42岁或43岁。张九龄进士及第,但因“丁父忧”返回韶州,未能参加“释褐试”,因此未能授得官职。张九龄此后在家守制。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卢氏太夫人去世。终年71岁或72岁。
唐开元二十三年(735),追赠张弘愈太常卿、广州都督,追赠卢氏太夫人桂阳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