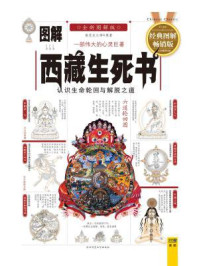对不文明和党派性的担忧,也属于美国政治的老生常谈之一。此种担忧在1996年大选的余波之中再度引起了关注;通过这次选举,克林顿总统得以连任,共和党则继续执掌参众两院。
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粗鄙不受欢迎,举国上下一致提倡文明礼貌。美国人已经厌烦了骂人广告、揭短竞选和党派结怨,同样,美国人也讨厌日常生活中的不文明举止,如在高速公路上横冲直撞,好莱坞电影和流行音乐中的暴力和野蛮,日间电视中厚颜无耻的爆料,向裁判吐唾沫的棒球明星……
克林顿总统和共和党领袖们知道民众对不礼貌的反感,于是承诺要超越党派偏见,寻求共同的基础。国会议员们策划了两党周末静修活动,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并设法用更文明的方式来表达双方的分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全国性委员会采取了措施来复兴公民身份和共同体。
美国人有理由担忧日常生活中的不礼貌,但切莫以为,举止文明、待人礼貌就能够解决美国民主的根本问题。在政治中,文明礼貌作为一种美德,往往被抬得过高。
礼貌存在的问题,正是引得政治人物赞美它的理由:礼貌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正常运行的民主政治往往充满了争议。我们推举政治家去辩论那些充满争议的公共问题,如:教育开支或国防开支是多少?用多少钱去救济穷人?如何惩治犯罪?该不该准许堕胎?我们不必顾忌辩论所造成的喧嚣和吵闹,那正是民主政治的声音和景象。 54
若是能够本着互相尊重的精神,而不是怀着敌意来进行政治辩论,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不过现如今,呼吁政治的礼貌,往往变成了好听的借口,以期对方少来追究非法竞选捐款或其他不当行为。同样,超越党派偏见的呼吁,也可能混淆合理的政策分歧,或者使无原则、无信念的政治得以合法化。
从新政到民权运动,有原则的政治一向是党派性政治,至少是意味着要动员那些政见相投的公民去为某个遭受反对的事业而战。
靠劝说或通过弱化政治分歧的办法,并不能根除今日美国生活中四处泛滥的不文明行为。那是伴随着我们的公共生活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病症,难以靠党派声音的弱化来加以疗治。美国人为不文明现象担忧,实则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隐忧:共同体的道德架构正在我们身边瓦解。从家庭、邻里到城市、城镇,再到学校、教堂和工会,这些机构一直以来都在为人们提供道德支柱和归属感,而今却变得岌岌可危了。
诸如此类的共同体有时被统称为“公民社会”的机构。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提倡文明礼貌(这固然也是令人欣喜的副产品),而且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习惯、技能和品德能够使民主社会的公民充满活力。
当然,公民社会的各个机构都有其特定的目标。学校旨在教书育人,教堂和会堂是为了崇拜,如此等等。而当我们上学或加入教会之后,我们也就培养了公民美德,拥有了好公民应有的品质。比如我们学会了如何顾及全体的利益,如何担负对旁人的责任,如何处理利益冲突,如何在尊重他人意见之时为自己的见解辩护。总之,公民社会的这些机构使我们摆脱了自私自利的心态,使我们养成了参与公益的习惯。 55
一个半世纪以前,托克维尔称赞美国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说它培养了“心灵的习惯”,为民主奠定了基础。如果托克维尔所言不虚,那么就有理由为公民社会的健康而担忧(姑且不说它影响了人们在商店、在街头的举止)。
倘若家庭、邻里、学校出了问题,它们就不可能培养出一个成功的民主政体所需要的积极向上、怀有公德的好公民。(最近选举中的糟糕局面便说明了这一点。)
这起码是形形色色的全国性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这些委员会冒出来,正是要想方设法来复兴公民身份和共同体。它们包括:本月在费城成立的“宾州全国社会、文化与共同体委员会”,威廉·贝内特和前佐治亚州参议员萨姆·纳恩领导的公民复兴全国委员会,前教育部长拉马尔·亚历山大任主席的慈善与公民复兴全国委员会,以及坐落在波士顿的公民社会协会(最近它公布的一项公民复兴计划由前科罗拉多州众议员帕特里夏·施罗德主持)。
这些努力能否重振美国的公民生活,首先取决于它们是否愿意去应对那些富有争议的难题,因为正是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因素,严重破坏了维护美德的共同体。它们必须抵制这种委员会特有的诱惑,避开充满政治色彩的问题。 56
表面上看,复兴公民社会的举措与提倡公共生活中的文明礼貌一样,都属于非党派性的诉求。使家庭、邻里、学校变得更好,这样的努力谁会反对呢?但是,重振公民社会的努力要想不引起争议,除非它停留在劝导层面,就好像独立日演讲和国情咨文那样。
任何提振作为价值载体的共同体的真正举措,都必须面对那些破坏共同体的力量。像贝内特先生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将维护美德的机构所受的威胁归于两大根源:流行文化和大政府。
在他们看来,说唱音乐和低俗电影教坏了年轻人,而大政府和福利国家则消磨了个人的创造性,削弱了地方自助的积极性,抢占了居间机构的角色。他们主张要修剪大政府这棵遮阴大树,这样,家庭、邻里以及教会的慈善活动就能够在阳光下、在猛长的大树被修剪后留下的空间里茁壮成长。
文化保守主义者确实有理由担忧流行娱乐的粗俗化后果,因为流行娱乐和广告攻势一起,勾起了消费的热望,导致了与公民美德格格不入的政治冷漠。但他们却错误地忽视了最为了不得的力量——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的腐蚀力量。
当大公司动用其力量,从急需就业机会的城市和州那里获得减税,分区规划变更、环保政策退让的时候,它们对于共同体的瓦解作用比任何联邦命令影响都要深远。当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致使富人撇开公立学校、公园和公共交通而遁入特权飞地的时候,公民美德就变得难以维持,公共的善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渐渐消逝了。 57
任何重振共同体的努力,都必须与那些蚕食社会结构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进行斗争。我们需要的政治哲学,应该探讨什么样的经济秩序最适宜于自治以及维持自治的公民美德。公民重振的举措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提供了消弭政治分歧的途径,而是因为健康的美国民主政体需要公民社会的重振。提倡文明礼貌也是同样的道理。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