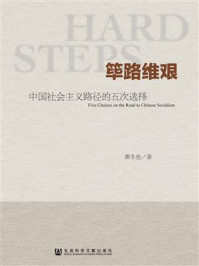我们知道,晚明以来以《功过格》、《阴骘文》等大量善书的出现为背景,形成了一股“道德劝善”的思想运动,这场“运动”是在16世纪中叶以降,伴随着阳明心学家所推动的心学运动之后而出现的,那么,阳明心学与道德劝善有何思想关联呢?在吾人看来,正如以上第一章所示,“劝善”其实是中国伦理学历史上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议题,尤其是自宋代晚期随着《太上感应篇》将“劝善”主题进一步彰显出来以后,在明代思想界逐渐受到关注,不仅在阳明心学运动中,“道德劝善”是其思想活动的重要内容,而且与心学运动相关联,大多数地方儒者、士绅以及官僚士大夫都在关注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即如何端正人心、整治风俗、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
依心学理论,它会告诉人们良知是内在的,所以每个人只要通过致吾心之良知就可改善自己、提升自己的道德人格,进而改善一家一乡乃至改善一国天下。然而除此以外,更有一种思想观点认为,仅仅依靠良知内在这一高度抽象的儒学心性理论是不够的,因为在劝人为善的同时,还必须告诉人们道德行为何以保证自己及其一家能得到相应的福祉,这正是《太上感应篇》乃至《功过格》等文献所宣扬的“转祸为福之道”(即“德福之道”)的思想主题。也正由此,晚明以来善书开始大量涌现,标志着一场新的思想运动正在酝酿、形成,我们称之为“劝善运动”。这场“运动”既有心学家的热心参与,也有普通儒家士人的积极推动。其目标则是通过行善积德以求得最大限度的福祉,进而重建理想的社会秩序。用儒家的传统说法,亦即通过“迁善改过”、“与人为善”以实现“善与人同”的社会理想。 [2]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心学与劝善之关系的问题。事实上,就心学思想之宗旨而言,当阳明将“致良知”作为一种道德说教向世人宣扬之际,其中就已蕴含了“劝善”的意味。而且,阳明自身对于“劝善”所具有的道德教化以及社会政治意义是有自觉意识的,他在晚年最后一次领军平定地方动乱之后, [3] 非常痛心地认识到“破贼”固然是一种“惩恶”手段,然而要使这些地方长治久安,最为有效的策略莫过于“劝善之政”。于是,他向朝廷上疏,指出:
为今之计,正宜剿抚并行。盖破灭穷凶各贼者,所以惩恶,而抚恤向化诸瑶者,所以劝善。今惩恶之余,即宜急为劝善之政,使军卫有司各官分投遍历向化村寨,慰劳而存恤之。 [4]
前此几年的正德十五年(1520),阳明在镇守江西、剿平湖广等地“叛乱”之后,亦曾直接向当地“顽民”出示告谕,要求他们“劝善纠恶”,措词不无严厉:
本院新行《十家牌谕》,以弭盗息讼,劝善纠恶。……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编排晓谕,使各民互相劝戒纠察,痛惩已往之恶,共为维新之民。 [5]
显然,阳明所说的“劝善”,既有道德教化的用意,更是出于社会治理的考虑。他在“上疏”、“告谕”等一类政治文献中,常常以“劝善”为说,以为与诉诸军事的“惩恶”手段相比,以道德劝化人心的“劝善”工作才是治理地方的根本之策,而“惩恶”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
阳明撰述于正德十三年(1518)的一部名篇《南赣乡约》, [6] 是平定地方动乱之后,为重建当地的地方秩序而发布的具有地方法令性质的公文,其中更是贯彻了“劝善惩恶”的思想。阳明认为地方动乱是由于“民俗之善恶”,而“民俗之善恶”固是由于“积习使然”,然而地方社会各种恶行的不断发生则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上面的原因,即“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的缘故;一是下面的原因,即由于“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熏陶渐染于里闬者无素,诱掖奖励之不行”的缘故,因此为从根源上防患于未然,阳明指出:
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他指明建立“乡约”无非就是为了“协和尔民”,同时也是为了推动互相之间的“彰善纠过”之实践,最终目的则是为了重建“仁厚”的一方风俗。为了更有效地推动“乡约”治理,阳明还作了一系列的具体规定,最具鲜明特色的措施是:“置文簿”三本,除一本为“名册”——即“会员”登记本以外,其余两本分别为“彰善簿”、“纠过簿”,实即善行恶行的记录本,这是为了“劝善规过”之用的,可见他的秩序重建的设想乃是以道德为核心的。须指出的是,阳明的这套“乡约”设计,对明代中晚期的“乡约”运动影响甚大,成为后世地方治理的基本文献之一。 [7]
令人关注的是,阳明的乡约设计不仅汲取了宋代吕大钧(字和叔,1031—1082)《吕氏乡约》中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宗旨, [8] 采用了朱子《增损吕氏乡约》中立“记善籍”、“记过籍”的方法, [9] 并且吸纳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颁布的《教民榜文·圣谕六言》的内容:“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10] 文中还提到了“鬼神鉴察”等宗教观念,并规定各乡村须“依法”祭祀鬼神,以便收到“民知戒惧,不敢为恶”之效,其云:
鬼神之道,阴阳表里。人虽无见,冥冥之中,鬼神鉴察,作善作恶,皆有报应。曩者已令乡村各祭本乡土谷之神,及无祀鬼神,再申明民间岁时依法祭祀,使福善祸淫,民知戒惧,不敢为恶。如此,则善良日增,顽恶日消,岂不有补于世道! [11]
这显示出在“榜文”一类的官方文书中社会政策与宗教政策往往结合得很密切。对照阳明《南赣乡约》所云,可看出除“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两条未被引用之外,其余均被阳明纳入“乡约”之中。
从明代社会思想史的角度看,将《圣谕六言》与《乡约》相结合,以便进一步加强“劝善规过”的教化作用,应当说这是阳明的首创。只是阳明在《南赣乡约》中没有直接点出“高皇帝”或《圣谕六言》之名,这说明阳明对于将《乡约》与《圣谕》作一番紧密的政教(教化)合一式的结合,尚无积极的态度。
然而到了他的弟子王艮(号心斋,1483—1541)那里,则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他直言不讳地宣称:
钦惟我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以孝弟为先,诚万世之至训也。 [12]
在心学运动中公开提及朱元璋《教民榜文》(即《圣谕六言》)这是首例。及至心斋之后,心学家们宣扬《圣谕》的意识变得日益高涨,例如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王栋(号一庵,1503—1581)、颜均(号山农,1504—1596)、罗汝芳(号近溪,1515—1588), [13] 以及浙中王门的周汝登(号海门,1547—1629)、北方王门的尤时熙(号西川,1503—1580)等人,就非常关注《圣谕》对于道德劝善、社会治理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特别是周海门,他在为会稽人朱培之建立的“明亲社”所撰的题词中宣称:“《六谕》之外无明亲,明亲之外无《六谕》。” [14] 非常明确地将《圣谕》定位为家庭伦理实践的纲领。至于尤西川,在其周围曾有人大量刊刻《圣谕衍》,并向乡村散发,据载:“伊阳遣人来,印《圣谕衍》三十部。……后又印《圣谕衍》下卷二百本,散于里甲。” [15] 可见,时人已将《圣谕》作为宣传品大量散布。而在早期的王门讲学运动中,也有不少心学家特别关注《圣谕》对于乡村治理以及家族和睦的重要性。 [16]
在心学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思想动向值得关注,依我所见,阳明的致良知教最终必然落实在社会层面的道德劝善,而他所倡导的以“乡约”治理基层社会、重整乡村秩序便是其劝善思想的具体落实。事实上,到了明代末年,对《圣谕》的重视已经不是个别心学思想家的兴趣爱好,而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例如即便对心学末流有严厉批评的高攀龙(号景逸,1562—1628)也毫不讳言地指出,诵读《圣谕》较诸“诵经”更能促进人们迁善改过:
人失学不读书者,但守太祖高皇帝《圣谕六言》。……时时在心上转一过,口中念一过,胜于诵经,自然生长善根,消沉罪过。 [17]
令人注目的是,高攀龙的这段话是作为“家训”二十一条之一,令其高氏子孙必须世代遵守的教条。
至于《圣谕》的通俗解说书,在晚明更是到了洪水泛滥的地步,而且不仅仅是将《圣谕》与《乡约》相结合,还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将律法及报应思想融入其中。例如,隆庆辛未年(1571)进士方扬 [18] 于万历年间担任随州州守期间,撰有《乡约示》一文,主张在讲乡约时,应结合《圣谕》,并配之以相应的法律条文,同时还可以辅诸《为善阴骘》之类的宣扬果报思想的劝善书,以“利害并陈,祸福具列”的方式向民众进行宣讲。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