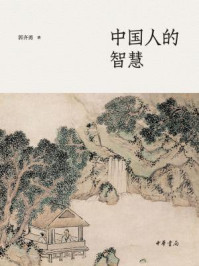太和之初的清谈是魏晋清谈的一个高潮。荀粲、傅嘏、裴徽三人在京都的清谈,可能只是当时清谈的重要场景之一。同时,后来正始玄学清谈的重要人物如夏侯玄、何晏、邓飏等,都曾在太和初活跃一时,对魏晋玄学的形成作出过重要贡献。只是由于史料的佚失,后人无从得知夏侯玄、何晏等人清谈的具体情况。可知的是,太和四年(230),魏明帝禁浮华,废黜了一批名士,以致魏晋玄学的形成被阻缓了,京都方兴未艾的清谈,由此沉寂了将近十年。通过回顾与分析这次禁止浮华事件,可以探知所谓浮华的实质,以及被禁的原因。
关于魏明帝废黜浮华之士的史迹,见于《魏志·明帝纪》:(太和)四年春二月壬午,诏曰:
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三国志》,页97)
在此前不久的太和二年(228),魏明帝下诏,强调“尊儒贵学”,“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太和四年的诏令,再次宣示进用人才以经学优秀者为先,同时指出后生进趋仕途“不由典谟”的倾向,一律罢退浮华不务道本者。什么是浮华?浮华主要指“不由典谟”“不务道本”,其实就是不重经学。
诸葛诞,便是禁止浮华事件中的罢退者。《魏志·诸葛诞传》说:“(诞)与夏侯玄、邓飏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诞、飏等修浮华,合虚誉,渐不可长。明帝恶之,免诞官。”这里,浮华之罪除“不由典谟”之外,又增加了“合虚誉”。“虚誉”是指诸葛诞与夏侯玄、邓飏等相善,互相吹捧,获取名誉。此风影响朝廷上下,以至京都翕然。
再读《诸葛诞传》裴注引《世语》,浮华之风的含义及罢退的浮华之士就更具体清楚了:
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三国志》,页769)
《世语》所说的浮华,主要指名士“共相题表”,即互相称扬,为之题目,有“四聪”“八达”“三豫”之目。此次被免官废锢的名士有十五人。
《魏志·曹爽传》中,也列出了废黜的名士名单:
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
裴注引《魏略》说:
初,(邓)飏与李胜等为浮华友,及在中书,浮华事发,被斥出,遂不复用……胜少游京师,雅有才智,与曹爽善。明帝禁浮华,而人白胜堂有四窗八达,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连引者多,故得原,禁锢数岁。
合以上数条史料可知,浮华的含义至少涉及三个重要方面,渊源有自,皆与汉末的风气有关。
一是学风上轻视经学的繁琐章句。这种浮华的学风,早在东汉的太学中就存在。《后汉书·儒林传》叙所谓“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是指传统的儒经章句之学渐渐不讲,多以自己的看法讲解经典。
二是言论华而不实,没有依据,不合义理。《后汉书》卷二五《鲁丕传》说:“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难者指辩论中的问难者或驳论文,说者指辩论或论文的立论。言辞华而伪,不切实用。
三是交游成朋党,不讲原则,互相题目,获取虚誉,名实不符。这种风气,也是汉末交游盛行,互相标榜的遗风。《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说:“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魏志·王昶传》说:“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可以肯定,当魏明帝听闻一批名士“共相题表”,有“四聪”“八达”等名目时,一定会联想到汉末党锢人物的互相标榜的风气。再有一件事直接刺激了明帝:夏侯玄自以为年轻俊美,知名当时,进见明帝时,与毛皇后弟毛曾并坐,觉得如玉树临蒹葭,不悦形于色。明帝亲见玄的狂妄无礼,左迁为羽林监。告密所闻与自己亲见,导致明帝愤而痛下杀手,禁锢了一大批浮华的名士。
太和四年明帝禁浮华,同他重视形名之学大有关系。《魏志·明帝纪》裴注引《魏书》,称明帝“好学多识,特留意法理”。显然,在学问上他与祖父曹操一脉相承。曹操是喜用法术的,晋初傅玄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形名。”(《晋书》卷四七《傅玄传》)而且,曹操“纠乱以尚猛”(见《傅子》),用严刑峻法。《魏志·明帝纪》裴注引《魏略》说:“时明帝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这二句是明帝特留意法理的证据。可惜走了极端,用特务手段侦查臣子,常以轻微过失就处以重刑。以此“法理”治国治政,与儒家的仁政和道家的无为而治背道而驰。曹操固然“纠乱以尚猛”,毕竟网罗到不少人才。明帝却将形名之学引至偏重于法家的邪径,把“浮华”的帽子扣到许多才能之士的头上,无情打击之,禁锢罢退之。这种作风,与他的祖父相去亦已远了。
明帝与其父曹丕也不同。文帝慕通达,已有魏晋开放自由的新型人格特征,又是个典型的文士,是当时文坛与学术沙龙的当之无愧的领袖,经常与文学之士赋诗作文、辩论学术、品鉴人物,本人也校练名理。明帝则“与朝士素不接”(《魏志·明帝纪》裴注引《世语》),臣下难见其面。由此推测,他与文学之士的关系,必定十分隔膜。既然与朝士素不接,不了解臣下的情况,却又喜欢“发举”,以示自己明察秋毫,无幽不烛。结果,揭发、举报必然成为获取讯息最主要的来源,诬告、陷害也就无法避免。上文引裴松之注引《世语》说,明帝禁浮华,而人白李胜堂有四窗八达,各有主名,于是逮捕胜,牵连出不少人。“人白”者,便是告密者。上有明帝“喜发举”,下必有告密者。故完全有理由说:史称诸葛诞、夏侯玄、邓飏等“修浮华,合虚誉”,可能确有言论、行为不检点之处,但这种夸大其词的罪名,恐怕是历史的另一种真实。
然则,我以为更具意义的历史真实,还是在揭示魏明帝禁浮华的深层原因,以及这一事件对魏晋玄学与清谈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上文所说,魏明帝“特留意法理”,这一学术理念,乃是他禁浮华的主因。“魏武初霸,术兼名法”。随后,王粲、傅嘏、卢毓等校练名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形名学逐渐转变为形上的名理学。黄初之末,太和之初,以荀粲、傅嘏、裴徽为代表的清谈人物,已在谈论《易》《老》《庄》的虚无玄远之理,离质实的儒家经学已有相当距离了。魏明帝偏重法理,既背离了“术兼名法”的家学,又不理解“校练名理”必然导致的虚无之学的学术走向,斥责夏侯玄、何晏、邓飏等人清谈为浮华。也不理解汉末以来新的人物审美,指责名士们的交游与品题为“合虚誉”。可见,禁浮华的实质,乃是对玄学的萌芽状态和汉末以来新的人物审美的全然不理解。
魏明帝禁浮华,是对魏初清谈的压抑和打击。对此,研究者已成共识。
 不过,京都清谈基本沉寂,不等于京都以外的情况也是如此。譬如在冀州管辂谈《易》,多数发生在魏明帝时期。再说,京都公开的清谈和交游不得不停止,而个人私下的学术研究仍可进行。例如明帝时何晏为冗官,有很多的闲暇时间,又正值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不可能闭门无所事事。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老子注》《论语集解》,是完全有可能始撰于正始之前的。夏侯玄的《本玄论》不知作年,他在正始年间长期戎马在外,曹爽集团于正始之末被诛灭后,他为避祸计,不蓄笔砚,以此推测,《本玄论》也有可能作于魏明帝时。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虽以正始玄学为成熟的标志,但在正始之前,走过了长达数十上百年的历程,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出现。从汉末的《易》学变迁,到魏初王粲、傅嘏校练名理,再到荀粲谈虚无玄远,夏侯玄作《本玄论》,魏晋玄学由萌芽而至渐渐成熟。魏明帝时期十余年间,是不可忽略的重要阶段。
不过,京都清谈基本沉寂,不等于京都以外的情况也是如此。譬如在冀州管辂谈《易》,多数发生在魏明帝时期。再说,京都公开的清谈和交游不得不停止,而个人私下的学术研究仍可进行。例如明帝时何晏为冗官,有很多的闲暇时间,又正值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不可能闭门无所事事。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老子注》《论语集解》,是完全有可能始撰于正始之前的。夏侯玄的《本玄论》不知作年,他在正始年间长期戎马在外,曹爽集团于正始之末被诛灭后,他为避祸计,不蓄笔砚,以此推测,《本玄论》也有可能作于魏明帝时。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虽以正始玄学为成熟的标志,但在正始之前,走过了长达数十上百年的历程,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出现。从汉末的《易》学变迁,到魏初王粲、傅嘏校练名理,再到荀粲谈虚无玄远,夏侯玄作《本玄论》,魏晋玄学由萌芽而至渐渐成熟。魏明帝时期十余年间,是不可忽略的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