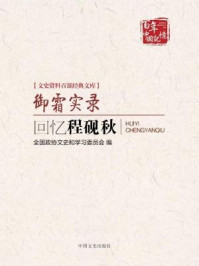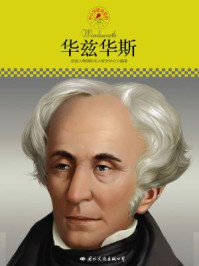路易·阿拉贡
曾与安德烈·勃勒东、菲利普·苏波一起创建“超现实主义”的法国诗人和小说家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虽然背着私生子的坏名,但从小就显示出极高的天分,特别表现在写作方面。他甚至在还不会写字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口述故事,由他的姨妈记下来。从六岁到九岁,儿童时代的阿拉贡写过六十多篇微型小说,加起来大约有两三本学生练习册那么厚,虽然有些小说的几个章节,每章只有几行字。他九岁那年,写出了一部长篇《卢内一家》。六年级考试时的一篇作文,法语老师认为写得很优美,被授予一等奖,并作为范文朗读给二年级的同学们听。成人之后,从1917年正式发表第一篇小说《贞洁小姐》献给大作家安德烈·纪德起,阿拉贡陆续出版了《阿尼塞或西洋景,小说》(1921)、《泰莱马格历险记》(1922)、《自由奔放》(1924)和《巴黎的农民》(1926),这期间还有其他几部作品在刊物上发表。作为一位作家,阿拉贡的创作,一开始就可说是十分顺利,但是正如俗话说的,有一好就没两好,阿拉贡在爱情方面遭遇了无比的坎坷。

南希·肯纳德
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家庭的南希·克拉拉·肯纳德(Nancy Clara Cunard,1896—1965)是伦敦社交界的名媛。她在国外受过教育,包括法国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军官、板球运动员西德尼·菲尔贝恩的婚姻破裂后,来巴黎定居,一身投入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运动。从这时起,她在举办上流社会交际活动的同时,先后出版了《不法之徒》(1921)、《尘世》(1923)、《时差》(1925)等诗集,并与几位作家、艺术家交往密切。南希生活十分随意,奥尔德斯·赫胥黎、欧内斯特·海明威、埃兹拉·庞德、詹姆斯·乔伊斯等,还包括路易·阿拉贡等,都是她的情夫,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
南希·肯纳德是1926年认识阿拉贡的,当时阿拉贡心情比较烦闷。她见阿拉贡“像一个英俊的王子那么帅”,一次两人一起乘坐出租车时,便在宽敞的车后座上“占有”了他。随后,两人一起去西班牙度假旅行,还去意大利看了南希的朋友诺曼·道格拉斯。1928年,阿拉贡帮助南希创建了“时时出版社”,属当时法国的一个比较小的著名出版社,一直运作到1931年。但是不多久,两人的关系就难以维系了。
南希喜欢旅行,阿拉贡只好陪着她去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德国以及法国的其他地方,这使他常常不能参加超现实主义团体的定期聚会。超现实主义是一个诗人的团体,本来,因为阿拉贡背地里还在创作小说,已使他和他们的关系有些不融合,如今这么一来,就更使他被团体怀疑与他们有矛盾。南希的个性也实在让阿拉贡难以接受。阿拉贡的传记作者皮埃尔·戴克斯写道:南希“不但常在酒吧间泡到很晚才回家,而且还喝得酩酊大醉。于是,她变得暴躁,无法自制,甚至发脾气,在精神上给阿拉贡造成很大的伤害。她还把自己过去的艳史讲给阿拉贡听,来折磨他……”(袁俊生译文)1928年,两人之间的感情已经破裂。9月里,南希带阿拉贡到了威尼斯后,阿拉贡甚至在这月中旬的一天服下安眠药水企图自杀。虽然做过军医的阿拉贡因“潜意识阻止他吞服致死的剂量”而安全获救,但是这爱情的痛苦,加上当时新出现在许多知识精英中间的共产主义和他原来的超现实主义的不调和,都使他在思想和创作上出现危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女人艾尔莎·特里奥莱适时地出现了。
艾尔莎·特里奥莱(Elsa Triolet)原名艾尔莎·卡冈(Эльза Каган),1896年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后来全家迁到莫斯科。她父亲尤利·阿列克山大洛维奇·卡冈是著名的律师,母亲叶连娜·尤利耶芙娜·别尔曼则是一位音乐家。
艾尔莎从小就喜欢文学。出于对诗歌的喜爱,她认识了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与她的认识,也让马雅可夫斯基见到了大她五岁的她姐姐丽莉,并把丽莉看成是他的至爱,从丽莉那里获得灵感,创作出不少好诗。
1917年,当时还是建筑学院学生的艾尔莎结识了法国驻俄国军事代表团的骑兵军官安德烈·特里奥莱,几个月后,两人结婚,外出旅游。
本来,艾尔莎以为可以很快回来。谁知十月革命后,苏俄封锁了边境的口岸。于是,她也只好漂流海外了。1921年,艾尔莎与丈夫离异,来往于伦敦、柏林和南太平洋中的塔希提岛。旅途中获得的感受,使她得以用俄语写出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在塔希提岛》,但迟至1925年才出版。这是艾尔莎的处女作,虽然两年前就已出版过一部她和朋友——未来的小说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合写的书信体小说《动物园,并非情书,或第三个爱洛绮丝》。她在这段时间的其他作品还有《林中草莓》(1926年,莫斯科)和《伪装》(1928年,莫斯科)。
艾尔莎往返于巴黎和莫斯科时,1924年在巴黎艺术家聚合的蒙帕纳斯住下,进入费尔南·莱热、马赛尔·杜尚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圈子。
早在1925年7月之前,艾尔莎就在“丁香园”酒店见到过阿拉贡。那段时间里,艾尔莎经常都在这家酒店写信、喝茶,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天早晨,阿拉贡参加超现实主义在这里举办的宴会,曾有一位朋友向他指认过坐在阳台上的艾尔莎。
1928年秋,马雅可夫斯基来巴黎,是艾尔莎邀请他来的,并为他担任翻译。当时,这位俄国未来派诗人在巴黎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名望,阿拉贡很想认识他,请他于11月6日在蒙巴纳斯附近的“穹顶酒家”见面。那天,阿拉贡的超现实主义朋友安德烈·蒂里翁也在那里,他因为所爱的女人离开了他,心情烦躁,独个儿躲在阳台上暗自神伤。阿拉贡上去安慰他时,蒂里翁记得艾尔莎也跟着上了阳台。她用目光审视了一下周围,像是开玩笑地说:“你们不让我看这个地方,都在这里干什么呀?”蒂里翁接着记述说:
阳台的后面,被用一块幕布隔成两部分,那里有一张又大又深的扶手椅。“就是在这里,还能做什么呢?做爱吗?”她说。我正好可以看到,她委身阿拉贡,大口大口地吻他。我猜得到发生了什么事。
一般都认为,1928年11月6日是阿拉贡和艾尔莎最终相识的日子,而且如原名为安娜·皮尔斯基的女小说家和传记作家多米尼克·德桑蒂所指出的,阿拉贡一定享受了与艾尔莎的第一次拥抱。但两人还没有马上结合,因为随后的那天晚上,阿拉贡不仅没有跟艾尔莎待在一起,反而去与南希跳舞。另有一次,他还向漂亮的舞蹈演员莱娜·安塞尔献殷勤。
不过,“艾尔莎虽然长得不像南希那么美”,皮埃尔·戴克斯写道,“但她有另一种韵味:女性美和典雅的气质与她的聪明才智相得益彰,就连阿拉贡也为她的聪明才智所折服”。于是,对一个刚失去恋人的男人和一个主动迎合男人的女子来说,《巴黎的放荡》的作者达恩·弗兰克说:“以后事态的发展不难想象。他们经常在城堡街幽会……”
1929年初,路易·阿拉贡和艾尔莎·特里奥莱一起住进了蒙帕纳斯区中心地段康帕涅街阿拉贡租来的工作室,开始同居。虽然他们迟至1939年才正式结婚,但从这时开始,此前的诸如莱娜等女人都消失不见了,他们两个真正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如艾尔莎在1929年4月8日的日记中所说的:“我们俩终于生活在一起了……这是我生活里难以想象的事件。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爱情的时光。”

艾尔莎和阿拉贡
从此之后,阿拉贡不但和艾尔莎在一起,还从他的这个极具聪明才智的女人那里获得了创作的灵感和其他的多方面帮助。
早年阿拉贡是经超现实主义诗人安德烈·勃勒东的介绍,参加达达主义等先锋运动的。本来,超现实主义者对苏联都抱有钦佩之情。为了探求意识形态,阿拉贡靠拢共产党,并像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激进知识分子那样,受到深刻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还曾因在法国号召革命,被判五年徒刑,缓期执行。
1929年2月20日,丽莉和她的丈夫勃里克外出旅游,经华沙到达柏林。丽莉打电话给艾尔莎和她母亲,于是阿拉贡和艾尔莎前去柏林看望他们。
丽莉的丈夫奥西普·马克西莫维奇·勃里克,其父虽是一位有钱的跨国大古董商和大珠宝商,但他本人在十月革命前曾参加过学生运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后,受到当时任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安纳托里·卢纳察尔斯基的重用,有研究者怀疑他可能还是苏联“肃反”组织“契卡”的秘密成员。勃里克在感情方面,崇尚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仿效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宣扬的“爱情自由”观,即恋爱自由、情感真诚和个性独立自主。他喜爱文学,尤爱诗歌,出版过诗集和评论集。基于他的这一爱情观,他不计妻子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情人关系,曾不止一次真诚地掏钱帮助马雅可夫斯基出版诗作。
艾尔莎和阿拉贡于3月22日到达柏林,与姐姐和姐夫一起待了十三天,直至他们去伦敦。交谈中,艾尔莎想通过勃里克帮助阿拉贡成为苏联文学机构的联系人。这一愿望虽然因为阿拉贡仍然没有摆脱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圈子而未能立即实现,但是后来毕竟还是起了作用。
艾尔莎看到阿拉贡具有文学创作的天赋,同时也看到这天赋被超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禁律束缚。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强调将经验的有意识领域和无意识领域完美结合,让梦和幻象的世界在“一种绝对的现实、一种超现实”中与日常的理性世界相连接。有些超现实主义者甚至一意追求无意识的自发显示,摒弃有意识的头脑的约束,甚至崇尚所谓的“自动书写”。艾尔莎坚信此种观念不仅无助于艺术创作,相反只会阻碍正常的艺术创作。她决意要让阿拉贡摆脱勃勒东,帮助他走出超现实主义的藩篱,跨上现实主义之路。同时她也明白,阿拉贡只有和超现实主义的老朋友脱离,才有可能去他向往的苏联。
1930年9月底,艾尔莎与阿拉贡从巴黎出发去柏林,看望她的与母亲待在一起的姐姐丽莉。马雅可夫斯基刚在4月14日自杀,除了在政治和文学上与“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及苏联当局发生龃龉,与丽莉和另一个女人的感情纠葛也是原因之一,这使丽莉陷入了无比的痛苦之中。在柏林,艾尔莎和阿拉贡遇到法国记者、电影作家乔治·萨杜尔,他正在等待签证去往乌克兰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首都哈尔科夫参加革命作家代表大会。既然萨杜尔的签证还得等待,无法跟随他们同往,于是艾尔莎和阿拉贡就只管自己走了(也有材料说是与萨杜尔一起走的)。一辆慢车带他们穿越波兰,到达苏联边境,接着他们见到了丽莉和一群朋友,于是顺利地到了莫斯科。经艾尔莎斡旋,阿拉贡得以受邀参加1930年11月5日至12日在哈尔科夫举办的作家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回到莫斯科后,阿拉贡和萨杜尔于12月1日同意签署了一份显然是由苏联文学界最高权力机构策划的“检讨信”。在这检讨信里,阿拉贡和萨杜尔承认,作为共产党员,本应让党去有效地监督自己的文学活动,并将此活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在这方面,他们两人犯了“原则性错误”。检讨信还表示,虽然自己与超现实主义团体中的其他成员所发表的个人作品没有任何关系,但只要这些作品打着“超现实主义”的名号,或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我们就应当担起责任来。尤其是安德烈·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因为它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进而拒绝所有的唯心主义思潮,特别是弗洛伊德主义”等等。
阿拉贡签字并做这样的自我批评,一个原因是与苏方的默契——这是邀请他们参加会议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涉及他与艾尔莎之间的关系,如传记作家所指出的:“阿拉贡无法拒绝签字,那是因为他得考虑艾尔莎及其家人的处境,尤其是得考虑丽莉的处境。拒绝签字就意味着和共产主义决裂,对于阿拉贡来说,也就意味着和他的爱情生活决裂。”
走上这条路后,必然的结果是回法国后与勃勒东决裂,同时必然地也开始由超现实主义的重视内部向外部方向转型,下决心走现实主义的道路。
此前,艾尔莎的前夫安德烈·特里奥莱每月都按时给艾尔莎寄1000法郎的生活费;如今艾尔莎已经与阿拉贡同居,自然不能再要这笔钱了。生活的拮据,让艾尔莎觉得不得不节制开支,同时又设法为著名服装设计师制作项链,并取得了成功。但是,为了支持阿拉贡,艾尔莎只好舍弃这项收入,凭借姐夫勃里克与苏联当局的关系,让苏联人邀请他们夫妇去苏联访问。结果,从1932年春至1933年春,他们两人在苏联逗留了一年,在此期间,阿拉贡得以担任苏联《世界文学》杂志法文版的编辑,既远离了超现实主义者,又受到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熏陶。1934年夏,阿拉贡又去苏联,出席苏联作家联盟第一届代表大会。1936年,再次去苏联访问,参加了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葬礼。结果也是明显的:阿拉贡出版了文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继《巴塞尔的钟声》之后,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了他以“真实世界”为总题的系列作品的第二部——小说《上等街区》。
《上等街区》描写了两个兄弟:爱德蒙·巴邦塔纳找了一个富有的女人做情妇,靠她来养活;阿尔芒·巴邦塔纳十七岁就离家进工厂做工。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探索法国的社会,书中融入了作家父亲所在的教区和母亲在土伦生活的回忆,当然也少不了他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如作品中的泰蕾丝·卡洛塔就与南希非常相似。
小说在苏联时动笔,于1936年6月10日完成,同年10月出版。在书的“后记”中,阿拉贡表示将此书献给多方面帮助他的、他亲爱的艾尔莎:“正是由于她,我才有今天。正是由于她,我才在厚重的云层里见到现实世界的入口,在那个世界里或生或死都是值得的。”
在1939年2月25日接到结婚证书后,“作家、报纸编辑路易·阿拉贡”和“作家艾尔莎·卡冈”于2月28日在巴黎第一区政府举行结婚仪式,他们的合法地位得到了解决。婚后的两个月里,他们一心创作,艾尔莎刚在几个月前出版了她用法文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晚安,泰蕾丝》。随后,夫妇俩穿越大西洋,应邀去纽约参加左翼作家代表大会。
艾尔莎说得对,从1928年两人结合时起,阿拉贡和她就“真正不可分离地在一起了”,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拉贡应征上了前线和德国法西斯入侵法国转入地下之时,阿拉贡也一次次与艾尔莎取得联系,团聚在一起,共同从事抵制纳粹的反抗运动。就算在两人一度被误解的时候,他们也都互相支持,互敬互爱。阿拉贡始终保持对艾尔莎的爱,并深深感谢艾尔莎的爱。
早在1931年的诗集《受迫害的迫害者》中,阿拉贡就有一首诗是题献给艾尔莎的,此诗描写诗人与超现实主义决裂后,因为有艾尔莎的爱的滋润,创作上才有新的开启。1941年的《断肠集》也是献给艾尔莎的,阿拉贡题献说:“献给艾尔莎,我每一次心的跳动都向着艾尔莎。”第二年,也就是1942年,阿拉贡出版了两部诗集《献给艾尔莎的赞歌》和《艾尔莎的眼睛》。诗人这样赞美他深爱的妻子:“形容她任何字眼不过分不荒唐∕我用云锦为她设计了一件衣裳∕我将使天使妒忌她晶莹的翅膀∕燕子妒忌她的宝气珠光∕大地的花卉将感到被冷落遗忘”;“……我……搜索枯肠啊呕尽心血方止∕凑成拙作战利品向你奉献”;“……我的明星我灿烂夺目的明星∕你怎能让我安心就寝∕世态炎凉挡不住我向你献心”。大作家安德烈·纪德称赞《艾尔莎的眼睛》中提前发表在刊物上的四首以“夜”为题的组诗说:“这是我多时来没有读到过的最好的诗。”
从1931年至1982年,在阿拉贡出版的差不多二十部诗集中,多出现有艾尔莎的名字,有的是部分,有的是全部为艾尔莎而作。他在诗中尽情赞美了艾尔莎的魅力,倾诉他对艾尔莎的爱,甚至说自己终于成了“迷恋艾尔莎的人”。他还以“迷恋艾尔莎的人”为题,写出多首诗篇,诗中写道:“不管你怎么做怎么说∕我曾是跟随你的影子……不管你怎么做怎么说∕我寸步不离你的脚印……∕不管你怎么做怎么说∕你被我死缠住甩不开∕你和我掺杂有往有来∕怎舍得我窃取的幸福∕扔不下使我战栗的爱……不管你怎么做怎么说∕离世之日已掐指可数∕天涯各方的人在叙述∕我贪恋在你的双膝上∕好似一把松开的花束∕不管你怎么做怎么说。”(本段和上一段的诗句,均引自沈志明的译文)异常感人地表达了诗人对艾尔莎的至死不渝的爱。
阿拉贡对艾尔莎的爱并不限于夫妻间的床笫之爱。就在他向好友坦言两人已经没有性生活之后,他仍然保持着对她的爱,甚至爱得更为深沉。这是因为如他在为《艾尔莎的眼睛》所作的长篇序言中又一次表示的,是由于自己有幸得到艾尔莎的启迪,才得以从迷茫中觉醒过来,并能“通过你(艾尔莎)的眼睛看清世界,是你(艾尔莎)使我感受到这个世界,是你教我懂得人类感情的意义”。也就是在《艾尔莎的眼睛》的结尾所表述的:“在宇宙毁灭、船只触礁之后∕会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会在大海的上空看到热切的∕艾尔莎的眼睛艾尔莎的眼睛艾尔莎的眼睛。”
心心相印、同甘共苦的爱,促使艾尔莎和阿拉贡两人在精神上沟通,并得到升华,从而在创作上获得成功。艾尔莎表现抵抗运动的短篇小说集《第一次冲突花费二百法郎》获1945年龚古尔文学奖;阿拉贡继续以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出《共产党人》六卷,尽管也有人认为是失败之作。1964年,《艾尔莎·特里奥莱和阿拉贡交叉小说集》出版。直至面对衰老挑战之时,阿拉贡仍然如戴克斯说的,“可以在成功的光环里去歌颂艾尔莎”:“撕开我的肌肤割裂我的躯体∕除天堂外你们还看到什么∕艾尔莎我的光明∕你们将那光明比作里面的颂歌∕将她那柔情∕比作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不但把对艾尔莎的爱扩大,以至和对法兰西祖国的爱糅合到一起,还从艾尔莎身上看到了女性的伟大,声称“女人是男人的美好未来”。
艾尔莎本来身体就比较差,终于在1970年6月16日永远离开了深爱她的丈夫。在9月安葬的那天,天阴沉沉的,冰冷的蒙蒙细雨把人的衣服都淋湿了。阿拉贡从一大堆玫瑰中取出一束来,将花瓣一朵朵摘下,放在爱妻的墓上。人们以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手势,可是他又取过另一束、第三束、第四束甚至第七束,不断地掰下花瓣,一片片放到艾尔莎的墓上。随后,他不用任何雨具,戴克斯说:“像钟摆一样在花堆和艾尔莎的墓穴之间来回走着……毫不动摇地来回走着。”戴克斯认为,“他是在强迫所有在场的人将这时间用来向艾尔莎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