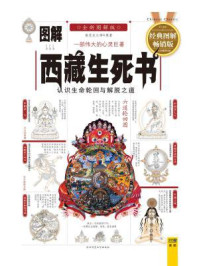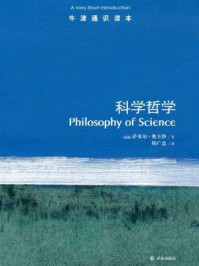在《悲剧的诞生》中,悲剧就其整体性而言,被界定为本原的矛盾、矛盾的酒神式解决以及对这种解决方式的戏剧性表现。 悲剧文化 和它的几位现代代表人物——康德、叔本华和瓦格纳——的特征在于再现和解决矛盾,即在矛盾的再现中以及在本原的基础上寻求矛盾的解决。“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在于智慧替代了科学成为终极目标,这种智慧以冷静的目光凝视世界的图景,以温柔的同情努力把永恒的苦难当作自身的苦难来把握”(《悲剧的诞生》,18)。然而,即使在《悲剧的诞生》中,也有成千上万处令我们感受到了与以上模式判然有别的一种新的概念。从一开始,酒神就是作为 肯定性的 神和 好肯定的 神同时出现的。他并不满足于在更高的超个人的快乐中“解除”痛苦,相反他肯定痛苦,并将它化为某个人的快乐。这就是酒神在多重肯定中得以 自我转变 ,不至于在本原的存在中消融,也不至于使多元性再次被并入原初之根基的原因。他肯定 成长的 痛苦,却不复制 个体化历程中的 苦难。他是肯定生命的神灵,对他而言,生命必须被肯定, 而不是 得到辩护或救赎。这后来的酒神之所以不能压住先前的,是因为超个人的因素总是伴随着肯定的因素,并且最终会呈现出它的优势。例如,书中曾出现永恒回归的先兆,这便是德米特得知自己将再一次分娩狄奥尼索斯的时刻,然而狄奥尼索斯的复活仅仅被诠释成“个体化的终结”(《悲剧的诞生》,10)。在叔本华与瓦格纳的影响下,肯定生命仍然只是被理解为消除普遍的苦难,理解为超越个体的快乐。“个体必须转化成非个体的、超越人类的存在。这是悲剧确立的目标”(《不合时宜的思想》,第3章,“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参看3—4)。
当尼采在工作的最后阶段回头看《悲剧的诞生》时,他认识到这本书有两个根本的变革超越了半是辩证法、半是叔本华的思想框架(《瞧!这个人》,“悲剧的诞生”,1—4)。其一正是酒神的肯定性格,他肯定生命,而非为生命寻求更崇高的答案或辩护理由。其二,尼采庆幸自己发现了一种对立,这种对立在他后来的工作中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因为在《悲剧的诞生》之后,真正的对立不再是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之间完全辩证的对立,而是狄奥尼索斯与苏格拉底之间更为深刻的对抗。反对悲剧、导致悲剧灭亡的不是阿波罗,而是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既不是酒神式的,又不是日神式的(《悲剧的诞生》,12)。他的观点被认为是一种古怪的倒错,“对于所有富于创造力的人来说,本能就是创造性的肯定力量,意识则起批判和否定的作用,在苏格拉底那里,本能变成了批判者,而意识变成了创造者”(《悲剧的诞生》,13)。苏格拉底是 堕落 的第一位天才。他让思想对抗生命,用思想来判断生命,并将生命设想成应该由思想评判、正名和拯救的东西。他令我们感到生命在否定的重压下被碾得粉碎,不值得渴望,亦不值得体验。苏格拉底是“理论家”,是悲剧人唯一真正的对立面(《悲剧的诞生》,15)。
然而,某种东西再一次阻碍了这第二个主题的自由发展。为了让苏格拉底与悲剧的对抗充分显露其重要性,为了让这种对抗真正成为“是”与“否”的对立,成为否定生命与肯定生命的对立,首先必须把悲剧本身包含的肯定性因素释放出来,让它毫无遮蔽地显示自己,摆脱一切依附状态。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尼采再也无法止步。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的对立也不得不退出最重要的位置,逐渐淡化或消失,以便真正的对立显现出来。最终,这种真正的对立本身也不得不作出改变,它不再满足于将苏格拉底视为典型的英雄,因为苏格拉底太希腊化,一开始由于他的明晰,显得有点过于阿波罗化,结尾被称为“苏格拉底——音乐之徒”(《悲剧的诞生》,15)又显得过于狄奥尼索斯化。苏格拉底并未全力否定生命;对生命的否定在他那里尚未找到它的本质。因此,悲剧人在纯粹肯定中寻找自己的元素时,必须认识到谁是他最深刻的敌人,即是谁在以真正的、确定的、本质性的方式进行否定。尼采非常精准地意识到了这一任务。因为他把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的对照——二神为解除痛苦达成和解——换成了更神秘的互补性对照,即狄奥尼索斯与阿里安
 的对照;这是因为在肯定生命时,一位女士,一位未婚妻的出现是必要的。狄奥尼索斯/苏格拉底则为真正的对立所取代:“我把狄奥尼索斯与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相对立——人们理解我吗?”(《瞧!这个人》,第4部分,9;《权力意志》,第3部分,413,第4部分,464)。尼采指出,《悲剧的诞生》在基督教的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并没有对基督教进行
仔细甄别
。而基督教恰恰既不是阿波罗式的,又不是狄奥尼索斯式的。“它否定美学价值,否定《悲剧的诞生》所承认的唯一价值;它是最深刻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相反地,在狄奥尼索斯式的象征里,肯定达到了最大的极限”(《瞧!这个人》,第3部分,“悲剧的诞生”,1)。
的对照;这是因为在肯定生命时,一位女士,一位未婚妻的出现是必要的。狄奥尼索斯/苏格拉底则为真正的对立所取代:“我把狄奥尼索斯与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相对立——人们理解我吗?”(《瞧!这个人》,第4部分,9;《权力意志》,第3部分,413,第4部分,464)。尼采指出,《悲剧的诞生》在基督教的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并没有对基督教进行
仔细甄别
。而基督教恰恰既不是阿波罗式的,又不是狄奥尼索斯式的。“它否定美学价值,否定《悲剧的诞生》所承认的唯一价值;它是最深刻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相反地,在狄奥尼索斯式的象征里,肯定达到了最大的极限”(《瞧!这个人》,第3部分,“悲剧的诞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