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世纪开启了人类的新纪元,各种高新科学技术层出不穷,既为人类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也给人类带来无穷困惑。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发达为人们提供了各种获取财富、知识、信息和交流的有利途径,人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以上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人对医学、医疗和疾病等的理解和判断,医疗的技术化和疾病的知识化越来越成为主流趋势。自18世纪中期以来,生物医学开启了人类认识疾病的科学性视角,以身体为本体的病因学理论主导着当前的医学发展,建立在此理论基础上的各种医疗科学技术越来越主导着人们认识和对待疾病的方式,过分的技术化带来人—病关系的异化。新型的生物—心理—社会—自然的医学模式与社会医学的诞生为人类认识疾病提供全新的视角,但它们的宗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为人类提供一个新的病因学理论,人类力图寻找的是致病的社会、心理、自然因素,而非从哲学、伦理学的认识论视角出发来重新审视疾病的本质、人—病关系、疾病的价值等。鉴于以上社会与时代背景,本人着力于寻找理解和解释疾病的伦理视角,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基本的伦理关系为框架来理解疾病的本质及其于人之存在的意义。
首先,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疾病伦理。在当前的医学研究中,“自然疫源性疾病”概念的提出集中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和疾病之间关系的认知,但这种认知仍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样的认识方式侧重于强调自然环境中可能存在的致病因素,并非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理解疾病以及从疾病中反观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为中心的疾病致思方式实质上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认识疾病,其对“自然”的界定也仅限于“自然环境”。本书立足于“自然”这一概念,从作为大自然的“自然”、作为自然规律性的“自然”和作为超验性哲学认识的“自然”三个层面来解析人与自然、人的疾病与自然的关系,这实质上与当前的环境哲学研究有着同样的理论基础。
环境哲学研究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首先是以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为前提的,重点在于凸显出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性与和谐共生性。在疾病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现代医学实质上仍然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理论为基础来进行阐释的,因而人的疾病仅仅是人体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负面结果,甚至人体本身也只不过是自然中的某种特殊物质,本书将其称为“疾病的自然化”,并没有看到人的疾病如人本身一样,拥有其自然属性,本书将其称为“疾病的自然性”。因而这一个部分论证,实质上是围绕“疾病的自然化”和“疾病的自然性”这两个范畴来进行的,重点在于批判前者的认识误区,它是一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论调的科学认识路线,后者却是一种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的哲学认识路线,主要借助中国道家老庄的自然概念、近代西方哲学家弗洛姆、艾默生的相关理论来论述。
然后,在“疾病的自然性”的基础上提出“疾病的道德性”,重点在于说明人的疾病如人本身一样,不仅仅是人体发展的自然规律性的东西,它更体现为人与“他者”之间道德关系的产物,疾病存在于人与一切“非我”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健康是生之自然状态,疾病是生之非自然状态,二者是对立统一的。疾病的道德属性体现为“生之应然”,是关系属性的,具有道德评价意义,个体须在与一切“非我”存在的道德统一中达到健康的自然状态。
其次,关于人与社会关系中的疾病伦理。当前的社会医学、医学社会学的研究重在寻找疾病产生的社会因素,但实际上,无论是单因素理论,还是多因素理论,都无法克服其中存在的认识矛盾,这种以“因果关系论”为基础的相关性研究并不能深刻地揭示疾病的本质。另一个问题是,目前无论是哪一个学科实际上都无法给“社会”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以实证调查方法为基础的社会医学研究大多数是以一定地区的人群为调查对象的,即使是以职业、性别、年龄等来进行抽样,还是需要选定地区——某些城市或农村地区,因而实际上仍然是以地理位置来定义“社会”,这样的定义与文化意义上的“社会”截然不同。
疾病的社会性实际上更与社会文化存在关联,而非地理位置意义上的“社会”。目前大致上形成了社会结构论、社会文化论、社会建构论、社会反应论等不同理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立足于社会文化来解释疾病。正是基于这样的状况,本书提出个体“主观社会”这一概念,它是个体通过一定的社会文化建构产生的心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疾病产生的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实际上是分不开的。疾病的社会性产生于人自身存在的社会性,但这种一般意义上的疾病的社会性无法说明疾病的个体差异性,因而我们使用“主观社会”概念来推论出疾病的个体差异性,揭示出疾病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与疾病有关联的应该是社会的伦理道德文化,而非其他文化形式。在众多的疾病解释理论中,伦理道德文化冲突导致的心理冲突是疾病的主要解释路线,无论是疾病的产生,还是疾病产生后,甚至对死亡的道德评价,都与一定社会的伦理道德文化价值体系有关,因而这个意义上的疾病本身并非像身体一样作为实体存在,它依赖社会的道德文化体系做出判断,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赋予疾病以不同的意义,因而它实际上是价值性的,而非认知性的。
在此基础上,本书继续探讨疾病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公共性问题,这也是基于疾病的社会性提出的概念,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以各种技术为主要进步力量的现代性社会之时,我们无法脱离“现代性”本身来认识疾病。无疑,疾病正如人自身一样,拥有着现代性的特点,这是以技术化为主要特征的人主体性的过分张扬产生的结果。而后现代性则是以对技术化、人的主体性的反思为主线来进行探讨的。疾病的公共性与社会性存在类似,但又有差别,疾病的公共性是比疾病的社会性更为一般性的概念。21世纪各种传染病疫情的暴发时刻昭示着疾病的公共性问题,这是当前疾病研究的重点问题,是全人类都应该引起关注的问题。
最后,关于人与自我关系中的疾病伦理。“身心关系”一直是医学研究中的难题,西方二元认识论前提下的“身心关系”是无法统一的,因为如此,甚至有现代学者认为“身心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的无解。现代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提出了很多理论来试图说明意识的产生和身心统一问题,但基本上坚持刺激—反应这样的认知主线。而医学研究中的身心疾病目前已经是得到认可与接受的,临床医学更多地依靠经验来做出诊断,并不试图寻找十分圆通的理论来支撑。也就是说,现代医学对身心疾病可以给出解释,但无法找到病根,其治疗的方法仍然局限在消除或控制身体上的不适症状。对于那些精神病患者,甚至是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目前并不能提供科学的诊断依据,导致临床诊断中的困境,在近代西方历史上也曾经产生生物医学主义与社会文化学派的分歧,以福柯为首的社会文化学派坚持认为人类的某些疾病实质上是社会强加在患者身上的文化烙印,实质上是一种社会道德歧视。因为理论上的分歧,进而使得精神病患者的收治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
无可否认,“自我”在严格意义上应该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伦理学中一般使用“道德自我”概念,但它们的实际内涵却是很难分清楚的,因而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弗洛姆曾经试图结合伦理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来建构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他提出“社会无意识”“社会品格”“社会自恋”这样的概念来分析群体的心理病态。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真正分歧在于对“人格分裂”“精神分裂”等症状的解释中,心理学的解释重点在于强调个体的心理、行为的社会不适应状态,个体与社会的一致被称为正常,反之,则不正常。而伦理学领域的解释则不是简单地使用这种适应性来做出评价,其基本的立场在于社会整体的伦理道德意识也是需要做出评价的,如果是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出了问题,当个体出现与社会不一致的状态之时,恰恰说明这样的个体是健康的。本书试图在以上认识的前提下分析个体道德人格发展中的疾病诠释,立足于个体道德人格的发展性与矛盾性及其在推动个体自我成长的作用来分析“自我分裂”“社会不适应”“人格障碍”等心理的病症。最后,论述“精神病的道德阐释”这部分内容,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人类对精神、意识疾病的不同观点及其对现代医学发展的深刻影响。
从当前国内的研究来看,目前尚缺乏以“疾病”为中心来研究的伦理学著作。在生命、医学伦理学研究领域,重点以“医患关系”“生命科学”“技术伦理”等为主题来展开研究,以相关问题和政策为研究对象,其论域离不开临床实践、公共卫生、生命科学领域中的具体问题,尤其是临床医疗和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这一领域中所引发的重要伦理问题。围绕“疾病”展开的研究,绝大部分是疾病文化史研究,尤其是传染病研究领域,历史上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发展的始末,人们从中所获得的传染病抗疫经验等,是这些研究所要重点陈述的内容,其研究范式实际上是历史学的。并且,这一类型的研究以西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研究为主。
在国内,相关疾病史的研究,或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疾病的并不多见,但也存在少数一些研究成果,如余新忠主编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其中收集了近年来从医学史、疾病史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另外,《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张泰山)、《中国抗疫简史》(张剑光)、《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于赓哲)、《药品、疾病与社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编)、《疾之成殇——秦宋之间的疾病名义与历史叙事中的存在》(陈昊)、《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张大庆)、《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于赓哲)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部疾病史研究著作。单纯地从伦理学角度来研究“疾病”的专著目前很难找到,因而本书的研究主题颇具有开创性意义。
蕴含在疾病中的伦理问题是研究者们近年来所热议的论题,但至今尚不存在系统、全面地论述疾病伦理的专著,众多的思想、观点等散见于一些学术论文当中。并且,有关疾病的概念、疾病与自然的关系、身心关系、儒家哲学中的病因理论等论题的研究虽然存在较多关于“疾病”“病因学”的论述,但其研究的视角繁多,未能统一从伦理学的视角深入展开论述。本书的目的在于系统、全面地对疾病的概念、疾病的自然化和自然性、疾病的自然性与道德性、疾病的社会性、疾病的现代性、疾病与自我建构的关联、个体道德人格与疾病的关系、疾病中的伦理实践、疾病与健康之间的伦理逻辑等展开研究。
在当前的各种研究成果中,虽然也有学者试图从这些关系中去探索疾病产生的病因,或试图从这些关系中解释疾病,但是未能有人系统、全面地阐述过伦理学视角中的疾病认识理论。例如,在医学领域,“自然疫源性疾病”概念揭示了自然环境对于人体的某些疾病产生的机制和深刻影响,但这种阐释是单向度的,仅仅凸显出自然环境与人体某些疾病产生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未能反视人体疾病所映射的自然环境的动态变化。因而本书的特色在于从两者的相互关系中揭示疾病,而非单向度的病因解释。同样地,从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角度来认识的疾病,不局限于从社会环境因素、个体道德人格与疾病产生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而是从二者之间的关系出发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重点凸显出疾病产生的“关系本体”,而非因果解释论的。
在当前的心身医学、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叙事医学的研究中,倾向于从“人病统一”的角度揭示二者关系,试图克服生物医学中“人病分离”的认知缺陷,但因为受二元认识论的局限,始终没有办法证成人病是如何统一的。本书从疾病产生的“关系本体”出发,克服生物医学中以“身体”为本体的疾病认识论局限,并凸显出人—病关系的发展性。立足于人类生活中的伦理关系来探索疾病产生的“关系本体”,这与当前生物医学研究中以“身体”本体为核心的疾病认识方法截然不同。另外,当前的社会医学仍然局限于从疾病产生的社会、心理因素出发来认识疾病,其疾病认识思维方式仍然是因果关系论,无法克服其中产生的认识论悖论。本书以“关系本体”论为基础,开启疾病认识论中的全新理论,试图在病因学理论上克服当前理论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为当前的疾病治疗实践提供更为圆通的理论指导,以减少疾病治疗实践中的伦理误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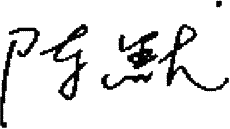
于桂林象山
二〇二一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