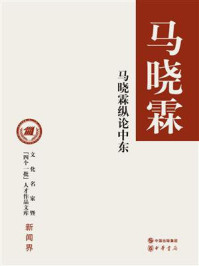一般来讲,政治哲学主要关涉的是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与其个体成员依据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建立关系从而实现二者和谐的问题。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以道德理性为基础构建个体内附于城邦的共同体伦理,而以洛克、霍布斯、康德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学凸显的是个体独立于政治共同体并受其保障的自由权利。黑格尔站在自由意志是人的本质规定这一近代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以逻辑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主义方式,把古代与近代政治哲学相耦合,构建起个体主观自由权利与共同体客观自由权利二者和谐共生的国家伦理。对于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所塑造的城邦伦理,黑格尔在怀着欣赏之情的同时又指责其缺乏内在的主体性,认为这是导致古希腊衰败的原因所在。与此同时,黑格尔在把主观性作为近代与古代相区分的原则的同时,对近代自由主义所秉持的论证自由的自然法理论与社会契约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特别指出,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也只是一种野蛮的主观任性,而把国家看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则是很随意的事情。说自由是人的本性,需要把它理解为人的使命与生活方式。这就是说,黑格尔区分了人的自由的本性与自由的实现的问题。马克思最初对政治哲学的思考以黑格尔的国家伦理视域中的理性自由为参照系,与黑格尔一样,致力于解决启蒙运动基于自然权利论与社会契约论凸显个体权利而贬损国家权威所造成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这一现代社会的困境,以求实现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之间的和谐共生。但是,由物质利益问题所导致的在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之间不能实现和谐共生的“苦恼疑问”,使得马克思不得不寻找与黑格尔不同的具体的实现途径。正如美国学者莱文所指出的:“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放弃了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权利理论,同黑格尔和古希腊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寻找一种支持集体主义和共同体的政治理论,黑格尔在道德和实体中找到了这个基础,而马克思发现这个基础在经济生活中。马克思使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依赖成为实体。马克思的政治理论是伦理学和经济学的综合。” [1] 德国学者卡尔·洛维特在《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断裂》中也讲道:“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市民社会当做一个需求体系来分析,这个体系的道德丧失在极端中,它的原则就是利己主义。他们的批判性分析的区别在于,黑格尔在扬弃中保留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差异,而马克思却想在清除的意义上扬弃这种差异,为的是建立一个拥有公有经济和公有财产的绝对共同体。” [2] 具体地说,黑格尔企图囿于资产阶级私有制而通过国家组织的有机构建以及符合自由理性的法制的理性创建,来达到作为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内在必然性体现的市民社会领域内的主观自由与作为人的相互交往所需要的外在必然性体现的政治国家秩序领域内的客观自由的具体统一,而马克思则清晰地决心颠覆黑格尔的自由哲学与国家伦理观的形而上学基础,从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入手,强调对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废除,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社会公共占有制,把私人劳动变成联合劳动,以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真正的和谐共生。借用加拿大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就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中,“作为人类营生活动的劳动,不再被严格地看作属于私人领域里的行为,而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公共、政治领域里的事实,才是他学说的重要部分” [3] 。这样,伴随着劳动从私人领域转化为公共领域,阶级对立得以消除,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政治国家也得以消亡,从而变为联合劳动的共同体,人的自由个性得以发展。这样,马克思最终扬弃了黑格尔的国家伦理生活的主张,开辟了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的以劳动解放为主线的以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和谐共生为目的的伦理之道。
本书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为主线,围绕着“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耦联”“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的解放的主题”“论马克思对近代政治哲学抽象性的批判”“论马克思的人权理论的方法论”“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功利主义维度”五个论题来进行编排,力图使该书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以期能够大致从整体上展现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精神面貌。事实上,从以上五个论题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政治哲学受英国启蒙运动的自由功利主义的影响要远比受法德的启蒙运动的自由理性主义的影响大得多。而黑格尔本人也是深受功利主义的影响,对自由问题有着更为符合历史发展进程并具有强烈的人的生存现实感的把握。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影响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政治哲学。
[1] [美]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4页。
[2]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断裂》,李秋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32页。
[3] [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