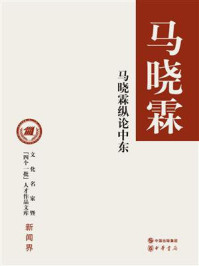我们在拙作《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的逻辑进路》[《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中阐述了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呈现出从《莱茵报》时期对代表特殊自由与特殊利益的市民社会同代表普遍自由与普遍利益的政治国家(法)间的对立所产生的“苦恼疑问”,到《德法年鉴》时期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造成的私有财产的解放这一手段与人的普遍的自由解放这一目的间的颠倒而感到的“困惑不解”,再到《巴黎手稿》时期对因资产阶级私有制而造成的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生命存在与对象化的劳动本质、对象化劳动与人的自我确证、内在自由与外在必然、个体生活与类生活之间的斗争而提出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发展的清晰的逻辑路线图。通过研读马克思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直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早期著作可以看出,在这一逻辑路线图中,鲜明地映现出黑格尔的自我意识逻辑的而又现实的运动的精神现象学的强烈印象。对此,我国著名学者张盾在《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中作了肯定。与此同时,他指出:“在政治哲学的领域内,劳动与财产是近代社会以经济为核心的政治生活的实体性内容,个人与社会则是近代政治的两种互相对立而又互为前提的主体性原则。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个人与社会、劳动与财产规定着政治之道德性的判断根据,因此它们理应成为思考黑格尔、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两个核心的论题。” [1] 就本章要表达的意思来讲,马克思早期对政治哲学的逻辑把握有着一个鲜明的伦理向度的坐标,这就是,《精神现象学》对自由的自我意识的伦理追问的历程嵌入其中,从而使之更凸显出鲜明的伦理向度。概括地讲,《莱茵报》时期对彰显特殊自由(特殊利益)的市民社会与昭示普遍自由(普遍利益)的政治国家二者之间的对立所产生的“苦恼疑问”,是《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环节由于劳动造成自身分裂为普遍性与个体性的对立而不能达到统一所产生的苦恼性的最初的现实的思想表达;《德法年鉴》时期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造成的手段(私有财产的解放)与目的(人的自由解放)的颠倒而感到的“困惑不解”,是《精神现象学》中理性环节的自我意识的颠倒(自由的普遍性与个体性的意识错乱),以及精神环节的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否定性(自由的普遍性被个体性的僭越)的现实的逻辑反思;《巴黎手稿》时期对因资产阶级私有制而造成的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生命存在与对象化的劳动本质、对象化劳动与人的自我确证、内在自由与外在必然、个体生活与类生活之间的斗争所造成的“历史之谜”而提出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是《精神现象学》中绝对精神环节继绝对宗教概念的发展实现了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和解。总而言之,正如卡尔·洛维特指出的:“黑格尔的最重要的原则,即理性与现实同一的原则,也是马克思的原则。” [2]
一般来讲,政治哲学主要关涉的是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与其个体成员依据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建立关系从而实现二者和谐的问题。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以道德理性为基础构建个体内附于城邦的共同体伦理,而以洛克、霍布斯、康德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学凸显的是个体独立于政治共同体并受其保障的自由权利。然而,黑格尔以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方式,把古代与近代政治哲学相耦合,构建起个体主观自由权利与共同体客观自由权利二者和谐共生的国家伦理。马克思最初对政治哲学的思考以黑格尔的国家伦理为参照系,并跃然于其博士论文中。其博士论文作为自由哲学的宣言书,正像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那样,马克思在其中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家”,指出他们对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进行了各自的特殊的充分体现,“这些体系合在一起形成自我意识的完整结构”。 [3] 从基本内容上讲,其博士论文已对三派合成的自我意识的完整结构的内容作了一定程度的阐述,包括感性世界基础上人类知识的真理性与可靠性的问题,哲学家关于他自身的特殊意识同现实世界(自由与必然、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对天体崇拜所产生的心灵迷乱(宗教)问题,自我意识作为个体独立的绝对原则的问题,人的快乐幸福何以可能的问题。不仅如此,对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强调的自我意识的辩证发展的思想,马克思予以了高度的承认,强调自由的自我意识哲学在世界化(自由的自我意识现实化)的同时世界要哲学化(世界要被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哲学的火焰所吞噬)。
精神现象学阐释的是精神实体即是主体的前提下,意识实现其自身(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绝对知识)科学发展从而达到认识其真正本质——绝对自由的伦理整体的过程。在《精神现象学》第四章中,黑格尔指出斯多葛主义代表的是纯粹的自由的自我意识的不变形态,它同主奴关系中基于劳动所形成的独立的主人与奴隶的各自的自我意识相一致,而怀疑主义代表的是经验任性的自由的个别形态,它与主奴关系中主人(欲望)与奴隶(劳动)彼此间否定相一致,这样一来,自我意识就双重化了自身,把主人与奴隶的两面性集中于一人之身而二元化的同时还没有达到统一,“这就是苦恼的意识” [4] 。也就是说,苦恼的意识根源于主奴关系,主奴关系使得自我意识自身分裂为以斯多葛主义为代表的不变形态与怀疑主义为代表的变化形态的对立,因而是自我意识对自身的双重化困境的矛盾的意识。然而,在精神现象学中,苦恼的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运动,历经理性环节的自我意识的颠倒(自由的普遍性与个体性的意识错乱),精神环节的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自大狂所造成的政治恐怖的痛苦,绝对精神环节的绝对宗教概念的发展在实体与自我意识之间实现和解,最终以绝对知识所理解的意识与自我意识统一中的纯粹的绝对自由这一伦理世界而告终。
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 [5] 。对此,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予以充分肯定,指出黑格尔与他之前的哲学家们相比,是从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理性,即是“根据整体观念来构想国家的” [6] ,国家作为整体机构通过创制符合人类理性的法律来教育与训导公民过着伦理生活,实现法律上与伦理上的自由。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对精神现象学中意识实现自身的科学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现实性原则”予以了高度的关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意识作为科学的过程必须具有现实性,否则,“科学就仅只是自在着的内容,内在着的目的,它还不是精神,而仅仅是精神的实体” [7] 。也就是说,意识作为最初的知识只是感性的意识,它要成为真正的知识或科学,必须经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道路——现实性的自为过程。对此,马克思以真正的哲学来看待,把现实性上升到时代性的高度,强调真正的哲学在精神上是时代的精华,“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8] 。
但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所面临的林木所有者与贫苦农民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对立的残酷现实中,黑格尔的理性的国家观念及其法律降低为维护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的同理性相抵触的手段而不再具有实现公共利益的理性,它没有照亮私人利益的空虚的灵魂。然而,基于对黑格尔式的国家伦理的认同的强烈感情,马克思仍然强调“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涉及物质的课题” [9] 。由此出发,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指责政府当局没有顺应人民的呼声,其管理的贫困导致了摩泽尔地区农民生活的贫困,这惹恼了政府当局,《莱茵报》被指企图阐述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理论而遭到查封。对此,在《评部颁指令的指控》中,马克思仍然从黑格尔的国家伦理出发,不得不态度含糊地指出:“《莱茵报》从来没有偏爱某一特殊的国家形式。它所关心的是一个合乎伦理和理性的共同体。” [10] 《莱茵报》被查封使得马克思在普遍的国家伦理与特殊的物质利益关系之间遭遇到了思想不能厘清的苦恼,这就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他在《莱茵报》时期遇到对物质利益(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而产生的理性的良心痛苦——“苦恼的疑问” [11] 。而这就是黑格尔的苦恼的自我意识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特殊呈现。由此开始,普遍利益(普遍自由)与特殊利益(特殊自由)、政治国家(政治共同体)与市民社会(个体利益)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政治哲学思考绕之以动的轴心。
《莱茵报》被查封使得马克思不得不退回书斋里来研究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的哲学基础并对其进行批判,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进行颠覆性的思考。在黑格尔那里,就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来讲,被理解为自由的绝对观念自身的内在的相像的逻辑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概念领域,由此最终得出“普遍利益和在普遍利益中保存着特殊利益,这是国家目的” [12] 的结论。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讲道:“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逻辑学的补充。” [13] 作为对黑格尔整个法哲学的反动,马克思在肯定黑格尔正确地看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的同时,指出黑格尔只是满足于从逻辑观念发展的表面解决问题,并得出如下结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 [14]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对市民社会成员的利己主义的自我意识的张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造成的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对立这一“现代性”问题发出了“困惑不解” [15] 的感慨,指责政治解放以事实上的私有财产的解放的手段颠倒了理论上的人的普遍解放的目的,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普遍解放让位于作为自我意识的人格体现的物的私有财产的解放,这是黑格尔的理性环节自我意识的颠倒(自由的普遍性与个体性的意识错乱),乃至精神环节的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否定性(自由的个体性对普遍性的僭越)的现实呈现。
在精神现象学中,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先是由意识的环节进展到自我意识的环节,继而由自我意识的环节进展到理性环节,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个体自我意识与他人的个体自我意识之间的需要的相互满足的劳动发挥其所导向的整体性事业(在其中,个体在为整体献身的同时从其中复得其自身)的独特作用。理性就是个体自我意识在与他人的个体自我意识相互满足的劳动中通过形成相互结合的整体性事业而实现对对方自由的相互承认,也就是,“意识确知它自己即是一切实在(自我意识的普遍的纯粹自由——引者注)这个确定性” [16] 。所以,伦理是自由的自我意识在与另一个自由的自我意识统一中的整体的理性实现。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就单纯的个体自我意识来讲,其目的是欲望与自然冲动,因而快乐就是个体的心的规律,而心的规律却屈服于伦理纲常与法律等外在的强制的必然性,从而自我意识遭受痛苦的情绪。于是,个体的自我意识陷入疯狂(自我意识阶段苦恼意识的继续),这种疯狂是一种矛盾或颠倒,即由于个体的心的疯狂,个体的自我意识把自身的心的规律错乱地当成自由的普遍的现实。法国大革命就是如此,自我意识的个体要力图实现自身的自由,并把个体的心的规律当成普遍的自由的本质(这种本质不是现实性的而是非现实性的普遍性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实践意识就要处心积虑地扬弃与其矛盾着的必然性以避免痛苦,力图使自己变成一个自在自为地合乎规律的现实,自为地发展成普遍性。为了最终实现自由的普遍的秩序这一本质,就必须牺牲意识的纯粹个别性,进入到德行的意识。而所谓的德行意识,在精神现象学里,就是个体性必须接受普遍的真与善的训练与约束,从而使得普遍的自由本质在个体的经验自由里获得现实性,而个体性的经验自由成为普遍的自由。
黑格尔认为,当理性的自我意识确信其自身是一切实在(自我意识的具体的普遍自由)时,自在自为的理性就成了精神。在精神环节中,启蒙意味着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主体性的觉醒。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启蒙的自我意识还只是一种纯粹识见,而“纯粹识见就是作为纯粹自我或否定性的纯粹意识” [17] 。因此,它仍然没有摆脱理性环节个体的心的自大狂,从而没有把精神实体的普遍自由本质作为本质,“而是把本质认作一种绝对的自我[主体]” [18] ,这种绝对的自我是一切个别意志本身,或者说,是一切人格和每个人格的自我意识,是欲望着的或实在的普遍意志,它通过“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意识与私人的意识之间的一种交互作用” [19] 的运动企图来完成实体的绝对自由的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事业。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普遍性事业实际上并不能够实现,因为普遍的意志只有在一个单一性的自我之中才是一种现实的意志,这样一来,一切其他的个别的自我意识就被排除于这个行动整体之外,因而结果是这个行动就不是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的行动,其实质是自由的个体性对普遍性的僭越。由此,黑格尔得出结论,绝对的自我,也即普遍的自由是不能够产生任何肯定性事业与行动,而只能是否定性行动与毁灭。于是,一种把普遍意志与个别意志协调起来的具有自身确定性的新的道德精神就出现了。一方面,这种道德精神追求与客观自然间的自在形式下的和谐,它不放弃幸福,有着欲求的现实行动;另一方面,追求与感性意志间的自为形式下的和谐,它在欲求的现实行动中履行着义务。因而,新的道德世界观是义务与现实之间被设定的自在而且自为存在着的和谐。
以黑格尔对个体自我意识的疯狂(现实成为非现实)与绝对自我的否定性(自由的个体性对普遍性的僭越)的批判为依据,以黑格尔所构建的新的道德世界观为参照,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政治解放及其所追求的人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般的、普遍的人的解放的理论,从而呈现出精神现象学的逻辑观念、概念特色与伦理诉求。具体地讲,政治解放的实践后果就是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获得独立,不再依附于政治国家而与其相分离,因此,政治解放从实质上讲就是在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表现为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公民权与经济共同体意义上的人权的对立。也就是说,政治解放以绝对自我自由的名义,在打倒封建主义及其统治者的权力的同时,以人民普遍自由的名义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在政治国家中个体成员是政治人、法人,他只有以抽象的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并享有普遍自由的权利,没有政治差别。可是,“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 [20] 。公民在作为市民社会成员时是现实的人,他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因而是与共同体分割开来的具有私人任意的个体,他所享有的人权是与共同体相分离的特殊自由的权利。因此,在这些私人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是需要等私人利益这些自然必然性把独立的个体联结在一起。在需要和私人利益方面,人具有非政治差别,譬如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差别,政治国家承认这些非政治差别,并以此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唯有如此,政治国家才感到自己必须作为政治国家,来体现自己所代表的那种纯粹的自由的普遍性。因此,马克思指出,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在意识与现实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 [21] 。天国生活是人作为公民,即类存在物在政治共同体中所享有普遍的自由权利,但是,在其中,个体的现实生活被剥夺了,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尘世生活是人作为活生生的人在市民社会中进行着利己目的的、互将为工具的私人活动,充满了现实的特殊性。马克思对政治解放本质的这一认识,与前已述及的黑格尔对绝对自我的绝对自由本质的批判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在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民权与人权进行区分的基础上,以黑格尔所构建的新的道德世界观为参照,马克思指出:“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正如我们看到的,公民身份、政治共同体甚至都被那些谋求政治解放的人贬低为维护这些所谓人权的一种手段。” [22] 对此,马克思提出了如下疑问:“为什么在谋求政治解放的人的意识中关系被本末倒置,目的好像成了手段,手段好像成了目的?他们意识上的这种错觉毕竟还是同样的谜,虽然现在已经是心理上的、理论上的谜。” [23] 这里,马克思所指出的谋求政治解放的人的意识的错觉——心理上的、理论上的谜,就是黑格尔所讲的理性的自我意识在普遍性自由与特殊性自由间所产生的错乱、颠倒或疯狂。马克思认为,要解开这种心理上的、理论上的谜是很容易的,一方面,谜的产生的原因在于政治解放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开来,政治国家在组织成为普遍事务的同时,政治国家并没有对市民社会加以批判,相反,它把包含着劳动与私人需要、利益和权利等市民社会的领域看作自己的持续存在的、无须论证的自然基础。另一方面,由因到果,谜的解开在于克服政治解放颠倒目的与手段,即颠倒人性与物性的缺陷,使人的世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也就是不再把私有财产的对立作为人的本质,而是个体的经验劳动及其关系变成类存在物与类生活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个体自身的力量真正成为社会整体力量的一部分,并且这种社会整体力量不再是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个体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人的普遍的自由解放才能完成。
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最终结果就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时期所指责的资本作为对劳动统治的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所造成的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对立,是资本的自我意识的现实化与劳动者自我意识的非现实化的对立,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的不可调和,表现为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成正比关系。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充分肯定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对人的生成(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异化及其异化的扬弃,具体地说,人在劳动的基础上作为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个体生活与类生活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最终成为自由自觉活动着的人)的确证作用的同时,对自我意识的抽象的利己主义本质,及其作为其现实表现的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所造成的异化劳动基础上的普遍自由(利益)与特殊利益(自由)之间的矛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把共产主义设定成为对私有财产——劳动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作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表现的人的生命存在与对象化的劳动本质、对象化劳动与人的自我确证、内在自由与外在必然、个体生活与类生活之间的斗争所造成的“历史之谜” [24] 的解答。这是对黑格尔的精神环节的自我意识的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和解中所达到的伦理精神、绝对宗教环节的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和解、绝对知识环节的概念式理解的绝对自由的扬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对《精神现象学》的体系作了如下编排:(A)自我意识。包括:Ⅰ.意识。Ⅱ.自我意识。Ⅲ.理性。(B)精神。(C)宗教。(D)绝对知识。紧接着,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是“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 [25] 。这就是精神现象学内在地蕴含着的“秘密”。由此看出,概括地讲,精神现象学最终目的是对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精神的本质的全部重新占有,使意识(纯粹的普遍自由)与自我意识(现实的特殊自由)之间历经诸环节而达到自在自为的统一基础上的绝对自由的伦理整体。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接受并发展了精神现象学理性环节中关于相互需要的满足的劳动基础上的整体性事业与个体自我实现之间有机统一的伦理意识的思想,指出正是在改造自然界的对象化的活动——劳动中,一方面,人才成为真正的自然存在物,自然也才能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人成为社会存在物,人在生产社会的同时社会也生产人。人的活动与享受都是社会性的。但是,由于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人的劳动发生了异化,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性、人的自我确证——对象化劳动变成了异己的动物般的活动,自身的劳动产品变成了他人的产品,人的对象化劳动的本质、人的需要与享受等现实性变成了非现实性,人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劳动着的人受着一种外在的必然性的奴役而丧失了自身的自由,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与劳动及其二者之间的能动的、内在的矛盾关系。资本作为支配劳动的权力,驱使劳动者为其创造财富,其结果是,资本在增殖的同时劳动在贬值。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共同性的本质作了明确的界定,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前提下,共同性只是相像中的普遍性,表现为劳动的共同性——劳动是每个人的天职,以及资本——劳动间平等地支付工资的共同性,但其本质是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也就是对劳动共同支配的共同性。“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 [26] 换言之,作为意识形态的共同性,资本主义的普遍意识(自由与平等)从本质上讲是普遍的资本家共同体这一现实的共同体的抽象的理论形式,也就是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自我意识抽象的普遍反映。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 [27] 。而对于资本家共同体所创造的工人的现实生活(异化劳动),这种抽象的普遍的自由意识恰恰是工人自由自觉的类活动的对立面,即个人自主活动的丧失。这意味着,对于工人来讲,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那种追求快乐与幸福的心的规律作为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受着作为支配劳动的权力——现实的资本家共同体这一外在的必然性的制约。
对于马克思来讲,工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幸福的实现,即是对自己真正本质的重新占有,必须扬弃作为外在必然性的普遍的资本家共同体。这是因为,资本家共同体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自然的掠夺进行财富积累而导致对工人自由自觉活动的扼杀,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成正比。从物性的角度讲,工业作为自然对人的对象性的生成性存在,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观察自然时的行动意识——感性的“心理学”,将其比喻为人的本质力量打开了的一本“书”。但是,马克思也敏锐地指出,对于工业这种感性的“心理学”,人们仅仅是把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看作是感性的、有用的对象形式,并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里,马克思汲取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启蒙的另一派,即英国的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所作的分析。功利主义强调有用就是作为纯粹识见的自我意识的现实的对象,“有用是启蒙的基本概念” [28]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人的内在的必然性、需要的感性的自然界,从有用性上讲表现为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即资本家的富有与工人的贫困,因此,马克思明确提出要以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来代替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就必须使得工人充分意识到无产与有产的对立,其实质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是无关紧要的,而必须理解为能动的矛盾关系,即劳动与资本的相互生成,劳动为资本增殖财富,资本为劳动提供维持其生存的生活资料。资本是支配劳动的权力,而劳动依附于资本。所以,马克思强调,人用自己的双脚立地而不是靠别人恩典为生才能是独立的存在物,人必须靠自己的创造来生活,“创造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 [29] 。这里,创造的概念,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绪论”中就已提出。他论述绝对观念在实现自身的自由本性的目的需要借助于人的特殊需要、欲望、热情、利益等手段时,指出绝对向前进展时遭遇到自由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无限的“对峙”或“冲突”,表现为特殊的自我意识间权利与义务的冲突,或自由的自我意识反对现行的已定的制度,这就是特殊的自我意识在历史上实现它自己的自由时所包含的一个普通的原则,即“创造的观念” [30] 。从精神现象学角度看,创造的观念是自我意识的自为的对象化、现实化与外化。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的创造活动被异化了。因此,劳动异化必须被扬弃,物的私人占有,即资本对物的占有必须废除。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作为人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是把人本身和自然界看作是人的本质的理论上和实践上人的感性意识的开始,它把世界历史最终看成是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基础上,人通过自身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而对自身的自然本质的直接占有,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 [31] 。这里,社会的概念,不是以国民经济学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只注重个体利益的真实性而把社会看作是个体的集合式的简单相加,因而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简单叠加的那种粗浅的认识,所以,马克思明确指出,必须避免功利主义对社会进行集合式理解的抽象做法,并把这种抽象的理解同个体对立起来。马克思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人的相互满足的劳动所形成的整体性的伦理生活逻辑观念指出,个体生活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个体生活较为特殊的或普遍的方式。共产主义就是个体生活与类生活的互为特殊或普遍的方式,是二者的有机统一。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度及其所进行的工业化生产,不仅造成工人的自我异化,而且也造成资本家自身的异化——仅仅满足于财富的积累而相互间自由竞争从而把自身等同于粗陋的对自然占有的动物般的物质欲望,因而,在实践中必然造成作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表现的“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等“历史之谜” [32] ,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上述“历史之谜”的解答。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讲的共产主义,一方面,就精神现象学的逻辑展开的思维方式来讲,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积极的扬弃,它是否定之否定的肯定过程,是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下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导致劳动者不能直接享受并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否定,因而是对劳动者个体对生产资料的共同的直接的占有的重新肯定。对于劳动者作为自然的存在物来讲,自由与幸福的一面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自然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另一方面,就精神现象学的逻辑展开的所要达到的普遍的绝对的自我意识的自由的伦理整体而言,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的“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等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对立的伦理性整体的解决方案,但它就此扬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环节的宗教(基督教)所诉求的实体与自我意识之间实现和解,以及绝对知识所理解的意识与自我意识统一中的纯粹的绝对自由。对于劳动者作为社会的存在物来讲,自由与幸福的一面就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与法律所规定的社会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成为人类社会的主人。成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主人,就是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把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对自然与社会的异己的关系还给人本身,使得人的普遍自由成为人的真正本质。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意义就是马克思曾明确肯定黑格尔的积极意义在于:“他——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 [33]
正是因为黑格尔的这一积极意义,晚期的海德格尔指出,没有黑格尔,马克思不可能改变世界。但又正如张盾所指出的:“不批判黑格尔,马克思同样不可能改变世界。” [34] 究其缘由在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这一积极意义同时也暴露出自我意识自身的“形式的”、“抽象的、思维着的本质” [35] ,因而,精神现象学关于人的自我产生、自我对象化、自我异化的运动,“是绝对的因而也是最后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安于自身的、达到自己本质的人的生命表现,……是人的神性的过程” [36] 。正是基于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把人的达到自己本质的生命的表现(类意识与类生活)的实现披上“神性”的外衣——从而呈现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 [37] 对立的窥见,马克思以对精神现象学批判的口吻讲道:“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即精神现象学作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的科学——引者注)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即精神现象学——引者注)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 [38] 这意味着,不同于黑格尔的把人的类意识与类生活的实现披上“神性”的外衣的做法,马克思以客观的而不是以精神的实践来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人的类意识与类生活。他指出,共产主义不仅是思想上或理论上的共产主义,而且是实践上或革命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否定之否定——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占有,以否定导致人的生命的现实异化的私有财产为中介,“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39] 。
与马克思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扬弃资产阶级私有财产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和解的共产主义伦理共同体不同的是,黑格尔企图囿于资产阶级私有制而通过国家组织的有机构建以及符合自由理性的法制的理性创建,来达到作为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内在必然性体现的市民社会领域内的主观自由与作为人的相互交往所需要的外在必然性体现的政治国家秩序领域内的客观自由的具体统一。换句话讲,立足于对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的批判,正如卡尔·洛维特在《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断裂》中所讲的,黑格尔与马克思都认为资本主义道德的丧失到了极端,因此需要建立自由人联合的绝对的道德共同体,但黑格尔是以伦理国家来规制市民社会从而在二者之间达到合理性,并没有要消灭市民社会;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及其为基础的政治国家是不合乎理性的现实,因而是虚假的共同体,为此必须通过共产主义的革命行动以消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1] 张盾:《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2]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断裂》,李秋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4]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58页。
[5]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启泰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8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7]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
[16]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75页。
[17]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7页。
[18]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8页。
[19]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2—13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28]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10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
[30]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309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页。
[34] 张盾:《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