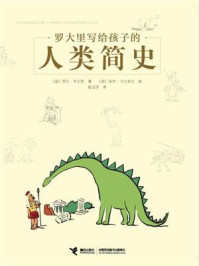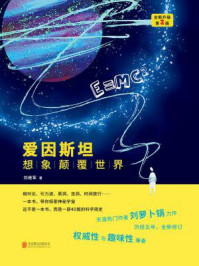布莱恩·阿瑟独自坐在吧台边的桌子旁,凝视着酒馆的前窗,尽量忽略那些为了早点开始“欢乐时光”
 而涌入酒馆的年轻都市白领。外面,在金融区的钢筋混凝土峡谷里,旧金山典型的大雾天气正变成蒙蒙细雨。这正符合他的心境。在1987年3月17日的这个傍晚,恰逢圣帕特里克节
而涌入酒馆的年轻都市白领。外面,在金融区的钢筋混凝土峡谷里,旧金山典型的大雾天气正变成蒙蒙细雨。这正符合他的心境。在1987年3月17日的这个傍晚,恰逢圣帕特里克节
 ,但他没有心情欣赏店里的黄铜制品、三叶草和彩色玻璃装饰,没有心情庆祝节目,更没有心情和穿着条纹西装、佩戴绿色饰物的伪爱尔兰人一起狂欢。他只想在愤懑中默默地啜饮啤酒。这位来自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此刻陷入了人生低谷。
,但他没有心情欣赏店里的黄铜制品、三叶草和彩色玻璃装饰,没有心情庆祝节目,更没有心情和穿着条纹西装、佩戴绿色饰物的伪爱尔兰人一起狂欢。他只想在愤懑中默默地啜饮啤酒。这位来自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此刻陷入了人生低谷。
而这天早上时,一切还显得那么美好。
这正是令人感觉讽刺的地方。那天早上动身前往伯克利时,阿瑟实际上一直期待着这趟行程,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称得上是“衣锦还乡”:这个从伯克利走出去的小伙子出人头地了。阿瑟真的很喜欢20世纪70年代初在伯克利的日子。伯克利坐落在奥克兰北部的山丘上,与旧金山隔湾相望,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地方,容纳了不同族裔的人、街头流浪者,还有各种异想天开的想法。阿瑟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在这里邂逅了高个子金发的统计学博士生苏珊·彼得森,并和她走进婚姻。也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阿瑟度过了自己的博士后第一年。从此以后,无论在哪里生活和工作,伯克利都是他心之所向的家园。
现在,阿瑟就要“回家”了。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系主任以及阿瑟曾经的一位教授共进午餐。但这是阿瑟在相隔多年后再次回经济系,当然也是他首次以学术同行的身份回归。此时的他,已经有在世界各地12年的工作经验,并且作为研究第三世界人类生育问题的学者享有很高声誉。这次,他是作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的身份回来的——这样的荣誉很少会授予50岁以下的人,而41岁的阿瑟带着这样的学术成就回来了。说不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们甚至开始讨论要不要对他发出一份工作邀请,谁知道呢!
是的,那天早上他真的很自信。为什么他几年前没有跟随主流,而是试图发明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方法呢?为什么他没有选择稳扎稳打,而是试图与某种尚未定型的、在一定程度上仍停留于想象层面的科学革命保持同步?
因为他无法将它从脑海中抹去,这就是原因。因为他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它。大多数时候,科学家们自己几乎都没有意识到。但是,经过300年的研究,在科学家们把一切都分解成了分子、原子、原子核和夸克之后,他们似乎终于要彻底颠覆这个过程。他们不再追寻最简单的组成部分,而是开始研究这些部分是如何组合成复杂的整体的。
阿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出现在生物学领域。在这个领域,人们花了20年的时间揭开了DNA、蛋白质和细胞中其他所有成分的分子机制。现在人们开始致力于解决一个核心谜题:数千万亿个这样的分子如何自组织成一个能够移动、反应、繁殖并存活的生命实体?
阿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发生在脑科学领域。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人工智能研究者正在努力解读心智的本质:我们头颅中数百亿个紧密联结的神经元是如何形成感知、思想、目标和意识的?
阿瑟甚至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发生在物理学领域。物理学家仍然在努力理解混沌的数学理论、分形的复杂之美,以及固体和液体的奇异内部运作。这里有一个深奥的谜团:为什么遵循简单规则的简单粒子有时会展现出最惊人、最难以预测的行为?为什么简单粒子会自发地组织成像恒星、星系、雪花和飓风般的复杂结构——就好像它们遵从于一种隐藏的对组织和秩序的渴望?
征兆无处不在。阿瑟无法准确用语言描述这种感觉。据他所知,还没有人能清楚地将它表达出来。但不知怎的,他能感觉到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不知怎的,旧的科学分类体系开始瓦解,一门新的、统一的科学即将诞生。阿瑟确信,这将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就像物理学一样“硬核”,并且深深根植于自然法则。但它将不再是对终极粒子的探索,而是关于流动、变化以及模式的形成和消解。它不再忽略所有不统一和不可预测的事物,而给个体性和历史偶然性留下一席之地。它不再是关于简单,而是指向复杂。
这正是阿瑟的“新经济学”发挥作用的地方。传统的经济学,就是他在学校里学到的那种,与复杂性视角相去甚远。理论经济学家无休止地谈论市场的稳定性以及供需平衡。他们把这个概念转换成数学方程式,并证明了相关的定理。他们如同接受宗教福音一般,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奉为金科玉律。但是当谈到经济中的不稳定性和变化时,他们似乎对这个想法感到不安,宁愿避之不谈。
但阿瑟已经接受了经济的不稳定性。他告诉同事们:看看外面,不管你喜不喜欢,市场并不稳定,世界也不稳定,而是充满了演化、剧变和惊喜,经济学必须考虑到这种动荡。现在,阿瑟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做到这一点的方法,要基于一个被称为“报酬递增”的原则——或者用钦定版《圣经》中的经文来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为什么高科技公司争相设立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地区,而不是设在安阿伯或伯克利?因为硅谷地区已经有很多老牌的高科技公司。已经有的,还会得到更多。在曾经的录像机市场上,为什么尽管Beta制式录像机在技术上略胜一筹,而VHS制式录像机却独占市场?因为一开始有较多的人偶然买了VHS制式录像机,这导致了后续较多的VHS制式影片出现在录像店,进而促使更多人购买VHS制式录像机,如此往复。已经有的,还会得到更多。
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阿瑟说服自己,报酬递增为经济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在未来,他和同事将与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携手,理解这个世界的混乱、剧变和自发的自组织。他说服自己,报酬递增可以为一种全新的、截然不同的经济科学奠定基础。
不幸的是,他没能说服其他人。除了他在斯坦福大学的直系学术圈子,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他的想法很奇怪。期刊编辑告诉他,这个所谓的报酬递增原则“就不是经济学”。在研讨会上,相当一部分听众的反应是愤怒:他怎么敢暗示经济是不均衡的!阿瑟为这种激烈反应感到困惑。但显然,他需要盟友,需要一些能够敞开心扉倾听他想法的人。这也是他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原因,至少是和“衣锦还乡”一样重要的原因。
这也就是为什么三人会相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师俱乐部,一起坐下来吃三明治。阿瑟以前的教授之一汤姆·罗森伯格,问出了那个自然而言的问题:“布莱恩,你最近在研究什么?”阿瑟给了他4个字的回答作为开始:“报酬递增。”经济学系主任阿尔·菲什洛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但是——我们知道报酬递增是不存在的。”
“更何况,”罗森伯格笑着插嘴,“如果它真的存在,我们就得立法禁止!”
然后他们都笑了,但并没有恶意。这只是一个圈内人的玩笑。阿瑟知道这是个玩笑,微不足道。然而,那笑声却不知为何戳破了他的全部期待。他坐在那里,无言以对。他最尊敬的两位经济学家就在面前,他们只是——听不进去他的话。突然间,阿瑟感觉自己很天真,甚至愚蠢,就像一个因为无知而不明白“报酬递增”并非真实存在的人。不知为何,这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剩下的午餐时间里,阿瑟都表现得兴致缺缺。这次重聚结束后,每个人都礼貌地告了别,阿瑟开上他那辆已经褪色的旧沃尔沃,开过海湾大桥返回旧金山。他在第一个出口就下了高速,驶入海滨大道,在目之所及的第一个酒馆门前停了下来。他走进去,坐在一堆三叶草之间,认真考虑自己是否要彻底放弃经济学。
在喝完第二杯啤酒的时候,阿瑟意识到这个地方开始变得非常嘈杂。年轻人蜂拥而至,庆祝爱尔兰传统的圣帕特里克节。也许是时候回家了。在这喝闷酒显然没有任何帮助。他起身走向车旁,蒙蒙细雨还在下着。
阿瑟的家位于帕洛阿尔托,距离市区以南35英里
 ,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郊区公寓里。当他终于把车开进自家车道的时候,已经是日落时分了。他的动静有点大。妻子苏珊打开前门,看着这个消瘦的、早早就已头发花白的男人穿过草坪。毫无疑问,他看起来一脸倦容、蓬头垢面,正如他此刻的心情。
,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郊区公寓里。当他终于把车开进自家车道的时候,已经是日落时分了。他的动静有点大。妻子苏珊打开前门,看着这个消瘦的、早早就已头发花白的男人穿过草坪。毫无疑问,他看起来一脸倦容、蓬头垢面,正如他此刻的心情。
苏珊站在门口问道:“在伯克利的情况怎么样?他们喜欢你的想法吗?”
阿瑟说:“糟透了,那里没有人相信报酬递增。”
苏珊之前也不是没见过丈夫从学术战场上归来。“嗯,”她试图宽慰他,“我想,如果每个人一开始都相信它,那就算不上一场革命了,不是吗?”
阿瑟看着她,一天之中第二次无言以对。然后,他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