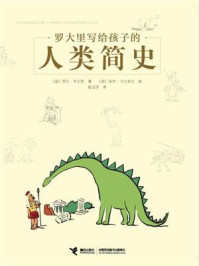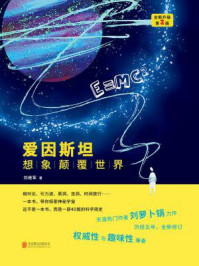2003年的春天,我刚刚成为一名博士研究生,接下来发生的两件平凡的小事,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一件事,就是我无意间找到了《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这本书。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本书被人们誉为“复杂科学的《圣经》”。最让我兴奋的是,在这本书中,我读到了一系列精彩的跨学科研究典范,比如遗传算法、人工生命、囚徒困境博弈、演化经济学等。更让我爱不释手的,是这本书娓娓道来的传记文学的叙事方式,它居然把晦涩抽象的学术概念与发现者们背后的故事完美地融为了一体。于是,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向我打开: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成了我心中向往的地方——这里面聚集了一群和我有着同样稀奇古怪想法的人,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得主盖尔曼、安德森、阿罗等,也包括我心目中的跨学科英雄,如霍兰、考夫曼、兰顿等。更关键的,是这本书让我坚定了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复杂系统研究。尽管它还很新,还不被大部分学者认可,但我坚定地认为自己应该为其奋斗终生。
第二件事,就是在这本书的启发下,我创建了最早版本的“集智俱乐部”——一个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名不见经传的小网站。起初,这个网站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展示在《复杂》一书中提及的大量好玩的计算机模拟程序,包括著名的《生命游戏》模型、人工鸟群Boid模型、自复制的元胞自动机、混沌边缘的计算等。作为一个爱好动手敲代码的理工男,我不想把对这些神奇的计算机程序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文字描述的层面。于是,我先是在互联网的海量数据中搜索;实在找不到的就自己动手去写;最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把搜集、编写的代码共享到了公开的网站上——这便是最早的“集智俱乐部”网站。我印象最深的一幕,就是在半夜三更终于调通了代码,看到了一群蚂蚁在我的计算机屏幕上“活”了起来,然后我忍不住大叫一声,搞得隔壁宿舍的同学敲管道以示警告。如果说《复杂》一书帮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能一睹令人兴奋的复杂科学新世界,那么“集智俱乐部”网站则帮我建立起和真实世界沟通的桥梁。有不少和我一样的复杂科学爱好者开始通过集智俱乐部了解到这门新兴学科,也同时了解到了我。当时我绝不会想到,集智俱乐部居然可以支撑到今天。
整整20年后的2023年,正值集智俱乐部成立20周年。颇为巧合的是,刚拿到《复杂》中文版权的中信出版社刘丹妮老师(曾策划了另一本复杂科学畅销书《规模》),就来问集智是否有合适的译者推荐。我的创业合伙人张倩,集智俱乐部公众号主编刘培源和副主编梁金,以及算法工程师胡乔主动组队认领了翻译任务。他们都是复杂科学实践者,在集智社区浸润已久,长期探索和传播复杂科学。最终几人合作完成翻译,由刘培源完成统稿。
在集智俱乐部20周年年会上,新老朋友数次聚会探讨当前复杂科学发展的热点问题,包括大模型的涌现能力、AI(人工智能)在复杂系统跨学科中的应用等话题,回顾了生命的起源、智能的本质等诸多在集智被反复讨论的“经典问题”。得知我们以集智俱乐部的名义,趁此时机组织重新翻译《复杂》时,有朋友提出不同观点:“《复杂》一书最早出版于1992年,最初引进中国也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重新翻译这样的老古董,是否还有意义?或者说,意义是否还有那么重大?”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当然是有意义的,集智俱乐部的成立从一开始就是与复杂科学牢牢地绑定在一起的,我们怎么能动摇呢?但又转念一想,朋友说得也很有道理。如今,混沌、分形、耗散结构、涌现、无标度、小世界这些曾让我们无比兴奋的概念已经渐渐变成了过去时,而人工智能大模型无疑也展现出取代系统动力学、多主体模拟、复杂网络分析等传统分析方法,成为新的跨学科研究主流工具的趋势。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复杂科学为什么还如此重要呢?
一番思索之后,我总结出了三个关键点。
首先,“复杂系统”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本身,仍然是我们当前需要深入探索的主题。2021年,著名的《科学》杂志联合上海交通大学更新了全世界最前沿的125个科学问题。其中包括生命起源、意识起源、气候系统基本原理、集体运动和群体智能的原理、宏观微观世界的模拟、经络系统的依据等一系列世界难题,而这些问题绝大部分与复杂系统有关。因此,尽管很多经典概念、方法已经逐渐淡出科研人员的视线,但是复杂系统之中的重大问题,仍然亟须深入探索。
尽管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可以自动从大数据中学习复杂系统的模型,从而预测未来的发展,但是自动化的算法仍然无法替代人类对第一性原理的追求。没有对复杂系统背后原理的深刻洞察,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其运行规律的。因此,我斗胆呼吁,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重视“复杂系统”这一历久弥新的研究对象,重新抽象它们的共同底层原理,而不是重新回到各个学科相互分立的、狭隘局部的还原论视角,排斥这门不那么时髦的学问。另外,对于大数据、AI等新的方法论和工具,我们更应该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兼容并蓄,博采众家之长,乃至为我所用,而不是一味地抱着老的方法和工具故步自封。
其次,《复杂》一书所描绘的学科大融合这一激动人心的提议,在今天看来更具有重大意义。无疑,今天的我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我们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顺势成立了“交叉科学部”。然而,究竟什么是“跨学科”?什么样的研究才是“交叉学科”研究的典范?如果你认真阅读《复杂》这本书,就会发现,彼时圣塔菲研究所的学者们所讨论的跨越学科,与我们今天普遍理解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有一点本质上的不同,那就是他们更多强调的是学科知识之间的大“整合”(integration),这种整合的背后必然蕴含着某种全新的统一性——这是超越具体系统和具体学科的普遍知识和规律的学问。尽管20年过去了,我们很难说圣塔菲研究所乃至全世界的复杂科学研究者们已经完成了这种整合,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这样的整合与简单地把两个学科乃至多个学科的知识和研究工具放在一起是完全不同的。
也许妄谈人类知识大整合多少有一些“蚍蜉撼树”的嫌疑,但今天的大语言模型不正是将整个互联网上的人类知识重新整合到了一起吗?虽然把一切都整合成“向量”这样的做法略显简单粗暴,但是从大语言模型所展现出的在通用人工智能方面的潜力来看,它的确展现出了人类知识大整合的曙光。而且,就目前来看,具备更高领悟能力的人类在学科整合方面无疑更具优势。为什么我们人类不领先AI一步,充分借鉴大模型的数据整合优势,尝试主动整合人类知识呢?
最后,就是重新翻译《复杂》一书,有利于我们在东西方文明相互交叉融合的背景下,重新定位复杂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如今,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正处于一个百年未遇的历史大变局。在这样的大变局下,我们每个人都正在见证东方文明的再次崛起。而就在《复杂》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对复杂系统的深入探索,必然会将我们引向古老的东方智慧。的确,如果你深入品味,就会发现,西方“复杂科学家”们的一系列发现,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种东方的味道。例如,“混沌与秩序的边缘”像极了我们的阴阳和谐发展;囚徒困境博弈所揭示出来的最佳策略——以牙还牙,仿佛也是深刻洞察了“仁者无敌”的道理;进化算法中“永远新奇”的追求仿佛是从另一个视角向我们揭示“大道无形”的道理。甚至我认为,如果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分别比喻成太极图中的“阳鱼”和“阴鱼”,那么“复杂科学”就是那个位于“阳鱼”中间的黑圆圈,即所谓的“阳中之阴”,它是阴阳相互转化、彼此交融的“枢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复杂科学无疑具备了更大的历史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摒弃西方科学,一味地参玄论道;同样,我们也不能摒弃东方思维,一味地强调分析与实证。由此可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复杂科学所要担负的责任是更大尺度的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与统一。
20年,对于日新月异的现代人类社会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跨度了。就像20年前的顶尖学者们很难想象人工智能会在今天突飞猛进一样,今天的学者也很难想象20年后的明天,人类各个学科知识的大整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复杂科学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