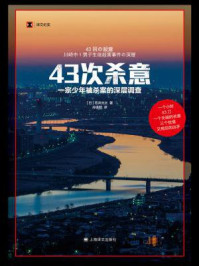她是我来到这个陌生环境认识的第一个人。
三十分钟之后,她换了个样子,站在桌前,双腿笔直,脚跟并拢,脚尖分开成精确的四十五度,膝盖合严,和我们初见时全然不同。
半小时前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跟我聊天:她做了环大学产业带,汇聚我区人才;她儿子在伦敦念建筑,前途明媚欢快;她熟练地圈点出自己工作与家庭的过人之处,拧成几个成功经验传授给我——如何与民营企业交流合作、如何帮孩子养成良好习惯、怎么陪伴青春期、申请国外学校有哪些窍门……
她的淡妆、齐肩发、西服、胸针、过膝合体裙、尖头高跟鞋都足够正式,但她的身体是松弛的,靠在椅背上,肩膀稍稍倾斜,手随意垂着,笑的时候咯咯咯,连带着腰部晃一下。
随后,按照领导秘书说定的时间,九点整,一分不差,她带我下楼,敲开另一扇门。这个办公室更大,此刻她突然变得拘谨,调整脚尖位置,绷紧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她说:“书记,这是新来的挂职干部。”
“书记”是这个院子里最大的领导。她迅速凝聚体态来面对他,我低头看看我自己,两只脚随意分开着,暂时还不太习惯那么凝聚。作为陕西省第七批博士服务团的一员,我就这样走进了西安市碑林区委区政府的大院。
2020年春天,陕西省委组织部向各高校下发文件:
陕组通字[2020]41号……为进一步鼓励引导博士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现就开展我省第七批博士服务团人选推荐工作通知如下……
我在陕西科技大学教文学和美学课程已近十年,每年收到类似的消息,逐行认真阅读却还是第一次。
我的工作是分析小说、诗歌和绘画,把内心的激荡传递给学生,在词句和理论中度过大部分时光。很难找到比这更加愉悦的职业,但我有时会想:除了教书,我能不能走出校园,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我对于官场的想象来自小说和电视剧的构建,真实的各级政府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我要如何和老百姓们交流?这些事情我都有兴趣去体验。
往年,政府坐班制与我幼小的孩子形成矛盾,只能作罢。今年则不同,孩子大了,我可以尝试更繁忙的工作。文件附表中有个单位离我家只有两公里,而且与我专业相近。如此合适,便不必再等待,立即提交申请——拟挂职岗位: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
经过筛选,省委组织部在初秋公布名单,全省五十余名博士去往政府和国企各个岗位挂职锻炼:农业、交通、医学、航天、能源、投资、环境、金融……以及我所在的“文化和旅游体育”部门。
这个部门是什么样的,我还不清楚。我见过书记之后,组织部长找我单独谈话,他说这个局有两位副局长病休,特别缺人手,因此急需挂职干部帮助。他还说,领导班子要团结,尽量不要议论病休的同志。“组织对你充满信心,欢迎你来到我们这儿,放开手去干!”
我来到的这个大院处在市中心西南侧,离西安市标志建筑“钟楼”不过数百米。政府门口的小街叫“南院门”,西安城里类似的地名还有“北院门”“书院门”“贡院门”等。我查资料才知道,“南院门”指的是“南面的衙门”,也就是说这个院子自古就是官府。我没想到,自己偶然选岗,却进入了一座有着响当当历史的衙门。清代初期的川陕总督行署和民国时期的陕西省议会、国民党省党部等都曾占驻此地。建国后,陕西省人民政府、中共西安市委也曾在此处办公。
这个院子的风貌配得上它的历史,藤萝与松柏轻绕,银杏扑闪着绿叶。房屋大多古朴,灰色雕花配上大屋顶,像是苏联建筑与中国古典建筑的合体,听说是1950年代设计的。2011年,西安市委搬迁至北郊的凤城八路,把这块宝地给了碑林区委区政府,碑林区又把文旅局安排在了院子的入口处。
初到局里的第一天,我握了几十双手。走廊里的棕红木门依次打开,工作人员从办公桌旁起身,介绍自己的姓名,伸出手来。年轻人笑容浓一些松一些,年长的人笑容淡一些紧一些。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例外,他的笑容非常谦恭、礼貌。我后来知道,他是办公室主任,姓栗。
每个人提到办公室主任都会跟我说两句话。第一句:“他可是陪过五任局长的人。”这句话是褒义,意味着他经验丰富,干这个岗位至少十几年。他一定办事妥帖,审时度势,能取得每一位新任领导的信任,不被换岗。第二句:“可惜他学历是中专,身份是工人,要不然,早提拔了。”这句话里全是惋惜。五任局长陪下来,他已经成了整个政府大院所有办公室主任的标杆,却没有上升空间。接下来的一年,我充分认识到了这两句话的含义。
我坐在自己桌前,身后是窗子,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右边的文件柜遮挡着一张堆满杂物的单人床,浅黄色格子花纹棉布盖住杂物,鼓鼓囊囊。那是病休副局长留下的东西,我不能动。我正在想象“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的第一份工作任务应该会是什么,栗主任带着充足的笑容进来,手上拎着一张军绿色帆布行军床,抱歉地告诉我午休只能这样凑合。他向我示范打开和折叠床的方法,然后依次交给我饭卡、钥匙、鼠标垫、WiFi密码。
第二次进来时,他手上拿了几个文件夹,说:“素秋局长,这是您今天要批示的。”
批示?这个词听起来架势很大的样子。这简直是始料未及的工作,我完全不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小芝麻官还需要批示文件。这些带着红头的白纸黑字,叠放整齐,落在我桌上,等待我的笔迹。
“批文件”,这是一个“副局长”到岗的第一件事,此后也将成为我每个早晨的第一件事。每份文件的抬头部分都有栗主任写的几句话,字漂亮,开头一般是“建议某某科室按照某某方式办理”,结尾分为三种:
请素秋局长阅。
请素秋局长阅处。
请素秋局长阅示。
“阅”,这个词,我见过,我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会用。但是,“阅处”“阅示”,完全陌生。我三十多年的词汇库里没有这两个词。我认识这几个文字的表象,却完全不知道背后的含义。我要根据这几个陌生的词汇,对这些文件做些什么事?
栗主任教我:“在您的名字上画圈圈,是最轻的,表明这事儿您知道了。签一个字儿‘阅’,加重语气,表明您阅读过了。‘阅处’,那是上级领导批给您的,您要拿出具体的方案做答复。‘阅示’,那是下级请您指示的,您来告诉科室具体该怎么做。”
在我完全不懂工作的时候,我不可能做出正确的“批示”,前三天的“阅处”“阅示”,我都得请教栗主任,我该写些什么内容。我首先得认识科长的脸,再和他们交谈,然后再“批示”。
我几次推门去文化科都走错了。所有办公室都相似:暗红桌椅,黑色沙发,还有墙壁,墙壁都是空白的。我从前的单位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设计艺术学院,我们活泼。每层走廊设置主题色,三层是鹅黄,四层是嫩绿。五层是淡紫吗?我记不清了。学院办公室墙上骄傲地展示学生们的漫画涂鸦,桌上有泥塑和石膏人像。
现在我独自拥有一间办公室,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装修。我买来电影海报贴在墙上——《花样年华》和《步履不停》,色调尽量柔和一些。透过柜子的玻璃门看得见里面的杂物,我想用纸挡起来。白纸太严肃,我把带植物花草的皱纹纸像糊灯笼那样糊上去,其实也算不上好看,甚至有些不和谐,但是我就是害怕那种整齐划一的肃穆影响我坐在这里的心情。房子里添一点颜色进来,这里的气氛就软一点,否则是硬的、冷的。
局长走进我房间,看见海报和花纸,愣了一下,没说什么。那我就能搬更多东西进来。我有一只灰粉的袖珍花瓶,还不如一颗柠檬大,它噘起豌豆大的小嘴,只能插一柄花叶进去。我还有一个粗朴的茶碗,摆上桌子,是个装饰。
现在我的办公室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在里面了。这黑白里的一点彩色,不知道会不会太出格。
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有九个科室,我管四个:文化科、文化馆、旅游科、图书馆(规划中)。
文化科、文化馆,这两个部门只有一字之差,二者工作有什么分别?按照文件定义,文化科负责社区文化建设、文化产业、文物,还要作为“文化馆图书馆的上级主管部门”协调工作。这抽象的描述连轮廓都勾不出来,我不知道我可以具体地做些什么。
文化馆馆长冯云额头没有一丝碎发,全部听话地汇拢至脑后,形成圆团发髻。发髻之大,令我羡慕。她的眼线、眉毛和睫毛都隆重,浑身上下有闪烁:耳饰是镂空蝴蝶,鬓角栖一朵刺绣团花,手腕嵌丝银镯翘起树枝幼果。四个科室负责人里,只有她把上月工作和下月计划逐条列出,一目了然;也只有她带来的资料是彩色的,风筝、古琴、剪纸、布糊画、彩绘陶俑的照片表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方面的活动归文化馆“管”。她的衣着里,有对这份工作的亲近。
旅游科主管景区。我们辖区最有名的景点是碑林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小雁塔),那我是否可以请教有关书法的事儿?或者可以经常看展?我喜欢看展。旅游科科长尴尬地笑了笑:“不是您想象的那样,您以后就知道了。”
图书馆馆长已经任命,但是工地还没动工。她暂时负责为“全域旅游”整理文件资料,需要我提修改意见。“全域旅游”这个词我没听懂,可是文件我看到了,有几十箱,从地面摞到我胸口。
总之,除了“非遗”工作十分明确之外,其余工作我都迷茫,打算用两周时间搞清。但是科长们说,两周太短了。
我研究他们带来的文件,想象未来可以做什么,写了几页笔记,去给局长汇报:“非遗”不能只是名号,要动起来。老字号餐饮要创新,可以组织餐饮行业优质培训课,请北上广专业团队来讲经验。官方微博语言要活泼,才会有流量,建议请历史方面的大V做讲座,比如于赓哲、马伯庸。辖区内的相声团体“青曲社”苗阜、王声在业内很有名气,不妨多联合他们做活动。碑林博物馆周边区域既然在拆迁扩建,那就趁势将街区商业模式做大致规划。原有的文房四宝店铺已经相当成熟,若能在书、画之外加上琴、棋,古代文人书案的美学元素就齐了。再铺设茶、花、香、食的店铺,生活美学与此交织,这个商区也许更有特点。碑林博物馆可以开发少儿旅游特色线路,不仅靠研学公司完成,内部要提炼适合少儿的知识载体和活动设计。用动画片复现碑刻过程,再加入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体验。对残障人群,除价格优惠外,我建议再提供一些特别服务,比如给听障人士专门派手语讲解员,每月一次义务讲解博物馆……
局长微笑着听我说完,称赞了我的工作热情,然后告诉我,我所设想的这些,统统不归我们管,我们局没有这样的权限。至于我们局到底管什么,再过几天我就明白了。
下午,我和文化科科长一起出门办事,去给文化馆的“社区服务点”揭牌。走出南院门向左拐,不远处有一座石雕牌坊,上书“德福巷”。这条巷子在西安有些特色,汇集茶楼、酒吧与咖啡馆,晚上比较热闹,白天倒没什么人。进入德福巷再拐个弯,路西的一栋小楼就是社区中心,腿有疾患的社区书记忙活着,跑上跑下,一块红绸缎覆在路边的牌子上。
社区干部不认识我,抬了抬眼皮,把头偏到一边去。文化科科长说:“这是我们新来的杨局。”干部连忙和我握手。仪式开始,工作人员五六名,摄影师一名,群众,无。有人给我准备了讲话稿,可是没有听众。我不太清楚我讲话的意义——在街边对着五六个人念稿子,然后等待他们鼓掌?不,我没有必要这样。我说:“我不讲了,直接揭牌吧。”摄影师稍微愣了一下,他请我不要那么着急,让我先把手放在红绸缎附近,方便他对焦:“您揭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慢,这样我可以多照几张,挑选。”我听从他的建议,红绸子缓缓地落了下来。
这里有免费少儿手工课,志愿者常来服务,可惜的是社区每天下午六点准时下班,没多少孩子过来。社区图书室有几个书架,以野史为主,也不乏农业栽培、健康养生。这些书脊的字大得突兀,像是挣破眼眶的眼珠,上面标明的出版社我全都没听说过。我特意看了看儿童书,单独看名字没问题,《唐诗三百首》《安徒生童话》……打开一翻,装帧彩绘简陋,译文删减乱改,一塌糊涂。
我暂时不敢表态,因为我不清楚这个事儿归不归我“管”。事实上,我还没闹清楚我的工作岗位和社区的关系。我出生以来的三十多年一直在校园,生活里没有“社区”这一级组织的概念。街道是什么?社区是什么?哪一级别更高?文旅局能管社区吗?我关于党政基层组织的常识实在太贫乏。
这时我接到栗主任短信,请我回去,在机关楼前喷泉附近乘车,与各局领导前去碑林博物馆改扩建拆迁工地检查工作。我有些困惑,拆迁不应该归我管,那是住建局或者环保局和发改委的事儿,怎么需要我去?
返回大院,上车之后我紧贴着车门坐,车上没人和我打招呼。我四肢缩紧,看着窗外。每到一站,究竟应该给领导把车门拉开,在车下等待领导下车?还是应该端坐着,让领导先下?我不确定哪个是正确答案,只有原地装傻。几站之后,秘书坐到我旁边的位子,他帮领导拉开车门,自己先下,然后在车下面做出“请”的手势。哦,这是标准答案。
工地的景象让我吃惊,离市中心数百米的地方竟然有这样的房子,入眼是拆迁的棚户、蛛网、洼地、破椽烂瓦,小巷里铺碎砖,踩一下,咕叽冒出黑水,我后悔穿了好看的皮鞋。窗玻璃碎了,艳红被褥卷起来挤在木板床上,露出灰棉絮。草丛间晾晒布鞋,证明有人在这儿住。一处民国老房早已空置,灰尘漫过脚面,院内艾蒿齐腰。石砖上的雕花下了些功夫,我凑到跟前去看纹样,突然有人跟我说:“这一户的情况,你们局的材料写好了没?”我完全不知道这一户和我们局有什么关联,像是小时候忘带作业被老师抽查。我看着他,他的花白胡茬没那么齐整,连带的表情也不那么正式,好像只是在和我聊天,并不需要我特别地回答,我这才放松了些。
这里的领导们大多穿衬衫或者翻领拉链夹克衫,只有他穿着暗红条纹T恤和牛仔裤。他没刮胡子,双手指甲长,衣领乱皱。这样的形象出现在队伍里,显得不合群也不积极,他的年龄又偏大,也许仕途不如意吧。开会讨论时他不讲大词,比较平实:“本周情况好转,动迁队能进群众的门了,能有人倒杯水了。”
今天,全车人只有他主动和我聊天,问我从哪里来,有没有什么不适应。我心里有点感谢他,以后开会再遇到,我也要主动和他说话。他似乎是不在意等级的人。在官场不在意等级,就像在家长群坚持不给孩子报补习班,在高校不重视职称名号,都比较难。也许一开始有锐气,久而久之,或被洗脑,或被排挤,或被利益诱惑,免不了从众。若走一条人少的路,在官场为群众尽力发声,在家长群里关心孩子的求知欲和快乐,在高校里专注知识和学生,那得内心笃定,才扛得住颠簸。
我揭红绸缎的照片很快出现在一篇图文报道里。合影中我职务最高,所以站在中间。正文也以我开头:
杨素秋副局长为××揭牌,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
图文之间对我的重视,在我心里撩起一丁点快乐。我的表情够不够好看?拍摄的角度合不合适?我把文字来回读了几遍,感觉自己真的“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做了贡献。
读第五遍或者第八遍时,我意识到不对劲,我在咀嚼自己的位置,嘴里是甜的。我贪恋这份甜,再咀嚼下去,以后会对自己职位、走位、排位、地位高度在意,发展成对权力的欲望,不断膨大,吞掉我。这种咀嚼已经损伤我的味蕾,我是个文学教师,我竟然丧失了分辨语言文字好坏的能力,以为“为我区公共文化建设……”这样复制的话语里包含了我的什么实质性功绩。那天,我不过撩起来一块红绸缎而已。
下午去文化馆,那里正在进行“非遗”艺人培训。我从后门进去,想旁听一会儿,馆长冯云见我来了,连忙把我拉到前台介绍。我推让了几下没推掉,只听见她说:“这是我们局新来的领导,大家欢迎。”
掌声响起来。我显然打断了他们的活动,给他们制造了麻烦,却还获得他们的掌声,这让我感到别扭。他们都比我年长,此刻我很明确,我不应该把自己树为中心。我鞠了一躬,就又站到了后面。
几天后,市里举办大型露天活动,要求各位局长参加。我们局长临时有事,我替她。第一排的“领导”只有我是临时替补的副职,坐在最右侧。主持人念名单,领导们依次向身后群众鞠躬示意。紧挨我左边那位莲湖区文旅体局局长已经起身,下一个应该是我,我掌心压着扶手准备站起来。可是主持人念到这里,停了:“下面有请第一个节目……”我刚刚要抬起来的下半身又回到了座位上。
主持人为什么单单把我漏了?因为我的级别和别人差半级,不够格。我有点失落,瞬间明白一件事——我们平常看演出做观众,都讨厌冗长的介绍领导的环节,可这个环节总也取消不了,为什么?我今天才明白了,因为领导喜欢这个环节,希望自己被介绍,因为差了半级没被介绍到的“领导”大概会失落继而憧憬自己有一天能够登上那半级从而获得被介绍的资格。被加上一个官职介绍时,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比平时悦耳。
在我踏入官场的第一个月里,我去过不同的场合,“被重视”的轻微快乐以及“被忽视”的轻微失落,都发生过。我把它们摘出来放在手心注视,它们从什么样的土壤里长出来,我要把土壤清除,我不允许以后我的心里再长出这种蘑菇。
今年,一起到政府挂职锻炼的博士服务团成员互称“挂友”。几个挂友问我同一个问题:“以你的职称,到一个区县级文旅局做副局长是不是挂低了?”他们对职务、职称、高挂、低挂了然于心,并且敏感地观察到别人的错置。我问了问栗主任,得知碑林区的级别特殊,副局长依然是副处级,这才解了旁人的疑惑。在这些事上我一向糊涂,高校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分为很多级。我自己是七级副教授吗?可能吧。反正我总也记不住。
我的稀里糊涂,不久就闹了笑话。“古道茶城”举办书画展,邀请我局出席并讲话,科员小全把他写好的讲话稿递给我,我大模大样拿着平展展的A4纸上台去念,念完之后在台上合影,稿子还在我手中。摄像师冲我频频摇手,不按快门,小全急得在台下做口型“藏!藏!”我完全领会不了他们的意思——原来,“领导”走台应该双手无物,步伐庄重。稿子要对折又对折,成一枚小物,藏在怀里,轻轻取出开讲。合影时更应藏起纸张,手中无墨,以示胸中有墨。而我,走台带稿,拍照带稿,看起来非常“没文化”。
除了这两次“没文化”以外,我短短的出镜还有两处不妥,都是小全跟我说的。第一,别的领导正讲话时,我转脸去看,不妥(我以为那样表示我在认真听,我以前就这么听学术报告)。第二,某领导面前,不能提“文化馆”三个字,他们之间有矛盾。我刚才提了两次,小全赶紧岔开话题,我没意识到。小全咬了几下嘴角,显得有些无奈。在他眼里,我的表现像个异类。他想要纠正我几句,又限于职务等级,不便多干预。
其实不仅是他,几日前,外人也觉得我是异类。那天我局召集民宿企业择优评奖,民宿老板们站在走廊里,穿绣花衣裳或棉麻长衫,步履闲适。可他们一进到政府会议室,就坐得出奇地直。
我看了他们的幻灯片,有猫有狗有咖啡,四周屋檐错落起伏,彩色衣裙在旧瓦和花草间摇曳,像透明油画轻轻动了起来。每人用五分钟介绍自己的项目,他们掏出稿子念,声音绷紧,像在朗诵,时不时打绊儿。我说放松点放松点,像平时聊天那样就行,但他们还是坚持念稿。我告诉他们,今天的会议让我有新奇感:“城墙根儿底下有这么多漂亮旅店,我都不知道,其他市民大概也很难知道。你们给我多讲一些细节,我可以帮你们写文章宣传。”散会之后,他们问我:“你是哪儿的?你讲话完全不像政府里人的语气。”
我笑了,人们对“政府语气”有刻板印象,但在真实官场中,也不是每一位官员都打官腔。我见过的人中,西安市文旅局局长就不讲陈词滥调。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市政府会议室,她先亲切地问候一句:“很久没有见到大家,又出现了一些新面孔啊。”接着,她注视着我们一二三四地讲了下去。她眉毛修剪整齐,妆容若有若无,不刻意为自己的面孔增添些什么。她全程不看手中的稿件,却将每个区县的特殊诉求记得一清二楚,直指核心,没有废话,最后轻点一下头,匆忙赶去下一个会议。她的风衣剪裁得体,双腿又长又直,背影像她的语言一样利落。
我踏进某一种职业,一开始只是凭本能讲话做事,现在我留心观察部分官员开会时的官腔。我有意抵挡,提醒自己千万不要那个样子说话。在我局的民宿评审会议里,我只希望群众觉得我性格好玩愿意做事,不想让对方注意到我的职务高低。
有时,我也得跟别人学着点。比如特色街区办的唐主任,任何时候发言都记得照顾前一个讲话者。他看了我一眼,说:“刚才杨局讲了三点,都非常中肯。下面我补充几句……”他这样熟练地承上启下,而我却总是横空而出,叽叽喳喳,没前没后。我这样可能会让其他人不舒服。
“一夕”民宿的老板不是来汇报的,他是评委之一。棕色马海毛毛衣和琥珀色纯圆框眼镜搭配在一起,像一只聪敏的山猫。他聊起他举办的音乐会、脱口秀、摇摆舞会和古着沙龙,他的语速快,眼神清亮,意识领先于同行。但他对我说话时还是稍微欠了身子,说:“就叫我小花吧。”这个男人的网名很容易记住。
小花跟我讲话的这个姿态应该不是他本色,这就像小全一样。小全是我们单位最年轻的干部,二十五岁。走廊里,他步态低平收敛,说话和声静气,谦让所有长辈。而我推开他办公室门看到的可不是这样。他为电脑桌前四十岁的“小姨”捶背,又挽着五十岁的“娘”去食堂排队——小全母亲才四十多岁,办公室里的中年女性全都被小全认作“娘”和“小姨”——但他只要见了我,立即鞠一下上身,礼貌得过分。
小全大概在心里估算过我和他的职位距离,办公室里的“娘”和“小姨”,没有职务,可以嘻嘻哈哈,对我则要敬而远之。我以前在学校里,别人不是这么对我的。学生见了我,扑过来摇我,连老师都不叫,直接叫:“素秋素秋!”
教师节快到了,几位已经工作的学生给我寄来花果茶,他们互相并不相识,却恰恰买了同一品牌的同一种味道——白桃乌龙。人过三十还能持续收获新的友谊,我得感谢高校教师这个职业。别的职场里多是冷漠争斗,高校却能遇到热烈的孩子。虽不频繁,但隔两年就有一两个能交心的朋友。我像是拿着布袋走在秋天的树林里,我不知道松果在哪里,但我知道,一定有松果在等我。
政府大院里,有没有松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