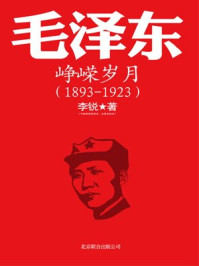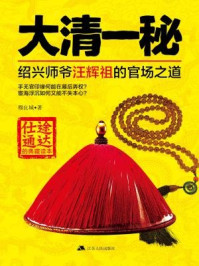约翰·弗伦奇爵士
伊普尔伯爵(Lord Ypres)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爵士。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一个单一目标,而这个目标实现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他最狂野的梦想。然而世事往往如此,野心的实现带来的是失望。在一场欧洲战争中指挥一支庞大的英国军队是他漫长而冒险的职业生涯所期盼并为之努力的工作。没有哪个白日梦有这样不现实。很少有任何事比马尔博罗
 和威灵顿
和威灵顿
 时代的重现更不可能,也很少有什么事比19世纪那支小小的英国陆军再次踏足欧洲大陆更不可能。这个大陆以普遍征兵制召集的军队数量达到了数百万之众!这是那些直到发生才让人相信的事件之一。
时代的重现更不可能,也很少有什么事比19世纪那支小小的英国陆军再次踏足欧洲大陆更不可能。这个大陆以普遍征兵制召集的军队数量达到了数百万之众!这是那些直到发生才让人相信的事件之一。
弗伦奇一开始想加入海军,但在帆船依然常见的时代,恐高这个缺陷对海军候补少尉的职业生涯是致命的。他很快转到一支轻骑兵团。随着岁月流逝,到南非战争前夕,他已经被看成英国陆军最好的骑兵指挥官。当一支远征军被派到好望角时,他在一场几乎一切都依赖骑兵的战争的开始指挥着骑兵部队。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第一次与他有了接触。也许连“有了接触”的说法都过了,因为我们在近十年时间里都不会再碰面。与那时候的许多将军一样,弗伦奇不赏识我。我是那种下级军官与读者众多的战争记者的混合,后一种人在军方思维里天然招人厌恶。一名年轻中尉风风火火地穿梭于战场间,信心满满地讨论最宏大的政策和战争问题而且有人倾听,褒贬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显然不受规则或惯例约束,从头到尾都在收获战争经历和奖章——这可不是一种值得鼓励或效仿的模式。
而这些一般偏见之外又加上了一层个人反感。我的老团长布拉巴宗(John Palmer Brabazon)将军一度自认为是弗伦奇在骑兵界的竞争对手。虽然他在南非战争开始前几年确确实实地被超过,1899年冬,在科尔斯伯格一带艰难紧张的行动中,他得到一个旅,在弗伦奇手下工作。弗伦奇严格细致。布拉巴宗年龄大得多,实际军衔更高,任性而且口无遮拦。摩擦开始了,争吵发生了,至少一部分布拉巴宗的刻薄话语被恶意传到弗伦奇耳中。布拉巴宗被剥夺了正规旅的指挥权,被派去任一个指挥义勇骑兵队的闲职。大家知道我同情我的前指挥官,是他的亲密朋友。因此,我也卷入这个更大范围的交战区。
尽管我参加了弗伦奇所部的许多行军和战斗,尽管我与他的几名参谋过从甚密,弗伦奇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对我没有任何礼节或好意的表示。对此我很遗憾,因为我听过他的种种事迹,如在科尔斯伯格战线巧妙防守,勇敢地冲过布尔人防线驰援金伯利等,我非常钦佩,而且这个笼罩着声名鹊起的光芒的勇敢人物也吸引了我。但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南非这层严霜造成的麻木直到1908年秋才消解。我当时在威尔特郡出席了弗伦奇指挥的一些重要的骑兵演习。他现在被视为我们在发生战争情况下的主要作战指挥官。我是一个〔在议会〕占有较大多数和可靠任期的政府的内阁大臣。他派一名军官向我提议见一次面。我们以大致平等的身份走到一起。一份友谊几乎从我们第一次谈话起就开始了。经历了随后十年的剧烈动荡,这份友谊依然可靠而温暖。
日益紧张的欧洲局势隐藏在和平的温暖天空与老生常谈之后,不为公众所知。但德国海军力量的稳定增长开始在不列颠帝国不断扩大的圈子里引发深深的不安。自1905年
 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以来,(声称不承担政策义务的)技术关系就存在于弗伦奇和英国总参之间。我和约翰·弗伦奇爵士都得到这些秘密事务的全面通报。于是我们在完全信任的自由氛围中讨论了未来及其巨大危险。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之后,我被派到海军部。此举的明确目标是提升我们的海军戒备到最高级别及——重要性仅稍次的——在特定情况下为了将整支陆军运到法国,建立海军部与陆军部的有效合作。约一年后,当弗伦奇成为帝国参谋部参谋长时,我们在重大问题上的合作成为一份积极而快乐的私交的核心。我们交换了各自职务所能获得的所有信息。他多次到我的海军部游艇“女巫”号(Enchantress)上做客,多次参观了舰队的演习、训练和重要的炮击演练。我们讨论了当时能想到的关于法国和德国间的一场可能战争和英国通过海上或陆地干涉的每一个方面。
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以来,(声称不承担政策义务的)技术关系就存在于弗伦奇和英国总参之间。我和约翰·弗伦奇爵士都得到这些秘密事务的全面通报。于是我们在完全信任的自由氛围中讨论了未来及其巨大危险。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之后,我被派到海军部。此举的明确目标是提升我们的海军戒备到最高级别及——重要性仅稍次的——在特定情况下为了将整支陆军运到法国,建立海军部与陆军部的有效合作。约一年后,当弗伦奇成为帝国参谋部参谋长时,我们在重大问题上的合作成为一份积极而快乐的私交的核心。我们交换了各自职务所能获得的所有信息。他多次到我的海军部游艇“女巫”号(Enchantress)上做客,多次参观了舰队的演习、训练和重要的炮击演练。我们讨论了当时能想到的关于法国和德国间的一场可能战争和英国通过海上或陆地干涉的每一个方面。
我还记得他说过在1913年的德国骑兵演习上受到的待遇。数十个中队旋风般列队行进,威风凛凛地展示。完成之后,威廉二世请他共进午餐。德国皇帝完全利用了他作为君主、元帅和主人的地位,大言不惭地说,“你看到了我的剑有多长,你还会发现它同样锋利!”弗伦奇这个议会政府的公仆只能默默接受这份发作。他是个性格暴躁的人,费了老大劲才克制住。
现在,爱尔兰问题粗暴地闯入英国政治舞台。自由党政府在激烈的政党冲突中为爱尔兰争取该党的《爱尔兰自治法案》。新教的北爱尔兰准备好用武力抵抗被排除出联合王国。在某个时刻,北爱的各种兵站和弹药库被认为有落入橙带党人
 之手的危险。有人提议用来自爱尔兰南部的强大帝国部队增强北爱卫戍部队,结果导致所谓的卡拉兵变(Curragh Mutiny)。军官们在私人感情和政治上同情橙带党人,错误地认为有人要命令他们率部对付后者。他们大批大批要求退役。士兵当然站在自己的军官一边。政府与陆军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裂。正全神贯注于欧洲事务的弗伦奇坚定地站在政府和陆军大臣西利(John Edward Bernard Seely)上校一边。随着所有各方认识到这场危机的可怕特征,事件很快平息。但卷入争议细节的陆军大臣辞了职,而帝国总参谋长在军队同僚眼中的形象大受打击,感觉必须追随陆军大臣而去。这是1914年5月末的事。
之手的危险。有人提议用来自爱尔兰南部的强大帝国部队增强北爱卫戍部队,结果导致所谓的卡拉兵变(Curragh Mutiny)。军官们在私人感情和政治上同情橙带党人,错误地认为有人要命令他们率部对付后者。他们大批大批要求退役。士兵当然站在自己的军官一边。政府与陆军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裂。正全神贯注于欧洲事务的弗伦奇坚定地站在政府和陆军大臣西利(John Edward Bernard Seely)上校一边。随着所有各方认识到这场危机的可怕特征,事件很快平息。但卷入争议细节的陆军大臣辞了职,而帝国总参谋长在军队同僚眼中的形象大受打击,感觉必须追随陆军大臣而去。这是1914年5月末的事。
弗伦奇的前途似乎完全终结。一个士兵在和平时期重新回到最高职位的事情不常发生。空缺被填补,小小的裂缝很快合上;一个新人上台;新的忠诚得以建立。另外,对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与自由党政府联系起来的将军,高级军官中有一股强烈的军事偏见的潮流。所有有影响力的团体间流传着各种消息:他无意继续指挥;他精疲力竭;他已经把握不了陆军的意见。他此时已近60岁。这是他的低谷期。
约在这一时期,在一片政治纷争中,我正在为定于1914年7月中的舰队测试动员做准备。这支舰队之前从未全面动员过,我说服了海军部的顾问相信,对皇家海军,一次实用的机械大修和程序革新比通常的海上大规模演习更有价值。我正在视察泰恩河上的大造船厂,请弗伦奇同行。7月初,我们乘船沿东海岸南下,在驶向朴次茅斯的路上视察了各种各样的海军设施。作战舰队8个中队的64艘战列舰及巡洋舰和小型舰艇已经在朴次茅斯集结。一周时间里,除了几名年轻军官外,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将军正深陷麻烦中。他确定他的军旅生涯结束了。满怀热情和精力,他被迫面对退休和无所事事的漫长空虚的岁月。如果大战终将到来,他只能作壁上观!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个人极好的脾气和率直平静地表现出来。我记得一天早上破晓前,我们从一只哨艇爬上岸,观看一架环绕飞机的初次试飞。我的年轻朋友阿奇博尔德·辛克莱(Archibald Sinclair)爵士在这架飞机上花费了巨额资金。我还记得与将军长时间在迪尔的海边旷地上散步。虽然弗伦奇神态自若,留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个心碎的人。
现在,看看运气是如何快速变换和打开大门的!这趟阴郁的航行后的14天内,约翰·弗伦奇爵士实现了他最乐观的梦想。在人类有史以来打过的最大战争开始时,他成为英国派往海外最优秀最庞大陆军的总司令!我再次看到他是在1914年8月5日那次重要的战争委员会会议上。其时英国已经对德国宣战,会议决定派整支英国远征军在他的指挥下进入法国。十天后,这次重大行动由海军部安全地及时完成。登上等在多佛尔的快艇前,他严肃但两眼闪着快活的光芒向我道别。但战争的结局却是辛酸的!
弗伦奇是天生的战士。尽管他没有黑格(Douglas Haig)的智力,也许还没有黑格骨子里的坚忍,但他有深刻的军事洞察力。在细节的准确性上,他不是黑格的对手,但想象力更丰富,也绝不会将英国陆军拖入长期持久的惨重伤亡。
这场战争的第一个震惊堪称紧张程度最高的戏剧。约翰·弗伦奇爵士很早就与指挥第五集团军和最左翼全部法军的朗勒扎克(Charles Lanrezac)将军闹翻了。朗勒扎克是一名杰出的指挥官,是战略军事科学的大师,在法国军事学院任教多年。出于多少个世纪的传统,许多法国人几乎是从生理上不喜欢英国人,他是其中之一。他瞧不起英军司令部,似乎认为他们弱小的军队获准来援助法国是他们的荣幸。不仅对盟友,对自己的参谋,他的举止也令人讨厌,这导致他的迅速毁灭。不过朗勒扎克从一开始就看出霞飞“第十七号计划”的愚蠢。他看出德军经由比利时的大规模右翼机动,看出它将成为这场战争的主旋律。他的情报地图一天天表明了这场庞大的曲线作战的发展。从8月的第一周起,他不断地向法军总司令部大声呼吁,说他的集团军应该转移到桑布尔河和默兹河,说他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增援。最终,他获准向北转移他的集团军。他们行军了一个星期。他到达沙勒罗瓦一带。在此,他将左翼让给英军,和他们一起以一比二的兵力对比守在德军穿过比利时的入侵路线上。
约翰·弗伦奇爵士也通过强行军到达该地区,除了与他合作别无选择。当时只是一名中尉的斯皮尔斯(Edward Spears)将军在他那本非凡的《联络官1914》(Liaison 1914)中为我们描绘了这个场面。英军总司令去拜访法国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弗伦奇的法语是英国人在那一语言上努力的极限。与18世纪的英国传统一致,他的法语单词发音用的是最粗暴的英国方式。他经常说到“‘Compiayny’在‘Iny’和‘Weeze’的会合处”。此际,一个战略要点在默兹河于伊(Huy)段。约翰爵士开始了这场礼节性交谈,问朗勒扎克是否认为德军企图在于伊强渡默兹河。于伊是他尝试过发音的最糟糕的名字。斯皮尔斯指出这个音只能用口哨吹出来!约翰爵士则将于伊念成“Hoy”。朗勒扎克陷在他对总体形势的深刻理解中,压抑不住对如此笨拙无知的蔑视。当约翰爵士的问题最终用听得懂的话翻译给他时,他很无礼地回答,“哦,不,德国人只有打渔才会到默兹河!”约翰爵士服现役多年,是手握五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的职业士兵,立即明白自己受到了无礼对待。在这个基础上,两位司令官肩并肩打了沙勒罗瓦和蒙斯(Mons)的大规模惨烈战役。
在林木纵横、崎岖不平的乡间,弗伦奇的炮兵几无用武之地。德国大军的重压摧毁了第五集团军战线。朗勒扎克洞若观火,下令立即连续撤退。他通过撤退挽救了局面是无可置疑的,但英国远征军也很有可能被包围或消灭。在蒙斯战役中独立坚持的英军面临两翼受敌的危险。约翰·弗伦奇爵士在他的回忆录中天真地告诉我们,说他一度想退入莫伯日(Maubeuge),等待希望中的收复战线。那里有围绕着宽阔的铁丝网和堑壕的堡垒。约翰爵士告诉我们,说他免于这一灾难是因为记起了哈姆利(Edward Bruce Hamley)的名言:“一支撤退军队的指挥官躲进一座堡垒的举动无异于沉船的人抱着锚。”当然,他从未认真考虑过如此荒谬的举措。相反,他也以最快的速度撤向巴黎。来自国内的指示让他可以独立行事,支持他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退向沿海。他感觉自己指挥着帝国仅有的训练有素的主力部队,如果这些人损失了,凭以组建新军队的核心就没了。然而,他也尽力与法军的撤退保持协调,在一片混乱中寄望杀一记回马枪来挽救巴黎。他意在为这最后一搏保持英国远征军的战斗力。
到达巴黎一带后,有感于这座都城即将到来的命运,他促请霞飞奋起一战,承诺自己也不退后。这也是霞飞的意图,但反击的时间地点尚未确定。约翰爵士收到一份直白的拒绝,同时法国司令部提到塞纳河以南很远的各个城镇是英国远征军应该撤到的地点,甚至没人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战机”。接着,当霞飞选择或巴黎军区司令加列尼迫使霞飞接受的时刻到来时,英国远征军突然被要求回头。确信法军正向巴黎后方撤退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没有立即摆脱这个念头,不想死守巴黎。我们只能说,“毫不奇怪”。到那时,朗勒扎克已经在人们所说的一致同意下被解除了指挥职务,此前他在吉斯打了一场硬仗,指挥了自己部队巧妙神速的撤退。他带着对战略的深刻理解、他的粗暴举止和怨恨回了家。
接着是法军相当马虎,但依然意义非凡的第二次艰巨努力。这就是决定性的所谓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尽管它实际从巴黎一直延伸到凡尔登,再绕到南锡——一条超过250英里(约合400千米)的战线。一旦确定了霞飞的决心,并且得到国内增援,约翰爵士转身向前突进。结果,英国远征军直接插入德军展开的右翼两支集团军之间张开的空隙。英军渡过马恩河并插入这条空隙的进军决定了这场挽救巴黎的宏大战役。经过相对小规模的战斗,德军右翼被突破,入侵军队的整条战线收缩了30英里(约合48千米),退到一个防守位置。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事之一,约翰·弗伦奇爵士有资格分享这份荣耀。
接下来是“奔向大海的赛跑”(race to the sea)
 。我们的军队经过连续补充,现在有七八个师和大量骑兵。法国政府批准我们转移到沿海侧翼。一些最优秀的法国将军(尤其是后来的法国陆军参谋长比亚 [Edmond Buat] 将军)告诉我,如果法军左翼的推进再大胆一些,德军将会被赶出其所占地区的很大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保有安特卫普变得极端重要;因为当时的战线有可能稳定在安特卫普—根特—里尔。当然,约翰·弗伦奇爵士为此极力争取。在圣奥梅尔附近下火车后,他向阿尔芒蒂耶尔和伊普尔推进。但德军准备了他们的反击。四个由年轻但经过训练的志愿者组成的预备役军在强力监督下被投入到英军的推进路线上。现在,约翰爵士在最真实的战争概念上冒了巨大危险。他将他的战线延伸到铤而走险的极端。右翼,他在阿尔芒蒂耶尔作战;左翼,他奋力向梅嫩(Menin)进发。一系列残酷悲壮的战斗随之打响。有时候,我们只剩下一线由伤亡惨重的士兵坚守的散兵坑;炮台也弹尽粮绝。但战线固若金汤,四个年轻的德国军被打败。这场苦战肯定在英国陆军史上占据了很高的位置。如果将军可以给现代战役带来任何贡献,没人的贡献会超过那位英国远征军司令。
。我们的军队经过连续补充,现在有七八个师和大量骑兵。法国政府批准我们转移到沿海侧翼。一些最优秀的法国将军(尤其是后来的法国陆军参谋长比亚 [Edmond Buat] 将军)告诉我,如果法军左翼的推进再大胆一些,德军将会被赶出其所占地区的很大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保有安特卫普变得极端重要;因为当时的战线有可能稳定在安特卫普—根特—里尔。当然,约翰·弗伦奇爵士为此极力争取。在圣奥梅尔附近下火车后,他向阿尔芒蒂耶尔和伊普尔推进。但德军准备了他们的反击。四个由年轻但经过训练的志愿者组成的预备役军在强力监督下被投入到英军的推进路线上。现在,约翰爵士在最真实的战争概念上冒了巨大危险。他将他的战线延伸到铤而走险的极端。右翼,他在阿尔芒蒂耶尔作战;左翼,他奋力向梅嫩(Menin)进发。一系列残酷悲壮的战斗随之打响。有时候,我们只剩下一线由伤亡惨重的士兵坚守的散兵坑;炮台也弹尽粮绝。但战线固若金汤,四个年轻的德国军被打败。这场苦战肯定在英国陆军史上占据了很高的位置。如果将军可以给现代战役带来任何贡献,没人的贡献会超过那位英国远征军司令。
仁慈的冬天降临苦难深重的战线,疲惫使双方大军陷入堑壕战。弗伦奇一生的最高篇章结束了。他之后的指挥浪费在突破由铁丝网、机枪和炮火组成的钢铁屏障的徒劳尝试上,既没有足够兵力,也没有必要的装备发起一场攻势。1915年3月,福煦在阿图瓦损失了10万法军士兵。4月和5月,约翰爵士在新沙佩勒和费斯蒂贝尔损失了2万英军。但他最大的失败是卢斯战役(Battle of Loos)。这是霞飞迫使约翰·弗伦奇爵士打的。它将从北侧协助50个法国师在香槟(Champagne)发起的攻击。
那一整年,我都与弗伦奇过从甚密,而且一直努力在他和基钦纳之间调解说和。我请求他不要同意1915年的这场秋季攻势。他自己的判断也是如此。我在内阁反对这次战役,直至被其他意见压倒。除非我们拥有压倒性的重炮、大量炮弹、步兵的绝对优势,当然还有适用于那一特定任务的机器——坦克,否则我们没有任何突破德国堡垒防线的手段。但没什么能打破霞飞的意志力和法军参谋部的看法。法军在9月下半月承受了可能多达25万伤亡的惨重损失,英军也招致了相应比例的损失。我以微薄之力尽力阻止它。我警告约翰·弗伦奇爵士说,新的战役对他将是致命的。它不可能成功,而他则会成为疯狂的希望挫败后的替罪羊。一语成谶。
1915年的这些灾难之后,我们进入这场战争的低谷。英国政府已经决定放弃达达尼尔海峡。我已经辞去战争委员会的职务,启程加入我在法国的义勇骑兵团。辞职的大臣总会遭到非难,那些解释不了辞职原因的人无一例外地受到谴责。那一刻,我当然不会尝试任何解释。我乘着驶离英国的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在船上打量各种各样的人群。他们属于英国陆军的每一个团,和他们走出战壕一样,他们正返回部队——满不在乎的人物、快活的人物、憔悴的人物——一群熙熙攘攘的好脾气的人。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听到弗伦奇的消息了。我前面提到,我是卢斯战役的强烈批评者。我在战争委员会极力反对法国司令部要求他执行的这项计划,我知道他为此受到伤害。我不担心。一个人的好运走到尽头时,会有一种已经坏到底的轻松感觉。然而,当船靠上布洛涅码头,我们列队走下跳板,踏上饱受苦难的法国土地时,港口接卸军官告诉我:“我们接到命令,请你去见司令。司令部的车在这里。”
几小时后,我与约翰·弗伦奇爵士在布郎克庄园一起用餐。他当时住在那里。那些没在大战中打过仗或至少在陆军服过役的人很难理解,从一名团级军官到指挥许多许多军的总司令,一级一级要向上排列多么巨大的高度。弗伦奇忽略了所有这一切。他对待我就好像我还是海军大臣,再次与他探讨战争的未来。
在那之后,他和我谈到他自己的处境。他说,“我只能随波逐流”。他描述了施加在他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是为了劝说他不吵不闹地放弃指挥权。(在英国,为了在不引起争吵的情况下完成已经决定好的事,人们通常会费上老大劲。)我在内阁的时候,还没意识到这些程序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但从他告诉我的情况,我认识到这个形势。
我最后要描绘的是他作为总司令的最后一天。他带我从前线回来,一整个白昼,我们一起驱车从一个集团军到另一个集团军,从一个军到另一个军。我们走进各级司令部,和他的将军道别。我这个非官方人物就在车里等。我们在毁坏的村舍里用一只设计精美的食品篮吃午饭。放弃高级指挥权的痛苦非常强烈。他宁愿放弃生命。然而,他坚定地相信灵魂的不朽:他觉得,如果你从胸墙上探出头,让一颗子弹穿过你的头,那也只是你再也不能与你的伙伴和同志交流。你还会在那里;知道(或许只是看到)所有的事件;形成你的想法和希望,但根本不能交流。只要你还关注世事,它将会让你担心。一段时间后,你的兴趣会转移。他确信新的光芒将会照耀;最终对所有人都更好,更明亮,更遥远。
然而,如果你故意从胸墙上探出头,你在新世界的开局会很糟糕。
那天的雨下了整整一天,这段谈话一直印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