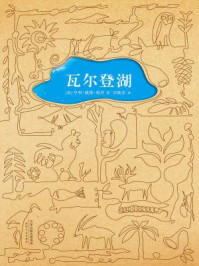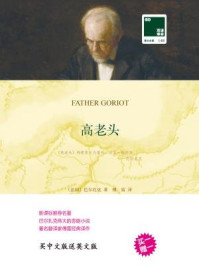在那些专门对您进行介绍的专栏文字中,令读者们感到震惊的,就是常常看到您的名字与让-保罗·萨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好像您是一位存在主义哲学的门徒一般。然而《局外人》与萨特式短篇小说相去甚远,同样您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还批评了……
(加缪打断了我的话。)我还批评了,确切地说,存在主义哲学。事实上,鲜有人准确知道存在主义到底是什么。因此,很多事情就很好解释了。就我的个人角度而言,我能够讲述的全部内容就是:
第一,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对于理性不够信任,因此无法相信什么思想体系。让我感兴趣的是搞清楚应该如何为人处世。更确切地说就是,当我们既不相信上帝又不相信理性之时,我们能够如何为人处世。
第二,存在主义具有两种形态:一种关系到克尔凯郭尔和雅斯贝尔斯,借助对理性的批判,通向神性;另一种,我称为无神论存在主义,涉及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不久之后的萨特,它同样以某种神化收尾,不过仅仅是对历史的神化,历史被视为唯一的绝对。至于我,我完全理解宗教解答的好处,而且我尤其看得出历史的重要性。但是在绝对意义上,我既不相信前者也不相信后者。我扪心自问,如果有人强迫我在圣奥古斯丁与黑格尔之间
 做出选择,会让我十分厌烦。我觉得应该存在某种二者都可以接受的真理。
做出选择,会让我十分厌烦。我觉得应该存在某种二者都可以接受的真理。
阅读您交给《战斗报》的一大批文章,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阿拉伯问题出现在您最为担忧的核心议题之列。您是法国境内少有的对这方面关系加以定位的人士之一,这在穆斯林群体中引发了大量期待。您能否为我们的读者明确指出,为了通向一种真正丰饶而富有创造性的法——阿政策
 ,到底应该走哪一条路?
,到底应该走哪一条路?
这说来话长。只谈一点,之所以法国现在依然得到尊重,这并不是因为其旧日的荣光。今天的世界根本不在乎那些旧日荣光。真正的原因在于,法国是一股阿拉伯势力,这是一个百分之九十九的法国人都忽视的真相。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法国想不出一个伟大的阿拉伯政策,对这个政策来说就再也没有未来可言了
 。对于一个贫困的民族来说,一个伟大的政策只会是一个模范政策。在这方面我只想说一件事:但愿法国能够真正地把民主政体引进阿拉伯世界,那么与之携手的将不仅有北非,还将包括其他所有传统上受其他势力摆布的阿拉伯国家。真正的民主在阿拉伯国家是一个全新概念。对我们而言,它将价值一百支军队和一千口油井。
。对于一个贫困的民族来说,一个伟大的政策只会是一个模范政策。在这方面我只想说一件事:但愿法国能够真正地把民主政体引进阿拉伯世界,那么与之携手的将不仅有北非,还将包括其他所有传统上受其他势力摆布的阿拉伯国家。真正的民主在阿拉伯国家是一个全新概念。对我们而言,它将价值一百支军队和一千口油井。
这种对于北非的深情厚意来自哪里?我们由于战争的偶然曾被引向这一地域
 ,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和您分享着同样的感情。
,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和您分享着同样的感情。
我在那里出生
 ,那是一个广袤的国度,具备未受损伤的力量。远离它那片天空,我总是感到自己有点像在流亡。既然您也熟悉那里,那么您肯定理解我的意思。
,那是一个广袤的国度,具备未受损伤的力量。远离它那片天空,我总是感到自己有点像在流亡。既然您也熟悉那里,那么您肯定理解我的意思。
《战斗报》以前经常要求政府和各个党派为那些他们认为对法国最为适宜的政策做出清晰定义。现在轮到您了,同样我也冒昧地请您为我明确讲述一下您的立场。
《战斗报》在它的时代定义过它的政治立场。不管表面如何,我们当时都很谦逊。我这代人将花上十年时间去创造那些属于他们的方式。我希望他们能够成功,我也将在自己的位置上为此努力,甚至我毫不隐瞒,我对那些传统上捍卫各类劳动者的政党更有好感。
不久之前,您放弃了您的记者工作。能问一下其中的理由吗?
我的那些理由在我看来都很恰当。
您的上一出戏《卡利古拉》的成功促使我引申到另一个话题。批评家们不断谈及某种哲学戏剧。您同意他们的说法吗?
批评家的职责是找出定义。作家们的任务是建构作品。二者不可能永远互相吻合。
您是否也同样认为,就像当下的舆论所说,您的戏剧包含着传达给人类的某种“消息”
 ?如果确实如此的话,这个消息是什么?
?如果确实如此的话,这个消息是什么?
我从未向耶稣祷告过。我的身体很好,谢谢您。
在您参与过的所有活动中,我知道其中有一件事是您不愿别人和你谈起的,那就是您在抵抗运动中的活动。不过,作为结尾,我还是坚持请您谈谈关于那一时期的某段回忆。
所以忘掉抵抗运动吧。它让那些不了解它的人急不可耐,大多数人没回得来。从今以后我们可以赋予抵抗运动的一切,就是静默与记忆。
最后再问一句,关于1944年夏季
 以来,在法国和世界上呈现出的政治与伦理方面的精神状态,您能给出哪些结论?
以来,在法国和世界上呈现出的政治与伦理方面的精神状态,您能给出哪些结论?
1944年以来的法国和世界?到了1960年,我们将有可能做出某种评判,它将有百分之一二的可能性是公正的。在此之前,但愿法国人对法国保持耐心,但愿法国对世界保持耐心,这是我能够给出的最革命性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