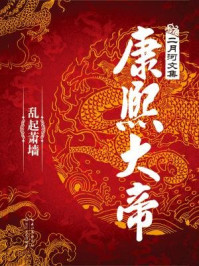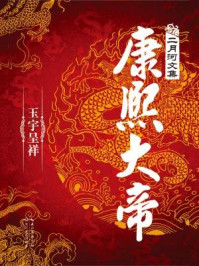嘉靖十九年(1540)以后,东亚的贸易中心从漳州转到浙江定海的双屿港,这一转变,与闽粤海寇商人北上有关。
明朝号称两京十三省,两京即为北京、南京,十三省中,浙江以人文财富排列第一。浙江的物产丰美,各种产品都是第一流的。“湖丝绝海内,归安为最,次德清,其次嘉之桐乡、崇德,杭之仁和,此外取于四川保宁,而山东、河南又次之。”
 可见,最好的湖丝产于浙江湖州及杭州数县。这些地方离宁波港不远,从海商的角度来看,宁波港非常重要,在这里可以采购到最好最便宜的湖丝。然而,由于当时的宁波港不对私商开放,海商们只有到宁波周边的港口想办法,这就导致宁波外海诸港的兴起。
可见,最好的湖丝产于浙江湖州及杭州数县。这些地方离宁波港不远,从海商的角度来看,宁波港非常重要,在这里可以采购到最好最便宜的湖丝。然而,由于当时的宁波港不对私商开放,海商们只有到宁波周边的港口想办法,这就导致宁波外海诸港的兴起。
嘉靖年间浙江双屿港成为东亚国际贸易的中心,该港的开发,与漳潮人有关。约在正德、嘉靖年间,部分漳州人到浙江宁波沿海走私贸易,
 渐有海寇混迹其中,双屿港成为他们的主要巢穴。关于双屿港,浙江巡抚朱纨在《双屿填港完工事》中说:
渐有海寇混迹其中,双屿港成为他们的主要巢穴。关于双屿港,浙江巡抚朱纨在《双屿填港完工事》中说:
访其形势,东西两山对峙,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门障蔽。中间空阔约二十余里,藏风聚气,巢穴颇宽。各水口贼人昼夜把守。我兵单弱,莫敢窥视。

海寇能在双屿扎根,与明朝的迁岛政策有关。明代前期,浙江贯彻海禁较为彻底。“海中山岙错列,林木荫翳,亡命奸徒,易于盘踞。元末方国珍乘之以据浙东。洪武间汤信国经略其地,迁徙其民,勒石厉禁,迄二百余年,莽无伏戎,岛无遗宼,则靖海之效也。”
 但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间,开始有一些福建的渔船到访浙江沿海的岛屿,在那里捕鱼,或是贸易。其中宁波府定海县海上的双屿港成为南方渔民汇聚的主要港口,而后又发展为海寇及海商活动的中心。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至浙江,“知沿海大姓,皆利番舶,勾连主藏,转鬻其货,牟利润已久”。
但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间,开始有一些福建的渔船到访浙江沿海的岛屿,在那里捕鱼,或是贸易。其中宁波府定海县海上的双屿港成为南方渔民汇聚的主要港口,而后又发展为海寇及海商活动的中心。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至浙江,“知沿海大姓,皆利番舶,勾连主藏,转鬻其货,牟利润已久”。
 双屿港的发展有个过程。后来双屿港发展成国际贸易大港,对东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极大。
双屿港的发展有个过程。后来双屿港发展成国际贸易大港,对东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极大。
明史学者探讨双屿港的海寇与海商,认为双屿港海上力量的兴起与福州的一次大劫狱有关。郑舜功在追溯浙海倭寇起源时说:“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邓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狱。”
 “迩者倭寇始自福建邓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狱,于嘉靖丙戌(五年,1526 年)越杀布政使查约,逋入海,诱引番夷往来浙海,系泊双屿等港,私通罔利。”
“迩者倭寇始自福建邓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狱,于嘉靖丙戌(五年,1526 年)越杀布政使查约,逋入海,诱引番夷往来浙海,系泊双屿等港,私通罔利。”
 可见,福建狱囚越狱入海,是浙江沿海出现闽中私商的契机,而后引发了倭寇侵扰江浙沿海的问题。
可见,福建狱囚越狱入海,是浙江沿海出现闽中私商的契机,而后引发了倭寇侵扰江浙沿海的问题。
 不过,虽说郑舜功将福建按察使狱囚犯越狱事件系于嘉靖五年(丙戌),但福建的史料记载此事发生于嘉靖九年(1530)。王应山的《闽都记》云:“嘉靖九年正月,福州狱变,贼戕大吏,囚人斩关趋连江,渡海而遁。三月,都御史胡琏以勘事至,遂留巡抚。未几召还。”
不过,虽说郑舜功将福建按察使狱囚犯越狱事件系于嘉靖五年(丙戌),但福建的史料记载此事发生于嘉靖九年(1530)。王应山的《闽都记》云:“嘉靖九年正月,福州狱变,贼戕大吏,囚人斩关趋连江,渡海而遁。三月,都御史胡琏以勘事至,遂留巡抚。未几召还。”
 《福州府志》的记载更为详细:“嘉靖九年,侯官狱囚反。时正月二十九日夜也。初,侯官县令黎文会酗酒,守狱者得囚金,纵之。有林汝美,故县吏也,以杀人论死;车小二,则郡剧盗也。二人私以兵器藏瓜中,遂率众斩关而出,杀侯官令,趋南门,将逃于海,适三司晨候御史于南察院,遂杀布政查约、参议杨瑀、都指挥使王翱、经历周焕。贼逸去,后颇追获。”
《福州府志》的记载更为详细:“嘉靖九年,侯官狱囚反。时正月二十九日夜也。初,侯官县令黎文会酗酒,守狱者得囚金,纵之。有林汝美,故县吏也,以杀人论死;车小二,则郡剧盗也。二人私以兵器藏瓜中,遂率众斩关而出,杀侯官令,趋南门,将逃于海,适三司晨候御史于南察院,遂杀布政查约、参议杨瑀、都指挥使王翱、经历周焕。贼逸去,后颇追获。”
 可见,这是一次历史上罕见的群体越狱事件,狱囚不仅集众越狱,而且杀死了省级高官多名。虽说越狱囚徒多人被捕,但其中有一些人从连江下海,后到浙江沿海进行私商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位叫着“邓獠”的商人。他在浙江双屿建立海上贸易港口。从其被称为“邓獠”来看,他应是漳州人,因而,“某獠”是漳州人骂人话中常有的,后来逐渐演变为“某佬”,有“大佬”的意思。明代海寇头目多被称为某“大佬”,这也是漳潮一带的习惯。
可见,这是一次历史上罕见的群体越狱事件,狱囚不仅集众越狱,而且杀死了省级高官多名。虽说越狱囚徒多人被捕,但其中有一些人从连江下海,后到浙江沿海进行私商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位叫着“邓獠”的商人。他在浙江双屿建立海上贸易港口。从其被称为“邓獠”来看,他应是漳州人,因而,“某獠”是漳州人骂人话中常有的,后来逐渐演变为“某佬”,有“大佬”的意思。明代海寇头目多被称为某“大佬”,这也是漳潮一带的习惯。
明代的史料表明,这位邓獠虽然越狱犯了死罪,但他到了浙江双屿港之后,不是进行海寇活动,而只是经营海上走私!这应是在双屿港走私利润实在太大了,让这位犯下死罪的人也以经商为主!此外,自明初以来,漳州时常有人因海上走私而犯罪被捕,关入福建省的按察使狱。这位邓獠应当也是同类人物,他一旦获得自由,便重操旧业,继续自己的海上贸易生涯。神奇的浙江双屿港,将海寇化为商人了!不过,据明代史料记载,双屿港的海上走私活动并非起源于嘉靖九年(1530)或是嘉靖五年(1526),在更早一些的年份里,已经有了海商活动。近来,浙东人项乔
 的一段话
的一段话
 引起注意:
引起注意:
卢镗都司亦是好汉。在浙宁波海中有双屿山,去观海卫百余里。海贼通倭夷,在海劫人停泊大船者,巢穴是山之中,耕田筑屋已二十七年,海上往来受害者无可奈何。巡视朱纨公委往擒之,不浃旬尽捣其巢穴,得贼船若干只,夷货若干金,夷首若干颗。浙人甚便之。今闽中海贼通佛郎机俱停泊于旧故(浯)屿山塞处,亦甚险固。来又令往擒之,亦生擒百余颗,尽决之。乃今以朱巡抚事坐狱,未得平反,岂天理耶!

项乔的这段话提到海贼在双屿港驻扎已经有二十七年,那么,他是在什么时候说这句话的?文中提到的朱巡抚即朱纨,朱纨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四月被免职,次年七月,朝廷下诏逮捕朱纨,朱纨闻讯,自杀于家。项乔说:“乃今以朱巡抚事坐狱,未得平反”,看来他说这句话时尚未得到朱纨的死讯,因此,他说这句话应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前推二十七年,即为嘉靖二年(1523),该年正为日本向明朝进贡之时,在宁波港发生“争贡案件”。“嘉靖二年(1523),国王源义植幼,不能制国,于是西海道遣宗设、谦导等,南海道遣人佐宋卿素等,各称贡,舟泊宁波。互相诋毁,遂至弄兵相杀,为地方大祸。”
 其时日本使者宗设在宁波一带杀人抢劫入海,震动朝野。而后,日本船只经常出没于浙江舟山一带的岛屿,并与这一带的私商有了接触,双方在此贸易。其后,日本人“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
其时日本使者宗设在宁波一带杀人抢劫入海,震动朝野。而后,日本船只经常出没于浙江舟山一带的岛屿,并与这一带的私商有了接触,双方在此贸易。其后,日本人“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
 所以,嘉靖二年(1523)被认为是浙东动乱之始。不过,闽南海商到双屿港还要更早些。
所以,嘉靖二年(1523)被认为是浙东动乱之始。不过,闽南海商到双屿港还要更早些。
浙江鄞县人戴鱀于嘉靖十一年(1532)说:
吾郡东滨巨海,自汉以来,寇盗屡发。近岁乃有一种漳船,窃市海外番货,如胡椒、苏木、名香、瑇瑁之属,潜入岛徼而侥幸射利者,私其什百之嬴,为之根柢槖穴。其始则犹虞触法网,畏缩掩覆,俟其来而为之市,而今则湍趋川溃,公行效尤,阑出外境,而导之入矣。夫居奇货以取厚殖者,数人之利也。延大盗以窥堂奥者,一郡之虞也,故君子睹微而知著,众人悦近而忽远。今以言其事则亦著矣。以言其害则亦近矣,何者?漳船之入吾海徼,才十五六年而止耳。稇载而来,固未尝垂槖而返,海上劫夺,至及渔樵。

如戴鱀在嘉靖十一年(1532)所说,此前十五六年,漳州的私人贸易船开始在浙江沿海贸易,其时应为正德十一年(1516),或是正德十二年(1517)。这说明大约在正德十二年(1517)前后,便有漳州船出没于浙东沿海!
就戴鱀所说的漳船贸易内容而言,嘉靖十一年(1532)左右来到双屿港的漳船带来了“海外番货”,如胡椒、苏木、名香、瑇瑁之类,这些商品无疑是漳州人从海外带来的,或者是他们与葡萄牙人贸易得到的商品。浙江是明朝财政力量最强的“首省”,民众是这一时代最富裕的,因此,民间消费能力较强。由于海禁,浙江民众对海外商品的需求被压抑多年,即使有少量商品入市,也满足不了民众的胃口。漳船将这些海外商品带到浙江沿海,很快激发了浙江市场的需求。郑若曾说:“商舶乃西洋原贡诸夷,载货泊广东之私澳,官税而贸易之。既而欲避抽税,省陆运,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浙人又导之,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可与贡舶相混乎。”
 “海中货市,各有行商地面。浙中开市,广省方物或皆利其径便,相涌而至。或彼此不相容,或庞杂不善处,致有门庭之扰。但世无无争之地,又开集列港,不为我民害可矣。”其后,浙江宁波海面多有闽粤海商活动。“旧时通倭商有林同泉、王万山、陈大公、曾老、陈恩泮六七起,伙有定数。行之既久,射利日增。”
“海中货市,各有行商地面。浙中开市,广省方物或皆利其径便,相涌而至。或彼此不相容,或庞杂不善处,致有门庭之扰。但世无无争之地,又开集列港,不为我民害可矣。”其后,浙江宁波海面多有闽粤海商活动。“旧时通倭商有林同泉、王万山、陈大公、曾老、陈恩泮六七起,伙有定数。行之既久,射利日增。”

这是双屿港海上贸易增长的基点。受到漳州人的影响,宁波商人也介入了海上贸易。万表说:“宁波自来海上无寇,每年止有渔船出近洋打渔、樵采,并不敢过通番者。后有一二家止在广东福建地方买卖,陆往船回,潜泊关外,贿求把关官,以小船早夜进货,或投托乡宦说关。我祖宗之法尚未坏也。二十年来始渐有之。”
 万表的《海寇议》得到郑若曾、胡宗宪《筹海图编》大量引用,该文发表时间应是朱纨平双屿港之后。据其所说,嘉靖十来年的时候,便有宁波商人到闽粤贸易,他们的特点是从陆上到广东福建,采办货物后,从海上回浙江。因浙江海禁较严,他们便托关系、走后门,用小船将货物运到宁波市场上出售。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他们是从海上回到浙江宁波,分析这种情况,他们应是搭福建商船北上的。其二,为了入关,他们总是贿赂海关管理者,或是托大户人家去说情,这就将沿海的大户人家卷入了海上贸易。从事海上贸易渐成了浙江沿海的“全民运动”,“向来海上市货暗通,而费归私室”。
万表的《海寇议》得到郑若曾、胡宗宪《筹海图编》大量引用,该文发表时间应是朱纨平双屿港之后。据其所说,嘉靖十来年的时候,便有宁波商人到闽粤贸易,他们的特点是从陆上到广东福建,采办货物后,从海上回浙江。因浙江海禁较严,他们便托关系、走后门,用小船将货物运到宁波市场上出售。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他们是从海上回到浙江宁波,分析这种情况,他们应是搭福建商船北上的。其二,为了入关,他们总是贿赂海关管理者,或是托大户人家去说情,这就将沿海的大户人家卷入了海上贸易。从事海上贸易渐成了浙江沿海的“全民运动”,“向来海上市货暗通,而费归私室”。
 其中大户的作用值得注意,他们往往与外来的漳州海商互通买卖。于是,漳州人逐渐形成每年都到浙江双屿港谋生的习惯。如戴鱀所说:“岁凡仲春,东南风始迅,番舶乃北行,入夏,风尤迅,海人水舶趠风,日可行数百里。”
其中大户的作用值得注意,他们往往与外来的漳州海商互通买卖。于是,漳州人逐渐形成每年都到浙江双屿港谋生的习惯。如戴鱀所说:“岁凡仲春,东南风始迅,番舶乃北行,入夏,风尤迅,海人水舶趠风,日可行数百里。”
 当然,戴鱀说这段话,考虑更多的是浙江海上安全问题。
当然,戴鱀说这段话,考虑更多的是浙江海上安全问题。
应当说,早期漳州人在浙江沿海的活动是十分谨慎的,唯恐触犯法网,所以,浙江人对他们并不反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前来双屿港贸易的漳州人越来越多,难免发生一些掠夺活动,因而威胁到周边平民的安全。“海寇初起时,不过五七十人。”
 “辛卯(嘉靖十年,1531 年)之秋,入我青屿,掠我子女,高樯大舶,轻肆我边圉,蔑视我官军,列城之将,防哨之兵,不敢向风而谁何,此其赍货而私市则然矣。假令包藏祸心,弄兵窃发于鲸波之上,则不知将又何如也。”
“辛卯(嘉靖十年,1531 年)之秋,入我青屿,掠我子女,高樯大舶,轻肆我边圉,蔑视我官军,列城之将,防哨之兵,不敢向风而谁何,此其赍货而私市则然矣。假令包藏祸心,弄兵窃发于鲸波之上,则不知将又何如也。”
 为什么沿海的官兵不敢过问海船水手的抢劫行为?这是因为,浙江官军向出海船只索贿,“宁绍奸人通同吏书,将起解钱粮物料领出,与双屿贼船私通交易”。
为什么沿海的官兵不敢过问海船水手的抢劫行为?这是因为,浙江官军向出海船只索贿,“宁绍奸人通同吏书,将起解钱粮物料领出,与双屿贼船私通交易”。
 项乔说当时官军的风气:
项乔说当时官军的风气:
其尤无忌惮者,渔樵之舟,动索常例而羁縻之,至于二三桅大舟下海,坐视不问,而惟索取号钱。总督十之,把总七之,挥十于尉,尉倍于旗,计一舟之费不下十余金,则可横行海上,恣为不法,官旗吞声而不敢问矣。然则何以望其弥盗而防奸也?正本澄源,必自此始,斯可以言治盗矣。

海船纳钱之后,就可在海上贸易,即使其中有人犯法,官军士兵也不敢问,因为,他们是有后台的。正如项乔所说:“窃谓浙闽海寇,其大有二,其在外也,岛夷窃发,漳人乘间,是之谓寇;其在内也,弗靖之民,实阴主之,是之谓奸。”
 此外,由于漳州人的海船较大,宁波一带的明朝水师对他们无可奈何。这让宁波一带的绅士十分不安。从戴鱀所说浙江沿海的情况来看,嘉靖九年(1530)从福州越狱的一些死囚并非全部转为商人,有一些原来就是盗匪的那些人,也从事抢劫,因而引起浙海方面的治安问题。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令人忧虑。浙江的黄绾说:“东南之事,莫大于浙闽海寇,凡浙之寇,皆闽之人也。闽之人始为回易,交通岛夷,以其货挟其人来吾海上,云为贾。或有为盗者,非尽为也。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则皆习为盗矣。盗得其利,官莫为惩,彼恣而无害,故日趋而日众,始而且闽之贾舶为之,继而南畿吴越贾舶亦或为之,继而闽之逃亡集四方无籍为之。又继而吾土之无籍亦或托为之。所以东南海寇,今为盛也。”
此外,由于漳州人的海船较大,宁波一带的明朝水师对他们无可奈何。这让宁波一带的绅士十分不安。从戴鱀所说浙江沿海的情况来看,嘉靖九年(1530)从福州越狱的一些死囚并非全部转为商人,有一些原来就是盗匪的那些人,也从事抢劫,因而引起浙海方面的治安问题。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令人忧虑。浙江的黄绾说:“东南之事,莫大于浙闽海寇,凡浙之寇,皆闽之人也。闽之人始为回易,交通岛夷,以其货挟其人来吾海上,云为贾。或有为盗者,非尽为也。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则皆习为盗矣。盗得其利,官莫为惩,彼恣而无害,故日趋而日众,始而且闽之贾舶为之,继而南畿吴越贾舶亦或为之,继而闽之逃亡集四方无籍为之。又继而吾土之无籍亦或托为之。所以东南海寇,今为盛也。”
 可见,为了防御海寇,福建的商船开始装备各种火器,抵抗海寇与官军。这种风气很快传染到吴越一带的商船、渔船,于是,海上船只普遍成为武装船舶。那么,该怎样处理这一问题?戴鱀说了他的考虑:
可见,为了防御海寇,福建的商船开始装备各种火器,抵抗海寇与官军。这种风气很快传染到吴越一带的商船、渔船,于是,海上船只普遍成为武装船舶。那么,该怎样处理这一问题?戴鱀说了他的考虑:
议者或曰:不如遂通之,胡椒、苏木之属,民之所资也。我得其资,彼获其售。至而如归,可以弭祸。噫嘻,是不独忽于祸变之虞,亦且戾于国家之法矣。我国家宅有四海,重译贡琛者不绝于道。然制御之方,科条之设甚明且肃也,故市舶之设,以待番夷之舶来贡者,许之互市有无,故中国之资,多取之四夷,如西北之马,东南之胡椒、苏木之属是也。……今使应入闽广之夷而改入吾郡已不可矣,况使中国之民挟戎器,驾巨舶,决海防,私出外境,市奇货以图厚利哉。又况使五郡之为之根柢槖穴,延盗贼入室,启之途而借之便哉。夫中国之民出外境市禁止物擅驾海舟,皆律例之所治者,而尚冒为之,若遂决其隄防而听其所为,则异日之祸,可噬脐乎。故曰私以番物市于吾境者,宜一切禁之便。

如戴鱀所说,当时已经有人提出:与其让不法贸易在海上进行,无人管辖,不如开海禁,允许通商,双方贸易,可以消除祸患。但是,戴鱀认为,这种做法很危险,弄不好引祸上身。事实也是如此。嘉靖十三年(1534)八月癸丑,“初,直隶、闽浙并海诸群奸民,往往冒禁入海,越境回易以觅利。”“会奸民林昱等舟五十余艘,前后至(台州)松门海洋等处,因与官兵拒敌,多少杀伤。寻执之,验其舟,所载皆违禁物。”
 其时,朝廷已经订立了严厉的海禁之法,一时改变为完全相反的政策,也有困难。另一种观点是彻底严禁。浙江士大夫的讨论一时没有结果,海上私人贸易仍在进行。为何一时没有造成大患呢?这是因为,在浙江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业巨头会有长久考虑,他们会自动约束部下的犯罪行为,以免引起官方注意,最后损伤全体的利益。不过,因双屿港一带的海上形势较乱,少数巨头很难控制整体的行为,双屿港成为案件多发地带。嘉靖十二年(1533)九月辛亥,“兵部言,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因而寇劫”。
其时,朝廷已经订立了严厉的海禁之法,一时改变为完全相反的政策,也有困难。另一种观点是彻底严禁。浙江士大夫的讨论一时没有结果,海上私人贸易仍在进行。为何一时没有造成大患呢?这是因为,在浙江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业巨头会有长久考虑,他们会自动约束部下的犯罪行为,以免引起官方注意,最后损伤全体的利益。不过,因双屿港一带的海上形势较乱,少数巨头很难控制整体的行为,双屿港成为案件多发地带。嘉靖十二年(1533)九月辛亥,“兵部言,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因而寇劫”。
 这也说明,当时漳州民常来到浙江沿海,他们虽以贸易为主,但已经有个别人变成海寇,袭击浙江沿海了。这使浙江方面感到了治安问题。
这也说明,当时漳州民常来到浙江沿海,他们虽以贸易为主,但已经有个别人变成海寇,袭击浙江沿海了。这使浙江方面感到了治安问题。
不过,在嘉靖十九年(1540)以前,浙江沿海的岛屿,以商业贸易为主,抢劫之类的案件较少。
虽说嘉靖十一年(1532)之时,戴鱀已经感到浙江沿海的海寇问题严重,但海寇大举袭击浙江沿海,则是嘉靖十九年(1540)之后的事。其原因在于,嘉靖十八年(1539)是浙江的大灾之年:
万历绍兴府志:嘉靖十八年五月,绍兴大水,衢婺严三府暴流与江涛合入越城,高丈余。沿海居民溺无算。萧山西江塘坏,县市可驾巨舟。万历金华府志:嘉靖十八年六月六日,金华八县大雨浃旬,北山蜃出,田碶、塘堰荡尽。东、义、永、武四县俱发洪,兰溪特甚,水高丈余,民无楼阁者,栖于屋脊。嘉兴府志:嘉靖十八年六月,嘉兴府旱蝗,大饥。杭州府志,嘉靖十八年:杭州自三月不雨,至于六月,井泉皆竭。

可见,当年的浙江水旱灾害不断,农业受到极大的打击,大灾之后,浙江商品市场不振,许多商品无法出售,连带工商业者也陷入了恐慌。次年,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纷纷到海上谋生,这使浙东海商及海寇势力大涨。《筹海图编》记载:“嘉靖十九年,贼首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港为巢。光头者,福人李七;许栋,歙人许二也。皆以罪系福建狱,逸入海,勾引倭奴结巢于霩衢之双屿港。其党有王直、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出没诸番,分?剽掠,而海上始多事矣。”
 如其所说,李七(李光头)和许二(许栋),都有可能是福州越狱囚犯中的人,《福建通志》亦载其事:“十九年,福州狱囚李光头等逸入海。注云:光头闽人,与歙人许栋皆以罪系福州狱,至是逸入海岛,招集诸亡命,踞宁波之双屿港,汪直、徐海、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皆附焉……又勾倭及佛郎机诸国互市。”
如其所说,李七(李光头)和许二(许栋),都有可能是福州越狱囚犯中的人,《福建通志》亦载其事:“十九年,福州狱囚李光头等逸入海。注云:光头闽人,与歙人许栋皆以罪系福州狱,至是逸入海岛,招集诸亡命,踞宁波之双屿港,汪直、徐海、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皆附焉……又勾倭及佛郎机诸国互市。”
 他们越狱后来到浙江沿海,一边做生意,一边杀人放火,成为海寇。从嘉靖九年(1530)越狱,迄至嘉靖十八年(1539)或是嘉靖十九年(1540),他们在海上活动已经有十年了。“初自宋素卿创乱之后,十八年金子老、李光头始作难,勾西番掠浙闽。”
他们越狱后来到浙江沿海,一边做生意,一边杀人放火,成为海寇。从嘉靖九年(1530)越狱,迄至嘉靖十八年(1539)或是嘉靖十九年(1540),他们在海上活动已经有十年了。“初自宋素卿创乱之后,十八年金子老、李光头始作难,勾西番掠浙闽。”
 “初,华人艳诸番货,私与市。嘉靖十七八年,闽人金子老为番舶主,而巢于宁波之双屿港。”
“初,华人艳诸番货,私与市。嘉靖十七八年,闽人金子老为番舶主,而巢于宁波之双屿港。”
 据李献璋的考证,金子老其人,也是原籍闽中的海寇。这给浙江造成很大问题。“乃今有不尽然者,边檄报漳民通番舶取息币,时肆摽掠。忧时者至募民为兵,乃帅其人昼夜警,日出鼓钲,日入燎辉,至振铎巡鼜,植棘树,墉坎山谷以守。人情汹汹,海邦驿骚,若朝不谋夕。”
据李献璋的考证,金子老其人,也是原籍闽中的海寇。这给浙江造成很大问题。“乃今有不尽然者,边檄报漳民通番舶取息币,时肆摽掠。忧时者至募民为兵,乃帅其人昼夜警,日出鼓钲,日入燎辉,至振铎巡鼜,植棘树,墉坎山谷以守。人情汹汹,海邦驿骚,若朝不谋夕。”
 综合以上史料所记,可知闽粤海寇对浙江沿海形成治安威胁,主要是在嘉靖十八年(1539)、嘉靖十九年(1540)之后。“然诸夷嗜中国货物,至者率迁延去。贡若人数,又恒不如约。是时,市舶既罢,货主商家商率为奸利,虚值转鬻,负其责不啻千万。索急,则投贵官家,夷人候久不得,颇构难,有所杀伤,贵官家辄出危言撼当事者兵之,使去,而先阴泄之以为德。如是者久,夷人大恨,言挟国王赀而来,不得直,曷归报?因盘踞岛中,并海不逞之民,若生计困迫者,纠引而归之。时时寇沿海诸郡矣。”
综合以上史料所记,可知闽粤海寇对浙江沿海形成治安威胁,主要是在嘉靖十八年(1539)、嘉靖十九年(1540)之后。“然诸夷嗜中国货物,至者率迁延去。贡若人数,又恒不如约。是时,市舶既罢,货主商家商率为奸利,虚值转鬻,负其责不啻千万。索急,则投贵官家,夷人候久不得,颇构难,有所杀伤,贵官家辄出危言撼当事者兵之,使去,而先阴泄之以为德。如是者久,夷人大恨,言挟国王赀而来,不得直,曷归报?因盘踞岛中,并海不逞之民,若生计困迫者,纠引而归之。时时寇沿海诸郡矣。”
 总之,无序的海上贸易容易引发商业纠纷,而商业纠纷很可能发展为劫盗。不过,当时这类情况还不是很严重,如果朝廷能够正视这一问题,在宁波设置海关,管理民间贸易,民间交易的小问题不至于发展成大规模的叛乱。
总之,无序的海上贸易容易引发商业纠纷,而商业纠纷很可能发展为劫盗。不过,当时这类情况还不是很严重,如果朝廷能够正视这一问题,在宁波设置海关,管理民间贸易,民间交易的小问题不至于发展成大规模的叛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漳州人之外,渐有其他籍贯的商人来到浙江双屿港,例如徽州人许栋和王直,就是他们之中的著名人物。如万表所说:
嘉靖十九年,时海禁尚弛,直与叶宗满等之广东造巨舰,将带硝黄、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赀,夷人大信服之。“称为五峰船主”。

许四即许梓,其兄许二、许三先年下海通番,赘于大宜、满剌加,自后许四与兄许一尝往通之。

近年海禁渐弛。贪利之徒,勾引番船,纷然往来于海上,寇盗亦纷然矣。然各船各认所主,承揽货物,装载而还,各自买卖,未尝为群。后因海上强弱相凌,互相劫夺,因各结
 ,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或五十只,或一百只,成群分党,分泊各港,又用三板、草撇、脚船,不可计数。在于沿海,兼行劫掠,乱斯生矣。
,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或五十只,或一百只,成群分党,分泊各港,又用三板、草撇、脚船,不可计数。在于沿海,兼行劫掠,乱斯生矣。

叶权的《贤博编》记载:
嘉靖丙午、丁未间,海禁宽弛,浙东海边势家以丝缎之类与番船交易,久而相习,来则以番货托之。后遂不偿其值。海商无所诉,一旦突至,放火杀数十人。

俞大猷说:“数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勾引西南诸番,前至浙江之双屿港等处买卖,逃免广东市舶之税。及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
 谢杰说:“其为中国患,皆漳人、潮人,宁绍人主之也。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但为此者,多乐宽纵而喜交通东南。承平日久,市舶之官,权胜流职。天顺以来,久与夷通。奸民率窜于此,因以为市。其在海上,武具力齐,虽有小盗,随见殄灭,是以濒海晏然,绝无寇警。”
谢杰说:“其为中国患,皆漳人、潮人,宁绍人主之也。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但为此者,多乐宽纵而喜交通东南。承平日久,市舶之官,权胜流职。天顺以来,久与夷通。奸民率窜于此,因以为市。其在海上,武具力齐,虽有小盗,随见殄灭,是以濒海晏然,绝无寇警。”
 顾清的《观海诗序》:
顾清的《观海诗序》:
今天下负海之邦,自青齐至于交广,惟江浙闽去海最近。其间负海而州,控接蕃夷者,闽又最近。出谯门弥望巨浸,鲸窝蜃居,倭奴、爪哇、流求、毛昌、赤王之蛮,风乘涛凌,不旬日可致几席下。顽狙之氓,逃征避辜,驾长舟、
 巨桅,挟群不逞之徒,岀没于洪波。时登岸公肆劫剽,急则踔汗澜走荒外,吏无所踪迹。盖濒海之邦,率有是,而闽与广为特甚。其一二人著名字者,海壖之民,日惴惴虞其至,有司者侦其它适,图旬月之安,则幸。矧敢与之角。
巨桅,挟群不逞之徒,岀没于洪波。时登岸公肆劫剽,急则踔汗澜走荒外,吏无所踪迹。盖濒海之邦,率有是,而闽与广为特甚。其一二人著名字者,海壖之民,日惴惴虞其至,有司者侦其它适,图旬月之安,则幸。矧敢与之角。

如上所说,当时的浙江和南直隶的商人都卷入了海上贸易,海上贸易已经不是闽粤商人的专利,而是东南四省沿海民众都参加的一项“事业”。谢杰说:“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者。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但为此者,多乐宽纵,而喜交通东南。”
 可见,当时的倭寇首领主要来自福建的漳州和广东的潮州,而后浙江的宁波、绍兴也都出产倭寇头目。其实,他们最早只是海上船帮的首脑,而后渐渐涉及犯罪活动。他们手下雇用了许多日本浪人,并利用这些日本浪人从事非法活动,最终,他们自己成为倭寇首脑。这有一个演变过程。
可见,当时的倭寇首领主要来自福建的漳州和广东的潮州,而后浙江的宁波、绍兴也都出产倭寇头目。其实,他们最早只是海上船帮的首脑,而后渐渐涉及犯罪活动。他们手下雇用了许多日本浪人,并利用这些日本浪人从事非法活动,最终,他们自己成为倭寇首脑。这有一个演变过程。
朱纨的《广福浙兵船当会哨论》提到海寇的活动:“愚考入番罪犯,多系广福浙三省之人。”
 他们的活动围绕着宁波外海的双屿港。“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司。其质契势家护持之,漳泉为多。”
他们的活动围绕着宁波外海的双屿港。“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司。其质契势家护持之,漳泉为多。”
 徐师曾说:“时有许栋者,啸聚双屿港,兼冒二法,众至五六万。”
徐师曾说:“时有许栋者,啸聚双屿港,兼冒二法,众至五六万。”
 朱纨曾亲自观察过又屿港的情况:“本年四月初七日,双屿既破,臣五月十七日渡海达观,入港登山,凡逾三岭,直见东洋中有宽平古路,四十余日,寸草不生,贼徒占据之久,人货往来之多,不言可见。”
朱纨曾亲自观察过又屿港的情况:“本年四月初七日,双屿既破,臣五月十七日渡海达观,入港登山,凡逾三岭,直见东洋中有宽平古路,四十余日,寸草不生,贼徒占据之久,人货往来之多,不言可见。”
 朱纨发现,双屿岛上“贼建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遗弃大小船二十七只”。
朱纨发现,双屿岛上“贼建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遗弃大小船二十七只”。

按,关于双屿港岛上的人数,一般认为中外海商海寇共有万余人,至少也有数千,为什么官军只看到寮屋二十余间?且与天妃宫十余间不配。所以,多人怀疑岛上的房屋间数。其实,这个海商与海寇们的临时住处与常人的住处是不一样的。海商海寇在海上大都是上百人居住在一条船上,他们在陆地上的临时居所,也不会盖成多间房屋,通常是盖一间巨大的寮棚,所有的人住在一起。这样,头目也容易管理众人。二十来间大型寮屋,如果每间寮屋住上三五百人,总数就是六千至一万人。为什么天妃宫会有十余间呢?这是因为双屿港的海商与海寇结成了团伙,每个团伙都会有自己的天妃宫,以便祭祀和商议。天妃宫的作用,大致相当于梁山的“聚义厅”吧。至于一间可住数百男人的大型寮屋,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大家可以想象。事实上,明代一直有同性恋起源于海寇的传说。
在这个时代,漳泉海商每年都要从福建沿海此上浙江,带去各种海外物产,但是,他们也会有海寇活动。黄绾在《甓余杂集序》中说:“凡浙之寇皆闽之人也。闽之人始为回易,交通岛夷,以其货挟其人来吾海上,云为贾或有为盗者,非尽为也,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则皆习为盗矣……始而闽之贾舶为之,继而南畿、吴越之贾舶亦或为之,继而闽之逃亡集四方之无籍为之,又继而吾土之无籍亦或托为之。”
 可见,江浙人逐渐卷入沿海的贸易。“浙人多诈,每窃买丝线、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
可见,江浙人逐渐卷入沿海的贸易。“浙人多诈,每窃买丝线、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
 “浙中于商之外,又有一伙灶户,专以采办为名,私造违禁大舡,不时下海。始之取鱼,继之接济,终之通番。”
“浙中于商之外,又有一伙灶户,专以采办为名,私造违禁大舡,不时下海。始之取鱼,继之接济,终之通番。”

总的来说,由于实行海禁制度,明朝对海上贸易缺乏管理。明嘉靖年间,海禁松弛,海上贸易逐渐恢复,嘉靖十九年(1540)之后,海上贸易中心转移到浙江宁波外海的双屿港。然而‘明朝的管理制度未能跟上,于是,海上出现一片乱象。嘉靖十九年(1540)之后,以双屿港为核心的海上贸易十分混乱,抢劫事件经常发生。到此贸易的海商为了安全纷纷加强武装,海商之间的纷争往往转化为武装斗争,甚至演化为对陆地居民的劫掠。在外人看来,双屿港已经成为海寇活动的中心了。
以上历史表明,来自漳潮的海上力量,才是双屿港发展的关键所在。一些文章将双屿港的发展归结为葡萄牙人来此贸易,其实不对。葡萄牙人是后到者,不是开发者。从葡萄牙人掌握的海图来看,在嘉靖前期,他们绘制的浙海的地图还是十分茫然的。但在嘉靖十九年(1540)之后,双屿港成为“海上闹市”,葡萄牙文献中出现双屿港的名字多了起来,大批葡萄牙船只到双屿港贸易,应当是在该年之后。其时,双屿港兴盛一时,不论是葡萄牙人还是中国东南各省的商人,都在岛上建立了拜神的宫庙,还有许多房子。这时的双屿港,已经是东亚的海上贸易中心了。
以上将海寇问题暂时搁置一边,主要叙述双屿港的对外贸易问题。
综上所述,浙江双屿港的兴起与漳潮私商有关。浙江舟山群岛盛产黄鱼,是福建渔民的传统渔场之一,每年春夏之间的黄鱼季节,来自江南各地的渔船涌入舟山群岛,其中也有来自福建的渔民。明代中叶,海禁松弛,海上贸易逐渐活跃起来。大约在正德年间,有一些福建私商开始到浙江沿海贸易。福建与浙江虽是邻省,但两省多为山地,交通困难,自古两省间的贸易都是以海路为主。明朝的海禁虽然一度使闽浙之间贸易转到陆上,但陆上运输成本远大于海路,所以,一旦闽浙之间的海路开通,当地的廉价优质商品便吸引了福建人前去贸易。这样,舟山沿海一些原被列入禁地港口,便成为私商往来的地方。经营海上贸易的漳州商人,并带去了东南亚的物产,引起轰动。定海附近的双屿港就是这样兴起的。迄至嘉靖九年(1530)或是五年(1526),一股福州越狱的大股海寇也来到双屿港,他们多为漳州人,按照漳潮的习俗被称为“某獠”,或是“某大獠”,“獠”是漳州一带对土著的贬称,后来民间的头目也被称为“獠”。獠字雅化之后,被写成“佬”,于是,“某大獠”便成为“某大佬”,反而成为民间流行的尊称了。从早期双屿港称霸的头目多为某大佬来看,在此地活动的私商以漳州人为多,其中也有潮州人,后来,加入其中的江浙人也不少。朱纨说:“贼首许二即许栋等,违例打造三桅异样大船,并草撇快马等船,专在海洋横行打劫。嘉靖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贼徒驾船三十余只。”
 这个团伙应当是双屿港海面最大的海寇商人集团。如朱纨说:“贼首许二等,纠集党类甚众,连年盘据双屿,以为巢穴。每岁秋高风老之时,南来之寇,悉皆解散,惟此中贼党不散,用哨马为游兵,胁居民为向导,体知某处单弱,某家殷富,或冒夜窃发,或乘间突至,肆行劫掳,略无忌惮。”
这个团伙应当是双屿港海面最大的海寇商人集团。如朱纨说:“贼首许二等,纠集党类甚众,连年盘据双屿,以为巢穴。每岁秋高风老之时,南来之寇,悉皆解散,惟此中贼党不散,用哨马为游兵,胁居民为向导,体知某处单弱,某家殷富,或冒夜窃发,或乘间突至,肆行劫掳,略无忌惮。”

其时,盘踞双屿港的许栋等人,与内陆有商贸关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六月十二日,“嵊县地方,盘获双屿贼首许二弟许四并番银一担,铁器一担,花缸二只,土内俱埋银。”
 很显然,他是在转移资本。有些军人也和他们进行贸易。“绍兴卫三江所军王顺与见获钱文陆各不合私自下海,投入未获叛贼冯子贵船内管事,与伊共谋投番导劫,常到海宁大尖山下泊船。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内王顺将卖剩苏木二担,胡椒半担,送已问结军人王雨接,卖银二十两,延久不还。”
很显然,他是在转移资本。有些军人也和他们进行贸易。“绍兴卫三江所军王顺与见获钱文陆各不合私自下海,投入未获叛贼冯子贵船内管事,与伊共谋投番导劫,常到海宁大尖山下泊船。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内王顺将卖剩苏木二担,胡椒半担,送已问结军人王雨接,卖银二十两,延久不还。”
 滨海的商人也经常造船下海贸易。“温州府乐清县民金正四,与见获族兄金小光,同县吴奇、沈歇、詹甫、朱岩、王正,从台州府黄岩县民刘亚相,太平县民张三,各不合违例擅造见获二桅大船,结伙下海与未获海贼帅四老等向导行劫。”
滨海的商人也经常造船下海贸易。“温州府乐清县民金正四,与见获族兄金小光,同县吴奇、沈歇、詹甫、朱岩、王正,从台州府黄岩县民刘亚相,太平县民张三,各不合违例擅造见获二桅大船,结伙下海与未获海贼帅四老等向导行劫。”

来自南直录的许栋及王直,原来都是著名的徽商。他们逐渐成为海寇商人共同的领袖。由于漳潮及江浙海商在双屿港的活动,引致葡萄牙、日本的商船只前来贸易,遂使双屿港成为东亚海上贸易的中心,建立了双屿及日本、东南亚乃至葡萄牙的贸易关系。
双屿港约在嘉靖十九年(1540)以后成为闽浙海寇商人的一个据点,这里即有海商贸易,也有海寇的劫掠,同时,他们还引来诸国商人到此贸易。龙思泰论双屿港:“在其繁荣兴旺的日子里,双屿成为中国人、暹罗人、婆罗洲人、琉球人等等的安全地带。”
 明代中期中国沿海常有爪哇和马来亚半岛的海寇活动,在葡萄牙人的文献中也有记载。双屿港出名后,这些人也来到双屿港。
明代中期中国沿海常有爪哇和马来亚半岛的海寇活动,在葡萄牙人的文献中也有记载。双屿港出名后,这些人也来到双屿港。
 其实,这些商人中,不仅有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商人,还有葡萄牙人和日本九州萨摩藩的商人。这种混乱中的国际贸易,最终带来许多问题。
其实,这些商人中,不仅有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商人,还有葡萄牙人和日本九州萨摩藩的商人。这种混乱中的国际贸易,最终带来许多问题。
关于日本浪人何时来到双屿港,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大致而言,自明初以来,日本贡船都是到宁波港进贡,久而久之,他们对宁波港周边地形渐渐熟悉,开始有人在周边岛屿采购所需商品。按郑晓的说法:“至正德中,华人通倭,而闽浙大官、豪杰实为祸首。”
 如果郑晓说的可靠,早在正德年间就有日本海商在宁波外海做生意了。嘉靖二年(1523),宁波发生了日本使者争贡事件,其后浙江海面的形势逐渐失控。《筹海图编》记载:
如果郑晓说的可靠,早在正德年间就有日本海商在宁波外海做生意了。嘉靖二年(1523),宁波发生了日本使者争贡事件,其后浙江海面的形势逐渐失控。《筹海图编》记载:
自甲申(嘉靖三年)岁凶,双屿货壅,而日本贡使适至。海商遂败货以随售,倩倭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西洋船原回私澳,东洋船通布海洋,而向之商舶,悉变而为寇舶矣。

如其所说,嘉靖三年(1524)后,倭寇或是“日本海贾”在东南沿海出没不止。浙江当大灾之后,亏本的浙商只好向日本商人低价抛售商品。日本商船得利之后,前来浙江双屿港贸易的商船越来越多。“西洋船原回私澳,东洋船通布海洋,而向之商舶,悉变而为寇舶矣。”嘉靖二十九年(1550),浙东人项乔追溯往事:“在浙宁波海中有双屿山,去观海卫百余里。海贼通倭夷,在海劫人停泊大船者,巢穴是山之中,耕田筑屋已二十七年,海上往来受害者无可奈何。”
 可见,就在嘉靖二年(1523)之后,已经有海寇占据双屿港,并勾结“倭夷”。然而,其规模还不很大。
可见,就在嘉靖二年(1523)之后,已经有海寇占据双屿港,并勾结“倭夷”。然而,其规模还不很大。
从《浙江通志》的海防志、祥异志来看,嘉靖三年(1524)之后,浙江沿海并无大股倭寇发生,这应当是官府厉行海禁的结果。迄至嘉靖十八年(1539)浙江大灾,农民破产,影响了浙江的市场。许多商人无法出售货物,只好贱卖。这给日本商人一个机会。嘉靖十八年(1539)又是日本进贡之年。据日本的《策彦入唐记》一书,嘉靖十八年(日本后奈良天文八年,1539)四月,日本遣明正使湖心硕鼎、副使策彦周良从五岛出发,五月抵达宁波。次年三月,日使湖心硕鼎等人抵达北京进贡。嘉靖二十年(1541)五月,日本使船从宁波出发,六月回到日本的五岛。

以上史料表明,日本使船进贡在华时间一般是三年。就浙东的历史而言,嘉靖年间,日本进贡三次,每次日本进贡之时,便是沿海倭患兴盛之时,因此,若说当时的浙东沿海的倭乱完全与日本人无关,只怕通不过历史考验。嘉靖十八年(1539)日本的进贡,同样带来许多问题。当日本正使到北京朝拜明朝皇帝之时,他们留守宁波的一些人便可在沿海岛屿做“生意”。如前所述,浙江双屿港的海寇,是在嘉靖十九年(1540)后越闹越大。这些海寇商人有来自日本的,有来自葡萄牙的,更多的是来自闽浙粤沿海的海寇。其中为首的是许一、许二等人。“明年癸卯(嘉靖二十二年,1543),邓獠等寇掠闽海地方,浙海寇盗亦发,海道副使张一厚,因许一、许二等通番致寇,延害地方,统兵捕之。许一、许二等敌杀得志,乃与佛郎机夷竟泊双屿。伙伴王直于乙巳岁(1545 年)往市日本,始诱博德津倭助才门等三人来市双屿。明年复行,风布其地,直浙倭患始生矣。”
 可见,当时宁波沿海已经有葡萄牙籍、日本籍海寇出现。钱薇评论:“国初倭患虽遍于沿海一带,然止倭耳,今也华人习知海外金宝之饶,夷亦知吾海畔之人奸阑出入,易与为市,况复杂以商舶。倭之来也,辄矫云求贡,苟或海防弛备,即肆劫掠,且如闽广群不逞之徒,明越诸得利之家,外交内诇,为彼耳目。”
可见,当时宁波沿海已经有葡萄牙籍、日本籍海寇出现。钱薇评论:“国初倭患虽遍于沿海一带,然止倭耳,今也华人习知海外金宝之饶,夷亦知吾海畔之人奸阑出入,易与为市,况复杂以商舶。倭之来也,辄矫云求贡,苟或海防弛备,即肆劫掠,且如闽广群不逞之徒,明越诸得利之家,外交内诇,为彼耳目。”
 徐献忠说:“嘉靖甲辰(嘉靖二十三年,1544)以来,海上负贩之徒,诱致倭夷,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因行劫。”
徐献忠说:“嘉靖甲辰(嘉靖二十三年,1544)以来,海上负贩之徒,诱致倭夷,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因行劫。”
 可见,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以后,日本的商船更多地来到双屿港。
可见,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以后,日本的商船更多地来到双屿港。
嘉靖二十七年(1548),朱纨在浙江审的一个案子牵涉到日本人和双屿港。“嘉靖二十五年福建福清等县通番喇哒见获林烂四等,纠集多人,发船入往至日本国,朝见国王,说我大明买卖甚好。国王借与稽天等银子五贯,计五百两。造船一只给予番铳二架、番弓、番箭、倭刀、藤牌、长枪、标枪等项利械,自三月内在本国开洋,到浙江九山海岛,思德双屿港系日本等国通番巢穴,欲投未获徽州贼许二等做地主。”船上除了林烂四等五十二人外,还有日本客商稽天、新四郎、芝兰等三名。
 按照日本人稽天的说法,福州人林陆观到日本贸易,所乘舟被大风打破,在日本住了三年,度日艰难。于是,萨摩藩主借给五贯银子,让他造舟回家。林陆观应是答应回到中国后以商货偿还,所以,萨摩藩主另派稽天、新四郎等五人跟随船只来取货物。稽天等人随身携带银子也有“六贯二百六十目”。
按照日本人稽天的说法,福州人林陆观到日本贸易,所乘舟被大风打破,在日本住了三年,度日艰难。于是,萨摩藩主借给五贯银子,让他造舟回家。林陆观应是答应回到中国后以商货偿还,所以,萨摩藩主另派稽天、新四郎等五人跟随船只来取货物。稽天等人随身携带银子也有“六贯二百六十目”。
 后来这艘船被浙江水师缴获。这条史料说明,约嘉靖二十六年(1547)之时,日本萨摩藩主通过借钱给中国船主的方式,插手双屿港贸易。不过,这艘船配备的武器相当多,甚至有最新式的火枪——“番铳”,可见,他们是做好战斗准备的。那一时代的海上商人,往往是半掠夺,半买卖,海寇与海商,很难分开。朱纨的《海洋贼船出没事》一文提道:
后来这艘船被浙江水师缴获。这条史料说明,约嘉靖二十六年(1547)之时,日本萨摩藩主通过借钱给中国船主的方式,插手双屿港贸易。不过,这艘船配备的武器相当多,甚至有最新式的火枪——“番铳”,可见,他们是做好战斗准备的。那一时代的海上商人,往往是半掠夺,半买卖,海寇与海商,很难分开。朱纨的《海洋贼船出没事》一文提道:
此皆内地叛贼,常年于南风迅发时月,纠引日本诸岛、佛郎机、彭亨、暹罗诸夷,前来宁波双屿港内停泊,内地奸人,交通接济,习以为常,因而四散流劫,年甚一年,日甚一日,沿海荼毒,不可胜言。

这两段史料表明,嘉靖十九年(1540)以后的浙江双屿港,有来自日本、暹罗以及葡萄牙人的商人屯驻贸易,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当时人说:“自嘉靖元年罢市舶,凡番货至,辄賖与奸商,久之,奸商欺冒,不肯偿。番人泊近岛,遣人坐索,不得,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久之,百余艘,日据我海隅不肯去。”
 番客在双屿岛,最大的问题还是找不到可靠的贸易对手。一不小心就受骗。有一伙包括葡萄牙人的团伙,“买卖往来日本、漳州、宁波之间,乘机在海打劫。今失记的日在双屿被不知名客人撑小南船载麦一石,送入番船,说有绵布、绵、湖丝,骗去银三百两,坐等不来。又宁波客人林老魁,先与番人将银二百两买段子、绵布、绵,后将伊男留在番船,骗去银一十八两。又有不知名宁波客人,哄称有湖丝十担,欲卖与番人,骗去银七百两;六担欲卖与日本人,骗去银三百两。今在双屿被获六七十人,内有漳州一人、南京一人、宁波三人及漳州一人斩首,一人溺水身死,其余遁散等语”。
番客在双屿岛,最大的问题还是找不到可靠的贸易对手。一不小心就受骗。有一伙包括葡萄牙人的团伙,“买卖往来日本、漳州、宁波之间,乘机在海打劫。今失记的日在双屿被不知名客人撑小南船载麦一石,送入番船,说有绵布、绵、湖丝,骗去银三百两,坐等不来。又宁波客人林老魁,先与番人将银二百两买段子、绵布、绵,后将伊男留在番船,骗去银一十八两。又有不知名宁波客人,哄称有湖丝十担,欲卖与番人,骗去银七百两;六担欲卖与日本人,骗去银三百两。今在双屿被获六七十人,内有漳州一人、南京一人、宁波三人及漳州一人斩首,一人溺水身死,其余遁散等语”。

无序的海上贸易很容易导致冲突,怎样引导海上贸易,使之有利于自己又不会出乱子?明朝在这方面做得很差,导致浙江沿海治安出了问题。
如上所述,嘉靖年间中国东南海疆的对外贸易重心从广州港转移到闽浙两省的港口。最早的重点港口是漳州龙溪县的海沧、月港,后来逐渐转移到浙江宁波双屿港,而闽粤交界处的梅岭、走马溪、南澳港一直在对外贸易中占有位置。要说明的是:漳州和潮州的港口,早在明代前期就和东南亚有贸易关系,既有外来的番船到本土贸易,也有本土的商船到东南亚贸易。当时进行对外贸易的私商以漳州人为多,潮州人次之。可以说,漳潮人是中国海商集团的基础。明代前期广州一带的海上私人贸易也是掌握在漳潮商人手上的。嘉靖年间,随着时代的变化,漳潮商人从闽粤边境北上,逐渐将泉州人、温州人以及浙江宁波一带的商人和徽商都卷入了海上贸易,从而扩大了海商集团。就贸易港口而言,潮州及漳州海港的繁荣刺激了闽浙其他港口的复兴,例如泉州的安海港和浙江的宁波港都进入了海上私人贸易时代,只不过安海的贸易不太显著而已。
这些位于中国东南的港口对外联系密切,当地的商人到东南亚各地贸易,本港也常有海外船只来访。杨国桢研究《渡海方程》等民间的针路簿,其结论是这些针路簿多以闽南的港口例如浯屿、太武山为出发港,而其线路伸展到东南亚的安南、占城、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诸港。
 这说明明代中期漳潮与南海诸港的联系仍在延续。福建商人沿着这些贸易线路到南海诸港贸易,来自东南亚的商船和海寇船,也常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诸个港口。
这说明明代中期漳潮与南海诸港的联系仍在延续。福建商人沿着这些贸易线路到南海诸港贸易,来自东南亚的商船和海寇船,也常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诸个港口。
从大背景来说,嘉靖年间东亚最流行的海上贸易线路是从暹罗到中国东南诸港,再到日本的九州。中国东南区域刚好位于这条最热国际贸易线路的中端,往来船舶选择中国东南港口为休整港口,在这里补充粮食、水果和饮用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这里购取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并销售东南亚的香料。中国的丝瓷不论在东南亚还是日本都是最畅销的商品。而中国的丝瓷类商品大都产于东南诸省。例如,来自江浙的丝绸,来自江西饶州的瓷器,来自福建的白糖。这是明代嘉靖年间中国东南海上贸易兴盛的原因和背景。
研究嘉靖年间中国东南诸港的海上贸易,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商人的主动性。晚明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化程度较高,工商业发达,需要海外市场,因此,有不少敢于冒险的商人向海外发展,输出中国商品,并获得利润。也可以说,这一时代东部亚洲的海上通道及海上贸易,其实是他们建立的吧。
在嘉靖年间中国东南的海上贸易中,漳潮商人的核心地位明显。海上贸易是从漳潮一带扩展到江浙区域。不过,江浙区域海商的崛起速度亦是惊人,他们从无到有,凭借着江南丰富的物产和资本,长袖善舞,很快成为中国海商中最强大的力量。嘉靖之后,因江浙方面厉行海禁,江浙海商基本退出海上贸易,这是很可惜的。一直到明代末年,江浙海禁松弛,江浙商人之中,才有些人卷入海洋贸易。
 他们人数不多,很快又遇到清代初年的海禁,所以,明代的江浙海商一直未能发展起来。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他们人数不多,很快又遇到清代初年的海禁,所以,明代的江浙海商一直未能发展起来。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嘉靖年间由南海诸国发来的商船被称为“番船”,番船中的一伙武装商人,被称为“佛郎机”,实际上,他们就是以马六甲为基地的葡萄牙殖民者!嘉靖年间他们出没于闽浙粤诸大走私港口,在生意上获得很大的成功。要注意的是:在葡萄牙人抵达东南诸港口之前,当地已经有发达的对外贸易,所以,不是葡萄牙人来到当地开发了当地的对外贸易,而是当地的对外贸易在漳潮商人的活动下,很早就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过,原先东南诸港的对外贸易都不如广州。当嘉靖初年广州一度拒绝海外贸易之后,对外贸易的重心便向潮州、漳州及宁波发展。由于宁波位于丝绸产地,而且对日本通航较为方便,最终宁波取代漳潮的港口,成为对外贸易中心。当嘉靖年间浙江与福建沿海发生倭寇问题之后,宁波沿海不适宜贸易,多数往来于中日之间的商人转移到广东潮州的南澳和福建漳州的月港继续贸易,而葡萄牙人经历波折之后,最终转移到广东的澳门进行贸易。以上是嘉靖年间东南诸港兴废的过程。宁波双屿港的退出,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重新集中于闽粤二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