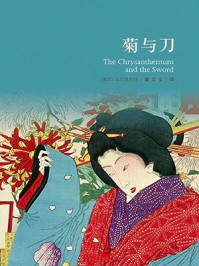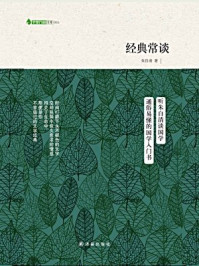《庄子》一书堪称文体大全,而在诸多文体中,寓言尤其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庄子》一书之所以被视作文学瑰宝,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书中寓言体现出来的,寓言构成《庄子》全书的主要部分;这点与其他子书不同,在其他子书中寓言一般不占主要地位,而是文章的附属品(《韩非子》中的《说林》等篇除外)。
 可以说,没有寓言,就没有《庄子》这部浪漫主义的著作。
可以说,没有寓言,就没有《庄子》这部浪漫主义的著作。
在对《庄子》的文学研究中,提及最多的即是对其寓言的研究。有的是把寓言作为单独研究的对象,挖掘它的文化内涵及在中国文学中的贡献等;有的是把寓言同重言和卮言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以探究《庄子》的话语特色;有的专门研究寓言中的各色人物形象;有的又把它同其他典籍中的寓言进行对比分析。《庄子》寓言的文学贡献、寓言与重言、卮言的关系等前面已有提及,本节主要关注对《庄子》寓言与其他典籍中寓言的对比以及《庄子》寓言中的人与物的形象塑造。
寓言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要早于《庄子》,但“寓言”一词最早是在《庄子》里出现的。
战国时期,“寓言”的创作进入繁荣期,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中,为了增强自身理论学说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诸子各家争相运用“寓言”这一手段,“寓言”的创作异彩纷呈。除庄子外,《孟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子书中的“寓言”,总数在千篇以上。与其他诸子著作寓言相比,《庄子》寓言最大特色在于题材全面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动物植物,乃至抽象观念等,无不为其所用。《庄子》大量运用动物甚至抽象名词创造“寓言”故事,这不但可与《伊索寓言》比美,在诸子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其次是题材的生活化,《庄子》的寓言世界生活气息浓郁,木匠、石匠、铁匠,厨师、商人、牧羊、喂马、伺虎、屠牛,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皆为《庄子》“道”统。
其次是题材的生活化,《庄子》的寓言世界生活气息浓郁,木匠、石匠、铁匠,厨师、商人、牧羊、喂马、伺虎、屠牛,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皆为《庄子》“道”统。
在诸多诸子著作中,《庄子》和《韩非子》尤以寓言故事见长,《庄子》里有近 200 则寓言(宽泛意义上统计),《韩非子》寓言 300 多则。两书的寓言以怎样的方式构建了各自的文本世界是很多学者关注的话题。综合相关研究
 ,两书寓言之异同可概述如下:首先,两者均通过寓言故事表达各自的哲学思想或学术主张,《庄子》中的寓言反映的是道家学派的思想,而《韩非子》中的寓言表现的却是法家学派的主张;从组织形式上看,《庄子》中的寓言没有独立地位,只是夹杂于文中,而《韩非子》中的寓言却呈现出相对独立且结构宏大的群落体制;从创作方法上看,《庄子》中的寓言多奇幻玄虚、生动形象,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且题材较为广泛,自然的、历史的、现实的,各类题材应有尽有,而《韩非子》中的寓言多质朴平实、庄重峻峭,呈现出现实主义特征,寓言题材较为单一,大多出自历史典故;从形象塑造上看,《庄子》寓言中的形象既有人物,又有动植物甚至是无生物,而《韩非子》寓言刻画的形象绝大多数只有人物。“庄、韩寓言在用法上,在文学一般特点上相类似,但二人政治观、人生观、审美观不同,故寓言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多有不同:一是博大虚灵,一是阴深阻滞;一是超越本体,一是贯注世俗;一是哲学的,一是政治的;一是养生的,一是治人的;一是浪漫的,一是现实的;一是轻松快乐的;一是沉重愁苦的;一是平民的,一是政客的;一是自然的,一是人为的。”
,两书寓言之异同可概述如下:首先,两者均通过寓言故事表达各自的哲学思想或学术主张,《庄子》中的寓言反映的是道家学派的思想,而《韩非子》中的寓言表现的却是法家学派的主张;从组织形式上看,《庄子》中的寓言没有独立地位,只是夹杂于文中,而《韩非子》中的寓言却呈现出相对独立且结构宏大的群落体制;从创作方法上看,《庄子》中的寓言多奇幻玄虚、生动形象,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且题材较为广泛,自然的、历史的、现实的,各类题材应有尽有,而《韩非子》中的寓言多质朴平实、庄重峻峭,呈现出现实主义特征,寓言题材较为单一,大多出自历史典故;从形象塑造上看,《庄子》寓言中的形象既有人物,又有动植物甚至是无生物,而《韩非子》寓言刻画的形象绝大多数只有人物。“庄、韩寓言在用法上,在文学一般特点上相类似,但二人政治观、人生观、审美观不同,故寓言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多有不同:一是博大虚灵,一是阴深阻滞;一是超越本体,一是贯注世俗;一是哲学的,一是政治的;一是养生的,一是治人的;一是浪漫的,一是现实的;一是轻松快乐的;一是沉重愁苦的;一是平民的,一是政客的;一是自然的,一是人为的。”

《庄子》寓言通过奇伟瑰怪的想象,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与物的形象。这些人物,无论是古圣先贤,还是鸟兽虫鱼,都是庄子之“道”的体现和承载者,折射出庄子之“道”的内涵。有研究指出,庄子创作寓言形象的思维特征是:立象以尽意、象征隐喻、启悟性与生发性。语言是思维的载体,不同的语言形式反映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有的用简论来阐述政见与道德规范;有的用辨析来说明哲理观点;有的用智巧来探寻世界的奥妙;而庄子则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来宣扬道家观点。
 所谓庄子独特的思维方式指的就是“立象以尽意”的方式,通过寓言形象的塑造以表达深奥的哲学思想,即内涵极其丰富却难以言说的“道”,如在《知北游》中,庄子通过创造蝼蚁、稊稗、瓦璧、屎溺等寓言形象来说明“道”之无所不在。而《庄子》寓言中呈现出的形象形形色色,无所不包,既有山川河流、花鸟虫鱼,又有天地日月、人鬼神怪,既有对统治阶级的刻画,又有对劳动人民的描述,以此表达庄子或憎恶或歌颂的强烈情感。正是这种“立象以尽意”的思维方式,使得《庄子》的寓言形象呈现出一种意蕴深刻的特点,反过来,又是因为这种象征隐喻思维的运用使其寓言形象表现出言有尽而意无穷之特点。作为读者,不能仅仅停留在形象的表面,而应体悟到形象的象征隐喻意义。然而,由于庄子寓言形象具有多层面、多指向的特点,因此,寓言形象的象征隐喻意义往往是朦胧多义的,在形象的启发下,读者的思维可以自由驰骋,尽情感悟。
所谓庄子独特的思维方式指的就是“立象以尽意”的方式,通过寓言形象的塑造以表达深奥的哲学思想,即内涵极其丰富却难以言说的“道”,如在《知北游》中,庄子通过创造蝼蚁、稊稗、瓦璧、屎溺等寓言形象来说明“道”之无所不在。而《庄子》寓言中呈现出的形象形形色色,无所不包,既有山川河流、花鸟虫鱼,又有天地日月、人鬼神怪,既有对统治阶级的刻画,又有对劳动人民的描述,以此表达庄子或憎恶或歌颂的强烈情感。正是这种“立象以尽意”的思维方式,使得《庄子》的寓言形象呈现出一种意蕴深刻的特点,反过来,又是因为这种象征隐喻思维的运用使其寓言形象表现出言有尽而意无穷之特点。作为读者,不能仅仅停留在形象的表面,而应体悟到形象的象征隐喻意义。然而,由于庄子寓言形象具有多层面、多指向的特点,因此,寓言形象的象征隐喻意义往往是朦胧多义的,在形象的启发下,读者的思维可以自由驰骋,尽情感悟。
《庄子》的寓言形象有三类比较突出:庄子的自我形象、理想人物形象和畸人形象。
 庄子的自我形象多出现于庄子的外篇和杂篇当中,如《至乐》中的庄子鼓盆而歌、《列御寇》中的庄子将死、《外物》中的庄周借米、《秋水》中的庄子濮水边对话、《山木》中的庄子见魏王、《知北游》中的庄子答东郭子等,在这些庄子的自身形象里,庄子是一个轻视名利、了悟生死的智者,与道合一、自由自在。羽化翩跹则是庄子的理想人物形象,庄子在书中刻画出的至人、神人或真人,如《逍遥游》中的藐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又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些神人、真人、至人顺应自然规律,自适逍遥,超越无限,达到精神生命的绝对自由,而自由的逍遥无待正是庄子对“道”的理解,也是庄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庄子在书中还刻画了一批形怪神美的畸人形象,如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和恶人哀骀它等人,他们容貌丑陋、形体残缺,但他们却能守住生命的本质,重视精神生命与道的体悟。庄子对他们的德行赞誉有加,试图通过这种形体与精神的巨大反差来表达“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也体现了庄子道不远人,道在自然的观点。
庄子的自我形象多出现于庄子的外篇和杂篇当中,如《至乐》中的庄子鼓盆而歌、《列御寇》中的庄子将死、《外物》中的庄周借米、《秋水》中的庄子濮水边对话、《山木》中的庄子见魏王、《知北游》中的庄子答东郭子等,在这些庄子的自身形象里,庄子是一个轻视名利、了悟生死的智者,与道合一、自由自在。羽化翩跹则是庄子的理想人物形象,庄子在书中刻画出的至人、神人或真人,如《逍遥游》中的藐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又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些神人、真人、至人顺应自然规律,自适逍遥,超越无限,达到精神生命的绝对自由,而自由的逍遥无待正是庄子对“道”的理解,也是庄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庄子在书中还刻画了一批形怪神美的畸人形象,如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和恶人哀骀它等人,他们容貌丑陋、形体残缺,但他们却能守住生命的本质,重视精神生命与道的体悟。庄子对他们的德行赞誉有加,试图通过这种形体与精神的巨大反差来表达“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也体现了庄子道不远人,道在自然的观点。
《庄子》寓言形象的艺术特征可用三个词来概括:奇诡、宏阔、深妙。林云铭评价《庄子》之文是“文情飞舞,奇致横生”
 。《庄子》寓言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奇谲怪诞,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异于常人的思想行为。最典型的莫过于“庄子将死”和“庄子妻死”这两则寓言,表达了庄子对于生死的独特荒诞的思想认识。(2)超凡离俗的能工巧匠。《庄子》寓言中有一大批来自社会底层的能工巧匠,如庖丁、梓庆、轮扁、工倕、捶钩者、匠石等人物形象,庄子对他们多有褒扬,《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徐无鬼》中的“匠石运斤成风”等寓言就是很好的例证。(3)新奇夸张的变形人物。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庄子运用夸张手法塑造的一批畸形人形象,这些形象主要集中在《德充符》中,如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等。庄子通过夸张描写他人对于这些畸形人的态度来映衬他们的德行和才干,从而强调“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道理。其次,《庄子》塑造出的寓言形象神与物游、气势豪放,如大鹏形象、大鱼形象、“天籁”形象等,它们从庄子的大视野、大境界里喷涌而出,“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抟”
。《庄子》寓言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奇谲怪诞,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异于常人的思想行为。最典型的莫过于“庄子将死”和“庄子妻死”这两则寓言,表达了庄子对于生死的独特荒诞的思想认识。(2)超凡离俗的能工巧匠。《庄子》寓言中有一大批来自社会底层的能工巧匠,如庖丁、梓庆、轮扁、工倕、捶钩者、匠石等人物形象,庄子对他们多有褒扬,《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徐无鬼》中的“匠石运斤成风”等寓言就是很好的例证。(3)新奇夸张的变形人物。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庄子运用夸张手法塑造的一批畸形人形象,这些形象主要集中在《德充符》中,如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等。庄子通过夸张描写他人对于这些畸形人的态度来映衬他们的德行和才干,从而强调“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道理。其次,《庄子》塑造出的寓言形象神与物游、气势豪放,如大鹏形象、大鱼形象、“天籁”形象等,它们从庄子的大视野、大境界里喷涌而出,“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抟”
 。《庄子》寓言形象的第三个艺术特征是深妙,庄子创造寓言形象目的是为了说理,常常借助简单寻常之事来说明深邃的哲学道理,在庄子笔下,花鸟鱼虫、天地万物都可以具有人的思想,并谈论深奥的哲理,因此说,拟人化为《庄子》寓言形象奇谲诡怪的重要表现,如寓言“朝三暮四”“罔两问景”等。这些拟人化的寓言形象在表达蕴含深邃的哲理同时,又传递出一种神秘虚幻的色彩。
。《庄子》寓言形象的第三个艺术特征是深妙,庄子创造寓言形象目的是为了说理,常常借助简单寻常之事来说明深邃的哲学道理,在庄子笔下,花鸟鱼虫、天地万物都可以具有人的思想,并谈论深奥的哲理,因此说,拟人化为《庄子》寓言形象奇谲诡怪的重要表现,如寓言“朝三暮四”“罔两问景”等。这些拟人化的寓言形象在表达蕴含深邃的哲理同时,又传递出一种神秘虚幻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