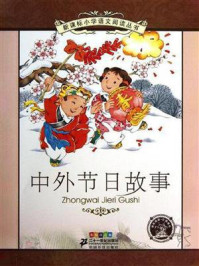上海等城市开埠通商后,西方文化娱乐元素开始逐渐渗入这些城市,打破了传统休闲娱乐消费模式在中国城市一统天下的格局。传统文化娱乐消费方式与西方文化娱乐消费方式开始在上海等城市碰撞、并存和融合,19 世纪后期这种趋势在上海、天津等主要通商口岸城市开始显现,以上海最为显著。
传统文化娱乐活动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不仅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特征且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各具特色的戏园、茶馆等不仅具有休闲娱乐功能,而且可以通过消费这些场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实现寄托乡愁、对家乡热爱等情感诉求。随着上海等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外来人口日渐增多,多种地方文化娱乐产品也向这些城市集聚,戏剧等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供给逐渐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消费需求也呈现不断增长趋势。
在近代中国,观看戏曲演出是各地居民的基本娱乐活动形式,就如清朝后期在中国居住半个世纪、跑遍大江南北的传教士约翰·麦高恩观察到的那样:“对中国人而言最受欢迎、最令人着迷的方式就是戏剧,虽然由于昂贵,普通老百姓负担不起,但中国的风俗是在空地上表演,因此每个喜爱看戏的人都可以尽情地观赏而不付任何费用。”
 一般市民时常可免费观看戏剧演出,如富人为父母等长辈祝寿、家中有重大喜事时,为让更多人分享他们的喜庆一般会请戏班子演戏酬宾。约翰·麦高恩还观察到当时中国富人的家门前搭起戏台,“笛鼓合奏的乐声通知邻人戏团已经准备来表演了。这一消息如野火般地传得很快,等演员们准备开始表演时,人们已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免费观看对他们而言亲切的表演”
一般市民时常可免费观看戏剧演出,如富人为父母等长辈祝寿、家中有重大喜事时,为让更多人分享他们的喜庆一般会请戏班子演戏酬宾。约翰·麦高恩还观察到当时中国富人的家门前搭起戏台,“笛鼓合奏的乐声通知邻人戏团已经准备来表演了。这一消息如野火般地传得很快,等演员们准备开始表演时,人们已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免费观看对他们而言亲切的表演”
 ,这种习俗即使在今天仍在中国多地存在。但中国戏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两广人喜爱粤剧,西北人偏爱秦腔,湖北人喜爱楚剧等。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汇聚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为满足来自不同地区人们观看戏剧的需要,提供各种各样地方剧种的演出场所应运而生。以上海为例,19 世纪 50年代就出现了专门表演昆剧等戏剧的场所——戏园
,这种习俗即使在今天仍在中国多地存在。但中国戏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两广人喜爱粤剧,西北人偏爱秦腔,湖北人喜爱楚剧等。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汇聚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为满足来自不同地区人们观看戏剧的需要,提供各种各样地方剧种的演出场所应运而生。以上海为例,19 世纪 50年代就出现了专门表演昆剧等戏剧的场所——戏园
 。19 世纪 60年代后江浙等地居民为避难或寻求商机等纷纷移居上海,难民中的有钱有闲群体是推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戏剧消费需求增长的主力。日本人纳富阶次郎在1862年所作的《上海杂记》中记录:“闻难民中多苏州之人,约有十余万众”,“上海本俗地,舞文弄墨者不多,偶来旅馆作风流之交者,皆难民中人。”
。19 世纪 60年代后江浙等地居民为避难或寻求商机等纷纷移居上海,难民中的有钱有闲群体是推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戏剧消费需求增长的主力。日本人纳富阶次郎在1862年所作的《上海杂记》中记录:“闻难民中多苏州之人,约有十余万众”,“上海本俗地,舞文弄墨者不多,偶来旅馆作风流之交者,皆难民中人。”
 19世纪后期上海在居民观看戏剧表演需求不断扩大的驱动下,各种戏馆茶园纷纷建立。同治五年(1866),英籍华人罗逸卿仿照北京戏园的样式,在上海租界内建造了第一座华人戏园(当时称为茶园)——满庭芳,该园是一座木结构二层楼,是当时上海设施最为先进的戏园之一,为招徕顾客,特地从天津邀请京剧演员到上海演出,实行一票制,即“楼上楼下每位票价一元”
19世纪后期上海在居民观看戏剧表演需求不断扩大的驱动下,各种戏馆茶园纷纷建立。同治五年(1866),英籍华人罗逸卿仿照北京戏园的样式,在上海租界内建造了第一座华人戏园(当时称为茶园)——满庭芳,该园是一座木结构二层楼,是当时上海设施最为先进的戏园之一,为招徕顾客,特地从天津邀请京剧演员到上海演出,实行一票制,即“楼上楼下每位票价一元”
 ,观众趋之若狂。有人称满庭芳开启了上海戏剧近代化发展的进程。满庭芳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上海戏剧消费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受其影响 1867年刘维忠(定海人)建造了丹桂茶园(也称丹桂轩)。为开拓市场,刘维忠亲自到北京邀请京剧名角到上海演出,还根据上海市民的消费心理和收入差别,按照座位的不同位置,采取差别定价营销策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设计了一些价格较廉的座位,使收入不高又热爱戏剧者也偶尔能消费一次,“开台楼上下佳座一律八角。包厢售六角,余下散座,价目较廉。因属比较名角,备受群众欢迎,盛况空前”
,观众趋之若狂。有人称满庭芳开启了上海戏剧近代化发展的进程。满庭芳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上海戏剧消费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受其影响 1867年刘维忠(定海人)建造了丹桂茶园(也称丹桂轩)。为开拓市场,刘维忠亲自到北京邀请京剧名角到上海演出,还根据上海市民的消费心理和收入差别,按照座位的不同位置,采取差别定价营销策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设计了一些价格较廉的座位,使收入不高又热爱戏剧者也偶尔能消费一次,“开台楼上下佳座一律八角。包厢售六角,余下散座,价目较廉。因属比较名角,备受群众欢迎,盛况空前”
 。丹桂轩因设备先进、名角荟萃,加上善于营销,一时间名声大噪,“桂园观剧”被当时上海人评为“沪北十景”之一,有竹枝词描绘其繁荣,“相传鞠部最豪奢,不待登场万口夸。一样梨园名弟子,来从京国更风华”
。丹桂轩因设备先进、名角荟萃,加上善于营销,一时间名声大噪,“桂园观剧”被当时上海人评为“沪北十景”之一,有竹枝词描绘其繁荣,“相传鞠部最豪奢,不待登场万口夸。一样梨园名弟子,来从京国更风华”
 。满庭芳、丹桂轩等新式京剧茶园与旧式茶园相比,装潢典雅、座位多且舒适,剧目、演出形式新颖,并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照明设备——煤气灯,一时间上海居民以及来往商旅、周边城市居民观看戏剧的热情被激发出来。在京剧获得成功的同时,昆剧、苏滩、猫儿戏(也称帽儿戏)、花鼓戏也纷纷设立固定的演出场所。成书于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沪游杂记》中记录:“文班唱昆曲皆姑苏大章、大雅两班所演,始于同治二年(1863)。自徽班登场而文班减色,京班出而徽班皆唱二黄。……丹凤园、同乐园亦以徽调间京腔。尚有帽儿戏、花鼓戏。”
。满庭芳、丹桂轩等新式京剧茶园与旧式茶园相比,装潢典雅、座位多且舒适,剧目、演出形式新颖,并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照明设备——煤气灯,一时间上海居民以及来往商旅、周边城市居民观看戏剧的热情被激发出来。在京剧获得成功的同时,昆剧、苏滩、猫儿戏(也称帽儿戏)、花鼓戏也纷纷设立固定的演出场所。成书于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沪游杂记》中记录:“文班唱昆曲皆姑苏大章、大雅两班所演,始于同治二年(1863)。自徽班登场而文班减色,京班出而徽班皆唱二黄。……丹凤园、同乐园亦以徽调间京腔。尚有帽儿戏、花鼓戏。”
 由上述可以看出,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不仅京剧消费有所增长,而且猫儿戏、花鼓戏、昆剧、粤剧等也都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反映了当时上海传统戏剧消费需求多元化发展情况。
由上述可以看出,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不仅京剧消费有所增长,而且猫儿戏、花鼓戏、昆剧、粤剧等也都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反映了当时上海传统戏剧消费需求多元化发展情况。
北京居民的戏剧消费也有所增长。慈禧太后等经常召京戏班进宫演出,王公贵族喜爱戏剧者甚多,“恭亲王溥伟喜观昆剧,能自唱,其左右亦能和之”,“内廷或颐和园之演剧,名优均须进内当差,若辈自称曰内奉”
 。王公仕宦或私蓄戏班,或叫“堂会”。“堂会”是指个人出资邀请演员在年节或喜、寿日在私宅或借饭庄、会馆、戏园等场所进行的专场演出。19 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的官僚富豪们时常邀请名伶为他们进行专场演出,有竹枝词感叹因“堂会”的流行导致戏园观众减少,“时兴小戏得人和,四大徽班势倒戈。虽是园中不上座,原图堂会彩钱多”
。王公仕宦或私蓄戏班,或叫“堂会”。“堂会”是指个人出资邀请演员在年节或喜、寿日在私宅或借饭庄、会馆、戏园等场所进行的专场演出。19 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的官僚富豪们时常邀请名伶为他们进行专场演出,有竹枝词感叹因“堂会”的流行导致戏园观众减少,“时兴小戏得人和,四大徽班势倒戈。虽是园中不上座,原图堂会彩钱多”
 。更有不少八旗子弟、纨绔子弟、官僚等终日流连戏园,有竹枝词形容:“茶园楼上列纷纷,宦款游来气炎熏”
。更有不少八旗子弟、纨绔子弟、官僚等终日流连戏园,有竹枝词形容:“茶园楼上列纷纷,宦款游来气炎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层社会的示范引领之下,市民纷纷效尤,有竹枝词描绘京师戏剧消费需求非常旺盛的情景,“典衣看戏是京师,谊重亲朋莫可辞”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上层社会的示范引领之下,市民纷纷效尤,有竹枝词描绘京师戏剧消费需求非常旺盛的情景,“典衣看戏是京师,谊重亲朋莫可辞”
 。
。
戏剧消费需求增长不仅在上海、北京出现,而且在保定、镇江、广州等城市也呈现增长趋势,这些城市都出现了固定的、商业性戏馆,1874年《申报》报道:“戏馆之设,京师为最,次则保定、天津、苏州亦然,余如各省城市乡村亦均有之。租界如镇江、上海皆有数处。”
 广州设立固定戏园的时间较晚,在戏剧消费需求增长的带动下,“道光时有江南人史某始创庆春园……未几,怡园、锦园、庆丰、听春诸园相继起”
广州设立固定戏园的时间较晚,在戏剧消费需求增长的带动下,“道光时有江南人史某始创庆春园……未几,怡园、锦园、庆丰、听春诸园相继起”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多地城市创建的戏园因地方官员怕滋生是非,往往是屡禁屡开,旋开旋闭。如上海虽屡次禁止开戏馆,但奏效甚微,因租界当局不配合,华界如果禁戏,戏园就迁移到租界内开办,也因此出现上海华界内越是禁戏,租界内戏园越多、生意越好。1874年《申报》围绕戏园的禁与不禁,发表了多篇文章,如 11 月 3 日刊登的《论戏园》一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戏园的益处,“大则可以尽孝养,中则可以寓劝惩,小则可以破忧愁。或因所谋不遂,或因远游他乡,或因劳苦终日,忧闷长宵无可以解忧者,自有戏园之设,亦可藉为消遣之地,较之嫖赌之事,不至倾家荡产,伤生败名。故不但日戏不必禁,即夜戏亦不必禁。何也?农工商贾日有正业,惟长夜无聊,始能为此耳”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多地城市创建的戏园因地方官员怕滋生是非,往往是屡禁屡开,旋开旋闭。如上海虽屡次禁止开戏馆,但奏效甚微,因租界当局不配合,华界如果禁戏,戏园就迁移到租界内开办,也因此出现上海华界内越是禁戏,租界内戏园越多、生意越好。1874年《申报》围绕戏园的禁与不禁,发表了多篇文章,如 11 月 3 日刊登的《论戏园》一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戏园的益处,“大则可以尽孝养,中则可以寓劝惩,小则可以破忧愁。或因所谋不遂,或因远游他乡,或因劳苦终日,忧闷长宵无可以解忧者,自有戏园之设,亦可藉为消遣之地,较之嫖赌之事,不至倾家荡产,伤生败名。故不但日戏不必禁,即夜戏亦不必禁。何也?农工商贾日有正业,惟长夜无聊,始能为此耳”
 。由《申报》的报道可以看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上海等城市居民在闲暇时观看戏剧演出的需求和愿望增强,也反映了戏剧消费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即视看戏为“玩物丧志”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开明人士已经认识到戏剧消费的经济功能、教育功能、社会功能,即观剧能为戏剧演员等提供谋生机会,且能帮助观剧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消遣解闷,长辈生日时演戏还可以达到考亲目的。
。由《申报》的报道可以看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上海等城市居民在闲暇时观看戏剧演出的需求和愿望增强,也反映了戏剧消费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即视看戏为“玩物丧志”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开明人士已经认识到戏剧消费的经济功能、教育功能、社会功能,即观剧能为戏剧演员等提供谋生机会,且能帮助观剧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消遣解闷,长辈生日时演戏还可以达到考亲目的。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等城市除戏剧消费需求呈现增长趋势外,其他本土娱乐消费如茶馆品茗、酒楼小酌、青楼行乐等也呈现繁荣景象。
休闲娱乐与餐饮、社交消费一体化发展使酒楼、饭店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消遣娱乐场所。当时商人商洽生意,朋友增进情感往往选择在酒楼、饭店等场馆内进行。一些酒楼、饭店为招揽顾客附设各种娱乐设施,如弹子房、棋牌室等,还可以叫妓女陪酒和演员来演唱。葛元煦在所著的《沪游杂记》中指出:“天津酒馆自同兴、同新两楼既闭,惟庆兴楼最著。新新楼、复兴园为金陵馆之翘楚。宁波馆虽多,皆自郐以下,鸿运、益庆差堪比数。泰和馆为沪人所开,菜兼南北,座拥婵娟,特为繁盛。津馆围碟点心不列账,统归堂彩。金陵馆叫局堂彩非一元即八角,故庆兴、泰和两馆出局较多。”

茶馆不仅是解渴消乏的地方,更是大众的休闲娱乐空间,交流商业信息、结交朋友的场所。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描述了上海茶馆众多,竞争激烈,之前生意兴隆的一洞天已经关门,丽水台也已经改营他业,松风阁、一壶春等茶楼异军突起,茶客众多,“同治初(19 世纪 60年代)大马路红栅外有一洞天,三茅阁桥沿河有丽水台,皆杰阁三层,楼宇轩敞。一洞天已闭歇,丽水台改寻常楼屋。惟松风阁以茶胜,宝善园以地胜。大马路之一壶春,宝善街之渭园、桂芳阁均极热闹。城中庙园茶肆十居其五,惟湖心亭最佳”
 。成书于 1893年的《沪游梦影》描述上海茶馆顾客盈门盛况,且有女性可以自由到茶馆品茗,“夫别处茶室之设不过涤烦解渴,聚语消闲,而沪上为宾主酬应之区、士女游观之所,每茶一盏不过二三十钱,而可以亲承款洽,近挹丰神,实为生平艳福”
。成书于 1893年的《沪游梦影》描述上海茶馆顾客盈门盛况,且有女性可以自由到茶馆品茗,“夫别处茶室之设不过涤烦解渴,聚语消闲,而沪上为宾主酬应之区、士女游观之所,每茶一盏不过二三十钱,而可以亲承款洽,近挹丰神,实为生平艳福”
 。可见,19 世纪 90年代上海茶馆已发展成为集大众聚会、酬宾、消遣、社交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场所。
。可见,19 世纪 90年代上海茶馆已发展成为集大众聚会、酬宾、消遣、社交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场所。
19 世纪后期西人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租界内建造跑马场、西式戏院、弹子房、西餐厅、咖啡馆等休闲娱乐场所,这些场馆最初是为满足外侨休闲娱乐消费需要而建的,但后来吸引许多华人前往消费。这一时期引起中国人兴趣的西式娱乐活动主要有观看赛马、马戏、影戏以及打弹子等。
1850年英国人霍格等在上海组织跑马总会,建造了中国第一个跑马场,因赛马活动与戏剧等娱乐形式相比,具有新颖性、竞技性、刺激性等特征,很快赢得上海等城市部分居民的喜爱。1859年王韬日记中就记录了上海很多华人观看赛马情况,19 世纪 60年代后钟爱赛马活动的华人越来越多。冯桂芬之子冯芳缉同治元年(1861)的日记中记录他在上海观洋人赛马的感受:“入其围中,至其所谓演舞台侧,略伫立顷,见四骑竞逐,衣各异色。俄又见二骑,皆捷如飞,诚不愧健步也。台侧列夷乐一队,其音沉着幽咽,亦觉入耳一新,士女云集,举国若狂。”
 到上海的商旅等如果赶上赛马活动,一般都要一睹为快,如 1879年王锡麒非常幸运地赶上了春、秋两次赛马活动,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观看赛马的情景,如春季赛马“游人云集,毂击肩摩,西人衣五色衣,稳坐马上,红旗一挥,奋辔争驱,星驰电掣间,已三四里。尽一周圈,乃止”
到上海的商旅等如果赶上赛马活动,一般都要一睹为快,如 1879年王锡麒非常幸运地赶上了春、秋两次赛马活动,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观看赛马的情景,如春季赛马“游人云集,毂击肩摩,西人衣五色衣,稳坐马上,红旗一挥,奋辔争驱,星驰电掣间,已三四里。尽一周圈,乃止”
 。需要说明的是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观看赛马者已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既有文人雅士,也有妓女负贩者,如《沪游杂记》中记录赛马的观众来自社会上各个群体,“大马路西,西人辟驰马之场。周以短栏,所以防奔轶。春秋佳日,各赛跑马一次。每次三日,午起酉止。或三四骑,或六七班骑,衣则有黄、红、紫、绿之异,马则有骊黄、骝骆之别。并辔齐驱、风驰电掣。场西设二厂备校阅,以马至先后分胜负。第三日增以跳墙、跳沟、跳栏等技,是日观者上自士夫下及负贩,肩摩踵接,后至者几无置足处:至于油壁香车、侍儿娇倚者,则皆南朝金粉、北里胭脂也,鬓影衣香,令人真个销魂矣”
。需要说明的是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观看赛马者已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既有文人雅士,也有妓女负贩者,如《沪游杂记》中记录赛马的观众来自社会上各个群体,“大马路西,西人辟驰马之场。周以短栏,所以防奔轶。春秋佳日,各赛跑马一次。每次三日,午起酉止。或三四骑,或六七班骑,衣则有黄、红、紫、绿之异,马则有骊黄、骝骆之别。并辔齐驱、风驰电掣。场西设二厂备校阅,以马至先后分胜负。第三日增以跳墙、跳沟、跳栏等技,是日观者上自士夫下及负贩,肩摩踵接,后至者几无置足处:至于油壁香车、侍儿娇倚者,则皆南朝金粉、北里胭脂也,鬓影衣香,令人真个销魂矣”
 。
。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天津的外侨在租界内也建造了赛马场,每年春、秋佳日居住在天津的外侨都分别举办赛马活动一次,每次活动三日。每当举办赛马活动,“人声哗然,蹄声隆然,各国之旗飘飘然,各种乐鸣呜然,跑马棚边不啻如火如荼矣。倾城士女联袂而往,观者或驾香车,或乘宝马,或暖轿停留,或小车独驾,衣香鬓影,尽态极妍,白夹青衫,左顾右盼,听奏从军之乐,畅观出猎之图,较之钱塘看潮,万人空巷,殆有过之而无不及焉。此数日,各洋行皆杜门谢客,海关亦封关停办公事”
 。古润招隐山人曾作诗歌咏天津西人举办赛马活动时观众的狂热情景:“草色平铺赛马场,骅骝开道竞飞扬,西人角逐成年例,如堵来观举国狂”
。古润招隐山人曾作诗歌咏天津西人举办赛马活动时观众的狂热情景:“草色平铺赛马场,骅骝开道竞飞扬,西人角逐成年例,如堵来观举国狂”
 。
。
19 世纪 50年代上海租界内西人建造了弹子房,王韬和朋友们偶尔驻足观看,但到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天津等城市一些大茶楼、大饭店、大酒楼等休闲娱乐场所内已经增设弹子房,消费对象主要为华人。1882年《申报》刊登的《观打弹记》中描述华人打弹子热情高涨情景:“外国游戏之事,有所谓打弹者,其弹有大有小”,因一品香拆建,“华众会(青莲阁前身——引者注)生意遂由是大盛,去年腊底至今年开正以来,竞至游人如织,入或不能出,肩为之摩,趾为之踵”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中国人创办的西餐厅如一品香、茶楼如华众会中都设有弹子房。有些中国人打弹子的水平甚至高于西人,1886年《申报》一文记载:“打弹一事,西人之所以为游戏之具者也。行入中国曾无几时而华人之工于打弹者殊不乏人。大弹则心力俱准,一举而击倒十椿;小弹则曲折如意,一手而连数十。如是者不可胜数。”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中国人创办的西餐厅如一品香、茶楼如华众会中都设有弹子房。有些中国人打弹子的水平甚至高于西人,1886年《申报》一文记载:“打弹一事,西人之所以为游戏之具者也。行入中国曾无几时而华人之工于打弹者殊不乏人。大弹则心力俱准,一举而击倒十椿;小弹则曲折如意,一手而连数十。如是者不可胜数。”
 不仅酒楼、茶楼附设有弹子房,而且张园、愚园等私家园林也设有弹子房。何荫柟光绪十年(1886)年到上海出差,日记中记录了观赏打弹子情形,“文达、宝生约游街肆,寓目皆属夷境。……绕西园一游,看弹子戏,此亦供纨绔一时之兴者耳”
不仅酒楼、茶楼附设有弹子房,而且张园、愚园等私家园林也设有弹子房。何荫柟光绪十年(1886)年到上海出差,日记中记录了观赏打弹子情形,“文达、宝生约游街肆,寓目皆属夷境。……绕西园一游,看弹子戏,此亦供纨绔一时之兴者耳”
 。
。
19 世纪 80年代外国的马戏、魔术、戏剧等在上海已受到部分市民的欢迎。马戏是杂技的一种,原指人骑在马上所进行的表演,现指各种野兽、驯禽表演的统称。“马戏”一词在中国出现于汉桓宽的《盐铁论·散不足》:“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唐朝时马戏在中国已达到很高技艺。清朝咸丰帝每到正月十五日都要观看马戏表演
 。19 世纪后期西方的马戏团偶尔会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演出,一般演出前都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葛元煦曾描绘了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马戏在上海的精彩表演以及市民纷纷前往观看的情景,“西人马戏以大幕为幄,高八九丈,广蔽数亩。中辟马场,其形如球,环列客座。内奏西乐,乐作,一人扬鞭导马入,绕场三匝,环走如飞,呵之立止。复扬鞭作西语,马以两前足盘旋行,后足交互如铁练状。旋以手帕埋泥中,使马寻觅,马即衔帕出场。内又设一桌,一杯内注以酒,摇铜铃一声,马屈后足作人坐,以前足距案衔杯而饮。少间一西女牵一马,锦鞍无镫,女则窄衣短袖,跃登其上,疾驰如矢。女在马上作蹴踏跳踯诸戏,有时翘一足为商羊舞,或侧身倒挂似欲倾跌者。复使人张布立马前,马从布下驰,女起跃仍立马上,三跃三过,不爽分寸。又一西人锦衣驰马,矫健作势,与女略同。使人执巨圈特立,马自圈下驰过,人则由圈内跃登马上,自一圈至六圈,轻捷异常。其余诸戏,备诸变态,绝迹飞行,诚令人目不及瞬、口不能状也”
。19 世纪后期西方的马戏团偶尔会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演出,一般演出前都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葛元煦曾描绘了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马戏在上海的精彩表演以及市民纷纷前往观看的情景,“西人马戏以大幕为幄,高八九丈,广蔽数亩。中辟马场,其形如球,环列客座。内奏西乐,乐作,一人扬鞭导马入,绕场三匝,环走如飞,呵之立止。复扬鞭作西语,马以两前足盘旋行,后足交互如铁练状。旋以手帕埋泥中,使马寻觅,马即衔帕出场。内又设一桌,一杯内注以酒,摇铜铃一声,马屈后足作人坐,以前足距案衔杯而饮。少间一西女牵一马,锦鞍无镫,女则窄衣短袖,跃登其上,疾驰如矢。女在马上作蹴踏跳踯诸戏,有时翘一足为商羊舞,或侧身倒挂似欲倾跌者。复使人张布立马前,马从布下驰,女起跃仍立马上,三跃三过,不爽分寸。又一西人锦衣驰马,矫健作势,与女略同。使人执巨圈特立,马自圈下驰过,人则由圈内跃登马上,自一圈至六圈,轻捷异常。其余诸戏,备诸变态,绝迹飞行,诚令人目不及瞬、口不能状也”
 。1882年 6 月 15 日至 8 月 16 日,美国著名马戏团——车利尼马戏团在上海虹口巡捕房后面搭建一个大棚进行马戏表演,几乎场场爆满,当时的票价为:官房收洋银 13 元(可坐 6 人),头等位置每位 2 元,有椅垫的二等位置每位 1 元,三等位置(板位)5 角
。1882年 6 月 15 日至 8 月 16 日,美国著名马戏团——车利尼马戏团在上海虹口巡捕房后面搭建一个大棚进行马戏表演,几乎场场爆满,当时的票价为:官房收洋银 13 元(可坐 6 人),头等位置每位 2 元,有椅垫的二等位置每位 1 元,三等位置(板位)5 角
 ,这对于当时居民的收入水平而言,是非常高的价格,但还是有众多市民不惜为之倾囊,“每夜观者达到二三千。青楼妙妓,菊部雏伶,锦障银鞯,络绎不绝……大家眷属,亦间有肩舆而至者,真有万人空巷斗新妆之概。此外尚有袋鼠、人熊之属,不能演剧,惟备赏玩而已。据云:此种戏术,沪上已演过数次,惟车利尼班最为出色云”
,这对于当时居民的收入水平而言,是非常高的价格,但还是有众多市民不惜为之倾囊,“每夜观者达到二三千。青楼妙妓,菊部雏伶,锦障银鞯,络绎不绝……大家眷属,亦间有肩舆而至者,真有万人空巷斗新妆之概。此外尚有袋鼠、人熊之属,不能演剧,惟备赏玩而已。据云:此种戏术,沪上已演过数次,惟车利尼班最为出色云”
 。
。
受中国居民欢迎的外国娱乐活动还有很多,如电光影戏,也就是早期的幻灯片。葛元煦也描述了当时电光影戏在上海演出时市民前往观看的热情及感受:“西人影戏,台前张白布大幔一,以水湿之。中藏灯匣,匣面置洋画,更番叠换,光射布上,则山水、树木、楼阁、人物、鸟兽、虫鱼,光怪陆离诸状毕现。……恍疑身历其境,颇有可观。”
 外国影戏深受上海大众的欢迎,上座率很高,1875年《申报》曾报道说:“近来月桂、金桂两茶园均演外国影戏,已列前报。乃昨悉富春茶园亦于今晚开演奇巧影戏,并用电器引火,格外光明,从此,领异标新,争奇斗胜。”
外国影戏深受上海大众的欢迎,上座率很高,1875年《申报》曾报道说:“近来月桂、金桂两茶园均演外国影戏,已列前报。乃昨悉富春茶园亦于今晚开演奇巧影戏,并用电器引火,格外光明,从此,领异标新,争奇斗胜。”

设在租界内的外国剧院也有华人前往观看。1874年西式风格的新兰心戏院建成,设有 700 多个座位,“院内宏阔、层楼整饬、华丽奇巧,便于观看,快畅安逸非常”
 ,“华人亦有往观者。而西人演戏,于唱歌跳舞甚为注意,且男演男戏,女演女戏……惟不常演耳”
,“华人亦有往观者。而西人演戏,于唱歌跳舞甚为注意,且男演男戏,女演女戏……惟不常演耳”
 。除了一些西方艺人常来华演出外,也偶尔有日本戏班到上海、天津等城市演出。
。除了一些西方艺人常来华演出外,也偶尔有日本戏班到上海、天津等城市演出。
魔术表演也受到部分中国人的欢迎。1874年英国魔术师瓦纳到上海演出,因运用对于中国人来说新奇的光电技术,让观众耳目一新,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看,“西人戏术以瓦纳所演为最奇,大约善用电气兼驱使搬运之法。或以鼓悬空,相离丈余将槌虚击,鼓即应声而响,使座客遥击亦然。又以小匣置客座,借客洋蚨数枚藏匣内,台中设玻璃盏一,术师持小棒念咒指匣,若令匣中之洋飞入盏内者。少顷则见空中有洋随棒所指,或疾或徐逐次入盏内,铿然有声。令客启匣,则空所有矣”
 。这次魔术表演活动《绛芸馆日记》中有记录:“四月二十一日朋友邀丹桂园,看西国术师演戏法、隐戏,新颖异常,颇觉悦目。”
。这次魔术表演活动《绛芸馆日记》中有记录:“四月二十一日朋友邀丹桂园,看西国术师演戏法、隐戏,新颖异常,颇觉悦目。”

此外,19 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很多西式娱乐活动在上海等城市出现,如体育娱乐。体育活动除健身功能外,还具有振奋民族精神、休闲娱乐等功能。咸丰十年(1860)外侨建立运动事业基金,成立上海总会、游泳总会、划船总会、高尔夫球总会等组织,并修建运动场馆。外侨在上海举办划船比赛活动始于同治二年(1863),光绪九年四月(1884)姚觐元途经上海,“观西人跑船之戏”
 。再如上海市民及来沪的商旅、学子等,以乘坐马车游玩为娱乐消费时尚,葛元煦也描述了当时乘马车主要人群、价格、游览路线等,“西人马车有双轮、四轮者,有一马、两马者。其式随意构造,宜雨宜晴,各尽其妙。近来华人设税车厂,驰驱半日,价约洋银两饼。贾客倡家往往税坐游行,近则沿黄浦、绕马路,远则至徐家汇、静安寺”
。再如上海市民及来沪的商旅、学子等,以乘坐马车游玩为娱乐消费时尚,葛元煦也描述了当时乘马车主要人群、价格、游览路线等,“西人马车有双轮、四轮者,有一马、两马者。其式随意构造,宜雨宜晴,各尽其妙。近来华人设税车厂,驰驱半日,价约洋银两饼。贾客倡家往往税坐游行,近则沿黄浦、绕马路,远则至徐家汇、静安寺”
 。可见,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的商人等以乘马车游洋场为时尚。19 世纪 90年代风和日丽时,乘坐马车游乐的人数非常多,还带动了马车租赁业务的快速发展,“向闻马车惟欧洲巨贾得以用之,今则华人设厂雇税,多至二千多乘……马车非马路不行,洋场大路,其平如掌。当夫风日晴和,偕二三知己,沿黄浦滩,登品泉楼,见夫裙屐少年或携仙眷,或挟歌姬,无不绣毂雕轮,络绎争飞”
。可见,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的商人等以乘马车游洋场为时尚。19 世纪 90年代风和日丽时,乘坐马车游乐的人数非常多,还带动了马车租赁业务的快速发展,“向闻马车惟欧洲巨贾得以用之,今则华人设厂雇税,多至二千多乘……马车非马路不行,洋场大路,其平如掌。当夫风日晴和,偕二三知己,沿黄浦滩,登品泉楼,见夫裙屐少年或携仙眷,或挟歌姬,无不绣毂雕轮,络绎争飞”
 。
。
19 世纪 80年代私家园林逐渐发展成为上海市民的重要休闲娱乐空间。申园、愚园、徐园、张园以及邑庙内的东、西园等不仅绿树成荫、回廊曲折,而且建造有茶楼、弹子房、酒楼、戏园、饭店等设施,其中以愚园、徐园、张园独盛
 。邑庙内有东、西两园,东园即内园,只有逢佳节,或兰花会、荷花会、菊花会期间才开启园门,任人游览。黄懋材在《沪游脞记》中记录:“沪上人家善养兰。每年四月初间,为兰花会于豫园(即西园,为前明潘允庵所建,后潘姓式微,归邑庙,改名为西园——引者注)。园在城隍殿后,一目内园,有延清楼,湖心阁诸胜,茶房酒肆及庙前东西二街,摆列兰畹俱满,名香异种,角胜争奇,士女游观杂沓,每至午夜方散。惟朱兰最贵,亲朋相与为贺。”
。邑庙内有东、西两园,东园即内园,只有逢佳节,或兰花会、荷花会、菊花会期间才开启园门,任人游览。黄懋材在《沪游脞记》中记录:“沪上人家善养兰。每年四月初间,为兰花会于豫园(即西园,为前明潘允庵所建,后潘姓式微,归邑庙,改名为西园——引者注)。园在城隍殿后,一目内园,有延清楼,湖心阁诸胜,茶房酒肆及庙前东西二街,摆列兰畹俱满,名香异种,角胜争奇,士女游观杂沓,每至午夜方散。惟朱兰最贵,亲朋相与为贺。”
 邑庙西园,“池心建亭,左右翼以石桥,名曰九曲桥;又有香雪堂、三棂堂、萃雅堂、点春园诸名胜。园西北隅亦有巨石迭作峰峦磴道,盘旋而上。沪地无山,重九妇女登高者多集于此。惜园内竞设有茗室及各色店铺,竞成市会,而凡山人墨客、江湖杂技亦皆托足其中”
邑庙西园,“池心建亭,左右翼以石桥,名曰九曲桥;又有香雪堂、三棂堂、萃雅堂、点春园诸名胜。园西北隅亦有巨石迭作峰峦磴道,盘旋而上。沪地无山,重九妇女登高者多集于此。惜园内竞设有茗室及各色店铺,竞成市会,而凡山人墨客、江湖杂技亦皆托足其中”
 。申园在静安寺西隅,“中构洋楼,四周花木,右偏并筑台榭、凿芳池,后设弹子房,任客嬉戏”
。申园在静安寺西隅,“中构洋楼,四周花木,右偏并筑台榭、凿芳池,后设弹子房,任客嬉戏”
 。也是园,亦名南园,祭祀文帝、斗母诸神,园中荷池广数亩,花开时上海市民纷纷前往观看。
。也是园,亦名南园,祭祀文帝、斗母诸神,园中荷池广数亩,花开时上海市民纷纷前往观看。
不少学者认同酒楼、饭店是近代中国城市的重要娱乐空间,如唐艳香的博士论文《饭店与上海城市生活(1843—1949)》探讨了近代上海饭店与城市社会发展、娱乐空间发展之间的关系
 。邹振环提出西餐馆就像一扇直观西洋异质文化的窗口,显现了西方物质与精神的综合形象
。邹振环提出西餐馆就像一扇直观西洋异质文化的窗口,显现了西方物质与精神的综合形象
 。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D.甘博,1918年 9 月至 1919年 12 月对北京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调查,他调研后指出“餐馆几乎是每个中国城市的社交和娱乐中心”
。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D.甘博,1918年 9 月至 1919年 12 月对北京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调查,他调研后指出“餐馆几乎是每个中国城市的社交和娱乐中心”
 。楼嘉军把 20 世纪 30年代上海的娱乐活动场所归纳为 10 类,其中将茶楼(茶馆)、酒吧、咖啡馆归为一类,即“娱乐餐饮类”
。楼嘉军把 20 世纪 30年代上海的娱乐活动场所归纳为 10 类,其中将茶楼(茶馆)、酒吧、咖啡馆归为一类,即“娱乐餐饮类”
 。课题组也认同上述观点,即酒楼饭店等餐饮场所是中国人的重要休闲娱乐场所。
。课题组也认同上述观点,即酒楼饭店等餐饮场所是中国人的重要休闲娱乐场所。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崇洋消费需求的影响下,西餐馆
 已经发展成为上海、天津等城市中高收入阶层的重要社交消遣场所。西餐馆一般提供弹子房等娱乐产品或服务,“外国菜馆为西人宴会之所,开设外虹口等处,抛球打牌皆可随意为之。大餐必集数人,先期预定,每人洋银三枚。便食随时,不拘人数,每人洋银一枚。酒价皆另给。大餐食品多取专味,以烧羊肉、各色点心为佳,华人间亦往食焉”
已经发展成为上海、天津等城市中高收入阶层的重要社交消遣场所。西餐馆一般提供弹子房等娱乐产品或服务,“外国菜馆为西人宴会之所,开设外虹口等处,抛球打牌皆可随意为之。大餐必集数人,先期预定,每人洋银三枚。便食随时,不拘人数,每人洋银一枚。酒价皆另给。大餐食品多取专味,以烧羊肉、各色点心为佳,华人间亦往食焉”
 。1892年《申报》对当时崇洋现象做了概括,指出“饮馔也,山珍海错非不鲜肥,而必欲以番菜为适口”
。1892年《申报》对当时崇洋现象做了概括,指出“饮馔也,山珍海错非不鲜肥,而必欲以番菜为适口”
 。《绛芸馆日记》的著者情况不详,他日记中记录了光绪六年(1880)到东洋茶室喝茶的愉快心情,“诣新开东洋茶室,更上楼啜茗,与中国稍异。每茶客各一小杯,杯下垫一盆。杯中伫茗,另由东洋糖点各一盆,百合桂元汤各一碗,用东洋女孩斟茶伺候,每客计价二角二分,别开生面,亦一乐也”
。《绛芸馆日记》的著者情况不详,他日记中记录了光绪六年(1880)到东洋茶室喝茶的愉快心情,“诣新开东洋茶室,更上楼啜茗,与中国稍异。每茶客各一小杯,杯下垫一盆。杯中伫茗,另由东洋糖点各一盆,百合桂元汤各一碗,用东洋女孩斟茶伺候,每客计价二角二分,别开生面,亦一乐也”
 。王锡麒光绪五年(1879)记录了他在上海洋酒吧品尝洋酒的愉悦感受:“乘马车游徐家汇,在黄浦之东,洋楼数十间,花木缤纷,铺设精洁,外国就馆也。有洋人携洋妇二在彼宴聚,园丁不令入。云来饮外国酒者,始含笑谢。入屋,洋酒数十种,菜蔬十余味,别有风致。洋妇顾其类谈笑,毫不作羞缩态。余饮蒲(葡)萄酿二盏,凉沁心脾。”
。王锡麒光绪五年(1879)记录了他在上海洋酒吧品尝洋酒的愉悦感受:“乘马车游徐家汇,在黄浦之东,洋楼数十间,花木缤纷,铺设精洁,外国就馆也。有洋人携洋妇二在彼宴聚,园丁不令入。云来饮外国酒者,始含笑谢。入屋,洋酒数十种,菜蔬十余味,别有风致。洋妇顾其类谈笑,毫不作羞缩态。余饮蒲(葡)萄酿二盏,凉沁心脾。”

传教士麦高恩观察到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存在两大宗教力量,即着迷于祖先崇拜和菩萨等神明的崇拜,他指出:“在中国,每家都供奉着至少一尊神像,以作为家庭的守护神,有的甚至会在家里供奉好几尊神像。中国的城市里有许多寺庙,里面供奉着人们耳熟能详的菩萨。有一些造价昂贵,还有些神像需要不断修缮。这些经费都来自平民百姓的捐赠。”
 在各种神明的诞辰,各地城市都有信徒到寺庙祭拜,如上海,“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后诞,粤、闽客商及海船皆演剧伸敬。三月二十八日为城隍夫人诞,乡镇妇女进香甚众;六月二十三日为火神诞,大东门内街市店铺皆悬灯结彩;二十四日为雷祖诞,庙在新北门内,毗连丹凤楼,为小穹窿;七月底为地藏王诞,庵在大东门南城脚;二、六、九月大士成道及诞辰,新北门内沈香阁、大马路红庙香火最盛”
在各种神明的诞辰,各地城市都有信徒到寺庙祭拜,如上海,“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后诞,粤、闽客商及海船皆演剧伸敬。三月二十八日为城隍夫人诞,乡镇妇女进香甚众;六月二十三日为火神诞,大东门内街市店铺皆悬灯结彩;二十四日为雷祖诞,庙在新北门内,毗连丹凤楼,为小穹窿;七月底为地藏王诞,庵在大东门南城脚;二、六、九月大士成道及诞辰,新北门内沈香阁、大马路红庙香火最盛”
 。在庙会期间,游客众多,如上海龙华寺,三月十五日为龙华会,“香火极盛”
。在庙会期间,游客众多,如上海龙华寺,三月十五日为龙华会,“香火极盛”
 。
。
这一时期上海等城市吸食鸦片、赌博、色情等不健康、不正当消遣需求极为旺盛。如吸食鸦片者众多,由上面能看出王韬的朋友中多人对鸦片成瘾,且认为是“一乐”。1862年一日本人在上海观察到“清国近几年,吃鸦片者甚多,官府遂不能制止。此于今之上海,以吴煦为首,官吏皆吃鸦片”,“清人云‘鸦片烟味甚美’,然其害甚大,危及人命”
 。19 世纪后期在烟馆吸食鸦片者不断增多的刺激下,烟室在上海租界内急剧增加,据 1872年《申报》报道,当时租界内烟馆有 1700 余家
。19 世纪后期在烟馆吸食鸦片者不断增多的刺激下,烟室在上海租界内急剧增加,据 1872年《申报》报道,当时租界内烟馆有 1700 余家
 。《申报》1873年 4 月 7 日刊登一篇题为《申江陋习》的文章,列出的几大耻辱,其中一耻就是“狎么二妓也”。“么二”指次等妓女,“长三”为高等妓女。《青楼二十六则》规定:“长三,亦名住家,加茶碗及侍酒、住夜皆洋三元,为长三。”
。《申报》1873年 4 月 7 日刊登一篇题为《申江陋习》的文章,列出的几大耻辱,其中一耻就是“狎么二妓也”。“么二”指次等妓女,“长三”为高等妓女。《青楼二十六则》规定:“长三,亦名住家,加茶碗及侍酒、住夜皆洋三元,为长三。”
 袁翔甫在《望江南》词中也描述上海狎妓成风,且有等级之别,“申江好,妓室等琼闺。旧好新知分冷热,长三么二判高低。身价也难齐”
袁翔甫在《望江南》词中也描述上海狎妓成风,且有等级之别,“申江好,妓室等琼闺。旧好新知分冷热,长三么二判高低。身价也难齐”
 。
。
有些人甚至视吃喝嫖赌为正当生活方式。为方便纨绔子弟等的吃喝玩乐,19 世纪 80年代上海的烟室、青楼、茶楼、酒楼一体化发展。约成书于 1893年的《沪游梦影》中指出:“今日租界中大小烟间鳞次栉比”,为招揽顾客,烟间装修得富丽堂皇,并聘用女堂倌,如眠云阁、南诚信“画栋雕梁,枕榻几案、灯盘茗碗,无不华丽精工,而复庭设中外之芳菲,室列名人之书画。夏则遍张风幔,不知火伞之当空;冬则遍设火筒,不知冰霜之著地”,“有以烟间兼酒楼者,大马路之最乐居是也;有以烟间兼茶室者,四马路之一层楼、五层楼、青莲阁是也;有以烟间兼书场者,华众会、论交楼、皆谊楼是也。风潇雨晦之际,一榻横陈,两友对叙,仅费青蚨百余片,即可流连半日,亦为人生乐事”
 。
。
多位外国传教士都提出教育普及程度低是造成赌博、鸦片在中国各地城市盛行的根本原因,如麦高恩提出除了极少数的家庭外几乎没有书籍、杂志,对于年轻人来说,“在漫长的冬夜,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打发时间。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可玩的,难怪他们只能找到两种消磨时间的方法,那就是赌博和吸鸦片。”
 因上海、天津等城市移民多,且单身男性比例非常高,也是造成赌博、吸食鸦片等不正当娱乐活动盛行的不可忽视因素。
因上海、天津等城市移民多,且单身男性比例非常高,也是造成赌博、吸食鸦片等不正当娱乐活动盛行的不可忽视因素。
读书看报既可以学习知识又能增长见识,还是知识分子的重要消遣方式。洋务运动期间一批洋务派官僚逐渐认识到学习西方文化、培养新式人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开设译书局,创建新式学堂,这些近代文化教育机构的设立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教育领域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教育消费模式的现代转型,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洋务,购买译著,阅读报纸。
图书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图书消费是发展性消费的重要内容。甲午战争前北京、上海等城市少数知识分子已开始购买西学类图书,以了解和学习西洋文化。西学图书消费需求的兴起,能从当时几个在中国影响比较大的翻译出版机构翻译、出版、销售图书的数量得到侧面验证。
江南制造总局在近代中国图书翻译出版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由其翻译和销售的图书种类和数量,能大体看出洋务运动期间西学图书的消费需求与供给情况。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自1868年开馆到1880年十多年间,翻译出版和销售的图书分为三类:一是已刊成并出售的图书,“已刊成书 98 种,共计 235 本,每本页数为 60 页至 100 页不等”,这些书至 1879年 6 月“计算所已销售之书有31111 种,共计 83454 本”;“已刻成地图与海道图,共 27 张,海道图大半为英国者,译出后俱在局中镌铜板印之,已销售者共4774 张”
 。二是已翻译完毕尚未刊印图书 45 种,约共成 124 本。三是未译全之书,共 13 种,内略有 34 本已译成
。二是已翻译完毕尚未刊印图书 45 种,约共成 124 本。三是未译全之书,共 13 种,内略有 34 本已译成
 。由上所述可看出,江南制造总局的图书销量已达一定规模,为适应业务扩大的需要,翻译等人员增加到 30 余人,“或刊板,或刷印,或装订,而一人董理,又一人董理售书之事,另有三四人抄写各书”
。由上所述可看出,江南制造总局的图书销量已达一定规模,为适应业务扩大的需要,翻译等人员增加到 30 余人,“或刊板,或刷印,或装订,而一人董理,又一人董理售书之事,另有三四人抄写各书”
 。江南制造总局译书局出版图书的消费对象是知识分子和教会、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校,“为官绅文士购存者多,又上海、厦门、烟台之公书院中亦各购存,如上海公书院,在格致书院内有华君若汀(即华蘅芳)居院教习,凡来咨取者,则为之讲译,而华君在局内时,与西人译书有十余种,故在院内甚能讲明格致”
。江南制造总局译书局出版图书的消费对象是知识分子和教会、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校,“为官绅文士购存者多,又上海、厦门、烟台之公书院中亦各购存,如上海公书院,在格致书院内有华君若汀(即华蘅芳)居院教习,凡来咨取者,则为之讲译,而华君在局内时,与西人译书有十余种,故在院内甚能讲明格致”
 。
。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通商口岸城市开设出版印刷机构,建立教会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和团体,如成立墨海书局、美华书馆、益智书社、同文书会、《申报》等出版机构,外国传教士等在中国创立出版印刷机构的动机是服务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西方列强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的思想观念,需从改变中国士大夫的思想入手,“士大夫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这就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
 ,而要改变士大夫群体的思想,就应以出版业为突破口。也因此,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创设了一批出版机构,如基督教在华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1887年成立时名为同文书会,1892年改名广学会,“意指广西国之学于中国”。广学会创办人韦廉臣在《同文书会发起书》中清楚表明了创办广学会的目的:“本会的目的归纳起来可有两条:一为供应比较高档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二为供应附有彩色图片的书籍给中国人家庭阅读”,“我们的目标是面向公众,包括知识界和商界,在我们向他们提供真科学的同时,要努力使之具有吸引力,以达到他们目前能够看得懂的程度”
,而要改变士大夫群体的思想,就应以出版业为突破口。也因此,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创设了一批出版机构,如基督教在华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1887年成立时名为同文书会,1892年改名广学会,“意指广西国之学于中国”。广学会创办人韦廉臣在《同文书会发起书》中清楚表明了创办广学会的目的:“本会的目的归纳起来可有两条:一为供应比较高档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二为供应附有彩色图片的书籍给中国人家庭阅读”,“我们的目标是面向公众,包括知识界和商界,在我们向他们提供真科学的同时,要努力使之具有吸引力,以达到他们目前能够看得懂的程度”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文化出版结构,除出版印刷宗教类图书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图书,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推广、销售,并取得显著成绩。如美华书馆 1893年设在上海北京路 18 号一家书店,“售出图书 159970册,各种小册子 237912 本”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文化出版结构,除出版印刷宗教类图书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图书,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推广、销售,并取得显著成绩。如美华书馆 1893年设在上海北京路 18 号一家书店,“售出图书 159970册,各种小册子 237912 本”
 。
。
格致书室是由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1885年在上海创办的,是当时中国唯一一家专门出售中文科技书刊的书店,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家科技专业书店,其中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所出的书籍占很大比重,即“夫格致书院本为英领事起手劝各埠西人捐设者,迄今书院大兴,皆赖徐君雪村之力办成”
 。到上海出差的知识分子一般都会去书店逛一逛。为扩展业务,格致书室还先后“在天津、汉口、汕头、北京、福州、香港、沈阳、烟台、厦门等城市设立分销处”,并开展免费代办邮购图书业务,1888年“通过个分销处所售出的图书达15 万册,书款达 17000 多银元”
。到上海出差的知识分子一般都会去书店逛一逛。为扩展业务,格致书室还先后“在天津、汉口、汕头、北京、福州、香港、沈阳、烟台、厦门等城市设立分销处”,并开展免费代办邮购图书业务,1888年“通过个分销处所售出的图书达15 万册,书款达 17000 多银元”
 。
。
这一时期西书最大的消费市场是上海、北京、广州等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城市。王廷鼎1878年途经上海,购买了“《谈天蠡测集》《海国图志》各书”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记录,光绪五年(1879)“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口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炫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书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记录,光绪五年(1879)“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口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炫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书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光绪九年(1883)康有为“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
。光绪九年(1883)康有为“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
 。光绪十年(1884)康有为“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
。光绪十年(1884)康有为“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
 。孙宝瑄在光绪二十年(1894)在北京购买《万国史记》(日本阿波冈本撰)等书。可见,洋务运动期间西学著作已影响到北京、广州、上海等地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但受阅读能力、消费能力等条件的约束,购西书者基本上为当时的文化精英。
。孙宝瑄在光绪二十年(1894)在北京购买《万国史记》(日本阿波冈本撰)等书。可见,洋务运动期间西学著作已影响到北京、广州、上海等地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但受阅读能力、消费能力等条件的约束,购西书者基本上为当时的文化精英。
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知识分子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有人时常购买报纸,如王锡麒 1879年 3 月到上海,“至新报馆,订《西国近事报》一分,《新报》一分,托荔泉按月汇寄”
 。
。
因报纸消费的增长,19 世纪 80年代后《申报》《万国公报》等报纸销量不断增加。由《申报》的销量也能从侧面看出新式报纸消费呈现增长趋势。1872年 4 月 3 日,美查出资白银 400 两,在上海创办了《申报》,初刊时仅售 600份,但很快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多家分销点,同年 6 月 28 日《申报》上刊登已在宁波、汉口、镇江、天津、苏州、杭州、湖州、嘉兴、盛泽、扬州、香港、广东、武昌、南京、北京等处设了分销点。1872年 9 月 9 日刊登的《本馆自叙》称,在上海已日销 3000 张,1877年《申报》每日销售量已达八九千份
 。该报自 1879年 11 月 29 日起,每期的第一版《报馆告白》都刊登各地销售点的详细地址,如 11 月 29 日有北京、天津、南京、武昌、汉口、扬州(共 3 处)、安庆、南昌、苏州、杭州、福州、宁波、香港、南宁、重庆、长沙等 16 个城市,合计销售点 18 处,并开展代为邮购业务,“其余外埠皆由各信局以及京报房代售”。《申报》立足市场需求,报道各种新闻事件,特别是及时报道一些公众所关心的突发事件、花边新闻,很受大众欢迎,销量迅速增加,1890年《申报》每天的销售量已达 2 万份
。该报自 1879年 11 月 29 日起,每期的第一版《报馆告白》都刊登各地销售点的详细地址,如 11 月 29 日有北京、天津、南京、武昌、汉口、扬州(共 3 处)、安庆、南昌、苏州、杭州、福州、宁波、香港、南宁、重庆、长沙等 16 个城市,合计销售点 18 处,并开展代为邮购业务,“其余外埠皆由各信局以及京报房代售”。《申报》立足市场需求,报道各种新闻事件,特别是及时报道一些公众所关心的突发事件、花边新闻,很受大众欢迎,销量迅速增加,1890年《申报》每天的销售量已达 2 万份
 。
。
通过上面考察能看出 1861—1894年我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的基本情况,为进一步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趋势,课题组选择当时中国南、北两个文化娱乐消费中心城市,即在上海和北京,分别选择典型样本进行深入解剖。
19 世纪 60年代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不断增加,从事洋务工作的官绅等关注西学者逐渐增多,知识分子群体等的文化教育观念也逐渐发生改变。1878年冬康有为到西樵山上的三湖书院求学,有幸认识了到三湖书院游玩的翰林院修编张延秋,这次会面是康有为一生的重大转折。在张延秋指导下康有为开始接触西学,“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深受启发,“于是舍弃考据扩帖之学,专心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
 ,从中也能看出居住在北京,任职翰林院编修的张延秋已经涉猎了不少西学著作。上海 19 世纪后期已发展成为我国的工商业、文化教育、文化娱乐等中心。因此,选择在北京、上海两个城市选择典型城市深入剖析这一时期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变迁趋势。
,从中也能看出居住在北京,任职翰林院编修的张延秋已经涉猎了不少西学著作。上海 19 世纪后期已发展成为我国的工商业、文化教育、文化娱乐等中心。因此,选择在北京、上海两个城市选择典型城市深入剖析这一时期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变迁趋势。
课题组选择冯芳缉、姚觐元、王锡麒、何荫柟等日记中与文化娱乐相关资料绘制表格(如表 1-4 所示),来进一步考察 19 世纪 60 至 80年代上海居民的文化娱乐消费的基本特征和变化的基本趋势。冯芳缉,同治戊辰进士,晚清时期思想家冯桂芬的长子。王锡麒(1855—1913),辑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光绪五年(1879)应顺天试北上赶考,途经上海,他日记中有不少在上海期间游乐记录。姚觐元,光绪初年曾任广东布政史,《弓斋日记》内记载他1879—1884年途经上海的见闻和游览记录。《绛芸馆日记》的著者情况不详,由日记能推断出,日记的主人消费能力很强,至少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何荫柟,著有《鉏月馆日记》,由日记能推断出其收入也应在中等以上。
表 1-4 1861—1886年上海文化娱乐消费情况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285-352 页整理。
由表 1-4 能看出 19 世纪 60 至 80年代上海居民的娱乐消费具有以下几点新变化:
一是中西文化娱乐消费方式并存。《绛芸馆日记》的著者不详,但可以看出他和朋友们的娱乐活动不仅有戏园观剧、茶馆品茗、书场听书等本土娱乐活动形式,而且出现了外国娱乐活动,如看东洋女子足技、西国术师演魔术、西人赛马、东洋茶室茗茶等。冯芳缉、姚觐元、王锡麒、何荫柟 4 人及其朋友们的娱乐消费中,也出现西式娱乐消费活动。但总体上他们五人的娱乐消费构成中,传统娱乐活动形式仍占主导地位,以戏园看戏、书场听书为基本娱乐形式。据不完全统计《绛芸馆日记》的著者到戏园看戏 71 次,其中到丹桂园看戏 27 次,金桂轩看戏 7 次,大观园看戏 9 次,天仙园 6 次,其他 22 次。到恒吉昌、畅福园、攀桂轩等听说书 15 次。
二是娱乐消费日常化。从上述冯芳缉、姚觐元、王锡麒、何荫柟等人的娱乐消费能看出,日常化特征显著。《绛芸馆日记》作者不详,他基本上每个月都到戏园看一两次戏或到书场听说书一两次,正月期间观剧、听书次数尤多,如1879年正月看了 8 次戏,即初二大观园、初三丹桂园、初四金桂轩、初五大观园、初七天仙园、十三日大观园、十四日大观园、十八日丹桂园看戏。再如他1876年正月初四鹤鸣园看戏。十八日游豫园看兰花会。十九日湖心亭茶叙,茶罢至大马路看西人赛马。姚觐元、王锡麒、何荫柟等人在上海时间较短,但是日常化特征也很明显,王锡麒 1879年 3 月 20 日到上海,然后基本上天天出入娱乐场所,即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观剧,二十三日游徐家汇。闰三月:初四游外国花园。初六游洋泾浜。初八观剧。十一日浦东观跑马(即赛马活动)。观赛马毕,天仙园观剧。十二日又到虹口畅游。
三是娱乐消费主体平民化。上海的娱乐消费主体不再局限于纨绔子弟、来往商旅、士绅等小众,而朝大众化、平民化方向发展。冯芳缉、姚觐元、王锡麒、何荫柟等人在日记中都提到丹桂园、愚园等娱乐场所游客众多。
四是文化娱乐产品种类增多。王锡麒在上海游乐后在日记写道:“宝善街一带车声隆然,往来雷动,泰西十七国货物,麕集鳞聚,惊心眩目,应接不暇。晚则煤气灯千百万盏,如列星……花月胜场,所在皆有,妖姬艳服,巧笑工颦”,他还对上海商业的繁盛、娱乐产品和服务的优良所折服,在启程返乡前到三雅园观剧,“色色俱佳,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感叹到“吾欲腰缠十万贯,于此筑销金窝!”

五是酒楼、饭店成为娱乐中心。浦五芳、金谷园、复兴园等当时上海著名的酒楼、一品香等西餐馆是姚觐元、王锡麒、何荫柟、冯芳缉等人及其朋友们消遣娱乐的重要场所。由表 1-4 能看出当时上海中上流社会为了加强朋友间的情感,经常相互邀约于酒楼、戏园;或者是中午宴饮,下午到张园游园或到戏园看戏,即“社交+宴会+娱乐”消费一体化发展趋势已经彰显。
孙宝瑄(1874—1924),浙江钱塘人,父诒经,官至光绪朝户部左侍郎,兄宝琦晚清时曾担任驻法、德公使暨顺天府尹等官,入民国后一度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岳父李瀚章,即李鸿章之兄,官至两广总督。孙宝瑄以荫生得分部主事,历工部、邮传部及大理院等职。传世的《忘山庐日记》中 1893年、1894年的日记大致能体现甲午战争前以孙宝瑄为代表的北京封建社会上层知识分子的文化娱乐消费的概况。
表 1-5 1893—1894年孙宝瑄在北京的休闲娱乐活动

资料来源:根据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64 页整理。
由表 1-5 能看出甲午中日战争前以孙宝瑄为代表的北京封建社会上层知识分子的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具有以下几点共同特征:
一是娱乐消费日常化。孙宝瑄和朋友们的娱乐活动日常化特征显著,他们有钱且闲暇时间较多,娱乐消费是他们日常消费的重要内容。
二是娱乐消费功能多元化。传统娱乐功能主要是娱乐神明和祖先,但这一时期娱乐消费功能中休闲娱乐和社交功能显著,茶馆品茗、戏园看戏有时是为消遣时间;有时也为庆贺生日等,如为庆祝母亲生日,“作傀儡戏”。他的朋友们为长辈祝寿也主要采取演戏酬宾,如 1894年 2 月“至全浙馆,林莲孙寿其母,称觞演剧,宾友杂沓”。
三是娱乐消费支出较大。孙宝瑄和朋友们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包括戏园、茶楼、酒楼、会馆等。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上海、北京等城市的会馆也是来往商旅、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孙宝瑄 1893年、1894年经常到全浙馆、湖广馆观剧。
四是观看戏剧表演为基本娱乐消费方式。孙宝瑄经常与亲朋好友到戏园看戏,他还在日记中说“余素性好丝竹,虽非知音,而听之忘倦,最喜徽曲,尤爱老生”
 。
。
此外,其他通商口岸城市娱乐消费需求也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变化。如宁波 1844年 1 月正式开埠通商,1850年在江北岸划出一片土地作为外国人在宁波的居留地,19 世纪 60年代太平军攻打宁波时,外国人居留地已非常繁华,有人描述:“在太平天国的革命尚处在高涨时期,浙东一带的富商巨室,纷纷迁入江北岸租界避居。一时洋场风气大盛,酒馆遍街。洋行林立。在桃渡路,有妓院、戏院和专供外人玩乐的弹子房。在中马路,则有专售外文书报及供外人吃喝的‘葆三’、‘美颐’商店;‘美颐’楼上还有总会,即赌场。‘蓬莱春’、‘渡江春’两家则是西菜馆,真是车水马龙,灯红酒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