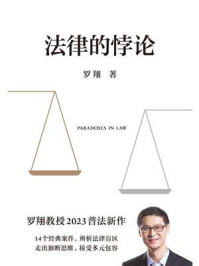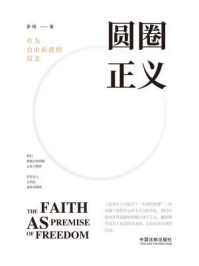2008年,一例裸聊案引起广泛争议,该案甚至被列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论述题。因在网络上裸聊,女子方某被某县法院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
方某三十多岁,失业在家,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尝试收费裸聊。法院审理查明,从2006年11月到2007年5月案发,方某的裸聊“生意”遍及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仅在电脑上查获聊天记录的就涉及300多名“观众”,网上银行汇款记录达千余次,计2.4万元。最后有一名“观众”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看了方某的裸聊,向公安机关举报。
方某裸聊的行为如何定性,究竟以何种罪名起诉,司法机关内部有多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第二种意见认为构成聚众淫乱罪;第三种意见认为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最后一种意见认为这纯属个人行为,没必要以犯罪论处,实在不妥,给予行政处罚即可。

法院的最终定罪受到了很多指责,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有人认为“传播”必须是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扩散,而方某的裸聊是一对一的,具有特定性,不属“传播”。
这里值得思考一下:如果一对一的传播属于刑法上的“传播”,涉及面是不是太广了?甚至丈夫给妻子发的视频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另外还需要思考:同步传输的视频图像既非视频文件,又非图片文件,这个能算是“物品”吗?
另外一个案件和老赖有关,王某欠债不还,被告上法院。法院对原被告进行了调解,王某同意还钱,所以法院出具了调解书。但不料王某老赖成性,拒不履行法院的调解书。王某后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被抓,一审判决王某罪名成立。王某提出上诉,二审推翻了一审判决,认为王某无罪。理由是王某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前提不存在。王某拒不执行的是调解书,而不是判决书,也不是裁定书。不要说一般人,估计很多法律人也区分不出这三种文书的区别。
被抓,一审判决王某罪名成立。王某提出上诉,二审推翻了一审判决,认为王某无罪。理由是王某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前提不存在。王某拒不执行的是调解书,而不是判决书,也不是裁定书。不要说一般人,估计很多法律人也区分不出这三种文书的区别。
表3:调解书、判决书、裁定书的区别

通俗来说,民事调解书是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所达成的协议,法官只是起到中间调和作用,不参与法律评价。但是判决、裁定(涉及实体)都会体现法官对当事人纠纷的评判。
虽然调解书生效后与判决书享有同等的执行力,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调解书。但是刑法第313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所只限于判决和裁定,不包括调解书,所以二审法院认为王某不构成犯罪。

看到这些案件,大家是不是有点迷茫了,觉得定个罪怎么那么麻烦。裸聊道德吗?老赖难道不应该打击吗?还考虑那么多干吗?随便安个罪名制裁不就得了吗?法律人为什么总站在犯罪人的立场上说话,难道不应该替被害人多考虑考虑吗?刑法的规定怎么老是保护犯罪人?立场到哪里去了?
的确,如果只是强调惩罚犯罪,成文刑法的出现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完全束缚了国家打击犯罪的手脚。如果没有刑法的约束,裸聊、赖账……一切令人不爽的行为都可以进行打击。古人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如果刑法的根本目的只在于打击犯罪,那么刑法就没有出现的必要,它只需存在于执法者内心深处,秘而不宣的刑法较之公开明示的法律更能打击一切所谓的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就像身上被装了个摄像头一样,干啥都不自在,干啥都觉得有双眼睛看着你——小心,你小子构成犯罪了。这样的后果就是啥也不敢干,啥也不想干,干啥都有罪,不干也可能犯罪。惶惶不可终日,罪与非罪,完全靠命。
岳飞之死让大家知道了“莫须有”这个罪名。犯罪可怕,还是不受约束的刑罚权更可怕呢?另一个例子是袁崇焕之死。袁崇焕被诬通敌,被判凌迟处死,可悲的是北京城中的百姓不明真相,对皇帝的说词信以为真,恨袁崇焕入骨,行刑之日,纷纷出钱买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吃,还边骂袁崇焕这个“叛徒”。袁崇焕临刑前口占一绝:“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相传他的部下“夜窃督师尸”,葬在北京崇文门的一个菜园子中。后代世代在此守墓。后来这成为一个公园,叫做龙潭公园,以前我经常在那散步遛弯。
相传他的部下“夜窃督师尸”,葬在北京崇文门的一个菜园子中。后代世代在此守墓。后来这成为一个公园,叫做龙潭公园,以前我经常在那散步遛弯。
如果刑罚权不受法律约束,恶劣的案件可能层出不穷。20世纪60年代,某地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巴某接到地委组织部电话通知,要他立即到地委报到,重新安排工作。次日巴某在路边等车,以为会有专车来接。正好两名警察押着犯人上了一辆卡车,所以巴某也上了卡车。当车在某地公安局停车,巴某下车准备走到地委组织部,结果警察把他关到了看守所,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就可以把一个无辜的人,甚至还是领导干部就关了起来。巴某一直喊冤,但一直没人理睬,这一关就是十六年。

看完这些案件,你还会觉得定罪不用多考虑考虑吗?
法律人其实非常不讨人喜欢,因为民众狂热时,他会强调冷静,人皆曰可杀,我意独怜之;权力高歌猛进时,他会强调限权,希望踩一踩刹车。有时法律人的观点不被人理解,可能只能用颜回对孔子的答问来进行安慰——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